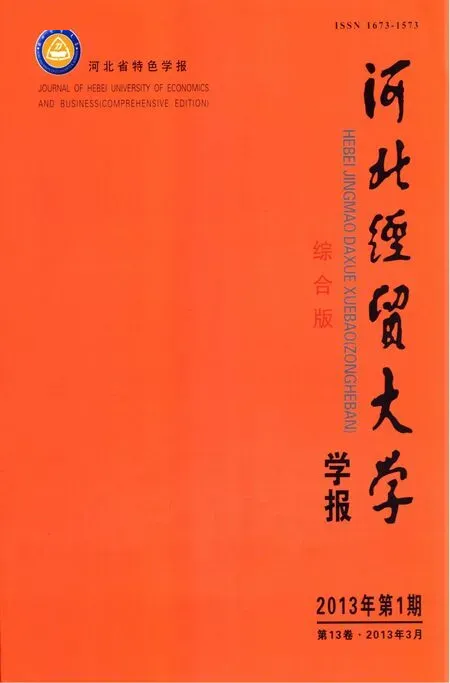单向的阅读与影响的焦虑
2013-04-06汤天勇
汤天勇
(黄冈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1996年重读鲁迅,余华顿然发现:鲁迅是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最简洁、最有学问的作家之一,置于卡夫卡、博尔赫斯与马尔克斯之间毫不逊色。其实,做余华与鲁迅的比较研究,在学界亦是个充满活力的课题:一是鲁迅与余华分别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创作高度;二是同为浙江籍作家,有着共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三是都有弃医从文的经历,从医的实践对文学创作或多或少有着影响;四是都是“拿来主义”的实践者,自觉地向西方作家学习写作技巧;五是两人有着相近的创作主题,无论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还是对现实的针砭。余华也承认,阅读别人的作品会影响自己。既便如此,余华仍然认为鲁迅的作品对其没有构成实质性影响,只会在情感和思想上支持他之后的写作。
一
1996年后余华在多个场合谈及过鲁迅的作品:或是正面谈到,如《狂人日记》《孔乙己》《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风波》及《故事新编》;或是浮光掠影,如《呐喊·自序》《娜拉走后怎样》。至于国内外公认的小说代表作《阿Q正传》却没有提及。吊诡的是,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余华笔下的人物“福贵”“许三观”与阿Q精神上的承继和变异。
《孔乙己》被余华推崇为世界短篇小说的典范,与《青鱼》(杜克司奈斯)、《在流放地》(卡夫卡)、《伊豆的歌女》(川端康成)、《南方》(博尔赫斯)、《傻瓜吉姆佩尔》(辛格)、《礼拜二午睡时刻》(马尔克斯)、《河的第三条岸》(罗萨)、《海上扁舟》(史蒂芬·克莱恩)、《鸟》(布鲁诺·舒尔茨)一并影响着他的创作。余华认为小说集中体现了鲁迅思维的迅捷与直抵现实的迅猛。思维与表达的媒介是语言,语言的简洁有助于表达效果的显现。小说的开头寥寥数语,就把孔乙己的特性与命运纤毫毕现。余华觉得小说的结尾写出了作家的责任感,一句话就把孔乙己“腿断”的悲惨现状表述清楚,干净利索。写作到了关键的地方,不是绕开,而是迎面冲上去,体现了鲁迅作为一个大作家对细部的洞察力和表现力。因为鲁迅的“语言像核能一样,体积很小,可是能量无穷。”[1](P39)他能“用非常简洁的语言来描述孔乙己的一生,那几乎是一种散文的笔调,但细节并不因语言的简练而丧失,相反,它很丰富、很饱满。”[2](P23)余华主要关注《孔乙己》的技巧层面,如开头与结尾的巧妙,语言简洁有力以及细部描写的丰富。
至于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出彩之处,余华捻出“举重若轻”四个字来概括,并认为这是鲁迅一以贯之的写作风格。他说鲁迅的语言“立即展现出人物的精神状态,像子弹穿透身体,而不是留在身体内,语言之锋利,真令人折服。”[2](P22-23)余华的阐释主要侧重两个方面,一是“举重若轻”的修辞策略,在情节趋向高潮之时,在情绪趋向激烈之时,不是继续推波助澜,反而冷淡处理,意在风轻云淡之处见出人物的真心理。二是鲁迅的语言富有力量,一针见血,能够直逼人的心灵与情感深处。
在余华看来,有些长篇巨制是正面面对(或描述)时代的写作,而鲁迅的《风波》以短篇反映时代特征。余华对这篇作品是有诸多保留的,只是觉得这篇作品也很好,但还没达到令他砰然心动的地步。小说的最经典部分是赵七爷的出场,“赵七爷的一条辫子,活灵活现地展示了时代的变革和那时时代特有的气象;赵七爷的一条辫子,也生生道出了所有小人物的无奈:变革是上头的事情,小人物没有自主的权利,一个不小心还要人头落地,只能取中庸之道,明哲保身。其实在现实社会,我们很多人依然是‘赵七爷’,或多或少有赵七爷的因子。”[2](24)赵七爷的辫子盘上与放下跟皇帝坐龙庭密切相关,虽然有些功利或者说油滑,却是在没有个人空间的社会生活中生存的唯一选择,是面对社会动荡的微弱反应。
对于《故事新编》中处理历史题材的方式,余华是认同的,“我喜欢鲁迅用‘邪’的方式来描写历史。他总是找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人物,如老子、墨子之类的先圣哲人,调侃一番,却又点出了他们的精髓。”[2](P24)鲁迅不正面述史记人,就思维进路而言,与余华不走常规路,反而以暴力接近人类与人性真实本相及戏说历史、爱情是一致的。但他没有逐篇评述,仅仅例举《非攻》将墨子写得活灵活现。但是,从其拿鲁迅与茨威格写史手法的比较来看,显然他更欣赏茨威格“写一个点”的方法,他比鲁迅的写法更有爆发力,更具想象力和洞察力。
“鲁迅作品有力的另一方面,就想应该是鲁迅的宽广,像他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在写百草园时的叙述是那么的明媚、欢乐和充满了童年的调皮,然后进入了三味书屋,环境变得阴森起来,孩子似乎被控制了,可是鲁迅仍然写出了童年的乐趣,只是这样的乐趣是在被压迫中不断渗透出来,就像石头下面的青草依然充满了生长的欲望一样。这就是鲁迅的宽广,他没有将三味书屋和百草园对立起来,因为鲁迅要写的不是百草园,也不是三味书屋,而是童年,真正的童年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这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家。”[1](P39)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环境发生变化,心情、心态也随之一变。余华欣赏的是鲁迅没有把三味书屋与百草园写成恐怖的地方,写成一个喻示封建礼教的场所,而是有快乐有百感交集的丰富。作家欲解决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不是剑拔弩张,而是“向人们展示的应该是高尚。这里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无论是美好的还是丑陋的,作家都应该一视同仁,作家应该满怀同情和怜悯之心,只有这样,作家的作品才能出现回声。”[3]
二
由余华对鲁迅的解读可知,他较多关注文学的创作技巧,比较集中在语言的简洁性和力量性、细节描写的洞察力上。相反,对于鲁迅文学创作的精神实质、写作目的与文体创新等鲜有涉及。显然,这些信息不足于证明鲁迅是20世纪中国甚至是世界上伟大的作家。换言之,无论作为先锋派代表作家,还是对现实的“正面强攻”,余华内心与鲁迅尚未靠近,余华所说的灵魂的交流也仅为理想状态。这又是为何呢?
第一,余华的创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国人在经历知识断奶后,对知识的渴求空前迫切。与传统断裂多年,再加上国家积贫累弱淤积成集体的不自信,让国人转向西方求知,寻求欧风美雨的滋润,希冀短时间内与世界同步。小说家也不例外,不是把目光回溯到孔子、庄子、司马迁、曹雪芹和鲁迅,而是在阅读西方作家作品时进行技术补课和引渡观念。先锋派作家马原说过:“根据我的观察显示的结果,作家这个行当的主要经验并非来源于直接经历(经验),间接经验占了他全部经验的大部分,也就是说,经验积累最丰富的作家往往是那些终生都在阅读的人,而不是那些终生都在奔波的人。”[4]余华不懂外语,他汲取写作养分只能依托翻译作品。所以,写作技巧的援引相对于文化观念、哲学思想的接受容易多了:
“……最后我选择了外国文学。我的选择是一位作家的选择,或者说是为了写作的选择,而不是生活态度和人生感受的选择。因为只有在外国文学里,我才真正了解写作的技巧,然后通过自己的写作去认识文学有着多么丰富的表达,去认识文学的美妙和乐趣,虽然它们反过来也影响了我的生活态度和人生感受,然而始终不是根本的和决定性的。因此,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一直以中国的方式成长和思考,而且在今后的岁月里我也将一如既往;然而作为一位中国作家,我却有幸让外国文学抚养成人。”[5]
余华在当代作家中,可以说是最善于移植的作家。他每一次转型,或者说写作困境出现后的突围,皆伴随着他喜欢的作家的影响。伊始,可能一个作家对其影响的痕迹比较明显,比如川端康成教会他细部描写,卡夫卡解放了他的思想等。随着阅读与接受视域的拓展,单个作家影响逐渐被众多作家的影响合力所取代。接受影响的结果,必然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到西方作家技术至上的认识中,并内化为考量文学优劣的心理图式。在作家没有哲学思想作为作品的内在支撑时,形式创新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一个作家,是否能够叙述这很重要,作家就像木工,手艺很重要。”[6]余华等以“手艺”为标杆衡量中国文学和作家时,技术的巧与拙也就关涉着作家优秀与否。鲁迅不仅是文学家,还是思想家。余华恰恰并非以思想见长,而以小说的技术试验终得擅场。所以,余华阐释鲁迅侧重于形式技巧,似乎也就无可厚非。
第二,余华与鲁迅都曾弃医从文,却有着不同的创作诉求。鲁迅为何做起小说,他是以小说为启蒙的工具:“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7]鲁迅写作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并非出于对文学的痴好,而是为了医治国民麻木愚昧的灵魂,拯救濒危的国家与民族。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能把救赎思想有机地融进文学中,虽然做的是遵命文学,丝毫不损小说的艺术性与审美性。余华弃医从文的目的很直接,用他的话说就是厌倦了牙医单调的工作以及医院规规矩矩的作息制度,向往的是文化馆那种自由潇洒的生活方式。虽然有评论家揭橥余华作品与鲁迅作品在创作母题、精神渊源上的接近性,但并不能佐证鲁迅对余华有多深影响;即使有影响,之于余华而言,亦非有意识地接受。因为:一方面,余华与鲁迅毕竟背负着共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同一文化影响下作家创作,如果说有相似的价值评判和精神向度也说得过去。另一方面,大凡优秀作家,其创作主旨和精神指向应该具有普世性和人类性。倘若藉此为证,不免有过度诠释之嫌疑。余华以暴力和苦难为书写主题,并非是一种深度写作的探询,而是寻求突围主流创作模式的一种有意而为之的写作策略。所以,余华并没有反思暴力背后的社会与文化根源,也没有为处在苦难境遇的人们以反抗的姿态和转身的希望,更多的是认同人性恶与苦难人生的合理性。此种写作说到底是现实的一元性展示,且是混淆了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对立的展示。正如余华所说:“一个作家总是要表达他的理解,过去我的理想是给世界一拳,其实世界那么大,我那么小,击出去就像打在空气上,有屁用,现在……世界在我心目中变得美好起来了。”[8]而鲁迅首先是一位启蒙者,其次才是一位作家。他写人性阴暗险恶,写现实人生悲惨,但更多希冀给人们希望,不致于完全沉沦在苦难之中难以自拔。知识分子的感时忧国,让鲁迅的启蒙有些苍凉和无奈:“我所说的话,常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始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至于‘还要反抗’,倒是真的,……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9]余华说他是为了接近真实才从事写作,而这个真实,对他而言即为“内心的真实”。余华与鲁迅“内心的真实”相同,都是对人类的现在与未来始终怀疑,失去希望。不同的是,余华认可了现实的黑暗与未来的不可捉摸,存在即合理;鲁迅面对现实的黑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希望的盾,抗拒着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10]“道”不同,难以为谋。写作意图的不同,自然会影响到余华对鲁迅的认同度。
第三,两个鲁迅,两种阅读。环绕在鲁迅周围的多声部是中国现当代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余华阅读鲁迅,自始至终无法置身于风景之外。所以,笔者大胆地认为余华阅读的鲁迅有着双重身份,即观念悬置的鲁迅和真实本色鲁迅。观念下的鲁迅,之于余华包含着以下几层意思:一是中小学期间认识的鲁迅。余华那一代人中小学是学习过大量的鲁迅作品的,有古体诗,有散文,有小说,也有杂文。余华说,那个时候的他读鲁迅的书就是娱乐,而非接受精神熏染与思想的传递。再加上余华未有社会经历和生活体验,小说的晦涩、文白夹杂,一般而言是读不懂的。再加上诗歌和杂文的沉闷,在余华意识中,鲁迅是位被时代夸大了的作家,是位仅仅比郁达夫好一点点的作家。二是意识形态化的鲁迅。建国后,鲁迅因有领袖钦定的身份——思想家、革命家与文学家——已成世人顶礼膜拜的偶像(无论态度诚挚与否),被树立成国民的精神向导。意识形态化的鲁迅声誉日隆,在“文革”期间成为惟一可以阅读的作家。这个时期的阅读,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意识下的阅读,鲁迅也成为政治文化的符号。“就像我小时候的‘鲁迅’。我所说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鲁迅’。那时的鲁迅不再是一个作家的名字,而是一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词汇,一个包含了政治和革命内容的重要词汇。”[11]“词汇”时期的鲁迅,不是作品建构的作家实体,而是环绕在意识形态的周围,成为诠释某种革命理念静止的符号,容不得质疑,容不得个人性的阐释。三是非议中的鲁迅。“文革”结束以后,鲁迅刚走下圣坛,又被置于争议之地,各种非议与否定接踵而至。不仅鲁迅作为文化偶像与精神导师的地位不断受到冲击,而且鲁迅的小说创作也不断被人质疑。①这些非议和否定,不可能不影响到余华的判断,当时,有人将其与鲁迅联系起来,他深不以为然。质言之,悬置在鲁迅身上的观念,必然会影响到鲁迅回归自身的时限与纯度,也会影响世人对鲁迅的了解。对于余华而言,自出生到写作定型,绝大部分时间接受的都是观念悬置的鲁迅。阅读的既定思维以及西方写作技术的快捷移植,一定程度上销蚀了对真实鲁迅精心审视的可能。
总观余华解读鲁迅的作品,笔者认为,余华与鲁迅的距离是小说家与文学家、思想家的距离。他对鲁迅热烈称颂,我愿意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或许是对采访者、研究者孳孳不息探赜二人之间关联的回应,抑或是缓解西化影响的焦虑。余华过于迷恋西方著名作家的创作技巧,写作的技术性僭越了思想性、精神性的进入。尤其是,余华始终回避与现实的深度对话,其写作不仅自我缺席,也容易陷入观念写作的囹圄。纵然他一再声明,文化根源于中国实践证明,余华回归现实与本土的创作,往往有些力不从心,以至于被批评家发现其写作有重复性现象,《兄弟》大肆渲染着市井作坊里的灰色噱头。看来,如何突围,如何正视自我哲学底蕴与人生体验的不足,对于余华而言,显得比写作技巧囤积尤为重要。
注释:
①新时期以降,非议、质疑鲁迅的代表作有李不识《何必言必称鲁迅》(《杂文报》1985年8月6日)、邢孔荣《论鲁迅的创作生涯》(《青海湖》1985年8月号)、朱文等《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北京文学》1998年10月号)、葛红兵《为二十世纪文学写一份悼词》(《芙蓉》1999年第6期)、王朔《我看鲁迅》(《收获》2000年第2期)、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收获》2000年第 2期)等。
[1]叶立文,余华.访谈:叙述的力量——余华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2,(4).
[2]余华.三十岁后读鲁迅[J].青年作家,2007,(1).
[3]余华.作家与现实[J].作家,1997,(7):7.
[4]马原.作家与书或我的书目[J].外国文学评论,1991,(1):112.
[5]余华.自述[J].小说评论,2002,(4):22-23.
[6]余华,李哲峰,余华访谈录[J].博览群书,1997,(2):46.
[7]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鲁迅全集(第 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6.
[8]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4.
[9]鲁迅.两地书·二四[M].鲁迅全集(第 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80-81.
[10]鲁迅.野草·希望[M].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81.
[11]余华.易卜生与鲁迅[J].读者,2011,(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