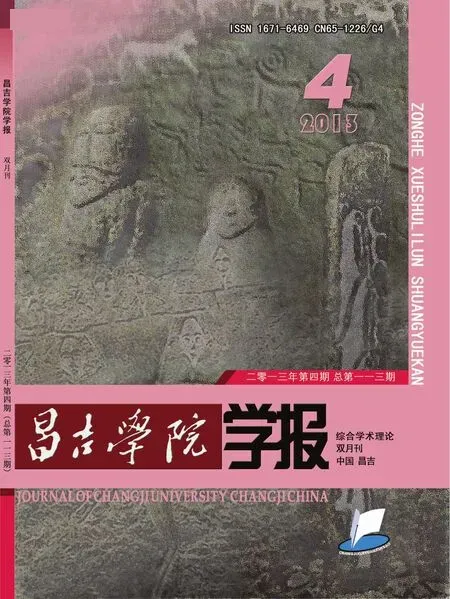试论习惯环保法
2013-04-02梅长胜
梅长胜
(中共马鞍山市委党校 安徽 马鞍山 243011)
试论习惯环保法
梅长胜
(中共马鞍山市委党校 安徽 马鞍山 243011)
习惯环保法作为习惯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和习惯法相同的特性。习惯环保法在一个社会共同体内,具有一定的确定性、统一性和权威性。习惯环保法多数扎根于少数民族地区,它是有其特殊的环境或生活习惯所引起的。本文的重点主要在于阐述习惯环保法产生的民族渊源、社会学基础及对其今后的引导方向。本文认为,习惯环保法的变迁决定于当地族群文化的变迁,而后者又决定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因而,习惯环保法的变迁最终取决于经济的变迁。
习惯法;神话传说;宗教信仰;民族禁忌;乡规民约
一、习惯环保法的概念
如前所述,“习惯环保法”属于“习惯法”之一部分,或者说,它是后者的一个下位概念或子概念。而众所周知,后者作为一个专门法律术语,源自西方的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在英美法系,习惯法是当事人解纷和法院裁判的当然法源;在大陆法系,习惯法(有时称习惯)也是各国成文法认可的重要法源。在百余年的西法东渐之际,国人将“习惯法”(连同“惯例”)连同大陆法系的法制一起引入中国。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官方就在旨在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民族大调查中正式使用该术语。对于该术语的定义,当下中国学界有不同见解。从经验主义的视角看,笔者认为习惯法是在特定区域、特定族群中自发生成的、规定或包含了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调整他们之间的行为和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的行为规则。在总体上,它是一套地方性的、由特定族群所拥有的知识体系。从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视角看,习惯法(连同习惯环保法)构成了特定族群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特别是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几种对习惯法不同观点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习惯环保法是指在特定区域内自发生成的、由特定族群自觉遵守的、规范他们之间的环境保护行为、调解和解决他们之间的环境利益冲突的行为准则,包括禁忌、碑文、规约等社会规范的总和。习惯环保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一种调节手段和机制,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地区有效地调整和规范人们的生活和行为,在个别地区甚至还替代法律发挥它特有的功能,扮演着法律的角色。同时对当地的环境保护和自然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此外也为传统保护与当代环境理念的接轨提供了一些经验和建议,所以研究它将有重要意义。
在查阅了大量相关文献资料后,笔者发现目前国内很少有介绍习惯环保法的专著,而且,就是其中谈到习惯环保法的内容的著作也很少。在国内,大部分学者只在习惯法的研究中(特别是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研究)稍涉及到一些关于生态保护方面的习惯法,如高其才在其著作:《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一书中,在财产习惯法中谈到了约定俗成的林木保护习惯方面。又如寸瑞红的《高黎贡山傈僳族传统森林资源管理初步研究》一文,杨士宏的《藏区习惯法的文化内涵》一文等等,其所涉及到的民族习惯环保法大都零星而不全面。只有很少部分人对少数民族的林木管理作了初步研究,如董浩的《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的保护》一文,该文通过作者亲身调研初步了解了云南少数民族的生态环
境观。又如宝贵贞的《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观探源》一文,明东、绍梅的《云南彝族水利山林习惯法及其功能》一文等。但这些文章只是将研究范围局限于某一个少数民族或某一地区的少数民族,算不上真正从理论上对习惯环保法进行深入地、全方位地研究。
二、习惯环保法的渊源
在笔者看来,“法的渊源”其实是一种法律隐喻,即将法比喻为像水流那样的事物,有一个来源或终极的起点。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它是人们追问法这个事物“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一种惯性思维所引发的理论问题。从文化的角度看,人们有关“法的渊源”的看法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个体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影响。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民族地区,习惯法文化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内容。相应地,习惯环保法文化也是如此。它在民族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和法律规范等各个方面都留下了深厚的痕迹。
当然,从理论的角度看,汉族地区也存在习惯法及其习惯环保法,但很显然,由于受到国家法的长期的、深入的影响,其浓烈程度不及相对保持自治状态的民族地区。故我们在此主要对民族地区的习惯环保法进行考察,这样更能反映习惯环保法的典型特征。下面笔者重点来讨论一下民族地区习惯环保法的渊源。
在大量史料证明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神话传说、宗教信仰、民族禁忌、乡规民约是民族地区民族习惯环保法的重要渊源。
(一)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是世界上所有民族早期生活的重要组织部分,中华民族亦不例外。从文化的角度看,它也是世界上所有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我国民族地区表现得特别突出。在我国民族地区,神话传说丰富而多彩,既表现了他们丰富的想象力,也表现了他们征服和利用自然,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望。例如彝族人认为,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山川、水火以及一树一石、一鸟一兽都由神灵主宰,这些自然现象既可造福于人类,又可为害于人类。为了祈福避灾,自然也是人们崇拜的对象。[1]据汉文史志道光《云南通志》说:“民间皆有祭天,为台三阶以祷”。《大理府志》也记载:“腊则宰猪,登山顶以祭天神”。土地是人们的衣食之源,而在彝人看来土地是由土神、田公、地母、田祖掌管的。贵州彝文典籍《献酒经》就有向天神、地神、树神、石神、水神、光神、雾神等十三种神灵献酒祈求风调雨顺、丰衣足食的记载;凉山的《毕摩献祖经》记述了对雕、鹞、水、森林、江河、野草、岩石诸神的崇拜,各少数民族还保留着许多自然崇拜的活动和仪式,如彝族的地神崇拜。云南巍山彝族每逢农历正月初一祭地神,祭法是以一树代表地神、彝语称“米司”,敬献以鸡血和鸡毛,祈求地神保佑五谷丰登。昆明西山彝族逢农历二月插秧时祭田神。届时,携腊肉、猪心、酒,饭等祭品,对秧田分焚香祈祷,撒祭品至田中保佑秧苗出得齐,长得壮。基诺族维护生态环境的方法,是令人所难以想象的。口头神话传说是基诺族保护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在手臂疼痛时就会照传说的方法用饭祭大青树鬼,眼痛时用米和水祭空心树中的水洼鬼,胸背痛时要祭塌方鬼,腰腿痛时要祭森林中的水潭鬼。祭前需经巫师占卜,一旦确定是上述哪种鬼作祟,人们就认为当时人的病因在于得罪了某一种鬼就要按照传统方法去祭祀。傈僳族砍树前要献山神,以防树砍倒了会打着自己,砍土地时不砍大树,否则大树神会怪罪。这也是信奉神话传说的表现。在无形中保护了环境。[2]
(二)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跟“神话传说”一样,也是世界上所有民族早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亦不例外。但与后者不同,宗教信仰还与传统哲学相结合,体面地进入了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之中。经验观察表明,在宗教信仰中存在大量的、有关当地族群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的观念和规则。例如,我国东北地区的萨满教中,存在为数不少的习惯环保法。从内容上看,主要有“观念层面的环保法”与“行为层面的环保法”,有“环保预防法”与“环保惩治法”。这些习惯环保法形态大都体现在该民族的宗教禁忌之中。例如,禁止砍伐森林的“树神禁忌”,禁止污染河流的“水神禁忌”,禁止猎杀动物的“图腾禁忌”。又如在那些信奉佛教的民族地区,佛教教义中就潜藏了大量的有关环境保护的观念和规则。而且与国家
法层面的环保法不同,这些佛教中的习惯环保法首先是从观念或精神层面,然后才是从行为层面规范着信众的日常行动,因而其内在的强制力更甚于国家环保法。例如,在西北高原,藏民族的原始宗教(苯教)中即已蕴含丰富的习惯环保法,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以实现人神(即“自然”)和谐为目的的“神山禁忌”,其早期源头可追溯至伟大的松赞干布。在历史上,松赞干布鉴于黄河、白河源头水土流失严重,林毁土坏,便引入佛教力量治理当地环境。由此,他确立了泽被后世的佛教“神山”和“公林”制度,前者为佛主所有,当地寺院管理;后者为部落共有,头人共同管理。由于松赞干布在藏民族历史上的崇高地位,他的上述规定也就神化、佛化,为后世的藏族人民所自觉信守。今天藏区的森林、野生动物之所以被较好地得到保护,松赞干布功莫大焉。在西南丛林中,云南的傣族和相邻民族也信奉佛教(具体是南传上座部佛教)。他们生活在丛林之中,对于自然环境的依赖度非常强。而佛教的教义刚好强调众生平等、珍爱生命、人与自然的和谐等,此种教义客观上非常有利于保护当地的各种动植物资源。今天我们仍可发现,西双版纳的植物与佛教的活动密切相关的达一百种之多,而且多数栽培在佛寺庭园中,对整个区域的生态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再如,从阿拉伯世界传入的伊斯兰在其教义中也拥有大量的习惯环保法观念或规则。例如《古兰经》上说:“灾害因众人所犯的罪恶而显现于大陆和海洋,以至真主使他们尝试自己行为的一点报酬,以便他们悔悟。穆圣还号召人们植树造林,绿化环境,任何人植一棵树并后经培育,使其成长、结果,必将在后世受到真主的恩赐”。[3]很显然,上述教义是在禁止人们对树木乱砍滥伐,对野生动物乱捕滥杀。[4]在基督教中也有类似的教义,基督教于20世纪有外国传教士传入高黎贡山周边的傈僳族,后成为傈僳族的主要宗教。圣经要求信徒不能偷盗,也不能有偷盗的想法,有想法同样是罪,所以,他们要求信徒不要去偷树,严重的将被开除出教。
(三)禁忌
如果说“神话传说”和“宗教信仰”尚属习惯环保法的间接渊源的话,那么“禁忌”则是习惯环保法的直接渊源,是各民族习惯环保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藏族习惯法中,以禁为形式的禁止占了很大的比例。[5]在彝族和基诺地区,首先,有许多禁止的内容涉及到环境保护。例如彝族人忌砍有巢的树木、忌砍坟场的树木,忌砍树下有洞穴的树木,忌砍独木和枯木,忌砍泥石流中的树木,忌砍水中倒的树木。[6]又如到基诺山寨,在山间道路和山林中,到处可见大青树枝干粗大,树冠丰盈,老空心树多粗大古朴,姿态奇特,他们是山寨的风光树,绝不用担心横遭砍伐。在原始森林的山寨中有不少清澈的水塘,许多水塘就是山泉,晴时不干雨时不混不满,堪称森林中的明珠,人们绝不会向潭中投扔杂物,更不会出现污染水潭之事,其所以如此,是与传统中食人者的鬼魂有关,人们要敬神而远之,这些传说已成为一种习俗性禁忌,它在维护生态环境中的作用并不亚于今日的严厉法律在民族地区中的作用。其次,有许多禁忌涉及到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例如,彝族人民认为虎、豹、熊、獾、猴与人近亲,捕食它们被视为禁忌。[7]在许多民族禁忌中,尤其是那些宗教禁忌,更是与环境密切相关,例如基诺族忌乱砍、乱碰生长在寨子周围的古树巨藤、巨石,不许攀登,砍伐神山上的草木树叶。不允许占用神山上的林地建房;不许在神山狩猎。一些宗教禁忌更是与森林的水土涵养功能密切联系在一起。例如许多民族忌砍水井、山泉池塘边的树木,也不得在这些地方开垦荒地,[8]不许在“神林”中打猎甚至行走,更不许在其中放养牛马牲畜。这已成为一种信仰观念的禁忌习惯,所以它在保护热带雨林的自然生态中具有法律性的效力。可以说,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各民族禁忌的一致目的。
(四)乡规民约
与“禁忌”一样,“乡规民约”也是习惯环保法的直接渊源,其中蕴含了大量的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不仅如此,相比于前者而言,由于它是当地族群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自发生成的约定性规则,所以还具有更强的目的性,并且以直接保护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更新和利用为显在目的。在我们这么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那些多民族杂居地区,各民族自发约定一些规约来进行环境保护,可能比前述神话传说、宗教信仰更规范、更直接、更有效。例如,广西金秀大瑶山就有关
于钓鱼期、撵鱼期、禁止网鱼的规定;[9]壮族也有禁止用毒药捕鱼的规定。又如,彝族人民有比较详尽的有关山林管理的乡规民约,其保护对象从公有林、庙林、水源林到风水林。彝文典籍《西南彝志》规定:“树木枯了匠人来种植,树很茂盛不用刀伤害。祖宗有明训;祖宗定下大法,笔之于书,传诸子孙,古如此,而今也如此”[10]。清朝道光年间,云南省景东彝区的乡规民约规定:“凡一村界内,无论公山、私山,不得擅自砍伐,行者照乡规罚银:一禁纵火焚山。犯者罚银33两,二禁砍伐林木,采枝者罚银3两3钱,伐本者罚银3两3钱;三禁毁树种地,违者罚银33两;若有在公山伐柞把者,每把罚银33两”。[11]四川西北的色达藏族部落也有相似的规定。在该地区,每一位上任达赖和摄政每年都要宣讲《日垄法章》,严禁伤害山沟里除野狼以外的野兽、平原上除老鼠之外的生物,违者皆给予不同惩罚的禁令。[12]“理塘拉木地区禁止人们挖药材,不论挖多少,是否挖到,也不管是在自己的地里或他人的地里,都要罚款。一人挖材罚30藏元 ,二人罚60藏元,以此类推。理塘拉木地区不准砍神树,也不准到其他头人辖区内砍柴,对上山砍柴者罚藏元12-30元,越界砍柴者除罚藏元10元外,还得退回所砍的柴,并没收砍柴工具。”[13]显然藏民族很早就意识到自然和生态环境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作用而加以保护。由于藏族习惯法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反映了藏民族文化的地域特点和科学性。
三、习惯环保法的社会学基础
由上文的分析我们发现,习惯环保法要在特定地区、特定族群中为人们自觉遵守,需要拥有一定的物质要求、心理要求和精神要求等方面的社会学基础。
(一)物质要求
从物质的角度看,民族地区独特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地理环境和人口分布状况等因素对该民族习惯环保法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决定意识,文化来源于物质”的论断,特定民族、特定族群所拥有的特定物质手段或形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意识形态,即他们的习惯环保法文化、观念、规则和实践。例如,西北地区气候干旱,生态环境脆弱,该地区的习惯环保法就比较注重对水土、森林和草地的保护;西南地区丛林密布,沟涧纵横,该地区的习惯环保法也就非常注重人与森林及其中动物的和平相处。因此,很显然,草原民族地区的习惯环保法必然不同于山地民族地区的习惯环保法。可以推论,东北黑土地上的习惯环保法也必然不同于西南热带雨林中的习惯环保法,西北高原地区的习惯环保法也必然不同于东南沿海地区的习惯环保法。一言以蔽之,与习惯法一样,习惯环保法拥有强烈的物质依赖性或地方性。
(二)心理要求
1.民族性格的影响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性格。例如,据笔者观察,西北民族的性格大都粗犷而狂放,西南民族的性格则多柔和而内向;北方民族的人民喜欢表现自己孔武有力的一面,而南方民族的人民则乐于给人一种精细敏锐的印象。民族性格对于该民族的精神风貌、行为方式和法律意识均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当然也就对其习惯环保法有着内在的、重要的影响。例如,由于历史原因,多数少数民族要么就是居住在大漠戈壁,要么就是居住在林海雪原,要么就是居住在热带雨林,要么就是居住在高原或草原,甚或是大洋海岛之中,鲜有居住在肥沃的江河平原地区的。这些对民族地区人民的性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脆弱的生态迫使他们小心翼翼地与自然相处,生怕触怒自然招致不必要的损失或灾难。因此,在他们的习惯环保法中处处显现着一种为求生存而神化自然、神化环境甚至是一草一木的心理倾向。
2.宗教信仰的影响
我们发现,在民族地区,既留存了那种原始的、天人合一的宗教观念,也发展出了那种亲近、改造自然的宗教思想。后者在那些农业条件比较好,工业基础也相对雄厚的民族地区表现得比较突出。例如在东北的民族地区,人们倾向于通过宗教中的习惯环保法表达了解自然、亲近自然的美好愿望。当然,就多数民族而言,他们的宗教大都是以与自然达成和解甚或融为一体为目的的。因而,神化自然中的一切事物,敬畏自然的任何举动,呵护自然的原初面貌,也就成了民族地区人民习惯环保法的普遍选择。这无论是
在佛教、伊斯兰教甚至是道教中都有反映。一句话,与自然和谐相处,对自然物心存感激,无不是民族地区宗教的首要教义。“《古兰经》和《圣训》反复倡导对动植物及一切自然之物应存仁爱之心,特别禁止人们无故屠杀幼畜、砍伐幼苗。”[14]
(三)精神要求
精神要求与心理要求有许多重合的地方,例如它们都是人们内心深处的主观意识之体现。但是,它们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任何一个人都有追求安全、秩序和自由等内在的心理要求,但是有许多人可能没有什么精神追求,只想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因此,严格地讲,精神要求是该族群当中的精英人物提出并予以细化的。从前文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一些精英人物(例如松赞干布)在习惯环保法的生成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首发”作用。这是我们在研究习惯环保法时不能忽视的地方。在当代,许多新型的环保观念在很多时候也是由精英人物提倡,尔后得到信众的支持而自发生成。例如笔者在青海藏区调研时,发现当地人在喝完酒后有打碎酒瓶的习惯,我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说寺院的长老告诉他们,如果喝完酒后不打碎空酒瓶,那么虫子或动物钻进去出不来,没几天就会死掉。同时,习惯环保法上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也表达了人们所追求的在处理人与外界事物关系上的“至境”,并且也得到当地宗教教义的理论化和系统化,从而很好地表达了人们在对待自然环境上的精神要求。
四、习惯环保法与当代国家环保法的协调
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是我们主旋律,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从应然层面上看,习惯环保法与国家法治,尤其是国家环保法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和谐的、互动的。一方面,习惯环保法要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离不开国家法治和国家环保法机制的支持。可以说,后者对前者的支持力度和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前者的物化程度。另一方面,习惯环保法又对国家的法治和国家环保法机制的运行会产生反向的推动或阻碍作用:双方关系协调得好,前者对后者就会产生正向推动作用;协调不好,结果就会适得其反。当然,习惯环保法也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事物。不论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还是依据我们的经验观察,我们都可以发现,在我国,民族地区的习惯环保法文化及其规则已经在悄悄地发生改变,这是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对意识形态发生影响的一个客观表现。很显然,这就要求我们捕捉和把握此种变化,并适时地调整国家的法治和环保法机制,以使之能够与习惯环保法相契合或协调。但是实践中我们发现,许多民族地区优秀的习惯环保法文化和规则没有被很好地传承下来,而所传承下来的习惯环保法往往又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与此同时,国家有关部门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或认同民族地区优秀的习惯环保法文化和规则,或者干脆对之不屑一顾。因而,如何协调上述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当前中国环境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
无论是从应然层面还是从实然层面上看,社会控制手段或机制都是多元的。国家法律本身的一个问题就是:法律的字里行间常常蕴涵着社会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叙事方式。因此在非主流文化和非主体民族地区的法律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多元文化的观念是必须确立的。在文化多元的理念指导下,我们甚至可以再往前一步,即不仅应当充分吸纳民族地区习惯环保法中的优秀的、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也要宽容地对待其中比较一般的甚或不大符合国家成文法规定的习惯环保法规定。如果我们仅站在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民族地区的习惯环保法采取挑剔、指责的态度,那么此种单边主义法治观必将导致现实存在的两套环保法机制的对抗或反目。只有相互尊重、取长补短的双边主义法治观,才能很好地协调上述两种社会控制机制在实践运行中的复杂关系。
各民族地区的环保实践中不乏通过多元文化来进行社会控制的例子。比如云南少数民族村寨中普遍订立的“村规民俗”,其中一般都包涵着各民族的传统习惯法,对于村社的秩序起到了很好的调控作用。在各地村规民俗的制定过程中,基层政府往往会提出一些示范性的意见,这就为当代(主流)生态保护理念和国家法融入民族社区提供了很好的途径。在版纳一个叫漫散的村寨,其村规民俗的第二条规定了不得挖断道路;第三条规定不得偷砍竹子;第九条规定应圈养牲畜,这些规定中,有村寨因袭已久的习惯法
(第二、第三条);有在生产生活中自发产生的新的环境意识(第九条);从民间公约或民间法的角度解决了当地的一些基本的环境规范问题。这种把传统民族文化和现代环境理念相结合的模式,是非常值得总结和借鉴的。
结语
笔者认为,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我们必须树立双边乃至多边的文化观和法治观,那种单边的文化观和法治观在实践已经被证明行不通。同时,多元的社会还要求我们不能以静止的眼光来看问题,而应当以发展的眼光和思维来看问题。文化在发展、习惯法在发展、习惯环保法也在发展,我们已然身处一个发展变化的时代。因而,我们要很好地协调国家法治与民间习惯环保法之间的关系,也就必须树立多边的、动态的法治观。例如在笔者调研的青海藏区,一些寺院利用当地人们的“神林”观念,扩大了对当地森林的保护区域,同时结合国家法治和当代科技知识,号召人们保护环境,保护自己,从而收到非常积极的效果。少数民族地区应该根据当地的实际境况来保护好环境,也可以通过多元文化的借鉴来保护好当地的环境。
[1]范文澜.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837-838.
[2]寸瑞红.高黎贡山傈僳族传统森林资源管理初步研究[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36.
[3]古兰经.30:41.
[4]宝贵贞.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观探源[J].贵州民族研究,2002,(2):86-87.
[5]华热.多杰.浅谈藏区环保习惯法[J].青海民族研究,2001,(6):32-33.
[6][7]卢春樱.试论彝族传统禁忌文化[J].贵州民族研究,1999,(4):95.
[8]李可.论环境习惯法[J].环境资源法论丛,2006,(6):27-40.
[9]曾思平.清代以来岭南地区瑶族习惯法初探[D].暨南大学,2002:11.
[10]彝文典籍.西南彝志.
[11]宝贵贞.少数民族生态伦理观探源[J].贵州民族研究,2002,(3):102-106.
[12]徐晓光.藏族法制史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331.
[13]高其才.中国习惯法论[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123-125.
[14]蔡家麒.论原始宗教[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6.
G03
:A
:1671-6469(2013)04-0022-06
2013-07-03
梅长胜(1970-),男,安徽来安人,中共马鞍山市委党校法学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法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