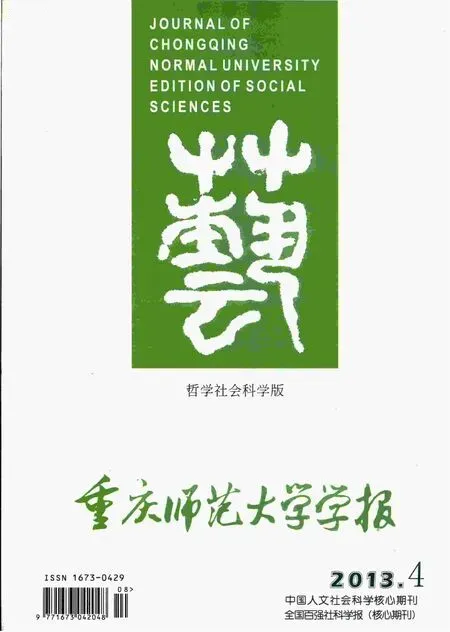文学接受·文学形式·意识形态
——“客观说”下的关系反思与理论建构
2013-04-02陈长利
陈长利
(中国矿业大学 文学与法政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传统上对形式主义文论的研究大多采用“科学主义”研究方法,忽略了形式主义文论的社会历史维度,以致一些问题无法进入理论视野,例如,看不到形式主义文论作为现代审美经验的反思形态的一面,看不到形式主义文论在现代社会承担的意识形态功能,不能把现代文论与前现代文论在性质上区别开来,形式主义文论内在逻辑演进线索模糊不清等。甚至有的学者得出偏狭的结论,如把具有现代性质的形式主义文论等同于中国传统文论的文法、句法,这就等于仅仅从修辞、技术角度来认识形式主义文论,而看不到它充满人文历史内涵的部分。实际上,形式主义文论作为现代文学在思想领域的反思形式,一方面联系着现代审美经验,另一方面联系着现代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功能的内在要求。
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等为代表的20世纪西方形式主义文论,被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概括为“客观说”,即“客观化走向”[1](31),被法国学者方丹在《诗学——文学形式通论》中称为“客体诗学”或“形式诗学”[2](2),在他们那里,形式主义文论或“客观说”具有现代文学范式的性质。本文讨论的话题是“客观说”或“形式主义文论”下的文学接受、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特点,认为“不透明性”关系、“透明性”关系、“半透明性”关系是形式主义文论三个逻辑发展阶段,即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的三种关系典型形态。
一、俄国形式主义:“不透明性”关系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文学形式思想是一种“语言形式”观。围绕文学语言特殊性问题,他们发现与总结出一系列独特的规律性认识,如“陌生化”思想、“文学性”思想,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的区别,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的不同,文学语言在艺术中的分布规律,形式主义文学语言观与传统的文学语言观的不同,故事与情节的问题,文学结构的问题,诗歌语言的想象、夸张、类比、比喻、廻复等修辞问题,等等。这些规律性大致相当于现代语言学研究中的“语法”,或者反过来说,是“语言学之应用于文学研究”。[3](3)
现代语言学对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直接影响无可置疑,但研究者往往忽略了人本主义思想如现象学、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及其思想来源尼采、叔本华等人的影响,以致把形式主义文论研究最终引向了科学主义研究的“独木桥”。现象学主张,人不单单能认识现象,而且能认识自在之物,人们对现象的判断总是和存在自身直接关联,而存在总是人们实际的生活存在。这样,研究语言实际上就是研究人的意识和实际的生活。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追求为艺术寻求新的表达手段,但他们都认为,新的技巧是为了服务于表现“存在的本质”。尼采、叔本华认为,不是理性而是“意志”才是知识的先天条件,它是感性的、实实在在的,而不是逻辑的、形而上学的。在感觉中原本就有一种纯粹的主动的东西,而不需要另外一种理性对它进行规范整理。
根据这些来源思想,不仅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精神并非要远离生活,而且,使文学独立出来恰恰是为了更能够回归生活,理论是对生活的发言;文学形式不是外在于存在的本质,而是为了把握存在本质的现代必要方式与途径;文学形式的性质是根植于“自身”而不是“外在”的东西,它们之间不是一种对立关系,而是一开始外在性就内涵在形式的主动性里面。
什克洛夫斯基宣称:“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颜色。”[4](11)显然表现出对意识形态的坚决抵制态度。这种拒绝态度,并不是说他们在政治上有什么新的成熟立场与主张,而是他们从所相信的哲学基础出发,提出对传统文论工具性的批判与挑战。传统文论代表是“学院派”,该学派混杂了俄国民主主义者的文艺思想和欧洲实证主义方法,其中别林斯基和法国学者泰纳影响尤大。就前者的影响而言,他们从普列汉诺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继承来“社会结构”五层次划分学说和“美是生活”的观点,进一步发挥阐释上升到方法论高度,致使艺术的一切特殊规律和手段,都消失在简单庸俗的物质生活条件即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之中,从而在艺术即风格的投影、风格即思想的反映、思想即人的阶级意识、人即社会的阶级分子这种类推之中,艺术时而是物质财富,时而是统一的思想,时而是党性的意识,时而是党性的下意识。总之,万变不离一点,艺术只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工具。就后者的影响而言,他们本着传记主义原则,重视作家个性、习惯、生平、事迹研究,把细枝末节的繁琐考证当作研究对象,为了作家意识而不惜牺牲作品的客观性。两派之间具有一致性,后者的理论根本上被纳入到了前者理论的结构里面。他们认为,学院派对文学知识认识贫乏,对艺术感觉迟钝,就连“对象是否存在也成了虚构”[5](22)。
在文学接受方面,他们拒绝迎合大众的阅读口味,也反对象征派批评。针对前者,他们主张借助文学恢复读者对生活世界的真实感受,解除意识形态强加给人身上的一套自动化程序与规范,使人们对石头的感觉更像石头;针对后者,他们反对其致力于抽象的宗教伦理问题思考,“以揭示生存的秘密和神秘的观念为己任”[4](3),在批评作品时不顾作品的存在实际,或者从宗教、心理学、形而上学出发,或者从批评者自我心灵或主观臆断出发,对作品任意图解。
正是在这种与意识形态和文学接受要素的关系系统中,文学形式的内在价值被确定下来。他们提出,“使诗学重新回到科学地研究事实的道路上来。”[5](23)这种“事实”至少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真实的世界,这被他们看成是文学观念产生的条件和基础。穆卡洛夫斯基针对什克洛夫斯基一开始只重视形式技巧的片面性指出,“虽然‘纺织方法’现在仍是注意的中心,但是一点也已十分明显,即不能完全脱离开‘世界棉纱市场的形势’,因为纺织业的发展(也在直接的意义上)不仅服从棉纱生产技术的发展(这一发展系列的内部规律性),同时也服从市场需要,即供求关系。”[6](28)二是精神史和艺术史以及两者的关系,这被看成是艺术发展的根本动力。日尔蒙斯基说:“作为艺术表现手法或者程序的统一风格之进化,是与文艺心理学的任务之变化,与审美经验和审美鉴赏力之变化紧密相关联的。但这也与时代的整个处世态度的变化紧密相关联。从这个意义上看,艺术中的重大的、根本性的进展(例如: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式建筑、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都同时涉及所有的艺术,而且被精神文化的普遍进展所决定。”[4](364)正是对这种“事实”的理解,奠定了他们文学形式的物质性、科学性内涵。
总之,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下的文学接受、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关系,表现为一种“不透明性关系”,它强调文学是以特殊的语言组织方式构成的独立的艺术世界,其目的在于再现客观世界的真实性关系,以唤回人对世界的存在体验,文学研究就是研究文学凭借抵达存在的那些特殊语言方式与途径,因此,它拒绝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也不迎合大众的阅读口味,文学的产生根植于社会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文学观念的变化是文学史与精神史、社会历史互动的结果。
二、英美新批评:“透明性关系”
新批评的文学形式思想是一种“有机整体”观。他们不像俄国形式主义那样,立足于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区别并重点在文学语言特殊性上做文章,而是一开始就把文学形式看成一个有机统一体,把整个文学世界包括文学史在内,看成一个更大的有机统一体。他们还认为,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新的作品加入而发生不断变化。
但是,如果对新批评的形式认识仅仅看到“有机形式”外观,看不到思想本身,就还是停留在“修辞”、“技术”层面。兰塞姆提出“本体论批评”思想,“本体,即诗歌存在的现实”,“它所处理的是存在的条理,是客观事物的层次。”[7](74)这就是说,新批评的精神旨向是对文学与存在关系的反思学说,这就把新批评的形式思想提升到了“意义”理解层面。他指出,“诗歌旨在恢复我们通过自己的感觉和记忆淡淡地了解的那个复杂难制的世界。就此而言,这种知识从根本上或本体上是特殊的知识。”[7](74)在他看来,诗的本质在于追寻世界本体的知识,因而反对把道德伦理、逻辑论证、情感发泄看成诗歌的本质。唯有此,才可能把这种现代性质的“本体论批评”与传统的道德批评、实证主义批评、表现主义批评区别开来。
新批评文论缘起于英国而鼎盛于美国,它产生的直接背景是传统的英国维多利亚批评,这种批评以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想为基础,主要采用印象式或传记式方法,重视批评者个体经验描述,缺少对作品本身的关注和价值判断。在早期,他们重视读者经验,能够使批评和读者之间建立起信赖关系,往往能赢得读者的赞同,从而变成社会集体经验。但这种情况到20世纪初发生了变化。经济上和国际上日益增长的矛盾,工人运动政治上的解放,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报刊业的垄断化和专业化,文学之分为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两种,以及许许多多其它倾向,这一切“破坏了维多利亚批评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8](577)。由于批评者的个人感受越来越脱离社会现实,于是主观批评、印象批评和作家传记式批评逐渐失去了读者的认同。这为以文本为分析对象的新批评的产生提供了历史契机,而且,一开始他们的理论就突出了与现实生活经验领域的密切关系。此外,新批评文论秉承英国经验主义传统,重视归纳而轻视演绎,拒绝从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角度研究文学,而主张一种实用性的文本批评。这种文论沿袭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以文本为中心的形式主义原则,追求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的批评目的,从而建立与读者一致的依赖关系。它继承与秉持经验主义传统和实用文学原则,本身即与英美实用主义意识形态一致。所以,在新批评文论下,文学接受、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之间,具有一种“透明性”关系。
韦勒克认为,对文学事实而言,存在一种经过几个世纪而不变的结构的本质,尽管“结构”在历史进程中会在艺术家、读者、批评家头脑中发生变化,但结构的本质依然保持完好,这样,人们就可以根据这个结构的本质对作品做出判断。这种结构的本质就是新批评文论所追求的,而这在根本上不能不受制于一种外在的集体的意识形态。他说:“艺术品似乎是一种独特的可以认识的对象,它有特别的本体论地位。它既不是实在的(物理的,像一座雕像那样),也不是精神的(心理上的,像愉快或痛苦的经验那样),也不是理想的(像一个三角形那样)。必须假设这套标准的体系存在于集体的意识形态之中,随着它而变化,只有通过个人的心理经验方能理解,它建立在其许多句子的声音结构的基础知识上。”[9](164)因此,文学语言具有一种“透明性”,“文学指向现实,谈论世界上的事情。”[10](25)在韦勒克这里,文学本体论追求、批评的尺度与意识形态具有内在一致性。
按照韦伯的观点,现代社会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随着科学精神的兴起而导致的宗教精神的衰落,一是现代学科划分导致的价值领域的独立。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社会发展动力密切联系宗教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伦理观念,但到了现代社会,“上帝死亡”后留下的是一片黑暗的非理性世界。为了摆脱这种非理性的梦魇,人文主义批判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或理性主义的冷酷无情,要求理性回归人的生活;与此相应,科学主义批判传统中狂妄的理性,要求放弃自由解放的宏伟叙事,让理性回归经验世界,在经验实证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为命题寻求表达的可能性,为知识寻求可靠的基础,为文化寻求无意识结构。正是面对非理性给人类带来的恐怖、战争和灾难,现代工具理性终于同人文主义达成某种一致,即社会由于工具理性所造成的压力,交付文学与审美领域来释放与缓解。韦伯指出,“艺术变成了一个越来越自觉把握到的有独立价值的世界,这些价值本身就是存在的。不论怎么来解释,艺术都承担了一种世俗救赎功能。它提供了一种从日常生活的千篇一律中解脱出来的救赎,尤其是从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主义那不断增长的压力中解脱出来的救赎。”[11](342)根据这种观点,现代社会之所以辟出一个自治的审美领域,根本源于现代性的矛盾与张力。正是由于以美育代宗教,成为审美自治领域在现代社会获得立法性的根据,瑞恰慈才说“唯有诗歌有能力拯救我们”[12](52)。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文学形式、意识形态、文学接受的一致性关系:文学之于意识形态,是代替了宗教衰落后留下的空白的位置,文学之于文学接受,起到精神救赎的作用。
总之,在新批评文论中,文学接受、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之间是一种“透明性”关系,文学形式以有机形式为轴心、以存在本体为追求旨向,与意识形态和文学接受之间具有一致性关系。由于宗教不再向人们提供他们生活所需要的精神支柱,而科学在感情方面又保持中立,只有文学或诗歌才能在协调人们生命经验的纷乱和冲动的同时向人们提供和谐的秩序,因此,它再次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与精神救赎的作用。
三、法国结构主义:“半透明性”关系
法国结构主义文论的文学形式思想在性质上是一种“功能形式观”,它是对新批评形式思想的再次超越。结构主义的文学形式思想不仅把历史上的文学文本看成有机统一体,把人类历史各式经验作为“大文本”来研究,还把文学结构与社会精神结构统一起来,进而发现文本结构在社会精神结构中所发挥的功能。
结构主义的产生深受现代自然科学、语言学、心理学的影响。在自然科学领域,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成为自然科学盛行的方法并向社会人文科学渗透,它们代替了传统原子论下注重孤立个体的模式。在语言学上,索绪尔将传统语言学研究从历时性研究转向共时性研究的语法规则,提出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历时与共时等二元概念,成为结构主义分析的基本范畴。在心理学上,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论证了个体心理成长过程不同阶段的结构性特征,启示了现代形式思维。尤其是皮亚杰概括的结构的三个基本特征即“整体性”、“转换性”、“自我调整性”,成为结构主义文论的方法论基础。
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形式理论最常见的部分是各种模式研究。如早在俄国形式主义者普洛普那里,他就在大量分析俄罗斯民间故事的基础上,概括出7种“行动范围”(反面角色、施与者、帮助者、被寻找者、迎信者、英雄、假英雄)和31种固定元素或功能。再如,格雷马斯概括出一个由六个行动位组成的模型,用来分析文本的叙事结构,它们分别是主语、宾语、发送者、接受者、反对者、帮助者,等等。但是,“模式”研究依然局限在文学领域,处于结构主义形式思想较低层面。
比“模式”认识更进一步的是“同构”思想,即文本结构与社会精神结构具有同构性。在结构主义那里,文本结构、语言结构、社会结构、神话结构之间彼此关联而同构,相同的观念体现在诸如庆典、仪式、血缘关系、婚姻法则、烹饪方法、图腾制度等丰富的文化形式之中。托多罗夫指出,“不仅一切语言,而且一切指示系统都具有同一种语法。这语法之所以带有普遍性,不仅因为它决定着世上的一切语言,而且因为它和世界本身的结构是相同的。”[13](97)戈德曼认为,一部作品的各个组成成分既作为独立功能出现在作品范围之内,也同时统一在一个共同的“世界观”之下,这种共同的“世界观”,就是意识形态。
正是以“同构”思想为前提,现代社会几乎所有领域都被意识形态化了。巴尔特通过对食品、家具、服装、建筑、文学艺术等分析,揭示出语言如何组织人们的现实经验。拉康则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得出相同结论。他的“镜像理论”认为,自我是空洞的、流变的、无中心的,无意识并不属于个体“内部”,而是来自个体“外部”,或者说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结果,自我的确立是在对周围对象关照中产生的,是“一种想象性的认同秩序”。在结构主义文论中,那种把文学从社会彻底独立出来的做法并不存在。巴尔特在谈到艺术风格时,强烈反对把风格看成某种写作的内在特征,而不是由经济和政治条件所决定的外在特征的观点,认为这是十足的虚伪,“它暴露了野心勃勃的资产阶级最后的历史野心,急于把人类的全部经验都纳入自己对世界的特定看法之中,并把这标榜为‘自然的’和‘标准的’,拒不承认它对此无法归类的东西。”[13](110)文本对社会的依赖关系成为结构主义文论思想的“题中之义”。
但是,文本结构与社会精神结构的关系,更根本的是一种“功能性”关系,而不是“复本”或“投射”关系。文本结构始终处于社会精神结构的指定位置,根据结构主义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没有哪个文本能呈现出整体的全部语法。要想实现部分与整体的功能性关系,必然要借助读者的阐释活动。就像列维·斯特劳斯做过的那样,他通过考察巴西内地印第安人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得出亲属制度、图腾制度和神话传说的内在结构性关系。就像福柯那样,他在研究西方思想史的时候,借助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分析,从而找到这些文本如何与一种“知识型”发生关系。因此,是阐释者充当了文本结构与精神结构之间的中介和桥梁,没有读者,文本结构与精神结构永远处于隐晦不明状态。
但是,结构主义文论并没有给读者以任何特权。它的功能仅仅是在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建立起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联系,读者处在相同的结构关系当中,除了再现“客观关系”外,他不能增添什么,或者减少什么。正是在这一点上,结构主义的读者观念与接受美学的读者观念显然不同,后者不仅起到再现结构中的特殊关系的作用,更重要的在于它对意义的生产方面。但是,读者的重要性被结构主义突显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中叶文艺理论研究重心“读者”转移,是结构主义文论发展的结果。
浪漫主义者柯勒律治早就提到过文学语言具有一种“半透明性”特点:“象征的特点,是以个体中的特殊之半透明性,或特殊中的一般抑或一般中的普遍之半透明性,来予以概括之;而最重要的,则是由贯穿并存在于暂时中的永恒之半透明性,来进行概括的。”[14](8)但这种“半透明性”是以文学与世界的象征性关系为前提的。不同于浪漫主义,对结构主义来说,文学形式只能作为整体的症候,却不能作为对整体的反映而存在,文学结构处于社会精神结构指定的位置,而不是整体的微观模型,更不是镜子。因此,以个别反映一般的传统典型观念在结构主义文论面前难以奏效。对结构主义而言,典型不是以特殊反映一般,而是结构对特殊的位置指定,传统的典型观念是对特殊的过度要求。
综上所述,本文从“关系主义”视角出发,把“客观说”下文学接受、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概括为三种形态: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为代表的“不透明性”关系,侧重文学语言的特殊性,文学作为一个独立自治的审美领域,意识形态与普通读者经验不能任意进入;以英美新批评为代表的“透明性”关系,强调形式与意义结合为有机统一体,文学具有追寻本体世界的能力,“美育代宗教”为文学在现代社会找到合法性地位,文学具有精神救赎的作用;以法国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半透明性”关系,侧重文本结构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性地位,文学处于精神结构的指定位置,通过阐释活动,文本结构与精神结构建立起复杂、曲折的联系。显然,本文是从文学内部与文学外部之间关系的角度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反思研究,对该文论具有再认识价值。
[1]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2]达维德·方丹.诗学——文学形式通论[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3]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C].三联书店,1989.
[5]维茨坦·托多罗夫.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6]波利亚科夫编.结构—符号学文艺学——方法论体系和论争[M].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
[7]约翰·克娄·兰色姆.征求本体论批评家[A].“新批评”文集[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8]罗伯特·魏曼.“新批评”和资产阶级文学批评的发展(1962)[A].“新批评”文集[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9]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M].三联书店,1984.
[10]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11]H.H.Gerth and C.W.Mills,eds.From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6.
[12]彼得·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3]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14]保罗·德曼.解构之图[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