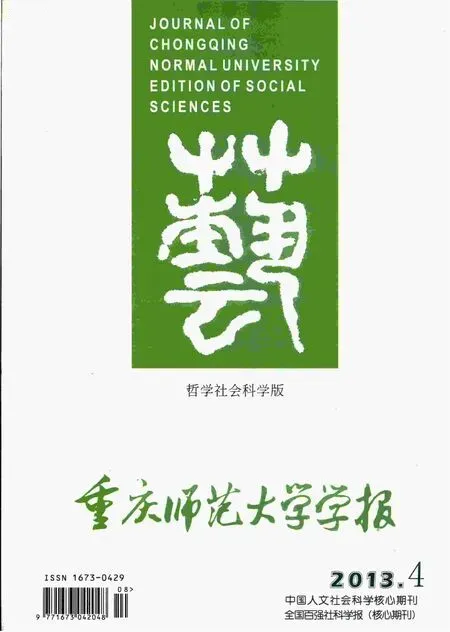从绍兴四年高宗手诏看其进取之志
2013-04-02陈忻
陈 忻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0047)
绍兴四年对于南宋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时段,这一年南宋成功挫败了伪齐的进攻,致使金人重新考虑伪齐刘豫存在的必要性,并终于在绍兴七年十一月废掉伪齐,这就为宋金真正意义上的和议奠定了必须的基础,也使南宋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与金的对峙,从而摆脱了奔避流亡的命运。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高宗对敌态度的从隐忍到抗击起着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赵鼎、张浚的全力以赴,还是将帅的通力合作,都是以此为根本前提的。自刘豫联合金人大举入侵,高宗连发手诏,其中发布于绍兴四年十一月的讨伐刘豫以定顺逆、起用张浚以成其事功的二次手诏最为重要。结合其发布的前后背景,可以清楚地看到南宋前期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以及高宗积极进取的对敌态度。
讨伐刘豫以定顺逆
刘豫自建炎四年七月受金人册封为伪齐皇帝,并于九月即伪位以后,就依仗金人,积极开展了一系列叛宋扰宋的工作。刘豫君臣对自己居于金人与南宋之间的处境以及对于金宋二者的抉择是非常清楚的。
对于金人来说,“大齐虽号皇帝,然止是本朝一附庸,指挥使令,无不如意。”[1](卷81,绍兴四年十月乙丑条,2册,135)“立豫者,欲豫辟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2](卷475,刘豫传,13800)对于刘豫来说,借助于金人之力方能安身立朝的事实也是非常明白的,伪奉议郎罗诱就曾说:“民心日夜望故主之来,所赖大金威惠,固无异心。使彼和间稍行,将不我援,则豪杰四起,不待赵氏之兵,而齐已诛矣。”[1](卷78,绍兴四年七月丁丑条,2册,98)这样的形势决定了刘豫一定要在外交上极力破坏南宋与金人议和的企望。绍兴三年五月,金人要求南宋遣重臣以取信,南宋“朝廷以果茗、縑帛遣刘麟,假道,麟不纳”[1](卷65,绍兴三年五月壬戌条,1册,846);绍兴四年正月,南宋派龙图阁学士枢密都承旨章谊、给事中孙近使金国,其来去都受到伪齐的干扰:“金国元帅府议事官安州团练使李永寿、尚书职方郎中王翊辞行。”“翌日,永寿发临安。诏通问使章谊等偕行。”“谊等至泗州,而伪境以檄来,言大金使、副已差官引伴赴阙,请权留南宋奉使俟旨。永寿复移檄宿州接引,谊等乃得俱北。”[1](卷72,绍兴四年春正月丙寅条,2册,30)七月,“谊等还至睢阳,为豫所留,以计得免。”[1](卷78,绍兴四年秋七月辛未条,2册,95)在破坏宋金议和之外,伪齐更通过金人与南宋朝廷争夺利益。绍兴三年十二月,金使李永寿、王翊入宋,“永寿请还伪齐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东南者,且欲画江以益刘豫。”[1](卷71,绍兴三年十二月己酉条,2册,26)伪齐倚仗金人的支持步步紧逼,正如翰林学士綦崇礼所分析:“豫父子倚重金人,且永寿等从豫所来,画江之请必出于豫。观其奸谋,在窥吾境土。”[2](卷475,刘豫传,13798)
对于南宋,伪齐俨然要与之分庭抗礼。绍兴三年七月,南宋韩肖胄、胡松年出使,“至汴梁,伪齐刘豫欲见之。副使胡松年曰:‘见之无害。’豫之伪臣欲令以臣礼见,肖胄未有以答。松年曰:‘皆大宋之臣,当用敌礼。’豫不能折。既见,松年长揖豫,叙寒温如平生,豫欲以君臣之礼傲之。松年曰:‘松年与殿下比肩事主,不宜如是。’”[1](卷67,绍兴三年秋七月乙丑条,1册,865)刘豫一定要与南宋对抗到底,因为他没有退路。伪齐奉议郎罗诱曾针对言论之劝谕刘豫幡然归宋而做出相反的分析云:“其一曰宜以卑辞通旧主,告以大金敦迫不得已之意,阴结猛援,速求剪伐。成即为君,败即不失为忠臣。陛下独不畏张邦昌之祸乎?北面奉符玺,退而复辟,犹且为齑粉,况又有甚焉者哉? 此可决者。”[1](卷78,绍兴四年秋七月丁丑条,2册,97)其实,刘豫自登伪位,就已经选择了不再回头的道路。建炎四年十一月,“国信副使宋汝为以吕颐浩书勉豫忠义,豫曰:‘独不见张邦昌乎?业已然,尚何言哉?’沧州进士邢希载上豫书,乞通宋朝,豫杀希载。”[2](卷475,刘豫传,13795)既然站在与南宋势不两立的立场上,伪齐当然就要抓住南宋政权压力重重之时机,千方百计地予以有效地打击。因为“若不乘其(南宋)弊而击,待其羽翮之成,提兵北向,则我齐一败涂地。”[1](卷78,绍兴四年秋七月丁丑条,2册,97)以此为出发点,伪齐对南宋采取了绝对敌视的态度。为了实现金人赋予的“辟疆保境”的使命,在北面,“刘豫介然处于其中,势不两立,必求援于金。”[1](卷74,绍兴四年三月丁卯条,2册,50)对南宋形成日益严重的威胁:“伪齐明置归受馆,厚立赏以招吾人,既遣李成侵襄、邓、郢州,又遣重兵归川口。”[1](卷75,绍兴四年夏四月丙午条,2册,63)除了积极与金人相应援,在南宋的北方制造军事压力之外,刘豫更在南方行动,远结南蛮,侵扰川、广,欲从经济上遏制南宋,必欲致南宋“鱼烂而亡”:
初,伪齐侍御史卢载扬上议,陈结南蛮扰川、广之策。大略谓:“今宋朝播迁,假息吴越,西失关陕之重兵,东绝齐鲁之徭赋,荆湖屯大寇,江浙防劲敌,固已颠沛矣。然而川、广交通,宝货杂遝,有金银茶马之贡、香礬缯锦之利资其雄富,未易陨越。为今之计,莫若列其利害,表于大金,大具海舶,各遣一介之使,南通交趾,结连溪洞,讲智高之旧策,约二广以分王,侵掠其地,俾财赋不入于二浙,将穷且迫。虽不加讨,亦必鱼烂而亡矣。”豫大悦,是日遣通判齐州傅维永及募进士宋囦等五十余人,自登州泛海入交趾,册交趾郡王李阳焕为广王,且结连诸溪洞酋长。金主遣使穆都哩等二十余人偕行。[1](卷68,绍兴三年九月乙卯条,1册,877)
刘豫北联金人、南接蛮氏的策略对于南宋朝廷来说是极为致命的。一方面,南宋为了与金达成和议而对伪齐采取隐忍的态度。“自豫僭立,朝廷以金故,至以大齐名之。”[1](卷82,绍兴四年十一月壬子条,2册,146)绍兴三年五月,南宋“枢密院言,已遣使诣大金议和,恐沿边守将辄发人马侵犯齐界,理宜约束。诏出榜沿边晓谕,如敢违犯,令宣抚司依法施行。”[1](卷65,绍兴三年五月乙亥条,1册,848)“朝廷既遣韩肖胄等行,乃俾元(指淮南宣抚司统制官解元——笔者注)退屯盱眙,且戒以勿侵齐地。”[1](卷65,绍兴三年五月己卯条,1册,849)绍兴三年十一月,“诏沿淮诸寨乡兵毋得辄擅侵扰齐国界分,用枢密院请也。”[1](卷70,绍兴三年十一月乙丑条,2册,16)另一方面,为争夺有利的生存空间,南宋与伪齐的军事摩擦、冲突也从未停歇。就其大者而言,绍兴三年二月,南宋京西招抚使李横率军一意向前,直入颍昌,“传檄诸军收复东京。是日,以其文来上,略曰:‘伪齐僭号,自速剪平,国运中兴。王师已进,西压淮、泗,东接海、沂,驿骑交驰,羽书叠至。我则兼收南阳智谋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义以行,乘时而动。’又曰:‘金商之兵出其先,荆湖之师继其后。若能纳欵,则悉仍旧贯;执迷不悟,则后悔难追。’”[1](卷63,绍兴三年二月甲子条,1册,827)绍兴四年五月,岳飞复郢州、复襄阳、复唐州:“初,伪齐将李成闻郢州失守,乃弃襄阳去,飞进军据守,遂复唐州。”[1](卷76,绍兴四年五月戊寅条,2册,77)六月,复随州。岳飞在中线的捷报直接拉开了南宋与伪齐正面的大规模较量。因为襄阳的重要地理位置决定了南宋与伪齐必定对之力争以据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五,绍兴四年四月庚子条就曾记载:
初,襄阳既为伪齐将李成所据,川陕路绝,湖湘之民亦不奠居。一日,宰执奏事,朱胜非言:“襄阳上流,襟带吴蜀,我若得之,则进可以蹙贼,退可以保境。今陷于寇,所当先取。”
襄阳对于南宋与伪齐双方既然如此重要,所以岳飞的捷报对南宋来说是极大地振奋了朝廷“中原可复”的信念。绍兴四年六月“丙午,执政奏事。上谓曰:‘岳飞已复襄、郢,尼玛哈闻之必怒。况今正是六月下旬,便可讲究防秋。倘敌人尚敢南来,朕当亲率诸军迎敌,使之无遗类,即中原可复也。若复远避为泛海计,何以立国耶?’”[1](卷77,绍兴四年六月丙午条,2册,85)另一方面,对于伪齐来说,则是不甘轻弃:“初,伪齐刘豫闻岳飞复襄阳,遣使乞师于金主晟,以求入寇。”[1](卷78,绍兴四年七月丁丑条,2册,97)这样的形势背景决定了南宋与伪齐之间大规模的正面冲突必然要爆发。也就是在这时,伪齐奉议郎罗诱向刘豫呈上南征策,文中详细分析了伪齐与南宋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优劣之所在,特别强调南宋有“可击者六”:金陵重地失其守;宰相无有任其责者;将骄而不和;兵纵而不戢;主孤而内危;民穷而财匮。罗诱鼓动刘豫抓住时机,一举灭宋:“陛下据全齐之地,豪杰之士云屯雾集;而赵氏兵穷力促,国势颠跻,此天亡之秋,所以假手于陛下。”“我无四议之惑,彼有六击之便,是乃万全之师,取天下如反掌。”[1](卷78,绍兴四年七月丁丑条,2册,97)对于罗诱的南侵奏议,“豫览之大悦,赐诱帛百匹,乘传赴阙,以诱为行军谋主”。[1](卷78,绍兴四年七月丁丑条,2册,99)并开始了实际的游说金人联兵南进的行动:
伪齐刘豫既纳其臣罗诱南征议,乃遣知枢密院事卢伟卿见金主晟。具言国家自大梁五迁,皆失其土。若假兵五万下两淮,南逐五百里,则吴越又将弃而失之,货财子女不求而得,然后择金国贤王或有德者立为淮王,王盱眙,使山东唇齿之势成,晏然无南顾之忧,则两河自定矣。青冀之地古称上土,耕桑以时,富庶可待,则宋之微赂又何足较其得失?[1](卷80,绍兴四年九月乙丑条,2册,119)
刘豫的说辞既从吴越的财货子女、青冀之地的富庶可待等经济利益诱劝金人,复以择金人所欢为淮王、占地利而断却南顾之忧的政治目的打动金人。于是,金人决计起兵,以应刘豫之请。南宋与伪齐的正面战争就此爆发。
绍兴四年九月,刘豫下伪诏曰:
朕受命数年,治颇有叙。永惟吴、蜀、江、湖皆定议一统之地,重念生民久困,不忍用兵,故为请于大金,欲割地封之,使保赵氏之祀。大金以元议绝灭,但欲终其伐功,力请逾坚,方见听许。岂期蔑弃大德,乃敢伪遣使聘,密期吞噬,是用遣皇子麟会大金元帅,大兵直捣僭磊,务使六合混一。[1](卷80,绍兴四年九月乙丑条,2册,120)
刘豫以“朕”自名,明确地向南宋宣称其“吴、蜀、江、湖皆定议一统之地”的政治野心,更以侮辱性的口吻声称“欲割地封之,使保赵氏之祀”。他直呼南宋之地为“僭磊”,誓言要“大兵直捣僭磊,务使六合混一”。如前所述,绍兴三年十二月,金使李永寿、王翊至行在,要求南宋归还伪齐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东南者,并要求划江以增益刘豫。绍兴四年正月乙卯,南宋遣“龙图阁学士枢密都承旨章谊为大金军前奉表通问使,给事中孙近副之”,“时金所议事朝廷皆不从。乃遣谊等请还两宫及河南地。命右文殿修撰王伦作书于金左副元帅宗维所亲耶律绍文、高庆裔,且以《资治通鉴》、木棉、虔布、龙凤茶遗之。”[1](卷72,绍兴四年春正月乙卯条,2册,28)这便是刘豫指斥南宋朝廷“蔑弃大德”、“伪遣使聘,密期吞噬”的依据,也成为伪齐公开联金南侵的理由之一。刘豫的伪诏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南宋的蔑视和敌意,这是对南宋朝廷的公开挑衅。面对刘豫的猖獗,高宗的愤怒溢于言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一,绍兴四年冬十月丙申条记载高宗言辞曰:“豫父子逆乱如此,皆朕不德所致。然以朝廷事力,遣一偏师,豫可擒也。徒以二圣在远,故屈己通和,觊还銮辂。今乃挟强敌之兵,复入为寇,此安可容忍!”
对于南宋政权来说,伪齐与金的联兵入犯,实乃又一次进入生死存亡的关口,诚如高宗赐韩世忠御札所言:“今敌气正锐,又皆小舟轻捷,可以横江径渡浙西、趋行朝,无数舍之远,朕甚忧之。建康诸渡旧为敌冲,万一透漏,存亡所系。”[1](卷81,绍兴四年冬十月己卯条,2册,127)在“谍报至,举朝震恐。或劝上它幸,议散百司”[1](卷80,绍兴四年九月乙丑条,2册,120)的关键时刻,赵鼎临危拜相,坚守“战固危道,有败亦有成,不犹愈于退而必亡者乎”[1](卷81,绍兴四年冬十月戊子条,2册,131)的理念,全力促成高宗亲征。绍兴四年十月丙子,高宗确定迎战伪齐:“上谓辅臣曰:‘朕为二圣在远,生灵久罹涂炭,屈已请和,而金复肆侵陵。朕当亲总六军,往临大江,决于一战。’”[1](卷81,绍兴四年冬十月丙子条,2册,126)绍兴四年十一月,高宗手诏云:
朕以两宫万里,一别九年,觊迎銮辂之还,期遂庭闱之奉。故暴虎凭河之怒,敌虽逞于凶残,而投鼠忌器之嫌,朕宁甘于屈辱?是以卑辞遣使,屈己通和,仰怀故国之庙祧,至于霣涕,俯见中原之父老,宁不汗颜?比得强敌之情,稍有休兵之议。而叛臣刘豫惧祸及身,造为事端,间谍和好。签我赤子,胁使征行,涉地称兵,操戈犯顺,大逆不道,一至于斯。警奏既闻,神人共愤,皆愿挺身而效死,不忍与贼以俱生。今朕此行,士气百倍,虽自纂承之後,每乖举错之方,尚念祖宗在天之灵,共刷国家累岁之耻,殪彼逆党,成此隽功。载惟夙宵跋履之勤,仍蹈锋镝战争之苦。兴言及此,无所措躬。然而能建非常之功,必有不次之赏。初诏具在,朕不食言。咨尔六师,咸体朕意。[1](卷82,绍兴四年十一月壬子条,2册,145)
高宗将矛头直指刘豫,斥其为“叛臣”、“逆党”,“大逆不道”,其依据就在于君臣之大义:“今者逆贼刘豫阴导金人,提兵南向。此在朝廷,当以正理处之。盖不讨贼豫,则无以为国……前此不欲轻发兵端,故隐忍以待衅。今贼豫启之,我欲乘机以举,则处以正理,不可失也……自古立国,必明君臣之义。陈常作乱,孔子请讨,此齐国之乱臣,而鲁不容。况贼豫,我故臣子,不讨则三纲大沦,何以为国?”[1](卷87,绍兴五年三月癸卯条,2册,236)从南宋朝廷一方来看,刘豫以“故臣子”的身份“造为事端,间谍和好。签我赤子,胁使征行,涉地称兵,操戈犯顺,大逆不道”,这样的行为是对君臣大义的决然践踏。所以针对刘豫伪诏所声言的“定议一统”、“务使六合混一”的狂言,高宗针锋相对地提出雪耻恢复:“尚念祖宗在天之灵,共刷国家累岁之耻,殪彼逆党,成此隽功”。高宗这种主动的、强硬的态度在同月丁巳的手诏中再次得到明确地强调:“朕不敢复蹈前辙,为退避自安之计”:
朕以逆臣刘豫称兵南向,警奏既闻,神人共愤。朕不敢复蹈前辙,为退避自安之计,而重贻江浙赤子流离屠戮之祸,乃下罪已之诏。亲总六师,临幸江滨,督励将士。[1](卷82,绍兴四年十一月丁巳条,2册,147)
正是在高宗坚定的抗敌态度之下,在宰相赵鼎、张浚等人的全力支持配合下,南宋取得了“士气大振,捷音日闻”[1](卷82,绍兴四年十一月戊午条,2册,148),“将士致勇争先,至于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1](卷83,绍兴四年十二月乙未条,2册,162)的大好形势。绍兴四年十二月,金人退师,“金军已去,乃遣人谕刘麟及其弟猊。于是麟等弃辎重遁去,昼夜兼行二百余里,至宿州方敢少憩。西北大恐。”[1](卷八十三,绍兴四年十二月庚子条,2册,164)
挫败伪齐与金人的联兵入侵,是南宋初期的大事件,无论是对南宋稳定地立足江南,还是最终与金人达成绍兴和议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高宗的决心与决定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保证南宋有序地、有效地应对敌人进犯的根本保证。
起用张浚以成事功
张浚一生忠义,建炎三年三月南宋朝廷内部发生明受之变。“扈从统制苗傅忿王渊骤得君,刘正彦怨招降剧盜而赏薄。帝在扬州,阉宦用事恣橫,诸将多疾之。癸未,傅、正彦等叛,勒兵向阙,杀王渊及内侍康履以下百余人……傅等迫帝逊位于皇子魏国公,请隆祐太后垂帘同听政。”[2](卷25,高宗二,462)在国家面临颠危的关键时刻,张浚约张俊、吕颐浩、刘光世、韩世忠起兵问苗、刘叛逆之罪,“浚乃声傅、正彦罪,传檄中外,率诸军继进。”[2](卷361,张浚传,11299),四月,复辟成功,高宗复位。在这一次事变中,张浚的勇气、胆识与能力得以充分展示。
张浚一生以恢复为己任,积极筹划对金出击之策。建炎三年七月,自请入川陕,“浚谓中兴当自关陕始,虑金人或先入陕取蜀,则东南不可保,遂慷慨请行。诏以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得便宜黜陟”。[2](卷361,张浚传,11300)建炎四年九月,张浚为解东南之困,谋引金兵于西以牵制之。“时金帅兀术犹在淮西,浚惧其复扰东南,谋牵制之,遂决策治兵,合五路之师以复永兴。金人大恐,急调兀术等由京西入援,大战于富平。”[2](卷361,张浚传,11301)但是,富平之战以宋师败绩而告终,导致南宋在川陕地区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方富平之败,秦、凤皆陷,金人一意睨蜀,东南之势亦棘。”[2](卷366,吴玠传,11414)。绍兴三年,朝廷遣王似副张浚,“浚闻王似來,求解兵柄。吕颐浩、朱胜非不悦浚,日毁之。诏浚赴行在所。浚力丐外祠,高宗弗许。四年二月,浚至。御史中丞辛炳,率同列劾,诬以危语。六月,以本官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居福州。”[3](张魏公传,4408)张浚虽斥逐于外,但其勇于自任、分画措置的治军能力却是为人所共知的:
张浚以枢府任川陕半天下之责,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以为定天下大计。虽赵哲离部,致有富平之败,而得刘子羽以保兴元,用吴玠以保大散关,遂有和尚原之捷,继有杀金平之捷,敌自是不敢犯蜀矣。[1](卷74,绍兴四年三月辛亥条引吕中《大事记》,2册,46)
浚在关陕三年,训新集之兵,当方张之敌。以刘子羽为上宾,任赵開为都转运使,擢吴玠为大将守凤翔。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财,而玠每战辄胜。西北遗民,归附日众。故关陕虽失,而全蜀按堵,且以形势牵制东南,江、淮亦赖以安。[2](卷361,张浚传,11301)
建炎初,潼关告警,羽檄交驰。浚以密院而任川陕宣抚之职。请任西事,分司秦州。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兴元一奏,勇于自任。擢刘子羽于参谋,而弛禁通商,输财济饥,熙如也。用赵開于总领,而民不加赋,军用自足,裕如也。而分画诸将,如吴玠、如王彦、如刘錡、如关师古等莫不属其指授之下。自是而捷于宝鸡、捷于箭栝、捷于和尚原、捷于杀金平,剑阁栈道赖以保全。此虽吴武安玠以下诸将战斗之功,而分画措置,莫非我魏公力也。而议者乃以秘阁崇儒,尚方铸印中伤之,虽圣明天子有“人言其过,朕皆不听”之论,而还朝以后,言者滋甚,浚不容不落职,出居外郡矣。[1](卷74,绍兴四年三月丁卯条引何俌《龟鉴》)
一方面是张浚“勇于自任”、善于“分画措置”、知人善任,其军事才能使其在金人与伪齐联兵入侵之际有了重新被任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又正当高宗决议亲征,“留意人物,固欲得贤士大夫协力以济国家之难”[1](卷81,绍兴四年冬十月癸未条,2册,129)的选任人才之际,于是,张浚的复出就成为必然的结果。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一,绍兴四年冬十月庚辰条记载:
鼎因称马扩极有才,可用。上曰:“宜令留守司使唤。”孟庾曰:“臣亦欲以此为请。”胡松年曰:“扩尝见臣,欲自将三千人御敌。”鼎曰:“扩尝因苗、傅事得罪。然诸葛亮能用度外人,区区庸蜀遂致强霸。”与求曰:“今日正当拔卒为将之时,臣闻扩持军严整,愿陛下留圣意,湔拭而用之。”上曰:“齐小白能忘射钩之仇,而用管仲。朕岂不能用扩?然能用之,止与三千人,非是,可令引见上殿,示以恩信,然后用之,彼必能效死力以报朕。”与求曰:“陛下驾驭诸将如此,何事不济?”鼎对曰:“陛下开大度用人如此,天下幸甚。”
高宗与赵鼎、孟庾、胡松年、沈与求讨论的是有关拔擢曾经受到苗、刘明受之变牵累得罪的马扩一事。其中赵鼎所言“诸葛亮能用度外人,区区庸蜀遂致强霸”,与高宗“齐小白能忘射钩之仇,而用管仲。朕岂不能用扩”的表态极为重要。度外用人、弃嫌用才是处于非常时期的南宋必须要具备的气度,也是高宗“开大度用人”,以期达到“示以恩信,然后用之,彼必能效死力以报朕”的最终目的所采取的必要措施或手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张浚的再起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绍兴四年冬十月,在赵鼎的大力主张下,张浚复起。“癸未,左通奉大夫福州居住张浚为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不许辞免,日下起发。赵鼎言:‘浚可当大事,顾今执政无如浚者。陛下若不终弃,必于此时用之。’故有是命。”[1](卷81,绍兴四年冬十月癸未条,2册,129)十一月“己未,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张浚知枢密院事。”“浚请遣岳飞渡江入淮西,以牵制金兵之在淮东者,上从之。及入见,上问鼎:‘浚方略如何?’鼎曰:‘浚锐于功名而得众心,可以独任。’于是上复用之。”[1](卷82,绍兴四年十一月己未条,2册,148)
然而,在张浚一面,富平之战失利之后一直受到持续不断的恶意指斥。早前,张“浚之在蜀也,尝以秦川馆为学舍,以待陕西、河东失职来归之士,给衣食养之。又新复州郡乞铸印,浚以便宜,先给而后闻于上。”这也成了绍兴四年三月张浚落职时被列数的罪恶理由。时任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舒清国所草张浚谪词有曰:“假便宜行事之势,忘人臣无将之嫌。肖内阁以招贤,拟尚方而刻印。”御史中丞辛炳复言:“浚之不臣,不窜之岭表,不足以塞公议。”于是,诏张浚福州居住。[1](卷74,绍兴四年三月丁卯条,2册,49)在当时,不仅朝廷上对张浚责难不已,就是在其下也是“下至草泽布衣之士,行伍冗贱之流,凡有求浚而不得者上书投牒,人人诟骂,肆言丑诋及其母妻;甚者指为不臣跋扈,极人间之大恶,皆归之于浚。”[4](174册,赵鼎《除宣抚处置使朝辞疏》,266)张浚的遭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就张浚本人而言,对于“加臣以大恶之名,陷臣于不义之地,隳臣子百世之节,贻孀亲万里之忧”的遭际悲愤委屈,“痛陨无已”:
先是,浚上疏辞免除命。且言:“臣以浅薄之姿,偶缘遭遇,寖获使令。仰惟陛下任之太专,待之过厚,而有怨于臣者窃毁之备至,有求于臣者责望之或深。上赖圣智之独明,乾纲之自断,保全微迹,不为废人。夫以失地丧师,累年无成,臣之罪恶,臣岂不知?至于加臣以大恶之名,陷臣于不义之地,隳臣子百世之节,贻孀亲万里之忧,言之呜噎,痛陨无已。训词所戒,传之天下,付在史官,臣复何颜,敢玷班列?”[1](卷82,绍兴四年十一月甲子条,2册,150)
绍兴四年八月,赵鼎在赴任川陕宣抚处置使之前,作有《除宣抚处置使朝辞疏》,其中就表露了对张浚事件的愤激之情:
向者陛下当建炎图治之初,遣张浚出使川陕,国势事力百倍于今。浚于陛下有补天浴日之功,陛下待浚有砺山带河之固。君臣相信,内外相资,委任之笃,今古无有,而终致物议,以就窜逐……今考究其用心,推寻其情实,丧师失地,错缪之迹则有之,未必尽如言者之甚也。大率专黜陟之典,受不御之寄,则小人不安于分义,谓名器可以虚授,爵赏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川蜀之士,至于醵金募士,诣阙陈论,展转相传,以无为有。一经指摘,何以自明?
张浚事件不仅对于张浚本人有如此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他人也产生了以之为鉴的负面作用:“有志之士虽欲冒犯死亡,为国立事,而每以浚为鉴戒也”。“夫以浚之功与陛下之信也,而谤者至此,则明君不能自信矣。”[4](174册,赵鼎《除宣抚处置使朝辞疏》,265)朝廷疑之、宰相不悦、同僚以宿憾毁短弹劾之,终将张浚经略关陕之功全然勾销。[5]在这样的状况下,在大敌当前、启用张浚之际,高宗的明确态度就显得格外重要。
张浚亲历谪贬的遭际,面对“不臣跋扈,极人间之大恶”等种种指斥,不免心怀恐惧怵惕之情,另一方面,对于朝廷和君主的忠义之情并未因得罪贬逐而更改,“浚虽得罪,犹上疏论敌伪暂和,心必未已。当益为备”,其奏疏仍然在为朝廷忠心筹划:“愿陛下早夜深思,益为备具。处将士家属于积粟至安之地,使出而战守者无返顾奔散之忧;精择人才,以抚川陕之师,使积年屯边者无懈惰怀望之意;江淮川、陕互为牵制,斥远和议,用集大业。”“臣奉使川陕,窃见主兵官除吴玠、王彦、关师古累经拔擢,备见可任外,其余人才尚众。谨开具如左。吴璘、杨政可统大兵,田晟可总一路,王宗尹、王喜、王彦可为统制。”[1](卷74,绍兴四年三月丁卯条,2册,50)
张浚爱国爱君的忠义精神与实际治军的能力,在南宋讨伐金齐入犯、急需拔用人才之际都是最佳的选择。所以当赵鼎向高宗提出:“陛下幸听臣言,骤用浚,恐台谏未悉,必至交攻。非陛下断自宸衷,无以息众议”之时,高宗便于绍兴四年十一月甲子手诏曰:
张浚爱君爱国,出于诚心。顷属多艰,首倡大义,固有功于王室,仍雅志于中原,谓关中据天下上游,未有舍此而能兴起者。乘敌首胜之后,慨然请行。究所施为,无愧人臣之义;论其成败,是亦兵家之常。矧权重一方,爱憎易致;远在千里,疑似难明。则道路怨谤之言,与夫台谏风闻之误,盖无足怪。比复召浚,寘之宥密,而观浚恐惧怵惕,如不自安,意者尚虑中外或有所未察欤?夫使尽忠竭节之臣怀明哲保身之戒,朕甚愧焉。可令学士院降诏,出榜朝堂。[1](卷82,绍兴四年十一月甲子条,2册,150)
高宗充分肯定了张浚的“爱君爱国”、“尽忠竭节”,既称其明受之变中“首倡大义,固有功于王室”,又赞其经略川陕“无愧人臣之义”。对于“道路怨谤之言,与夫台谏风闻之误”,给予辩白。这就遏制了于张浚不利的众议,为张浚复出后发挥真正意义上的作用扫除了障碍。
张浚复出,果然不负朝廷之望。他的声名威望对内激发起南宋将士的勇气:“浚遂疾驱临江,召韩世忠、刘光世与议,且劳其军。将士见浚来,勇气自倍。浚部分诸将,遂留鎮江节度之。”[1](卷82,绍兴四年十一月甲戍条,2册,155)对外则具有震慑力量:“始,粘罕病笃,语诸将曰:‘自吾入中国,未尝有敢撄吾锋者,独张枢密与我抗。我在,犹不能取蜀,我死,尔曹宜绝意,但务自保而已。’”[2](卷361,张浚传,11301)“初,张浚至江上,令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募军民,王愈、王德持书抵右都监宗弼所,为言张枢密已在鎮江。金人问愈:‘吾闻张枢密已贬岭南,安得在此?’愈出浚所下文书。见浚书押,色动,即以右副元帅昌书约日索战。”[1](卷83,绍兴四年十有二月丁亥条,2册,160)而且,张浚的无论是在战争中和战争后的实际指挥措置之功也为高宗所称道:
知枢密院事张浚奏捍御敌马次第,且言久相持,恐其别生奸计。已与诸将会议,凡可以克敌者无不为也。上曰:“浚措置如此,敌必不能遽为冲突。”沈与求曰:“晋元帝时,兵力未强。然石勒寇寿春,帝集将士相持三月,其下至有劝降者,王导拒之。敌远来,久相持非其利也。”上曰:“朕得浚,何愧王导!”[1](卷83,绍兴四年十有二月戊戍条,2册,163)
知枢密院事张浚奏金人潜师遁去,今已绝淮而北,见行措置招集淮南官吏还任、抚存归业人户等事。上曰:“刘豫父子强诱金人,拥众南侵,窥伺江浙,其志不浅,今乃一夕遁去,其所亡失多矣。然敌马方却,而浚已能为朕措置如此,可谓孜孜奉国,知无不为也。”[1](卷84,绍兴五年春正月丁未条,2册,168)
张浚一生孜孜奉国,力求恢复,不仅在反击伪齐刘豫的进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日后在孝宗朝亦有大建树。笔者在此借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四,绍兴四年三月丁卯条所引何俌《龟鉴》的言论评价张浚之功:
自张公之出行边郡也,今年命诸将观机会,明年檄诸将观兵势;今日召诸帅议军事,明日命诸帅分军屯。书押之示,敌人动色;号令之下,奔走惟命。不曰今日之事,有进击而无退保也,则曰若诸将渡江则无淮南,而长江与敌共也。大仪之役,伏兵四起,贝勒就擒;寿春之胜,展帜示之,敌众奔溃。镇江劳军,韩世忠移书乌珠,有张枢密在此之言,金人相顾失色,敌于是有雪夜之走采石;徇师之令一下,诸将以死鏖战,我于是有李家湾之捷。前乎富平之失,此魏公也;后乎江上之胜,亦此魏公也。人无愚知,作之则奋;师无利钝,激之则锐。兹非其验欤!
绍兴四年南宋击退伪齐与金人的联合进攻,在这次关键性的战役中,高宗的坚定不移、赵鼎全方位的筹划以促成高宗亲征之举、张浚忠义奉国,倾力向前、以及文武之臣的全力合作终于成就了这次战功。本文限于篇幅,只以高宗有关讨伐刘豫和起用张浚的手诏为中心,分析时事,得出结论,以见当时的南宋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并对高宗的对敌态度作出事实求是的评价。
[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Z].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宋史[M].中华书局,1985.
[3]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M].中华书局,2007.
[4]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Z].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5]陈忻.南宋宰相赵鼎奏疏的忧愤之情[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