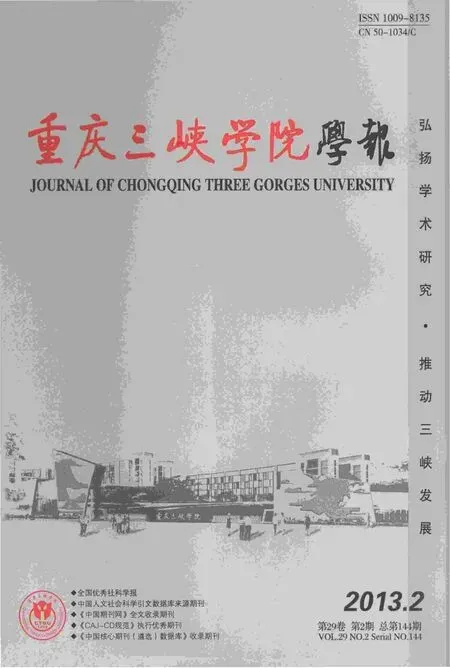正面宣传论的理论预设及其可行性分析
2013-04-01江卫东
江卫东
(华中科技大学,湖北武汉 430074;重庆三峡学院,重庆万州 404100)
“正面宣传”这一说法,当代中国人耳熟能详,基本上已经成为一种“日常用语”,对其内涵的理解大致是:所有“宣传”都是并且应当是“正面”的,使用正面的材料,追求正面的效果。这一思想的源头可谓源远流长,古代史志编撰中讲究“为长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恐怕也有同样的考虑。但“正面宣传为主”成为一种指导新闻业发展的“方针”,只能说是最近三十年的事。有学者考证指出,1989年11月李瑞环在全国新闻工作研讨班上的讲话是“正式提出并加以全面论述”这一“新闻宣传方针”的,并且“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方针,明确引领我国新闻传播事业长达20余年”。[1]这一讲话其实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讲的,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作为指导新闻工作的一种方针,推而广之,甚至教条化、绝对化,可能就会发生不少问题。比如,什么是“正面”,多少是“为主”,以及什么是“宣传”等概念内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实践上,其分寸也很难把握,让广大新闻工作者松紧失度、左右为难。对于这个理论和实践难题,各路专家学者和广大新闻从业者做了大量理论论证和经验阐释等工作,但似乎都忽略了对这一方针的“理论预设”进行思考和讨论,以至于很多论争限于盲目和无谓。
一、关于理论预设
所谓“理论预设”,即理论前提。被誉为现代逻辑学奠基者的德国哲学家弗雷格(Frege)首先对“预设”(presupposition)问题作出研究,他认为,“人们在通过一个句子做出声言时必然存在显而易见的前提,即在声言中所用的专有名词必有所指。”[2]377作为逻辑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最近30多年被引入到语言学研究领域,成为语义和语用研究的基本课题,所以预设又被分为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两种。简言之,本文所谓的“理论预设”,意指一理论的成立与否依赖于另外一个或几个不言而喻的观点或理论是否成立,若理论预设站不住脚,那么该理论也难以成立,成为一个伪命题。
关于“正面宣传”论的内涵,有很多繁琐复杂的分析,但归根到底,其核心内涵“亦即其本质,在于强调建构正确的舆论导向。”[1]换言之,以正面宣传为主,当然是“为了实现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为了获得宣传者所希望的正面效果。然而,这效果最终要落实在受众那里,不是宣传者简单地传播“正面”内容所能解决的。就好比“媒婆介绍对象”,能否成功“结婚”,最终取决于男女双方实际条件的适应情况以及“你情我愿”,而媒婆的“正面宣传”充其量只是建立一种认识关系的开端。大家都知道“媒婆的嘴是天下最靠不住的东西”,男女任何一方都会对媒婆的话思量再三、甚至要“实地考察”一番的。拉斯韦尔说:“成功的宣传有赖于在适宜的条件下对各种方法的巧妙运用”[3]155,正面宣传要想取得正面效果,当然也依赖于诸多前提条件以及具体操作方法、运用艺术等的限制,其中,其理论预设是否成立,成为考察其命题真伪或能否取得预期传播效果的试金石。
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正面宣传论的理论预设进行一番深入的分析和探究。
首先,传播者进行正面宣传决策前,必然认为作为宣传对象的受众心智不成熟,善恶不分、是非混乱,是需要“教育”、“灌输”的,这是必要性的预设;同时,必然认为受众是孤立的、脆弱的,面对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的宣传教育攻势,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的,这是可能性的预设。其次,如果传播者不仅仅是个信息传者,而且还是个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威权政府”的话,那么他的正面宣传就具备无可置疑的权威性,因为在其宣传背后矗立着的硕大无朋的国家机器,对任何叛逆或异见都构成某种强大的压力和威慑。在这种情境下,必然发生“沉默的螺旋”效应,正面宣传的效果可能会比较好,这是传播者权威性的预设。第三,正面宣传要想产生正面效果,除了上述受众预设、传播者预设之外,还必须存在一个传播环境的预设,即必须存在一个信息渠道单一、甚至是唯一的传播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只有一种声音,不可能存在与此种正面声音不一致的不同声音或负面声音。因为传播者所梦想的正面传播效果的大厦是建立在“肥皂泡”之上,负面声音的出现就像一根针,必然会戳破那个美轮美奂的“肥皂泡”景观。
下面,即对上述三个理论预设展开具体分析。
二、受众预设
19世纪后期,美国进入大众传播时代,产生了一种传播理论,即“大众社会”理论(mass society theory)。该理论提出了关于个体、媒介作用以及社会变迁本质的几个基本假设,其中一个重要的假设即认为,一般受众因为脱离了传统体制的保护而变成了孤立、脆弱的个体,所以他们难以逃脱大众传媒的影响和操控[4]50。在这一传播理论的基础上,1920年代美国又出现了一种称之为“魔弹论”(Magic bullet theory)的宣传理论。该理论同样把受众看成是软弱无力的,难以抵抗大众传媒旨在影响和改变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宣传攻势,“外部刺激,就像大众传媒所传播的那些信息,能够让任何一个人以一个宣传大师所希望的方式那样行动”[4]77。
同样,正面宣传论的理论预设也认为一般受众是孤立而脆弱的,其心智如同婴儿一样不成熟,需要社会精英的引导和革命政党的教育,否则,他们自己无法辨别是非,判断善恶,掌握真理,甚至无法认识自己的利益所在,更不可能获致“真正的”幸福和未来。
那么,作为信息接受者的人民大众,是否具有独立理性、从而具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还是相反,他们只是“群氓”、从而必须处于“受教育”、受训导的地位?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古今中外不外乎两类,一类即前现代传统社会主张后者,认为人民大众无知无识,必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如中国儒家政治文化认为君民之间的关系应当像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君主对人民“应该像父母对待子女那样实行道德教化”,臣民对君主“应该像子女对待父母那样恭敬”[5]63;另一类即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力主前者,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特的、有理性的,因而是平等的,通过自己的理性判断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托克维尔说:“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6]7近三百年以来世界潮流的发展大势,用国父孙中山先生话说,民主自由“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人民大众成为历史发展的主人,人民有能力认识自己、实现自己,从前那种“以吏为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所以,不论是“大众社会”理论、“魔弹论”还是正面宣传论,这些理论假设都被近代以来政治学的新发展、20世纪中期以后传播学实证研究以及接受美学受众研究等所否定。也就是说,一般受众并非那么被动、脆弱甚至弱智,相反,随着文化和教育的普及、民主运动的深入以及各种利益团体的形成,广大受众的素质不断提高,理性思考能力不断增强。他们面对各种媒介传播和宣传,是积极的、批判的解读者和文化意义的创造者,大众传播的宣传效果其实没有那么强大、直接和可怕,对受众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受到种种因素的局限和制约,效果如何尚无定论。
三、传播者预设
根据社会学家孙立平的观点,解放后到改革前,中国实行的是一种“总体性社会体制”,“是以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和垄断为基础的”。这种“总体性社会”(total society)形成了国家直接面对民众的两层结构,“国家对民众的关系表现为直接的总体性控制和参与式动员”,国家具有高度的社会动员能力,而民众则对国家形成了“组织性依附”,同时在信息传播方面形成了强大的由上而下的单向沟通系统[7]。简言之,在这种“总体性社会”中,国家或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民众从生到死所需的一切资源全部仰仗于政府的供给,因此,政府为了实现自己提出的各种目标所开动的“正面宣传”机器,一般而言是非常高效的,民众只有顶礼膜拜而不可能有所质疑。
可是,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展开,原先的“总体性社会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虽然直到目前为止,一些至关重要的资源仍控制在国家手中,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资源流入民间。这些由民间多元拥有的非国家垄断资源,使得社会成为一个与国家相并列的提供资源和机会的源泉,同时,在‘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基础上,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正在开始形成。这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正在开始构成当今中国民间统治精英的雏形。”[7]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新的独立社会力量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国家、社会和民众的面貌和关系,政府那种“神圣的权威性”风光不再,利益的多元化必然导致声音的多元化,当权者一厢情愿的“正面宣传”也就无可挽回地走向式微。比如,作为正面宣传的一种重要体裁的“典型报道”,曾经在中国新闻媒介上红得发紫,对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产生重大影响,现如今,在广大受众中逐渐失去公信力,就是一个例证。陈力丹认为,“支配典型报道及其观念的是小农经济及其要求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政治意识”,并预言“典型报道观念是文明程度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它将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步消亡。”[8]165
四、传播环境预设
长期以来,我国的媒体上只有一种声音,基本上是正面的声音,毫无疑问,这是贯彻“正面宣传为主”方针的必然结果。于是,一个段子便广为流传:“我有一个梦想:永远生活在新闻联播里,那里的孩子都能上得起学,穷人都能看得起病,百姓住每月77元的廉租房,工资增长11%,大学生就业率达到99%。我想永远生活在新闻联播里,那里物价基本不涨,交通基本不堵,环境基本改善,罪犯基本落网。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埋在新闻联播里。”这里,广大公众对官方千篇一律的正面宣传的嘲弄和不信任,一目了然。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针对这一现象就提出过发人深思的反问:“为什么资产阶级报纸敢于把我们骂他们的东西登在报纸上,而我们的报纸却不敢发表骂我们的东西呢?”[9]358
如果说这种正面宣传曾经产生过一定正面效果的话,我想与曾经国人所处的封闭的信息环境有决定性关系。封闭的环境,只有一类信息,人们无从比较、无从辨别,正面宣传比较容易自圆其说,因而有可能俘获一些简单的头脑。然而,著名报人张季鸾指出事情还有另一方面,“其一,宣传过于统一严整之结果,人民神经久而麻痹,反使宣传失效;其二,报纸专为政府作宣传机关之结果,全国言论单调化……最后促使报纸失去信用。”[10]412不仅如此,张季鸾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政治上的危害:“压迫批评,专听歌颂之辞,对于治者来说,在政治上为自杀之道。”[10]408
尤其是在当下新媒体应用方兴未艾的信息化时代,一方面,信息环境由封闭转变为开放,众多声音扑面而来,不同角度的真相纷然呈现,微博等社交媒体上越是负面信息越是容易获得热烈追捧;另一方面,“当下时代的话语方式的基本特征是断裂,即不同群体的话语方式截然不同,仿佛来自两个星球”[11],特别是“政府与民间的话语断裂”[12],使得政府宣传的公信力大打折扣。这时,正面宣传还想取得预期效果,简直是天方夜谭;甚至更会激发人们的逆反心理,偏要对那些正面宣传作负面解读,张季鸾说“当局滥用宣传,恶化新闻,其恶影响是迫使报界专在社会黑暗面逞其笔锋”[10]408,正是指的这种情况。其实,英国文化研究的杰出代表人物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与译码理论”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指出,在一个自由开放的信息环境中,“受众对媒介文化产品的解释,与他们在社会结构的地位和立场相对应”[13]421,当今中国所处转型时代导致的社会结构变迁和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出现,必然带来对文本的多元化解读,正面宣传所追求的那种高度统一的正统主流化宣传效果,恐怕是真的勉为其难,或者无功而返,甚或适得其反。
综上所述,正面宣传论认为正面宣传必然产生正面效果,其隐含的三个理论预设,即受众心智不成熟需要教育引导、总体性社会的政府权威无可质疑、信息传播渠道单一而受众无法接触负面信息,其实存在种种问题,因此,建立其上的正面宣传论是否能够成立的问题值得深思和探讨。
[1]张勇锋.舆论引导的中国范式与路径——“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新探[J].现代传播,2011(9).
[2]熊晓华.广告用语中的预设理论及其效应[J].安徽文学,2008(3):377.
[3]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M].张洁,田青,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Stanley J. Barran & Dennis K. Davis.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Foundations,Ferment andFuture,Third Edition[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5]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
[6]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7]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5864,2012-05-28.
[8]陈力丹.淡化典型报道观念和再谈淡化典型报道观念[C]//陈力丹自选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9]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Z].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10]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11]http://book.ifeng.com/culture/1/detail_2 010_04/08/514987_0.shtml,2012-06-09.
[12]http://www.shekebao.com.cn/shekebao/node 197/node207/userobject1ai2835.html,2012-06-09.
[13]张国良.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