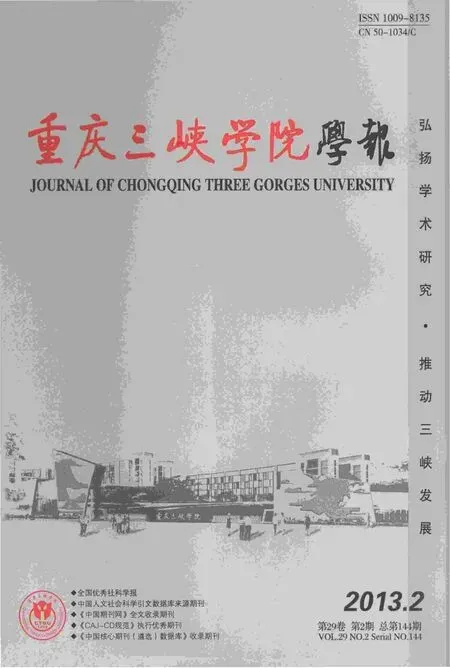论毛姆中短篇小说的创作特色
2013-04-01王燕
王 燕
(四川泸州医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泸州 646000)
一、陌生化叙事——云谲波诡的文本叙述
虽然毛姆被公认为是“写实主义”作家,他自己也曾坦言小说创作尤其是小说取材与真实生活的渊源关系,但他并不止于追求对真实生活的“照相机”式还原,相反,在其中短篇小说中,他不遗余力地采取各种陌生化手段进行叙事,从而赋予其文本叙述和写实主义创作以云谲波诡的创新异质。
这种陌生化叙事首先表现在文本中。毛姆总是以“虚构真实”之名,拉开文本与读者的距离,使其站在一个更加公正客观的立场能动地解读文本,在充分调动想象的同时深度区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于是,读者在毛姆中短篇小说中“虚构与真实悖反之言”随处可见。如《露水姻缘》中先借“尽管我跟下面讲的这个故事压根儿没有什么联系,但我还是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叙述,因为在读者面前,我不想装样,强不知以为知”[1]45,表述自己叙述的真实立场,继而又以“整个故事的情节就是我要讲的这一些,至于产生这些情节的原因,我就只好进行猜测了。读者读完小说以后,或许认为我的猜测是错的,但谁能保证自己的猜测完全正确呢?”[1]45说明叙述之不可靠性;又如《外表与事实》中开篇即以“从英国某大学讲授法国文学的一位教授那里,我听到了下面这个故事;至于它的真实性,我不敢担保。不过那位教授品格高尚,如果不是确定可靠,他是绝对不会讲给我听的”[3]76,阐释文本叙事的绝对真实和可靠性,但紧接着却马上以“他向来引导学生们对三位法国作家感兴趣,因为照他看来,法国的民族性格就体现在这三位作家的作品之中。他认为,读了他们的作品,你就能够十分了解法国人民。教授说,要是他有权力的话,他就规定:谁要想上台当政的话,就得先通过关于这三位作家作品的严格考试,否则,他才不相信那些跟法兰西民族打交道的人呢”[4]76。戏谑之语消解权威的真实,直言故事的虚构性与复述之不可靠性。
表面上看,这些虚构与真实之悖论消解了其中短篇小说的真实性,实则不然。正是在这种虚构与真实的悖反中,读者得以从“被动阅读”的窠臼中解放出来,全面领悟艺术真实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本质特性。
其次,戏剧性结局是这种陌生化叙事之又一表现。一方面戏剧创作的成功经验使得毛姆对戏剧性情有独钟,另一方面出于对戏剧、小说等艺术创作的共性的深度把握,使得毛姆不仅在理论上将戏剧效果视作理想追求,“作家并非只是踏实地记录生活,而是要将生活演绎成戏剧,因此,他宁愿牺牲可信度也要照顾戏剧效果,他所面临的考验就是既让读者觉得可信又能实现艺术效果”[2]133,而且在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实践中也乐于以戏剧性结局“背离”读者期待,在创新文本叙述的同时,丰富读者体验。因此,他的中短篇小说往往在故事发展至高潮之时,突然逆转,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
如《整整一打》中玩世不恭的重婚犯埃利斯眼看不能实现自己要找“整整一打”女朋友的愿望,却因为波切斯特小姐的“自愿上钩”而如愿以偿,委实让坚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读者猝不及防。又如在《外表与事实》中,苏尔先生发现情妇李塞特背地里与其他男人有染后,不是如同读者所预料的那般大发雷霆,进而抛弃或惩罚李塞特,而是为了虚荣心,主动撮合她与情夫结婚。如此一来他觉得他的情妇就不再是一个小小的时装模特,而是一位体面的太太,不是别人欺骗他,而是他欺骗了别人,自己的名誉保住了,获得了奇怪却又情理之中的心理平衡和满足。
再次,元叙述和互文也是造就毛姆中短篇小说陌生化叙事的重要因子。作为一位艺术家,毛姆似乎酷爱“授人以渔”胜过“授人以鱼”,故而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中他总是有意无意言明自己的创作过程和创作观,在使文本实现陌生化效果的同时,最终形成元叙述和互文特色。
如在《外表与事实》开篇,专门用大段文字解释文本命名与英国哲学家布雷德利的哲学著作同名的渊源,直陈自己对这部哲学著作的看法,读起来费劲,却发人深省,英语地道,妙趣横生。又如《蚂蚁和蚱蜢》开篇就谈“我”关于拉·封丹同名寓言寓意的理解和观点(不认同其“勤奋会得到报偿,而游手好闲则要受到惩罚”的寓意),以此指涉文本创作源起,继而又以此为基点,依托乔治的烦恼(自己勤奋却劳无所获,弟弟汤姆游手好闲却少劳多得)言明自己的创作意图:驳斥寓言中蚂蚁谨小慎微的处世态度是好的,人们一般得来的社会生活常识是正确的观点,表明生活未必是公平的。再次,如《人性的因素》中“我”除了多次表达对卡拉瑟斯创作的不屑一顾以外,还直接阐述他关于小说创作的见解:“我喜欢有开头、有发展、有结尾的故事,还喜欢言之有物。我想,环境描写固然重要,但只有环境而无其他就仿佛只有镜框而没有画,这就没多大意义了”[1]240。
二、悖反的张力——矛盾立体的人物形象
在《三位日记体作家》中,毛姆曾如是说:“可是人从来都不是平板一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小说家的任务会更加简单——但小说也会更加无聊。人身上最为奇怪的是,最一致最不协调的品质往往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所以这人似乎是一团矛盾,让人不明白这些品质到底如何共存,如何能融合在一起成为某种始终如一的个性”[2]195。毛姆一语道破人之矛盾立体性,执此观念,他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中着力塑造了一系列悖反的人物形象。
其一,这些人物的悖反性表现在人物类型的多重众相上。在毛姆的中短篇小说中,虽然人物类型繁多,不仅种族相异,有白人、黄种人、黑人等;身份不一,有官员、贵妇、平民、罪犯、学生等;职业有别,有律师、外交官、模特、股票经纪人、邮递员、医生、殖民者等;而且性格差异悬殊,有的骄横跋扈,有的盛气凌人,有的谨小慎微,有的好吃懒做,有的郁郁寡欢,有的冲动急躁,有的杞人忧天,有的乐观豁达。表面上看,这些人物类型很难走到一起,但却因为旅游度假、宴会沙龙、疾病治疗、作奸犯科等机缘聚合在一起,并受“自我表达欲望”的共性驱使,或各说各话,将对方置于冲突地位,由此充分展示人物个性,揭示其个性形成的深刻渊源。
如《大班》中,洋行经理自以为自己是个重要人物,因此抱着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歧视中国人,看不起职员和下人,一心想谋害上司取其位而代之,最终却因为“公墓恐惧”而僵死办公室中。又如《蒙德位古勋爵》中蒙德拉古勋爵在“数落”和侮辱自己的同事格里菲思致其毁灭性打击,及以外交官的高姿态粗暴对待奥德林医生后,最终死在自己恐惧的噩梦中。
毛姆创作中或用“异极相吸”的手法,看似完全悖反的人物最终出人意料地成为夫妻或者朋友。如《整整一打》中埃利斯和波切斯特小姐无论是在身份职业、性格特征还是道德观念方面,均有天壤之别:前者是平民百姓,玩世不恭、妄自尊大且道德败坏;后者是贵族子女,用情专一、循规蹈矩、品行端正,完全处于悖反地位,但最终却因为埃利斯的“执着式玩世不恭”和波切斯特小姐的“坚守的崩溃”,两者选择结合私奔。
通过塑造和描绘人物类型的悖反式张力,毛姆的中短篇小说不仅人物类型多样化,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这些类型人物一反传统类型人物“扁平”形象,构造出一座矛盾立体的人物画廊。
其二,这些人物的悖反性表现在单个人物的多重矛盾性格之上。只要稍加审慎,不难发现无论是毛姆的中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表面上看,这些人物优雅正直、诚实善良、富有教养,受人欢迎,实则又都带着各色各样的面具,如贪婪、狠毒、虚荣且自私自利等,人物的“缺陷”非常明显。如《午餐》中女人既想骗取一顿丰盛的午餐,又不想失面子,于是假借崇敬之名,采取“欲擒先纵”的方式以退为进,屡次得寸进尺,直至花光我一个月的积蓄。临走之前,她还不忘以“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姿态劝告“我”要像她那般少吃。一个贪婪且虚伪的女人形象便跃然纸上。
又如《患难之交》中看似正人君子、深受众人欢喜的伯纳明知道自己公司没有空余职位,无力给穷困潦倒的特纳提供差使,但却又不直接加以拒绝,而是抱着“置人于死地”的戏谑和狠毒心态,让身体虚弱至极的他冒险转着水流湍急的灯塔游泳一圈,结果让其死不见尸。由此在表面的“善”与深层的“恶”的巨大悖反张力中,伯纳之“恶”昭然若揭。再如《信》中被众人认为气质不凡、品行良好的克罗斯比太太,明明是出于仇恨狠毒残酷地杀死了情夫哈蒙得,但她却假借众人对哈蒙得的“恶评”和利用丈夫的同情心,取得法律的宽恕和人们的同情。她面对法官乔伊斯的询问,如实招供气愤及杀人经过;面对释放后乔伊斯太太的安慰,假意感谢,嫉妒、虚伪、狠毒的立体形象由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为了让中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更加深入人心,毛姆除了着力塑造立体化“缺陷”人物之外,还坚持以“矛盾性格”为基点,刻画悖反人物,赋予其丰满形象内涵,启发读者深思人性之弱点。如在《人生的残酷现实》中,他就塑造了一个“矛盾”的亨利形象:他既希望涉世未深的儿子一切顺利,又希望儿子遭受挫折;既希望儿子平安无事,但又为儿子虽然没有听从自己的忠告,却相安无事且利益双收(占了一个女人的便宜和赢得了两万六千法郎)深感烦恼。又如《插曲》中因为彼此相爱,弗雷德和格蕾丝一个铤而走险,不惜触犯法律取悦心上人,一个誓死苦守,甘愿放弃优裕生活从事艰苦工作。苦等良久后,两个有情人眼看就要成为眷属,但弗雷德却性格姿态突然逆转,生发出对格蕾丝的厌恶,进而背弃盟约,致死后者自杀。由此可见,毛姆笔下人物“矛盾性格”之深,深入骨髓。
三、结 语
毛姆的中短篇小说不仅以“虚构的真实”、戏剧性结局、元叙述和互文等陌生化叙事赋予其文本叙述异质特色,创新了读者的阅读体验,而且在展示类型人物的多重性格和悖反张力中塑造了一批矛盾立体的人物形象,使其小说超越了传统小说“扁平式”的人物描绘。毛姆小说创作特色的卓绝表现,值得后人研究。
[1]毛姆.毛姆小说集[M].刘宪之,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
[2]毛姆.观点[M].夏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