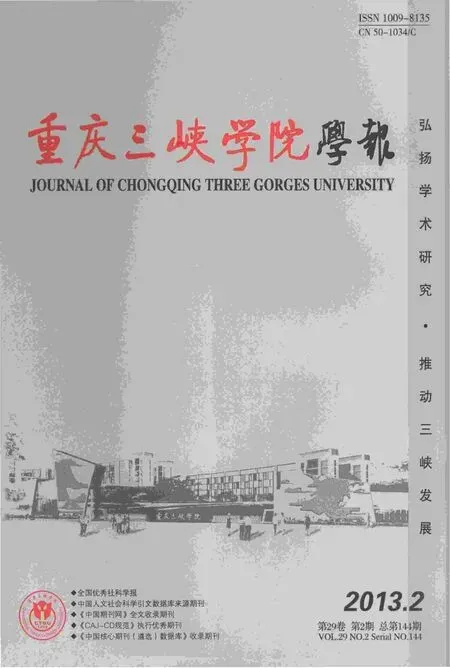大众文化对羌族传统节日传承与发展的影响
2013-04-01詹园媛
詹园媛
(西南民族大学预科教育学院,四川成都 610041)
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形态逐渐进入中国,后工业社会中的大众文化现象越来越牢地占据了中国大众的生活空间。西方大众文化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在强势的大众文化的影响下,作为羌族文化重要载体的羌族传统节日呈现出新的形式。羌族传统节日的传承与发展正面临着机遇和挑战,这就要求我们把握好大众文化与羌族文化的契合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动和促进羌族传统节日的传承与发展。
一、羌族传统节日传承与发展现状及意义
我国少数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丰富多彩的传统节日,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与本民族的宗教、历史、社会、饮食、服饰等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传统节日作为一种载体和复合性的文化表现形式,居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框架的核心位置,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粹都附丽在、展现在完整的节日活动之中。”[1]可以说,传统节日(如羌族传统节日瓦尔俄足节和羌历年)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缩影,是各族群众进行物质生产和精神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是各族群众相互了解、尊重及传承和发展文化的重要途径。
5·12特大地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国内外众多学者也深入到四川阿坝州羌族地区进行考察和研究,全力抢救、保护和传承这个“云朵上的民族”的文化奇葩。瓦尔俄足节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2009年10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羌历年正式列入了《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3]地震后,很多原生态的羌族文化遗产被损坏,保护、传承和发展羌族文化迫在眉睫。羌族传统节日既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还具有整合其他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实现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相结合的作用,同时也能传播和弘扬羌族文化,增加羌族的民族认同感,扩大羌族文化在海内外的影响力。
西方大众文化以一种新的文化态势冲击并影响着中国旧有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以其大众媒介性、商业盈利性、休闲娱乐性和强烈渗透性的特点从中国大都市发展延伸到全国各地。汶川地震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重视下,便捷的交通和强有力的宣传把羌族文化更多地展现人们面前,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游客来到灾区了解羌族文化。但与此同时,以大众媒介为依托的大众文化也在羌族地区有了愈加肥沃的生长土壤,以瓦尔俄足节和羌历年为代表的重要传统节日开始呈现出新的形态。在新的节日庆典模式下,羌族传统节日的文化底蕴更多地被形式化和表演化,原有的宗教信仰、崇拜英雄、历史沉淀等功能被弱化,这与羌族文化的传承本身是相悖和冲突的。当然,我们不能全盘否认大众文化,而应在中国大众文化主流思想引导下,把握好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时代发展契机,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羌族传统节日,让羌族文化为更多的海内外人士所了解,以羌族传统节日为平台拉动羌族地区经济发展,并对促进羌族文化的国际化交流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
二、大众文化语境下羌族传统节日的具体表现形式
(一)大众文化产生的背景及定义
大众文化的形态最早是在西方社会形成的,最早出现时间可以追溯到18和19世纪。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渐加剧,大众文化逐渐成为西方国家最独特的文化现象,打破了统治阶层和精英文化对文化的垄断。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研究者代表有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他们对大众文化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商业性、盈利性的文化,容易使人丧失自身的价值判断力,导致价值和信仰的危机。伯明翰学派在批判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压迫、虚伪和欺骗的同时,主张积极构建具有主体性、能动性和批判性的大众文化消费群体。后来,新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重新理解大众文化,重新审视大众传媒,对大众文化和大众传播持肯定乐观的态度。
总的来说,大众文化是工业社会以来与现代都市及大众群体相伴而生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物质依托的,受市场规律支配的,平面性、模式化的文化产品形式。国内很多学者在看到大众文化的弊端的同时,也提出大众文化的和谐价值,对大众文化进行解读并提出和谐发展的出路。
(二)羌族瓦尔俄足节和羌历年的新模式
与以往各村各寨各家各户庆祝瓦尔俄足和羌历年的“个体化”不同的是,现在采取的是政府参与主办的集体化模式。当地政府充分运用了大众文化的大众媒介工具,通过大量宣传,统一组织安排来扩大节庆的影响力。2009年的瓦尔俄足节持续一个星期,期间加入了歌手大赛、“萨朗姐”选美,瓦尔俄足庆典仪式及羌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等诸多活动,还有相关纪念邮票的发行、羌绣、羌文化摄影作品展出、演唱会等。表演者均是来自各个村寨的经过选拔的村民们,由当地政府打造安排,老师负责组织排练歌舞,还有大量媒体、专家、游客到现场,盛况空前。2012年的羌历年,由政府组织和安排,各个羌寨的村民们很早就排队来到茂县政府广场参加羌历年的庆祝活动,祭神喝咂酒、打起羊皮鼓、跳起热情的羌族锅庄,四川卫视及相关网站都进行了实时报道。很多当地人及外地游客纷纷拍照留念,尽情地感受着节日的气氛。
大众文化拥有四大特征,即:大众媒介性、商业盈利性、休闲娱乐性和强烈渗透性。这四大特征在现在的羌族瓦尔俄足节和羌历年的庆典中都有所体现:第一,大众媒介性。羌族传统节日的庆典对外界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很多媒体到场进行现场直播及其他方式的报道;其次,商业盈利性。节日庆典吸引了很多当地或外地的群众,观众构成具有异质性和多元性,针对节日庆典推出的相关文化产品受到关注,拉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第三,休闲娱乐性。众多参与者和观摩者中能真正了解庆典所体现的羌族文化意义的人并不多,很多都是抱着来看看来凑凑热闹的心态。第四,强烈渗透性。庆典参与者会不由自主地受到当时氛围的影响,产生愉悦感,主动自愿地接受安排来感受热闹的气氛。
三、大众文化利弊分析
(一)大众传媒对羌族传统节日文化的发扬与曲解
1.在当今多元化发展的社会,羌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必须借助大众媒介。大众媒介通过对羌族重要传统节日瓦尔俄足节和羌历年的宣传和呈现,让更多的羌族人树立了民族自信心,培养了民族认同感,同时,也让外族人更加了解羌族文化。
2.大众传媒并不是纯粹的形式,而是包含着价值和政治代码的形式,即一种权力关系的体现。例如,羌族的传统节日瓦尔俄足节是以祭祀歌舞女神萨朗姐为目的,也称为“歌仙节”,反映了羌族长期游牧及其农耕文化,带有妇女群体活动与母舅权大的特征。而在媒体的包装下,却给人一种笼统宏观的直观印象,节日本身的内涵被模糊掉了。同样,当今社会“美女经济”的火热宣传在羌族瓦尔俄足节上也得到了体现,在庆典仪式上正式公布了“萨朗姐”的选美排名,如果说羌族美女是媒体宣传的一个噱头的话,那也确实吸引了众人的眼球。如果在大众媒介的造势宣传下,羌族文化中的精髓变成一项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务,一场视觉听觉盛宴,一种人们娱乐猎奇的途径,羌族精英文化就会被逐渐弱化,保护民族精粹就永远无法实现。
(二)经济发展给羌族节日文化带来的收益与损失
1.通过对羌族传统节日的开发,既可以满足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又可以吸引了大批游客,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羌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传统节日的传承和发展也有了经费支持。
2.大众文化商业盈利性的负面影响,可能导致当地政府、开发商和村民在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上的偏差,常常表现为文化商品质量低劣,漫天要价,表演化增加,渐渐失去羌族人民原有的朴实、真诚、好客的优良品质,更多的是为了迎合外来游客的需求,以便获得更多更大的利润,而以往原生态的羌族文化易趋于被大众文化所同化。
(三)外来文化对羌族传统节日的丰富与侵蚀
羌族传统节日在政府的安排下进行大规模的造势和宣传,大批本地村民和外地游客包括很多国际友人都积极热情地参与进来,本地村民因为常年的风俗习惯已经非常熟悉节日的流程和内容,他们非常乐意向人们展示羌族传统节日的风采。在2009年瓦尔俄足节的大型庆典上,勤劳善良的羌族妇女在舞台上身着节日盛装,热情地传递着过节的快乐和愉悦,台下也有很多羌族村民前来观看。在2012的茂县羌历年庆祝过程中,很多非表演者也参与进来,尽情感受节日气氛,同时,在庆祝活动中,也出现了一些带有汉族文化特色的舞龙的表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羌历年的庆祝已经融合了部分他文化的元素,总之,在大众文化的语境下,羌族传统节日在自身文化展演的基础上,还带有一些更符合游客的休闲娱乐模式,众人可参与,大家一起快乐欢歌,一起品尝咂酒,一起跳舞扭胯。西方文化随着大众文化的发展也逐渐深入到羌族地区,很多西方节日如情人节、圣诞节等在羌族年轻人中也非常流行,他们忽略了自身的文化传统,往往只是作为看客来过节。羌族传统生活中的节日本没有观众,节日是大众的狂化,彰显了人们对生活的欲求和对生命的理解,建立在对羌族传统节日本质的理解上,一代代羌族人才能把节日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下去。但是如果传统节日过多的舞台化和模式化,很多本族民众就没有参与的机会,而适应了观看表演的方式。长期以往,羌族传统节日就会失去本族人的心灵精神支柱,那还有什么传承意义呢?
四、结 论
大众文化既给羌族传统节日的传承和发展带来契机,同时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我们既要充分利用大众文化的“正能量”,也要规避其“负能量”,找准羌族传统节日与大众文化的契合点,加强对文化产业及相关产业的管理和监督。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还需加强新一辈羌族人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宣传,提高他们的能力和审美情趣。只有建立在本族人对羌族文化精髓的掌握的基础上,羌族传统节日才能有更广更好的传承与发展的前景。
[1]刘魁立.中国节典:四大传统节日[J].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N].光明日报,2006-06-09.
[3]田廷广,周毓华.羌历年节日志——以“5.12”地震后直台村为例[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