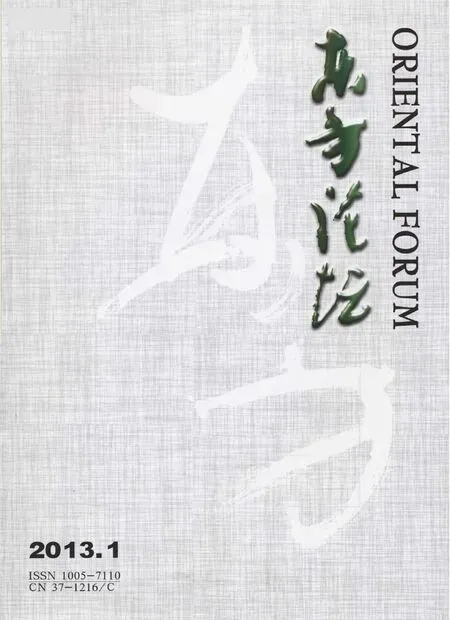读《嵇康美学思想述评》
2013-03-27吴海庆
吴海庆
读《嵇康美学思想述评》
吴海庆
中国古典美学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注精神和鲜明的人文关怀特色,这种精神和特色往往以两种对立的方式表达出来,即要么是把审美和传统的政治伦理价值相结合,把张扬政治伦理价值作为自己的目的,要么把自身置于传统伦理的对立面,强调艺术美对于伦理价值的超越性,突出个体自由与政治束缚的不可调和性。这两种方式都以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民的和谐生活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前者认为艺术与审美具有如风行草上的教化功能,后者以为艺术与审美只能通过陶冶个体情操、涵养人文精神产生如细雨润物般的效力。魏晋时期特立独行的嵇康的美学思想显然是属于后者的,近读卢政的新作《嵇康美学思想述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本书围绕和谐主题对嵇康美学思想展开的深刻阐释与我的感受非常切近,且书中能够把嵇康美学思想依托于整个中国古典美学的大和谐境界和处处透露着时代气息、个性品质的特色十分清楚而有力地表达出来。
首先,作者紧扣当时的社会思潮、政治境遇对嵇康美学思想进行解读和阐释,力求还原嵇康美学思想形成时的真实语境,准确地传达其追求和谐的思想精髓。
在人们的印象中,嵇康有一种狂放不羁的性格,生活实践中与世俗社会格格不入,所以嵇康的人格意趣似乎与和谐没有什么关系,然卢政的分析使人不得不放弃这种印象式认识。嵇康心中的理想人格是“至人”,卢政在书中把这种“至人”的特质概括为紧密联系的五个方面,即:志存高远、得志为乐、言行一致、任性而为、刚肠疾恶等。这五个方面细究起来,都是以和为本的,在《家诫》中嵇康说“人无志,非人也”,将确立正确的志向、高尚的理想、完善的人格看作锻造人生的第一要务,这实际上体现的是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要求作为个体的自我与整个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崇高希冀保持高度的和谐一致。这种一致不仅体现在精神与观念上,而尤其体现在不折不扣地实践行动上。得志为乐是践行理想时的顺利状况,而言行一致、任性而为、刚肠疾恶的“狂者”姿态反映的则是在实现自己的理想遇到阻力、困难时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应有的不屈不挠的固守与战斗行为,这种固守和战斗在嵇康看来可以使自己因问心无愧而赢得内心的宁静与和谐。在嵇康的眼中,“和”不是唯唯诺诺,隐匿自己的思想,压抑自己的个性,相反,为了反抗如司马氏之类飞扬跋扈的当权者和令人窒息的封建专制统治,必须与强权抗争,视阿谀权势的小人为仇雠。事实上,“尚奇任侠”的嵇康,最后正是以一种悲剧性的壮美,成就了其光耀中华民族历史的“硬骨头”形象。本书通过对“狂者”、“硬骨头”这些看似不和谐的形象的深入分析,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古代一大批嵇康式的知识分子追求大和谐境界的真诚与执着。
创作是嵇康表现自己和谐理想的重要方式,书中把嵇康的诗文美及对诗文美的追求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峻切豪壮、清远脱俗和辩雄理彰。古代当权者打着仁义道德的旗号干尽了非人道的勾当,至魏晋时期,司马氏主导下的朝廷更是趋于极端,如庄子所言,仁义道德成为“禽贪者器”,同时也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为了恢复我们民族和谐自然的天性,保持知识分子健康向上的活力,嵇康极力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从而促进了“重自然、尚超越、求和谐为特点的新的审美意识”的成熟。嵇康的美学主张无疑是对两汉时期确立起来的由统治阶级主导的伦理美学的颠覆,标志着中国美学史上一种新美学的崛起。经验表明,一种新的美学思想的诞生必然伴随着美学形式或美学风格上的创新,卢政在书中所概括出来的嵇康诗文美的特色正是这种创新一个方面。与其“唱反”品质和“异端”色彩相呼应,嵇康诗文在形式与风格上也必呈异彩,语言上峻切豪壮,“居高临下,旁若无人,喜笑怒骂,涉笔成文”,处处激荡着我们民族得自大自然的桀骜不驯的“龙性”,意趣上清远脱俗,与他那个时代“直窥人生本体的极有情致”的玄学丝丝入扣。
“声无哀乐论”是嵇康提出的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美学观点。对这嵇康一美学观点的是非对错,学术界历来争论不休。然而,本书并未陷于这种难辨是非的争论中,而是紧密联系于当时的社会实际、艺术实践与哲学新质等方面来阐明这一美学命题的本质与内涵。书中指出,春秋以降,以哀为乐,以悲为美的习尚绵绵不绝,到了汉魏之际,走向极端,马融《长笛酶赋》、蔡邕《琴赋》以垂泪为贵,曹操喜欢慷慨慨悲歌,曹丕酷爱悲笳微吟,正所谓物极必反,于是便有了嵇康在继承扬雄、桓谭、王充等人反叛精神的基础上展开的对悲情主义美学的批判,并提出了著名的“声无哀乐论”。嵇康这一美学命题的直接目的在于阐明音乐的本质特征是“自然之和”。嵇康认为,音乐的基本形式是旋律,即由声音的高低、长短、强弱以及音调和节奏等形成的节奏,好的音乐,其旋律无论猛静,都呈现为和。好的音乐根本上都源于自然之和,与人的和谐的自然天性是完全切合的,因而音乐便具有了对人“导养神气,宣和情志”的功能,可以把人的心灵引向恬淡、平和、宁静和优雅的境界,从而使人“处穷独而不闷”,获得美的享受。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从字面上看是一个较为纯粹的艺术哲学命题,但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则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现实命题,正如卢政在书中指出的那样,“声无哀乐论”本于时代的反叛价值,是对司马氏集团借名教伐异己之腐败政治的抗议,所以这一命题实质上不是要突显礼乐矛盾,而是要申明音乐与现实的强烈的不可调和性,是嵇康的和谐的社会理想与混乱污浊的现实相冲突所激起的思想火花。
其次,作者持守自己一贯的实践存在论美学立场,尽可能以全球化的文化视野来阐释、发掘嵇康美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努力使古代传统文化转化为一种当代文化力量。
以朱立元先生为代表的我国当代实践存在论美学认为,马克思的存在论特色主要体现在始终从实践出发审视人的存在,从具体的社会关系出发来思考人的存在。卢政的《嵇康美学思想述评》一书正是坚持通过对嵇康的生存环境和所处的现实社会关系的研究,来阐明嵇康美育思想的合理性和实际价值的。书中指出,嵇康的美育理论作为魏晋时代美育思想潮流的代表,以促进个体的自由和谐发展、提高人的生命质量为宗旨,淡化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主张通过美育把主体内在的才性、气质、智慧和精神风貌等调整到最佳状态。嵇康美育思想关注的重心是个体的生命与生存,他认为从小的方面说美育可以修性保神、安心全身、体逸心冲、形神相亲;从大的方面看,美育则可以使人达到大道无为,与自然合一的境界,而这才是个体的人生最大的幸福和最好的意义。当然,个体的生存离不开社会整体,个体美育与社会美育环境息息相关,因此,嵇康也充分论述了社会美育问题。嵇康认为,社会教育的根本目标是让异化的社会回到自然之和的状态,但是,当时的德教和礼教都是与人的自然天性相悖的,是虚伪的,这时,只有没有哀乐内涵的非道德性的音乐能够以其所依托的自然之和来主导和统一真善美,因而只有以音乐为中心的艺术与审美教育才能够担当起移风易俗的责任,恢复人格的自然基础,促进社会的整体和谐。
书中指出,对于嵇康美育思想当代意义的判断,应当立足于当下的社会现实特点。我们的社会已经步入价值多元时代,虽然我们的社会仍然有自己宣扬的普世价值和伦理规范,但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和价值立场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都受到或即将受到尊重。从现在和未来的社会关系来看,卢政认为应特别关注嵇康美育思想中关于“个体本体”的精神观念。嵇康美育思想以个体本体为中心,从个体本体出发探讨美育的社会价值与时代作用,以此反观当下的中国美育,显然是在重复着历史的习惯性错误。这主要表现在我们现在的教育仍然以社会实践、集体理性规范来排斥个体的感受性,以社会和民族利益消解个体的需要,这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环境及社会的发展趋势。当代美育要获得充分的现代性,就要以史为鉴,突破一般理性主义的樊篱,充分把握现实社会关系,关注个体的需要、个体的自由、个体的精神性、个体的生存目的以及个人的心理建设等,从操作层面上看,就是要更多地通过艺术与审美教育使人们对于人的存在价值形成更强的自主表达的意愿和更好的自由表达、自我确证的方式。总之,作者从实践存在论美学视角解读嵇康美育思想,既在实际运用中丰富了当代存在论美学的内涵,也找到了理解嵇康美育思想的新的源泉。
第三,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富于辩证精神,魏晋玄学尤以发幽辨难著称,嵇康美学思想既从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的思辨方式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又直接受到玄学思辨方式的启示,从而使其美学形成了“辨雄理彰”的特色,本书能够抓住嵇康美学这一集民族性、时代性和个体性于一体的特征,纵横捭阖,正反递论,推陈出新。
中国古典美学所追求的和谐不是抽象的、静态的,而是具体的和动态的,也就是说和谐必然是经由对立面的斗争而达于统一的动态过程,要阐明这一过程的普遍意义,就必须对这一过程具有十分深刻的认识、辩证的理解和细致、精准的把握。嵇康在阐发自己的和谐审美观时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由于嵇康的文章多是针对具体问题有感而发,所以其理论的逻辑形态并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本书作者通过对材料的归纳和分析使其辩证的逻辑思维形态昭然可见。
书中指出,嵇康的和谐美学观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内心世界等各个方面与环节的整体和谐,是一种大和谐。人与自然之间要建立和谐的关系,最主要的是要解决好情与物的矛盾关系。千百年来,人们竭尽所能来满足自己的物欲,这从总体上来说是自然的,合理的,然而,也不可否认,在很多情况下,人对物的追求并非自己的本性所需,而是在贪婪的心理欲求的驱使下进行的掠夺性攫取,这种超越本性的对外物的贪婪追逐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冲突。嵇康认为,实际上,人的幸福,人的真正的“富贵”不在于对万物的形式上的占有,而在于“意足”和“通物情”。人与万物同禀元气,其情可通,如若人能通万物之情,“与天下同于自得”,那便是“意足”,只有“意足”的人才是世界上最为富贵幸福的人。
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要建立和谐的关系,嵇康认为主要是处理好抑与导的关系,就是说,对于个人过度的欲望与情绪必须适当抑制,对于人的合理的欲求则应该正确引导,抑其所遁,导其可奉,整个社会便可“远近同风”,个体欲求与社会普遍价值便可达于一致。嵇康的这种思想与儒家一贯的中庸主张是一致的,嵇康的特别处在于充分肯定生命个体的地位,把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置于自然之和的基础上,主张通过艺术与审美的方式使人在自由中实现自律,而不是以道德约束的方式强制性地使个体服从于社会和威权。
对于构建个人内心和谐的途径问题,嵇康也是以辩证的思维方式,寄托于对公与私,或者说“显情”与“匿情”这对矛盾的正确处理上。所谓显情与匿情,卢政书中的解释是显情即“显露自己的真实情感,敞开自己的心扉,以坦诚之心待人,超越世俗,只按照自己内心的愿望去做,越名任心,放浪形骸”,而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就是匿情。在嵇康看来,一个人越是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越说明他是有公心的,越是有公心的人,也就越容易导养神气,“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声无哀乐论》),使自己的内心世界淡泊清纯。
通过这样辩证的分析和研究,卢政的《嵇康美学思想述评》一书不仅阐明了嵇康美学思想的要义,而且从中合理地导出了生态平衡、生态和谐的当代美学意蕴,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千百年来中国美学精神的历史传承与变革趋势,听到了古人与今人在面对相似的生存问题时发出的共同心声。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