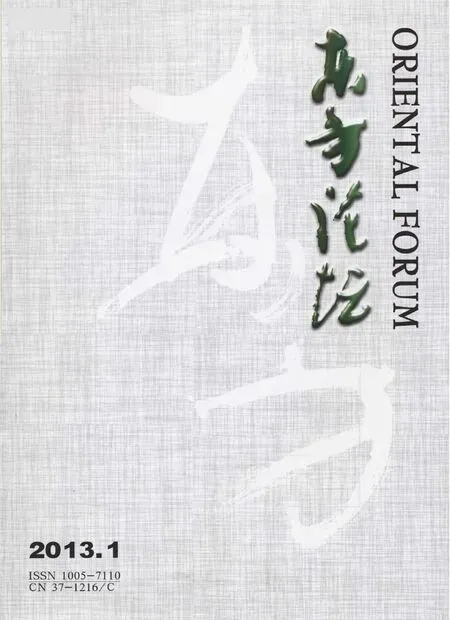古今维吾尔语心理范畴词汇内部概念关系研究
2013-03-27彭凤
彭凤
(新疆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54)
古今维吾尔语心理范畴词汇内部概念关系研究
彭凤
(新疆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54)
古今维吾尔语言心理范畴的词汇在形式特点上自主地区分为两个次范畴:其一,动词性词汇形式表达的是个体心理活动的经验范畴概念;其二,名词表达的是人们对心理现象的认知范畴概念。这两个次范畴的概念关系发生了古今的变化。古代回鹘文献语言心理范畴词汇形式表现出的概念关系恰恰记录了该民族对抽象心理活动经验内容自然认知的过程。
维吾尔语;历时对比;心理范畴;概念关系;认知语言学
古今词语的对比,一般是在两个有确定演化或替换关系的词语之间展开,考察语音的变化、语义的更变,似乎没有语音演化关系的语言形式是没有办法展开历时对比的,这是传统的结构主义研究者在历时研究过程中,把视角仅局限于语言形式,在它们之间建立对比共项“同中求异”的结果。浑沌语言文化学却为没有语音演化关系的古今语言形式的对比提供了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它从范畴着眼考察古今词汇,使得古今无语音演化关系的词汇有了对比基础(相同的概念范畴)。
一、古回鹘文献语言心理范畴的词汇特点
在李增祥、买提热依木等合著的《古回鹘文文献语言简志》①李增祥,买提热依木,张铁山著,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中,我整理出了心理活动范畴的词汇表现,由心理活动的词语加缀构成表示对人类情感、意志结构认知的名词概念,并已经以绝对的数量呈现出一种规则性,抽象心理范畴的名词都表现出派生性特点。古代回鹘文献语言中表示抽象心理名词的形式有:
(一)由表心理活动的动词加反身态词缀“n”,再缀加名词的构形词缀变为抽象心理名词。(这些词汇大都出自回鹘佛教文献)
例如:
(1)ög(ü)rünčü“高兴”(AYC226/2), 由Őg(ü)rünč“兴奋”(AYC22/5)+ü构成;
(2)küwänčäng“理想、意志、骄傲、傲慢”(MSI96/20)由küwän-+č(MSI96/21)+äng构成;
(3) ögdi “奖赏、嘉奖”(AYC346/5),UW Mi32/a)由ög-“赞美、夸赞”+di构成;
(4)qataγlantačï“刻苦的人、付出艰辛的人”(MSI106/25)由qataγ+-la-+“有坚定信念、刻苦努力” ( MSI102/12,198/3)+tačï构成;
(5)basïnč“压制、压力”(MSI170/22)由bas-“压、按压”+ïn(构成被动态的后缀)+č构成;
(6)aymanč“恐惧”(MSI174/2,AYC417/3)由ayman-“怕”<ay-+ma-+n-(动词的反身态后缀)+č构成
(7)irinč“贫困、可怜、不幸” (MSI154/9,AYC169/9)由ir-<är-“做” +n-(动词反身态后缀)+č构成;
(8)saqïnč“思念、想念、怀念”(MSI113/24,AYC25/5) 由saqï-“想”+n-“思念、想念、怀念”(动词的反身态后缀)+č构成;
(9)sawinč“高兴、兴奋”(AYC92/11,UW Ad01/3)saw-“高兴、兴奋”<sab-+n-(动词的反身态后缀)+č构成;
(10)őgürünč“高兴、兴奋”(MSI215/23,AYC22/5)由őg-+ür+ün-“高兴、兴奋”(动词的反身态后缀)+č构成;
(11)umunč~umïnč“欲望、渴望、希望”(AYC601/14)由umu-+n-(AYC605/1)~umï-+n-“希望”(AYC637/8)(动词反身态后缀)+č构成;
(12)ïnanč(MST116/5, AYC640/5)ïnan-“相信”+č构成;
(13)yarlïqančučï“发慈悲的人、有慈悲心的人、有善心的人、行善的人、宽宏大量的人”(AYC204/5,AYC21/22)yarlïq+a+n-“发慈悲、行善”+čučï构成;
(14) qorqïnčïγ“恐惧、畏惧、惧怕”(AYC172/ 17)由qorq-“怕、惧怕、畏惧”+ïn-(动词的反身态后缀)+ čïγ构成;
(15)küsänčig(AYC120/6)由küsän-“希望、盼望”<küsä-“ 希望”+n-“ 希望、盼望、渴望
(二)还有部分表心理概念的抽象名词是由心理活动概念的动词加缀“š”构成,例如:
(1)alqïš“赞歌”(MSI124/20,AYC276/22)由alqï-“赞叹”+š构成;
(2)busuš“悲伤”(AYC101/21)由busu-“发愁”( AYC367/18)+ š构成;
(3)sïqïš“愁闷、忧愁”(AYC180/7)由sïq-“捏、掐、卡” + ïš构成;
(4)küsüŝ“愿望、希望”( MSI124/5,AYC11/7)由küsü-<kősa-< kőza-“期望、盼望” +š构成;
还有一些派生结构在数量上不占多数,只是个别现象。例如,“ilinmäk( 挂念、挂心)”,是由“ilin”(被挂、被悬挂)+mäk构成的;“inäl(信仰、信奉)”是由na(信、信奉、信仰) ”+l后,发生音变构成。
以上都是对抽象心理范畴的抽象名词在结构规则上的描写,如果从个体名词形式的整体来看,都可以归纳为一个特点,即派生性的特点。也就是说,在回鹘文献语言中,表示心理活动的名词都是派生形式,而且呈现出一种普遍性。
二、现代维吾尔语言心理范畴词汇特点
在现代维吾尔语言中,几乎所有的表示抽象心理结构的名词都是在共时语言词汇体系内不可分解的最小语义单位,并在这些词汇形式的基础上派生出个体心理经验行为的动词。心理抽象词汇形式几乎不再和生理经验感受的词汇形式存在语音上的联系。
从整体上来看,现代维吾尔语言中这238个(笔者博士论文根据《现代维吾尔语言实用词典》做的数据统计)表示心理结构的抽象名词,已经不再体现出古代回鹘文献语言心理抽象名词形式的派生特点,表示抽象心理结构的名词几乎都是共时体系内部不可分解的非派生形式。而60个表心理活动的非派生动词,在整个词汇体系中也都是孤零零的,一般没有由之而派生的抽象名词。这就意味着,古代回鹘文献语言中,由心理活动动词派生出这一行为实体化名词形式的派生规则,已经整体的消失。这是一种规则的变化,从而产生了新的词类关系结构:在现代维吾尔语言中,心理活动的抽象名词形式都表现出共时体系内的不可分解性和非派生性,同时,成为心理活动动词形式得以派生的形式基础。例如,从“εqidε”(信仰、信念)派生出与之相关的心理行为“εqidε baγli-”(信仰、崇拜、崇尚)的词汇形式,从而在抽象心理范畴的词语形式中,形成了不同于古代回鹘文献语言的另一种词类形式的关系格局,即心理活动名词派生出相关心理活动动词。
总之,在古代回鹘文献语言中,表示心理范畴的心理名词大都是由表示具体行为的动词派生而来的,表现为派生形式的特点,而现代维吾尔语言中,抽象心理名词大都是共时体系内部不可分解的最小语言单位,表现为非派生形式的特点。
三、心理范畴内部概念关系格局问题的探讨
对比古今维吾尔语言抽象心理范畴的词汇形式特点后,一个很明显的整体变化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在古代回鹘文献语言中,表示人类情感、意志结构的名词是由个体经验行为的动词派生而来的,词语形式表现出派生的特点;而在现代维吾尔语言中,则完全相反。抽象心理活动的动词几乎都是由心理结构的抽象名词派生而来的。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在认知的基础上产生并体现认知。认知发展先于语言,并决定语言的发展,语言是认知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所以,维吾尔语言心理范畴之词汇形式的内部联系的规则性以及古今在派生关系上完全相反的规则性体现,促使我们开始从人类认知的角度考虑,抽象心理名词概念和抽象心理动词概念形成的先后问题。
这一问题在语言学领域被提出,特别是在汉语中,似乎听起来很古怪。过去,我们对汉语心理活动词汇的研究,仅仅从形式所具有句法功能上来对它们进行分类。其结果是:一个表示心理范畴的词汇形式既可以充当谓语,又可以充当主语,即有名词性的句法功能,又有形容词、动词的句法功能。例如:
我 很 快乐。
快乐 围绕 在我们的周围。
在第一个句子中,“快乐”充当句子的谓语,体现出“快乐”一词的谓词性功能;而在第二句中,“快乐”是句子的主语,该词又具有名词性的功能。这是以共时的研究方法,只关注形式、忽略语义的必然结果。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从概念的角度考察,二者存在范畴上的差别。前者表达的是一种内心的感受,是以个体心理经验为内容的,是指代心理活动行为本身的符号;而后者指代的是一个抽象事物,按照经验主义巨匠洛克的观点,是把这种行为的认识和整体人联系起来,在个体经验行为的基础上对整个人类心理结构的认识并得出结论:人类确实存有这种心理,是对人类情感和意志结构的认识,属于认知范畴的概念。
在中国哲学领域中,早在中国的程朱理学思想中从形而上学的本体论角度明确地区分为两种事物。朱熹认为,每一事物从生成时,便有一个理居于其中,这个理构成该事物的本性。人也是如此。人性就是人类得以生成之理居于其个别人之中,人性和人心的区别在于,心是理加上气之后的体现,是具体的、个别的,而性是抽象的。心可以思想、感觉,但性不能有这些活动。人类之理是共同的,而人则各有不同,这是因为一个人必须禀气而生,“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凉水中,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之中”。由此可见,对这两个概念的区别认识,古而有之。只是将抽象和具体的两种概念实体化,并当作是客观实存,探究其间的关系,构建世界本体的理论体系的结果,他认为先在之理,禀气而后生,先由抽象之理,而后生具体之相。而唯物主义者则认为,人们是在对个别人的经验行为的认识基础之上,得出的对人类心理结构的一般认识。
如果我们从语言历时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两种概念的产生时间孰先孰后?这一问题(也就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分歧所在)从汉语的词汇形式上是得不到回答的。因为,在汉语中,二者的能指在形式上没有任何区别,无法以形式辨其先后。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也是这一问题被汉语界忽视的原因。但在英语中这却是没有办法回避的。因为,在英语中,两个概念是以不同的形式区分的。例如,“happy”和“happiness”,但由于研究者的关注点在词汇的功能上,人们往往将-ness当作词汇形式的语法功能的标记,而忽视两个词语之间的概念差异。我们通过形式的繁简,能够很清楚地看出,“happiness”是由“happy”派生而来的,即抽象心理名词是由表示个体心理感受的词汇形式派生而来的。而且这种现象不在少数。
例如:
当然,英语中也有一部分心理词汇如同汉语一样,在这两个概念的语音形式上没有做区分,例如“scare (害怕)”、“shame (害羞)”、“doubt (怀疑)”、“hope(希望)”、“wish(希望)”等。这些词,正如汉语一样,既可以表示抽象事物,也可以指代行为动作。但是只要能够通过形式的繁简,分辨出派生次序的,一般情况下,都表现为有时间或人称限定的相对概念派生出实体化名词概念的规则。
也许正是因为英语在形式上对语法功能的差别作出区分,才会使西方人从很早就从语言上关注这两种概念的区别,并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区别了这两个观念的来源。17世纪,英国经验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巨匠, 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教育思想家约翰·洛克(John Lock, 1632-1704),他和霍布斯(T. Hobbes)为代表的联想主义心理学成为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发端。他在探讨人类知识的起源中,就将精神实体中的所有观念(抽象心理名词所指)的来源归于人们对心理活动方式的反思。换句话说,心理范畴的抽象事物的概念来源于人们对心理活动的反思,前者的认知基于后者之上,后一个观念的获得先于前一个。至少是在自然认知的理论逻辑上是这样的。
洛克将人类所获得观念分为简单的观念和复合的观念。简单观念指的是“只含有一种单纯的现象,或只能引起思想中一种单纯认识,不能再区分为各种不同的观念。”[1](P46)复合观念被分为三种:情态、实体、关系。而对应于动词和名词所指的心理行为观念和精神实体观念就分属于复合观念中的情态和实体两大类。他认为心理变化只有通过经验感觉和反思得来,“他们像其它简单观念一样,是无法形容的,也不是他们的名称能够定义的。我们只能凭经验知道它们,就像我们凭经验知道简单的感官观念一样” ,“痛苦和快乐,以及造成它们的善和恶,都是旋转我们情感的枢纽。如果我们反思自己,观察这些事物(善和恶)在各种各样的观念之下如何在我们心中起作用,考虑它们能产生什么心理变化或内在感受(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它们的话),我们便可以由此观察到我们的情感。”[1](P86)
而他认为思想和意志结构的观念是在那些经验感知到的情态观念之上假设和推理的结果。各种情态观念(心理活动的观念)被认为是一种精神实体的各种能力,属于复合实体观念中的可感的次要性质。“我们断言思考、推理、惧怕(情态观念)等作用不能自己存在,也不能想象它们属于某种物体,或者为某种物体所产生,于是我们想它们是其它的一些实体动作,我们称之为精神的动作……。我们有物质观念是因为我们假设打动我们感官的可感性质可以有某种东西支撑,而我们有精神实体的观念是因为我们假设思想、知识、怀疑、推动力等可以有一种东西支撑。对于物质实体(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们假设它是简单观念的基础;同时我们假定精神实体(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是我们自身感受到的那些操作的基础。”[1](P130)而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心理作用,都被归因于精神实体的能力,“凭这些能力通过感官使我们生出各种观念来。”[1](P132)也就是说,思想和意志的名词概念源自人类对心理经验观念来源的推理,被认为是一种精神实体的各种能力。正如前苏联学者Α. Ґ. 斯皮尔金的观点,这一推论的认知方式是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把无生命的对象和现象人化的产物。
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精神实体的概念(整体人之性的概念)都是建立在对“对象特性”(个体人之心)经验认知基础之上的,是人们对“脑的心理活动”认知的结果,属于人类对心理现象的认知范畴。也就是说,从语法功能角度区分为两个不同词类的词汇形式,从概念上也可以区分为心理范畴下的两个次范畴:动词性词汇形式表达的是个体心理活动的经验范畴概念,而名词表达的是人们对心理现象的认知范畴概念。
洛克的观点是否考虑到了英语词汇形式体现出的概念区分和联系,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维吾尔语言中,无论是古还是今,从词汇的形式来看,都清楚地将其区别为两个不同的词汇形式,在语法功能上区分为两种词类,并且从概念上聚合为两个心理范畴的次范畴,只是这两个次范畴之间的关系古今在词会形式上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
四、古代回鹘文献语言的心理范畴内部的概念关系格局体现了人类概念化认知的自然过程
认知语言学将人类认知机制确定为研究目的的认知语言学通过分析词语各义项之间或有渊源关系的词语概念之间的内部联系,找出词汇联系的共性,从而得出了人类概念化认知的一般规律。语言是在认知的基础上产生的,并体现认知。认知发展先于语言,并决定语言的发展,语言是认知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认知是人们基于经验对事物进行概念化、范畴化的过程,概念化形成是对事物本身性质和特征的认识,范畴化是对事物之间种属关系的认识。认知是人们对于经验的重组,经验才是认知活动的对象。无论是概念化还是范畴化回答的问题都是:这个事物本身是什么?对具体事物的意象是直接来自感官的经验,抽象事物意象的形成是对具体事物的意象基础上加工和综合的结果,表达的是事物的意义和内容。“人的认知有可能向两个平面扩展:一个是具体抽象平面,构成了具体概念到抽象概念间的隐喻引申(extensions), 产生了抽象词语和抽象意义。另一个由特指(specific)概括平面,构成了由基本范畴向上下衍生的不同详细程度的范畴等级,产生不同详细平面(levels of specificity)的词语。”[2](P205)
古代回鹘文献语言中,抽象名词的派生性特点,从具体到抽象,恰恰体现了该民族(基于主体的经验联想利用相似和相关联想)对心理经验范畴内容的认知和表达。认知主体的想象力是连接具体概念和抽象概念的纽带,产生了大量的派生特点的抽象心理词汇,从具体到抽象。例如:古回鹘文献语言中“ilinmäk”(挂念、挂心)是由经验动作的语音形式“ili–”(挂,悬挂),加反身态后缀“n”,加名词形态后缀“mäk”构成。很显然,抽象动词“ilinmäk”是由“ili–”派生的。没有具体概念“ili–”的表达形式,就不会有“ilinmäk”。正如,汉语中没有“牵”这一经验行为,如何会有“牵挂”这一心理活动的的词汇。语音的相似性及语音的繁简程度,使派生关系及词汇产生时间的先后昭然若揭。
又如,sïqïš“愁闷、忧愁”(AYC180/7)又是由sïq-“捏、掐、卡”加缀“ïš”派生而来。以派生形式为主的心理范畴词汇形式的格局,体现着古维吾尔民族成员在人类一般认知规律支配下对心理活动经验内容本身的自然认知过程。
如果说古代回鹘文献语言中这两个次范畴之间的概念关系记录着维吾尔先民对心理范畴概念自然认知和概念化表达的过程,那么,什么原因使得维吾尔语言这两个次范畴之间的概念关系结构发生了变化呢?仅仅限于语言的内部,以外来词汇的冲击和影响可否解释某一范畴内部词汇概念关系结构的变化呢?语言结构的变化属于思维无意识行为的结果,我们是否能在思维无意识领域的变化中找到关联呢?如果维吾尔语言其他范畴的词汇概念关系结构也发生了关联性的变化,我们是否还能以“偶然”现象置之不理呢?正如历时语言学家确定语言的亲属关系一样,以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作为构拟的基础,在任意的语言符号中寻找规则的对应,从而确立其间的历史联系。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也同样决定了每一个词汇概念结构的任意性。如果某一范畴的词汇概念关系具有模型一样的结构,同时几个范畴的概念关系结构的变化都能聚焦于某一点,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词汇概念关系结构的变化归因于这一点呢?这并不是幻想式的假设,而是在语言材料分析基础上的逻辑。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就此搁笔,这不是语言的描写,而是对语言现象的解释。于是,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从语言的研究滑入到了人类学研究之中。
[1] 洛克. 人类理解论[M]. 谭善名, 徐文秀译.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7.
[2]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责任编辑:冯济平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the Internal Conceptual Relationship Subordinating to Uighur Psychological Category
PENG Feng
(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Urumqi 8300054, China )
The author investigates and contrasts modern Uighur and ancient Uighur lexical structure of words of the Uighur psychological category, and finds out that words of both modern and ancient Uighur are divided automatically into two second-rate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 formal characteristics of those words. One refers to all kinds of personal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s, and the other refers to people's cognition of various human psychological structures. The concep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ategories has wholly changed. Focusing on the linguistic phenomenon, the author gives forth his points from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about the conceptual relationship, which words of the psychological category reflect in forms as a record of the ancient Uyghur's naturally cognitive course of understanding the psychological concepts.
Uighur; historical contrast; psychological category; conceptual relationship; cognitive linguistics
H215
A
1005-7110(2013)01-0101-05
2012-03-28
彭凤(1977-),女,四川泸县人,新疆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化语言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