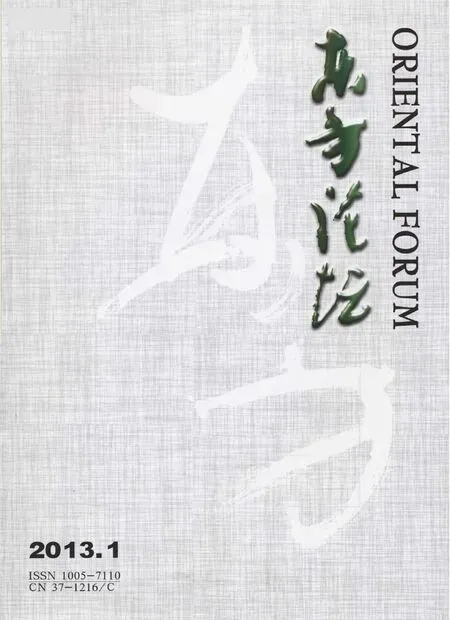论《红楼梦》对传统叙事结构的突破
2013-03-27武建雄
武建雄
(滨州学院 中文系,山东 滨州 256600)
论《红楼梦》对传统叙事结构的突破
武建雄
(滨州学院 中文系,山东 滨州 256600)
《红楼梦》对小说传统写法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叙事结构上。主题的复合性使得《红楼梦》在叙事整体结构切分上具有多层次的特点。从宏观建构考察,《红楼梦》采用了单线贯穿、多线并进的叙事方式;从微观结构上看,《红楼梦》在情节组织上具有“生态性”的特点,体现出向传统美学回归的迹象。
《红楼梦》;叙事结构;叙事线索
《红楼梦》叙事结构的研究,在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众多问题中显得首当其冲。这不仅牵涉到有关现存百二十回的文本是否存在续书的问题,而且更是关系到对作者文本创作命意初衷的理解。新红学诞生之初,虽然学界即提出《红楼梦》后四十回为续作的石破天惊之论,且拥疋者甚多,然而学界至今仍存争论。笔者以为既然续书问题尚不能定论,不妨姑且以现成的百二十回本作为立论的基础。
论《红楼梦》的结构,首先须明了它表达的主题。关于《红楼梦》的主题,学术界争议颇多,然综其论述不外三个方面: (一)宝黛爱情说,(二)贵族(贾府)兴衰说,(三)青年女子命运说。论者以为在已经无法窥知作者原创动机,而文章又确切包含了三个方面信息的情况下,综合三方主题分析结构,必然造成逻辑上的矛盾与混乱,既然如此,不妨从每个主题出发分别研究《红楼梦》的建构,虽然难成总观,亦可条分缕析。
百二十回本《红楼梦》通体关合呈环状结构似已无可置疑,分析《红楼梦》的结构,不仅要从关合处把握其宏观的建构,更要从其圆周动运的过程把握其微观的组织。只有综合考察《红楼梦》的文本结构构成,才可准确把握其对传统小说叙事的突破。
一
从宏观上分析《红楼梦》的结构,对文本行分段分节来解构《红楼梦》的主旨命意,是许多学者长期以来一贯的做法。清· 王希廉认为“《红楼梦》分作二十一段看,方知结构层次。”[1](P536)周汝昌认为每九回一段,其十二段百零八回[2](P142);霍松林认为百二十回可分为五段[3](P693);邸瑞平认为百二十回可分为六段[4](P126)。立论的依据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各异。
如前所述,论者认为《红楼梦》分段必须参照作品的主题。既然研究认为作品的主题并非单一,而是如上文论及三者兼而有之,那么依据不同的主题对作品整体进行分割,其切点必然会有所不同。与其综合三个主题进行切分造成作品不同部分之间联系的混乱与逻辑上的矛盾,尚不如从每个主题出发分别对作品加以解析。又有作品前五回作为一部《红楼梦》结构之总纲,因而从不同主题出发解析百二十回《红楼梦》的结构,实则应始于作品第六回。
下面,论者就自己的浅见分而论之:
(一)从宝黛爱情主题出发[5]
六到十九回为一段,此段为宝黛爱情的初恋阶段。“黛玉含酸”之“含酸”二字透露出初恋的信息,而“静玉生香”一回中,二玉说笑中提及“金配玉”之事,则更是爱情萌芽的明证。
二十到三十二回为二段,此段为宝黛爱情的热恋阶段。“宝黛论心”、“共读西厢”、“黛玉春困”、“黛玉葬花”、“宝黛诉肺腑”,宝黛爱情日深,两心相应无猜。
三十三至五十七回为三段,宝黛爱情已日趋于成就。“宝玉赠帕”、黛玉“题帕定情”、“宝玉梦呓”、“宝玉夜探”、“紫鹃试玉”,说明宝黛爱情已经巩固,非“金玉”之说能攻破。
五十八回至九十回为四段,宝黛爱情崩溃。“黛玉惊梦”初露悲兆,而“黛玉焚稿”及至黛死钗嫁,终于千日恩爱毁于一朝。
(二)从贾府盛衰主题出发
六至十八回为一段,此段展示贾府初盛的景况。十三至十五回的“浩浩荡荡”如“压地银山”般的秦氏丧仪充分反映了贾族的豪奢,及至十七至十八回元妃省亲时,见到豪华的大观园都说“以后不可太奢,此皆过分之极”。
十九至五十四回为二段,贾府极盛阶段。三十七、八回“探春结社”、四十回“贾母夜宴”、五十三回、四回“元霄夜宴”极写贾府繁盛,贾家人事正旺。
五十五回至八十回为三段,贾府内部出现危机,繁盛景象日渐倾颓。五十五、六回探春理家,贾家易主预示贾府景况的转变,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更明显地揭示出贾府由盛而衰的诱因,从七十六回“品笛联诗”中可听到其处于末世的悲音,而七十七回“晴雯屈死”及七十九回“迎春误嫁”则“渐渐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
八十一至百十九回为四段,贾府彻底衰败阶段。九十五回“元妃薨逝”,贾府靠山已倒,一百回“探春远嫁”已大失贾府颜面,百零五回“贾府被抄”,昔日强大的贾族已如既倒之狂澜而难以挽回,百一十回贾家最高统治者贾母寿终,百十九回宝玉出走,终至落得个“树倒猢狲散”。
(三)从青年女子命运说主题出发
六至三十八回为一段,群芳初绽阶段。十六回“元春才选”、二十六回黛玉春困、三十回“宝钗扑蝶”、三十七回结海棠社显示了大观园众芳初绽、生机勃勃一派热闹景象。
三十九回至六十四回为第二段,众芳争奇斗艳,各放奇情异彩。四十回鸳鸯宣令、四十四回平儿理妆、四十八回香菱苦吟、五十一回薛小妹编诗、五十二回晴雯补裘、五十六回探春兴利除弊、六十二回湘云醉眠、众芳才艺风情展露无遗,而六十三回群芳开夜宴则如百川归海、满汉全席、梁山义聚,其盛艳之极自不待言。
六十五回至七十六回为三段,秋风将至,众芳即将凋零。六十六回“尤三姐情耻归地府”、六十八回“凤姐大闹宁国府”、六十九回“尤三姐吞金自逝”、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伴随贾府内乱、时运衰微,众芳运命难以自保,以至七十五回夜宴而发悲音,品笛而感凄清,联诗而悲寂寞。
七十七至百二十回为四段,众芳败谢。七十九回迎春误嫁中山狼、九十回元妃薨逝、九十七回宝钗嫁痴玉、九十八回绛珠魂归、一百回探春远嫁、百零六回湘云出阁,不久姑爷暴病而亡、百二十回妙玉遭劫、百十回凤姐卒、百十五回探春出家,大观园众芳凋谢、水逝云飞,“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以上为笔者就不同主题对作品进行的结构上的不同析解。之所以每个主题均以四段划分,乃是由于传统音乐、戏曲讲究起、承、转、合,而学界又多认为《红楼梦》依春、夏、秋、冬四季为线索,因此按照四段划分的方法符合创作的一般规律。另外,既依主题划分段落,难免出现划分不尽的情况(如第一、二种主题划分),然而囿于特殊的划分依据,出现诸如此种情况亦属正常。
二
《红楼梦》在宏观叙事上呈现出怎的结构特点,这是解读一部《红楼梦》首要的问题。关于此一问题,研究者很多,也依据各人的立论依据而提出了种种不同的看法。笔者谨将截止目前有代表性的观点列举几种。(一)对称结构。提出此观点的是周汝昌。他认为全书共108回,每9回为一个单元,据此敷衍出《红楼梦》在叙事上为扇合结构,其中54回与55回为全书的折点。(二)四季结构。这种观点认为《红楼梦》全书在情节结构的安排上体现着“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递进与演化。(三)三重奏式的复合结构。这种观点认为《红楼梦》一书的叙事并没有突破传统小说,只是巧妙地把历史传奇、爱情传奇、宗教传奇的三大叙事结构模式交织为一体,从而构成了一个丰富的、多维的叙事结构模式。
不论是对称结构、四季结构还是三重奏结构说,都是试图用一种已有小说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简单结构模式将《红楼梦》纷繁复杂的叙事纳入其中,以期对作品的结构作出合理的解读。实际上,这样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只反映了学者一厢情愿式的自我解读,并不符合创作主体的最初动意,也不符合创作学的规律。创作本身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心智活动,作者笔下人物的活动、情节的设计与结构的安排不仅要受到作者既往人生体验、阅历的影响,又要受到作者当下一时一地心理活动的影响,更何况像《红楼梦》这样叙事上高度复杂、艺术安排异常独到,且又普遍被认为原作者只创作了八十回残篇的作品,要把其叙事上的宏观结构用一种简单的模式来概括说明,显然是错误的。小说创作是灵动活泼的心智活动,而不是建筑工程,可以对材料随意堆造。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三重奏结构、四季结构与对称结构,都不能科学、客观地解析《红楼梦》的宏观叙事结构特点。
抛开人为对作品结构进行划段与切割,以期用一种几何式的优美图式来对《红楼梦》高度复杂的结构特点进行概括说明的思维俗套,我们会发现,《红楼梦》在浩繁的情节衍伸蔓延、故事波澜起伏中,一直维持着叙事结构上的严密有序,紧凑而不紊乱,正如清人张新之说的“但观其通体结构,如常山蛇首尾相应,安根伏线,有牵一发而全身动之妙。”[6](P685,687)《红楼梦》叙事结构的严密有致,并不体现在外在的宏观构建,而是体现在内在的主线设计之中。
《红楼梦》在宏观叙事上采用了主线贯穿的艺术手法,实现了作品外在结构与内在结构的浑然天成。对于《红楼梦》所采用的主线设计,目前主要观点有几种: (一)以石头为主线; (二)以刘姥姥为主线; (三)以宝、黛、钗爱情婚姻为主线; (四)以宝玉、王熙凤为主线。如果从贯穿作品内在结构、组织宏大叙事的角度来考察,无疑“石头”是作者构思主线的不二选择。在整部《红楼梦》中,“石头”与宝玉二位一体,“石头”成为叙事始终的在场者,即使在没有宝玉的回目中,它也作为叙事角色亦因宝玉的在场而存在,因此石头成为通灵而无时无处不在的叙事主角,全书所要描绘的一切都是在石头的视野中发生的,它以其冷峻的目光剖析着世间的人情百态,瞩目于纯情儿女的悲欢离合,洞察着人生的空虚幻灭,在这出人生的悲剧舞台上,作者既入乎其中,一往情深、积极有为地参与和面对世事;又出乎其外,超然物外地审视和观照着俗世的历史与人生。[7]把“石头”这个中心意象既作为观照者又作为叙述者的叙事方式,同时承担全书人物与情节组织的功能,在以往的小说中是不多见的,是作者曹雪芹对传统叙事方式的大胆突破与创造性发展。
三
《红楼梦》微观层面叙事的章法特点,甲戌本第一回脂砚斋用“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等大量铺排的词藻来评价。这些词藻无一例外地带有自然性、形象性的特点,而非学理性、思辨性的学术语言。脂砚斋用这些极生动的词汇来形容《红楼梦》微观层面的叙事,他究竟想传达出怎样一种信息?
在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的传统中,线性结构与因果链条式的情节组织一直成为小说内在结构的一种稳定模式。这种传统模式体现出了作者对表现对象与组织材料的任意凌驾与强力支配,这样的做法会使叙事悬念迭出、情节陈陈相因,始终抓住读者眼球,形成较强的阅读效果。然而这种人为设计叙事的方式,可以让作者先入为主、概念化、抽象化的哲学思维得到明确表达,但却会使文学在本质意义上背离生活太远而显得刻板教条。《红楼梦》以前的长篇章回小说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文学是源于自然生活而表现自然生活的,只有始终契合自然、贴近生活,真实地反映出生活的“原生态”,在丰富与鲜活的“事体”与“人情”中浸润作者的思想,文学作品才会血肉丰满、生气活泼。
《红楼梦》对小说叙事传统的颠覆在于其突破了单线结构与因果相陈的叙事方式。在《红楼梦》中,叙事线索多线并进,重叠交织,同时“情节”被大大淡化、细节化、枝蔓化。《红楼梦》第一回就告诉读者,小说比历来风月事故更加“琐碎细腻”,以往写风流人物,不过传其“大概”而已,而《红楼梦》则着意从“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的日常生活细节开始,精细刻画和深人体现“儿女之真情”与复杂深广之整体“人情”。这使得《红楼梦》中“情节线索”的安排,具有极为细致、错综、枝蔓、复杂的“间三带四”之特征。[8]《红楼梦》之“结构”,并非某种深层的因果逻辑,而实质上是一个充满有机性质、生态性质的“事体”。《红楼梦》如此叙事的方式被称为“网状结构”。
“网状结构”的叙事方式接近生活的原生态,符合自然人事的规律。生活的原生态本身就是琐碎细腻的,千头万绪交织而纷繁复杂。《红楼梦》叙事正像生活本身那样错综复杂、琐碎细腻,但毫无死板拮据之感,小说微观叙事之笔势,如游龙戏凤、行云流水之中极尽错综变化之妙,充满着错落有致,微妙复杂的意义张力,而所有人事细节之间,更充满了息息相通、波澜起伏、生动细致的“感应。比如《红楼梦》第33回写到的一个精彩情节:宝玉挨打。宝玉被父亲痛打,由于金钏自溺和琪官失踪两件事,而这是早在第30回就已发生的事了。宝玉和黛玉刚刚和好,不意出言不慎,讥笑宝钗,反被宝钗当众讽谏,心中无趣,没精打采,出来散步。走到王夫人房内,适见王夫人睡着,就与金训调笑。不幸金钏说错了话,叫王夫人听见,打了一个嘴巴,并让她母亲带去。作者至此,不再写金钏的结果;续写的是宝玉从王夫人房里出来,遇见龄官画蔷;继而脚踢袭人;继而晴雯撕扇;甚至作者把宝玉丢开,突然写到湘云,从湘云重返到宝玉。一天,宝玉正和湘云谈话,忽报父亲的话,雨村要见,心中不乐;路遇黛玉,又叙了一段私情。到读者几乎把金钏被逐忘了的时候,忽听金钏“投井了”。宝玉听见这个消息“心中早已五内摧伤,茫茫不知何往,背着手,低着头,一面感叹,一面慢慢的信步来至厅上”,谁料又遇父亲。故事至此,陡然紧张起来。贾政见宝玉这样垂头丧气,葳葳蕤蕤的神色,本就生气;忽然忠顺府长官又向他讨宝玉藏匿的琪官,又加了一层气;最后,又听到金钏之死。于是三气并发,终致对宝玉动了无情的打手。这一段描写可谓一波三折,曲张有致,在宝玉挨打这一情节主线之中,穿插了金钏自溺、脚踢袭人、晴雯撕扇、闷见雨村等等一系列事件,然而纷繁而不零乱,周密而细致,由一件事而串联起了如此众多不同的人物与事件,表现出如此错杂、浑厚、饱满的生活内容,又随物赋形、细腻逼真地刻画出不同人物的鲜明个性。
“生态性”是《红楼梦》微观叙事的鲜明特征。《红楼梦》以多线并进、枝蔓交织的叙事方式最大程度地反映了生活的原生态样貌,体现了我国古代文化中“天人感应”的思想精髓。同时,在叙事中有意识通过季节性情节相对集中的安排,去呈现贾府兴盛衰败的四时气象;通过艺术结构上有规律的春夏秋冬四季性循环,来组织起庞大的叙事,行文运笔无不注意自然与人事的息息关联,生动地阐释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小说创作中的独到运用。而脂砚斋用“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等描述自然现象的词汇来概括《红楼梦》微观叙事的特征,也正是传达一种“生态性”的信息。
“生态性”的叙事方法的形成标志着小说创作观念向着生活本体回归的倾向。早在两千多年的老庄道家美学观念里即强调度物要“天人合一”、“顺乎天理”,即人对审美客体的裁夺要顺应客体本身的自然规律。从这一观念出发,古代的艺术家形成了反对人力穿凿扭捏而成的“峭然孤出”的牵强矫情的造物,强调艺术创造应该巧夺天工、合乎自然、一派天成,也正是这种中国小说所特有的“天人相合”的艺术追求,才赋予《红楼梦》以天然浑成的艺术整体感。
综上所述,由于《红楼梦》创作主旨的非单一性,决定了对其文本整体结构的切分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从不同主题出发而进行的结构切分,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红楼梦》叙事的宏观结构上,打破了传统小说单线行进的模式,采用主线贯穿、多线并进的方法组织起庞大的叙事,同时实现了主题表达的立体化。从微观结构考察,《红楼梦》在叙事上的情节线索,是在细节化、枝蔓化、错综交织中行进的,而各个章回、各个段落、各个细节之间,既不落于线性因果关系之“形迹”,而就其“神理”而言,却又充满了有机性的、互动呼应的关联,就好像是一个多元复杂、自在自为、而又天然浑成的“自然生态圈”。《红楼梦》在小说叙事结构上的创造,打破了古典小说写法的传统。
[1] 王希廉. 红楼梦总评[A]. 朱一玄. 红楼梦资料汇编[C].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3.
[2] 周汝昌. 献芹集[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
[3] 霍松林. 中国古典小说六大著鉴赏辞典[M]. 西安: 华岳文艺出版社, 1988.
[4] 邸瑞平. 红楼梦撷英[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5] 蓉生. 试论红楼梦的结构[J]. 红楼梦学刊, 1992, (3).
[6] 张新之. 红楼梦读法[A]. 朱一玄. 红楼梦资料汇编[C].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3.
[7] 孙敏强, 孙福轩. 再论《红楼梦》“石头”意象[J]. 红楼梦学刊, 2005, (6).
[8] 张洪波. 《红楼梦》之复调结构与浑成事体[J]. 红楼梦学刊, 2004, (2).
责任编辑:潘文竹
The Breakthroughs of Traditional Narrative Structures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WU Jian-xiong
( Chinese Dept, Binzhou University, Binzhou 256600, China )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made breakthroughs in writing style in comparison with traditional novels. The breakthrough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its narrative structure. Topical complexity endows the novel with many levels in the whole narrative structure segmentation. Viewed from its macro-construction, the novel adopts the narrative style of a single line running through with many other lines coming along. In terms of its microstructure, i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ecologicalness" of its plot organization, a sign of returning to traditional aesthetic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narrative structure; narrative thread
I207
A
1005-7110(2013)01-0097-04
2012-10-09
武建雄(1978- ) ,山西河曲人,滨州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