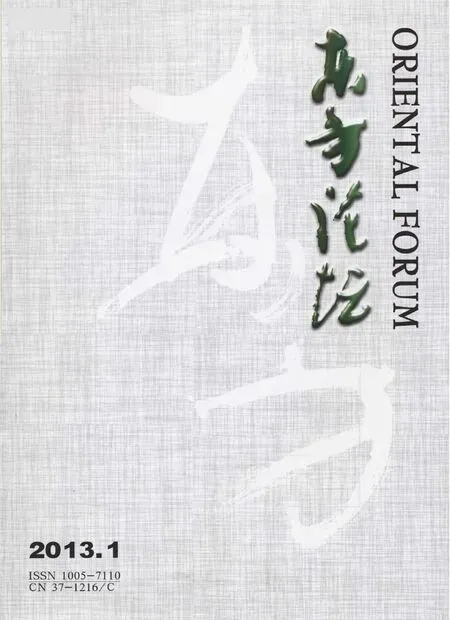中国现代文学怨恨体验的五大原由
2013-03-27王明科赵斌张海燕
王明科 赵斌 张海燕
(喀什师范学院 人文系,新疆 喀什 844008)
中国现代文学怨恨体验的五大原由
王明科 赵斌 张海燕
(喀什师范学院 人文系,新疆 喀什 844008)
怨恨的现实根源是社会历史处境;现代化追求导致了反抗传统的怨恨,传统的强力遗传导致了反抗传统而不得的怨恨;现代性悖论性导致了反抗现代性的怨恨;建构现代文化的艰难导致了建构中的怨恨;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与传统式威导致了回瞥中的怨恨;忧国忧民忧天下的济世思想与改变现实世界操作层面的实践欠缺之间的矛盾是知识分子产生自我怨恨的结构性根源,价值追求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由自我怨恨的动力性根源。
中国现代文学;怨恨;源由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怨恨体验不是专家名人发明出来的,更不是笔者杜撰而成的①笔者对“新怨恨”理论的初步尝试性建构参阅:王明科: 《“新怨恨”理论与文学批评》,《湖南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172-176页。 ②参阅:王明科:《中国文化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中的五大弊病》,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第21-26页。(注:中文摘要被《光明日报》2005年3月29日第8版转载;主要观点被《新华文摘》2005年第11期第162页转载;主要论点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5年第4期第190页转载; 全文正文被中国人民大学资料复印中心《文化研究》杂志2005年第11期第52-58页转载)。,而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真实存在着的,是中国文化内部各种力量相互冲突相互发展②过程中的一种情感体验,是现代中国人在心理上一切创伤的投射与反映:愤不发而生怨,怨积久而生恨。
一、怨恨的现实根源是社会历史处境
众所周知,现代中国不是在本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达到充分发展的时候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在农业自然经济濒临崩溃、外国多国列强联合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强行侵略的历史条件下,在担惊受怕与侮辱欺压的历史条件与现实环境中产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一方面,已经掌握了统一政权,并且取得了比较发达的物质文明的西欧资产阶级,肆无忌惮地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全方位地入侵、刺激、压迫、奴役中国,这直接诱发并导致了受压迫受苦难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愿望,增强了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与推翻腐朽专制统治的急迫感与主观要求。但是另一方面,在短期内实现这种急迫愿望的唯一手段的革命——其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使得革命的道路异常曲折,付出的代价异常惨烈。因此,怨恨的产生就是必然的。面对反封建的文化革命、反帝的民族革命、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阶级革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土上,外战与内战等种种战乱,常常是血的代价换不来革命的早日成功,一切惨不忍睹现象的出现都是语言所无法形容的,于是,受辱与忍辱成为现代中国国民的集体有意识心理。国外是异族侵略,国内是军阀混战,这种独特的历史进程与黑暗现实决定了怨恨情感就成为现代中国人具有普遍意义的心理体验。因此,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怨恨心理极其巨大。在某种程度上说,近现代中国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外战争、军阀混战、阶级斗争、国家革命、社会改革等实际上都是怨恨的产物。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创造性反映,必然会具有极大的怨恨心理,而小说作为最直接、最灵活、最广泛的表达体裁,也必然最充分、最丰富、最有力地反映着这种怨恨体验。小说创作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客观现实社会的反映,它虽然不是静态与僵硬的一面镜子,而是加入了审美理想与价值追求以及各种虚构与创造的动态的富于变化的精神产品,但这一切都建立在客观社会生活的基础之上。
可见,中国现代小说的怨恨貌似作家个人怨恨情绪的发泄,但实际上仍然是基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怨恨心理反映,即使那些个人情绪很浓厚的创作,即使有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家个人的自叙传如郁达夫的小说,但实际上它仍然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的产物,因为作家本人的创伤,实际上都是来自于他人;作家本人的怨恨①作家的怨恨之个案研究参阅:王明科:《怨恨与无名氏创作的文化理想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第221-231页。(注:主要观点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6年第2期第189页转载)。,说到底还是来自于于社会,即使私人之间的恩怨,其间也存在许多社会的因素。尤如郁达夫《沉沦》中主人公“他”喊出的一样: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二、反抗传统弊端与现代陷阱中的怨恨
对中国现代任何一位能够在文化反思中产生反抗型怨恨的文化人而言,其反抗中的怨恨基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他们通过各种不同途径获得了西方文化视界(至少是城市文化视阈)后已经具有了世界文化视野(至少是现代文化视域),在异域不同文化的比较与反观下,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弊端,并且在理智上要以自己的文化实践来反抗传统弊端,从而产生了对传统的深深怨恨。尤其当可供比较的文化系统如西方文化在相比之下显得更发达时,这种怨恨就极为强烈。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发现现代化带来了许多不可预料的灾难,于是又表达出对现代性之悖论性的极大怨恨——他们既因现代化追求而反抗与怨恨传统,同时又因现代性悖论而反抗与怨恨现代。于是,反抗中的怨恨②反抗中的怨恨之个案研究参阅:王明科:《反抗与怨恨: 中国现代六大作家的现代性体验之一》,《学习与实践》2006年第9期第121-127页。王明科: 《反抗中的怨恨:对鲁迅思想的新解读》,《学术导刊》(香港)2006年第期第102-107页。就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现代性的怨恨体验之一。
现代化追求导致了对传统在反抗中的怨恨。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而言,如果要追求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他们无疑会产生对传统诸多弊端的反抗,而在这个反抗的过程中,怨恨体验的产生不可避免:怨传统以皇帝为中心,恨传统以君王为本位;怨法家直言不讳为专制帝王霸权服务,恨儒家全力维护天子权力与等级秩序;怨孔子的“仁爱”是君臣父子上下远近等级亲疏模式中的仁爱,恨孟子的“贵民”是为稳固君权才贵民而不是为平民自身贵民;怨道家被权势排斥侧身江湖的犬儒主义态度与出世哲学,恨佛家欲求现世幸福不得而只寄希望于来世的虚无思想;怨墨家虽然能够埋头苦干却始终被排斥在中国文化的边缘,恨其他各家均处于被忽视被压制被损害被侮辱的弱势地位;怨传统在体系上形成稳定僵化与顽固落后的结构,恨传统在功能上造成反科学与反人性的排他性能;怨传统的统治阶级最能欺人,恨传统平民老百姓最能自欺;怨统治阶级极力想办法让人们做稳奴隶,恨千百万平民老百姓深怕做奴隶而不得;怨传统农民不被逼上生存绝路能暂时做稳奴隶就不会起义,恨传统农民起义的目标仍然是为了自己做成新的统治阶级;怨农民暴动为的仅仅是衣食玉帛与妻妾子女等兽性方面的满足,恨其起义以权利金钱为本质以不劳而获的福寿康乐观念为特征;怨农民起义不是为推翻一切统治者以保障每个个体的平等自由,恨其只是将别人对自己的专制统治变为自己对别人的专制统治。
传统的强力遗传导致了反抗传统而不得的怨恨。传统虽然可以变化,但同时却具有极强的承前启后的抵制变化的耐久性、完整性、迁延性与生殖性,其霸道表现在它先在于个体生命的诞生而存在,在个体因尚未形成自觉文化意识而不具有抗拒被灌输的能力时就强行无意识地烙印于个体身心行动之中,以后随着个体的成熟虽然产生了反抗传统的意识,但其潜意识仍然与传统不得不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传统通过家庭社会、文化思想、道德信仰、制度规则、行为习惯、心理定势等种种复杂隐秘的方式顽固地遗传在个体的每一存在时间与每个生存空间,没有人能够脱离传统。每个人不得不接受传统并从其中获取各种信息,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属于某个传统,任何探究都必须从传统出发。因此,传统绝不是过去、古典、陈旧、古代,不是曾经已经凝结成型的一种客体,而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整个时间延续中的一个过程。传统构成了现代的基础,规约着现代的发展,同时也为现代化提供了一定的资源基础与动力条件。可见,传统无法灭除、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不仅具有历时性更具有共时性。笔者认为,传统可以看作文化生成的基因,可以变异但不会消失。传统貌似在现代化面前不断后退但其实并未因此失去在当代和现实中的作用力,甚至这种作用在某些范围与某种条件下还具有很大的威胁力量。不说统治者极力利用传统的力量,仅从人性本身的意义来说,传统不但与人的原始心理需要密切相关,如畏权、怕事、恐众、怀旧、恋乡、亲情、道德感等,而且体现了人们对神圣性、依靠性、确定性、稳定性、规范性的追求,同时也保证了世界的有序性、法规性、协调性,使人们在心理上存在一个信仰寄托,从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人际交往的平衡、个人心灵的安宁。因此,无论何时何地,传统总是拥有大量不同阶层不同愿望的守卫者,其间既有大量既得利益者,又有许多盲从者,从而导致传统在有意无意之间具有了明显极强的排他功能,能够持久通过道德、心理、行为、风俗、信仰、利益等种种力量而对抗反传统力量,它既容易使传统信徒产生强烈的情感依附,又容易使反传统斗士陷入孤立无援,从而导致反抗与威胁传统即意味着质疑与威胁自我——因此,致力于锐意改革与创造发展的反抗传统者往往会因反抗传统而不得而陷入无尽的怨恨:怨自己无能恨传统强大,怨自己孤立恨传统霸道。
现代性悖论性又导致了反抗现代性缺陷中的怨恨。现代性转型之所以产生回瞥中的怨恨体验,其根源就在于现代性本身与生俱来的悖论性。笔者认为,现代性的悖论性至少要从四个方面来理解: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矛盾构成了现代性在整体结构上的悖论。社会现代性本身内部就是个悖论性结构。文化现代性的本身内部也是个悖论性结构。现代性的几大价值要义之间也是个悖论性结构——自由与平等之间充满紧张。独立与民主之间充满抵触。博爱被专制强奸,忏悔被礼教扼杀。
三、建构现代文化艰难挣扎中的怨恨
为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一部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致力于现代文化的重新建构,其构建依据不外乎民族化、世界化、现代化三大原则。笔者认为,对于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最起码的文化立场应该是对文化的现代化追求;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文化建构无疑要以中国文化为支点,一切要从中国文化的民族化出发。但许多人将民族化与现代化以及世界化对立起来,这种误解导致了他们许多不必要的怨恨①建构中的怨恨之个案研究参阅:王明科:《建构:中国现代七大作家的文化反思品格》,《东岳论丛》2005年第4期第98-102页。王明科:《圆满建构中的八重难堪》,《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75-80页。:怨追求现代化与世界化就难顾全民族化,恨顾及民族化就阻碍了现代化与世界化。
中国文化的研究者约有五类:一是从未接触过外国文化的中国学者,由于自始至终生活在中国文化的完整语境里而很自信自己的眼见体察,但其实他们未必深知中国文化的优劣利弊,水中之鱼难以跳出水外客观评说水之冷暖,他们往往怨西方文化不合中庸之道,恨中国文化不能一统天下。二是海外华人,了解中国文化但因乡土情结与身份认同而偏于高扬甚至在遥望与回忆中美化中国文化,他们常常怨中国文化近代衰落,恨西方文化到处蔓延。三是成长于中国文化,以后因游学、翻译、阅读而或直接或间接地获取中西两种不同文化视野的中国学者,能够在异域视野启迪中得到常人所不察觉的发现,在中外文化比较中对各自的优劣利弊有着清醒认识,但他们对异质文化的解释很容易因胭脂说其美而因麻斑定其丑,由于比较很难严格在相同层面或同一标准上进行,往往拿西方文化精华来指责中国文化糟粕,又拿中国文化精华来指责西方文化糟粕,错位对接,以优比劣或以劣比优,或来个中庸想当然地将中外文化调和得无比圆满完备,并美其名曰“世界文化”或“全球文化”,他们经常怨中体西用,恨西体中用。四是外国学者,能客观观察中国文化但由于身在其外而极难洞察其复杂内涵与深层奥妙,岸上飞鸟极难咂摸水之甘甜,他们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但同时也多有误解甚至隔阂。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大多来自严格受官方控制的公开出版物,很难深入原生态的文化内部亲身体验,难以觉察中国文化表面现象的有限与遮蔽甚至虚假,比如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就是如此。部分西人或希望中国永成古董以供鉴赏,或出于讽刺嘲笑与故意误导,或有其他政治与经济方面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经常不遗余力地鼓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怨中国文化从现代走向未来,恨中国文化从强盛走向世界。五是另类,约有四种:第一种学人怨历史残酷恨现实黑暗,力抗中国传统,诅咒中国社会,对讲究所谓民主、自由、平等的西方文化报以过分幻想;第二种学人怨现代社会动荡,恨现代道德沦丧,由于看到现代化带来了许多负效应而企图重新张扬传统文化,以求得对现代性弊端的纠正与弥补;第三种学人怨命运不公,恨世事艰难,经历了中国政治的太多运动与斗争,在一次又一次的文化革命中或亲身遭受或耳闻目睹了各种惨剧,接受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被扣帽子、打棍子、改造、批斗、坐狱、流血等吓破了胆,再也不敢有自己的文化追求与思想个性,他们宁可没有思想操守与文化主见也不原冒险自讨苦吃,他们宁愿成为“跟跟派”也不愿被人污蔑为卖国亲洋,因此导致了过分的民族文化情结与护国情绪,在建构中国现代文化时不敢面对西方文化的大量拿来。第四种学人对西方文化几乎没有了解,他们所反对的就是他们所不了解的,他们愿意言说的就是他们自己了解的中国古代文化,因此他们怨现代化而恨世界化。然而,总的看来,上述一切怨恨都与对民族化的狭隘误解有很大关系。
中国的几大文化主力都似乎缺乏对此的足够认识,更渴望自己在中国文化运动中扮演英雄角色,从而导致了许多怨恨心理的产生。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几大文化流派关于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考察中可以看出,对民族化的误解是各大思潮之间论争与彼此怨恨的根本原因。其实,建构中国现代文化的三个支撑点,即民族化、世界化、现代化之间不是互相矛盾对立的,而是相互促进共生的:保守主义不必因坚持民族化而怨现代化恨世界化,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不必因追求世界化与现代化而怨民族化恨本土化,中国马克思主义也不必固守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机械的教条主义而怨自由主义恨激进主义。
四、回瞥传统中产生的怨恨
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导致了对中国传统在回瞥中的怨恨①回瞥中的怨恨之个案研究参阅:王明科:《在回瞥中怨恨,在怨恨中回瞥》,《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12期第 67-75页。王明科: 《回瞥与怨恨:中国现代七大家现代性体验》,《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8期(A),第138-147页。以及对中国现代性的怨恨。由于中国现代性的悖论性与特殊性,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会产生对现代性的深深怨恨,并将文化拯救的目光投向传统,形成了回瞥传统中的怨恨。
从现实中国实际情况来看,由于西方现代性的世界性扩张不仅使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家政治出现严重危机,而且使中国传统精神的价值信仰和制度理念均遭极大质疑,所以中国现代性不仅涉及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问题,同时涉及了中国国家现代化与中国政教现代化的问题,涉及到与西方社会从制度到文化的民族生存性比较问题,甚至直接关涉着中华民族与中国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导致了中国价值结构的民族传统偏爱,导致了中国始终存在着体用之辩以及激进与保守的论争。不象英、法等西方国家借助17至18世纪的工商业革命和启蒙思想运动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现代化转变,中国现代化自晚清以来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与混乱。不象西方现代化是摆脱中世纪宗教神学束缚的世俗化及理性化,中国现代化始终面临对中国传统的重估、批判、改造、转换、更新的难题。民族生存问题使中国人在情感上不容易接受西方现代性入侵的事实——国人心中的中国是老大古国,博大精深,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因此,妄自尊大,宝自有而傲睨万物的“中华中心主义”的 “天朝”思想根深蒂固。同时,专制政治的历史遗产,小农经济的大量存在,市场文化的严重匮乏,农业社会的继续沿袭,家族文化的保守封闭,严重阻遏着中国现代化的行进。加之西人希望中国永远落后愚昧,国人也警惕西方的和平演变与文化殖民,在被侵略的大背景下时时高涨的国家主义情绪与民族主义情结,使中国人面对中西文化碰撞时很难接受西方现代性的突然强行进入。而当传统中国在现代西方的有力挑战面前一败涂地与全面崩溃时,中国现代化历程就始终伴随着太多的犹疑与徘徊,痛苦与怨恨。
传统的式威导致了回瞥传统时对于传统的怨恨。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激烈转型过程中,传统权威已经不被视为神圣,其真实性已经受到质疑。“中国古代文化在从春秋战国到鸦片战争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其自我封闭的性能是逐渐加强的,这并非说它没有程度的增长和量的积累,并非说它的这些成果都是毫无价值的,而是说它的发展速度是日趋缓慢的”,[1](P35)因此传统面临着重新评价与创造性的建构,它已经不能全面成功地帮助现代中国人们认识和改造现代中国世界,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社会与中国现实生活,陷入了危机,面临着崩溃。这就导致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回瞥传统的同时又产生了对传统的极大怨恨:怨传统过时,恨传统式威;怨传统衰惫,恨传统危机。笔者早就指出:中国传统史官文化说到底就是:“狼狗猫的文化:狼文化是主子食人的文化,狗文化是依附主子为主子出生入死谋划方略帮主子吃人以获取分食的文化,狼文化与狗文化是想方设法奴役人让人安做奴才的文化,猫文化是安于做或愿意做或至少想做奴才甚至做奴才做出瘾能从其中感到生存快乐而乐于做奴才以求得赐食的文化。这三种文化都以食肉(即以牺牲他人命运及其劳动成果)为基础而非自谋生路”。[2](P24)
当中国传统的生命力衰微时,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就构成了强烈对立,其对立不仅体现在于个体性与整体性的不同侧重——尽管传统文化对于人之价值的讨论兴起很早,如道家视人的价值在于自然性的恢复,孔孟认为人的价值在于社会性的仁义,墨家认为人的价值在于兼相爱交相利,法家认为人的价值在于争名夺利,但是,中国文化却一直没能产生以个人价值为本位的文化,究其原因,根本问题就在于儒家君主专制主义学说在理论上的源远流长以及在现实中的强力渗透;而且还表现在于人与文化的不同立足点——现代追求个体价值与人权保障,立足人的立场以自由、独立、自主的个人为标准,从人的解放与公民权利出发,为了人的个性自觉而去重构传统使其走向现代化;而传统却以其文化的习惯力量与既定的心理定势甚至霸道行径不断表达着对个体人的漠视与对个性人的压制。
现代更注重民主、平等、自由、可能、原创、个人、多元,而传统却极力维护专制、等级、秩序、服从、为奴、教条、集体、一元。现代性摆脱了传统文化强力先定的道德信仰,虽然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的困惑、失落、不安、迷茫,但其重要功能是保证了个人价值的实现。从人与文化的关系看,虽然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塑造人,但在始源与根本上说是人创造了文化而不是文化创造了人,因此回瞥传统并不是逆历史潮流的倒退,而是在回瞥中对传统企图作出新的创造,抛弃其糟粕而拿来其能够对现代世界产生重要意义的精华,因为现代化实际上取决于每一个文化个体的具体选择,当现代社会的绝大多数人追求自由平等而反对专制强权时,即使文化遗老有多么高明的心智能力与阴谋诡计也不能遏止现代化的发展——现代性悖论并不能否认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与全球普遍性,也不能否认落后国家将现代化作为应然诉求的可理解性。其实现代化不存在价值与事实、应然与必然之间的矛盾——现代化不是应不应该的问题,而是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事实不能怀疑而只能寻求解释。
所以,一方面,致力于现代化追求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反思与批判出发,怨传统落后,恨传统霸道;从个人的生存发展出发,怨传统讲究等级秩序,恨传统漠视个性自由。另一方面,对于因怨恨现代性缺陷而回瞥传统的人来说,他们最终也将会产生对传统式威及其弊端的怨恨:在怨恨现代中回瞥传统,在回瞥传统中怨恨传统。
五、知识分子由外向转为内向的自我怨恨
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反抗中有怨恨,在建构中有怨恨,在回瞥中也有怨恨。一方面,由于他们已经获得了西方文化的参照视野,就不可避免地怨恨本土文化的许多缺陷。异质文化的接受使他们已经有了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的强毅追求,并使他们文化心理的构建从根本上迥异于中国传统人格特征。另一方面,作为要求进步的具有“人”的自由、平等、独立意识的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们虽然在理智上追求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但在道德情感体验与审美价值判断方面却不时地回眸传统,传统有意无意的延续继承引起了他们内心情感的深层骚动,大力批判与深刻悲悯结合为艰难矛盾的灵魂对抗。甚至在局部情况与特定场合中,传统对现代知识分子造成的无形制约阻力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理性反抗动力。当他们认识到自身这种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以后,他们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极大的自我怨恨①知识分子的自我怨恨之个案研究参阅:王明科: 《孔乙己: 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11期上半月期,第35-41页。王明科: 《存在的怨恨: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多重难堪》,《社会科学评论》2006年第1期,第67-73页。,这种怨恨体验过程表现为由外发转向内省,由怨恨社会制度转向怨恨知识分子本身,由怨恨他者转为怨恨自我。
忧国忧民忧天下的济世思想与改变现实世界操作层面的实践欠缺之间的矛盾是知识分子产生自我怨恨的结构性根源。从传统知识分子即“士”起,中国知识分子一开始就宿命般地深陷这个矛盾之中。从知识视野与真理论证方面来看,“士”的眼光与胸怀均高于下层民众与上层重臣;但从社会地位上说,“士”的地位略高于一般民众,但却明显始终低于各级官僚;而从权利力量方面来论,“士”既没有拯救人民苦难的力量,也没有干预上层决策的权利,更不拥有直接操纵现实的实际权力。忧国忧民的“士”可以用言语批判社会的黑暗与时局的腐败,但同时却因无权无势而无能力改变黑暗社会与腐败时局,当这种社会关怀与言语批判伤及到统治阶级或者个别当权者的利益与安危时,“士”的良心与正义往往会变成违法乱纪的确证。当人民被逼走向起义,社会真正开始动荡之时,“士” 其实既不能广泛发动社会与大力组织民众联合暴动反抗,也不能就知识分子本阶层组成牢靠联盟去申讨时政流弊揭穿政客的种种阴谋,更不敢拿着武器去找有枪杆的政府算帐,而是就良知论良知,就动荡骂当局——而这正中了统治阶级的需要:需要用少数知识分子的“毒苗”来掩藏有权有势有机会做恶的自身官僚体系中的问题与罪恶,需要顺应“民意”来杀几个知识分子以泄公愤暂时缓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尖锐矛盾的白热化,需要通过宰杀知识分子“绵羊”而取得杀一儆百的恶做剧效果。面对专制帝王的焚书坑儒与株连九族的文字狱,知识分子除了忍受别无它法,因此他们心理积蓄着深仇大恨,但对暴君官僚与专制制度的怨恨丝毫不能改变现实社会与“士”人自己的实际状况, 所以他们不免将对于社会与暴君的怨恨逐渐转向对于知识分子自身的怨恨:怨自己无能,恨自己孱弱;怨自己无法改变现实,恨自己只能空谈。
价值追求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由外向转为内向的自我怨恨的动力性根源。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而言,现代性转型在价值领域意味着从传统儒家价值观向现代自由价值观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主动、自然、自愿的而是被动、被逼、革命的,因此价值转变的过程便是价值危机的过程,并且这种危机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首先是传统价值的危机,比如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取向危机,儒家精神信仰意义的取舍危机,儒家等级社会制度规则的秩序危机。其次是现代性价值的危机——将欲取代传统价值观念的现代性价值体系其实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明范式,而是多种因素的尖锐对立和复杂思想的紧张冲突。凡此种种危机,对其感受最清醒、最沉重、最紧迫的人就是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老农民完全可以继续以儒家的三纲五常来维持四世同堂,只要他们还有土地;小市民完全可以按照西方的拜金主义忙得不亦乐乎,只要他们还能赚钱;官僚们仍然想维持传统等级秩序与所有奴隶习惯与统治术略,这样有利于他们的统治;资本家仍然不顾一切地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因为有钱就是硬道理,有钱可以摆布一切甚至操纵政治——只有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只有他们在穷困与卑微中,仍然关注着价值与意义、思想与文化的危机,因此他们的怨恨就是最深刻、最复杂、最有代表、最有意义与最值得关注的心理情感体验。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危机是传统的法家、儒家、墨家、道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中国佛家等无法解决的,也是现代的自由、平等、正义、独立、民主等不能解决的,更是西方的博爱、忏悔、赎罪、祷告、唱诗不能解决的,所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并继续经受着多方面多层次的多重价值危机。如果社会要正常运转就得依靠保守主义的传统秩序与科学主义的理性工具,如果社会要进步就得依靠激进主义的反抗力量与自由主义的民主自由——在既相互冲突又互相抑制的多元价值并存系统中,旧价值体系的崩溃并不意味着其在局部与个别已经失去意义,新价值理念的建立也并不意味着其在所有领域已经具备完全的意义,也并不等于它就是最合理、最普遍、最完善的价值意义。如果要求得社会秩序的稳定,那又如何实现个人的自由?如果要实现个人的发展与独立,那又怎么保证社会的公正与平等?如果现代社会还需要终极关怀,那怎样处理因追求自由而带来的多元价值?如果承认了多元价值的并存,那又如何建立确定的统一的终极价值理念?如果种种价值发生冲突时,那又如何解决冲突?如果多元价值可以整合,那又怎样建立新秩序?如何来排序?哪个最重要最紧迫?如果价值冲突可以解决,那又以什么作为整合的基础?
所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就具有了极大的自我怨恨心理:因怨恨自我而寻求自我突围,因突围不了自我而怨恨自我;在怨恨自我中承担着突围,在承担突围中怨恨着自我,由此在不断的怨恨与突围中艰难地寻求着中国现代新价值的重建。
综上所述,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的怨恨体验,是有许多原因的:首先是由于历史上与现实中的战争动乱所导致,其次是反抗传统弊端所引起,再次是因为急于建构现代完美新文化而不得所导致,次次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却不得不回瞥传统而引发,最后是由于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而产生了自我怨恨。
[1] 王富仁. 中国现代文化指掌图[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2] 王明科. 论鲁迅反传统思想[D]. 中国优秀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 2003.
责任编辑:冯济平
The Seven Causes of the Resentment Experienc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ANG Ming-ke ZHAO Bin Zhang Hai-yan
( Dept of Humanities, Kashi Teachers' College, Kashi 844008, China )
Resentment in reality originated from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predicament. The pursuit of modernization led to the resentment against traditions. The strong inheritability of resentment led to the resentment arising from failure to fight traditions. The paradox of Chinese modernity led to resentment against modernity. The difficulty in constructing modern culture resulted in the resentment in the midst of construction. The difficulties in reconciling their concern for the country and people with their deeds to change the world are the source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self-resentment. Pursuit of value is the motivation-based origin of their self-resentment.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resentment; cause
I206
A
1005-7110(2013)01-0071-07
2012-11-06
喀什师范学院2012年度教学研究教学改革课题(喀师教发〔2012〕105号)重点立项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材建设研究与实践”阶段性成果。
王明科(1973-),男,甘肃庄浪人,文学博士,喀什师范学院人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赵斌(1966- ), 男, 新疆喀什人,喀什师范学院教授。张海燕(1968-),女,山东潍坊人,喀什师范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