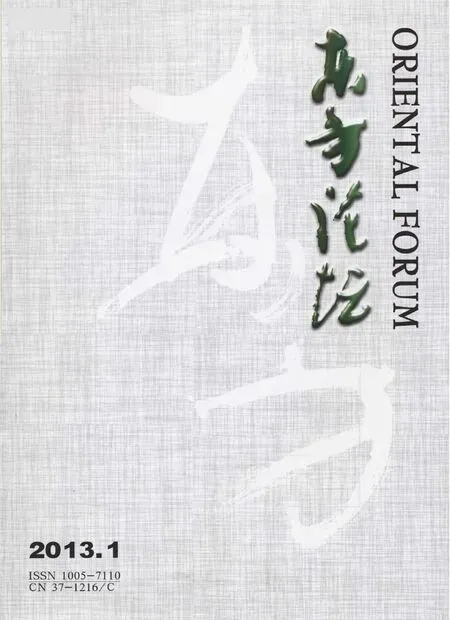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与语言、诗
2013-03-27马小朝
马小朝
(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与语言、诗
马小朝
(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海德格尔要人们重新关注人存在的意义问题,而澄清存在意义的哲学之思则必须通过语言、诗的研究路径。海德格尔强调人的存在与语言具有密切关系,其语言观是对传统语言观、更是对传统哲学观的解构。海德格尔向往的语言是诗意语言。从诗意语言出发,海德格尔生发出了他的文学艺术观。
海德格尔;存在;意义;哲学之思;语言;诗;文学;艺术观
海德格尔是当代西方哲学界最有创见的思想家之一。海德格尔认为西方思想的纯正源头是柏拉图以前的古希腊思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把思想弄成了哲学,弄成了形而上学。最初的形而上学尽管还保持着古希腊思想的伟大精神,但已开始遮蔽人的存在问题。后来的形而上学始终没有超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旧框架,最后在黑格尔和尼采那里发展到顶峰。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历史的发展也是对古希腊纯正源头的变异。人最初因为惧怕自然的强大力量而寻求技术的支持,但技术却反过来挤占了人的位置。海德格尔强调,形而上学的思想框架和技术统治的专制蛮横终于孕育出一个没有神性、从而也不关心人存在价值的世界。海德格尔要提醒人们重新关注一个久久被忽略的问题,即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海德格尔说:“任何存在论,如果它未首先充分地澄清存在的意义并把澄清存在的意义理解为自己的基本任务,那么,无论它具有多么丰富多么紧凑的范畴体系,归根到底它仍然是盲目的,并背离了它最本己的意图。”[1](P15)海德格尔认为,澄清存在意义的新的哲学之“思”可以通过语言、诗而挣脱形而上学的僵化束缚,捣毁技术霸权的强行奴役,从而为神性的重新来临、人的存在意义的回归创造新的可能性。
一、存在之思与语言
海德格尔说:“生存论概念把科学领会为一种生存方式,并从而是一种在世方式:对存在者与存在进行揭示和开展的一种在世方式。然而,只有从生存的时间性上澄清了存在的意义以及存在与真理之间的‘联系’,才能充分地从生存论上阐释科学。”[1](P421-422)那么,如何“从生存的时间性上澄清存在的意义以及存在与真理之间的‘联系’呢”?海德格尔先指出人的存在是由时间构成的,他说:“我们必须把时间摆明为对存在的一切领悟及对存在的每一解释的境域。必须这样本然地理解时间。为了让人能够洞见到这一层,我们须得源源始始地解说时间性之为领会着存在的此在的存在,并从这一时间性出发解说时间之为存在之领悟的境域。”[1](P23)海德格尔然后说明时间的延伸就是历史,他说:“此在的存在在时间性中发现其意义。然而时间性也就是历史性之所以可能的条件,而历史性则是此在本身的时间性的存在方式。”[1](P25)所谓存在的时间性、历史性,其实就是人类文化实践活动从低级向高级,人的生命存在从物质往精神的逐步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最伟大的标志性转折就是语言的发生发展。所以,海德格尔认为语言对人的存在的时间性、历史性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其实,18世纪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就曾经从发生学的角度,揭示了原始人如何凭借诗性智慧给外在的万千气象和内在的繁复情感命名,从而使人类如何有了一套可以指示千奇百怪现象事实、可以表达超经验感觉的语言工具。维柯还告诉我们,古希腊人、希伯来人的神话就是通过一个个以具体神灵为标志的象征隐喻,给内外在世界的诸多事物命名,从而凭借语词的魔力使诸多的事物有了笼统的概念,使人类的思维活动有了特定的概念排列、组合及分类。正如恩斯特·卡西尔所说:“神抵力量的真来源,每每是神的名称,而不是神本身。”[2](P644)也可以说,古希腊人、希伯来人就是通过象征隐喻性语言为内外在世界事物的逐一命名过程,使人头脑里关于世界的表象逐步清晰、完整,使人心灵的原始经验与情感逐步累积、沉淀,从而推动了人类思维意识的逐步发展;古希腊人、希伯来人尤其更借助各种神灵的名称作为其精神追求的寓宅,促进了人更积极主动与世界相交往,更深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实践活动的扩展和深化。海德格尔一方面也从发生学的角度指出:“语言,凭借给存在物的首次命名,第一次将存在物带入语词和显象。这一命名,才指明了存在物源于其存在并到达其存在。这种言说即澄明的投射。”[3](P69)另一方面更说明人的存在与语言的密切关系,他说:“在一种更源始的意义上,语言是一种财富。语言足以担保——也就是说,语言保证了——人作为历史性的人而存在的可能性。”“我们——人——是一种对话。人之存在建基于语言。”[4](P41)甚至直接强调有语言的地方才有人的世界,他说:“语言不只是人所拥有的许多工具中的一种工具;相反,惟语言才提供出一种置身于存在者之敞开状态中间的可能性。惟有语言处,才有世界。”[4](P40)以此为基础,海德格尔断定重新检查一切基本哲学观念和语言本质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重大任务。[5](P263)海德格尔说:“规定着此之在,规定着在世的展开状态的基本存在论性质乃是现身与领会。领会包含有解释的可能性于自身。解释是对被领会的东西的占有。只要现身同领会是同样源始的,现身就活动在某种领悟之中。同样有某种可解释性来自现身。”[1](P196)而“言谈同现身、领会在存在论上是同样源始的。”“现身在世的可理解状态道出自身为言谈。可理解状态的含义整体达乎言辞。”“把言谈道说出来即成为语言。”[1](P196-197)“在言谈之所云中得到传达的一切关于某某东西的言谈同时又都具有道出自身的性质。”[1](P198)“言谈通常说出着自身,而且也总已说出了自身。言谈即语言。而在被说出的东西里向已有领悟与解释。语言作为被说出的状态包含有此在之领悟的被解释状态于自身。被解释状态像语言一样殊非仅止现成的东西;它的存在是此在式的存在。”[1](P203)所以,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译者在其附录一《关于本书一些重要译名的讨论》中这样说:“‘领会’本身是可能性的‘筹划’,‘筹划’的基本方式是‘解释’,而‘解释’通过‘言谈’来进行。”[1](P522)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探讨“逻各斯”的概念时指出,“逻各斯”(logos)在希腊原文中的意义是言谈。亚里士多德曾经把言谈的功能精细地解释为“合乎语法的言谈”,“逻各斯”就是让人看某种东西,让人看言谈所谈及的东西。言谈“让人”从某某东西方面“来看”,也就是让人从话题所及的东西方面来看。只要言谈是真切的,言谈之所谈就当取自言谈之所涉,只有这样才能把所涉的东西公开出来,从而使他人也能够通达所涉的东西。这种“使公开”的意义就是展示出来让人看。[1](P40-43)“逻各斯”这个词后来具有的各种含义、以及人们所作的随心所欲的阐释,例如它一向被解释为理性、判断、概念、定义、根据、关系等等,皆不断遮蔽着它的本真意义。海德格尔在探讨“道”的概念时也认为:“也许‘道路’一词是语言的源始词语,它向沉思的人道出自身。老子的诗意运思的引导词语就是‘道’,‘根本上’意味着道路。但是由于人们太容易仅仅从表面上把道路设想为连接两个位置的路段,所以人们就仓促地认为我们的‘道路’一词是不适合于命名‘道’所道说的东西的。因此,人们把‘道’翻译为理性、精神、理由、意义、逻各斯等。但‘道’或许就是产生一切道路的道路,我们由之而来才能去思理性、精神、意义、逻各斯等根本上也即凭它们的本质所要道说的东西。”[6](P165)“澄明着和掩蔽着之际把世界端呈出来,这乃是道说的本质存在。”[6](P167)海德格尔进而强调:“表示如此这般思的词语之运作的最古老的词语,即表示道说的最古老的词语,叫做逻各斯——即显示着让存在者在其‘它是’中显露出来的道说。然而,表示道说的同一个词语逻各斯,同时也是表示存在即在场者之在场的词语。道说与存在,词与物,以一种隐蔽的、几乎未曾被思考的、并且终究不可思议的方式相互归属。一切本质性的道说都是对道说与存在、词与物的这种隐蔽的相互归属关系的响应和倾听。”[7](P203)海德格尔深感忧虑地告诫人们:言谈所谈及的东西、道说所道出的存在,却可能僭越言谈、道说,甚至反过来成为支配言谈、道说的形而上的理性规定。
言谈所谈及的东西、道说所道出的存在,何以可能僭越言谈、道说,反过来成为支配言谈、道说的形而上理性规定呢?海德格尔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角度考察了其中的原因。他指出,科学研究不是个别人的事业,必须有众多的人加入其中,这就需要相互交流,而交流又必须借助符号,特别是书面的、口头的语言符号。这样,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语言越来越被视为一种交流知识的工具,一个能为人们所了解、使用的符号系统。海德格尔因为对此在的“思”深感兴趣,而所谓此在的“思”既然同语言的道说密切相关,那么,语言就应该具有哲学本体论意义,同时也应该具有探问人存在意义的路径。海德格尔说:“现行的观点将语言认作为交流的工具。”“但是,语言并非是且并非首先是所要交流的听得见的和写出来的表达。语言并非只是将公开的和遮蔽的作为意图才转化到语句中去,不如说语言自身使所是,作为所是之物,首先进入了敞开。”[3](P68)“语言乃是一地域,也就是说,它是存在的家园。语言的本性并非在指称之中消耗自身,它也不仅仅是具有指号或密码特性的事物。因为语言乃是家园,我们依靠不断穿越此家园而到达所是。”[8](P120)海德格尔意在强调,语言更应该是存在之居,语言包含有对存在的显露,语言使人的存在在展开状态,仅仅把语言视为工具就大大贬低了语言作为“逻各斯”的意义。海德格尔说:“人表现为言谈的存在者。这并不意味着唯人具有发音的可能性,而是意味着这种存在者以揭示着世界和揭示着此在本身的方式存在着。”[1](P201)海德格尔相信,当人思索存在时,存在问题就进入了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寓所(house of being),人栖居在语言寓所中,使用语词思索和创作的人们就是这个寓所的守护者。
海德格尔的语言观是对传统语言观的解构,更是对传统哲学观的解构,具体而言,是对传统哲学观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解构。按照传统哲学观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人理所当然地是认知的主体,世界是人的认知客体,人总是面对着一个被动地等待着自己去认识的世界。在人与世界的这种关系中语言的功能是“再现”和“表现”,即帮助人这个认知主体“再现”客体的外在世界,“表现”主体的内心世界。海德格尔的语言观却告诉我们,人类的心智不是一面消极的镜子,只被动地映照现成外在世界的倒影,人类的心智更有一种主动的框架组织功能和想象创造功能。更进一步说,人类的心智可以通过想象性创造功能,创造出一个人类不得不相交往的客观人文文化世界,并在创造人文文化世界的同时建构起更有广度和深度的主观心智世界。海德格尔由此把传统的人与世界二元对立关系解构了,再也没有主体与客体之分了。人向世界开放,与此同时,世界也向人显露。在这种情况下,语言顺理成章地从原来的“再现”和“表现”的工具跃居到超越主体的地位。也就是说,不再像过去认为的那样是人讲语言,而是语言有自行道出的特点。海德格尔说:“但是在事实上,语言才是人的主人。”“因为,严格地说,是语言在言说。人只是在他倾听语言的呼唤并回答语言的呼唤的时候才言说。在我们人类存在物可以从自身而来并和自身一道成为言说的全部呼唤中,语言是至高无上的。”[9](P187)海德格尔这种观点的意义非同小可,在某种意义上它具有分水岭的性质。什么叫真(真理、真实) ?亚里士多德以来,“符合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影响极大。所谓符合论,就是强调再现、表现与判断、实际相符合。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凡以不是为是、是为不是者,这就是假的,凡以实为实、以假为假者,这就是真的。”[10](P81)他还在《范畴篇》中举例说:“一个人存在着这个事实,蕴涵着‘他存在着’这个命题的正确性,并且这种蕴涵的关系是交互的;因为,如果一个人存在,那么,我用来断定他是存在的那个命题也就是正确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用来断定他存在的那个命题是正确的,那么他就是存在的。但是,那个正确的命题绝不能是这个人的存在的原因,而这个人存在这个事实,看来才是这个命题之所以为正确的原因,因为命题的正确或错误取决于这个人存在或不存在这一事实。”[11](P46)海德格尔却说:“陈述的‘真在’(真理)必须被理解为揭示着的存在。所以,如果符合的意义是一个存在者(主体)对另一个存在者(客体)的肖似,那么,真理就根本没有认识和对象之间相符合那样一种结构。”[1](P263)很久以来,人们一直以为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对人产生意义的世界。现在,海德格尔告诉人们,这个实实在在的世界并不存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文本的世界、语言的世界。
二、存在之思与诗
海德格尔所关注的语言既不是严密、完善的理想语言,也不是具体多样的日常语言。理想语言追求逻辑的确定性,这正是海德格尔所反对的那种与存在相敌对的形而上学的根源。海德格尔更强调的是:“语言首先而根本地遵循着说的本质因素,即道说。语言说,因为语言道说,语言显示。”[12](P217)日常语言则仅仅是交际工具,它直接与此在的沉沦、烦、闲聊等非人状况相关,从而也不足以亮出存在并且形诸语言。海德格尔说:“言谈本质上属于此在的存在机制,一道造就了此在的展开状态。而言谈有可能变成闲谈。闲谈这种言谈不以分解了的领悟来保持在世的敞开状态,而是锁闭了在世,掩盖了世内存在者。”“无根的人云亦云竟至于把开展扭曲为封闭。”[1](P205)海德格尔所真心向往的语言是诗意语言(poetic language)。因为诗是最具有原始创生性的语言。维柯的诗性智慧研究就深入探讨了人类语言文化符号的诗性发生学原理。维柯说:“在诗的起源这个范围之内,我们就已发现了语言和文字的起源。”[13](P220)维柯认为:“野蛮人的最初的语言一定是在歌唱中形成的。”[13](P107)“所有异教各民族的历史都有神话故事性的起源。”[13](P151)“一切野蛮民族的历史都从寓言故事开始。”[13](P102)“最初的哲人们都是些神学诗人。”[13](P151)诗性智慧凭诗性的歌唱创造出识别外在事物和内在心灵的语言,语言又编织出解说人类历史的神话。神话就是人类文化世界的诞生,人类文化世界的诞生就是人类历史性的发生,从而也就是人性的实现。歌唱(诗)、语言浑然融会于诗性,诗性与历史性的交相纠缠建构起了人类文化世界,人类文化世界的创造完成了人类从野蛮自然本性向文明社会人性的脱胎换骨,从而实现了人的存在。海德格尔因为坚持人的存在的历史性,所以也认为诗意语言是同人的原初存在方式相连并直接使存在呈现的本真语言、纯朴语言。海德格尔说:“诗与思乃是道说的方式,而且是道说的突出方式。”[6](P169)“人类此在在其根基上就是‘诗意的’。”[4](P46)“与诗人这首独一的诗的真正对话不外乎是诗意的对话:诗人之间的诗意对话。但也可能是——甚至有时必须是——思与诗的对话,这乃是因为两者与语言之间有着一种突出的、尽管各各不同的关系。思与诗的对话旨在把语言之本质召唤出来,以便终有一死的人能重新学会在语言中栖居。”[14](P25)“语言本身在根本意义上是诗。……语言不是诗,因为语言是原诗;不如说,诗歌在语言中产生,因为语言保存了诗意的原初本性。”[3](P69)海德格尔因为认为诗、文学艺术是“真正的存在之思”,所以,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逐步转向研究艺术、诗的问题,并且从诗意语言的研究出发,自然地生发出了相应的文学艺术观。
海德格尔说:“艺术所是,应从作品推论。艺术品所是,我们只能在艺术的本性中获知。任何人都轻易地看到我们游弋于循环之中。一般的理解要求避免这种循环,因为它违反了逻辑。艺术所是,能从现实的艺术品的比较考察中获取。如果我们事先不知道艺术所是,我们又如何断定我们的这种考察是真正地建基于艺术品之上呢?”[3](P22)海德格尔依据他关于存在的时间性、历史性和主客观统一性的哲学立场,认为要探讨艺术的本源还不得不从这种循环开始,他说:“为了发现在艺术品中真正支配的艺术的本性,让我们探及一下具体的艺术品,并询问一下艺术是何和艺术为何。”[3](P22)他询问的第一个结果是“艺术品肯定是一制作物,但是它所表达的东西超过了自身所是。作品将这别的东西诉诸于世,它使之敞开。”“但是在艺术品中使这别的什么敞开出来的唯一因素以及与别的什么因素结合起来的唯一因素,仍是艺术品的物性。”[3](P23)海德格尔然后归结出三种关于物性的传统解释:第一,“物作为其特征的载体”;[3](P27)第二,“物无非它者而只是感觉的复合”;[3](P28)第三,“物是有形的质料”。[3](P29)海德格尔进一步认为:“第一种解释避免物与我们亲近,将它弃置甚远;第二种解释则使之过分急切强压在我们身上。在这两种解释中物消失了。因此必须避免这两者的夸大。物自身必须让它居留于自我包容之中,必须承认其坚固性。”[3](P29)而“物的恒定,物的坚固性,建立在质料与形式共生的事实上。物是有形的质料。”[3](P29)第三种解释尽管也不能给出“物性”的满意回答,但却可能指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那就是通过质料与形式引向了自然物质存在与人工制造活动,引向了人工制造活动中的功用性器具。所以,海德格尔说:“在解释物的过程中,那种把质料和形式作为尺度要求获得独特支配地位的观点难道是偶然的吗?对物的这种规定源于器具的器具性存在的解释。器具,因为通过人的制造活动而进入存在,所以,它与人的思考特别熟悉。同时,这种熟悉的存在物在作品中占据一独特的位置。我们将循着这条线索去首先寻找器具的器具性因素。也许这将启发我们思考关于物的物的因素,作品的作品因素。”[3](P33-34)那么,“哪条道路是通向器具的器具性呢?我们又如何知道器具事实上是什么呢?”[3](P34)海德格尔选择了凡高的“一双农鞋”的油画,作为其说明器具性,物的因素,作品因素的例子。
海德格尔说:“农妇穿着鞋站着和走着。这就是鞋如何真正地发挥作用。我们正是在器具的使用过程中,实际地遇到了器具的器具因素。”[3](P34)“只要我们只是一般地想象一双鞋,或者简单地观看画中徒然在此的空空洞洞无人使用的鞋,我们将永远不会发现器具的器具存在真正是什么。”“但是,从农鞋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劳动者艰辛的步履显现出来。这硬邦邦、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集着她在寒风料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永远单调的田垄上步履的坚韧和滞缓。鞋皮上粘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夜幕降临,这双鞋底在田野小径上踽踽而行。在这农鞋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成熟谷物宁静馈赠及其在冬野的休闲荒漠中的无法阐释的冬冥。这器具聚集着对面包稳固性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再次战胜了贫困的无言的喜悦,隐含分娩时阵痛的哆嗦和死亡逼近的战栗。这器具归属大地,并在农妇的世界得到保护。正是在这种保存的归属关系中,产生器具自身居于自身之中。”[3](P34-35)“器具的器具性确实存在其有用性之中。但是这种有用性又植根于器具有根本存在的充实性之中。充实性即可靠性。凭此可靠性,农妇被置于大地无声的召唤中去。凭此器具的可靠性,她把握了自己的世界。世界和大地为她而在,伴随她在她的存在方式中的一切存在只在这儿,即在器具中采用器具的方式。”[3](P35)海德格尔在这里从“有用性”出发分别引出了两对特殊内涵的术语:充实性与可靠性,世界与大地。充实性来自人战胜贫困、争取自由的艰辛劳动,而艰辛劳动又展示了人创造世界的喜悦;可靠性来自人无怨无艾、顺应自然的坚韧步履,而坚韧步履则显示了人归属大地的实在。由此,凡高这幅“一双农鞋”的油画无疑是要给人们揭示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从而也揭示人类存在的真理。正如海德格尔进一步所说:“我们已经寻找到了器具的器具存在。然而,这是如何寻到的呢?我们不是通过对一双实际在眼前的鞋的描述和解释,不是通过对制鞋工序的讲述,也不是通过对发生于此处或彼处的鞋的实际运用的观察,而是使我们面对凡高的绘画。”[3](P36)“凡高的绘画揭示了器具,一双农鞋真正是什么。这一存在者从它无蔽的存在中凸现出来。古希腊人称存在者的显露为aletheia。我们称为‘真理’,但在使用这一字眼时几乎不假思索。如果在作品中发生了一特别存在者的显露,它的为何和如何的显露,那么,艺术中的真理便产生了和发生了。”[3](P37)“在艺术品中,存在者的真理将自身置入作品。‘设入’此处意味着,即置放在显要位置上,一个存在者,一双农鞋,进入作品,处于其存在的光亮之中,存在者的存在的显现恒定下来。那么,艺术的本性将是:存在者的真理将自身设入作品。但是,迄今为止,人们还认为艺术是与美的东西和美有关,而与真理没有关系。”[3](P37)海德格尔显然是要明确地说明:艺术作品不是人对现成事物的模仿,更不是人对事物普遍本质的再现。所以,海德格尔还说:“但是,艺术即真理将自身设入作品的命题,是否会使已经过时的观点,即艺术是现实的模仿和反映卷土重来呢?……长久以来,真理的本质被看作是与所是的一致。但是我们是否以为,凡高的绘画描绘了一双现实存在的农鞋,而且是因为他成功地做到如此,它才是一艺术品呢?我们是否认为,这幅画把现实之物描画下来并使之成为进入艺术家制造的产品中去呢?绝对不是。”[3](P37)海德格尔还以迈耶尔的诗作《罗马的喷泉》为例说:“这首诗既不是对实际现身的喷泉的诗意描绘,也不是罗马喷泉的普遍本质的再现。但是,真理却设入了作品。”[3](P38)海德格尔再进一步追问:“艺术是以自己的方式敞开了存在者的存在。这种敞开,即显露,亦即存在者的真理产生于艺术品中。在艺术品中,所是的真理将自身设入作品。艺术乃是真理将自身设入作品。那么,什么是这种不时作为艺术出现的真理自身呢?什么是这种将自身设入作品呢?”[3](P40)海德格尔为了更清楚阐明真理自身设入作品的问题,又以希腊神殿为例进一步解释了前面引出的“世界与大地”。海德格尔说:“这一建筑包含了神的形象,并在此遮蔽之中,通过敞开的圆柱式大厅让它显现于神性的领域。凭此神殿,神现身于神殿之中。神的这种现身是自身中作为一种神圣领域的扩展和勾勒。然而,神殿及其围地不会逐渐隐去进入模糊。正是神殿作品首先使那些路途和关系的整体走拢同时聚焦于自身。在此整体中,诞生和死亡,灾难和祝福,胜利和蒙耻,忍耐和衰退,获得了作为人类存在的命运形态。这种敞开的相联的关系所决定的广阔领域,正是这种历史的民众的世界。只是由此并在此领域中,民族为实现其使命而回归自身。”[3](P42)我们不难明白,神殿是人创造出来的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它寄托着人的希望、梦想。“建筑屹立于此,建立在岩石的基础之上。作品的这种建基道出了岩石那种笨拙然而无所迫促的承受的神秘。建筑屹立于此,建筑顶住了其上凶猛的暴风雨,同时也首先使暴风雨自身显现了其暴力。……它澄明和启明了人靠何和在何之中,建立其居住。我们称这种基础为大地。”[3](P42)不难明白,神殿又是矗立在大地上的一个类同于石头、树木的存在物,它承受着自然的日晒、风吹、雨淋等。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与大地其实分别表示人性与自然性,或者人存在的历史性与自然环境的原生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的存在依赖自然环境而享有根基,自然环境则依赖人的存在而发生意义。所以,海德格尔进一步说:“当一世界敞开了自身,它提出胜利和失败,祝福和咒诅,支配和奴役问题的历史性的人性的决断。”[3](P60)“当世界敞开自己时,大地也出现了。它显示为万物的承受者显现为守护在其规律之中的自我隐含者。世界要求它的决断和衡量并让存在物达到其道途的敞开。大地,承受和凸现,力图保持自身关闭和将万物交付给自己的规律。冲突并非作为一撕裂的裂口般的裂缝(Riss);不如说,它是敌对相互归属的亲密关系。这一裂缝以一共同基础使它们达到它们统一的本源。”[3](P60)从最基本的人性与自然性、人存在的历史性与自然环境的原生性为出发点,还可以派生出一系列的辩证关系:比如人类社会目的与自然生态规律、超验精神理想与经验生活现实、价值设定与知识判断、自由游戏与道德功用等等。所以,海德格尔说:“神殿作品屹立于此,它敞开了一个世界,同时又使这个世界归回于大地。如此大地自身才显现为一个家园般的基础。”[3](P43)人的世界与自然大地辩证地交融发生在艺术作品中,即“通过建立世界,作品显现了大地”,“作品使大地进入到世界的敞开之中,并使它保持于此。作品使大地成为大地。”[3](P43)“世界是在历史性民众的命运中,简单和基本决定的宽阔道路的自我显露的敞开。大地是那永久的自我归闭者及其庇护者的无所迫使的显现。世界和大地相互根本不同但又不可分离。世界建基于大地,大地通过世界伸出。”[3](P48)“世界和大地的对立是一种抗争。”[3](P48)海德格尔还说:“真理的发生的一种方式便是作品的存在。建立世界和显现大地,作品是那种斗争的承担者,在斗争中存在者整体的显露,真理产生了。”[3](P54)“我们在现实的作品中寻找其本性。艺术的现实性的规定根据那在作品中发挥作用所是,根据真理的发生。这种发生,我们认为是世界和大地之间冲突的抗争。”[3](P56)海德格尔使用“世界与大地”的比喻,精辟地说明了文学艺术活动是人类社会目的与自然生态规律、超验精神理想与经验生活现实、价值设定与知识判断、自由游戏与道德功用等等对立统一的历史文化实践活动。所以,海德格尔尤其倾慕荷尔德林的诗句:“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上。”[9](P188)那么,包含着“世界与大地”的作品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海德格尔说:“作品的作品因素就在于它由艺术家所创造。”[3](P56)什么又是艺术家的创造呢?海德格尔说:“一作品的创造需要技艺。伟大的艺术家给予技艺以极高的评价。”[3](P57)“人们已充分指出,对艺术品知道相当多东西的古希腊人用techne代表技艺和艺术,并用同样的名字technites称为技艺者或艺术家。”[3](P57)而“所有艺术作为让所是的真理出现的产生,在本质上是诗意的。艺术的本性,即艺术品和艺术家所依靠的,是真理的自身设入作品。这由于艺术的诗意本性,在所是之中,艺术打开了敞开之地,在这种敞开之中,万物是不同于日常的另外之物。”[3](P67)“如果全部艺术在本质上是诗意的,那么,建筑、绘画、雕刻和音乐艺术,必须回归这种诗意。”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作品,狭义的诗歌,在艺术领域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3](P68)
海德格尔通过从诗意语言为起点,追问“艺术品的物性”引出了“质料与形式基础上的器具性”,再通过追问器具性而引出了“真理的设入”和“世界与大地”的比喻,最后通过说明“真理的设入”和“世界与大地”的发生而回到了诗意语言的终点。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与语言、诗终归获得了本体意义上的统一。所以,海德格尔认为:“艺术是真理设入作品,是诗。”[3](P69)“艺术的本性是诗。诗的本性却是真理的建立。”[3](P70)而“诗意并非作为异想天开的无目的的想象、单纯概念与幻想的飞翔去进入非现实的领域。诗作为澄明的投射,在敞开性中所相互重叠和在形态的间隙中所预先投下的,正是敞开。诗意让敞开发生,并且以这种方式,即现在敞开在存在物中间才使存在物发光和鸣响。”[3](P68)“诗意并非飞翔和超越于大地之上,从而逃脱它和漂浮在它之上。正是诗意首先使人进入大地,使人属于大地。并因此使人进入居住。”[9](P189)所以,海德格尔既反对把文学艺术当作急功近利的道德教化工具,也反对把文学艺术视为一种非功利的纯精神梦幻和人生饰物,他认为二者都忽视了文学艺术与人存在的原始的、固有的联系。所以,海德格尔一方面说:“作诗显现于游戏的朴素形态之中。作诗自由地创造它的形象世界,并且沉湎于想象领域。……诗宛若一个梦,而不是任何现实,是一种词语游戏,而不是什么严肃行为。”[4](P37)另一方面又说:“诗看起来就像一种游戏,实则不然。相反地,在诗中,人被聚集到他的此在的根基上。”[4](P49)海德格尔的文学艺术研究,本是其置疑现代科学技术物化威胁、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思想禁锢的哲学思考的重要内容。所以,海德格尔要把文学艺术活动还原为围绕人“存在”的历史文化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使人趋向存在的真实、领悟生命的价值。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在一贫乏的时代里作一诗人意味着,去注视、去吟唱远逝诸神的踪迹。”[8](P69)“看来必定是诗人才显示出诗意本身,并把它建立为栖居的基础。为这种建立之故,诗人本身必须先行诗意地栖居。”[15](P107)
[1]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87.
[2] 转引自卫姆塞特, 布鲁克斯. 西洋文学批评史[M]. 颜元叔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7.
[3] 海德格尔. 艺术作品的本源[A]. 诗语言思[C]. 彭富春译.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1.
[4] 海德格尔. 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A].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C]. 孙周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5] Wolfgang Bernard Fleischmann edited. Encyclopedia of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Volume 1,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 , Inc. 1967.
[6] 海德格尔. 语言的本质[A].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C]. 孙周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7] 海德格尔. 词语[A].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C]. 孙周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年.
[8] 海德格尔. 诗人何为[A]. 诗 语言 思[C]. 彭富春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1.
[9] 海德格尔. 人诗意地居住[A]. 诗 语言 思[C]. 彭富春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1.
[10] 亚里士多德. 形而上学[M]. 吴寿彭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11] 亚里士多德. 范畴篇[A]. 方书春译. 范畴篇 解释篇[C].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
[12] 海德格尔. 走向语言之途[A].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C]. 孙周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13] 维柯. 新科学[M]. 朱光潜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14] 海德格尔. 诗歌中的语言[A].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C]. 孙周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15] 海德格尔. 追忆[A].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C]. 孙周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责任编辑:冯济平
Heidegger's Thoughts on the Existence with relation to the Language and Poetry
Ma Xiao-chao
( School of Humanities, Yantai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China )
Heidegger hoped that all people c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uman existence again. He believed that the new philosophical thoughts must by means of language and poetry clarify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He emphasized that there is close relation between human existence and language. He further destructed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language and philosophy. He was looking for the poetic language and his view of literature emerged from the poetic language.
Heidegger; existence; meaning; philosophical thought; language; poetry; literature; artistic outlook
I0
A
1005-7110(2013)01-0041-07
2012-04-22
马小朝(1954- ),男,山西侯马人,烟台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外国文学及西方文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