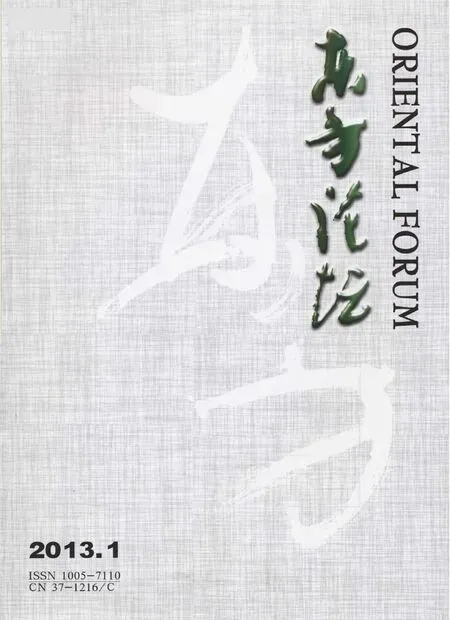中国古代“三代”“四代”历史意识溯源
2013-03-27王灿
王灿
(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中国古代“三代”“四代”历史意识溯源
王灿
(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尚书》在中国学术史上,最早按照虞、夏、商、周四代的顺序编纂,这种“四代”观念多见于先秦古籍,应是春秋战国时代才形成,是反向构筑起来的华夏历史系统,即由周、商、夏依次上溯而至尧、舜时代,体现了华夏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的内涵是:历史是在 “天下一统”的情形下运行的,历史的主体是“一统”的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而不是分裂的各个小族群。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华夏历史意识也是一种“大一统”政治观,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华夏历史意识还与“华夷之辨”密切相关。《尚书》“华夷”思想以文化为根本标准,并没有绝对的血缘界限和地域区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灵活性,与现代民族意识有很大不同,这是王道史观最重要的体现之一。
《尚书》; “三代”; “四代”;虞夏商周;历史意识;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
“夏商周”“三代”并提乃至“虞夏商周”“四代”并提的现象,是中国古代典籍中常见的现象。这种提法起源于何处?有何历史意蕴呢?
关于“三代”观念及其历史意蕴,刘家和先生曾经谈到:“在《尚书》和《诗经》里,还未见‘三代’一词。显然, 在周王朝尚未终结之前, ‘三代’就还不能作为历史反思的一个既定的对象出现。在《左传》里, 成公八年所记韩厥之言中开始提到‘三代’(可见在孔子以前, ‘三代’观念已经出现)。”[1]在论及《史记》时,刘先生进一步指出:“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首先是《五帝本纪》,随后就是夏、殷、周三个本纪以至秦、汉诸本纪。如果不看内容,人们是会有可能把五帝、三代之君误会为先后相承的统一国家的君主的。《史记》所反映的当然是大一统了的汉代的观念。中国文明自三代始,夏、商、周还不是真正的统一国家。这在今天已经为人们所公认。但是,难道司马迁的三代统一的观念就只有其自身时代的影响而没有任何历史的根据吗?不,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司马迁是历史家,他不能凭空说话,而是言必有据,尽管他的史料依据有时并不太可靠。他写夏、商、周三代本纪,所根据的是《尚书》《诗经》《左传》《国语》以及先秦诸子书中的有关资料。就以‘三代’的观念来说,他是有其充分的历史根据的。三代观念的源头见于《尚书》之中。传世的二十九篇《尚书》(伪古文诸篇除外)就是按虞、夏、商、周的朝代次序排列的。”[2](P306-307)刘先生指出:司马迁按夏、商、周顺序编排,是反映了“大一统”思想,而实际上观念的源头见于《尚书》之中;夏代应该存在过,并且夏、商两代确曾是当时的共主,这些因素正是“大一统”思想得以萌芽的最初土壤。[2](P306-309)张富祥先生除了表达了与刘家和先生基本相同的观点外,又进一步认为: 《尧典》和《舜典》的内容呈现为“文明进化论的断制”,《禹贡》篇“展示的是统一国家的政区设计”,这些都是“大一统”思想的体现;而“大一统”观念实堪称为“大义”中的“大义”,[3](P115-117)对《尚书》历史思想的重要影响予以极高评价。易宁先生也在论文中探讨说:周人已经认识到了夏、商、周三代相承及其与“天命”关系,这是“中国古代历史认同观念”的滥觞。他还指出:许倬云先生从金文入手,在《西周史》中也曾注意到这一点。[4]可见,学者们都注意到了夏、商、周三代史料被依次编排所体现出的历史意识,其本身带有“大一统”和“民族认同观念”的因素,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一、先秦古籍的“四代”“三代”意识
在探讨先秦时期“四代”或者“三代”历史意识之前,需要解释“华夏族”一词的起源以及该族群的历史发展等问题。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是上古时期华夏大地上的主体民族。[5](P422)叶林生先生曾经发表《“华夏族”正义》一文,系统梳理了华夏族的名称来历和华夏族本身的发展源流,指出:“华夏族从开始便是个复合概念,不是指古代某部族;华夏族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至春秋战国时才开始用‘华夏’作中国的代称,对远古的原始部族不能使用这个称谓。”[6]
既然华夏族在春秋战国才基本形成,那么它的前身则不能用“华夏族”这一称呼。因为中国历来以文化认同作为划分族群的最重要标准,因而在华夏族的诸形成要素中,文化同样占据主要地位。在华夏族形成之前,势必经过渐进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华大地上的主要人群对于华夏文化的认同感与日俱增,已经具备了华夏族的胚胎或者萌芽。但是,华夏族毕竟没有正式形成,“华夏”的称呼也没有正式出现,因而不能称之为华夏族。应该找出一个比较合适的词汇,这个词汇既能在时间上涵括华夏族尚未形成、只有其胚胎甚至萌芽的时期;又能包括“华夏族”这一词语的内涵。比较妥当的做法就是使用“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这一概念。[5](P422)这既基于文化在中国古代族群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又考虑到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共同体。因而,在本文中,我们用“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来概括华夏族的萌芽、发展乃至形成时的形态。这一族群的主要活动地域就是《尚书》所反映的中原及其周围区域,他们都认可华夏文化,构成《尚书》中虞、夏、商、周四代的历史主体。
在先秦古籍中,虞、夏、商、周四代依次排列的情形,在《尚书》中最早出现。下面将今本《尚书》的篇章目录按照先后顺序大致列出(以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为据),以探讨其后的历史意蕴:
书序(卷一)
虞书(卷二——卷五):1. 尧典 2. 舜典 3. 大禹谟 4. 皋陶谟 5. 益稷
夏书(卷六、卷七):6. 禹贡 7. 甘誓 8. 五子之歌 9. 胤征
商书(卷八——卷十):10. 汤誓 11. 仲虺之诰 ……25. 西伯戡黎 26. 微子
周书(卷十二——卷二十):27. 泰誓上 28. 泰誓中 ……57. 费誓 58. 秦誓
从上述可见,《尚书》的这种编排顺序与后世“大一统”王朝正史中将各主要朝代相续排列的格局相同,很显然,《尚书》将虞、夏、商、周视为四个先后相继的“朝代”,它们各是那个时代的“中央王朝”,而历史的主体也只有一个:华夏大地(以中原地区为中心)上的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这种意识,反映出《尚书》的编者将华夏大地上的所有民族视为同一民族文化共同体即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历史的唯一主体就是这个民族文化共同体。因而,我们可以称这种历史观念为“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历史意识”,简称“华夏历史意识”。
《尚书》所记载的时代,起自尧舜禹时期,终于东周秦穆公时期(春秋早期)。《尚书》既反映了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史实和传说,又折射了它在被整理、编纂过程中的思想观念,因而《尚书》实际上可以反映出双重的历史内容。《尚书》所记载史事与编纂者及其所在时代思想之间的张力,使得我们可以借此窥见隐藏在《尚书》编纂体例和特殊用语背后的历史思想。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历史意识,就是《尚书》历史思想中较隐蔽但又非常重要的方面,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值得深入探讨。
其实,这种虞、夏、商、周“四代”并提的现象,春秋战国的先秦古籍多有之,可以作为例证。比如,张富祥先生就曾在论文中缕列过: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故有得神以兴, 亦有以亡, 虞、夏、商、周是也。”又成公十三年: “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 亦既报旧德矣。”又襄公二十四年: “昔之祖, 自虞以上为陶唐氏, 在夏为御龙氏, 在商为豕韦氏, 在周为唐杜氏。”又昭公元年: “虞有三苗, 夏有观扈, 商有女先邳, 周有徐奄。”
《周礼·考工记》: “有虞氏尚陶, 夏后氏尚匠, 殷人尚梓, 周人尚舆。”
《国语·郑语》: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 其子孙未尝不章, 虞、夏、商、周是也。”
《墨子·明鬼下》: “昔虞、夏、商、周, 三代之圣王, 其始建国营都日, 必择国之正坛, 置以为宗庙。”
《墨子·非命下》: “子胡不尚(上)考之商周、虞夏之记?”
《吕氏春秋·审应览》: “今虞、夏、商、周无存者, 皆不知反诸己也。”
《韩非子·显学》: “殷周七百余岁, 虞夏二千余岁, 而不能定儒、墨之真。”[7]
除张先生所举之例外,[5](P423)先秦古籍中还有个别将“虞夏商周”连称的例子,如:
《记》曰:“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唯其人。”语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国治,君之谓也。[8](P635)(《礼记·文王世子第八》)
鸾车,有虞氏之路也。钩车,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绥,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夏后氏骆马黑鬛,殷人白马黑首,周人黄马蕃鬛。……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有虞氏之绥,夏后氏之绸练,殷之崇牙,周之璧翣。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用之。[8](P944-954)(《礼记·明堂位第十四》)
除了在字面上将“虞夏商周”连称的例子外,先秦古籍中还有一些关于“四代”的说法,虽然没有并提“虞夏商周”,但是其意涵与“虞夏商周”连称相同:
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记》曰:“三王、四代唯其师。”此之谓乎(《礼记·学记第十八》)
另外还有将“夏商周”或“夏殷周”之类连称之例: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有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9](P23-24)(《论语·为政第二》)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9](P210-211)(《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10](P134)(《孟子·卷五·滕文公上》)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10](P136)(《孟子·卷五·滕文公上》)
当然“三代”之说则尤其多。下面分类列举。首先,《礼记》中的“三代”之说最多,请看以下几例:
反哭之吊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于是为甚,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孔子曰:“殷已悫,吾从周。”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8](P271-272)(《礼记·檀弓下第四》)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8](P656)(《礼记·礼运第九》)
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诏侑武方,其礼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礼其犹醵与!”[8](P743-744)(《礼记·礼器第十》)
肆直而慈爱,商之遗声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识之,故谓之《齐》,明乎商之音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音者,见利而让。[8](P1147)(《礼记·乐记第十九》)
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8](P1376)(《礼记·哀公问第二十七》)
《左传》中的“三代”之说也颇多,下面略举两例:
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之禄。夫岂无辟王,赖前哲以免也。《周书》曰:‘不敢侮鳏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11](P734)(《春秋左传·成公八年》)
郑子产聘于晋。晋侯疾,韩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寝疾,于今三月矣,并走群望,有加而无瘳。今梦黄熊入于寝门,其何厉鬼也?”对曰:“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韩子祀夏郊,晋侯有间,赐子产莒之二方鼎。[11](P1243-1246)(《春秋左传·昭公七年》)①“三代”连称,《左传》和《礼记》尚有其他例子,此处不再多引。
《孟子》中也有“三代”之说: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由恶醉而强酒。”[10](P191)(《孟子·卷七·离娄上》)
还有“虞夏”连称之例:
景公与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望见齐国,问晏子曰:“后世孰将践有齐国者乎?”晏子对曰:“非贱臣之所敢议也。”公曰:“胡必然也,得者无失,则虞夏常存矣。”[12](P471)(《晏子春秋·卷七》)
另外,在成书年代较晚,但所涉素材多为先秦时期的古籍亦有一些例子:
公曰:“四代之政刑,论其明者,可以为法乎?”子曰:“何哉?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公曰:“以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否,不可。臣愿君之立知而以观闻也,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则缓急将有所不节,不节君将约之,约之卒将弃法,弃法是无以为国家也。”[13](P164)(《大戴礼记·四代第六十九》)
至于当时人们为什么有时不将“唐尧”时期专列为一代,《尚书正义》中曾有解释说:
正义曰:《尧典》虽曰唐事,本以虞史所录,末言舜登庸由尧,故追尧作典,非唐史所录,故谓之《虞书》 也。郑玄云“舜之美事,在於尧时”是也。[14](P20)
由于《尧典》是舜时史官所记录,因而,《尧典》中所涉及之关于尧的事情,都是由于追记而得,因而不把唐尧之时专列为一代。《尚书正义》还接着解释了“虞夏同科”之理由:
案马融、郑玄、王肃、《别录》题皆曰《虞夏书》,以虞、夏同科,虽虞事亦连夏。此直言《虞书》,本无《夏书》之题也。案郑序以为《虞夏书》二十篇,《商书》四十篇,《周书》四十篇,《赞》云“三科之条,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14](P20)
《尚书正义》的理由是:由于虞舜和夏禹之事往往相连,很难截然分清,所以可以合为一类,故称“虞夏同科”。
总之,以上所列举古籍,除最后的《大戴礼记》外,主要内容都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其共同点是,都将虞、夏、商、周(或夏、商、周)视为前后相续的、统治华夏民族所居之广大区域的四个(或三个)“大一统”“王朝”,历史的主体就是一个:“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既然先秦时期相当多古籍都有这种观念,这就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这种观念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而毫无疑问,在这些之中,《尚书》是最早的源头。
二、“三代”“四代”历史意识与历史实际之间的差异
滥觞于《尚书》、存在并发展于先秦时代的华夏历史意识,与虞、夏、商、周时代的历史实际是有差异的。
考古和文献研究都表明,先秦时期,中华大地上曾经是“万国”并立,到春秋时期也有百余个国家同时存在,并不存在像后世那样的“大一统”国家。虽然当时确实存在一个“共主”,共主政权对地方政权也有一定影响力,但这毕竟不是后世的“大一统”王朝,二者不可相提并论。换言之,当时既没有出现秦朝、汉朝那样的“大一统”王朝,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华夏民族。因此,就历史实际而言,《尚书》所表露出的历史意识不应该超越它所记载的那个时代,不应该反映出“大一统”王朝相继并立的观念和类似于“华夏民族为唯一历史主体”的历史意识。然而,今本《尚书》却是按照虞、夏、商、周“四代”顺序编排的,实际上,这里隐含的历史思想就是: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及其所在的虞、夏、商、周等“大一统”国家,是历史发展的唯一主体。
那么,《尚书》这种虞、夏、商、周四代相继的编排顺序及其显现出的华夏历史意识,它们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历史意识的自然扩大。有学者曾言:“所谓历史意识,就是对过去的感知和理解。初级的、感知的历史意识是先天固有的,也可称作本能的、不自觉的历史意识,它来自人类最重要的本能之一:记忆—回忆。”[15](P5)越往远古,限于条件,人们的活动区域相对越小,其历史意识所反映的生活范围亦越小。最初,人们对于历史的认知主要还是关于自己祖先、家族或者部族发展史的记忆和回忆。吴怀祺先生在谈及原始历史意识的发展历程时曾说:“为了自身的生存,远古的先民从最初仰观俯察自然变化中,产生出经验的观念,这就是原始历史意识。……从图腾崇拜到远祖崇拜、近祖崇拜,反映出原始历史意识的发展。从虚幻的始祖和真实世系的结合,进而表现为对先祖的‘慎终追远’,这本身就是在混沌的挣扎着向前发展的漫长的进程。如果说图腾崇拜还只是以虚构的始祖业绩鼓舞氏族的成员,那么,祖先崇拜则是追念先祖在开拓中创造出的真实业绩,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16](P173.P177)吴先生在此指出历史意识所反映的时间段会不断拉长,由切身而范围最小的“经验的观念”到“图腾崇拜”“远祖崇拜”“近祖崇拜”,历史意识所反映的人群范围也逐渐扩大。但在以氏族、部落为主要生活集团的远古时期,人们历史意识的思维范围最大也不过是自己部族的发展史。随着更大人群的出现,这种历史意识所反映的范围也会逐渐扩大。在远古时期,历史意识所反映的时间段和地域范围,随着经验范围的扩大,呈现递增趋势,这是有道理的。总之,历史意识随着地域和生活范围的扩大而发展,是华夏历史意识的第一个成因。
其二,对民族和文化的认同不断加强。张富祥先生指出: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应该是一个“纵向的历史行程”,“古人对中国古史的认识也确是越往后而越往前延伸,对古史的‘编年’也是逐渐清晰起来的”,在这方面“古史辨派”的观点有其合理之处。[5](P422)在《尚书》编纂时,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随着文化成果的累积和普及程度的提高、文献记载逐渐渗入人们的意识之中,人们对这一共同体及华夏文化的认同感越来越强,编纂者自觉不自觉地用后世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稳固的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来想象他们以前的时代,认为自虞、夏以来都是如此,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是自古以来就如此牢固结合的。于是他们不自觉地将虞、夏、商、周四代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编排,视之为统一的王朝相继,历史的唯一主体就是这些王朝的人民群体: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很明显,这是《尚书》后世学者在编纂《尚书》的过程中,将自己及自己所生活时代的历史观念渗入《尚书》中,使之被改造,从而体现为现在“四代”相继的面貌。换言之,所谓虞、夏、商、周“四代”相继的观念,实际上是在后来随着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滥觞与凝聚,才逐渐产生出的,这种涵盖各部族、各地域的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历史意识,多见于先秦古籍,它们多是春秋战国时期成书,可见这种“四代”观念也应该是春秋战国时代才形成的,是反向构筑起来的“华夏”历史系统,即由周、商、夏依次上溯至尧、舜时代。关于这点,张富祥先生曾有过较详细的论述。[5](P422)
张富祥先生还曾在相关论文中,对华夏历史意识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和推断:“纯从史学上讲,我国古代官修的编年体王朝史和诸侯国史是到西周后期才开始出现的(确切的纪年始于公元前841年),想来人们对上古历史的完整认识也应到这时才开始确立。《尚书》按虞、夏、商、周‘四代’的顺序编辑, 正反映了这一历史认识的程序。大概在夏、商之际, 虽已可能有‘夏商’的联称,而由于当时社会组织体系的松散、社会变动的无常、华夏民族共同体观念的薄弱以及历史记录的缺乏等因素,人们的‘断代’观念还相当模糊。到西周时期, 随着民族融合的加强、文化的进步和文献的增多,人们的共同体观念和历史观念日趋强化,才逐步对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有了完整的认识,并进而追加虞舜历史而构成了‘四代’之称(同时也已上溯到唐尧以前)。”[7]张先生这段论述从社会组织体系、民族融合、文化的进步等角度说明了“四代”意识的产生缘由。
其三,从不同的历史视角出发,可以导致产生不同的历史观念。葛兆光先生曾经指出:现代西方学者视一些原始状态下的民族为“未开化”者,认为他们都最终要像西方那样进化到“开化”状态,这种观点,其实质是要将历史中的地域差异转化为时间差异,从而造成历史发展的统一模式,亦即“西方中心”的“线性进化论”模式。[17](P10-11)葛先生从地域差异和时间差异的转换入手,看待历史观念的实质问题,非常具有启发性。同样,依此思路,我们可以看到: 《尚书》编纂中也清楚地反映出夏、商、周是相互递嬗的三个朝代(如果算上“虞代”是四代),在此基础上建构出“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历史意识,①除了需要特殊强调外,本文以下都将“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历史意识”简称为“华夏历史意识”。但是,如果是其他学者的特殊称谓如“华夏认同”时,则遵从原作者的说法,不妄改动。并进一步发展出以后的“大一统”思想。从地域和时间差异相互转换的角度看,这种思想的实质是将本来并不十分准确、并不绝对的所谓时间差异(夏商周三族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并存的),转化为绝对存有时间差异(夏商周三代相继而非并立),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相同的地域意识(“华夏”大地上的统一王朝),同样也最终建构了一种历史发展的统一模式(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发展模式),这种历史观念本身涉及历史主体和历史变动两方面的问题,并且在日后逐渐发展为了“大一统”的政治观,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其四,民族融合的加强和国家走向“大一统”趋势的愈加明朗,提供了华夏历史意识的时代背景,强化了华夏历史意识。华夏历史意识的产生和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越往历史的后期,这一意识就越得到强化。这种强化既和上述的历史记忆、文化进步、历史视角有关,也与历史发展中客观形势的变化有关。总体上看,从虞夏时代到商周时代,我国的政治统一性是不断加强的。[18](P2-129)这种政治上统一性的加强,既是文化和历史意识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影响这二者的因素,三者交互为用,彼此影响。特别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周天子的权威大为下降,但是,相反,列国数目锐减、整个华夏大地走向“大一统”的趋势并不因此而改变。这种日趋明朗的统一趋势,都使得华夏历史意识被不断强化。从这个角度看,华夏历史意识也是“王道”理想在新历史形势下的再现。
三、总结
作为古代“王道”理想的具体表现之一,华夏历史意识对中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以及民族凝聚力。曾有学者言:“中国历史有很强的延续性,这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分外强烈”,[19](P35)这种说法自然有其相当道理,尤其是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但是,“中国历史有很强的延续性”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分外强烈”二者之间是相互为用、相辅相成的。从精神的能动性这一角度而言,强烈的历史意识对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同样起到很大促进作用;“大一统”观念对保持国家的统一和壮大也非常关键。《尚书》是中国文化最早的经典,更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华夏历史意识在政治思想上表现为极强大而独特的“大一统”政治观,而这种“大一统”政治观又与中国史官制度结合一起互相作用:史官制度将“大一统”政治思想转化为统一的民族意识,统一的民族意识在包括史书在内的文化典籍中又表现为“大一统”政治观,并通过政治制度和官员施于现实政治和文化,史官制度及其文化又被强化,如此循环不止。可见,华夏历史意识和“大一统”观念二者本为一体,又各有侧重,交互为用,对铸造中国“大一统”国家及其历史思想传统,对形成从未断裂的中国文化和历史这一奇迹,确是厥功甚伟。
参考文献:
[1] 刘家和. 从“三代”反思看历史意识的觉醒 [J]. 史学史研究, 2007, (1): 1-6.
[2] 刘家和. 史学经学与思想: 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5.
[3] 张富祥.〈尚书〉概说 [A]. 郑杰文, 傅永军主编. 经学十二讲[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4] 易宁. 中国古代历史认同观念的滥觞——〈尚书·周书〉的历史思维 [J]. 史学史研究, 2010, (4): 3-6.
[5] 张富祥. 东夷文化通考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6] 叶林生. “华夏族”正义 [J]. 民族研究, 2002, (6): 60-66.
[7] 张富祥. 华夏考——兼论中国早期国家政制的酝酿与形成 [J].东方论坛, 2003, (4): 37-45.
[8]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简体字版) [M]. 李学勤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9]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简体字版) [M]. 李学勤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0]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简体字版) [M]. 李学勤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社, 1999.
[11]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简体字版) [M]. 李学勤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2] 吴则虞. 晏子春秋集释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13] [清]王聘珍. 大戴礼记解诂[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14] 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 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简体字版) [M]. 李学勤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5] 郭小淩. 西方史学史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6] 吴怀祺, 林晓平.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总论 先秦卷 [M]. 吴怀祺主编, 合肥: 黄山书社, 2005.
[17] 葛兆光. 中国思想史(第1卷)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18] 周谷城. 中国政治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19] 庄国雄, 马拥军, 孙承叔. 历史哲学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责任编辑:侯德彤
Origin of the Historical Concept of “Three Dynasties” and “Four Dynasties” in Ancient China: Its Significance and Influence
WANG Can
( College of Humanities,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471023, China )
In Chinese academic history, The Book of History was the first to be complied in order of the four dynasties. This four-generation concept, often observed in the pre-Qin books, was formed only in the Spring-and-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t is a Chinese historical system established in a reverse direction, i.e., from Zhou, Shang, Xia up to Yao and Shun periods. This shows that history runs in a unified country rather than in a cluster of divided kingdoms. This outlook of great harmony has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ver later centuries. The Book of History treats culture as the root, without a clear blood or regional boundary. It is very inclusive and flexible.
The Book of History; three generations; four generations; Yu, Xia, Shang and Zhou;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the cultural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K092
A
1005-7100(2013)01-0006-07
2012-11-26
本论文是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中国古代史论研究”(编号12RWZD08);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学术研究项目“儒学史论文献汇编”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并得到河南科技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的资助。本文的写作受到了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张富祥先生的具体指导,谨此致谢。
王灿(1972-),男,山东枣庄人,博士,河南科技大学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学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