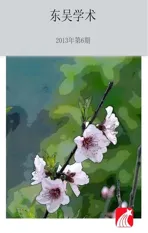《废都》二十年:贾平凹小说在国外的研究
2013-03-27史国强
史国强
改革开放之后,经 《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最早一批翻译成英文的作品里,就有贾平凹的作品。①《中国文学》(英文版)1951年创刊,被称为对外传播中国文学的重要窗口,在50年的时间里,出版590期,在上面出现的作家和艺术家,超过2000人次,译载文学作品3200篇,其中就有贾平凹的 《果林里》、《帮活》(1978年第3期),《满月儿》(1979年第4期),《端阳》(1979年第6期),《林曲》(1980年第11期),《七巧儿》、《鸽子》(1983年第7期),《蒿子梅》、《丑石》(1987年第2期),《月迹》、《我的小桃树》(1993年第2期)。见姜智芹《欧洲人视野中的贾平凹》,《小说评论》2011年第4期。一九八一年“熊猫丛书”开始对外发行,出版贾平凹的作品集《天狗》和《晚雨》,之后外文出版社还出版了贾平凹的英文散文集 《老西安:废都斜阳》(Old Xi’an:Evening Glow of An Imperial City)。可以说,贾平凹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走出国门的作家之一。
与国内的汉译英相比,国外对贾平凹的研究兴趣,发生的要晚一些。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研究文章在著名英文刊物上陆续出现,其中以评论《浮躁》与《废都》者为多数,择其要者,如劳伦·贝尔法(Lauren Belfer)的《评〈浮躁〉》,②Lauren Belfer,“Review of Turbulence,”New York Times(Sept.22,1991).保罗·哈钦生(Paul E.Hutchinson)的《评〈浮躁〉》,③Paul E. Hutchinson,“Review of Turbulence.”Library Journal 116 (1992):145.王德威的《评〈浮躁〉》,④David Der-wei Wang,“Review of Turbulence.”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6,1/2 (1992):247-250.金克雷(Jeffrey C.Kinkley)的《评〈浮躁〉》,⑤Jeffrey C.Kinkley,“Review of Turbulence.”Choice 29(April 1992):1235.卢恩(K.C.Leung)的《评〈浮躁〉》,⑥K.C.Leung,“Review of Turbulence.”World Literature Today 67 (Winter 1993):232.此外还有雷金庆(Kam Louie)的《男阉》,⑦Kam Louie,“The Macho Eunuch:The Politics of Masculinity in Jia Pingwa’s ‘Human Extremities.’”Modern China 17,2 (1991):163-87.罗鹏(Carlos Rojas)的《蝇眼》,⑧Carlos Rojas,“Flies’ Eyes,Mural Remnants,and Jia Pingwa’s Perverse Nostalgia.”positions: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14,3 (Winter 2006):749-73.查建英的《黄祸》,⑨Zha Jianying,“Yellow Peril.”Tri Quarterly 93 (Spring-Summer 1995):238-64.王一燕研究贾平凹的专著《叙述中国》,⑩Wang Yiyan,Narrating China:Jia Pingwa and His Fictional World.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6,reprintedin 2012.及司徒祥文研究贾平凹早期作品的博士论文。《浮躁》在国外可谓好评如潮,这与小说一九八八年获得美国的“美孚飞马文学奖”不无关系。与这股评论热潮几乎同时发生的,是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译出的英文版《浮躁》。①Jia Pingwa,Turbulence,trans.Howard Goldblatt,LSU Press,1991.2003年《浮躁》复经Grove Press出版社发行平装版。此后评论文章不断出现。
从研究文章的标题评判,以 《男阉》、《蝇眼》、《黄祸》最为称奇,几乎与流行小说不相上下,若是从研究的深度和宽度评判,首选王一燕的《叙述中国》。此外,以上几位研究者还有一个特点,他们虽然是用英文研究贾平凹的小说,但他们的汉语水平为一般国外研究者所不及,他们不是自幼说中文,就是身边有说中文的太太,所以研究的水平,也为一般人所不及。最后还要提到司徒祥文的博士论文The Peasant Intellectual Jia Pingwa:A Historico-Literary Analysis of His Life and Early Works(《农民知识分子:贾平凹早期作品论》)。论文的作者明确表示,以贾平凹为研究对象,是要让中国文学走出国门,与普通的外国读者见面。②John Edward Stowe,The Peasant Intellectual Ja Pingwa:An Historico-Literary Analysis of His Life and Early Works,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Toronto,2003.下面将逐一评述上文五位的研究成果,希望国内读者从中有所借鉴。
不过,不要就此推断,他们的研究能得出同一个结论。比如,小说《废都》的名字就被译成了好几个,可谓五花八门,各得其所:Ruined Capital(废都),The Abandoned Capital(被抛弃的都城),Capital in Ruins (废墟上的都城),Fallen City (陷落的城),Deserted City (空城),Ruined Metropolis(废都),Abolished Capital(废都),Defunct Capital(死都),以上还是英文的译法,法文的译法更浪漫:La Capitale déchue(近乎没人要的都城),因为法语里的femme déchue与汉语的“失足女子”相差无几。好在还是凭借这个法语译名,《废都》获得了法国一九九七年度“费米娜文学奖”,这个奖项与龚古尔文学奖、梅迪西文学奖合称法兰西三大文学奖。贾平凹不仅是中国,也是亚洲第一位获此奖项的作家。“费米娜文学奖”要求入选作品发行一定的册数 (八万?)以上才能入围,所以,凡获奖者必先拥有国内外的读者,读者的多少又与评论文章相关,这几个因素同时发生,作品才可能入选,作者要有相当的实力才行。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作者的因素之外,上面提到的文章,也有推波助澜之功。
《人极》的男性政治
雷金庆撰写的长文《男阉:贾平凹小说〈人极〉中的男性政治》,③雷金庆撰写此文时身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大学,现为香港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学术研究旁及文学、语言、历史、哲学,著有《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刘婷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等专著。从历史、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角度,研究分析贾平凹的《人极》(一九八五)。④《人极》最早发表在1985年《文汇月刊》的10月号上,1988年经朱虹译成英文,题为“How Much Can a Man Bear?”(《一个男人到底能承受多少?》)。雷金庆生在中国,熟稔中国历史,所以他能高屋建瓴,先从历史入手,指出中国人的观念与三大传统相关:封建传统、五四传统、一九四九年之后“十七年”形成的惯性,这三种传统互相抵牾,又互相依存,裹挟着中国社会不停地旋转流动,在这三种传统的裹挟下,凡是以性爱和性别为话题的写作,几乎无一不是经过男性来完成的。即使五四时期有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人物反复撰文批评压迫妇女,提倡自由恋爱,自由婚姻,但他们到底还是男性,他们的写作还是从男性的角度出发的。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十年,流行的是性爱清教主义,在公开发行的出版物里几乎找不到哪怕是三言两语的性爱描述。等到改革开放的七十年代末,这种极端的清教色彩才有所改变,出现了张洁、谌容等书写女性的女作家。不过,令人感到滑稽的是,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不论出自男作家还是女作家,所关注的依旧是女人的不幸,很少旁及女人不幸的根源所在——男性。八十年代中期之后,才有少数男作家在小说中探讨他们的性行为,可惜,结果并不理想。这一时期在女性中普遍流行的看法是,在中国很难找到真正的男人(real man),或能被称为汉子的男人,“太监化”(eunuchization)成为普遍现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贾平凹发表了他的小说《人极》。
雷金庆指出,《人极》的发表又与 “寻根文学”不无关联。曹文轩就在其《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一书中,用一章来寻找“硬汉”形象,以为蒋子龙、张贤亮、张承志、梁晓声等作家更接近海明威或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所描写的“硬汉”形象,其特点是:(一)冷漠的外表下储藏着深沉的情感,(二)不可摧毁的意志和超出常规的韧性,(三)他们永远是打不败的。①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251-26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杰克·伦敦小说《墨西哥人》里革命者李维拉与这个定义相吻合。)曹文轩如此浪漫的定义,大概也是对中国没有好汉的一种反拨或自我反省。不仅是小说,电影(如《黄土地》和《红高粱》)和歌曲(《西北风》)也在呼唤真正的男人。《人极》中的男人光子,也部分地有着上文提到的品质,但雷金庆的兴趣不在何谓好男人,他是从性别与阶级的角度出发,研究贾平凹对男人气魄的歌颂,进而分析性别和等级与社会权力和社会控制等概念的关系,其目的是考察八十年代中国的人际关系。
《人极》描写两青年与两女子。弟弟光子以劁猪骟驴为生。村上发水,光子捞上一姑娘亮亮,“其女年轻,面润如生”。两人将她救活。光子外出,哥哥拉毛与姑娘发生关系。光子骂拉毛“猪狗不如”。拉毛自杀。亮亮因上告入监。光子为拉毛“守孝”三年。光子又遇乞讨女白水。白水被“造反派”强奸,生一子虎娃。光子与白水成家。有夫之妇白水被其丈夫夺走。“文革”结束,亮亮出狱,与光子结婚,继续四处告状,终为其父平反。亮亮病死,虎娃与光子疏远。孑然一身的光子陷入虚幻。
雷金庆发现,光子身上有着男子汉的品质,虽然以劁猪骟驴为生,但他始终坚守道德底线,对女人表现出稀有的男人风度,而且他还有着强健的体魄和超人的胆识(“当下口叼了一把砍刀,溜下水去”),称得上“阳刚”概念的化身。与之相反,亮亮颠覆了传统女性“阴柔”的形象。她的出现不仅造成了拉毛的死,还最终引发光子与虎娃的分裂。虽然她以执著的精神,让父亲沉冤昭雪,但出狱后的她已经变成粗糙的女人,后来成为教师又患上水肿病,身体臃肿,脾气暴躁,不仅颠覆了自己的形象,也失去了女性的魅力,还好,她的灵魂始终没有被玷污。雷金庆认为,从阴阳的角度分析故事并不牵强,因为贾平凹对古老的乡土文化总是怀着眷恋之情,故事里的种种安排,与其说是机缘巧合,不如说是小说家的有意为之,如光子手里的刀,不仅是传统上男性形象的饰品,还执行着另外两种功能,捞人(用来砍断河里的水草)与劁猪(“寒光一闪,就在猪腿根后划出血口”),所以砍刀又是男性权力的象征。
亮亮出现后,兄弟两人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拉毛之所以自杀,不仅是因为他与亮亮的关系,还因为光子骂他“猪狗不如”。拉毛在亮亮身上不当地运用男性权力,结果这一权力马上就被褫夺了。亮亮无意中破坏了兄弟两人的关系,而且对失去处女身份并不显得格外在意(“卧房里就走出亮亮,头发乱乱的,蛾眉初颦,两腮赤红。”“是我不好,光子哥!你不要怪他,是他救了我,他提出那事,我报他救命之恩。”)。红颜祸水的母题又幽幽地闪现出来。之后亮亮一走十年(因上告篱监)。拉毛因理智被情感所战胜,失去了继续扮演男子汉的资格,原来亲如手足的关系 (雷金庆文章怀疑他们有同性恋倾向)宣告破裂。如夏志清所言,《水浒传》中的男人,绝性是他们之所以为好汉的唯一证据。拉毛不仅不能自控,自损形象,而且破坏了他与光子之间可能出现的关系。拉毛死后,光子“大悔,痛哭得死去活来”,“不谈婚事,不近女色,蓬首垢面,形如饿鬼,村人以为痴傻”,如是者三年。事实上,与拉毛兄弟关系的破裂,光子也难辞其咎,所以才要以平时用在父母身上的三年“大孝”,把自己从愧疚中解脱出来。光子的所作所为虽然近乎礼,但后来的结果证明,他又违反了儒家所为的“孝道”:没能生出自己的孩子,说明他在成为男子汉的同时,男人的另一个身份(父亲)也遭到了阉割,陷入顾此失彼的矛盾。亮亮通过一次次的上告,达到了为父平反的目的,但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男不女”的她不仅没能为光子生出孩子,反而疾病缠身,过早地离开人世,没能继续她神圣的教师职业。
严格地说,这是一出时代的悲歌。光子、拉毛、亮亮、白水,他们的青春白白地掩埋在“文革”政治的废墟之下,述说着各自的哀痛。坚守道德底线的光子也好,被情欲压倒的拉毛也好,他们都没能实现男子汉的所有定义。在政治压迫、社会地位面前,所谓男子汉的气概,不过是一纸空谈,女人也不可能独自改变自己的角色。亮亮死后,“光子没有哭,也没有流泪”,与当初的他判若两人,他的表现不是海明威所说的“从容不迫”或“处变不惊”,倒更像是一个男人的绝望,他发现自己才是被“阉割”的对象。
《黄祸》:一部《废都》出版史
查建英(Jianying Zha)为她研究《废都》的长文取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名字,①查建英1959年在北京出生,1981年入南卡罗来纳大学,之后又入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著有《中国流行文化》(China Pop:How Soap Operas,Tabloids and Bestsellers are Transforming a Culture,1996),《八十年代访谈录》(2006)和《弄潮儿》(Tide Players,2011)。她还在《纽约客》、《纽约时报》等刊物发表文章,被称为中国的女史景迁 (Jonathan Spence)。文章标题中的“黄”指“色”,其实“黄”字在英语里与“色”无关。大概是为了吸引英语读者的目光,效果如何姑且不论,仅就内容而言,这部长文确实是少见的好文章。查建英不用玄虚的理论,专凭读书的感悟和实地踏访,以大散文的形式,为英语读者送上了古都斜阳的种种景象和贾平凹的写作经历,以及《废都》出版前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文章指出,在“革命的烈焰早已熄灭之后,如今中国男女胸中燃烧着一股更古老、更恒久的火焰:性”(仿佛外国人就不食人间烟火)。对古城西安的人来说,没了性,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在性之外,弥漫在古城大墙之内的,就是吃喝玩乐,行贿受贿,钩心斗角和尔虞我诈。可就是在这么一座古老的城市里,走出了现代意义上的作家贾平凹,他的《废都》出版后,横扫文坛,被称为“一九九三年引发文学与出版大地震的小说”,出版不出数月,五十万册告罄,十几种盗版出世。
歌颂与批评纷至沓来。歌颂者称《废都》是描写“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史诗”,“中国当代文学高大的里程碑”;批评者将矛头指向其中的性描写,说小说里的部分文字“低俗”,是“肮脏的男人性心理”,不如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写得既有深度又有姿态。“扫黄办”的人也不知如何是好:《废都》出自一贯严肃的作家贾平凹,他怎么能写出黄色小说呢?更有不少自封的精英批评家发出慨叹: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在迅速萎缩,他们为了生存不惜要满足性饥渴的大众读者,文学的粗俗化,首推《废都》。也有人希望,借着《废都》的成功,“中国文学能走出低谷”。批评家张颐武却从文学史的角度指出,《废都》是分水岭,中国文学所谓的高低之分,从此再无必要,文学读物正在找回二三十年代纯粹读物的地位。不论批评家态度如何,等到一九九三年年底,《废都》在中国几乎是妇孺皆知了。那一年,贾平凹四十一岁。
此前贾平凹的作品以农村为题材,为乡村中国描绘出一幅幅清纯、温馨、五彩缤纷的画面。《废都》是他的陡然转向,是他的第一部以“城市”为题材的小说,也有人称之为他的第一部成熟的小说或“中年”小说。显然,在他看来,城市并没有多少感人的地方,不过是藏污纳垢之所,社会的和政治的系统已经生锈,城市里的人要么牢骚满腹,胆小如鼠,要么自我满足,不思进取。小说之所以取名《废都》,如作者所说,历史上,西安是十二朝古都,虽然已经今不如昔,但先人遗风还在,自豪与骄矜并存,造就出自卑与自豪相互混合的心态,因为无能,生发出冷峻的智慧,因为尴尬,生发出难言的痛苦,所以说西安人的文化心态最为典型,也可以说,西安乃中国的废都,中国乃世界的废都,世界乃宇宙的废都,写西安人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写一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贾平凹充满哲理的预言,既没有引来麻烦,也没有引起必要的注意。性和钱才是时人追逐的目标。
查建英在文中说,也有人将《废都》称为现代版的《红楼梦》,《红楼梦》在中国,与《源氏物语》在日本或莎士比亚戏剧在英国的地位不分伯仲。《红楼梦》写了四大家族的故事,《废都》也写了四大才子,后来才将叙述集中在庄之蝶身上。与《红楼梦》相同,《废都》也把现场安排在一个大院里,种种关系、各式人物,与《红楼梦》相差无几。两者都没有提到发生的历史事件,都对人物有着深入的刻画。曹雪芹刻画出贾宝玉这个情种的原型,贾平凹的庄之蝶也可以称为成年后的贾宝玉,他们与不同女子的关系构成了故事推进的线索。《红楼梦》以悲剧结尾,人去楼空,《废都》里绝望的男主角,最后也是一走了之。等小说下印刷厂之后,又有人说“《废都》是现代版的《金瓶梅》”。这部以写男女关系著称的作品,在文学上也足可称道,《红楼梦》就深受其影响。《金瓶梅》是禁书,将《废都》与之相提并论,大大提高了读者的兴趣。还有人猜测,原来贾平凹是要写一部现代版的《红楼梦》,后来不知怎的变成了《金瓶梅》。
小说当年七月出版,一个月之内,第一版四十八万册被读者抢光,出版社又加印十七万册,到一九九三年年底,所印数目至少不下百万册,盗版还在其外。此时有消息传来,有关部门将公开批评《废都》。责任编辑田珍颖对查建英说,小说出版后,她和社里的同事能感到来自“上面”的压力,外面谣言不断,但还没有正式通知。社里的第二版还不能马上投入市场。二渠道的盗版书借此大赚了一把。
《废都》出版之前,出版社竞相报价,最后北京出版社抢得书稿,又在《十月》上发了一期。据说贾平凹之所以把《废都》送与北京出版社,原因是社里一女编辑也是陕西人,将书稿连读十遍,表现出深刻的理解,令贾平凹为之动容。还有人说贾平凹收到百万稿酬,其实是记者把一千字一百五十元,读成了“1,000,150”,后来被传成一百万稿酬。至于作者到底收入几何,至今无人知道。
为揭开谜底,查建英在田珍颖的安排下,亲自到西安拜访因病入院的贾平凹。下面是她近二十年前描写老西安与贾平凹的几行文字。
我到西安那天,碰上下小雪。从机场到市区,开车行驶近两个小时。泛着黄色的河水缓缓流淌,前后左右是孤寂的大平原,平原尽头那座西安城,仿佛一头疲惫的老牲口站立在空寂的大地上。一家家外形普通的商店和饭店以局促的姿态排列在通向中央鼓楼的大街两旁。虽然才下了雪,但街道依旧显得凌乱肮脏,房子的建筑风格也毫无灵感可言。四周唯一称得上雄伟的建筑,就是那道古墙,城墙下面是西安有名的旧物市场……①Zha Jianying,“Yellow Peril.”TriQuarterly 93 (Spring-Summer 1995):238-264.
查建英的描写,与《废都》的风格不相上下。她在医院见到了贾平凹。
贾平凹相貌平平,与照片上相同,我在北京各处都能见到他的照片。他中等身材,软软的一头泛光的黑发,头颅硕大,皮肤发白,一双棕色的眼睛稍显不安。他还生着病,面容泛白,动作迟缓,看上去要比四十出头的他年大了一些。他衣着随意,说话有一种很重的乡村口音——有几次我要请老宋翻译才行——你很容易就能把他当成谁家初次进城的堂兄。我马上发现他思维敏捷,知道自己是谁。②Zha Jianying,“Yellow Peril.”TriQuarterly 93 (Spring-Summer 1995):238-264.
接下来贾平凹耐心地为来访者讲述《废都》的成因、结构、主题和中心人物,告诉她哪些描写可能引发争议,说他自己从来没在后面炒作。第一版之所以有所删减,是怕排印时遇到麻烦,他自己删了一些,责编也删了一些。他不是庄之蝶,《废都》是虚构的小说,不是自传。传统上,中国读者习惯的小说,知识分子要正派,里面不能写性,结局要好,《废都》打破了这三条定律,颠覆了传统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公开写性,结局也不幸福,没有一线希望。之所以写知识分子,因为他熟悉他们。他们属于就要灭绝的悲剧阶层。国内精英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有批评家说,人们希望生出个可爱的婴儿,不料生下来之后孩子一身屎一身尿。贾平凹指出:“上了年纪的中国人走不出我们的过去,我们的历史。就连我们这代四十几岁的人,也走不出来。我为此感到悲哀。不是为我自己,是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这大概就是《废都》的成因。
如何解读《废都》,一位欧洲汉学家的评论可能更有价值。他说:“这是小说,不是政治论文。女性主义者指责(里面的)性和性别问题,她们的话也有道理。但性描写是小说里最没意思的部分——贾对性行为所知无几,不过是取材中国的旧小说。小说诱人的精彩的地方,是以如此清晰的无情的文字描写出中国社会系统从里到外的运作方式……这是大家都熟悉的生活方式,他们知道所有的潜规则和社会规范。他们知道斗不过这个系统,他们也知道这种陈旧的游戏还可以继续玩下去。这就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这幅画面,还没有哪个当代作家比贾平凹画得更好。”①转引自Zha Jianying,“Yellow Peril.”TriQuarterly 93(Spring-Summer 1995):238-264.
一九九四年一月底,北京新闻出版局下发通知:尚未售出的《废都》予以罚没,北京出版社上交小说利润三倍的罚款,同时写出书面检讨。
贾平凹的恋旧情节
还是研究《废都》,罗鹏(Carlos Rojas)②罗鹏(Carlos Rojas)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著有The Great Wall:A Cultural History (《长城:一部文化史》,2010)和NakedGaze:ReflectionsonChineseModernity(《裸视:反省中国的现代性》,2009)等,并与妻子周成荫合译余华的《兄弟》(2009)和阎连科的《受活》(2012)。的角度与查建英明显不同。查建英从历时的角度出发,梳理小说出版前后的众多文化现象,描述中外男女读者的意见,是以女性主义者的姿态,怀着几分优越感,评判《废都》的短长,因为被小说的表象所牵引,总离不开一个“色”字。罗鹏发表《蝇眼:残垣与贾平凹的恋旧》是在二〇〇六年,此时《废都》的文学价值已经显现出来,经过时间的清洗,小说的真实面目也变得清晰起来,研究者可以望着“秦砖汉瓦”,逐渐深入研究一度被视为专门写“性”的《废都》。下面是罗鹏的长文提要。
小说开始后,庄之蝶拾到一块城墙砖,以为是汉砖,妻子反驳说,一块城墙砖说是汉朝的,屋里的苍蝇也该是唐代的了!汉砖与苍蝇是物化的历史遗存,讲述着十二朝古都的风风雨雨,可叹的是,无法逆转的现代化进程就要把这些“文物”彻底扫光,但苍蝇总要飞回来的,表明自己幽灵般的存在,将现在和过去连接起来,为西安人感念昔日帝国的辉煌扮演证人的角色。在贾平凹那里,汉砖和苍蝇都是恋旧的依托,读者也可以借此感悟男主角夕阳残照式的“颓废”心态。一边是永恒的历史,一边是被迫的遗忘,《废都》是对这两者之间关系的一次无能为力的深刻反省。
从收集古物开始 (现实中的贾平凹也是如此),男主角进而开始迷恋女足,为此,他又把鞋子送与唐宛儿。庄之蝶迷恋唐宛儿和柳月的脚,接下来混淆了女人和物品之间的关系,把女人也视为收藏之物,所以从他的角度来说,反复把玩才能证明他的珍惜。不仅是庄之蝶,他的朋友阮知非也有大批的收藏。阮知非表面上收藏的是女式皮鞋,但实质上他是在收藏每一双鞋子后面与女人发生的故事,凡是故事无不与过去相关,所以他也是个恋旧的种子。庄的另一位朋友汪希眠也好收藏:西汉的瓦罐、东汉的陶粮仓、陶灶、陶蝉壶,唐代的三彩马、陶俑,以及古瓶、古碗、佛头、铜盘。至于赵京五,他的得意收藏是砚台,端砚、兆砚、徽砚、泥砚,而且生产年代古久,每一方砚上都刻有使砚人的姓名。较之秦砖汉瓦,历史在他这里更为实在,更有质感,他几乎可以借着砚台与先人对话了。
小说中描写的古镜和古钱,更有着非凡的象征意义。庄之蝶将一面古镜送与唐宛儿,后者爱不释手,反复端详,以为自己是古代的美女,对着铜镜照个不停。小说将要收尾时,庄之蝶又将另一面铜镜送与柳月,柳月发现这面镜子与唐宛儿卧室里的那一面难分彼此,庄不无感伤地告诉她:我不能见到唐宛儿了,看到这镜不免就想到那镜……
与此相同,小说里的一枚古币,因为在庄之蝶和他的女人中间不停地流转,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十年之前,庄初来西京,汪希眠的妻子暗里取走了他的一枚古钱,之后挂在身上,以为垂饰,后来她对庄坦白说:
这是我那次去你们家看牛月清,顺手从你的窗台拿的铜钱儿。我想我已得不到你,却要把你的东西戴在身上。这事汪希眠全不知道,今日全给你说了,我再把它送你。这不是完璧归赵,是它十几年戴在我身上,它浸蚀了我的汗,我的油,我的体味儿,完全成了我的命魂儿,送了你也让你知道我是怎样一个女人。①贾平凹:《废都》,第198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柳月在浴室里见水龙头上挂着一枚铜钱,觉得可爱,就装在兜里。等庄发现钱币在柳月身上,就朝她要。后来庄妻也发现了这枚铜钱,心想必是哪个女人送他的。其实,钱币早已失去原来的价值,之所以还能在他们身上流转,把庄与其生命中的几个女人连在一起,不能不说这其中还有着恋旧的成分,铜钱俨然成了前朝遗物的化身。钱币的这一功能,几个女人未必知道,但庄的心里是明白的。钱币经过一次次流转,其地位也变得不同一般,不仅有着原来的文物价值,又平添了男人与女人无言的情愫,使一枚物化的钱币死而复生,拥有了一种亘古的生命力。
《废都》中的以物寄情,还表现在西京那道城墙上。贾平凹自己就在《老西安》里说他爱古如痴,八十年代翻修城墙,顺手从工地上取回了三块旧砖。可以说,西安人对古城历史的恋恋不舍,更多的是通过那道大墙来实现的,因为有了城墙,才让人联想到昔日古都的威严、繁华、稳重、安全、先进、灵感、成功,乃至不可一世。城墙不仅是西安最著名的地标,也是贾平凹个人的心理依傍,小说里周敏就好几次在墙上吹埙,以此来排遣胸中的郁结,庄对埙吹出来的曲子心领神会,如此一来,埙、古墙、古城、历史、怀旧,又形成了一种女人之外的逻辑关系,一种更牢固、更接近灵魂的关系,与之相比,肌肤之亲不过是临时的排遣,所以小说开始不久,庄之蝶驮砖回家的描写,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妻子牛月清不解丈夫的恋旧癖好,批评他是捡破烂的,而且捡来的东西无论如何也派不上用场,她被丈夫冷落,两人最终分道扬镳,不能不说与她的麻木有着一定的关系。
按照罗鹏的理解,古都西安本身就是一个硕大的文物,里面弥漫着历朝历代的文化信息,幽灵般的回音不时通过埙的演绎,传入男主角的耳底,所有这些都是他不忍失去的,是他精神存在的依托与证明。从这个角度分析男主角的颓废与恋旧,可能更接近他精神演变的轨迹,可能厘清收藏与抗拒健忘症之间的关系,最终如一些批评家所指出的,《废都》中的性与色不过是表面文章,文化变迁在知识分子中引发的颓废感及其外化的收藏癖,也不一定就能有效地传承文明,西安人也好,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人也好,他们能不能继往开来,才是症结所在。毫无疑问,庄之蝶他们还将继续颓废下去,无论是说西安的苍蝇是来自唐朝的,还是说西安的苍蝇的眼睛是双眼皮的,都无法改变古城落伍的事实。要是庄之蝶他们依然抱着恋旧心态不放,还暗自沾沾自喜,停留在历史的驿站上,他们自己迟早也将变成被他们收藏的“文物”。对此,贾平凹显然是有着先知般的预见,所以二十年后回望《废都》和其中的人物,不能不说这是一部警世良言。其实贾平凹在小说的后记中早就点明了他的题旨:
这本书的写作,实在是上帝给我太大的安慰和太大的惩罚,明明是一朵光亮美艳的火焰,给了我这只黑暗中的飞蛾兴奋和追求,但诱我近去了却把我烧毁。②贾平凹:《废都·后记》,第256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我们不能拒绝一位舍生求法的作家送上的厚礼。
《叙述中国:贾平凹的文学世界》
与上述评论家的长文相比,王一燕(Yiyan Wang)③王一燕现为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在《叙述中国》之外,还为Chinese Fiction Writers,1950-2000(《中国小说家1950-2000》)撰写了“贾平凹”,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Volume Three Hundred Seventy,New York:A Bruccoli Clark Layman Book,pp.111-120,2013;她大概也是第一位用英文将贾平凹与外国作家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见“Language,Time and Introspection:MargaretAtwoodandJiaPingwa,”(《语言、时间、内省:贾平凹与玛格丽特》)Australian-Canadian Studies,Vol.15,#2&Vol.16,#1,1997-8;王一燕正在用中文改写《叙述中国》,收入贾平凹2006年之后出版的《秦腔》、《古炉》、《带灯》,将在中国出版。这部研究贾平凹的学术专著就显得更为厚实,更为系统,更为公允,也更为全面,可以说,是国外学者对贾平凹的重要作品、创作历程及文本美学所进行的最为深入的研究。此书二〇〇六年以英文出版,二〇一二年再版,此时《废都》最初引发的那些争议早已尘埃落定,国内外的评论已将研究方向转向贾平凹小说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叙述中国:贾平凹的文学世界》也是迄今为止以贾平凹为研究对象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英文著作。《叙述中国:贾平凹的文学世界》分为十一章。第一章绪论,讲述贾平凹的成长历程,着重探讨贾平凹与其他作家如鲁迅、沈从文、老舍等的传承关系及作家与故乡的渊源;第二章写贾平凹从“乡土作家”走向城市的转变;第三章写《废都》及其文化背景,从国族寓言形成的角度,探讨所谓“文化闲人”的生存空间;第四章写《废都》中才子佳人小说中盛行的男性“阴柔”及其文化根源;第五章写《废都》及其女性人物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第六章转入《白夜》,分析小说的互文性,第七章写《土门》与故乡的失落,研究那些徘徊在故土与都市现代性之间的农民;第八章写《高老庄》与反乌托邦的故乡;第九章写地方事件与 《怀念狼》的关系;第十章研究贾平凹的诗歌、散文和文本个性;第十一章为结语,分为两部分:“叙述中国以及关于故乡的文论”和“真实性与虚构的疏离”。书后附录有四:“访谈贾平凹”,如国外论家所说,是“颇有价值的一手资料”,①Alexander C.Y.Huang,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68,No.4 (Nov.,2009),pp.1272-1274.“贾平凹生平创作年表 (一九五二-二〇〇五)”,“贾平凹自传与评传列表 (一九八一-二〇〇四)”及“贾平凹出版作品年表 (一九七七-二〇〇五)”。
如王一燕所分析的,贾平凹的作品有一明显特征,就是他能以杂糅的形式,将中国文化、叙事、故乡统摄起来,而且并不回避这一过程中作者的目的。他的不少故事都发生在商州,证明作者是在从地理、历史及人类学的角度,有意塑造他小说里的故乡,这一过程又是连续的漫长的,因为贾平凹相信,他的文字能再造出一个更接近真实的故乡。贾平凹在用写作告诉读者,在他的文学宇宙中,商州才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他要通过自己的写作,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把这一逐渐被人们遗忘的传统继续下去。如他所言,没有商州就没有中国。
在语言方面,贾平凹相信,陕西乃汉唐故地,这里的方言能更好地再现出古代汉语的魅力,为此他在写作时有意使用当地的(尤其是乡间的)语汇点缀他的文本。②贾平凹讲过一个故事,外国人与西安宾馆大堂接待员说汉语,后者答以西安方言,外国人问对方为何不讲普通话,接待员答道:过去在汉朝唐朝,西安话就是标准的普通话。贾平凹:《老西安:废都斜阳》,第3页,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9。在历史上,从文明初现,到王朝更迭,演绎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贾平凹的文学世界并非完全来自自己的想象,他曾不止一次到乡间探访,考察故乡的历史和文化结构,从“寻根”开始,到“国族”写作,他所表现的民俗民风,无不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只有将他的商州故事读成一部文学化的地方志,才能感悟这些故事的宽度和深度。
王一燕总结说,贾平凹的小说表现了自明末清初以来,中国现代小说本土主义写作的传统,其中有着对故土的依恋,对其落后现状的焦虑,对原始质朴的民情民风与村寨、乡镇、市井、街巷、风土习俗的钟爱。贾平凹的写作聚合了一方风土上各种现实素材的商州系列故事,为文学本土主义的定向和叙述中国的构思,提供了本土场域文学表达的范例。这个文学范例将三个元素收容进来:一部有文学色彩的商州民族志;一部从中国古典叙事传统发端的叙事结构;一种拒绝欧化和政治话语、传递纯正汉语美感的叙事语言。
王一燕的专著出版后,国外学者颇有好评。如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指出,用一部专著研究一位作家,现如今已是明日黄花,这种现象不免让人感到遗憾,所以这部著作才让人格外稀罕,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他都喜欢这部材料充实、研究深入的著作,其特点是文字清新,结论公平,结构合理,译文可嘉。显然王一燕是站在贾平凹一边的,但值得称道的是,她能以理服人,以证据说话,与之相比,或是因为所谓道德取向批评贾平凹,或是为他大唱颂歌,都是不足取的,这方面王一燕显得更为理性,进退有据,很少表现出个人的成见。读完这部著作,在葛浩文那里,小说家贾平凹的地位变得更高了,不再是那个“不相信葛浩文能说中文的农民作家”。①据葛浩文说,聂华苓推荐他翻译贾平凹的《浮躁》,小说英文版1991年出版,美孚“飞马文学奖”顾问委员会邀请贾平凹携夫人访美,两人在葛浩文家停留数日。贾说汉语口音重,说台式中文的葛听贾说话有麻烦。Howard Goldblatt,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Vol.13,No.2,Fall 2006。有关国外对《浮躁》的评论,见姜智芹 《欧洲人视野中的贾平凹》,《小说评论》2011年第4期。
传统文人与现代知识分子
司徒祥文(John Edward Stowe)也是国外研究贾平凹的专家之一。②司徒祥文现为加拿大怀雅逊大学 (Ryerson University)中文教授,其博士论文The Peasant Intellectual Jia Pingwa:A Historico-Literary Analysis of His Life and Early Works(《农民知识分子:贾平凹早期作品论》)文字清新,叙述通俗,以研究贾平凹早期作品见长。他的论文从贾平凹的成长经历和早期作品入手,揭示出贾平凹的传统文人与现代知识分子这一混合身份形成的外部原因和内在原因。一方面,贾平凹将自己的文化传统视为写作源泉,一次次地从中借用,汲取,戏仿,消化,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使其作品拥有了古典小说的审美质地;另一方面,贾平凹还在不断创新,将作品的触角指向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社会有所担当,与现实的存在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进而形成一种少见的张力,在美学上达到一种古今杂糅的叙事效果,这也是贾平凹与众多其他作家不同的地方。
司徒祥文指出,之所以称贾平凹为传统文人,是由他的写作方式所定义的。贾平凹虽然成长在社会主义中国,但是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和经典读物的浸染。这方面贾平凹的父亲贾彦春是其儿子最好的榜样。贾彦春是山村教师,当地少有的读书人。贾平凹在父亲身旁耳濡目染,从小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贾平凹读小学后就能给父亲写信,门门功课都要高出其他孩子一等,所以后来在一九七二年能被选送西北大学,专修中国文学。大学期间,凡是遇到古典小说,贾平凹从不放过,悉数阅读。他的诗歌和小说创作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此后三十几年,读书写作成了贾平凹的精神伴侣。所以读者总能在贾平凹的文字里找到明清文士的痕迹。司徒祥文的判断也得到了鲁晓鹏(Sheldon H.Lu)的证实:
明目张胆地写性很容易吸引部分读者,不过,成熟的读者才能发现(《废都》中)那些巧妙的暗指和与明清古典小说平行的文字,如《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以及戏剧《西厢记》。《废都》的语言可谓五色杂陈,其中不乏白话文、文言文、口语、欧化句,及标准的普通话。所以就出现了表面上的矛盾:从发行的数字判断,《废都》是最流行的小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同时又是现代“文人小说”的集大成者,非精英读者又怎能尽得其妙。③Sheldon H.Lu,“Intellectuals in the Ruined Metropolis at the Fin de Siecle” in China,Transnational Visuality,Global Postmodernity,(Stanford:Stanford UP,2001),pp.254-255.
贾平凹身上不仅有着传统文人的因子,同时,他还是一名现代定义上的知识分子。司徒祥文写道,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七年间,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政治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就在其 《狱中笔记》(Prison Notes)指出,“人人皆为知识分子,因此可以说:但在社会上不是所有的人拥有知识分子的功能”。④⑤ Edward Said,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s,(NY:Vintage,1994),p.3,6.正是在“社会上”,贾平凹才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不过他的这种“功能”是通过写作来完成的。考察贾平凹的早期作品,不难发现早在一九七八年,他就通过小说《满月儿》清楚地表达了对社会的关注。此后,贾平凹站在人民一边,揭穿谎言,挞伐邪恶。按照萨义德的定义,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批评腐败,保护弱者,挑战瑕疵或压迫人民的政府”。⑤这些贾平凹都做到了。
司徒祥文在文中并没有过高地评价贾平凹的地位。他坦白地指出,贾平凹的确是传统文人,现代知识分子,但这些仅仅发生在中国,如同大多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作家,贾平凹也才开始走出国门,西方世界的大多数读者对他仍然一无所知。①司徒祥文指出,虽然港台作家也用英文出版作品,但这批作家在西方世界并没有被视为一流作家。目前,贾平凹的英文作品已经成为国外大学里中国文学或文化研究的对象,但在这些学术研究之外,很少能发现小说家贾平凹。司徒祥文以贾平凹为题撰写论文的目的,也是要向西方推荐作为小说家的贾平凹。按照他的说法,理解一个作家,才能理解作家身后他的国家、民族、文化,乃至那里的人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贾平凹和其他作家,就有着非凡的价值,不仅要研究他的小说,还要研究他的诗歌与散文的关系,传统上经典小说如 《红楼梦》、《金瓶梅》等与贾平凹作品的关系,贾平凹与其他中国作家如沈从文、高行健、阿城在写作上的关系,释、道哲学与贾平凹写作的关系,以及贾平凹对女性的态度。研究上述题目,首先要对这位谜一般的中国农民知识分子进行全面的梳理。
司徒祥文在其论文后列有 “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与文学大事年表”,“贾平凹生平与作品年表”和他亲手翻译并注释的十个贾平凹的短篇:依次为 《满月儿》(Two Sisters)、《月迹》(Moon Traces)、《丑石》(The Ugly Stone)、《一棵桃树》(The Little Peach Tree)、《夜籁》(The Evening Music)、《入川小记》(Travel Notes of a Visit to Sichuan)、《弈人》(Chess Players)、《闲人》(I-dlers)、《笑口常开》(Always Bursting Out Laughing)及《坐佛》(Sitting Buddha)。
贾平凹一九七三年在地方杂志《大众艺术》上发表了他的《一双袜子》,那时,现在与他一同写作的大多数作家不是在农村插队,就是在军队服役,再有些更年轻的作家还没有出生,二十年后的一九九三年《废都》出版,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部地标性作品,如同加西亚·马尔克斯,贾平凹在那一年完成了一个作家的成人礼,之后又过了二十年,《带灯》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时代在变,小说在变,方方面面都在变,但不变的依旧是传统文人与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谨以此文纪念《废都》出版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