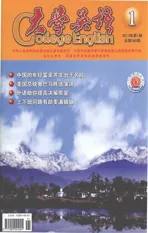为自由而战的女人:评《法国中尉的女人》一书中的新女性
2013-03-26王佩玉
王佩玉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0872)
1.一个存在主义新女性
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被广泛解读为优秀的存在主义作品。人们赞扬女主人公萨拉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新女性,鼓励男主人公查尔斯获得了存在主义自由。然而,在将这部实验小说视为自由颂歌的同时,很多人忽略了作品更深层所蕴含的痛苦。本文旨在讨论《法国中尉的女人》一书中,由被决定的和决定性环境所引发的自由之痛。
与书中的欧内斯蒂娜·弗里曼相比,萨拉·伍德拉夫全然是“另一类女人”。萨拉拒绝接受她所处时代的价值观,拒绝按照时代的传统生活。她是所处时代和所在社会的异类,一个19世纪的人却有着20世纪人所持有的思想。她拒绝屈从社会配置给她的传统生活,就像杰夫·拉克姆所说:“她以一种最好的存在主义的方式,通过自己的选择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自己,一个真正的自己,不需上流社会的认可,也不受他们宣扬的道德和传统的束缚”。 (Olshen1987:78)
然而,每个人的成长都要经历风雨。为了实现自由,萨拉要面对的是不利环境将加诸于她的不可避免的痛苦。
2.是苔丝还是简爱?——自然主义眼光下萨拉的悲剧
托马斯·哈代说:“悲剧可以由宇宙固有的或人类机构所导致的不利环境造成”(Schiff2001:107)。他的著名小说《德伯家的苔丝》讲的就是:人并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那么首先,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德伯家的苔丝》和《法国中尉的女人》两部作品中女主人公背景的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法国中尉的女人》中,作者提到“四代以前,他的祖辈们还是声名煊赫的绅士。他们跟德雷克家族甚至还是远亲。其实,此事纯属道听途说,谁知天长日久,居然弄假成真,他们也便成了弗朗西斯爵士的嫡系后裔”(Fowles1994:51)。 萨拉的父亲和苔丝的父亲一样,都对自己的出身耿耿于怀。苔丝的父亲为了自我欺骗拿自己是贵族血统这种事情吹嘘,萨拉的父亲则拿先祖的尊贵地位来吹嘘。两部小说中,这种对出身的狂热实际上给很多人都造成了不幸,特别是对书中的女主人公们来说,尤为如此。这种狂热导致了苔丝的堕落并最终将她送上了谋杀犯的不归途。《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萨拉的父亲试图重膺先祖的地位和财富,但最终戏剧化的失败让他自己变的疯疯癫癫,还害得女儿穷困潦倒。
我们再研究一下萨拉的教育和青春时期。作者提到萨拉的父亲是个佃农,逼迫萨拉“明智的”离开原来的班级,转到爱塞特的女子学校学习。萨拉是个孤儿,做过家庭教师,受过教育,并不富裕,这些跟简·爱的经历如出一辙。跟夏洛蒂·勃朗特著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简一样,萨拉是个离群的、孤独的、饱受压抑的浪漫主义者,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找寻幸福。作者现实的描述了萨拉·伍德拉夫的背景,也借此从社会学和心理学上解释了,萨拉为何最终会落入惨境,变成等级社会中的一个异类。萨拉所处的阶层,使她所受的教育恰好害了自己。因为正是所受的教育使得她成为异类,让她在精神上脱离了自身的阶层。尽管父亲被送进疯人院后,萨拉正是凭借教育,在多尔切斯特附近的人家做家庭教师得以维生。但她的阶层没有给她任何的可能性,让她可以成为社会的主流,或者有机会与他们谈谈。所以对她这样的底层人士来说,教育及日益增长的视野和自我觉醒绝不是幸福和自由的源泉,而是不折不扣的诅咒。小说中,萨拉与法国中尉的浪漫故事是虚构的,自己想象出来的。萨拉故意编造自己的故事和身份,即使这些完全毁了她的名誉她也不管。尽管萨拉的努力看上去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但是她的两段罗曼史(包括与法国中尉的虚构情缘,以及与查尔斯的真实情感)似乎都是为了满足自己潜在的那些欲望,那些由阅读沃尔特·司各特的爱情故事、简奥斯汀的小说和其它诗歌等等所激起的欲望。这么一来,文学作品的阅读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来说,似乎就成了她们不满的来源,甚至对她们是十分危险的事情。总而言之,萨拉注定要为她所在的时代和社会中自己所处的地位和阶层而承担痛苦。
3.自由之痛——一个迷惘的女人
与欧内斯蒂娜不同,萨拉代表的是更加自由的女性。她看起来并不认可传统观点,不认为男人才能担当养家者和保护者的角色,特别在向查尔斯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她说:“我希望就这样做我自己,而不愿意成为我未来的丈夫——不管他多么善良,多么宽容——所希望我成为的那个样子”(Fowles1994:353)。作者将萨拉描写成维多利亚时代的新女性。“她转过身,望着查尔斯……我们有时可以从现代人的脸上看到一个世纪前的人的表情,但永远不能看到一个世纪后的人的表情”(Fowles1994:146)。然而,较之于20世纪的自由女性,萨拉还是跟她们相差甚远。在那样一个决定性的环境中,萨拉个人的强烈意愿还远不足以让她胜出。
萨拉坦承,她选择跟随法国中尉从而选择了耻辱,这种做法让她获得了身边的人所无法理解的“自由”。这使她 “完全不同于其她女人”“一钱不值”“几乎不再是人了”(Fowles1994:142),她从而获得了一种消极的优越感,可以“有时候甚至可怜”那些没和她做相同选择的女人们(Fowles1994:142)。这显然是存在主义的腔调。然而尽管她知道自己可怜、孤独、有些自由,但她却没能理解自己的这些可怜、孤独和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在爱塞特的最后一幕,当她的谎言被揭穿时,她只能说:“不要叫我解释我做过的事情,我解释不了。再说,也不应当解释”(Fowles1994:279)。“就连我也理解不了我自己”(Fowles1994:354)。正是这个对自己缺乏清晰理解的问题,成为了萨拉痛苦的其中一个重要来源。然而这种痛苦是不可避免的。从个人层面讲,是因为萨拉一直都只关注做自己,没能把自身与维多利亚时代其它的类似例子联系到一起来看。此外,她的行为似乎也是史无前例,因而对于她的现代思维当时还没有人能够解释或者接受。所以尽管她能极好的描述自己的疼痛、苦闷和孤独,她的眼界却也仅能局限在当时的时代。也就是说,她只有经历,却没有知识和自我认知;她经历过自由,却没有真正抓住自由的精髓。从这个角度理解,萨拉的追求自由之路自然会不可避免的布满无法克服的痛苦和愤怒。
4.无奈的自由——父权制下势弱的女性
另外,萨拉的痛苦也与性别弱势和处处存在的社会偏见所设置的束缚息息相关。当查尔斯表示自己理解萨拉时,萨拉很快就回道:“你不理解,史密逊先生。因为你不是一个女人,不是一个生来要作农夫的妻子但后来又受过教育要……变得更好的女人,你也不是一个生而尊重且热爱智慧、美和学识的女人……我的心向往着这一切,而且我不认为那是出自虚荣”(Fowles1994:138)。尽管有权力的地方就有反抗,但是《法国中尉的女人》一书清楚的告诉我们:权力和反抗都是受历史限制的。萨拉看上去其实也只是罗塞蒂家的一个边缘人物,即使是维多利亚时代最自由的女性也无法给女性的自由问题一个满意的答案。
尽管萨拉已经在那样一个饱受等级限制的社会中接收到了超出自己阶层的教育,但她还是一直觉得自己是个适应不了环境的人,是个令周围人讨厌且与他们相异的人。她对查尔斯说:“多年来,我觉得自己可能遭到了某种神秘的诅咒而注定……孤独……我的整个生命似乎已陷入孤寂之中……好像命中已经注定,我永远不能跟同类人建立友谊,永远不可能建立家庭,永远会被排除在这个世界之外”(Fowles1994:139)。她诋毁自己名誉的做法似乎有些出人意料,让人难以理解。对于她执意保持自己创造的堕落女人的形象,我们也许可以这样理解:这可以加强她的疏离感和独特性。她说:“我有一种她们不能理解的自由。我已把侮辱和指责置之度外了……我只是法国中尉的娼妇”(Fowles1994:142)。这是一个极为负面的身份,是在往自己脸上抹黑。但正是这个身份,能够迫使受到震惊的社会至少给萨拉一个地位,尽管是个消极的地位。他们视萨拉为危险人物,但起码这让他们意识到她也是一种力量,意识到她和维多利亚时代那些中规中矩的女性迥然相异。所以,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萨拉对于社会准则的藐视,仍是受制于那无所不能的社会规范的力量。无论萨拉的意愿多么强烈,她永远也逃不出社会限制的樊篱。
作为一名决心挣脱时代要求的女性,萨拉不想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要求做个贤妻良母,但却仍然希望得到同辈人的理解。在安德克立夫崖时,格罗根和查尔斯认为,萨拉致力于追求的首先是坦诚后的解脱。用萨拉自己的话讲却是寻求查尔斯的理解和宽恕。尽管她想被理解的想法已经有些让人难以理解了,但她想为自己其实根本没做的事情而获得宽恕的想法则更加令人费解。显然,她实际只是在为做自己、做一个不符合社会要求的异类这样的行为而请求宽恕。所以,萨拉还是受到外部世界压力的限制的。小说也借此告诉我们,个人总是要面临的一种困境就是,即使不同历史阶段或不同社会的决定性大小或残酷程度有所不同,人总是要受外部世界力量的限制。
今天,我们可以接受一个事实:就是性是爱情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并不肮脏,性只有在堕落或商业化了的时候才是肮脏的。因此,绝不应把性同罪恶联系到一起。我们不应把精神和肉体割裂开来,应该将它们视为一体。这部小说可以被视作解析维多利亚时代性压抑的权威之作。欧内斯蒂娜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她只能接受最纯洁的亲吻,只允许查尔斯亲吻她的脸颊、前额或手背。但她却觉得自己已经深陷爱河,非常愿意引用各种热情的诗句来向未婚夫表达自己对他的深爱。而且在维多利亚时代,男性遭受的性压抑也一点儿都不少,比如查尔斯就得忍受屈辱签订合同,承认自己不再有资格被视为绅士。由于维多利亚时代,这种对性的看法产生的影响无处不在,导致查尔斯与两个女人的关系都是扭曲的,一个受禁止的压抑,另一个受负罪感的影响。尽管维多利亚时代,名誉、贞洁和诚实是最高的美德,但萨拉却故意反叛这些并且大胆的称自己为“法国中尉的娼妇”(Folwes1994:142)。她宣称:“我有一种她们不能理解的自由”(Folwes1994:142)。然而,任何反叛都是得付出代价的,萨拉也毫不例外的需要因这坏名声而背负羞辱。萨拉意识到,社会一旦将她毫不合理的归入到了社会底层,那她为除去耻辱的标记所做的任何努力都是于事无补,她永远都得携带“有罪的莱姆女人”这样的标记。萨拉在自己异类的角色中获取力量,尝试寻找自由,寻找那些被时代的道德标准缚住的上流社会的女人所得不到的自由。她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空间,那里她是不可触及的,因为那已远远超出了社会所能接受的范围。在这点上,她有些像纳撒尼尔·霍桑笔下的海丝特·白兰。她自己创造的孤独就是一道屏障,帮助她抵御住外界的冷眼。但另一方面,这孤独也正是她不符合社会规范所要付出的代价。
5.存在主义的痛——子虚乌有的自由
最后,获得自由所遭受的最大的痛苦则是来自于自由的不完整性。萨拉在艺术家一家中的角色更偏向于适应者而非反叛者。小说结尾,萨拉没能按照自己的目标成为一个完全的异类,成为完全自由的新女性。她只不过成了罗塞蒂家的一个模特,“有机会与天才们说说话”(Fowles1994:353),并且“以一些微不足道的方式”协助天才们(Fowles1994:353)。她甚至后悔自己过去的选择。“他们告诉我说,如果一个画家不是他自己的最严厉的法官,那么他就不配做一个画家。我相信这是对的。我想我毁掉我们之间已经开始的东西也是对的,那关系之中有着某种虚假。”(Fowles1994:351)
此外,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质疑萨拉所获得的自由究竟是否是真实的。“法国中尉的娼妇”并非萨拉的真实身份,那只不过是她自己构想出的一个角色,是她给自己戴的一副面具。“我那样做是为了让人们可以指着我的背说三道四,瞧,那个女人就是法国中尉的娼妇——好吧,让他们说去吧。我那样做是为了让人们知道我过去痛苦,现在也痛苦,像这个国家每个城市每个村庄的人一样痛苦”(Fowles1994:142)。她这样解释选择扮演这种角色的原因:“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它办法可以改变我的境况……我有时候甚至可怜别的女人,觉得我有一种她们不能理解的自由。侮辱也好,指桑骂槐也好,都不能动我一根毫毛,因为我已把侮辱和指责置之度外了,我一钱不值,我几乎不再是人了,我只是法国中尉的娼妇”(Fowles1994:142)。因此,萨拉的自由是通过讲述虚假的故事而得来的。那自由的基础是她的想象而非现实,因而那自由也只存在于她的想象之中,在现实之中则子虚乌有。
总之,并非如许多评论家认为的那样,小说热情的讴歌了萨拉对自由的追求和对维多利亚时代伪善的藐视。实际上,《法国中尉的女人》讲述的是在被决定的和决定性的环境中追寻自由所遭受的痛苦乃至绝望。
Olshen, Barry N. (1987). John Fowles [M].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
Fowles, John (1994).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Schiff, Joanthan (2001). Ashes to Ashes: Mourning and Social Difference in F. Scott Fitzgerald’s Fiction [M]. AssociatedUniversity Press Inc.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