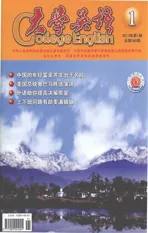家庭困境:麦卡勒斯短篇小说中家庭里的女人
2013-03-26高凌飞
高凌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0191)
一、引 言
卡森·麦卡勒斯,20世纪美国小说家,22岁时完成的《心是孤独的猎手》使其一举列入著名作家行列。麦卡勒斯的小说以对孤独的探寻为主题,深刻剖析了当代人情感和内心的孤独,表达了孤独是绝对的主题。麦卡勒斯自己也说,精神隔绝是她大多数作品主题的基础。她的第一部作品与之相关,几乎全部有关,并且此后她的所有作品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有所涉及。”(McCullers1959)在人们更多的关注麦卡勒斯关于孤独症的描写时也有人注意到,麦卡勒斯对成年女性的描写特别是她们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即母亲和妻子的描写时极少数和非正面的。在她的小说中,“母亲形象”被赋予模糊甚至邪恶的意义,“妻子形象”也是如此非理性和疯狂。在卡尔看来,在卡森的创作生涯中,在她出版的小说里她从来没有描述过哪怕一种幸福的、安全可靠的母女关系(Carr1975)。麦卡勒斯之所以如此描黑女性的家庭形象,与她本人和母亲的关系有着极大的联系。
“在某种意义上,卡森同玛格丽特(卡森的母亲)的关系就像第二次婚姻。卡森被安全的系在母亲的围裙上,就像她感到无助地被诱入她本人帮助编织的一张麻烦的、悲剧性的婚姻之网中。虽然她极度需要她的母亲,但是,她抱怨,有时甚至痛恨将她们栓在一起的这根脐带”(Carr1975)。
而父母感情的相对疏离和对对方的不干涉在卡森的心里烙下了这样的画面:家人在卡森的眼里从来没有过其乐融融的情境,有的只是欲言又止和令人喘不过气的奇怪的爱。玛格丽特在卡森家所扮演的角色深刻的反应在卡森的小说中,特别是她的短篇小说中,成年女性在家庭中的生存困境被刻画的淋漓尽致。作为母亲,作为妻子,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有着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二、母亲与孩子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不同年龄、阶层、种族的女人被置于或置出雇佣劳动力之内或之外,结婚率和生育率在这期间也大幅变动。除却这些变化,不变的是女人对孩子的关心,这主要是作为母亲的角色,偶尔作为看护所的护士或富人家的保姆显露出来的。就如巴萨模所说,女人的母性是为数不多的造成劳动性别分工的广泛且持久的因素(Balsamo1996)。由于看到女性与生育、哺乳、照顾孩子之间的自然联系,女人必须做“母亲”就变得天经地义了。作为结果,尽管女人的“母性”不论对家庭结构还是社会结构都产生着深远影响,却很少有人认真去分析它。
霍多罗提到,从历史角度来说,真正对生孩子和养孩子的生理需求已经大幅减少了,但“母亲”仍然扮演者家庭中至关重要的角色,女性的母亲角色被赋予更对心理和意识形态的意义,对如何定义女性的生活也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Chodorow1999)。孩子出生的过程是一个矛盾的过程,女人一面享受着即将做母亲的喜悦也承受着一系列生理和心理的压力,而分娩带来的巨大的身体上的痛苦也使母亲对刚出生的孩子潜意识中怀有仇恨心理,当孩子意外夭折时,母亲会感觉到背叛,这种仇恨的情绪就从心底一跃而上。然而,由于缺乏报复对象,女人很可能转化为自我厌恶。在麦卡勒斯的《被附身的男孩》中,休的母亲由于小女儿的早夭而企图自杀。母亲这种“生活的变化”对整个家庭产生了不可修复的影响。男孩休亲眼看到母亲倒在血泊里,却从母亲自杀、送往精神病院、出院、“康复”这一系列过程中没有哭过,自始至终压抑着自己的情绪。他害怕去二楼看他的母亲,整个事情在他看来都太“怪异(odd)”了:
“他缓缓地上楼,这时的心跳倒不像是打篮球而是快速击打的爵士鼓,在他每上一级时越跳越快。他拖着脚步,仿佛是在过膝深的水中行走。然后他在楼梯扶手旁站住。这房子显得怪异疯狂……由于被恐惧包裹,所有物体在他看来,无论是楼下的桌子还是楼上的沙发,都是那么的失常和刺眼,尽管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事物……”(McCullers1955)
情绪在他看到浴室里空空如也时瞬间释放了,“他将自己埋在铺着玫瑰图案的被子里,如释重负的哭了,从长时间以来紧张、阴冷的疲惫中解脱了,这哭泣瞬间贯穿了他的全身,平息了他那有如擂鼓的心”(McCullers 1955)。而母亲进来问他为什么哭时,男孩竟然不能解释,这种突然之间产生的隔阂是男孩遭遇被最爱的人背叛后的必然结果。
这篇小说“部分的萌芽于卡森在1954年的精神焦虑”,源自“她对母亲的忧虑和矛盾的态度”。他心里想着对这个世界上他最爱的母亲的怨恨。“最后几个月这种愤怒在爱和愧疚之间跳来跳去”(Carr1975)。卡森在对与母亲的爱-恨-愧疚的关系在这部小说中有着充分的反映。母亲与孩子看似亲密实则根本无法沟通的困境在麦卡勒斯的短篇小说中经常出现。
同样,在《家庭困境》中,孩子们的母亲同样是有着病态人格的女人:酗酒、做饭难吃,甚至在给小女儿洗澡时把孩子的头给磕破。这都不是正常的母亲所能做出来的事。“安弟往后退缩,想离她远一些,因为他感到害怕”“我的孩子不要我了”“这时,他突然想到孩子们一回也没有提到他们的母亲”(McCullers1951)等等,都说明了孩子对母亲的害怕、厌恶甚至仇恨。在麦卡勒斯的小说里,孩子与母亲的关系总是紧张的,母亲总是怪异和疯狂的。母子之间的交流总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麦卡勒斯笔下的母亲是带有原罪的夏娃而不是圣母玛利亚,圣母“是罪人夏娃的反面,她踩死了脚下的蛇;她是救世的调节者”(Duden1993),而夏娃“却是该罚入地狱的”。所以这些“母亲”承受着各种压力且不被孩子们理解,她们是永远得不到救赎的罪人。
三、妻子与丈夫
在分析到婚姻时,雷德克里夫布朗和其他一些英国人类学家强调了婚姻中权利和责任的转换,它是从夫妻双方中一员的同族传递给另一族的。女性在自己族群中扮演的角色会逐渐淡化转而接受男方家族传递给她的权利和责任。妻子的角色在人类历史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家庭中心的,妇女的权利和权威也显示在家庭中,而厨房、卧室这种彰显女人家中地位的场所是女性尽全力捍卫的地方。在小说《鬼魂附身的男孩》中,男孩提到的母亲唯一优点就是做饭好吃,而“母亲”这一角色出现的场景也只有两个:厨房和卧室。可见作为家中的女主人,她的活动领地主要是家庭内部,而“做饭”是所谓女性家庭内部的责任,做饭好吃与否关系着一个婚后女人的人格是否成立。而在《家庭困境中》,艾米丽将盛辣椒面的罐子当做肉桂粉罐子,撒在给孩子们做的烤面包上这一严重不符合“贤妻良母”形象的举动也导致了后来一系列的紧张状况。做饭能力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女人的身份地位。
在《被附身的男孩》中,男主人,也就是休的爸爸在小说的结尾才露面。前面以休的叙事角度看,男主人似乎是一个好爸爸的形象,“爸爸和我几乎每星期六都会去打猎,我们打一些斑鸠和鸽子”(McCullers1955),这里,男孩用的是“Daddy”这个词,而在小说结尾,男孩的爸爸真正出现时,男孩是叫他“Sir”,并且紧张异常。可见,男主人在家中并不见得是一个温柔体贴的人。而女主人,休的妈妈的作为妻子,在丈夫营造的紧张家庭环境中,也亦步亦趋:“我以前从未买过一双彩色的鞋”,“他的妈妈停止了跳舞,静静的站在床边。她的脸突然平静且悲伤‘我六月就要43岁了’。”而休的爸爸在看到妻子的转变后也说“她看起来那么高兴那么美,比她这些年来都要漂亮”(McCullers1955)。可以想象,休的妈妈在嫁人、生子之后的生活是乏味无趣的。之前的生活对于这个女人来说只是厨房和卧室两个空间的转换,即使是康复之后,她最终出现的地点也是厨房,最后的动作也是做饭。最后父亲的提议是:“很快就到夏天了,一起去野炊吧,我们三个。”父亲着重强调了“三个”,之前偶尔去打猎也是儿子和他一起去,妻子完全被排除出了“家庭户外活动”,是妻子的“死亡”让丈夫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让他重新去“关注”自己的妻子,只有死亡这样的重大转折才使家人又一次“关注”到自己,这样的代价对与当时的女人来说是太过于沉重的。
而在《家庭困境》中,夫妻的对峙和冲突则表现的更为强烈。小说开头就写到马丁对“家”的感觉:可是这一年来,离家越近,他越是感到紧张,他几乎不期望旅途的结束了。马丁不想回家的主要原因就是不想见到妻子。妻子的酗酒让他感到无措,马丁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最终他将问题归结到搬家,是从南方小镇搬到纽约影响了妻子:“她原来是习惯于南方小镇那种懒洋洋的温暖氛围的,是习惯于家庭、亲人、儿时的朋友的圈子里活动的……”,而马丁则觉得“有时候,他们之间会产生一种无法解释的怨恨……他发现艾米丽身上隐藏着一种粗俗的性格,这与她那自然纯真的天性是格格不入的。为了喝酒,她扯谎,用莫名其妙的花招来哄骗他”(McCullers1951)。其实这与麦卡勒斯的母亲也是很相似的,麦卡勒斯的母亲玛格丽特也酗酒,并因此直接影响了麦卡勒斯,导致麦卡勒斯也养成了常年酒不离身的习惯,这是导致她瘫痪和早逝的重要原因。妻子对环境的不适宜却在当时没有引起马丁的注意,在小女儿出事后马丁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对妻子的不信任也越发严重,他甚至将这种担心扩张到怀疑妻子会出轨,给他戴绿帽子,所以马丁“一时间憎恨和不满其自己的命运来了;他恨他的妻子。”马丁是“愤怒”的,因为“他的青春被一个废物般的酗酒女人糟蹋掉了,连他的男子汉凌云气概也无形中受到了损害”,他将家庭不幸的原因归结于妻子,却在看到熟睡的美丽的妻子之后产生了身体的欲念,马丁就在这样的爱恨交织中过着每一天。和《被附身的男孩》一样,在《家庭困境》中,麦卡勒斯同样让女主人公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之后才引起家庭成员,特别是一家之主:丈夫的“关注”。家庭关注的缺失是妻子“犯错”的原因,而丈夫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结束语
在麦卡勒斯的小说中,“精神隔绝”永远存在,孤独是永恒的,交流时不可能的,然而,在麦卡勒斯的短篇小说中,她进一步探讨了这种孤独存在的根源,如对身份、死亡、未知的困惑。《家庭困境》和《被附身的男孩》着眼于女性的孤独,发掘了女性,特别是婚后女性在家庭中存在的打不破的“冷暴力”的步步紧逼下所表现出的人格和身份的破碎,这些女性表现出来的“怪异”不是她们自身,而是家庭中身份和关爱的缺失造成的。20世纪以来,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是可喜的,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家庭压力也导致她们在找寻自我时更加困难,从而产生了各种家庭问题。一个核心家庭的组成要素是夫妻和孩子,这其中哪一方出了问题都会对整个家庭的和谐产生影响,而传统意义上操持家政的女性则成了造成问题的替罪羊,如果不打破传统,从问题核心,即家庭模式和家庭身份上查找原因,家庭幸福是不可企及的,家庭成员间的有效交流也是无法实现的。
Balsamo, Anne Marie (1996). Technologies of the Gendered Body: Reading Cyborg Women. Feminist Bodybuilding [M].Duke University Press.
Chodorow, Nancy (1999).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uden, Barbara (1993). Disembodying Women: Perspectives on Pregnancy and the Unborn. How the Body Became aShowcase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cCullers, Carson (1998). Collected Stories of Carson McCullers. A Mariner Book [M]. N.Y.: HOUGHTON MIFFLIN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