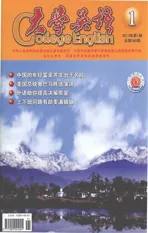论林语堂译创过程的读者意识
2013-03-26郑玮
郑 玮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论林语堂译创过程的读者意识
郑 玮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林语堂学贯中西、译著等身。通过分析林语堂本人对读者观的相关阐述,同时结合其文化观、语言语体观以及宗教哲学观等,从译创作品的选材、译创过程中对读者的关照以及译创作品取得的域外效果,说明林语堂具有强烈的读者意识,并指出林语堂所力求达到的作品可读性和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性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对中国典籍翻译具有启示性作用。
林语堂;译创过程;读者意识
一、引言
林语堂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集作家、语言学家、翻译家、甚至发明家于一身。对林语堂的研究虽然曾经历上个世纪40年代到1979年的“沉寂期”(王兆胜1996:253-254;傅文奇2006:102),但自80年代初以来,林语堂研究逐渐复苏,并于近些年来得到快速发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角度呈现多样化,曾一度不受学界重视的翻译研究视角也逐渐得到关注。但纵观所有这些研究,对林语堂的读者意识却鲜有涉及。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将以林语堂的英文译创作品为出发点,通过分析其本人对读者观的相关阐述,同时结合其文化观、语言语体观以及宗教哲学观等,从选材、译创过程以及接受效果等方面说明其强烈的读者意识,最后指出其读者意识对今天所提倡的中国典籍翻译具有很强的启示性作用。
二、林语堂的译创文学及其读者意识观
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通过同时用英汉两种语言进行翻译和创作,担当起“对中国人讲西方文化,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的重任,并且成就斐然,其中仅英文译创作品(包括汉译英译作与英文创作)就达40余部(冯志强2011:1)。根据姜秋霞等(2009:96-97)的研究,林语堂的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之间呈现出丰富的互文关系。不仅如此,林语堂的很多作品融翻译与创作为一体,即翻译中有创作,创作中有翻译,两者难解难分。这些作品不仅向世界传播了中国文化,也给林语堂带来了“真正的世界公民”和“文化大使”等美誉,迄今为止在这一领域内几乎无人能够企及。
林语堂的非凡成就固然与其精深的双语功底和中西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其在译创过程中所怀有的强烈的读者意识同样功不可没,甚至为其作品在传播阶段受到的强烈反响和广泛好评起着关键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在最能够全面阐释其翻译思想的《论翻译》中,林语堂(2009:492)提出“忠实、通顺、美”三个翻译标准,并将其分别阐释为:第一,译者对原文方面的问题,第二,译者对中文方面的问题,第三,是翻译与艺术文的问题。紧接着,林语堂又将这三个方面分别进一步阐释为:译者对原著者的责任,译者对中国读者的责任以及译者对艺术的责任。显而易见,“通顺”、“译者对中文方面的问题”都说明“译者对中国读者的责任”。尽管文中林语堂的表述针对的是英译汉的情况,因而只涉及中国读者,但这对汉译英同样适用。林语堂这种把读者纳入到翻译理论研究领域的现代翻译思想,不仅突出了读者的主体地位,更丰富了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这足以说明林语堂在翻译理论上具有强烈的读者意识。
林语堂的读者意识同样体现在其创作上。他在《八十自叙》中强调说:“我创出一种风格。这种风格的秘诀就是把读者引为知己,向他说真心话,就犹如对老朋友畅所欲言毫无避讳什么一样。所有我写的书都有这个特点,自有其魔力,这种风格能使读者跟自己接近。”(冯志强2011:208)
此外,他还提出过“感动读者”和“敬重读者”的译创策略(冯志强2011:193)。林语堂这种在翻译和创作方面始终为读者着想的强烈读者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为他的译创作品赢得大量的海外读者群,同时也为他赢得巨大的国际声誉。
三、林语堂的读者意识在其译创过程中的体现
1.林语堂译创过程中对读者的关照
(1)翻译选材
林语堂所处的那个年代,西方正处于高度工业化的发展时期,物欲横流、生活浮躁,人们深感彷徨,在对神秘的东方文化存在偏见和误解的同时,也对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东方古典哲学观和无为闲适、知足常乐的生活特点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王少娣2008:42)。深受中西文化熏陶的林语堂深知西方的社会心理,出于对以老庄哲学中的人生态度以及儒家哲学中“中庸之道”会通整合而成的中国哲学思想的肯定和欣赏,以及为了迎合当时西方高度工业化社会压力下人们对回归自然的向往以及对了解神秘东方的诉求,林语堂选择以宣扬闲适生活以及介绍中国核心哲学为主题的作品作为其翻译文本,同时也将这些主题体现在其创作之中。《浮生六记》、《幽梦影》、《冥廖子游》等众多作品的翻译以及《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等多部作品的创作都明显地体现了这些主题。这些文本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和误读,同时也基本符合西方文化的各种规范,能够满足当时西方人的文化心理需求,甚至拯救了西方工业社会中物质主义泛滥所带来的极端危害。正如冯志强(2011:192)所说,“西方读者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林语堂的主题确定与文化选择,是林语堂英文著译的内在动力”。
林语堂选材上的这种读者意识无疑与其文化观密切相关。林语堂从小受到中西两种文化的浸淫,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既不同于“西化派”的过于激进而对民族文化妄自菲薄和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也不同于“国粹派”的固步自封和对传统文化的抱残守缺,林语堂的世界文化多元化立场为他造就了一种超越东西方文化之上的文化整体观,即不同文化可以兼取互补与会通的文化全局观念(冯志强2011:30-31)。基于这种文化的整体观,林语堂在面对西方科学主义、物质文明给人类精神生活带来彷徨与恐慌之时,极力提倡以东方文化中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智慧来拯救工业社会中被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等所奴役和束缚的灵魂,并在实践中译创了数十部以立体、多维地展示其中国文化观的相关主题作品。
(2)译创过程中的翻译选择
首先,译创内容的选择与修改。林语堂是一位编辑,编辑过程中他始终奉行“开卷有益,掩卷有味”这一坚定不移的目标(冯志强,朱一凡2011:30),这使他在后来的译创过程中特别关照读者,并使其系列译创作品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在自己编译的《中国传奇》的《林氏英文本导言》中林语堂就明确地指出:“本书乃写于西洋人阅读,故选择与重编皆受限制”(王少娣2008:42)。而在编译《生活的艺术》等作品时,更是不断根据读者的实际需要,相继修改许多内容,甚至通过举办“林语堂”比赛,与读者互动,结果取得意想不到的轰动效果(冯志强,朱一凡2011:30)。正因为林语堂译创过程中尊重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其作品最终能够达到“视域融合”的目标。
其次,不同翻译技巧和策略的使用。由于中西方文化迥异,加之读者对译文的解读机制早已浸濡在其所属的文化环境里,中英之间的翻译难度很大。这就需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考虑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接受能力,采用各种不同的策略和技巧将源文本中涉及文化元素的内容传达给译文读者。林语堂深知文化和语言的密切关系,并且对中西文化造诣颇深,其强烈的读者意识使其在译创过程中大量使用增译(包括直译加注、音译加注)、省略、句式调整、文化补偿等手段,尽可能用符合目标语读者阅读习惯的措辞、句式、语篇结构等进行表达,以增强文本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同时也非常注重用目标语读者所熟悉的文化信息进行意义传递,力求在传播中国文化精神的同时将语言的行为模式纳入到文本读者的文化范畴,降低其阅读难度,满足其阅读期待,增强其阅读兴趣,最终达到翻译的目的。
第三,副文本的丰富运用。林语堂是一位学者型的翻译家和作家,其译创作品以丰富多样的副标题、前言、序言、注释、导读、评论、附录、绘画等不同的副文本形式,将自己对原作的认识和理解以及需要对读者进行解释和说明的内容形成文字,与读者进行交流,不仅为其在阅读前做足心理上的准备,而且提供大量的阅读线索,全面而有效地扩充信息量,从而为读者扫清从语言到文化等方面的阅读障碍,最终准确而完整的达到深层理解的期待程度。可以说,林语堂通过在译创文本中增加副文本,“让译本/创作文本走进了读者,并且吸引读者走进了作者的世界,最终使译者、读者与作者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冯志强,朱一凡2011:31)
第四,视读者为知己的语言风格。国内研究林语堂的专家施建伟教授认为,《生活的艺术》等作品之所以能脍炙人口,除了内容上有的放矢,符合西方读者的口味之外,也借助于那种把读者当作知心朋友吐露肺腑之言的“对话体”笔调,使读者亲切地感到:“林语堂在对我讲他的真心话”(卞建华 2005:43)。也就是说,这种笔调很适应西方读者的阅读心理。这点和林语堂(2009:503)在《论翻译》中所强调的“译者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相吻合,只不过该译论中目的语读者是汉语读者,而在译创过程中,林语堂根据的是西方读者的心理而已。这点源于林语堂对英文写作风格的清晰了解—他深知英文书面语与口语相接近,使其更加贴近大众的生活、易于读者理解与接受。他在《八十自叙》中所强调的那种视“读者为知己”的风格,即朴素平易、明晰流畅的“娓语体”,被广泛地运用于译创之中,这种轻松、闲适、通俗、幽默的行文风格最终得到了西方读者的认同与青睐。
此外,林语堂对读者的亲近还体现在某些细节上。例如,《吾国吾民》的第一章有这样一句话,“… for behind the creation of literature and the events of history there is always the individual who is after all of prime interest to us(林语堂 2000:16)(因为在文学创作和历史事件的背后,总是那些单个的人使我们产生最大的兴趣)”,显然,林语堂在这里把自己当成了读者(即句中的“我们”)中一员,这种叙述语气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使西方读者倍感亲切,其作品内容自然也就更容易被接受。
林语堂在语言语体方面表现出来的这种对读者的用心无疑与其语言学家的身份以及甚至“使以英文为母语的人既羡慕又深自惭愧”(王少娣2011:4)的美妙的英文造诣分不开。源于对英语“亲切文体”的深刻了解,林语堂坚信“英美人所谓的好英文就是pure,simple English的英文白话”(冯志强 2011:154),这种“娓语体”在译创作品中的大量使用不仅能让西方读者易于消除接受中国文化的心理障碍,而且能使他们在亲切的氛围中自然地接受中国人独特的生活艺术和生活哲学直至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2.林语堂的读者意识产生的域外效果
基于林语堂自身深厚的中西语言文化功底以及上文所述的强烈的读者意识,林语堂的译创作品成功地把中国文化精神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传递给西方读者,使他们能够领略到东方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国智慧的无穷魅力。其作品不仅在当时的美国颇为畅销,并且很快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地产生强烈的反响。不仅如此,林语堂的很多作品一版再版,根据亚马逊书店的最新统计(冯志强2011:180),《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美国的智慧》、《啼笑皆非》等大部分作品于2008年11月再次以精装版重印,显示了其作品恒久的生命力。对于林语堂的成功,正如其好友乔志高所说,“不单是靠文字的精湛,也是基于他热爱祖国文化,同时有独特的见解。对他广大的读者,无论中外,他有一种common touch,平易近人的笔触,不爱唱高调或是钻牛角尖。这也是他的著作流传远近、历久弥新的缘故”(冯志强2011:194)。这段话再一次说明读者意识是林语堂在海外大获成功的重要因素。
四、结语
王佐良(1997:42)在《严复的用心》一文结尾曾提出“吸引心目中预定的读者—这是任何译者所不能忽视的大事”,林语堂正是这样一位用心于读者的翻译家。这点不仅体现在其《论翻译》中对读者负责的表述当中,更体现在其译创过程中的不同阶段。林语堂译创作品能取得如此良好的社会效果,与其心中装有读者、力求与读者的期待视野达到“视域融合”的用心分不开。可以肯定地说,对林语堂读者意识的研究是林语堂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林语堂读者意识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其文化观、语言语体观以及宗教哲学观等密切互动的结果,而所有这些因素的互动使其译创过程中力求达到在作品的可读性与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性之间取得平衡与和谐。
近些年来,国内翻译界逐渐重视并正在大力推广中国典籍的外译,但是迄今为止,成效一般。林语堂译创作品在国外的大获成功及其产生的持续影响力对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中国典籍翻译无疑具有很强的启示性,是每一位典籍工作者特别需要思考并颇具研究价值的问题。
卞建华(2005).对林语堂“文化变译”的再思考[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
冯志强(2011).中国智慧的跨文化传播——林语堂英文著译研究[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冯志强,朱一凡(2011).编辑出版家林语堂的编译行为研究[J].中国翻译(5)。
傅文奇(2006).近十年来林语堂研究的统计与分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5)。
姜秋霞,金萍,周静(2009).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的互文关系研究——基于林语堂作品的描述性分析[J].外国文学研究(2)。
林语堂(2000).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林语堂(2009).论翻译[A].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修订本)[C].北京:商务印书馆。
王少娣(2008).试论林语堂翻译文本的选择倾向[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3)。
王少娣(2011).跨文化视角下的林语堂翻译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王兆胜(1996).近几年林语堂研究述评[J].社会科学战线(1)。
王佐良(1997).翻译:思考与试笔[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3-02-02
郑玮(1977-),女,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