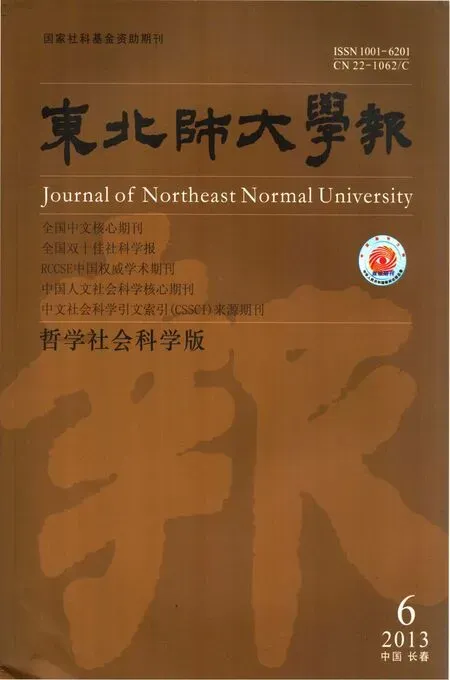严复对宗教起源的探究及二重性
2013-03-24魏义霞
魏义霞
(黑龙江大学 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作为中国近代西学第一人,严复翻译了西方的八大名著,此外还有关于宗教的著作,即英国人宓克的《支那教案论》。该书并非宗教理论专著,然而,严复在按语中表达了对宗教的看法,并且分析了中西之教的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冲突。不仅如此,在翻译、宣传西方思想时,他对宗教多有涉猎,同时介绍了孔德、斯宾塞、亚当·斯密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宗教思想。与严复介绍、翻译的名学、进化论、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学相比,宗教方面的内容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从严复对宗教起源问题的探究入手,领悟严复的宗教观及其二重性。
一
严复对宗教的起源问题兴趣盎然,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探究奠定了他对宗教的基本态度,形成了独特的宗教观。严复对宗教的理解和界定是从追溯宗教的起源问题开始的,具体方法是将宗教问题纳入到社会学之中,侧重从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入手揭示宗教的起源。对此,他的总看法是:“由是而知民业贵贱之分肇于智慧者为多,而始于武力者为少。智慧首争于巫医,由巫医而生君长。具有巫医滥觞而演为今日之二类人:一曰宗教家,又其一曰学术家。是二类之民至今反对,不知其至何日乃合为一途者也。夫巫医之徒皆以使物通神,弹厌呵禁为能事,旱能致雨,潦使放晴,而又有前知之验。则由是而有研究物情,深求理数之人,夫如是谓之学术家;又由是而有笃信主宰,谓世间一切皆有神权,即至生民,其身虽亡,必有魂魄,以为长存之精气者,如是谓之宗教家。宗教、学术二者同出于古初,当进化程度较浅之时范围极广,而学术之事亦多杂以宗教观念,无纯粹之宗风,必至进化程度日高,于是学术之疆界日涨,而宗教之范围日缩。二者互为消长,甚者或至于冲突,此至今而实然者也。”[1]316-317按照这个说法,宗教是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社会分工只在极少数情况下始于武力,大多数情况下则是智慧的产物,而人类智慧之渊源不外乎巫、医两家;在后来的社会发展和演化中,巫术演绎为宗教,医术演绎为学术。这表明,宗教与学术的关系是双重的:第一,宗教与学术同出一源,正如“巫医之徒皆以使物通神,弹厌呵禁为能事,旱能致雨,潦使放晴,而又有前知之验”一样,宗教与学术的内容往往相互混杂,不可截然分开——这一点在人类社会初期表现得尤其明显和突出,“学术之事亦多杂以宗教观念”便是明证。第二,宗教与学术随着社会的进化程度日高而渐行渐远,二者判然分明,乃至相互冲突,彼此的势力范围也由此而呈现出此消彼长之势——“学术之疆界日涨,而宗教之范围日缩”。
在宗教起源的问题上,严复特别介绍了孔德(Comte,严复译为恭德)和斯宾塞的观点,同时对两人关于宗教起源的学说进行了比较。对此,严复写道:
然则宗教滥觞又何如?宗教起点,其存于今有二说焉。其一发于法人恭特;其一发于斯宾塞。二家之说皆有真理,而后说尤胜。请今先明其第一说。彼谓人之心理不能安于所不知,而必从而为之说也,又往往据己之情以推物变,故物变必神鬼之所为。而是神鬼者,又有喜怒哀乐爱恶之事,是故宗教之起,必取山川阴阳而祀之。震电风涛之郁怒,日月星慧之流行,水旱厉灾之时至,彼之智不足以与其所以然也,则以为是有神灵为之纲维张主。神之于物变,犹己心志之于百为,故其祠山川、祀阴阳也,所祀所祠非山川阴阳也,祇畏其主之神而已。是说也,其所据之心理公例,所弥纶至广。凡古人之拜明神、警天变,皆可用此例以为推。且由是而知必科学日明,而后宗教日精,宗教日精由迷信之日寡也,宗教、迷信二者之不可混如此也。
此其说固然。然以谓一切宗教之兴皆由是道,则吾人又未敢以其义为无漏而其说为至信也。盖使即野蛮人,抑村里小民之心理而实验之,未见其于物变恒作尒尒之推求也。旦作夕息,鼓腹含哺,纯乎不识不知而已。问以日月之所以周流,霜露之所以时施,彼将瞠目而应曰:是之为物固如是也。夫即两问之物变而叩其所由然,如是而不能通,乃以为是居无事而披拂之者有鬼神焉,其情如已,是其时圣哲之事也,而非所望于蚩蚩然休养生息者矣。彼以谓主变有神,而神又无形气之可接。则神鬼观念,彼必先成之于心,夫而后可举以推物变明矣。而是鬼神之观念,果何自而起欤?[1]317-318
孔德是西方现代哲学中实证主义的创始人,与严复推崇的穆勒和斯宾塞一样是不可知论者和实证主义哲学家。严复肯定孔德是社会学(Sociology,严复读为梭休洛支或梭休罗支,意译为群学)的奠基人,并且对其社会学和经济学理论予以介绍:“群学西曰梭休洛支。其称始于法哲学家恭德。彼谓凡学之言人伦者,虽时主偏端,然无可分之理,宜取一切,统于名词,谓曰群学。即如计学,亦恭德所指为不能独立成专科者也。”[2]这表明,严复对孔德的思想是熟悉的,却没有翻译孔德的著作。与对待孔德的态度不同,严复翻译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对斯宾塞以生物学讲社会学的为学程序佩服得五体投地,对其以天道贯通人道的哲学大全(综合哲学体系)更是赞不绝口。其实,孔德与斯宾塞一样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并且与斯宾塞一样将社会的存在、发展与宗教联系起来。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严复对两人关于宗教起源的观点深表认同,断定“二家之说皆有真理”,在这个前提下偏袒斯宾塞的学说——“后说尤胜”。
孔德认为,人类社会的形态与知识的发展互为表里,具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宗教,第二阶段是形而上学,第三阶段是实证主义。在社会的初级阶段,知识的有限使人不能解释各种自然现象;为了慰藉不可知带来的恐惧,人们认为万物通神而对之顶礼膜拜。宗教起源于无知,也就是说,此时的科学尚无力对各种自然现象作出解释,由于“人之心理不能安于所不知”,宗教应运而生。由此可见,孔德对宗教起源的认识侧重人的心理原因,故而与不可知密不可分。孔德的这个观点与严复对宗教起源的解释相符。因此,严复认定“此其说固然”,与斯宾塞的观点一起归为“真理”。
与此同时,严复指出,孔德的观点对是对了,却不全面:如果像孔德那样断言宗教皆源于此——“一切宗教之兴皆由是道”,绝非“无漏而其说为至信”。具体地说,孔德的漏洞或不全面之处在于:对于原始人来说,大多生活在无知亦无识的状态之中,推究万物由来者充其量只是极少数人;况且,这些人赋予万物的神灵观念又从何而来?在严复看来,孔德并没有对这些问题予以解答,而斯宾塞的宗教起源说较好地解释了这些问题。于是,他接着写道:
斯宾塞之言宗教起点也则不然。彼谓初民之信鬼始于人身,身死而游魂为变实,而尚与人间之事,如是名曰精气观念animism。乃从而奉事之,亲媚之,以析人事之福利。惟先位此而后推之为鬽,为天神,而宗教之说乃兴。故宗教者,以人鬼为起点者也。然而人鬼之信又何从昉乎?曰始于以人身为有魂魄也,信人身之有魂魄,又由于生人之有梦。浅化之民以梦为非幻,视梦中阅历无异觉时之阅历也。以梦为非幻,于是人有二身,其一可死,其一不可死。又因于生理学浅,由是于迷罔失觉、诸暴疾无由区别,而不知似死真死之分。谓似死则暂死而魂返,真死则长往而魂不返,于是有臬[来]复招魂之事,以灵魂为不死而长存。此中国古制,一切丧礼祭仪之所由起也。
民之造像範偶而拜之者,非信是像偶为有灵也,亦谓有神灵焉主是像偶者。则由是而有多神之教,多神而统之以一尊,则由是而有太岁,有玉皇,浸假而多神之说不足存,于是乎有无二之上帝,此读内[旧]新二约可以得进化之大凡者也[1]318-319。
与孔德侧重从人的心理揭示宗教的起源,进而将宗教的起源归结为由于不可知而带来的恐惧有别,斯宾塞认为,先民的宗教观念始于对自身的认识,由于相信人死而灵魂不死,故而奉事之;之后,推及万物有灵,宗教意识由此而起。这就是说,宗教起于人鬼之际,正如做梦现象使先民相信人的灵魂可以离开形体而存在一样,原始人将人的死亡视为灵魂永远摆脱体魄而成为鬼神。严复认为,斯宾塞对宗教起源的解释在宗教由多神教到一神教的演变中得到证实,更具有说服力。有鉴于此,他对宗教起源的理解与斯宾塞更接近。
总之,通过对宗教起源的探究,严复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宗教与不可知如影随形。他始终突出宗教与不可知的密不可分,强调人对不可知的畏惧与生俱来,人最感恐惧的不是痛苦本身,而是对不可知以及对未来的不可预知。循着这个思路,严复热衷于从不可知论的角度来揭示宗教产生和存在的根源:“培根曰:人之畏死,犹小儿之畏空虚,非畏其苦也,畏其不可知而已。故使当前可乐,彼必不取所不可知者而尝试之也。乃至生极无憀,愿望尽绝,其趋死甘如饴耳。故老氏曰:‘民不畏死。’死之不足畏,以生之无可欣。”[3]1014这就是说,面对不可知之境,人们只能依靠宗教来摆脱恐惧,通过信仰宗教来寻求心灵的慰藉。第二,宗教与信仰相随,主要指信仰鬼神。与此相关,根据“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严复认定《周易》为宗教之书。一言以蔽之,宗教是不可消除的,并且皆言灵魂和死后之事。
二
严复对宗教起源的探究在某种程度上厘清了宗教概念,并且直接决定着他对宗教的理解和态度。通过对宗教起源的追溯和探究,严复指出宗教起源于信仰,同时强调并非所有信仰都是宗教,因为宗教所信仰的是鬼神和灵魂不死。这就将宗教与信仰、宗教信仰与一般信仰区分开来,避免了宗教的泛化。严复对宗教的界定及其意义通过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比较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早在《日本书目志》的“宗教门”中,康有为就给宗教下了这样的定义:“合无量数圆首方足之民,必有聪明首出者作师以教之。崇山洪波,梯航未通,则九大洲各有开天之圣以为教主。太古之圣,则以勇为教主;中古之圣,则以仁为教主;后古之圣,则以知为教主。同是圆颅方趾则不畏敬,不畏敬而无以耸其身,则不尊信,故教必明之鬼神。故有群鬼之教,有多神之教,有合鬼神之教,有一神之教。有托之木石禽畜以为鬼神,有托之尸像以为鬼神,有托之空虚以为鬼神,此亦鬼神之三统、三世也。有专讲体魄之教,有专讲魂之教,有兼言形魂之教,此又教旨之三统也。老氏但倡不神之说,阮瞻为无鬼之论,宋贤误释为二气良能,而孔子《六经》、《六纬》之言鬼神者晦,而孔子之道微。岂知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诗纬》以魂为物本,魂灵固孔子之道。而大地诸教乃独专之,此亦宋贤不穷理而误割地哉!”[4]在这里,康有为指出宗教起于“敬畏”,“必明之鬼神”;这个观点与严复对宗教的看法尤其是斯宾塞的观点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康有为讲宗教的根本目的在于立孔教为国教。为此,他将宗教的发展分为太古、中古与后古三个阶段,进而宣称中古之世的宗教以仁为教主,即“太古之圣,则以勇为教主;中古之圣,则以仁为教主;后古之圣,则以知为教主”。正是基于用三世、三统说对宗教递嬗轨迹的整合,康有为将仁说成是中古宗教的核心,这个时代的各个宗教派别无不如此。至此,康有为将孔教归为宗教,并且指出孔教在宗旨上与佛教、基督教(康有为称之为耶教)别无二致——作为中古宗教,都以仁为宗旨和信仰对象。由强调宗教敬畏开始,以用勇、仁、智整合宗教演变的轨迹终,康有为分不清宗教信仰与一般信仰的区别,导致泛宗教倾向,这种倾向在他对宗教与哲学、理学等的学科分类上突出反映出来。
梁启超做《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力图将宗教与哲学分开,却陷入更大的泛宗教误区。对于宗教,他给出的定义是:“‘宗教是各个人信仰的对象。’……对象有种种色色,或人,或非人,或超人,或主义,或事情。只要为某人信仰所寄,便是某人的信仰对象……信仰有两种特征:第一,信仰是情感的产物,不是理性的产物。第二,信仰是目的,不是手段;只有为信仰牺牲别的,断不肯为别的牺牲信仰……从最下等的崇拜无生物、崇拜动物起,直登最高等的如一神论,无神论,都是宗教。他们信仰的对象,或属‘非人’,如蛇、如火、如生殖器等等;或属‘超人’,如上帝、天堂、净土等等;或属‘人’,如吕祖、关公、摩诃末、耶稣基督、释迦牟尼等。不惟如此,凡对于一种主义有绝对信仰,那主义便成了这个人的宗教。”[5]在这里,梁启超与康有为一样归一切信仰于宗教,不仅与康有为一样由于信仰与宗教相混导致泛宗教倾向,而且在泛宗教论上比康有为走得更远——在这方面,梁启超将人列为信仰对象,声称对于恋爱的人来说,恋爱的对象就是彼此的宗教便是明证。
与康有为、梁启超相比,严复对宗教的界定更为明确,强调教在西方语境中具有确切的内涵:“故凡世间所立而称教者,则必有鬼神之事,祷祠之文,又必有所持受约束,而联之以为宗门徒党之众。异夫此者,则非今西人之所谓教也。”[6]910这表明,宗教有信仰,也有教旨教仪教规,并且有组织形式。无论教仪教规还是组织形式都划清了宗教与信仰之间的界限,避免了归一般信仰于宗教的现象。不仅如此,严复特别提出了宗教信仰的排他性:“且诸宗之起,多在古初。民智方新,传闻斯信,则一切感生神异之说,布于人间。宗自谓神授种,必言天眷,于是诸教始樊然并立。同己所以事天,异者沦于永劫。所关者重,故不止于党同伐异,入主出奴已也。”[6]910严复对宗教信仰排他性的认识和强调解释了宗教之争——特别是基督教在中国近代社会引发教案的原因,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划定了信仰与宗教、宗教信仰与一般信仰的区别,故而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泛宗教论拉开了距离。
与此同时,严复对宗教起源的探究表明,既然宗教起于鬼神信仰,那么,宗教是有神论。事实上,严复不仅彰显宗教的鬼神信仰,而且强调由低级的多神教进入高级的一神教是宗教的进化法则,并以此为依据对世界宗教状况进行概括和考察。这意味着他以鬼神信仰作为宗教演变程度的标准,对各地宗教进行区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严复写道:“欧洲诸教,皆起安息大食之间,一曰犹太,二曰基督,三曰摩哈穆。而基督、摩哈穆流布最广。基督者,耶稣也,本犹太人,故因犹太旧教,起为新宗,垂二千年。其支流最众,曰希腊,曰罗马。罗马又号公教,指斥公教者,则修教也。修教有路得,有葛罗云,而行于诸国者,又各少异。此非专攻讨论,则无由知其正变沿革者矣。故基督之流虽多,要皆以耶稣为帝子,皆信其降生杀身,以赎人类本生之罪孽者也。犹太、基督、摩哈穆,三教虽异,要皆以崇信一神为本旨,此其大较也。非、美二洲之土番,与夫欧亚之北部南溟,或奉树石,或祀龟蛇,至一切动植之属,是曰多神之教。言教理者,以此为最下。雪山恒河之间,是为印度。印度有圣人曰佛,其立教以无神为本旨。故其竖义,能空诸有,而立最高之说,行于日本支那者,盖二千载矣。”[6]910-911在这个视界中,欧洲的宗教分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摩哈穆),其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播最广,基督教在2 000年的流传中教派众多,都信仰耶稣基督。基督教源于犹太教,以罗马的天主教与希腊的东正教为最。罗马天主教是公教,经过宗教改革的基督教称为新教,新教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严复译为路得)教和加尔文(Calvin,严复翻译为葛罗兰)教最著名。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虽然各不相同,却皆属于一神教,或曰高级宗教。非洲、美洲的土著居民和欧亚大陆北部信奉多神教,属于低级宗教。恒河流域的印度信奉佛教,佛教是无神教,宣扬诸法性空,流传至中国和日本,已经具有2 000多年的历史。
严复对世界宗教分布以及对各种宗教的介绍言简意赅,各个区域、各种类型的宗教皆囊括其中。这个介绍以地理分布与信仰对象为经纬线,将信仰对象分为多神、一神和无神三种类型。线索明朗,逻辑周延,让人对世界宗教的存在状况一目了然。不用太多留意即可发现,严复在这里的说法与前面的说法之间隐藏着一个逻辑矛盾:根据对宗教起源的考察,严复认为宗教起于信仰,而宗教信仰有别于一般信仰之处是崇拜鬼神,坚信灵魂不死。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鬼神的崇拜作为宗教的本质特征是不可缺少的。循着这个思路,宗教可以有多神教与一神教之分,却不可能存在有神教与无神教之别。换言之,既然宗教是有神论,无神论便不能成为宗教。在这个前提下,严复将佛教列入对世界宗教的考察中,让人不禁心生疑窦:佛教究竟是不是宗教?依据严复的一贯看法,佛教并不主张灵魂不死,甚至压根就否认灵魂的存在。对此,他特意指出,佛教所讲的喀尔摩(karma,又音译为羯磨或羯摹,意译为业)并非指灵魂:“而真不主灵魂者独佛耳!其所谓喀尔摩,与其所以入涅槃而灭度者,皆与诸教之所谓灵魂者大殊。”[3]1016至此可见,严复的宗教观与佛教观是矛盾的:既然佛教不讲灵魂,不属宗教,为何将佛教纳入对世界宗教的考察之中?如果佛教是宗教,作为宗教的佛教为何不崇拜鬼神乃至不言灵魂?在宗教由多神教向一神教的进化中,佛教处于何种序列?对于这些问题,严复并没有给出必要或明确的解答。
三
严复对宗教起源的探索和对宗教概念的界定始终突出宗教与不可知的内在联系,哲学上浓郁的不可知论情结使他分不清哲学与宗教的界限,最终导致另一种泛宗教倾向。严复多次声称自己生平最爱哲学,而他所讲的哲学以不可知论为主要内容,是西方的赫胥黎、斯宾塞、穆勒和牛顿的思想,中国的《周易》《老子》《庄子》与佛教相互和合的产物。严复的宗教观与哲学观密不可分,哲学上的不可知论注定了他热衷于与不可知之境密不可分的宗教。浓郁的不可知论情结以及宗教与不可知论密不可分甚至使他的宗教与哲学相互印证,共同指向不可知论。与对哲学的喜爱和不可知论情结息息相关,严复无论是对于佛教的思维缜密还是修行实践都大为折服,除了赞叹“宗教之多思维,殆莫若佛”[3]1014之外,还一再将佛教的自在与西方哲学的“庇因”(Being,今译为存在)相提并论,对于佛教不可思议的顶礼膜拜更是无以复加。在此基础上,他以不可思议为中介,将佛教与西方的不可知论相互诠释:“又如释氏之自在,乃言世间一切六如,变幻起灭,独有一物,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以其长存,故称自在。此在西文,谓之persistence,或曰eternity,或曰conservation,惟力质本体,恒住真因,乃有此德。”可以看到,严复眼中的哲学经典《周易》《老子》《庄子》和佛教皆与宗教具有某种撇不开的关系,甚至相互纠结。在他看来,由于都是不可知论,它们都强调可知者止于感觉而彰显宇宙本体的不可感觉性,至少都含有某种程度的宗教性。这使严复分不清哲学与宗教的界限,在模糊两者界限的前提下对佛教、《周易》《老子》《庄子》与宗教相互诠释:一方面,严复反复将自己认定的中国哲学的经典《周易》、《老子》和《庄子》与宗教思想相互诠释。例如,他将《老子》的思想与宗教混为一谈,多次将之与佛教、基督教相提并论:就《老子》与佛教的相互诠释来说,对于《老子·第十四章》的“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他的评语是:“老之道纪,其形容处,大类释之涅槃。”[7]1081就《老子》与基督教的相互诠释来说,对于《老子·第十六章》的“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他的评语是:“夫耶稣教可谓知常者矣,以其言爱仇如己。”[7]1081另一方面,严复将西方灵学会的观点与《周易》《老子》和佛教的思想相提并论,乃至混为一谈,由此对之坚信不移,肯定其“所言皆极有价值”:“查英国灵学会组织,创设于一千八百八十二年一月,会员纪载、论说、见闻,至今已不下数十巨册。离奇吊诡,有必不可以科学原则公例通者,缕指难罄。然会中巨子,不过五、六公,皆科哲名家,而于灵学皆有著述行世。巴威廉Sir William Barrett F.R.S.于本年二月《同时评阅志》Contemporary Review中方出一论,意以解国人之惑。谓会中所为,不涉左道,其所研究六事:一、心灵感通之事。二、催眠术所发现者。三、眼通之能事。四、出神离魂之事。五、六尘之变,非科学所可解说者。六、历史纪载关于上项者。所言皆极有价值。终言一大事,证明人生灵明必不与形体同尽。又人心大用,存乎感通,无孤立之境。其言乃与《大易》‘精气为魂,感而遂通’,及《老子》‘知常’、佛氏‘性诲’诸说悉合。”[8]721
在西方哲学中,实证主义与不可知论互为因果。在这方面,深受西方影响的严复哲学亦是如此。由于强调一切皆源于感觉,轻视理性的作用,对于感觉范围之外的存在只能存而不论,这就为信仰留下了地盘。严复的宗教观与他个人的信仰息息相通,乃至成为晚年的心灵寄托。严复少年时留学英国,对英国的经验论和实证主义情有独钟;由于秉持实证主义原则,坚持一切认识都源于感觉经验,他提倡“即物实测”,反对心成之说,而他所反对的心成之说就包括宗教及其崇拜的上帝在内。例如,在评点《庄子·齐物论》篇的“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时,严复写道:“世人之说幽冥,宗教之言上帝,大抵皆随其成心而师之之说也。曰福善祸淫而不容,事偶而赦罪宥眚;中国之想像,则袞冕而圭璋;西人之为容,则袒裸而傅翼。凡此者,皆随其成心以为之说。至其真实,则皆无据。”[9]不仅如此,他多次指出宗教与科学殊途,断言宗教起于信仰,缺少实证而对之含有微词。尽管如此,由于秉持不可知论而为信仰留下地盘,严复不能割断与宗教的联系。结果是:不可知论与宗教相互造势,严复晚年转向信仰之境。这一点在他晚年所写的信件中淋漓尽致地反映出来:
鄙人以垂暮之年,老病侵寻,去死不远;旧于宗教家灵魂不死之说,唯唯否否不然;常自处如赫胥黎,于出世间事存而不论Agnostic而已。乃今深悟笃信,自诡长存,故不觉与贤者言之覼缕如此也。心之精微,口不能尽,惟进道修慧,昭视无穷……每有极异之事,庸愚人转目为固然;口耳相传,亦不问证据之充分与否,此最误事。故治灵学,必与经过科学教育,于此等事极不轻信者为之,乃有进步。复生平未闻一鬼,未遇一狐。不但搜神志怪,一以谬悠视之;即有先辈所谈,亦反复于心,以为难信。于《丛志》鬼神诸论,什九能为驳议;惟于事实,则瞠视糹舉舌,不能复置喙耳[8]722-723。
神秘一事,是自有人类未行解决问题。往者宗教兴盛,常俗视听,以为固然。然而诞妄迷信,亦与俱深,惑世诬民,遂为诟病。三百年科学肇开,事严左证;又知主观多妄,耳目难凭;由是历史所传都归神话。则摧陷廓清之功,不可诬也。然而世间之大、现象之多,实有发生非科学公例所能作解者。何得以不合吾例,憪然遂指为虚?此数十年来神秘所以渐成专科。而研讨之人,皆于科哲至深。观察精密之士,大抵以三条发问:一、大力常住,则一切动法,力为之先;今则见动不知力主。二、光浪发生,恒由化合;今则神光焕发,不识由来。三、声浪由于震颤;今则但有声浪,而不知颤者为何。凡此皆以问诸科学者也。其他则事见于远,同时可知;变起后来,预言先决,以问哲学心理之家。年来著作孔多,而明白解决,尚所未见。故英之硕学格罗芬(Lord Kelvin)临终,谓廿世纪将有极大极要发明,而人类从兹乃进一解耳[10]。
在此,严复强调,研究灵学“必与经过科学教育,于此等事极不轻信者为之”,带有实证主义痕迹。然而,正如他自己所坦言的那样,已经改变了对神秘之事存而不论的态度。这一点从严复晚年对神秘之事和西方灵学的津津乐道中即可见其一斑。这种兴奋点的转移本质上是对宗教态度的转变,归根结底取决于严复个人信仰的转变。当然,在严复那里,无论是对宗教的态度还是信仰的转变都始终与不可知论息息相通。
综上所述,严复对宗教的理解始终交织着信仰与实证的矛盾:由于宗教起于信仰,科学起于实证,宗教与科学殊途,秉持格致救国的严复对宗教持否定态度;由于确信科学越发达,开拓的可知之境越多,留下的不可知之境越大,而不可知之境只能诉诸信仰,由此为宗教留下势力范围。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信仰的并非是有神论的宗教,而是对无法实证的不可知之境的敬畏或存而不论。循着这个思路,如果在将宗教的演变轨迹由多神教到一神教的基础上再向前推进一步,由有神论走向无神论的话,可以破解不讲灵魂的佛教何以成为宗教的矛盾,也更符合严复本人的宗教信仰。可惜,严复本人没有这么说!
[1]严复.天演进化论[M]//严复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2]严复.《国计学甲部》残稿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847.
[3]严复.《法意》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4]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三[M]//康有为全集:第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97-298.
[5]梁启超.评非宗教同盟[M]//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966-3967.
[6]严复.《原富》按语[M]//严复集: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7]严复.《老子》评语[M]//严复集: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8]严复.与侯毅书[M]//严复集: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9]严复.《庄子》评语[M]//严复集: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1107.
[10]严复.与俞复书[M]//严复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