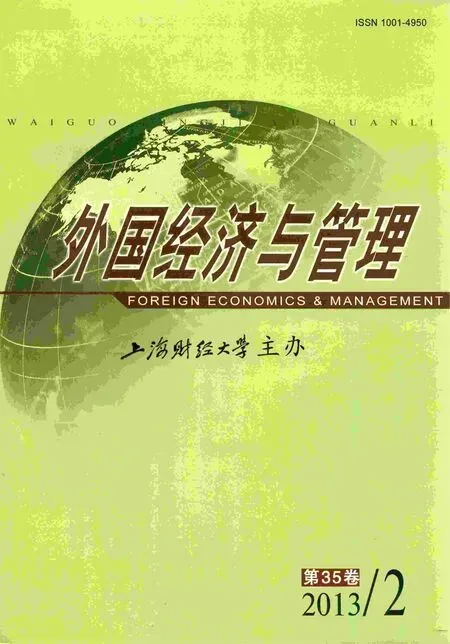吸收能力构念解析与理解误区解读
2013-03-19王天力张秀娥
王天力,张秀娥
(1.吉林大学 商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2.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117)
一、引 言
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是近20年来组织和战略管理研究领域出现的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在许多组织与战略管理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引用,其丰富的内涵和强大的解释力为组织和战略管理研究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新视角,因此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然而,随着吸收能力研究数量的不断增多,对吸收能力构念理解随意化和内涵界定泛化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如随意拓展(randomized extension)、同义反复(tautology)和象征性引用(ritual citation)等问题普遍存在。对吸收能力构念的理解存在比较严重的分离问题,即与经典文献的构念定义和前提假设相分离(Cronbach和 Meehl,1955)。对构念进行严谨、科学的定义,是构建理论最重要的前提条件(陈晓萍,2008),所以有必要重新研读吸收能力的原始定义和前提假设。此外,吸收能力构念内涵界定不清,也会影响相关研究的效度以及吸收能力研究的累积性进展。因此,本文通过对国外英文经典文献的系统梳理和仔细分析以及对吸收能力构念的溯源性回顾,来认真解读国内学者在理解吸收能力构念方面存在的主要误区,分析造成这些理解误区的主要原因,并对吸收能力构念及其维度进行解构和重新建构。
二、吸收能力构念起源探析
吸收能力作为理论构念是由Cohen和Levinthal于1989年在《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上发表的《创新与学习:研发两要素》(Innovation and Learning:The Two Faces of R&D)一文中正式提出的。然后,他俩在1990年《管理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上发表的《吸收能力:学习与创新的新视角》(Absorptive Capacity: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一文中进一步丰富了吸收能力的内涵。到目前为止,吸收能力作为一种理论已经成为组织和战略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解释工具。截至2012年12月15日,Cohen和Levinthal(1990)的这篇论文在Google学术论文数据库中的被引用频次已经达到17879次。吸收能力一提出就备受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吸收能力构念为组织和战略管理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或者说从组织吸收能力的角度能够更好地观察和解释组织的资源配置和绩效问题;第二个原因是吸收能力与同时期出现的组织学习、战略联盟、知识管理以及先前的资源基础观等理论形成了相互补充和促进的态势,从而一度成为组织和战略管理研究的热点问题。
实际上,在Cohen和Levinthal之前,就有学者进行了相关表述。例如,Tilton(1971)、Evenson和 Kislev(1975)、Mowery(1983)以及 Allen(1984)都提出过研发管理有助于企业提高内部技术能力和吸收能力。不过,这些学者并没有给出吸收能力的确切定义。而Cohen和Levinthal(1989)却在这些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产业组织如何和为何要进行研发投入进行了详细的经济学阐释,并用数据实证检验了研发投入对吸收能力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们俩还用一个能引起共鸣的简明术语“吸收能力”来命名自己的理论阐释。从此,吸收能力正式受到管理学者尤其是组织和战略管理学者们的关注。
Cohen和Levinthal(1989)提出了“组织的先期研发投入可以提高组织从环境中识别、消化和利用知识的能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企业‘吸收能力’”(the ability to identify,assimilate,and exploit knowledge from the environment—what we call a firm’s“absorptive capacity”)的观点。同时,他们还把研发—销售收入比(R&D/Sales)作为测量吸收能力的主要指标来实证检验自己提出的理论模型。这篇文章给出了吸收能力的开创性定义,同时不无创见地指出了研发对于提升企业吸收能力的积极作用。但遗憾的是,这篇文章所界定的吸收能力内涵与其所采用的测量指标并不匹配,因为该文把吸收能力界定为“一种学习过程”(a learning process)和“一种能力”(a capability),但在实证和模型中却把吸收能力等同于研发支出(R&D spending),这相当于把吸收能力视为静态的资源,而不是动态的过程和能力,因而与其自身为吸收能力界定的内涵相矛盾。
Cohen和Levinthal(1990)在重申自己1989年提出的主张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对个人认知结构和问题解决方式(individuals’cognitive structures and problem solving)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吸收能力的内涵,同时更加强调吸收能力的过程和能力特征。他们俩把吸收能力从个人层面拓展到组织层面,并且指出组织的吸收能力是先前创新和解决问题经验的副产品,因而是建立在组织成员个人吸收能力(individual absorptive capacities of the organization’s members)即个体的先前知识和经验之上的;吸收能力具有过程特征,是一种动态的学习、消化和应用过程,具有累积性和路径依赖性,并且依赖于组织内部沟通和共享的能力(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and share internally)。其中,知识沟通和共享对于组织的吸收能力尤为重要。这些内容也正是Cohen和Levinthal(1990)论述吸收能力的前提假设。他们俩(1990)认为,由于组织的研发活动能够帮助组织积累知识和经验,形成动态学习和路径依赖,并且促进组织的知识沟通和共享,因此,研发投入能够促进组织吸收能力的提高。与此同时,这篇文章还给出了现在我们已经耳熟能详并广为引用的吸收能力定义“企业识别、评价、消化和商业化利用外部新知识的能力”(a firm’s ability to value,assimilate,and commercially utilize new,external knowledge)。最后,他们俩继续采用相同的模型、数据和方法,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以及组织吸收能力与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
Cohen和Levinthal(1994)题为《幸运青睐有准备的企业》(Fortune Favors the Prepared Firm)的文章进一步拓展了吸收能力的内涵,增加了吸收能力的预见性含义,认为吸收能力不仅包括识别、消化和应用能力,而且还应该包括准确预见未来技术机会的能力。当下对吸收能力的投入未来会带来回报,即所谓的“幸运青睐有准备者”。
由此,吸收能力作为构念得以在Cohen和Levinthal(1989、1990和1994)的三篇文献中形成和建立。尽管它们都是以企业研发为框架进行的研究,但这三篇文献还是比较清晰地界定了吸收能力作为构念的定义和内涵,同时也对其前提假设、前因变量(研发投入)及结果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它们明确表达了这样一个主旨性观点:通过研发投入,企业可以获得某一特定领域的新知识、然后把新知识与企业的产品和市场开发联系起来,建立适当的组织流程和制度来保证这些知识在企业内部共享,并且利用这些知识来创造为开发新产品和新市场所必需的新知识。这些内容实际上阐明了构成组织吸收能力的三种核心能力,即外部知识识别能力、外部知识消化能力和外部知识利用能力。现在,Cohen和Levinthal的三篇论文(1989、1990和1994)被公认为是构建吸收能力这个构念的奠基性文献。
与此同时,吸收能力在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也借鉴了其他一些相关理论,如资源基础理论、动态能力理论、组织学习理论和知识管理理论等。吸收能力理论与这些理论既有重叠,又有区别。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竞争优势由企业内部资源决定(Penrose,1959)。吸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组织的资源,如组织的人力资源、研发投入、组织结构和组织能力等,但吸收能力更是一种动态能力和过程。资源基础理论是一种静态理论,它可以从结构方面解释吸收能力的构成维度,但却难以解释吸收能力的形成路径和成因。动态能力理论关注组织外部环境的变化,认为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取决于企业获取、构建、整合和重构内外部资源以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Teece等,1997;Eisenhardt和 Martin,2000)。吸收能力具有资源配置、整合的很多动态特征,更强调知识配置、整合、利用乃至创造的动态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动态能力(Zahra和George,2002)。组织学习理论认为,组织学习是组织有效处理、解释和反馈组织内部信息进而改进组织行为的过程(Agyris和Schön,1978),但组织学习更加关注有关组织内部消化的问题。组织通过提升自己的知识理解能力来调整决策行为,最终提高自身的组织和行为能力(Fiol和Lyles,1955)。组织学习能够解释吸收能力的形成路径和过程,而吸收能力也能促进组织学习的开展。吸收能力作为构念其实包含了组织学习的某些结构维度。知识管理理论涉及知识的应用和创造,同吸收能力的关系更加密切。知识管理理论从组织知识管理的角度出发,对组织内外部知识的识别、评价、吸收和转化过程进行了分析,而组织的吸收能力也是从组织识别、消化、应用知识等方面来描述组织知识管理能力的形成过程。组织的知识基础和知识管理过程决定组织的吸收能力(张洁等,2012),而组织利用自己的吸收能力识别、转化与应用外部知识的过程也会影响组织的知识基础和知识管理过程。吸收能力理论与这些理论相互借鉴和融合发展,成为自20世纪以来组织和战略管理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三、吸收能力构念内涵界定
在阐述吸收能力起源时,我们提到了Cohen和Levinthal(1989和1990)对吸收能力所下的权威定义。另有一些学者又在该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吸收能力定义。例如,Mowery和Oxley(1996)把吸收能力定义为企业处理从外部引进隐性知识所需的技能和能力。Kim(1998)把吸收能力界定为企业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Dyer和Singh(1998)在Szulanski(1996)研究的基础上把吸收能力进一步定义为企业识别(identify)、消化(assimilate)、应用(apply)其他企业知识的能力,并且认为吸收能力是一种建立在组织间“社会性互动”(sociological interaction)、由合作伙伴发展起来的合作过程(collaborative process that the partners develop)以及合作伙伴成员间关系(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members of those firms)之上的能力。Lane和Lubatkin(1998)从吸收能力的二元对偶关系出发提出了相对吸收能力的概念。他们俩认为,吸收能力是相对的,随着“老师”企业的知识类型、“学生”企业与“老师”企业激励机制和组织结构的相似性以及“学生”企业熟悉“老师”企业问题解决方式的程度的不同而不同。Zahra和George(2002)认为吸收能力是一种动态能力,是一整套企业据以获取、消化、转化和应用外部知识的组织惯例和流程(a dynamic capability,a set of organizational routines and processes by which firms acquire,assimilate,transform,and exploit knowledge),并进一步将吸收能力分为潜在吸收能力(potential absorptive capability,即组织获取和消化外部知识的潜在能力)以及现实吸收能力(realized absorptive capability,即组织实际转化和利用已获得的外部知识的能力)。Lane等(2006)结合Cohen和Levinthal(1990)的吸收能力定义,从过程的角度把吸收能力定义为企业利用从外部获取的知识的能力,并且把企业利用从外部获取的知识分为三个连续的过程(sequential processes):一是通过探索性学习(exploratory learning)来识别和理解(recognizing and understanding)外部新知识的潜在价值,二是通过转化性学习(transformative learning)来消化(assimilating)新知识,三是通过利用性学习(exploitative learning)来利用新知识创造商业产出(commercial outputs)。这一定义充分体现了吸收能力的过程/能力属性,是吸收能力静态观向动态能力和过程观发展的新起点。Lichtenthaler(2009)依据Lane等(2006)关于吸收能力的动态能力/过程观认为,吸收能力是关于识别和理解(recognize and assimilate)外部知识、保持和激活(maintain and reactivate)外部知识以及重组和应用(transmute and apply)外部知识等多个学习过程的互补性动态能力。
国内也有学者研究过吸收能力问题。例如,王国顺和李清(2006)在研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的知识转移问题时把后者的吸收能力界定为识别、理解、学习和应用能力。王睢(2007)认为,吸收能力实际上是组织自身的吸收能力①与组织间关系的函数,是一种基于组织间关系的相对能力,一种嵌入在合作情境中的跨组织能力。张洁等(2012)把吸收能力定义为组织通过从环境中感知各种变化来获取、消化、吸收和转化外部知识②并将其应用于商业用途的能力。
虽然以上学者所下的吸收能力定义有所不同,但都是建立在Cohen和Levinthal(1990)的基础定义之上的,他们都认为吸收能力是涉及知识识别(recognize)、评价(evaluate)、消化(assimilate)、转化(transform)、整合(integrate)和应用(apply)的能力和过程。尽管如此,后续很多研究往往缺乏对经典文献的准确研读,从而导致对吸收能力构念的理解出现了很多误区。
四、吸收能力构念理解误区解读
应当说,有关吸收能力构念的理解误区既源自于Cohen和Levinthal的奠基性研究,又可归因于后人对Cohen和Levinthal研究的错误解读(Lane等,2006)。下面对有关吸收能力的主要理解误区逐一进行解读。
(一)“吸收能力只与研发相关”
许多实证研究(如 Mowery等,1996;Ahuja和 Katila,2001;Meeus等,2001;Tsai,2001)都是在研发活动的情境下研究吸收能力问题的,并且用研发强度(R&D intensity)或申请专利数量来测量吸收能力。它们把吸收能力视为由创新活动带来的知识,认为企业的吸收能力主要取决于企业的研发强度,因而过多地注重吸收能力的结构特性,而忽视了吸收能力具有的识别、消化和应用过程的特点。一些研究者忘记了吸收能力构念存在的前提条件,其中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尽管Cohen和Levinthal(1990)赋予吸收能力构念丰富的内涵,认为企业的吸收能力具体体现为企业的社会认知和累积性渐进过程,但是,他们俩在1989和1990年的两篇文献中都采用研发强度作为衡量吸收能力的操作化指标,而没有论述吸收能力的过程/动态能力性质,从而导致后续研究(如 Mowery 等,1996;Meeus 等,2001;Tsai,2001)大多采用研发强度来测量吸收能力,并且促成了单纯用研发强度衡量吸收能力和以技术型企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研究倾向。这种把吸收能力狭隘化的做法大大缩小了吸收能力构念的丰富内涵,导致一些学者误认为吸收能力只涉及研发问题,进而严重影响了后续吸收能力研究结论的效度。例如,Tsai(2001)发现研发强度正向影响创新,而 Mowery等(1996)和 Meeus等(2001)却先后得出了研发强度不能显著影响组织学习和创新的结论。
(二)“吸收能力就是既有知识”
一些学者(如 Mowery等,1996;Kim,1998;Ahuja和Katila,2001)把吸收能力等同于知识基础——即组织既有的知识基础,包括与学习伙伴的知识内容或知识的相似性。他们忽视了Cohen和Levinthal所界定的吸收能力的原始内涵,尤其是忽视了原始定义的过程/能力特征。虽然有些研究(如 Lane和Lubatkin,1998;Lane等,2001)也提到了吸收能力的过程和能力特征,但没有界定吸收能力的可操作化定义,并根据这样的定义来实证检验对外部知识的消化和应用过程。把吸收能力等同于组织的既有知识的做法导致了对已有有形知识的过分强调,如创新、发明、专利数等,而忽视了更多的无形知识产出,如知识管理过程和知识创新过程等,而后者恰恰对企业的发展具有更大的意义。同时,把吸收能力等同于已有知识的做法还导致了相关研究停留在静态水平,并且忽视了吸收能力的动态过程和能力特征。另外,这一理解误区还造成很多研究存在自变量和因变量同源的方法问题,从而严重影响了研究结论的效度。
(三)“企业的吸收能力取决于企业知识的稀缺性”
一些学者(如Mowery等,1996;Ahuja和Katila,2001)由于受资源基础观(RBV)结构/内容学派的影响,认为企业的吸收能力取决于企业知识的稀缺性(scarcity of the firm’s knowledge)。在 RBV的结构/内容学派看来,企业的竞争优势取决于企业是否掌握了稀缺的资源,即能否实现理查德租金(Ricardian rent)(Schulze,1994),企业自己能够获取或者阻止竞争对手获取他们没有的稀缺资源,就能够大大提高自己的竞争力(Barney,1986;Peteraf,1993)。但事实上,吸收能力的原始内涵更多地受到RBV过程/能力学派的影响,即吸收能力作为一种能力强调的是对资源的配置、整合和利用,而不仅仅局限于企业所掌握的稀缺资源(如稀缺知识)(Kogut和Zander,1992;Amit和Schoemaker,1993;Nonaka,1994;Lane等,2001)。这一理解误区导致后续研究只关注企业已经掌握的稀缺知识,从而严重影响了吸收能力研究向过程和能力方面的拓展。
(四)“企业的吸收能力与员工个人关系不大”
很多研究者认为,企业吸收能力是一种企业层面的吸收能力,它主要与企业层面的知识引进、知识转化和知识创新有关,而与企业员工个人关系不大。因此,学者们在他们构建的吸收能力实证模型中很少考虑企业员工的个人因素。其实,企业吸收能力并不能排斥它与员工个体认知之间的关系,企业员工会对企业的吸收能力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企业尤其是知识密集型企业的重要员工在这方面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即使是一般企业的普通员工在企业知识的吸收、消化、应用、维系和创造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其实,吸收能力构念从一开始就十分强调员工个体认知对企业吸收能力的重要性,因此,“企业的吸收能力不仅仅是行业和企业特征的函数,而且还是员工个体吸收能力以及组织整体结构和流程的函数”(Cohen和 Levinthal,1990)、“个体特有的知识、心智模式、环境审视、创新方式等都是组织获得吸收能力的前提条件”(Cohen和Levinthal,1990)。Cohen和Levinthal在1990年发表的论文中就提出了“个体认知是企业吸收能力的基础”,“审视企业员工的个体心智模式与企业的共享心智模式有助于洞察应该识别什么样的新知识、如何转化和组合新知识以及如何利用新知识”等观点。尽管如此,很多学者仍然为简化起见把吸收能力构念作为单维变量来处理,而没有把员工个体认知这一重要的变量纳入企业吸收能力研究的实证模型。对员工个体认知的忽视导致企业吸收能力研究忽略了对人这个最主要因素的考量,进而造成吸收能力研究缺少了员工这个关键主体。
(五)“把吸收能力的结构维度等同于前因变量”
现有的吸收能力研究不乏对吸收能力结构维度的阐释。但是,一些研究把吸收能力的结构维度等同于影响吸收能力的前因变量。例如,Cuellar和Gallivan(2006)认为吸收能力包括既有知识基础、知识整合能力、组织动机、组织结构、文化匹配性和交流渠道六个维度;Tu等(2006)认为吸收能力包括既有相关知识、知识交流网络、组织内部知识交流风气或氛围、知识搜寻机制等四个维度;陶峰(2009)把研发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知识管理制度看作是企业吸收能力的四个主要维度③。其实,影响吸收能力的前因变量有很多,如先前知识、研发水平、组织结构、组织战略、文化相容性、员工人力资本、网络嵌入性等(Cohen和Levinthal,1990;van den Bosch 等,1999;Lane等,2001),但这些因素并不能等同于吸收能力的结构维度。吸收能力的结构维度主要包括知识识别能力、知识消化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这三种能力才是企业吸收能力的三个主要结构维度,但它们不是影响吸收能力的前因变量。造成这一理解误区的主要原因,一是片面解读了吸收能力的经典文献,二是对吸收能力的结构维度缺乏正确的认识,具体表现为对吸收能力构念进行随意拓展(即没有严格根据经典文献进行定义)和泛化(没有严格援引经典文献,而只是象征性引用),而尤以同义反复(tautology)和象征性引用(ritual citation)最为常见④。这些问题导致吸收能力研究很难专注于一些实质性问题,难以获得累积性进展。需要说明的是,对原文的直译加剧了吸收能力构念的抽象性和模糊性,从而导致对吸收能力构念理解的随意化和内涵界定的泛化。
五、对吸收能力构念的解构和再建构
在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们通常把一些专门用于科学研究和理论建构的概念称为“构念”(construct)。其实,构念就是为了构建理论或研究问题而创建的抽象概念,它不同于普通的概念,往往具有情境性和专有性特点。构念是构建理论的基本元素。因此,构建理论的最重要前提和基础就是要准确、概括性地定义要测量的构念,清楚地确定构念的理论边界。只有准确界定的构念才具有理论建构和实践指导意义。构念界定模糊,就会导致模糊的研究命题或者假设,还会导致对要研究的事物或现象的错误认识,甚至导致难以积累相关知识(Osigweh,1989)。
那么,什么样的构念才算是界定准确的构念或者好的构念呢?通常,好的构念应该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具有完备性和简易性。构念既要尽可能全面地涵盖所有的相关要素,又要精练,也即构念的定义既不能过于宽泛也不能过分狭隘。能否精准界定构念,是检验学者理论素养的试金石(Whetten,1989)。此外,采用重复定义的方法,是不可能很好地界定构念的,也就是说不能把类似、相近的概念作为构念定义的一部分(Pedhazur和Schmelkin,1991;Klein等,1994)。二是清晰界定构念的层次和内部结构。构念的层次也就是我们据以描述研究现象的分析层次,构念的分析层次决定测量层次(Chan,1998)。构念的内部结构就是我们常说的维度结构,会影响测量指标的开发,并决定构念的边界。三是说明构念的特征、主要前因、相关性与结果。这里所说的构念特征是指一个构念区别于其他构念的主要特点,因而构念的特征是构念的重要标签。提出构念并对其进行测量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探讨目标构念与相关构念之间的关系。因此,可能的话,应当说明目标构念与其他主要构念间的相关或因果关系。
根据上述标准,重新对吸收能力构念的原始内涵、结构和特征进行解构,目的是要进一步明确、细化和重新建构吸收能力的内涵、内部结构和主要特征,以期对这个构念进行更加科学、准确的界定和维度建构。
首先,吸收能力的内涵。从Cohen和Levinthal(1989和1990)的经典文献到后来权威学者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吸收能力的本质内涵是“企业识别、评价、消化外部新知识,最终把它们应用于商业化产出的能力”。其中,“对新知识的识别、评价、消化和应用”是吸收能力的本质规定性,我们必须根据本质规定性来界定吸收能力。吸收能力的范围规定性就是吸收能力构念的分析层次——企业或者组织,也就是吸收能力主要是指组织识别、评价、消化和应用外部新知识的能力。“商业化产出”表示应用吸收能力的最终结果,也就是说,吸收能力的最终结果不是简单的知识学习和应用,而是要实现“商业化产出”,也就是要将知识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实现实质性的知识创新。所有这些构成了吸收能力最重要的核心内涵,对吸收能力这个构念的界定和拓展都必须基于其核心内涵。
其次,吸收能力的结构。吸收能力的结构是指吸收能力的维度结构,即吸收能力主要包含哪些方面和内容,或者说它有哪些构成要素。在Cohen和Levinthal(1990)那里,吸收能力的确要受到员工个体的先前知识,管理者和一般员工掌握或积累的相关工作技巧、技术和经验以及研发水平等很多要素的影响,但其主要构成一直是识别、消化和应用能力三个维度。在Kim(1998)那里,吸收能力包括学习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在van den Bosch等(1999)那里组织结构和整合能力是吸收能力在组织层面的体现;在Lane等(2001)那里,吸收能力包括先前的知识积累、文化相容性、业务相关性以及组织结构、战略和员工人力资本等内容,不过他也认为吸收能力的实质就是了解、理解和应用知识的过程能力。吸收能力的外延很广,而且一直在拓展,但从经典文献可以看出,吸收能力的核心内涵结构始终没有改变,仍然是对外部知识的识别、评价、消化、转化以及整合和应用的能力。
最后,吸收能力的过程/能力特征。最初,吸收能力构念就被认为“更多是一种能力,体现在过程当中”。Cohen和Levinthal(1990)认为,吸收能力包括识别评价、理解消化和应用能力,是一种累积性渐进过程。Lane和Lubatkin(1998)认为吸收能力包括识别评价、理解和应用能力。van den Bosch等(1999)认为,吸收能力最重要的体现是整合能力,整合能力是一种动态过程和能力,是企业对其从外部获得的知识与内部知识、人力和物质资源进行社会化、协作化和系统化的能力。Zahra和George(2002)认为吸收能力分为获取、消化、转化和利用知识的能力,这也是过程观的体现。Daghfous(2004)在研究总结的基础上指出吸收能力由获得外部知识的能力、改造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能力构成,因而也体现了吸收能力的过程观点。Lane等(2006)对吸收能力的研究最充分地展示了吸收能力的过程特征,他们建立了吸收能力过程、前因、后果分析模型,认为吸收能力包括探索性学习、转化性学习与利用性学习。探索性学习旨在识别、理解和获取外部新知识,而组织成员的知识基础和认知方式决定知识识别、理解和获取的程度。转化性学习旨在消化从外部获取的知识,个体层面上的转化是个体将新知识与已有知识相联系的过程,而组织层面的转化则是通过知识管理来实现知识在组织各部门之间的共享和转移,最理想的状态就是组织通过消化新知识来形成理解知识的集体图式(collective schema)。利用性学习旨在应用经过消化和转化的知识。Cassiman和Veugelers(2006)将吸收能力分为获取能力、消化和转化能力以及应用能力,这同样也是过程的体现。Lichtenthaler(2009)采用了Lane等(2006)的过程分析方法界定了吸收能力。Lewin等(2011)在吸收能力前因变量的研究中认为,吸收能力包括识别和获取、消化和吸收、应用和商业化的能力。可见,有关吸收能力的主要文献都是从过程/能力视角来理解吸收能力的。从过程/能力视角来理解吸收能力,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吸收能力构念的内涵,同时也有助于揭示外部知识转化为内部能力的机理。
应当说,目前对吸收能力构念的表述及其维度划分并不十分准确和清晰,有含混、抽象、模糊甚至随意化和泛化的倾向。大多数学者即使能从过程视角把吸收能力理解为组织处理外部知识的过程,包括识别、获取、消化、转化、整合和应用等不同环节,但具体的定义界定和维度划分仍然差异很大。值得注意的是,直译对这种倾向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而且很多文献采用了Lane等(2006)和Lichtenthaler(2009)界定的吸收能力定义和划分的结构维度,但把“explorative learning”、“transformative learning”、“exploitative learning”⑤直译为“探索性学习”、“转化性学习”和“利用性学习”。然而,这些汉语词语虽然在语义上与原语意思相近,但实际上并不完全对等。如汉语的“探索”有探访、探寻、多方寻找之意,“转化”有转换、改变之意,而“利用”则有发挥效能、采取手段为己服务或谋利之意⑥。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差异较大,译成汉语以后词义本身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变化,很难实现与原目标词语的完全对等(Hambleton和 Patsula,1998;Harkness,2003)。因而,直译成汉语后的“探索性学习”、“转化性学习”、“利用性学习”不能完全涵盖其原语的“recognize”(识别)、“evaluate”(评价)、“understand”(理解)、“assimilate”(消化)、“transform”(转化)、“integrate”(整合)和“apply”(应用)之意。更重要的是,这几个汉语词语在中国语言文化背景下具有更多的引申意思,如“探索性”在汉语中还有“开拓”、“进取”、“探寻”的外延含义;“利用性”还有“操纵性使用”、“功利性使用”、“利己性使用”的引申含义⑦。此外,译成汉语以后也就失去了“能力”的含义,从而导致国内读者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些构念的原意,最终影响了吸收能力构念在汉语语境下的研究效度。
在结构维度划分上,Zahra和George(2002)的“两部分四维度”法得到了较多的支持,“潜在吸收能力”(获取、消化)和“现实吸收能力”(转化、利用)为一些实证研究所验证。然而,把消化和转化能力分别归属于潜在和现实吸收能力,这种划分却与知识转化的认知过程存在矛盾。因为从认知学的角度看,知识转化是指把新知识整合进既有认知体系,是消化知识的认识过程的一部分。而且,人们一旦发现新知识,自然就会根据自己业已掌握的知识来理解新知识,理解新知识和把新知识整合进既有知识的过程可能是同时发生的。有关组织要素与吸收能力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显示,知识转化与知识利用、知识消化的相关度是一样的(Jansen等,2005)。Carmen Haro-Domīnguez等(2007)的实证研究以Zahra和George的四个维度为基础对消化与转化进行了合并。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从外部获取知识,首先要求组织对知识进行识别和评价,在确定其价值符合程度以后再进行消化和转化,消化和转化并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泾渭分明,而是消化中有转化,转化中也有消化,两者是非间断连续进行的,对已经获取的外部知识的消化和转化通常包含在组织知识扩散的过程中。最后,组织在既定创新目标的引导下,对已消化和转化的知识进行重新整合,用于实现商业化产出。因而,在详细和透彻理解英文文献的基础上,从过程视角,笔者总体上认同Lane等(2006)和Lichtenthaler(2009)对吸收能力构念界定的定义和划分的结构维度,并且认为这几位学者从过程视角把吸收能力理解为组织学习能力的做法是科学的,但不主张采用直译的方法把相关英语术语翻译成汉语,而应该取其意而转其形,既保留英语构念的核心内涵,又采用便于国人理解的相对应的汉语术语。因此,笔者主张对“explorative learning”、“transformative learning”和“exploitative learning”进行意译,从而保留它们分别含有的“识别和评价能力”、“消化和转化能力”和“整合和利用能力”的意思。这样,既能反映英语吸收能力构念的核心内涵,又可避免直译造成的抽象性和模糊性,以便国内读者更好地理解吸收能力及其相关构念的内涵和结构维度,从而提高这些构念及其相关研究的效度。
由此,本文基于吸收能力的过程观,参照Cohen和 Levinthal(1990)、Daghfous(2004)、Lane等(2006)以及Lichtenthaler(2009)等所下的吸收能力定义和划分的结构维度,从动态过程和能力的视角将吸收能力的定义进一步拓展完善为“企业识别和评价、消化和转化外部新知识并最终把新知识整合应用于商业化产出的动态过程能力”。吸收能力的结构维度是识别评价能力、消化和转化能力以及整合应用能力。识别评价能力是指企业识别和判断外部知识的能力;消化和转化能力是指企业理解和解读外部知识并将其转化融入自己已有知识系统的能力;而整合应用能力则是整合利用经过消化、转化的知识创造新知识并用新知识实现商业化产出的能力。
六、结论与展望
吸收能力作为理论构念从产生至今已有20多年,其本身的丰富内涵和较强的解释力使其同与之交叉的资源基础、动态能力、组织学习、知识管理等理论一起得到了迅速发展,同时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随着吸收能力理论研究的不断升温,国内有些学者陷入了以上种种理解误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国内学者没能正确理解吸收能力的经典英文文献和核心内涵,没有严格根据吸收能力的核心内涵以及经典文献提出的吸收能力定义与相关前提假设开展相关研究。另外,翻译方面的问题也是导致错误理解吸收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进而引发了不少随意拓展和泛化吸收能力构念的问题。
吸收能力构念是吸收能力理论的核心和基础,对这一构念进行解构和再建构、提高它的完备性和科学性,自然有利于提升构念的效度和相关研究的积累。本文首先在系统梳理和分析国外经典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吸收能力在构念内涵、结构、过程/能力等方面的内容要求,对吸收能力构念的理解误区进行了深入解读,分析了误区的成因和影响。与此同时,对吸收能力结构维度英译汉的准确性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当前这一构念结构维度的汉译名与原文名的不对等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笔者对英译汉问题的看法和建议,在翻译吸收能力三个主要结构维度“explorative learning”、“transformative learning”、“exploitative learning”时注意保留三者英文分别含有的“识别评价能力”、“消化和转化能力”和“整合应用能力”意思,从而使这三个结构维度的汉语表达更加接近英文原意,同时体现吸收能力的动态能力特征。最后,本文对吸收能力的定义进行了拓展和完善,以便更加清晰地体现吸收能力的内涵确定性、结构完整性和过程/能力特征的鲜明性。
后续吸收能力研究,首先应该加大研究吸收能力动态形成过程的力度,研究吸收能力的识别评价、消化转化和整合应用的具体过程以及不同结构维度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关系。其次,开发能够反映吸收能力过程特征的操作化测量指标,不但采用知识基础和存量这样的固定值指标,而且还要采用过程和能力指标,如把组织主导逻辑、问题解决方式、知识共享惯例、激励机制等作为吸收能力的操作化测量指标,这样的复合指标无疑要比研发强度这样的单一指标更有解释力(Szulanski,1996;Lane和Lubatkin,1998;Lane等,2001;Meeus等,2001;Lane等,2006)。第三,考察企业员工个体认知对企业吸收能力的影响,尤其要研究员工个体如何审视外部环境、识别和评价外部新知识、消化和转化新知识以及整合利用新知识等问题,以揭示企业吸收能力与员工个体认知之间的关系。第四,加大吸收能力前因研究的力度,着重研究知识类型以及组织惯例、流程、运营和制度设计等对组织吸收能力的影响和作用机理,以便清晰揭示吸收能力的形成条件,以及吸收能力作为中间变量促进组织创新或提高组织绩效的过程和作用机理。最后,扩大吸收能力研究的对象,注重对中小企业、新创企业和研发投入较少的非高科技企业的研究(Lichtenthaler,2009),以扩大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并且把吸收能力研究拓展到创业阶段。
总之,后续吸收能力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对吸收能力内涵的准确和深入理解,重视对经典文献的正确解读和引用,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开展吸收能力的过程/能力动态研究,从而不断拓展、建立、检验和完善吸收能力理论和研究框架。
注释:
①这里的“组织自身的吸收能力”与吸收能力构念存在同义反复的问题。
②这里的“消化吸收”与吸收能力构念本身存在同义反复的问题。
③详见陶峰《知识溢出、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57、58页。
④这里的同义反复是指用意思相近的词语或词组来描述、定义概念或构念;象征性引用是指非实质或非核心地引用概念或构念。
⑤参见Lane等(2006)的英文文献。
⑥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主编的《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800、1709、1264页。
⑦参见《当代汉语词典》(国际华语版),李行键主编,2008年;《现代汉语规范辞典》(第2版),2010年。
[1]Amit R and Schoemaker P J H.Strategic assets and organizational rent[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3,14(1):33-46.
[2]Argyris C and Schon D.Organizational learning:A theory of action perspective[M].Reading,MA:Addison Wesley,1978:89-121.
[3]Barney J.Strategic factor markets:Expectations,luck,and business strategy[J].Management Science,1986,32(10):1231-1241.
[4]Cassiman B and Veugelers R.In search of complementarity in the innovation strategy:Internal R&D and external knowledge acquisition[J].Management Science,2006,52(1):68-82.
[5]Chan D.Functional relations among constructs in the same content domain at different levels of analysis:A typology of composition models[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98,83(2):234-246.
[6]Cohen W M and Levinthal D A.Innovation and learning:The two faces of R&D[J].Economic Journal,1989,99(3):569-596.
[7]Cohen W M and Levinthal D A.Absorptive capacity: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0,35(1):128-152.
[8]Cohen W M and Levinthal D A.Fortune favors the prepared firm[J].Management Science,1994,40(2):227-251.
[9]Cronbach L J and Meehl P.Construct validity in psychological tests[J].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55,52(4):281-302.
[10]Daghfous A.Absorptive capacit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knowledge-intensive best practices[J].SAM Advanced Management Journal,2004,69(2):21-27.
[11]Dyer J H and Singh H.The relational view:Cooperative strategy and source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8,23(4):660-679.
[12]Eisenhardt K M and Martin J A.Dynamic capabilities:What are they?[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0,21(S.I.)(10/11):1105-1121.
[13]Fiol C M and Lyles M A.Organizational learning[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5,4(4):803-813.
[14]Hambleton R K and Patsula L.Adapting tests for use in multiple languages and culture[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1998,45(1/3):153-171.
[15]Jansen J P,et al.Managing potential and realized absorptive capacity:How do organizational antecedents matter?[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5,48(6):999-1015.
[16]Kim L.Crisis constru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Capability building in catching-up at Hyundai Motor[J].Organization Science,1998,9(4):506-521.
[17]Klein K J,et al.Level issues in theory development,data collection,and analysi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4,19(2):195-229.
[18]Kogut B and Zander U.Knowledge of the firm,combinative capabilities,and the replication of technology[J].Organization Science,1992,3(3):383-397.
[19]Lane P J and Lubatkin M.Relative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interorganizational learning[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8,19(5):461-477.
[20]Lane P J,et al.Absorptive capacity,learning and performance in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1,22(12):1139-1161.
[21]Lane P,et al.The reification of absorptive capacity:A critical review and rejuvenation of the construct[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6,31(4):833-863.
[22]Lewin A Y,et al..Microfoundation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absorptive capacity routines[J].Organization science,2011,22(1):84-85.
[23]Lichtenthaler U.Absorptive capacity,environmental turbulence,and the complementarity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process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9,52(4):822-846.
[24]Ma del Carmen Haro-Domīnguez,et al.The impact of absorptive capacity on technological acquisitions engineering consulting companies[J].Technovation,2007,27(8):417-425.
[25]Meeus M T H,et al.Patterns of interactive learning in a high-tech region[J].Organization Studies,2001,22(1):145-172.
[26]Mowery D C,et al.Strategic alliances and interfirm knowledge transfer[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6,17(Win.S.I.):77-91.
[27]Nonaka I.A dynamic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J].Organization Science,1994,5(1):14-37.
[28]Osigweh C A B.Concept fallibility in organizational scienc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9,14(4):579-594.
[29]Pdehazur E J and Schmelkin L P.Measurement,design,and analysis:An integrated approach[M].Hillsdale,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91:32.
[30]Penrose E T.The theory of growth of the firm[M].New York,NY:Wiley,1959:21.
[31]Peteraf M.The cornerstone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A resource-based view[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3,14(3):179-191.
[32]Schulze W S.The two schools of thought in resource-based theory:Defini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J].Advance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1994,10(1):127-152.
[33]Szulanski G.Exploring internal stickiness:Impediments to the transfer of best practice within the firm[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6,17(1):27-43.
[34]Teece D,et al.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7,18(7):509-533.
[35]Tsai,W P.Knowledge transfer in intraorganizational networks:Effects of network position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on business unit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1,44(5):996-1004.
[36]Van den Bosch F A J,et al.Coevolution of firm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knowledge environment:Organizational forms and combinative capabilities[J].Organization Science,1999,10(5):551-568.
[37]Whetten D A.What constitutes a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9,14(4):490-495.
[38]Zahra S A and George G.Absorptive capacity:A review,reconceptualization,and extens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2,27(2):185-203.
[39]陈晓萍等主编.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7,64,231.
[40]王国顺,李清.基于吸收能力的跨国公司知识转移过程研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1):762-766.
[41]王睢.吸收能力研究现状与重新定位[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7,(7):1-8.
[42]张洁等.吸收能力形成的前因变量及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分析——吸收能力作为中介变量的实证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2,(5):2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