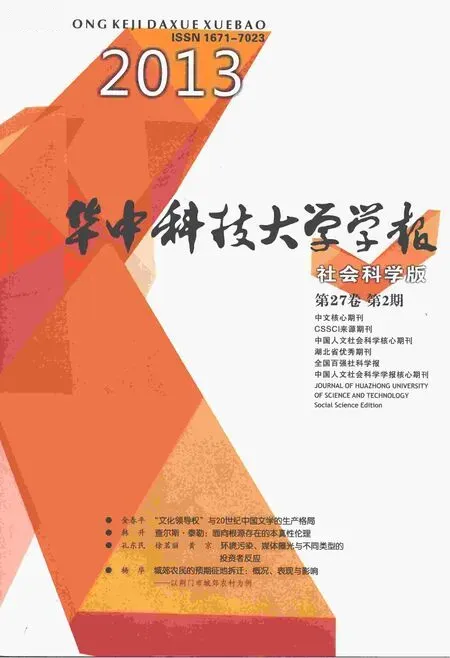财政分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兼论调节中国收入差距的对策选择
2013-03-06马万里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马万里,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一、引言
当前,中国经济正受到内外双重压力的影响。从外部环境看,对外贸易受到美国与欧盟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对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了外部的空间压力;从内部环境看,出口、投资和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处于非均衡状态,消费长期不足,经济结构失衡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了内部的结构压力。因消费受到居民部门收入水平的制约,收入差距过大已经对中国经济形成了连锁反应,所以,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仅具有公平视角的社会伦理意义,而且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市场管效率,政府管公平,因此,提及政府公平(或分配)职能,通常只注重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再分配的作用,通过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抽肥补瘦”是政府再分配职能的主要手段;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支出、提高人力资本的规模与质量进而提升个人获得收入的能力从长期来看也会影响初次分配格局①。而很少有文献关注政府对初次分配的影响,对财政分权影响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文献就更不多见。由于现实中的政府是多级次的,特别是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中国财政分权实践时会得到如下的基本事实:地方政府支出占全国公共支出的比重由1994年的69.7%提高到2011年的84.9%②,17年间上升了 15.9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94%,地方政府几乎承担了除国防和外交中央专属开支以外的全部公共支出。基于上述事实,我们有理由相信,地方政府对收入分配具有重要影响,而且本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影响体现在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两个层面。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采用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财政分权为制度背景,构建政治、经济与收入分配三维综合分析框架,分析了财政分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论证了财政分权框架下政治激励与财政激励对收入分配的独立与综合影响,并基于中国的实证检验提出了有关的政策建议。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既弥补了当前关于财政分权与收入差距研究的理论的不足,又提出了中国收入差距更深层次的成因和解决问题的新线索和新思路,因此本文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文献述评
解决收入差距问题关键在于找到引致收入差距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关于收入差距的成因,学者们曾做过大量分析,并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例如,郑功成(2010)认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偏大与社会保障不健全直接相关,所以收入分配改革必须重视并发挥社会保障的作用[1]。第二种观点认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与产权制度缺失有关。例如,安体富等(2012)认为,产权制度的不完善是引起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平和贫富差距的重要根源,因此,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分配制度与矿产资源产权制度能从制度上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2]。第三种观点认为,要素错配是城乡收入差距的诱因,如赖文燕(2012)认为,在我国城乡要素市场人为分割情况下,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受到限制,要素错配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3]。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文献使我们对收入差距的成因有了充分的认识,然而,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完善产权制度和促进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城乡间合理配置似乎还只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尚未触及问题的核心。诚如Coase(1974)所言,实证研究都希望建立可以指导我们对各种活动进行管理与筹资的一般规则,然而这些规则必须从关于不同制度框架下的活动是如何被实施的研究中推演出来才会有用[4]357-376。事实上,除上述三种观点外,也有文献认为,目前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体制是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制度根源。例如,贾康(2010)、李稻葵(2011)认为,现行财政体制是引致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源[5,6],这为解决中国收入差距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但遗憾的是,两位作者并没有进一步分析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使财政分权影响了收入分配。关于财政分权与收入分配的关系,Jütting等(2004)发现,分权改革有助于提高公众参与程度、增进公共部门责任感、改善政府治理水平,而这些都是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7]。而Bardhan和 Mookherjee(2005)认为,分权的体制提高了地方政府对本地居民整体福利的责任感,但地方精英可以通过政治影响力、“政治献金”的方式来换取公共服务的优先权,因此,公共支出可能会更偏向富人,并 不 利 于 贫 困 减 少[8]675-704。Kappeler 和Valila(2008)进一步指出,财政分权会降低具有再分配性质的公共投资占总公共投资的比重[9]562-570。Hao 和 Wei(2010)的研究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导致了收入差距扩大[10]181-206,陈工和洪礼阳(2012)的研究则认为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差异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11]。
值得肯定的是,已有研究为解决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为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现实提供了更宽的思路与更开阔的视野,然而不足之处在于:(1)没有具体详尽地分析财政分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缺乏必要的理论机制分析。虽然陈工等(2012)讨论了财政分权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性,但相比于城乡收入差距而言,要素分配对于收入差距具有更根本的影响。(2)部分国外文献从政治角度分析了财政分权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但由于中西方政治传统的差异,我们需要具体考察中国的情况。(3)尽管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水平明显相关,然而,经济增长或人均GDP不可能是决定收入分配的惟一手段,政治对收入分配也具有重要影响,换言之,应从新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①。
三、财政分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理:一个分析框架
(一)财政分权、自利动机与地方政府行为异化
与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仁慈型政府”假定不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更加关注地方官员在维护市场、促进竞争与推动经济增长中的激励和行为,因此,与最初就是和地方政府良好作用联系在一起的传统的财政分权观点不同,新一代财政分权理论更注重对地方官员激励的研究。诚如Bird(1993)和Weingast(2006)所言,尽管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决策方式有点类似于市场化,然而地方政府并不会天然地对辖区选民的需求做出反应,而是有自身的利益考虑。只有当政府间的财政安排提供正确激励时,“靠近民众”的地方政府才能够更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12]207-227[13]。因为,财政分权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意味着很多。如果把地方政府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并有其自身的追求目标而不仅仅是中央政府的政策执行工具的话,那么,财政分权就意味着地方政府获得了追求自身利益和目标的手段,财政分权的程度也就意味着地方政府对这些手段可利用的限度和目标的实现程度。这里的手段表现为分权框架下地方政府支出安排的自主权与财政收入的剩余控制权。所以,具有自利倾向的地方政府就会利用财政分权所赋予的独立收支权限谋取私利,从而偏离公共需求,导致行为异化。
(二)“用手投票”与“用脚投票”机制的缺失与地方行为异化的加剧
与西方财政分权建立在联邦制基础上不同,中国的财政分权始于一个集权化的政治经济空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建立在集权制下的政府委任制基础上,缺少“用手投票”的公共选择机制。这样一种财政分权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政府对辖区民众需求的重视程度。与此同时,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中国无法出现居民与政府双向选择而形成Tiebout(1956)意义上的俱乐部式的最佳社区[14]416-424,因此,“用脚投票”机制的缺失使中国式财政分权并没有经典分权理论下的地方政府间竞争所能带来满足民众需要的更多更好的公共品。所以,地方政府在缺少双重约束的情况下,会加剧行为异化,以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利益追求。
(三)地方政府行为异化与收入分配
无论是从支出一方还是从收入一方衡量,财政分权本身无所谓好坏[15],关键要取决于财政分权实施主体的动机。因此,就财政分权与收入分配而言,本文的分析起点就在于:中国的地方政府面临着什么样的激励机制?它会有哪些目标追求?文本的落脚点就在于:地方政府在既定激励下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取向?这些行为对收入分配产生了哪些影响?关于中国地方政府面临的激励问题,周黎安(2007)提出了“政治晋升锦标赛”的概念[16],即在行政和人事集权的条件下,上级及至中央政府通过经济增长考核下级官员并决定官员的政治晋升与否。在中央政府的GDP考核下,地方政府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招商引资等手段,维持着较高的地区经济增长,并在“标尺竞争”[17]的放大下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然而,并不仅仅是政治激励可以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财政激励亦十分重要。傅勇(2008)的研究揭示了,虽然分税制改革使财权向中央政府集中,但地方政府仍然获得了一定的收入筹集权力,且中央以转移支付的形式保证了地方政府对分税制改革的支持与对经济增长收入的分享,中国分权体制下的财政激励继续激励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18]。那么,地方政府行为异化是如何影响收入分配的呢?
图1所示是财政分权框架下地方政府行为取向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导向以及资本稀缺的农业型经济的约束下①,在“GDP增长考核”下,为促进经济增长并取得财政收入,地方官员就可以用财政分权所赋予的支出和收入自主权来影响收入分配。首先,政治晋升机会的有限性与地方官员任期的制约会促使地方政府采取以扩大投资为手段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②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取得更大的政治晋升资本、更多的财政收入,经济增长的结果是相对稀缺的资本获得了较高的边际报酬,资本及企业收入增加,而恶性税收竞争的存在会进一步抬高资本边际报酬,同时政府获得了更多的税收,所以,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初次分配差距产生了;其次,为吸引稀缺的外来资本,地方政府会增加一些影响企业选址的财政支出(如基础设施建设),这导致地方政府在增进生产(production-enhancing)的公共品上花费更多,最终会系统性扭曲财政支出结构。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偏向会导致对社会保障和对个人的转移性支出减少,财政分权降低了具有再分配性质的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初次分配形成的收入差距经过再分配环节之后依然较大。特别是对于贫困地区而言,异化的分权激励会使地方政府为吸引外来资本不得不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改善投资环境,从而使贫困地区陷入“锁定”状态,产生收入差距中的“马太效应”。

图1 财政分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
四、财政分权、政治激励与收入分配
本文将地方政府及领导人视作理性人,既追求政治权力也追求经济利益,其行为表现之一是谋求政治晋升或连任。图2所示是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政治激励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所谓政治激励,是指下级政府领导人的晋升或连任取决于上级政府还是辖区选民。在中国的政治集权下,地方官员的政治激励来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也就间接决定于中央政府的政治偏好。在中央政府“GDP增长考核”下,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地区经济增长,由于资本稀缺,通过增加经济建设支出改善投资环境以吸引资本流入便成为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除增加经济建设支出外,恶性税收竞争也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主要手段。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在所难免。

图2 财政分权下政治激励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
另外,由于缺少必要的监督与制约,行政管理费逐渐膨胀,在平衡预算的制约下,因各项支出是此消彼长的互替关系,地方政府用于社会保障和人力资本等社会性支出下降,从而引致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剧①。如表1所示,2007年地方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支出规模为7039.18亿元,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8.4%,而2011年对应数字分别为26260.88亿元和28.3%,四年间规模增加了273.1%,年均增加68.3%,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这种增长虽然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有一定关系,但地方政府在政治激励下对经济增长的渴求无疑成为经济建设支出增长的主要推力。

表1 2007-2011年地方财政支出按功能性质分类②
与此同时,2007年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为12472.39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32.5%,而2011年对应的数字为22963.71亿元和24.8%,四年间规模增加了84.1%,年均增加约21%,行政管理支出规模过大、增长速度过快,所占比重过高③。随着民生财政投入的逐年加大,地方财政社会文教费支出规模逐年增加,由2007年的16378.45亿元提高到2011年的38620.7亿元,增加了近2.5倍,社会文教费支出在地方财政支出总额中所占比重基本上保持在42%左右,社会文教费支出的逐年增加对于提高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进而提高个人收入能力、改变收入差距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问题依然存在,社会性支出的比重应进一步提升。
以降低税率为代表的恶性税收竞争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不仅导致了初次分配中收入向资本要素倾斜而使劳动报酬下降,由于总体税率的下降以及经济建设费和行政管理费的挤压,地方政府用于人力资本和社会保障支出的财力会更加趋向紧张。以社会保障支出为例,2011年地方财政用于对个人的转移性支出占地方全部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的比重仅为21.3%,其中,对城市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与救济支出分别为733.55亿元和850.71亿元,占地方全部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比重分别为6.9%和8.0%(表2),比重过小,无法发挥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

表2 2011年地方财政对个人转移性支出情况
可见,扭曲的政治激励会引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社会保障支出与人力资本支出不足,进而对个人收入能力和未来要素分配产生影响;经济建设支出的增加和税收竞争的加剧会使收入分配进一步向资本倾斜,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下降。上述两个方面的影响最终会扩大收入差距。
五、财政分权、财政激励与收入分配
本文的财政激励是指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包括税收激励与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激励两个部分。图3所示是财政分权下财政激励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作为理性人的地方政府及领导人其行为表现之二是充裕本地财政,实现财政收入最大化。由于经济增长直接决定财政收入水平的高低,换言之,GDP最大化就代表财政收入最大化,所以,按照“成本——收益”对称原则,地方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决定了地方政府工作重心及财政支出的主要投向。我国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以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代表的生产性税收,2003-2011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与城市维护建设税①四项税收占地方税收收入比重的平均值是73%,最高是2004年的81%(图4)。

图3 财政分权下财政激励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

图4 2003-2011年地方税收及地方四税比重②
地方财政对生产性税收的高度依赖势必导致其工作重心偏向经济增长,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税收竞争形式招商引资,以实现GDP最大化,既可以增加政治晋升资本,又能增加地区财政收入,可谓“名利双收”;同时,地方政府也会将大部分支出用于服务企业,财政支出结构偏向问题会进一步加剧。
此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是地方财政另一个重要的财政激励,这种激励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结构来加以说明(表3)。自2008年以来,地方政府获得的“税收返还”由4282.16亿元增加到5188.55亿元,增加了21.2%。由于“税收返还”直接与增值税和消费税增收挂钩,因此,地方政府要想获得更多的“税收返还”就必须下大力气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换言之,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并获得按财政体制规定的收入之外,还会从中央政府获得一份额外的收入作为增长奖励。专项转移支付由2008年的9962.39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7386.26亿元,四年间增加了74.5%,年均增长18.6%,增长的规模和速度非常之快。专项转移支付的使用由于必须以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为基础,因此地方政府纷纷热衷于“跑部钱进”争取专项资金,一旦项目和资金在本地落户,就意味着地方财政的“财源滚滚”和经济总量的增加。另外,专项补助必须要求地方政府按比例配套资金,地方政府获得的专项转移支付越多,财政资金配套压力就会越大。

表3 2008-2012年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与结构
尽管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重都是最大的,但是由于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按照“基数法”测算的①,而均等化转移支付规模和比重过低,部分项目已异化为专项补助并成为部门利益的代表,各级政府无法统筹调度各项财力,地方财政再分配职能受到财力制约。
综上所述,地方政府面临的税收激励和转移支付激励强化并放大了地方政府在政治激励下对经济增长的偏爱②,使地方政府更加热衷
如表4所示,自2000年以来,地方政府经济建设支出规模由2649.8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26260.9亿元,11年间增加了23611.1亿元,年均增长比例为8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GDP总量也快速上升,分别由 2000年的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发展成果更多地被资本要素和政府分享,初次分配中收入向资本(企业)和政府倾斜,劳动要素获得了较少的报酬。同时,经济建设支出与行政管理支出的增加和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合理使地方政府调节收入差距的能力受到财力制约,对个人转移性支出的不足会使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初次分配差距经再分配环节之后依然较大。
六、财政分权下政治激励与财政激励对收入差距的综合影响
本文第四、五部分从政治激励与财政激励角度分别探讨了财政分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事实上二者是内在统一的,会同时强化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渴求并推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和恶性税收竞争。32917.7亿元和99214.6亿元增加到 2011 年的311485.1亿元和 472881.6 亿元;与此同时,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地方财政五项收入规模也伴随着投资规模和GDP总量的增加而迅速增长,由2000年的6373.4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33889.8亿元,地方政府经济建设支出、地方财政五项收入均与投资总量和GDP增长呈现同向增加的趋势。

表4 地方财政与国民经济相关情况汇总 单位:亿元
再来考察资本收入与劳动者报酬情况。自2000年以来,资本报酬和非金融部门劳动者报酬由14103.7亿元和25061.7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63322.0亿元和73831.9亿元,两者之比由2000年的56.3%变为2011年的85.8%,说明资本报酬规模增长快于劳动者报酬规模的增长①。之所以选择非金融部门劳动者报酬作为比较,主要出于以下原因:首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有很大比例的资金来源于金融部门的贷款,此外,近年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如雨后春笋一般迅速扩张,经济发展对资金的渴求会使金融部门的收入高于其他部门,使金融行业工资高于其他行业工资水平②;其次,考虑到政府部门收入除基本工资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没有统计的收入项目,所以劳动报酬项不足以反映政府部门劳动者报酬的真实水平,不具有可比性。因此,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计算了表4中各项的实际增长率,以便于更好的比较。

图5 地方政府财政与国民经济相关项目增长率
如图5所示,地方政府经济建设支出增长率波动较大,2000年至2007年增长率逐渐放缓,但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增长率由2007年的4.5%提高到2008年的49.2%,之后增长率再次放缓,总体上表现为上升的趋势;地方政府五项收入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GDP总量增长率基本上同向变动,且波动不大;非金融部门劳动者报酬增长率由2001年的7.8%上升到最高点2007年的19%,之后开始回落,增长率下降为2009年的10%,劳动者报酬增长率表现平缓且呈现下降趋势;而资本报酬增长率在经历2001年的负增长之后迅速提高到 2004年的 14.7%,最高为 2006年的46.7%,尽管之后有所下降,但一直高于劳动者报酬增长率,2008年资本报酬增长率为29.4%,仍然比劳动者报酬增长率高出12个百分点。
七、结论
本文基本结论是,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政治激励与财政激励使地方政府将政治晋升、获取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捆绑在一起,政治激励与财政激励同时强化并放大了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渴求,为增长而竞争使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在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最终增加政治晋升的资本。地方政府上述行为的结果是初次分配中收入分配向资本要素和企业以及政府倾斜,劳动报酬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下降,再分配环节后的收入差距依然较大。这是导致中国收入差距的体制性和根本性因素,与贾康(2010)和李稻葵(2011)“现行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安排是导致我国收入差距的制度根源”的观点一致。因此,笔者认为,调节中国的收入差距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完善地方官员的绩效考核体系。建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政治激励约束机制,强化民众的参与权、表决权,从制度上保证政府官员对民众负责,加强社会公众的监督制约能力,确保政府支出的民主化和公共化。其次,重构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应调整和完善目前的财政体制,与合理确定政府间转移支付规模相结合提高中央政府财政支出比重③,上述事关社会公平的事权,使中央政府责任“归位”,同时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和测算方法,建立自上而下科学、规范、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从长期来看,应该优化税制结构、完善地方税体系,避免地方政府对流转税等间接税收的过度依赖。最后,必须把财政分权作为一项完整的制度体系看待,在认清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动力机制和局限性的基础上,正确合理地设计改革方案,以创新的思维彻底地系统地改造现有的财政体制,对于调节日益扩大的中国收入差距而言是最根本性的举措。
未来的改革必须通过上述制度设计,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及官员能够权衡效率与公平,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加关注收入分配问题。正如阿瑟·奥肯所言,“我为市场欢呼,但我的欢呼不会多至两次”,我们应该“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20]116。
[1]郑功成:《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分配的基本制度保障》,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0年第6期。
[2]安体富等:《影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平的若干产权制度问题研究》,载《财贸经济》2012年第4期。
[3]赖文燕:《要素市场配置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载《当代财经》2012年第5期。
[4]Coase,R.H.“The Lighthouse in Economics”,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74,17(2).
[5]贾康:《财政体制改革与收入分配结构调整》,载《上海国资》2010年第12期。
[6]李稻葵:《财政税收体制需要调整》,载《英才》2011年第1期。
[7]Jütting,J.,etc.“Decentralization and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Exploring the Impact”,OECD Development Center Working Paper,No.236,2004.
[8]Bardhan,Pranab,Mookherjee,Dilip.“Decentralizing antipoverty program deliver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89(4).
[9]Kappeler,A.,Timo V¨alil¨a.“Fiscal Federalism and the Composition of Public Investment in Europe”,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8,24(3).
[10]Hao,R.,Wei,Z.“Fundamental Causes of Inlandcoastal Income Inequality in Post-reform China”,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2010,45(1).
[11]陈工等:《财政分权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载《财政研究》2012年第8期。
[12]Bird,Richard M..“Threading the Fiscal Labyrinth:Some Issues i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National Tax Journal,1993,46(2).
[13]Weingast,Barry R.Second Generation Fiscal Federalism:Implications for Decentralized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Working Paper,Hoover Institution,and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Stanford U-niversity,2006.
[14]Tiebout,C.M..“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6,64(5).
[15]Litvack,Jennie,Junaid Ahmad,and Richard Bird.Rethinking Decentr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World Bank Sector Studies Series,Washington,D.C.,World Bank,1998.
[16]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载《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17]张晏等:《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与中国省级政府公共支出溢出效应差异》,载《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
[18]傅勇:《财政分权改革提高了地方财政激励强度吗》,载《财贸经济》2008年第7期。
[19]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