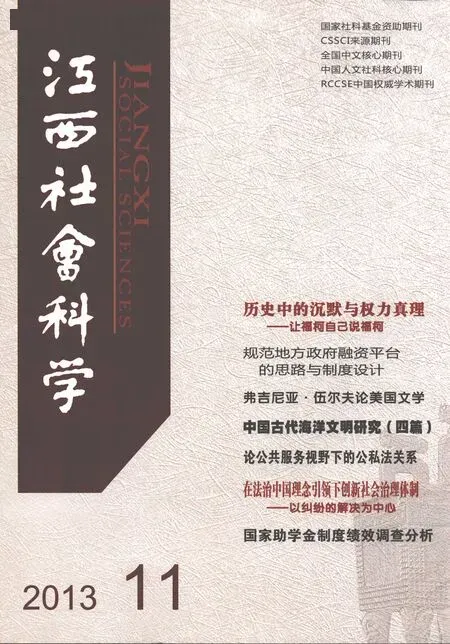“非虚构”写作:个体经验与公共经验的困窘
2013-02-19林秀琴
林秀琴
“非虚构”写作:个体经验与公共经验的困窘
林秀琴
“非虚构”写作是新世纪文学的一种叙事策略,“非虚构”文本对底层表现出特别的关注,现代化语境下的农村现实和工业浪潮下的打工者阶层的生活与情感是“非虚构”写作着重突显的经验场域。“非虚构”写作着力于寻求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的重叠,但并没有解决或消除从个体经验上升为公共经验的叙事机制内在的困窘,从而使其对底层经验的书写仍然流于象征意义上的整体性和表面的真实。
“非虚构”写作;底层;经验;场域;叙事机制
林秀琴,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文学博士。(福建福州 350001)
“非虚构”写作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事件,几部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的陆续出版,说明当代的“非虚构”写作正处于发酵与蓬勃的态势。同样,对非虚构写作的研究也刚刚开始,许多概念仍处于争议之中。譬如,就“非虚构”这一术语而言,它的有效性、合法性都有待厘清;此外,“非虚构”写作是否将成为新世纪文学的重要思潮,它在文学写作与理论建构上的空间在哪里,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学界加以探讨。本文旨在从“非虚构”写作的文本阅读与批评中,对新世纪文学提供一个问题式的观察与思考:“非虚构”写作是一场叙事革命,抑或是一种叙事策略?在关注现实、直面人生这一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延续与发展中,它能否提供一个独特的经验场域,能否树立一种独特的伦理视角?它能否还原中国现代性的复杂图景,它的叙事伦理会否遭遇叙事的内在困窘?这些问题关系到“非虚构”写作未来的发展空间,也将影响当代文学如何处理文学与现实这一关系的视野与能力。
一、“非虚构”写作:叙事策略与美学态度
“非虚构”显然是作为“虚构”的对立面出现的,从字面意义来理解,“非虚构”写作是指向“真实”的写作。但是,以索绪尔为代表的20世纪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对“真实”——作为绝对的客观的真实——的瓦解,使一切语言的呈现都具有了“虚构”的性质,所有的“真实”都是叙述的结果。这个意义上,“非虚构”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真实”,而只是基于事件、人物的“总体真实”这一愿景,增加作家对人物、事件的描述与理解的客观性与纪实性。
“非虚构”这个概念进入当代文学的视野,源于 《人民文学》杂志在2010年将 “非虚构”写作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事件予以推动和倡导。那么,何谓“非虚构”呢?《人民文学》在2010年第2期的《留言》中如是说明:
这一期我们新开了一个栏目,叫 “非虚构”,何为“非虚构”?……我们认为,它肯定不等于一般所说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我们也希望非作家普通人,拿起笔来,写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传记,还有诺曼·梅勒、杜鲁门·卡波特所写的那种非虚构小说,还有深入翔实、具有鲜明个人观点和情感的社会调查,大概都是“非虚构”。
《人民文学》的这个说法只是划出了 “非虚构”宽泛的外延范围,而非定义。从被视作“非虚构”写作的重要代表作品——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注:系《梁庄》的单行本)和《梁庄在中国》,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陈庆港的 《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 (2000—2010)》,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郑小琼的《女工记》、王小妮的 《上课记》、乔叶的 《拆楼记》等——来看,它们所获得的赞誉主要来自这些作品对“现实”的广度与深度的呈现。这种内涵特质显然契合《人民文学》同期刊出的“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的旨趣:
“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的宗旨是:以 “吾土吾民”的情怀,以各种非虚构的体裁和方式,深度表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表现中国人在此时代丰富多样的经验……“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特别注重作者的“行动”和“在场”,鼓励对特定现象事件的深入考察和体验。
以 “行动者”的姿态与实践,“深度表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表现中国人在此时代丰富多样的经验”,显然是“非虚构”写作计划的核心指向。的确,上述作品均是立足于当下,倾向于关注当下社会现实,尤其是聚焦于当下社会变革加剧的历史语境下,高速运转的现代化、工业化运动所引发的社会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变化,特别是底层民众从物质生活到精神世界的裂变,其间充溢着作家对社会与现实的省视与剖析,也不乏人文关怀的精神。
那么,“非虚构”写作是否标示了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乃至叙事伦理?这是许多卷入“非虚构”写作论争的学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它关系到“非虚构”写作作为一个概念或范畴的有效性、合法性。显而易见的是,“非虚构”写作不是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在叙事形态上,“非虚构”写作呈现的可能是包括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等在内的不同的叙事方式的综合;在叙事伦理上,对社会性、真实性的追求又使得它与上述文体之间具有共享的特质。对此,张文东用“中间性”和“边缘性”来描述:“我认为非虚构是一种创新的叙事策略或模式,这种写作在模糊了文学(小说)与历史、纪实之间界限的意义上,生成了一种具有‘中间性’的新的叙事方式。 ”[1]
对“真实”的追求是“非虚构”写作的重要动力,但事实上,这也成为“非虚构”写作被诟病的主要原因。“非虚构”写作很大程度上被当作一种具有文学性的深度新闻调查,技巧细节和审美张力上的薄弱使它在文学的领地中显得孤立。因此,与其将“非虚构”写作视为新世纪文学在文体、形式上的创新 (譬如文体上的综合性),不如将其看作一种刻意为之的叙述策略。换言之,《人民文学》对“非虚构”写作的倡导,重点在于强调了一种由“行动”、“在场”、“吾土吾民”等关键词串联起来的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的知识立场:“我们希望推动大家重新思考和建立自我与生活、与现实、与时代的恰当关系。”[2]这些表述直白地指向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试图重新粘连文学与生活的脐带,强调文学与现实的互动、文学对现实的介入,以及对“真实”的突显、对“当下”与时代性的强调,使之接续上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
“非虚构”写作的兴起显然与20世纪90年代晚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化环境和文学写作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各种呓语式的私人写作或者沉迷于玄幻、穿越的文学叙事,既无力承担与延续20世纪90年代以来先锋文学在叙事实验与探索上的功能,相反,在艺术形式的追求上更加显露出粗糙、粗鄙的趣味——这些创作固然不是当代文学的全部,然而在网络媒体的技术催化下,这些写作吸引了人们对文学的大部分关注。同时,这些写作也日益表现出与现实生活的疏离,即使它们的确表达了某种特殊的生活体验,譬如韩寒、郭敬明、卫慧、棉棉等提供的所谓城市精英、白领阶层流连于酒吧、咖啡馆的光鲜生活与幽暗暧昧的私密内心,抑或是诸如《甄蠶传》这种古代宫闱秘史叙事中刻意渲染的名利场下复杂残酷的人性。种种离奇曲折的情节铺排,包装着各种欲望的噱头,这种引诱几乎让大众欲罢不能。无可置疑的是,这些文本显然首先是作为“消费文化”的文本而存在的,对大众趣味的迎合与引导很大程度上基于对消费市场的研判。这样的写作既无力呈现和表达广阔的生活,更欠缺文学关怀现实与生活的能力。
另一方面,如果把视野扩展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语境的变化和发展,我们对文学所处的时代及其特征会有更清晰的认识。由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所启动的这场被命名为“现代化”的社会运动,经过三十年的积累,已经深刻地改写了中国社会的整体图景,经济体制的变革并非孤立的事件,城市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不仅缔造了诸如北上广等国际化的城市生活和城市体验,广大的农村也卷入了这场旋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和文化气候。这种结构性的社会变动有着丰富、复杂的层次,其间充斥着各种利益的对抗、资源的争夺、阶层的分化、经验的矛盾……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的 “裂变期”。这种裂变已从物质的层面深入到文化的层面,对既有的社会结构、经济面貌、文化生态带来了全面性的瓦解乃至颠覆。它所带来的当下时代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是那些以个体经验莺莺细语的私人化写作,或者以历史为消费对象的玄幻、穿越文学,所不可能呈现与描述的。如果文学写作沉迷与驻步于这些经验,而忽略社会生活中更宽广、更尖锐、更深刻的部分,其所带来的伤害将十分深远。
二、“非虚构”写作的经验场域
无论能否跨越文学与历史、现实与想象的鸿沟,“非虚构”写作始终是一种基于文学话语内部的叙事选择。“非虚构”写作同时指向了当代文学写作的两个向度:一是文学的经验场域;一是文学的叙事(写作)伦理。这两个向度包含着一系列问题:“非虚构”写作关注和表现何种现实?如何表现与叙写其对象?由谁来关注和表现?“非虚构”写作能否提供一个独特的经验场域,能否树立一种独特的伦理视角,这是决定“非虚构”写作未来走向的重要因素,也是考量新世纪文学现实主义写作的重要尺度。
《中国在梁庄》和 《十四家》提供了现代化语境下两种不同的农村景象。梁鸿笔下的故乡“梁庄”,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气候舒适,但是,“田园牧歌式”的想象和抒情已经无法搁置在这片土地上:破败的老屋、荒废的农田、污浊的水塘、沦为养猪场的小学、留守在村落的儿童和老人,这些破败的形象无法激活一个村庄的活力,村落已经从昔日的生机勃勃沦落为一个衰败的“废墟”。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对村庄外在的呈现,而是在人与事的叙述中直指村庄情感伦理的失落。这种失落很大程度上源于现代性社会语境下村庄结构的裂变:迫于生存的压力,大部分青壮年外出务工,村落的核心被掏空了,家庭分离、儿童失教,人伦之情被压抑。在现实的生存压力面前,亲人之间的天伦之乐显得奢侈和脆弱:
他们看到的是,他们的房屋越来越好,哪怕他们不得不夫妻、父子、母女常年分离;他们不再需要忍饥挨饿过日子。他们可以在春节时回到村里,坐在新房子里,招待亲朋好友,这仅有的几天,可以使他们忽略掉那一年的分离……[3](P33)
一幢幢比邻而起的小洋楼象征着村庄“富裕”的外壳,而“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生着锈”却直指村庄的 “空壳化”。作者将梁庄的际遇描述为“困在泥淖中的乡村”,一方面自然包含了乡村外在的凋敝,另一方面更指向了这种“空壳化”对乡村内在生活肌理的破坏。
与 “梁庄”相比,《十四家》呈现的农村更加沉重压抑,作者以克制的笔调,在诸多的生活细节描述与场景的想象性还原中,呈现了中国西部山区十四家农民在新世纪十年间的生活面貌。在破旧的窑洞、干瘪的粮袋、外出乞讨的佝偻背影中,我们触摸到生硬结实的贫困,生老病死,顽强挣扎。这种触目惊心的贫困,刺激与更新了我们对现时的农村社会的想象与认识,它所突显的 “前现代社会”的生活状态,与我们充斥着物质主义的城市生活经验以及日益“后现代化”的文化体验,构成了一种尖锐的对比。这种对比所带来的震撼使我们触摸到了中国现代性社会图景的复杂与分裂的部分。
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与郑小琼的《女工记》把目光移向了另一个底层群体:流动在各个城市、忙碌在工业流水线上的工人——他们来自中国大地广袤的村庄,来自梁鸿笔下破败凋敝的乡村,或者来自陈庆港笔下偏远穷困的山区。某种意义上,这些关注乡村农民的文本与关注城市打工者(农民工)的文本,构成了一种现实语境与意义生产的互文关系。这两部作品呈现了工业化浪潮下中国农民工的生活现实与内心情感,对这两部作品的讨论时常被放置于“打工文学”的场域。许多论者已经指出,两个作者均来自于他们所叙写的阶层。因此,这两部作品不仅更具有个体经验的色彩,身份的“草根性”无形中同时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同时,这些作品体现了“非虚构”写作所强调的“在场”,以及一种有意识的“行动者”对当下的记录与呈现的文学立场。
工衣、打卡、流水拉、扳手、出租屋……《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以词条的形式串联起打工者在单调、机械的工业流水线上的生活画面。这些词条就像是流水线上的零件,又像是机床上切割出来的零碎的片断——这种片断化、零碎化也是打工者生活经验的描述,不断变换的厂服无声记录了工人流逝的青春与生活的酸甜苦辣。这种断裂、碎片的个体经验指向了现代化工业时代的语境,忙碌运转的机器不断调动资本扩张的胃口,企业主的私人利益建立在各种廉价的加班津贴、有毒的工业材料、工伤保险的欠缺等等各种黑工厂的资本链上,打工阶层个体的独立与尊严被碾碎在工业浪潮的巨大机床上,乃至付出身体的代价:
珠三角早期的财富积累建立在这些数量惊人的工伤和职业病的基础上,利用年轻的生命的折旧、损害和死亡为代价,财富的基座下积下了一层层粗厚的血痂和伤疤。[4](P120)
这在郑小琼的 《女工记》中也有令人触动的表现。《女工记》中一首首以女工姓名为题的诗歌,实际上可以看作一个个奋斗、挣扎在南方工厂机器流水线上的女性肖像和命运图景。为了生计,她们远离家乡,抛下年幼的孩子,与丈夫分离,甚至出卖了身体的健康乃至生命。《兰爱群》一诗中:
咳嗽,恶心……她遇见肺部/泥沙俱下的气管,塞满毛织厂的毛绒/五金厂的铁锈,塑胶厂的胶质……它们纠结/在胸口,像沉闷的生活卡在血管/阻塞的肺部,生活的阴影/她遇见肺部,两颗枯黄的树木 /扎在她的肉体,衰老的呼吸。[5](P32)
兰爱群在广东当了十五年的女工,尘肺折磨着她病痛的身体,打工生涯换来两个小孩读完大学、老家盖起新楼,这让兰爱群“疲倦苍白的脸上泛出笑容”。这当然不是孤立的个案,际遇相近的,还有“在大朗毛织厂的缝盘机上”“织起了楼房,为儿子织起了媳妇”,最终死于癌症的伍春兰(《伍春兰》);为了多挣一百多元的工资放任自己的双手在各种有毒的化工洗涤液中浸泡的刘乐群;被机器吃掉了三只手指,最后却在厂方的冷漠推诿中独自哭泣的谢庆芳……一个个的女工,她们付出的辛劳、身体的病痛乃至生命都不过是工业时代资本机器上廉价的没有体温的符号。一茬茬的青年女工,将自己的青春与生命给了冷漠的机器,用惨淡的人生换取微薄的生存资本。她们的呼喊和哭泣,她们的坚忍和屈服,化作了《女工记》中一句句愤怒而无奈的诗歌。
贫困的乡村,或是在工厂里廉价售卖青春与健康的打工生活,这些沉痛的书写是当下社会现实经验的重要部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的进步是不争的事实,城市化现代化的巨大步伐不断刷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大国崛起”的宏伟蓝图激励着中国人的自信心。改革开放的南方,往往成为中国现代性宏伟叙事的蓝本,密集的工业流水线、形形色色的跨国公司、畅行全球的 “中国制造”、不断刷新的经济产值、崭新繁荣的城市、福布斯财富排行榜的席位……这些符号共同叙写了中国现代性宏大叙事的辉煌篇章。但是,“历史进步”的主旋律也可能掩盖一系列的复杂图景,资本的扩张与财富的积累已然显示了一系列的后果:资源的掠夺、自然环境的破坏、劳动剥削、贫富差距的扩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社会阶层的对立、文化传统的断裂,道德伦理的变质,等等。上述文本的意义,就在于他们“还原”了中国现代性想象图景中这些被忽略、被无视的部分。
三、个体经验与公共经验的重叠与疏离
“非虚构”写作所强调的“在场”、“亲历”,一方面既强调写作者在扮演“观察者”、“参与者”的过程中形成带有作者鲜明视角的个体经验性;另一方面,“非虚构”写作所强调的“现实”书写,要求文学直面当下现实,关注、理解与探讨现实社会的公共议题,因此,文学重又被赋予“社会公器”的身份,作家必须在个体经验与公共经验之间寻求稳妥的结合。这种寻求个体经验的公共性的书写,成为“非虚构”写作的显著的特点。
《中国在梁庄》发表在 《人民文学》时的篇名叫 《梁庄》,出版时方改为《中国在梁庄》,意在对梁庄作为一个个体、具象身后的总体与象征即 “乡土中国”进行彰显,梁庄被视作一个并非孤立的个体,而是中国农村普遍性的一种表征。该书的前言表达了“梁庄”与“中国”的隐喻关系以及作者对普遍性、总体性的追求:
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由此,透视当代社会变迁中乡村的情感心理、文化状况和物理形态,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中国乡村之间以什么样的关系存在?[3](P2)
《十四家》以“中国农民生存报告 (2000—2010)”作为副题,用意相似。分布于甘肃、云南、山西、贵州四省的十四户农民,以个案的形式显示了一个同质性的存在——中国内陆山区农村的贫困现实。作者陈庆港作为一个新闻摄影记者的身份不能不被提及,“新闻”强调的是事件的具体性和针对性,但在《十四家》中,作者不仅有意识地呈现十四个农村贫困家庭的整体性的社会影像,并使这些个案呈现出具有阶层属性的人文精神——对应于物质贫困所显示的坚忍顽强的个体精神:“他们在二十一世纪还过着这样的生活,却从不抱怨、不放弃,坚持通过自己的劳动艰难地默默地改变着自己的命运。无论他们那种生活状况,还是那种不屈的和命运抗争的精神,在我看来都很打动人。”[6]同样,郑小琼表现的是不同的女工个体并呈现出不同的个体性经验,但是,她们又分享着相近的生活背景、命运遭际和情感状态,作为女性和农民工身份的结合体,她们既承担了传统的女性的社会职责和文化功能,又背负着现代工业化这一社会公共事件的各种责任与后果:付出辛劳的血汗与生命,以家庭的破裂、分离与个人情感的压抑为代价,换取生存的物质资本。《女工记》是在无数个案的基础上,通过个体经验的相似性显示了女性农民工这个特殊的阶层作为社会“共同体”的特质。
这些“共同体”显然都是“底层”的一部分。对社会底层群体的关注是文学承载 “公共性”的重要方式和传统。文学对“底层”的彰显,表达了文学对社会与现实的重新关注与介入。这种独特的文学品质在“非虚构”写作中被充分地扩大了:“底层”成为非虚构写作介入现实的重要通道。这里面当然包括《人民文学》对“关注时代脉搏”或“重返大地”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呼吁;也包括梁鸿所呼吁的“走进现实与事实”,“走进日常生活,而不是观念的生活”的“一种谦卑的行动写作”的知识分子立场[7];还包括陈庆港所强调的人文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与反醒。他尖锐地指出,我们的社会日益崇尚物质主义,鼓吹成功人士的辉煌,然而,“对于几千万人的贫困的生活状态,我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屏蔽了这种现实”[8]。因此,对底层的关注更应成为当下社会人文价值关怀的重点:“我们这个社会除了成功者,还有更多更广大的弱者,他们的存在不该被忽略,甚至正是他们成就了那些成功者,他们应该被改变。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而对待农民的态度则考验一个民族的良心,我们的社会应该更公平地对待他的每一个成员。 ”[6]
这些文本在个体经验的表达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在寻求个体经验的公共性上却又表现出相同的旨趣,即都致力于将个体经验上升为公共经验。梁鸿、陈庆港所表现出来的对底层的外部观察,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和知识训练的经验是契合的。根据梁鸿的自述,《中国在梁庄》的“叙述者”几易其主,最终选择了让包括作者父亲、乡支书、老贵叔、县水利局长、菊秀等在内的各式乡村人物“代表”自述的方式[7],这一努力可以读解为对底层人物“声音”的“真实”呈现的追求。但是在文本中,我们不仅经常与作者本人的叙述、评论乃至文人式的抒情相遇,而且,作者的视角是串联与组织上述底层声音的最突出的线索,作者不时地引导我们将叙述者作为一个“他者”去观察。作者与叙述者的分离使其对底层经验的呈现表现出强烈的疏离感,与之相应的是作者明晰而又活跃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意识,后者成为《中国在梁庄》的情绪基调。相比之下,郑小琼和萧相风对打工生活的描述与呈现更多地带有叙述者自我的色彩,无论是在打工生活的索引式的全景描绘中所流露的调侃式的无奈,或是在女工群像的书写中喷薄而出的悲愤与悲切,这种发自内心的体悟带来的灵魂悸动呈现出独特的美学景观。由于这些书写本身就来自于“底层”,这种底层经验的特殊性创造了一种新的观看底层的角度与方式。由于作者、叙述者、叙述对象一定程度上的同一,这些“底层”的呈现更直接,也更抒情化。由于个体经验与公共经验的部分重叠,郑小琼和萧相风从个体经验中演绎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公共经验的行为。
但是,从“打工文学”作为一个文化现象与文学事件的历史生产机制中①,我们可以发现,出身于打工阶层的写作者呈现自我个体经验的“无意识”,进入公共视野之后就进入了一种由外在力量推动的文化 “发酵”——它变成了一种被有意识强化和突显的公共意识。与此相应的一种表现即是,在借由个体经验的书写获得的自我体认中,将这些个体经验上升到公共性领域进行探讨,逐渐成为打工文学的写作自觉。在《女工记》的《后记》中,郑小琼交代了《女工记》的形成过程,其中,对女工生活、情感和命运的有意识的追踪、记录与访谈,促成了这部传记式的女工群像的诞生。在这里,郑小琼从打工阶层中分离出来,竭力成为一个富于使命感的独立的观察者。这时,这些作家的身份开始变得暧昧,他们既是打工阶层的一员,但又兼有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在《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和《女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叙述者与叙事对象之间的距离。这些文本至少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底层经验:叙述者自身底层经验的抒写、叙述对象底层经验的抒写、叙述者对叙述对象底层经验的认知。《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对南方打工生活的叙写明显带有一种“美学化”的痕迹,《女工记》也不时流露出叙述者对女工情感与命运的理解与认知,甚至也不乏批判的色彩。这种既融入其中又置身事外的叙述视角能否打通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的隔阂?它能否提供一种“真实”(源于其中一员的真切感受)而又客观(跳出特定视角制约)的阶层经验?这个问题显得似是而非。问题的另一面是,《中国在梁庄》或者《十四家》的知识分子视角又能否统领底层叙事的全局?这种来自阶层外围的叙述视角是否也将遭遇“真实代言”这一叙事伦理的危机?
2005年前后关于底层叙事的一批争议和讨论表明,“底层能不能表述”、“底层能否被表述”,知识分子能否真实有效地为“沉默的大多数”代言,诸如此类的问题仍然困扰着当代的文学写作与批评。在南帆看来:“这些疑虑始终纠缠着一个世纪的文学史。文学企图表述底层经验,但是,身为知识分子的作家无法进入底层,想象和体验底层,并且运用底层所熟悉的语言形式。”[9]与这一场争论相关的,是2010年左右 “打工文学”论争对这一问题的再次突显。李云雷就指出,虽然“打工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是从打工者中涌现出来的,但 “作为个体的底层或打工者,是否能为整体性的‘底层’代言”,以及“作为个体的底层或打工者,是否能为‘自己’代言”,仍然是个问题。 [10]
事实上,问题不仅仅在于作者、叙述者与叙述对象三者之间呈现出的是重叠或疏离的关系,也不在于作家是否应该具有为底层代言的使命,而在于:一种统一有序的具有公共性与普遍性的声音是否可能?换言之,“底层能不能表述”、“底层能否被表述”——这些问题实际指出了从个体经验寻求公共经验这种叙事机制的内在困窘,将个体经验上升为“典型”的做法更像是夫子自道——来自于知识的自我生产,来自于对个人化、碎片化的经验进行整合的意识形态魅影。“底层”也好,“打工文学”也好,这些概念已经被过度和宽泛地使用,从叙述对象到知识立场,这些概念甚至有沦为意识形态消费品的嫌疑。与其纠缠于“底层”的意识形态功能,不如回到具体的文本。在这批“非虚构”写作中,基于现代化历史背景下的广阔的现实领域,至少被更广泛地呈现出来,无论它们呈现的农村经验和打工经验是完整的还是破碎的,是个人的还是公共的。让文学回到公共空间,寻求个体经验与公共经验的转化,是文学重回现实与历史的重要途径。这必将涉及对具象与总体、个体与社会、现实与历史诸多关系的描述与呈现。对公共性、集体性经验的强调,其本意应在于回到现实的纵深,呈现历史的复杂性,而不是将文学重新导向某种粗陋的宏大叙事;同时,它的作用还在于重新尊重社会个体的经验与感受,寻求各种差异的独立的社会思考,从而使社会话语的表达更具开放、包容与多元性,而这种努力也将丰富和活跃社会话语的内部生态。
注释:
①宫睿哲对此有较为系统的陈述,特别是深圳文联对打工文学持续大力的推动、引导与话语建构。见宫睿哲:《打工文学的制度生产与及文化政治》,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1。
[1]张文东.“非虚构”写作:新的文学可能性?[J].文艺争鸣,2011,(3).
[2]李敬泽.文学的求真与行动[N].文学报,2010-12-09.
[3]梁鸿.中国在梁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4]萧相风.词典:南方工业生活[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
[5]郑小琼.女工记[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
[6]陈庆港《十四家》专题[N].浙江日报,2012-05-29.
[7]梁鸿.一种谦卑的行动写作 [J].中国图书评论,2012,(12).
[8]陈庆港,汪修荣谈新作《十四家》[EB/OL].http://book.sina.com.cn/news/a/2011-08-20/1820 290012.shtml.
[9]南帆.底层:表述与被表述[J].福建论坛,2006,(2).
[10]李云雷.“打工文学”:新的美学萌芽[N].社会科学报,2010-03-18.
【责任编辑:彭民权】
I206.7
A
1004-518X(2013)11-007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