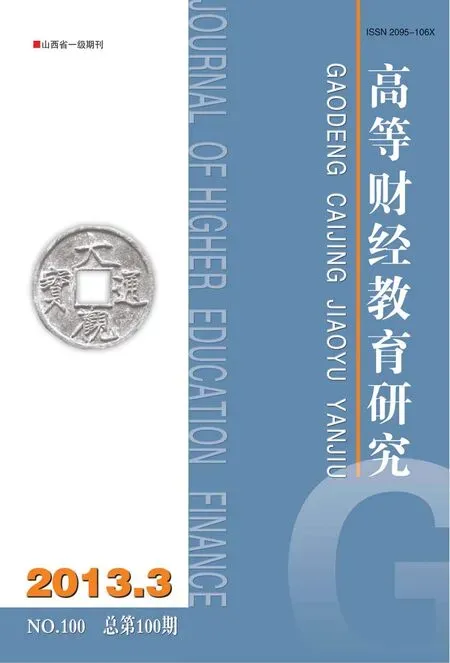《中国法制史》教学中的“守”与“变”
2013-02-15王志林
王志林
(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
《中国法制史》教学中的“守”与“变”
王志林
(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
《中国法制史》教学过程中贯穿着“守”与“变”的协调互动。课程属性与教学目标上,在坚持专业基础的同时,应彰显通识性和实践指向;应主动对现有教材体系通过增补、压减与重构进行调整;教学素材选取上,应加强学生阅读原始文献的训练,实现自读能力的提升,注重素材的经典品质与实践属性,关注学生的兴趣取向,并有意识地从学术研究成果寻求智识支持;对于重点知识和基本学理规律,应在坚持内容结构的前提下,创新表达视角和呈现方式。
中国法制史;法学教育;教学改革
美国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指出:“所有的法律思想都力图协调稳定必要性与变化必要性这两种彼此冲突的要求。”协调“稳定”和“变化”这对矛盾体是世间事物的普遍规律,不仅法律思想如此,法律制度乃至传承知识和理论的法学教育也不能例外。法律制度演进中的稳定与更张,知识传播方式的传承与更新,受众兴趣需求的恒定与变化,都使得法律教育教学中必须很好地协调稳定与变化的关系。当前,法学教育中的诸多矛盾冲突,均与“稳定”与“变化”之间的紧张存在关联。本文以“守”和“变”的协调为立足点,对法学本科核心课程《中国法制史》教学中的心得体会进行阐释梳理,以期探索该门课程教学改进的有效途径,并期望对法学学科整体的教育教学有所裨益。
一、课程属性与教学目标的“守”
(一)课程属性:通识性的专业基础课程
《中国法制史》具有历史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性质,同时也是一门旨在“阐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发展、变革的规律和近代转型的历史必然性”的基础性课程。“核心”地位与“专业基础”属性本来足以凸显《中国法制史》课程的重要,却难掩现实中面临被“边缘化”的窘境。①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实用功利风气的浸淫,部分师生缺乏对专业历史的认同和学习自觉,认为“故纸堆里的东西没有用处”,知识艰涩、陈旧,又脱离应用实际;另一方面,《中国法制史》教科书体例陈旧,知识大量重复,一些教师习惯采用单一“灌输式”的教学方式授课,使得课堂氛围沉闷,也影响了课程评价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笔者赞同应当突出《中国法制史》课程的“通识性”,作为专业基础性的补充。目前,国内法学院系《中国法制史》课程通常在大学一、二年级开设,此时,学生们还未系统接触部门法的具体知识和理论,是普及通识课程的有利时机。通过厘清中国法制发展的线索,体会中国传统法制变迁的轨迹与规律,能够从“历史”的角度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德国著名法学家、历史学派大师萨维尼在1814年就曾指出:“法学家必当具备两种不可或缺之素养,此即历史素养,以确凿地把握每一时代与每一时代法律形式的特性;系统眼光,在与事物整体的紧密联系与合作中,省察每一概念和规则。”换言之,法学是历史性与系统性的统一。现代法学教育的任务,不仅仅在于培养法律技术人才,培养具有良好法学素养和现代法制理念的新型公民的社会价值更高。法学知识具有职业性与公共性的双重属性,在当前偏重前者的背景下,法学教育需要通识性课程作为基本要素。明确中国法制史的通识性课程的属性,有助于激发以历史视角理解专业的自觉,提升专业理论素养,培养历史人文情怀;也能使教师从传统的知识讲授的窠臼中摆脱出来,更加注重法制发展进程中的思想性与人文价值,转向“法学人的养成”和“现代公民塑造”的教学目标。
(二)教学目标:传授前见知识与积淀法学素养
通识性专业基础课程的属性定位,将对《中国法制史》课程的教学目标产生影响。从传授知识的角度来看,法制史知识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为理解当下的法律提供作为理解基础的“前见”。“前见”是哲学诠释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人们在进行理解中无法避免的前提条件,前见在很大程度上统治着我们的历史意识。对于知识传播者而言,传播的知识与其理解的前见密切关联;对于知识接受者而言,从外部获取的知识又将构成自己未来理解的条件和前提。作为教师,尤其是史学课程的教师,自身能否确保所传授知识的“正确性”,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同时,由于教师传授的知识将成为学生理解的“前见”,则课程传授的知识在补充课程教科书知识体系不足,引导学生拓宽视野,乃至培养学习兴趣方面,均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笔者认为,面对《中国法制史》课程的困难,教师不应一味地通过强调“有用性”来强证自身教学工作的正当性;相反,教师仍应坚守课程知识的正确和对学生的有益引导。
《中国法制史》课程应摆脱“知识体系完整性”的过分束缚,以引导帮助学生积淀法学素养为根本目标。其实,很多教师对“灌输式”教学方式的弊端和危害都有清醒认识,但囿于“完成基本课程体系”目标的惯性支配,面对有限课时与庞大知识体系的冲突,不得不采用。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对这种方式进行了有意的规避。对于课程完整性,更多从框架上去界定,而不是从具体知识点上去判别。目前,很多学者都提出,应当对逐个朝代铺陈开来的“断代式”课程体系进行修正,将中国法制史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大跨度”的阶段划分,从而有效避免在大量重复性知识上消耗课时,同时增强带有一定理论分析水平的“小专题”的内容。笔者对此非常认同。《中国法制史》在知识实用性上似乎存有不足,但在思想性和理论涵摄能力方面独具优势,非常有利于学生法学素养的培养与提升。《中国法制史》课程教师应当通过课程的思想性、内容和表现方式,来充分展现法学历史发展的独特价值,在培养学生法学素养方面有所作为。
二、课程体系设计中的“变”
(一)教材:教学参考而非教学标准
本科教学具有重知识、重体系的特点,需在规定课时内,将该门课程的基本知识体系传授给学生,以使学生建立起相应课程的知识框架,为今后从事实际工作或者深入研究打好基础。因此,教师有责任对教材及常规课程体系进行深入理解,并适时做出调整。笔者在课程讲授中,就明确教材为“教学参考”而非“教学标准”。它只是对教学体系和知识内容进行了基本界定,但并不构成教学内容的限制。面对刚刚升入本科的同学,高中阶段形成的“教材为中心”的学习习惯影响依然很深,与大学课程的开放性之间存在一定冲突,因此应当明确告知。
之所以判定教材的“参考”属性,还是源于现行《中国法制史》教科书存在诸多不足的现实。教材数量虽然大幅增长,但“千人一面”,高度雷同;结构设计上,从夏商延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采用“断代体”安排,“一朝一章”,循规蹈矩;内容上,严守“法制思想”、“立法状况”、“部门法展开”(刑法—民法—行政法—司法制度)的套路,鲜有调整;素材选用上,“正史”居主导,“立法”唱主角而“实践性”素材稀缺,古文献资料多为“点缀”,很难给人一种整体的语境感和完整体验,等等。现行教材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与当前“名家牵头、集体创作”的编著惯例有关。笔者认为,教师不是教科书的“传话筒”,在坚持专业共识和课程基本标准的前提下,敢于呈现出自身执教的一些特性,这本身也是教学工作的创新价值所在。
(二)课程体系:增补、压减与重构
对于有论者提出的将《中国法制史》课程体系向“大断代”、“小专题”方向改革的建议,笔者表示赞同。考虑到教学实践中学生的接受程度,在实际讲授过程中作了妥协,即不采用大跨度划分的体系,而是对“一朝一章”的体系进行小幅度的整合,重点则放在讲授内容的调整上面。
笔者将课程安排为十讲:一是导论——对课程属性,即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线索与规律、学习方法等内容进行了总括式介绍;二是中国法的起源——夏商时期的法;三是中国法律传统的肇端——西周法制;四是文化原创时期的法思想与法律改革——春秋战国时期的法;五是帝制奠基时期的法制——秦汉时期的法;六是大分裂、大融合时期的法——魏晋南北朝法制;七是传统法律的成熟及其延续——隋唐至明清时期的法;八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启动——晚清的法制变革和法政思潮;九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艰难实践——民国法律的兴衰;十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重启——新中国法制变迁与法治追求。
以上十讲内容的安排,是对常规课程体系进行增补、压减和重构的结果。增补方面:夏商时期法制中增加了中国古代“圣人制法”和“法起源兵”两种学说的介绍;第四讲中,突破了传统“法制史”与“法律思想史”的划分界限,以儒、墨、道、法四家为例,增补了先秦法律思想的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制中,突出了“律学的发展与繁荣”这一问题;明清法律内容中,增补了明清小说中有关法律实施情况的介绍,结合学校财经法学教育的特色定位,对明清时期的商事习惯法等内容也作了增补介绍。压减方面:对隋唐至明清这一时期的内容,压缩为一讲来讲授(课时安排延长至8个左右);对于历朝基本法典的介绍,仅以唐律、清律作为范例,其余简略;对于近代法制史部分,与当前的法律发展密切相关,则对内容进行了较大幅度地整合重构。比如,以宪法及宪政实践作为一条主线,对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制进行了整合。同时,民事法律制度、现代司法制度的建构及其实践运行,作为贯穿这一时期法制的重要线索,也作为专题进行讲授。
通过课堂的讲授实践,笔者感觉学生们的整体思路更加清楚,教学过程中的重点也能够做到相对突出,并可以有针对性地与学生们将要学习的部门法学,如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司法制度等内容进行一定的互动,效果较为显著。
三、教学素材选取:“代读”向“自读”的转变
笔者认为,教学素材的筛选拓展,对于提升教学质量意义重大,也是体现教师课堂教学价值的重要方式。《中国法制史》教学当中,应当突破“代读”的隔阂,借助更加丰富的原始文献来呈现教学内容,更多地还原历史的独特风貌,让学生有更多的“自读”体认。所谓“代读”,是指通过阅读教材,经由教材编著者对历史的理解来间接地接近历史,它能够便捷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具有肯定的积极价值。但是,“代读”的受众始终受制于学术精英对历史的理解,这种理解在形成有益前见的同时,也会限定理解的边界,削弱读者受众直接接近历史并获取直接第一手感悟的能力。基于直接理解文本的“自读”,能有效地校正“代读”模式的不足。②因此,应当通过增补教学素材(主要是文献素材)的范围和数量,提高学生们“自读”的能力,深化对法律发展理解的能力。通过这种基本的阅读理解训练,来达到培养专业素养和进行文化知识传承。
(一)注重经典文献素材的引用
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古典文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也是后人理解历史文化的文本视域。前文已述,通行的《中国法制史》教材中,引用文献过分倚重“正史”,而且引用中的“解构”和“碎片化”现象严重,很难将古典文献的前后语境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很多学者均对这种现象提出了批评质疑。笔者在教学实践中,也进行了改革的尝试。
例如,在讲授“中国法的起源:夏商时期的法”中,关于中国法律起源的学说,是一个增补的知识点,笔者就引用了《尚书》中文献,来对“圣人法制观”进行阐释。在介绍“法起源兵(战争)”这一观点是,同样可以借助《尚书·甘誓》中的记载做出直观的表达: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通过这段记载,能使得“法起于兵”不再仅仅是一个既定的知识结论,而被还原为一种史实。作为本科阶段的同学们,对于经典的文化价值,也容易形成自觉认同。
(二)尊重学生兴趣,选择具有实践取向的素材
笔者认为,《中国法制史》教学难点还不在于知识和理论的传授,而是如何提振学生的学习兴趣。一味地批评学生对于历史的实用观念,单向度一厢情愿地灌输法史学的理论功能,不如关照学生的兴趣,适时地进行引导。
前文已述,《中国法制史》教材编排的“立法中心主义”已经受到诟病,学生也对“活的法律”、“法律在过去是如何实施的”等问题更感兴趣。因此,中国历史上法律如何实施,其实施的效果如何,应是课程知识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讲授安排上,笔者就引用了官方司法档案和一些民间资料中的案例作为素材。
在讲授清代中央司法体制时,就从乾隆朝重要的官方司法档案《驳案新编》③中找到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案例。比如,“刑律·人命”所载“王四儿射杀军官满仓一案”,王四儿本系兵丁,因酗酒被本营游击满仓掌嘴惩戒,王四儿遂起意箭射报复,后用家藏的竹弓夜间伺机射伤满仓头部。对于本案,西安巡抚认为,王四儿“实系怀忿放箭,并无杀害之心,将王四儿照凶徒生事忿争,执持刀枪弓箭伤人例拟军”。案件依照司法程序上报刑部后,刑部认为,弓箭本可致人死亡,且射中头部“透帽至骨”,满仓未死只是意外幸运,本案应按谋杀人未死处理,驳回。可见,围绕案件的性质和法律适用产生了分歧。巡抚重审后认为,王四儿所用之竹弓“并非操演之角弓”、“柔软无力”,所用箭头也是“旧秃箭头”,且验伤结论为“止射头皮,无甚损伤”,仍持原拟。刑部认为,所用之弓已经丢弃,竹弓之说系王四儿一面之辞并无确证,并对巡抚使用了强硬的措辞,“岂容任意狡供,代为开脱?”遂再次驳回。巡抚最终“服从”,认为“蓄意谋害,希图泄忿,情事显著”,将王四儿依(谋杀)律拟绞监候。刑部的认定意见终占上风。从该案中,可以非常直观地反映出,中国古代中央司法官员与地方司法官员关于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中的分歧对抗与寻求妥协一致的机制。
中国传统社会中法律人及其实践活动,也是笔者基于增强实践取向而关注的一个问题。课程中,相应地增补了中国古代讼师的内容介绍。通过清代笔记小说《虫鸣漫录》记载的一个案例,可以反映出古代讼师对于奸罪性质的区分及处理实际问题的智慧。具体案情是:某人与其婶通奸数年,后反悔。其婶佯说有事将其侄骗来,后将其绑缚,告侄强奸罪。其求助讼师,讼师只告诉他四个字:“求恕,初犯”两个字。当本案被告堂上以“初犯”名义请求原告宽恕时,其婶当堂怒曰:“尔奸我数十次,何言初犯?”地方官认为,既然双方关系已有几十次,绝非强奸,遂以和奸结案。类似容法律知识与实践经验于一体的案例素材,容易引起学生们的兴趣,能起到较好的课堂教学效果。
(三)吸收科研成果,提升教学品质
科研成果对于教学工作能够发挥支持作用。在教学过程中恰当地运用教师自身或者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能够增强科研与教学互动的效果,有益于增强教师进行学术探索的动力,并显著提高教学品质。
笔者从博士就读期间开始,就将“传统法律解释学”作为研究主题,并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这些过往的学术训练和成果积累,其实可以运用于教学实践当中。在讲授魏晋南北朝法制时,就增补了“律学的繁荣”这一问题。出发点是想告诉学生: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将解释文化经典的方式,自觉地运用到了法律解释当中,并且形成了具有民族传统的法律解释体系。律学当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先民对法律理解的知识、技术和观念。例如,“流刑”是中国封建五刑制中的一种刑罚,如何理解“流刑”的内涵呢?根据训诂中的“义训”规则,“流”与水的象征意义关联十分密切,流水不可能倒转,对于被判流刑的罪犯,自己“终身”或者连带子孙不得返回原籍的制裁实质就很容易理解了。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探讨中国法律文化与“水”的一种意向关联。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法大学王人博教授的论文“水:中国法思想的本喻”,就给笔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此外,学术研究方法,也有重要的价值。在研讨中国传统法律解释学过程中,通过历史考证法的运用和文献解读,中国传统学术进行知识考证的严谨作风和求实的精神能够得到鲜活的呈现。前人们在缺乏现代科技工具的帮助下,对于知识的探求艰辛而执着,“一字一句皆考其来历”的科学态度和学术品格,值得我们缅怀与崇敬,更值得我们去传承和实践。
四、重点知识和学理规律:“守”与“变”的互通
尽管课程体系设计上可以调整创新,教学素材选取上能够彰显教师个性,但本科教学仍有其基本要求,即需要将本课程的重点知识和学理规律向学生做出完整的讲授。这是教学过程应当坚守的原则。具体到《中国法制史》课程中,纵向时间阶段上来看,西周至春秋战国是一个重点时期,中国礼法秩序、诸子各家的法律思想、基本政治体制由此奠定;清末以来的近代转型时期,是中国法律近现代化的起点,同样意义重大。从基本的学理规律来看,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特质,中国传统法律的构成及其演变线索,中国传统法律实施的机制和运行状态,都是重点内容。这些重点时期和基本学理规律,构成了中国法史教学的经线和纬线,决定了教学的基本格局,是万变不能偏离之宗。同时,对重点内容和学理规律的呈现方式,则可以有灵活机动的多样选择。两者可以互通互动,相得益彰。
比如,春秋战国的法律改革是一个重要的教学内容,对于这个需要“守”的内容,就可以用“变”的形式表达出来。教科书当中,更多是沿着变法的背景、变法的内容、变法的理事影响这一逻辑线索组织的。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就进行相应的调整,通过以政治法律家(具体为李悝、吴起、商鞅)个人为中心的方式来进行讲授。课程准备中,通过文献查阅,理解这些变法者的生平经历,将“变法”作为他们人生经历的组成部分来予以呈现,将视角转移到人上面来。以“商鞅变法”为例,典型的文献素材在《史记·商君列传》中,通常教科书在介绍变法内容时也是引用《史记》的记载: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笔者在此基础上,关注了商鞅的个人命运。《史记·商君列传》同样有记载并有司马迁的一段评论,兹录之:
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强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通过以上文献,作为法律改革家的历史形象展现出来,“刻薄寡义”结果却“搬石头砸了自己”,但也可见作为改革家的商鞅身上强烈的求生欲望与抗争品格。笔者以此为例,重点就历史上法律改革家的悲剧命运、不为传统道德标准所推崇的特征在课堂与学生进行了互动交流,由此可见包括法律在内的制度改革的艰难。基于此,我们对于中国当前进行法制建设的改革历程应有理性认识,并做好艰难前行的准备。
五、结束语
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尝言:“人生禀气不齐,固有不能自知适当其可之准者,则先知先觉之人,从而指示之,所谓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适当其可之准,非教之舍己而从我也。”……“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笔者在法制史教学过程中感受颇深,教师并非“先知先觉”之人,需要不断努力提升自己的理论知识水准和修养;教学的核心在于让学生“自知适当其可之准”,而不在于机械复制课堂内容;成就学问,必须有“功力”和“性情”的共同支持,缺一不可。《中国法制史》教学中的所“守”所“变”,在某种程度上,仅是对上述思想见解的具体实践。
注释:
①中国法制史属于法学中的“冷门”专业,研究生招生时常常需要从其他专业调剂。学生认为法制史知识陈旧古板,与实际应用无涉。2012年,教育部高教司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更是出现了将“中国法制史”和“经济法”从法学主干课名单中取消的“乌龙”事件,在高校法学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尽管在教育部明确表态此事属于“编辑疏漏”后,事件的影响才逐步平息,但从中亦可见中国法制史课程地位的动摇迹象。
②关于“代读”与“自读”的关系问题,已有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思考。梅新林、葛永海从大众传媒这一角度入手,分析了“经典代读”模式产生的理由和合理依据,在深入分析“经典代读”可能造成的文化缺失基础上,探讨传媒、学者和大众在应对“经典代读”造成问题时所应扮演的角色,指出应当促成由媒体主导的“经典代读”向公众自身主导的“经典自读”转变。参见梅新林、葛永海的“经典‘代读’的文化缺失与公共知识空间的重建”,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152-166页。
③《驳案新编》由全士潮等六位清代刑部官员纂辑,收录了乾隆年间(乾隆元年—乾隆六十年)遵驳改正的318个重要案件。它是一部专门的驳审案例汇编作品,对于反映清代中央司法运作特别是重大刑事案件的处理情况,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1][美]罗斯科·庞德.邓正来,译.法律史解释[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2.
[2][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许章润,译.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37.
[3][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356.
[4]王志林.清代驳审制度考论——以《驳案新编》所载案例为中心的考察[J].政法论坛,2009(4).
[5]王人博.水:中国法思想的本喻[J].法学研究,2010(3).
[6]宋从越.“话的法律”的讲述者——教师在中国法制史课程中的作用[J].阴山学刊,2013(2).
[7]徐祖澜.定位与创新:中国法制史教学改革刍议[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9(2).
[8]胡谦.法学本科阶段《中国法制史》教学体例与内容的思考[J].长沙大学学报,2006(6).
[责任编辑:秦兴俊]
The Stabilizing and Innovating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Legal History
WANG Zhi-lin
(Law School,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Taiyuan 030006,China)
The interaction of stabilizing and innovating exists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Legal History.In the attribute and teaching object of the course,general education and practicality should be attached more importance.The teacher can adjust the course system through adjusting the knowledge.In the field of selecting of teaching source material,the teacher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improving the students’ability of oneself-comprehension through showing more one-hand classical documents.The teaching materials should be classical and practical,suited to the study interests of students.The teacher also can use the achievement of academic research to improve teaching effect.At the same time,on the foundation of teaching whole system of knowledge and academic theory,the teacher should be willing to innovating the means of expressing and comprehending.
Chinese legal history;legal education;innovation teaching
G642
A
2095-106X(2013)03-0012-06
2013-07-18
王志林(1978-),男,山西长治人,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教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是法律史、法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