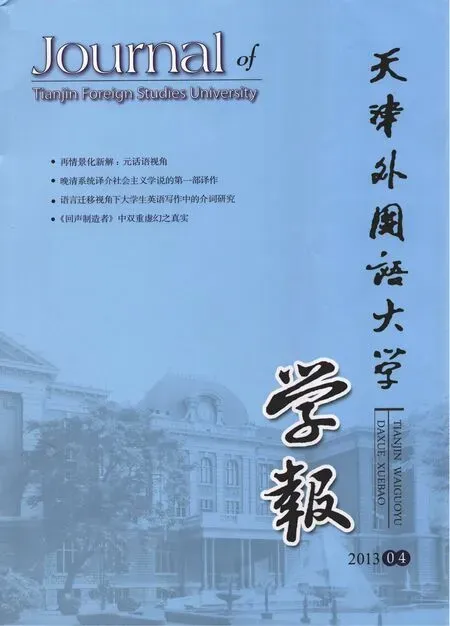语言模糊美意象的建构与解读
2013-02-14王雪莹
王雪莹
(天津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天津 300204)
一、引言
模糊语言存在于言语交际中,如“小的房屋”、“高的建筑”、“美的服装”,什么程度才算“小”、“高”、“美”,界限意义并不确切,使得概念表达具有模糊性。然而正是这种模糊语言的外延不确定、内涵无指定,成为一种弹性语言,具有更大的概括性和灵活性(崔传明,2010)。目前学术界多从定量与定性的视角进行研究,郭丽娜(2000)从共时的角度分析语言的模糊性特点,并揭示出模糊语言的本质。李春华等(2002),万来声(2002)对语调、词义、语法和跨文化的模糊修辞进行描述。苗东升(2000)进一步拓宽模糊语言学研究的领域,将诗眼和词眼视为模糊美词语。余富斌(2000)将模糊语言的意象研究应用于翻译实践。语言社会性研究的多元化丰富了对模糊语言的认知,但其变化条件、变量组合与相互影响因素等认知主体的心智活动并未纳入研究的向度。模糊语言作为人的一种交际手段,实际上具备了社会现象的本质属性(武玉洁,2010),从心智语言学视角研究语言的模糊性,将对阐释模糊美的意象生成具有重要意义。
二、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回顾
语言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产物,也是认知活动的工具,乔姆斯基称语言为“心灵之镜”,他把内在语言看成一种心脑状态,是人类实现语言能力的集体组织(蔡曙山,2010)。随着心智哲学逐渐成为认知学科方向发展起来的崭新学科,在研究语言意义时,研究者把语言表征与人类共有的涉身体验、语言、文化等因素联系起来,使语言内部的心智因素成为研究重点。Searle(2004:159)指出:“语言问题的认识依赖于更为基础的对心智问题的认识,意义和意向性是先于语言的心智能力,语言依赖于心智,甚于心智依赖于语言。”Lakoff(1980:166-169)则将人类认知的能力重新奠定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之上,认为内在语言与身体、大脑、本能结合起来,各种语言形式下产生的意识、心身、意向性、感知等问题被赋予了语言能力。
语言最重要的性质是基于心智的,人们的语言活动分为语言学习、语言记忆和语言运用,其过程为语言信息进入大脑长时记忆系统后,人们根据语言的形式和功能对语言信息进行加工,建立各种相关联系,这一复杂的过程涉及人的心脑活动。当人们对语言能力和意识的诸多问题做透彻地研究时,心智研究转移到前台,并着重对大脑功能和身心关系的探索。因此,心智语言学的研究是从认知主体的心智活动契入,最后回到语言中去,即“语言—心智哲学理论—语言”(徐盛桓,2011)。
三、基于心智理论的模糊语义分析
模糊用语作为一种弹性语言在言与意间的张力下升华为模糊美,这一升华过程涉及了心智哲学所关注的知觉、推理、记忆等心脑反映,认知主体的思想情感和模糊意识。
1 模糊意义的实质
1965年美国科学家札德提出的模糊理论使模糊语言、模糊心理、模糊修辞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与精确语言相比,模糊语言是人们认识中关于对象类属边界和性态的不确定性(李晓明,1985:66),这揭示了模糊概念的实质,即事物和现象的模糊性先是在人们意识中反映,进而在作为思维载体的语言中得以反映。从心脑活动来看,语言的模糊意义首先是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构成难以分解的统一体,成为一种本体模糊性映射在人的头脑中形成了思维和认识的模糊性,例如,昼与夜的循环、春夏秋冬的交替本无确切的界限可言;其次,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在把握对象的类属意义时缺乏明晰的界限或精确的划分,使语言形式表达不明确,例如鲸鱼、鳄鱼并非鱼类,人们给其命名时,只抓住其在水中生存的特征,而忽略其他特征,造成了模糊语义;再次,在语言运用过程中,出于语言表达的策略需要,人们故意使用一些语义模糊的词语以适应不同的交际需要,如“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办理”中的“有关”一词就没有规定按照哪一个法规办理;最后,不同社会角色身心意识的介入,有意识模糊事物界限,促使模糊意义的生成。
2 语言的模糊功能
语言的模糊功能是主观因素、经验因素、意识因素、情感因素以及其他种种与认识主体心身相关因素的映射,在交际过程中,其独特的语言信道、思维空间、意蕴表达在语言物理属性、心理属性和意向性上的心智意识体现得尤为明显。
2.1 独特的模糊信道
任何事物都具有固定的物理属性,模糊语言也不例外,Kempson(1979:125)将模糊性词语分为四类:指称模糊(referential vagueness)、意义不确定(indeterminacy of meaning)、缺乏确指(lack of specification)、意义析取(disjunction)。它们表达的概念因缺乏明确的界限和精确的物理定义域,形成独特的物理属性——模糊信道容量广。语言表达的模糊化使认知主体必须依赖对外在世界综合性的认识来理解意义潜势,模糊信道随之拓宽。伍铁平先生曾举过一个例子,假如要求某人到会场找一个他不认识的人,只需要模糊地描述出“中年、身高体胖、高鼻梁、大耳朵”即可,但是用精确语言“36 岁零8 个月,身高1.8 米,体重95 公斤,鼻高2 厘米,耳长7 厘米”,反而难找此人了。通过对比发现,模糊语言因其信道宽更易于为听话人所接受和记忆,当语言的物理属性作用于人的大脑后,激发了对模糊信息的记忆与提取,使信息容量增大,认知主体根据不完整话语信息寻求模糊语义的物理范畴,对客观事物进行识别与处理,推断出客观事物的完整形象,这一经过整合后的模糊语言在信息识别方面明显优于精确语言。相比之下,精确语言运用的是精确思维,但认知主体因缺乏对有限信息容量的物理类属进行有效判定,而无法将传达的精确信息和所指对象进行匹配。可见,这种独特的模糊信道是人类进行模糊认知、模糊推理,把握客观事物本质的重要途径,模糊语言由此扩大了语义表达的信息容量,增强了交际效果。
2.2 模糊思维与意象
模糊语言的物理属性体现其独特的模糊信道,而心理属性体现于意象的模糊思维,通过一定的修辞结构进行传递。人们对模糊词语“蓝色”是通过视觉获得感知的,但当说“我的心情如同湛蓝的天空一样”,话语的心理属性依附于语言的物理属性,并形成对这个颜色词的一种思维空间,认知主体通过视觉所感知的天空与当时自己的心情结合起来,“蓝色”这一客观的物理事件发生了主观的身—心改变,由“天空湛蓝”的物理感受涌现为“内心澄清”的心理感受,寄生于语言的心理属性中。这种心理属性表现为人的感知和感受(徐盛桓,2010),由人的眼、耳、鼻、舌、身对事物进行感知,再由感官获得的感受(色、声、香、味、触)反映到大脑,延伸至信念、意向等心智表征上,通过隐喻等修辞方式寓于语言之中。《红楼梦》中对柳湘莲的性情描写使用了“眠花卧柳”的隐喻修辞,这种模糊修辞依赖于主体的认知方式和认知能力,映射出一种开放式模糊思维,人们通过对“花”、“柳”的记忆感知而生成一种柔软的感受,物理感受与抽象的性情概念相联系,模糊思维下产生的意象随附于对柳湘莲性格的认知空间中,这种转化过程拓宽了“花草之情”思维空间,涌现出一种对柳湘莲性情的更为广阔的模糊意象思维——世家子弟的风流形象。语言的心理属性拓展了文学形象的表达思维空间,文学作品中常用己知事物表达新概念,而开放的思维空间使模糊语言在意象、情感、意境、风格方面的表达难以计量。
2.3 模糊话语的意向性
认知主体对话语对象的总体态度,如爱慕、憎恨被称为意向性,诸如信念和欲望之类的心理意向要通过某一话语方式体现,模糊话语由于蕴含了认知主体对描写对象在认识上的模糊,自身的情绪、愿望等心理意识取向,从而产生意向性。例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被问在英国读书期间曾吸食大麻的说法是否属实时,以“吸食大麻违反美国法律,我没干违反美国法律的事”的回答对话语进行模糊控制,将自己的心理意向反映在语言中。在缺乏特定的信息或是有意保留信息情况下,话语主体运用模糊表达产生特殊的意向性,既让公众相信了他的清白,又不用担心日后被人们发现真相后会指责他撒谎。模糊话语有意保留信息,避免把话说得太直白,Searle(2004:172)指出,话语意向性是通过语言的结构特性反映出某一种心理模式并对内容的描述构成了意向态度。同样,听话人对模糊话语在心智空间也将做出意向性的判断,通过语言的模糊信道、模糊思维和主观上的心理干预、过滤、解释、重组,构成一种合理且符合自我意愿的解释,或“克林顿没有吸食大麻”,或“即使他在英国吸食大麻也不受美国法律制裁”,从而形成模糊话语的多维意向性。这种意向性是核心意识和记忆共同运作的产物,体现了认知主体在言与意之间的取向态度、意图和趋向。
综前所述,模糊语义外延宽,伸缩性、适应性与包容性强,提高了语言表达的灵活性,在交际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协调作用(毛荣贵,2005:330)。认知主体的心智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同的交际对象和交际目的使语言意义多样、富于不确定性和启示性,模糊美的意象应运而生。
四、由言到意的模糊美意象
模糊概念要比明晰概念更富有表现力(伍铁平,1999:44),艺术的模糊美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作者运用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段对事物进行模糊类比,唤起读者的联想与想象。语言的启发性和暗示性使这种含蓄的模糊语言通过以言抒意、言不尽意的抒情范式,让人在言外思而得之,以获得言已尽而意无穷的模糊美意象。
1 以言抒意
古人注重观物取象,通过类比加工成有象征意义的语言符号,在模糊美的言与意之间,以言抒意正是认知主体先通过眼、耳、鼻、舌、身对外界信息摄入,形成物理感知,进而引发一定的心理感受,最后通过联想、推思、判断、理解等心理活动对修辞语言产生的意象予以表达。
(1)香花的文艺作品
这是1957年毛泽东在讨论文艺作品时提出“香花”与“毒草”概念后便广泛沿用下来的一种表达,在探讨文艺“双百”方针的时候,常常涉及“香花”、“毒草”的问题。用“香花”比喻中国的文学艺术作品和学术作品时,读者通过感官(鼻)对香花味道的体验唤起知觉经验和意向判断,将花的香味上升为对“香花文艺作品”的感受,延伸至心智上形成了对文艺作品的心理感受,获得了一种积极、健康的意向性,这种较为模糊、有暗示意味的语言信息容易激活读者的思维,因而将“文艺作品”比喻为“香花”,语言意象渐次递深,读者通过“言”体味文艺作品的“意”,在情感意识的作用下,使文艺作品的阳光性和健康性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意象空间,这种修辞的模糊美内在而抽象,蕴涵了话语的核心思想。
(2)思悠悠,恨悠悠。(白居易《长相思》)
汉语中许多附加式重叠词语生动表现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各种感悟,直诉意识深层,诗人将“意”的蕴含意义置于人们对“悠悠”一词的感悟之中,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言“情动于衷而形于言”,诗词中的“言”必然经过物理属性、心理属性最终上升为某一意向态度。诗句中“悠悠”的模糊表达,程度之深不可计量,内涵抽象的“言”使诗句中“意”的可能性扩大,读者基于自身经验,从对模糊信道的认知到意象的模糊思维,获得爱、恨、喜欢、希望等心理上的某种意向性,体味诗中妇人对丈夫思念与怨恨交织的愁苦之情,在感知与感受“悠悠”的思念怨恨的程度和时间长度增强了模糊美的意境,从而由模糊修辞的“言”美感受到模糊的“意”美,若将“悠悠”改为精确词语,有了年月的期限,读者的思维便会锁定于时间的长短上,而闭合了模糊的思维空间,无暇感受“思”与“恨”意象之美,诗句因缺少了“情”也就无法传递“意”。《长相思》中所运用的模糊修辞的表达形式不仅激发了读者无限绵延、无可估量的心理感受,涌现为又“思”又“恨”的悲凉意象,而且令读者在无奈与悲伤的意境中体味诗句盼归的主题。诗词往往借助于语义界限相对较灵活的模糊语言,以言抒意,升华成模糊美,从而获得抒情特质的感受意。
2 言不尽意
言不尽意是另一种模糊美意象的抒情范式,其文字向内凝缩,意义向外延展。交际主体的身心意识活动成为欣赏模糊美的核心,主要通过自我体验感受模糊语言的意象,采用类比—联想—意象来替代概念—判断—推理。
(3)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塞上》)
诗句中虽然只有10 个字,却形象地绘出塞外雄奇瑰丽的风光,此外,景物的描摹凸现了大漠粗犷、诗人刚毅的精神。读者的心灵可以延伸至人烟以外的事物,大漠除了烟和落日没有其他形态的生命,一片孤寂,读者亦可从“烟”字中感受到景物之外的活动,如边塞的战争、士兵的怨声。这种空间的延伸是一种概念化的逻辑框架对直觉对象所处空间的抽象规范。当任何个体感知对象时,所把握的不是对感知对象属性的全部把握,只是对其整体精神、特征等的抽象概括,并通过个体意志、情感、体验加以整合所产生的开放意象。由于任何形式的话语行为都是以语词为思维的起点和归宿,表达出的“言”富于感性,唤起了读者微妙的直觉,而类比中的“意”却纷繁抽象,不受时空限制和逻辑的约束,由类比到联想再到意象,对模糊美的意境感受可谓言已尽而意无穷。
为什么会产生言已尽而意无穷的模糊美意境呢?从根本上说,就是人类心智活动的感知和感受。感受是通过语言和行为表达发生在人身上的某种特殊的感觉(王姝彦,2010),而人的大脑除了具备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之外,还有悟性思维的能力(刘佐艳,2003)。读者并非消极、被动地接受,而是积极主动地把模糊语言作为审美客体,通过身心的感受进行心智的编码,将语言信息进行记忆、存储、提取、加工进而形成概念、判断、推理等的思维意识,最终“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
(4)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终南别业》)
诗中以“水”、“云”作为物理事件起点,以“穷”、“起”作为事件变化的结果,通过“行”和“坐”产生身—心关系,以语言表达某种感觉,传递某种感受之意,这样的意识活动是基于人类对意识现象的某种共同反应。古人为表达诗句中的“象”和“意”,摒弃了对水、云变化过程的精确表述,而使用意象组合给予了认知主体广阔的思维和逻辑空间。诗词中以云和水物理事件的变化作为思维的起点,以云和水心理属性的涌现作为思维的归宿,通过对水和云的感觉认知,唤起对生活的意向态度,最终上升为对云和水的感受意。因而由感受真实山水的现象质转化为感受语言表征的山水意象,随附在诗中模糊美的意境之中。其实模糊语言中的意境,同认知个体的意识活动有关,诗人用意或许并不停留于对山水自然的赞叹,而在于抒发对闲适而自由生活的赞美。读者获得的感受意还可以上升一个境界:在绝境中不要失望,不要放弃,处事豁达。因此,渗透于文学作品中“书不言尽,言不尽意”模糊美的意境,其实是人们对语言里所表征的意识对象产生的一种类似于感受质的那种难以言喻的心理感受(徐盛桓,2010),属于更为含蓄内敛的模糊美。
3 翻译过程中模糊美意象的转化
模糊美不仅是一种跨文化的对话,也是考验译者对源语与译语间审美的认知与建构。在审视和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模糊美时,译者需要面临两次交流,与源语作者的交流和与译文读者的交流。作为语言模糊美感的传递者,有必要利用“言”与“意”之间的微妙关联,对语言进行感知、联想以再现模糊美的意象。
原文:Some fishing boats were becalmed just in front of us.Their shadows slept,or almost slept,upon that water,a gentle quivering alone showing that it was not complete sleep,or if sleep,that it was sleep with dreams.
译文一:在我们面前停泊了几条渔船,它们的影子在水面上睡着了,或者说是几乎睡着了,一个轻微的颤动,说明影子没有完全睡着,假如说是睡着了,也是一边在睡,一边在做梦。
译文二:渔舟三五,横泊眼前,樯影倒映水面,仿佛睡去,偶尔微颤,似又未尝深眠,恍若惊梦。
原文以becalm,shadows,water,quiver,sleep和dreams 凝练地勾勒出渔船宁静伫立于水中的画面。becalm 表现出渔船的静,sleep和sleep with dreams 的拟喻修辞赋予了渔船的一种睡意之美,quiver 再现出渔船稍纵即逝的驿动。译文一忠实地表达了原文的字面含义,却未能摆脱英语语言的束缚,忽略了言与意的关联,从而令人费解,船影怎么睡?水和船怎样相互交融?哪里透着恬淡的意境?译文二兼顾了模糊美的意与象,改用汉语的波浪式流水句,把单个事物加以组合凸现出整体,以“渔舟三五”、“仿佛睡去”等四字结构的表达高度意合,从而生成全新的意象,在状物上侧重事物的隐含美,依赖于个体的审美知觉经验和想象力与物象之间进行美的联系,对becalm,sleep和quiver 感知,随附在对渔船情境的心理属性之中,以神驾驭形,使译文读者获得以言抒意的模糊美意境,这种模糊美意象的转换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翻译活动中模糊美意象的转换十分必要,译者对语言的认知和审美能力直接影响译文的生成与质量。原文的语言逻辑分明,叙事条理清晰,在写景状物上侧重事物的逻辑美,以临摹形式展现宁静、惬意的模糊美,译者需要处理好笔墨精确与模糊的平衡,在言与意之间,摆脱言的束缚,着重意的表达。就两译文而言,译文二的语言富有诗意,符合模糊语言的属性特征,为译文读者搭建信息和思维空间的平台,使意蕴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同样,在汉译英时译者也要考虑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在追求模糊语言的认知环境时,尽可能留给读者一定的想象空间。请看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诗词意境重在意蕴和情趣,主旨不在写景,也不在抒情,主要是为了反衬那站在“灯火阑珊处”的“他”。“他”究竟是什么样子,词里没有说,只是一个模糊意象,留给读者巨大的意向性思维空间,或许是作者心中苦苦追求的恋人,抑或是作者追慕的一种境界、品质。这种含蓄性诞生了模糊美,虽是一种不确定性,却是一种审美体验,使人回味无穷,从而独具艺术魅力。对于这种言不尽意的模糊美意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融入景、融入情方能译出意境之美。
One night’s east wind adorns a thousand trees with flowers;
And blows down stars in showers.
Fine steeds and carved cabs spread fragrance en route;
Music vibrates from the flute;
The moon sheds its full light;
While fish and dragon lanterns dance all night.
In gold-thread dress,with moth or willow ornaments,
Giggling,she melts into the throng with trails of scents
But in the crowd once and again
I look for her in vain.
When all at once I turn my head,
I find her there where lantern light is dimly shed.(许渊冲译)
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建立在逻辑推理上,这种方式被称为“纵向思维”(连淑能,2010:342),尤其在英语语言中,常常运用各种暗示逻辑的标记和词语形成感悟语义、驰骋想象以形摄神(毛荣贵,2005:299)。鉴于此,译者在翻译时分别运用and,while,but,when衔接,顺应英美读者的文化心理结构,突出语言的逻辑美以唤起译语读者的联想,来再现原文中抒发情感的隐含美。在再现原诗句中多维的模糊美意象时,译者需要将现实的客体世界和幻想的主体世界交融,审视英汉语言在表情达意上的差异,求真实、求逻辑方可淋漓地体现出原文的语言与意象。译文的前八句记述了诗人眼中所见,以夸张的修辞形式来重构景象,将原诗中的“星如雨、香满路、暗香去、蓦然、灯火阑珊处”等模糊美感进行贴切地变通,译为stars in showers,fragrance en route,melts into the throng with trails of scents,when all at once和where lantern light is dimly shed,拓展了英语读者情感体验的思维空间,使得译文中模糊美的意象无限延伸。在诗词最后部分,“众里寻他千百度”被译为I look for her in vain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被译为I find her there where lantern light is dimly shed,译文由演绎过渡到归纳,体现了译者对原诗句的审美意识、情感世界和内心感受。译文的语言虚实携手,在外延与内涵上最终获得言已尽而意无穷的模糊美意境。
五、结语
朱光潜(1982:476)先生曾经概括说:“言是固定的,有迹象的;意是瞬息万变的,是飘渺无踪的。”正是言与意之间的微妙关联性揭示了模糊语言的本质和规律,读者通过观察和联想,以自我的涉身经验领悟语言的意向性,在动态环境中寻求模糊美的意象和意境。沙夫(1979:355)指出:“交际需要语词的模糊性,这听起来似乎是奇怪的。但是,假如我们通过约定的方法完全消除了语词的模糊性,那么我们就会使我们的语言变得如此贫乏,就会使它的交际和表达的作用受到如此大的限制。”因此,在研究认知机制和言语交际需要下形成的模糊语言时,认知主体通过心脑反映,运用思想情感和模糊意识剖析语言中的模糊修辞、语用模糊,可为阐释模糊美的构建提供丰富的土壤,也为解读模糊美言与意的意象和意境提供广阔的审美空间。
[1]Kempson,R.Semantic Theory[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2]Lakoff,G.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3]Searle,J.Mind:A Brief Introductio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4]蔡曙山.人类心智探秘的哲学之路——试论从语言哲学到心智哲学的发展[J].晋阳学刊,2010,(3).
[5]崔传明.浅议模糊语言的修辞功能[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0,(11).
[6]郭丽娜.语言模糊性的特点及其共时性研究[J].汕头大学学报,2000,(4).
[7]李春华等.语言的模糊性和语境的解释功能[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3).
[8]李晓明.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9]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10]刘佐艳.关于语意模糊性的界定问题[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4).
[11]毛荣贵.翻译美学[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12]苗东升.诗与禅与模糊思维[J].中国文化研究,2000,(3).
[13]沙夫.语义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4]万来声.模糊理论在翻译中的运用[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3).
[15]王姝彦.“可表达”与“可交流”——解读“感受质”问题的一种可能路径[J].哲学研究,2010,(10).
[16]伍铁平.模糊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17]武玉洁.从翻译的角度看语言的模糊性[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4).
[18]徐盛桓.感受质与感受意[J].现代外语,2010,(4).
[19]徐盛桓.语言研究的心智哲学视角[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20]余富斌.模糊语言与翻译[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10).
[21]朱光潜.朱光潜论文集[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