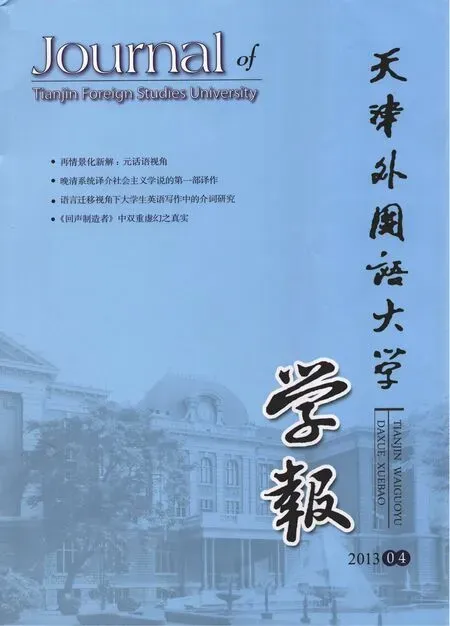小说《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的叙事风格
2013-02-14冯红
冯 红
(天津外国语大学 基础课部,天津 300204)
一、前言
威廉 ·狄恩·豪威尔斯(William Dean Howells,1830-1920)是美国现实主义的作家和评论家。他的代表作 《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The Rise of Silas Lapham,1885)是19世纪晚期美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典范。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赛拉斯从一个贫穷的乡下人,发迹并进入美国上流社会,最终又因为良知导致破产,再次回归故里的故事。作者在小说的叙事上做了精心的设计,创作了一首源于不同人物以及不同阶层的各种声音汇成的复调。同时作者又通过有意地利用叙述者以及叙述接受者在评价、态度、身份和视角上的细微变化影响读者对特定人物的判断,实现对人物的真实性的刻画。
二、叙事的复调性
复调(polyphony)原本是一个音乐术语,意指多个具有独立意义的旋律声部按一定的规律有机结合而成的多声部音乐形态。19世纪初,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Bakhtin)将这一术语引入到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vsky)的小说研究中,使其带有隐喻的性质。在作品中读者常常可以感到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声音的交流。不仅如此,读者还能感觉到这几种不同的声音可以和谐地统一于一部作品的总体的基调之中。作品所追求的是把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外部世界和内在世界放在同一个平面上。从多个角度呈现给读者一个立体的作品,旨在表明世界是众多个性鲜明且独立自主的声音在交流和争鸣的大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无论多么微弱的声音都可以被听到。《赛拉斯 ·拉帕姆的发迹》在叙事上就具有这样的复调特征。作者希望用复调性的叙事向读者传递一种普遍性的、现实主义的道德观。“小说要传递的道德观不会仅仅呈现在一次交流的某个固定点上,而是动态的交流和循环。这种动态的交流和循环正是人物不同声音构成的复调。”(Barton,2001:183)只有通过倾听每一位人物的声音,并参与到其中,读者才能准确地理解作者的意图。首先,从小说的题目看,读者一定会得到某种暗示——小说的道德核心集中于某个特定的人物,而且相应地会倾向于崇尚该特定人物所代表的阶层的道德观念。题目预设性地表明代表劳动阶层的赛拉斯注定具有高尚的道德水准。可是,继而读者会发现小说的叙事时而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最终,读者会慢慢地领悟到作者并不希望让任何一个单一的、清晰的人物或者阶层的道德规范在叙事中占据主导的地位。“作者不把自己的评价和态度强加给读者,而是让读者发挥想象,参与文本的建构,与小说中的聚焦人物共命运,推动小说的发展。”作者有意且巧妙地引领读者去认真倾听多种声音,包括来自劳动阶层的赛拉斯、珀西斯、休厄尔、科里一家及其社交圈里的其他人物。作者有意引入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以避免读者将任何单一人物或者阶层的观点当作毫无争议的道德规范。“豪威尔斯并不想让他的读者永久性地支持任何一个人物的观点。”(Seelye,1991:55-56)
小说以赛拉斯接受记者巴特利·哈伯德的采访展开了故事的情节。读者了解到巴特利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缺乏同情心。他利用良好的教育撰写文章蓄意嘲笑赛拉斯(Howells,1982:863)。作者一开始是引导读者去同情赛拉斯。赛拉斯并没有怀疑巴特利的意图,当他注视着这位年轻的记者时,仿佛看到了他自己刚刚走入社会时的情形(ibid.:871)。这种共鸣不仅使赛拉斯主动将巴特利送回报社,而且赠送巴特利的妻子玛西娅一整套拉帕姆公司最好的涂料(ibid.:875-879)。作者的目的在于让读者清楚地看到赛拉斯的坦率慷慨和巴特利的尖刻势利所形成的鲜明对比。至此,赛拉斯以及他所代表的劳动阶层在读者的心里占据了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小说的题目隐含地表明创业之初的赛拉斯并非道德高尚。巴特利这一人物在第一章当中最为关键的作用在于他一开始就注入了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在第一章当中,赛拉斯提到了他曾经在涂料生意当中有过一个合作伙伴罗杰斯。当巴特利轻描淡写地评论了这位合作伙伴时,赛拉斯却面露怒容。读者一下子就会感觉到赛拉斯的这一举止是很反常的。巴特利瞬间感到了赛拉斯态度上的变化,敏感地知道每个人的记忆当中都有过心酸的时刻,巴特利很清楚这是不能再触碰的痛点(ibid.:874)。读者一定会对巴特利身上突然产生的对心酸经历的共鸣产生兴趣。读者倾向于相信巴特利的感觉——他和赛拉斯都做过问心有愧的事。读者不得不被迫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可爱的赛拉斯居然在某种程度上与冷漠无情的巴特利有着十分相似的经历。巴特利的反衬作用打破了读者的预设——来自劳动阶层的赛拉斯是道德楷模。
如果赛拉斯是不完美的,那么在随后的内容中,同样来自劳动阶层的赛拉斯的妻子珀西斯就自然地进入了读者的视野。在第一章当中,作者隐含表明了赛拉斯从前的生意伙伴的情形将会形成整个叙事当中关键的不确定性因素。到了第三章的时候,赛拉斯和珀西斯出人意料地遇到了罗杰斯。珀西斯认为,赛拉斯对罗杰斯的行为是应该受到道德谴责的。赛拉斯坚持认为自己问心无愧。通过第一章的内容以及题目的暗示,读者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赛拉斯对妻子撒了谎。整个小说的叙事张力集中在一个核心问题上:赛拉斯与罗杰斯之间的生意是否是诚实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读者就需要重新树立一个完美的道德典型。珀西斯很了解她的丈夫并坚信赛拉斯并不是那么诚实的。作者在此处试图引领读者选择珀西斯。读者也会倾向于相信珀西斯的判断。“尽管小说在一开始将珀西斯描述为赛拉斯的精神引领者,但是作者此时又开始渐渐地减弱她身上光环的亮度了。随着赛拉斯道德水准的提升,珀西斯却沦落了。”(Goldman,1986:42)赛拉斯面临的最重要的道德考验是他是否应该在隐瞒不报的情况下,将毫无价值的厂子卖给别的买主以避免倒闭的风险。可是,读者最初无法知道到底是珀西斯还是赛拉斯最先意识到这种选择是不道德的行为。珀西斯先说出了她的观点,再卖给别人就会像罗杰斯一样的不道德。赛拉斯告诉珀西斯不要担心,他是不会这样做的(Howells,1982:1121)。前面的叙事似乎为赛拉斯对良知的判断留下了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但是,在此处的叙事当中作者又渐渐地将赛拉斯而不是珀西斯定位为小说的道德楷模。赛拉斯询问珀西斯该不该隐瞒实情。珀西斯很勉强地说“可以”。当面对有可能使他们免于破产的实际买主时,赛拉斯“充满焦虑地偷看了妻子一眼,他在她那没有得到任何的帮助……现在到了紧要的关头,到了他特别需要她的洞见的时候”(Howells,1982:1167-1168)。作者已经巧妙地让读者明白没有妻子的建议赛拉斯也有能力做出有道德的决定了。但是,作者的所作所为决不仅仅是简单的道德化身的转移。细心的读者会再次发现玄机——赛拉斯即使秘而不宣地卖出厂子仍然不能还清债务。这就提供了对赛拉斯所谓的道德的选择的又一至关重要的解读:赛拉斯决定不那样做并非出于良知,而是他已经意识到出卖厂子也不足以免于破产的真实状况。
笔者认为,作者是在有意地留给读者许多需要思考的伦理和哲学问题。“豪威尔斯没有任何意愿想要将赛拉斯塑造为一个圣人。”(Manierre,1962:36)即使当读者的注意力从珀西斯的身上移向赛拉斯的身上时,当读者期待着赛拉斯的道德发迹时,作者仍有意使情况复杂化,使读者无法真正地确立任何一个单一的人物或者阶层为小说的道德标准的唯一代言人。“作者暗指英雄出自于人们对英雄敬慕和尊重的心理,英雄主要是人的创造,并不是伸手可及的人,而这些人可以帮助我们面对世事的复杂性。”
既然劳动阶层的赛拉斯夫妇不是读者期待的道德楷模,那么在上流社会能否寻找到这样的人物呢?小说又呈现给读者一位潜在的道德引领者,牧师休厄尔。当珀西斯和赛拉斯发现他们误以为汤姆·科里会娶他们的小女儿艾琳,而不是大女儿珀涅罗珀,但实际情况刚好相反的时候,他们去找牧师休厄尔寻求建议。休厄尔告诉他们要遵循“最小伤害法”,按照这一原则,汤姆应该与大女儿结婚,因为他们彼此相爱。深爱汤姆的小女儿一定会感到难过,但是一个人受伤害总是比三个人都受伤害要好很多(Howells,1982:1085)。显然,作者并不想让崇尚上层社会价值观的休厄尔成为小说的道德引领者。因为毫无例外,几乎所有的主要人物无论来自何等阶层,在没有休厄尔的帮助下,都能够使用最小伤害法去应对汤姆与两个女孩之间的关系。比如,在决定找休厄尔咨询之前,珀西斯问她丈夫,“有用吗?没人能让我们看到与真相不同的东西”(ibid.:1082)。显然,牧师也不是多么高明之士,不能成为小说的核心道德的引领人。作者也不想让读者对休厄尔产生纯粹的敬意。“作者提供了一些线索,以便让读者将休厄尔视为虚构的小说当中的一个多愁善感的思想怪人。”(Barton,2001:185)
总之,作者不想成为一个公开的道德上的说教者。他想要塑造一系列的吸引读者的人物形象,使读者形成对不同人物及其社会状况的自己的判断。小说自始至终演奏了一曲复调,它是不同人物的声音汇成的乐章。
三、作者利用叙述者和叙述接受者影响读者
1 作者利用叙述者影响读者
从一开始,读者就可以看到小说的叙述者(narrator)常常对赛拉斯的形象加以损毁,总是将赛拉斯定位为语言不雅,举止粗俗的形象。“叙述者似乎特别有兴趣显露赛拉斯缺少文化修养和文雅品位的特点。”(Young,1992:45)例如,叙述者称赛拉斯自以为“漂亮的”佛蒙特州的家是“丑陋的”,并且暗中表明这座房子恰恰是因为刷了一层拉帕姆家的涂料以及阳台式的走廊而变得更加“难看”(Howells,1982:865-866)。又如,恰恰当赛拉斯如数家珍般地因第一次使用他的涂料而感到喜气洋洋之际,叙述者却以对赛拉斯外省发音的评论来终止这一喜庆的时刻(ibid.:867)。这样的描述使读者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将叙述者的判断视为作者的判断。显然,叙述者的这种口吻带有崇尚上流社会的审美和品位的倾向性。读者不禁要发问:叙述者的趋炎附势是否与作者如出一辙呢?如果读者认为这就是作者的真实意图,那就是中了作者的圈套。作者此时想要读者在某种程度上将叙述者所崇尚的上层社会的价值观视为权威性的,并且作者的确希望这一点会让读者与赛拉斯之间产生距离。当读者进一步阅读时,就会理解作者为什么要使叙述者的判断复杂化的原因。因为叙述者仅仅充当了作者的工具,叙述者并不是作者真实意图的代言人。种种迹象表明作者有意拉开他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而且有事实表明叙述者的判断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而这些都是作者的有意之举。例如,叙述者通过安娜·科里的视角生动地描述了布罗姆菲尔德的生活状况,特别具有讽刺意味。“三年前,安娜已经嫁给了罗马富裕的青年画师,他说的远比画的要好得多。安娜将布罗姆菲尔德带回波士顿生活,在那里他一直继续夸夸其谈,一事无成。”(ibid.:948)显然,叙述者在嘲讽有教养的上层社会的人士时与嘲讽粗俗的拉帕姆一家时都是那么的一针见血。可是,这种反讽的口吻使读者很难确定叙述者到底支持哪一方。读者也许会进一步得出结论:作者并不希望读者不经过仔细的思考就接纳叙述者的带有阶层倾向性的判断。
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也可以从叙述者在小说早期的评价与读者在文本其他部分得到的信息之间的自相矛盾之处得到验证。“到了生意繁荣的某个阶段,拉帕姆夫人已经对她的丈夫的所有事件做了记载,但是由于他们的生意的扩大,她就不再具有妇女能够‘成功应对’事件所需要的细致的天性了,那些生意上的繁杂学问让她觉得很紧张。”(Howells,1982:888)叙述者的这一评价的确让读者倾向于相信珀西斯不具备处理复杂生意的能力。然而,这一评价又与其他地方提供的信息不相符。例如,在叙述者给出这样的评价之前,读者了解到正是珀西斯首先鼓励赛拉斯使用他的涂料,也正是珀西斯第一个指出该涂料的市场价值和定位的。“珀西斯明白赛拉斯的涂料具有不易燃的特点,所以可以利用最近好几起汽船重大的火灾事件在市场上得以热销。”(ibid.:867-868)又如,珀西斯建议赛拉斯对他们的新家制定一个最高的成本规划,不要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建设方面,而应该投向更容易安全脱身的销售上面。她嘱咐赛拉斯要远离高风险的投资等。在赛拉斯没有听她的建议而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以后,读者明白了如果赛拉斯听从珀西斯的建议,拉帕姆一家的生意一定会拥有还清债务的能力,甚至赛拉斯最终也承认情况确实是这样的。又如,当赛拉斯最后向珀西斯说出了他的财政危机时,她面对着他:“一脸严肃的表情,眼睛里充满了勇气。”(ibid.:1119)珀西斯身体体现的勇敢和坚毅似乎与前边叙述者对珀西斯做出的评价很不相符。读者并没有简单地同意叙述者对珀西斯的能力的评判,他们渐渐地明白了珀西斯也许比她的丈夫更具有生意的头脑。
笔者认为,作者是在有意地人为制造出一些前后矛盾的细节,其目的就是让读者去置疑叙述者评判的精确性,并同时借此拉开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当读者继续阅读时,读者还会发现叙事者对待赛拉斯的评价也是前后矛盾的。叙述者之前一直在贬低赛拉斯的审美能力,并且让读者对赛拉斯的审美品位形成负面的印象。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尽管故事中许多精心设计的叙述者的评价是很隐晦的,但是读者还是能够看到赛拉斯实际上是具备一定的审美品位的。比如,赛拉斯在将自己的新家与同样时尚的波士顿邻居的家做了这样的对比:“如此精美和谐的房屋令他着迷,就像那些从未受到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听到一曲美妙的音乐那样入迷。他意识到他的精美之作与那些西摩曾经在后湾指导他的时候让他注意的房屋的正面之间有着天壤之别,那些过分修饰的房屋的正面给人一种喧闹感和自以为是的感觉。”(ibid.:1151)叙述者明显地在这里将赛拉斯描绘为一个很有品位的人。这一判断与叙述者之前的判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目的是让读者意识到叙述者对赛拉斯的判断并不是完全可靠的。
笔者认为作者是在利用叙述者影响读者的判断。读者应该能够注意到,当赛拉斯经受住道德考验的时候,叙述者对他的态度变得温和了许多,也减少了歧视赛拉斯代表的下层社会的话语。叙述者在评价、态度以及用词上的转变是有显著的分界线的。叙述者对赛拉斯一家人的恶言恶语多数集中于小说的前半部分。可以说,作者在小说前半部分的意图是想向读者介绍一个虚构的小说世界,其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个完美的道德楷模。这就是为什么叙述者常常会表达对赛拉斯和珀西斯负面评价的原因。叙述者与作者之间时而出现的观点上的不同是一种写作技巧上的有意之举。叙述者就是作者用来吸引当时19世纪代表上层社会价值观的部分读者的工具,同时作者利用叙述者获得了读者的信任,引领读者相信叙述者讲述的赛拉斯的故事场景就是读者自己真实世界的一部分。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在叙述者的影响之下,读者渐渐对赛拉斯产生了敬意。此时读者眼中的赛拉斯已经成为一个在道德上发迹的普通好人形象了。他的生活有两个实实在在的目标,一个是通过合乎道德的生意来挽救他的财政危机,另一个是为他的女儿们创造幸福的生活。在赛拉斯变得越来越令人尊敬的时候,作者也让他的叙述者放弃了他的阶层偏见。读者因此被引领去更多地关注赛拉斯身上体现的优秀品质。
2 作者利用叙述接受者影响读者
“叙述接受者”(narratee)一词由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普兰斯(Gereld Prince)于1971年提出。普兰斯认为:“凡叙述,无论是口述还是笔述,是叙述真事还是神话,是讲述故事还是描述一系列有连贯性的简单动作,不但必须以(至少一位)叙述者而且以(至少一位)叙述接受者为先决条件,叙述接受者即叙述者与之对话的人。”(胡亚敏,2004:53)事实上,从该术语的字面意义上也可以看出,叙述接受者是叙述者话语的听众。叙述接受者不同于小说的真实读者,他一直处于文本之内,是作者可以进行操控并引领真实读者最终领悟其真实意图的工具。叙述接受者作为文本之内的听众(读者)在身份、评价及态度上的有意变化会影响文本之外的真实读者对小说人物的理解。比如,“当科里一家再一次回到波士顿生活的时候,是7月初了。波士顿的夏天是很容易度过的,可是,如果你很早就出城的话,那么当你十10月份回来的时候,就会觉得过了一个很漫长的夏天,但是,如果你就待在波士顿的话,就会觉得夏天稍纵即逝,好像夏天缩短了一个来月似的”(Howells,1982:976)。这段话很明显是说给上层社会中的一员“你”的。叙述接受者“你”是有身份的富有的人士。小说的场景就如同真实的19世纪的波士顿一样,只有富有的人才能负担得起到城外去避暑。笔者认为,作者试图提醒文本之外,现实当中有特权身份的真实读者意识到他们的社会评判标准与科里一家人所代表的上层社会的标准是一样的,他们的价值观不同于来自劳苦阶层的拉帕姆一家的价值观。
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赛拉斯经历了财政危机的不断加剧、良知上的挣扎以及最后道德上的升华。相应地,此时的叙述接受者的身份和态度也悄然发生了转变。叙述接受者的身上似乎多了一些平民的气质了。当赛拉斯夫妇与休厄尔交谈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自我痛苦,才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我们只不过是这个世界上不断出现的众多不幸的人们中的一员罢了”(ibid.:1084)。
显然,这段话中的叙述接受者“我们”在身份上已经从贵族变成了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人。态度也变得更平和,“我们”如同其他普通人一样,能够静静地倾听同样没有阶层身份差别的叙述者讲的故事。又如,“零零星星的事情总会激怒我们,以便我们自愿地放弃它们;这个世界以及生活本身会令我们大多数的人觉得痛苦不堪,所以我们最终很愿意高兴地与它们做个了断;这个家里充满了令我们痛苦的记忆,所以这个家里每个要弃它而去的人更多的是主动放弃而不是被迫离开”(ibid.:1190)。在接近小说尾声的这段话中,叙述接受者“我们”不仅是普通人,而且是经历了各种困难依然淡然处之、乐观向上的普通人。这其实也是主人公赛拉斯人生经历的真实写照——一个不完美的普通人实现了道德上的发迹。作者利用对文本之内的读者的控制,影响文本之外真实读者对主人公以及作品想要传递的道德观的理解,使主人公的人物形象真实、丰满。
四、结语
小说《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在叙事上独具风格。作者所要表达的道德观体现在众多人物汇成的复调之中,同时作者利用叙述者以及叙述接受者去影响读者的判断,以避免将主人公刻画成一个浪漫主义式的完美的人物形象,而失去小说的现实主义意义。小说的作者给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思考和理解的空间。身处其中的读者,需要不时地驻足思考,才不致错过美丽的风景。
[1]Barton,J.C.Howells’ Rhetoric of Realism:The Economy of Pain(t) and Social Complicity inThe Rise of Silas Lapham and The Minister’s Charge[J].Studies in American Fiction,2001,(29).
[2]Goldman,I.C.Business Made Her Nervous:The Fall of Persis Lapham[J].Old Northwest,1986,(12).
[3]Howells,W.D.The Rise of Silas Lapham in William Dean Howells:Novels 1875-1886[M].New York:Literary Classics,1982.
[4]Manierre,W.R.II.The Rise of Silas Lapham:Retrospective Discussion as Dramatic Technique[J].College English,1962,(23).
[5]Seelye,J.The Hole in Howells/ The Lapse inSilas Lapham[A].In D.E.Pease (ed.)New Essays on The Rise of Silas Lapham[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6]Young,A.The Triumph of Irony inThe Rise of Silas Lapham[J].Studies in American Fiction,1992,(20).
[7] 胡亚敏.叙述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