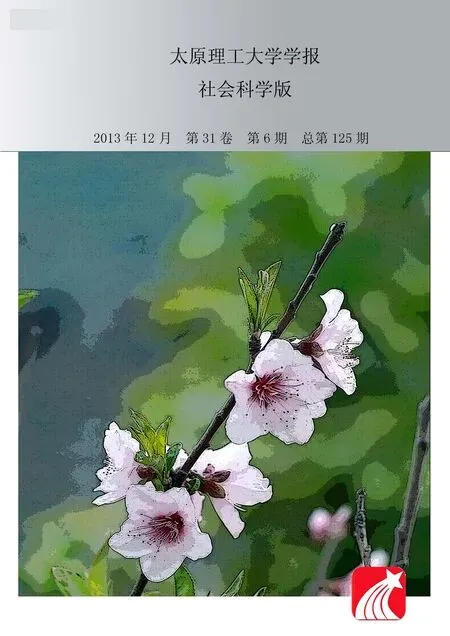消费文化中的身份建构与审美诉求
——以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为研究对象
2013-02-14赵洪涛
赵洪涛
(湖南科技学院 中文系,湖南 永州 425000)
凡勃伦作为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制度学派创始人,其理论不仅在经济学界有着重大影响,在其他领域也有着启示意义。凡勃伦对他之前的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批判,是建立在心理学和文化上的,通过对心理学基础与形而上学基础的批判来进行。他主张将经济学研究对象确定在各种现实制度上,将各种制度归结为心理分析,包含文化史、历史及宗教的内容。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其论著《有闲阶级论》之中,因此,我们可以在文化领域对他的理论进行研究,这样就不会因为专业之间的差异而产生隔膜。
一、消费文化中的身份建构
在《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论述了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阶级—— “有闲阶级”的产生及生活状态。按照凡勃伦的历史叙事,“有闲阶级”因人类的社会分工不同,即男女之间的不同分工、生产业务与非生产业务之间的不同分工而产生。非生产业务被视为是光荣的,生产业务则是身份低下的标志。凡勃伦在绪言中说:“在阶级差别中最具突出的经济意义的一个特点是,各阶级的正式业务彼此之间截然不同。上层阶级按照习惯是可以脱离生产工作的,或者是被摒于生产工作之外的,是注定要从事于某些带几分荣誉性业务的。”这里“非生产性业务”在人类社会早期不是无所作为的意思,而是迥别于耕种性的生产业务。在原始社会,受到推崇的是男性强壮、魁梧的体格与果敢、坚毅的性格,因此,男性骁勇善战的本能得到了极大发展,这表现在男性打猎和与外族争斗等非生产性事务上,男性如果染指生产性领域则会被轻视,还会伤害其自尊心。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劳动被赋予了歧视性,“劳动是受到蔑视的,因此就有了惹人厌恶的性质”[1]。那些从事掠夺、战斗及打猎事务的男性就可以获得较高的身份与地位,而从事采摘等事务的女性地位就相对低下。这种由分工的不同而决定社会地位不同的观念构成了人们的一种文化心理。未开化社会的男女分工为后来的“有闲阶级”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真正意义上的“有闲阶级”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的。根据凡勃伦的观点,所有权的产生肇始于战争中对女性俘虏的占有,战争中被俘获的女性成为男性的战利品,导致了以男性为主的家庭制度的产生。此后,居于家庭核心的男性的奴役范围不断扩大,就连同族女性也成了被奴役者。之后又从对女性的占有进一步扩大到对她们的劳动产品占有,至此,所有权产生了。私有制将对财富的占有变成了一种竞争,占有财富就会获得荣誉,“这是一个带有歧视性意义的特征”[1]。“歧视性目的”按照凡勃伦的解释,是用来形容现象的一个词,不带有褒贬之意,主要是用于人与人之间的对比,对人进行分级,评价人们的价值。在原始社会用掠夺和战争得来的战利品建构身份和获取荣誉的方式在所有权产生之后就变成了依靠财富来建构社会身份。这种转变一直存留在此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于是,人们用财富的多寡来衡量自己的地位与身份,一旦拥有的财富高于同级别社会层次的人,就会有成就感,若低于别人则感到失落。即财富使人们在心理上获得了一种社会地位。
财富需要向别人显露才能表现出自己的身份。显示自己财富有的方式就是向众人表明自己是无需从事生产劳动的,因为劳动在有闲阶层中被视为是下贱和有辱身份的事情。将“闲”作为一种不同流俗的生活方式,与消费构成了直接关系,为了向人们证明自己有足够的财富可以不从事生产活动,富人在消费方面刻意趋避与生产相关的事物,比如在服饰、家具与设备这些消费品的选择上注重它们的时尚色彩,而不是它们的实用色彩,因为实用常与从事生产有关。在日常生活中,有闲阶层会雇佣一些仆役用以消费,借助人数众多的仆役来显示自己的有闲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仆役与一般的商品并无不同。这种人力上的浪费到了后来更是在仆役性别上刻意选择。有闲阶层认为男仆比女仆更加适合显示自己的阔绰生活,“尤其是那些漂亮、壮健的汉子们,……用他们来做这件工作比用女仆更合适,因为由此可以表明在时间、人力上较大的消耗”[1]。奴仆们很少参加劳动生产,他们执行的是一种“代理有闲”的功能,意思就是他们将显摆有闲作为凸显主人富有与身份的象征,事实上这种为闲而闲的事务令奴仆们叫苦不迭。虽然有一部分奴仆从事实质性生产劳动,为整个家庭或家族的生活提供服务,但其实这些奴仆在生产之外的一定量的时间之内是被虚耗的,仍然是在被有闲阶层用来显示自己身份的存在。
在饮食方面,食物的消费也是与身份联系在一起的,这可以追溯到人类的掠夺时期。那时候,处于上层阶级的男性对某些食物的享用是垄断的,食物的消费被烙上了身份的印记。那些沉迷于享乐生活的有闲阶层不但不会受到指责,相反,因他们在饮食上的放纵而引起的某些病态体征会被人们视为“尊贵”或“文雅”的标志。不仅是饮食,在其他方面,比如住所、衣着、装饰品、娱乐品等方面,有闲阶层都是挑选最好的来消费,这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享受,其中仍然具有身份荣誉性的因素,能够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适当消费精美物品就会被认为是有身份的,不然就被看作是卑贱的。这种在饮食等方面对品质的考究逐渐影响到有闲阶层的生活方式,他们不但要懂得享受,还要学会识别这些物品,对消费品具有高度的鉴赏能力,“对有闲生活中的种种事物——……他应当成为行家”[1]。以恰当的量来进行消费就成为了衡量有闲阶层是否懂得遵循礼仪的重要标准。对这种现象,德国文化哲学家西美尔做出过解释,他认为,“每一个时尚,就其本质而言,都是阶级时尚,也就是说,每次刻画的都是一个社会阶级的特性。这个阶级以其外表的相似,对内统一联合,对外排斥其他阶级”[2]。有闲阶级在时尚追逐与礼仪考究上花费大量的精力,其意在于表明自己是无需去从事生产的,有大量时间、金钱来挥霍。为在消费贵重物品方面获得荣誉,有闲阶层相互之间展开竞争,通过馈赠珍贵礼物,举行豪华宴会等形式来实现 “歧视性目的”。
交际也具有一种身份建构的意义,这种身份建构在消费上。一个没落的贵族或富贵之家,其身家不足以维持有闲生活时,他会投奔一个财富远在他之上的富贵之家,成为其门客或扈从,消耗他过剩的财产,充当代理消费者的角色。这种代理消费需要遵循某种规则,即代理消费者需要向别人和主人表明,这种消费或有闲生活是主人所赐予的,荣誉归主人。代理消费者需要在公开的交际场合中出现,比如在宴会上,扈从或门客们的消费会使主人获得一种荣誉,因为来客知道他们的消费是拜主人之所赐,是一种明显性消费,目的就是让别人知道主人的阔绰。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不同群体间的交际变得普遍,为了借助素不相识的人进行宣传,使自己获得好名声,需要显露自己的家底,只有金钱才能使素昧平生者记忆深刻。凡勃伦认为,现代社会中明显消费的趋势更胜于明显有闲。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人们交往的圈子很小,彼此之间关系密切,人们用以彰显自己身份的方式在明显有闲与明显消费之间并没有多少差别,即不管是刻意浪费时间还是浪费金钱在成就个人的荣誉方面没有多少区别。
二、消费文化中的审美诉求
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对消费文化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审美诉求也进行了详细分析,这种审美诉求其实和有闲阶级的身份有着密切关系,之所以将这个因素单独列出来,是因为它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与意义。在明显性消费的宗教信仰消费中,凡勃伦着重谈论了消费文化中的审美诉求。在宗教信仰消费中,不论是建筑物还是其他物品,都带有刻意装饰的成分,比如庄严宏伟的教堂,精美华丽的法衣等等,这些物品不是为了让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而是在奉行金钱荣誉的原则,彰显神的伟大,因为人们认为世间僧侣的生活习惯与神的好尚之间应该保持一致性,宗教事物上的美学原则是为了强化神的不朽。在人们的想象中,神具有不凡的品质,这些品质自然是人们将人间的诸种伟大品德加诸其上的结果。那么何种生活才配得上神的品质与地位呢,“我们觉得凡是属于神性的,必然是一种格外宁静的、有闲的生活习惯。”[1]人们心头涌现出来的神在形式上的具有美学夸饰成分的环境下,笼罩在权力与金钱的光芒之中。此外,作为神仆人的僧侣在服饰上也十分讲究,他们不能在朝拜神灵时使服饰沾染上劳作的气息,这关系到神灵的身份。僧侣们在信仰消费中的美学追求与执行代理的有闲职务联系在一起,通俗一点说,他们是在替神灵挣面子。
金钱荣誉原则也影响到其他消费品的审美形式。有闲阶级在消费品美学上的诉求从很大程度上说是出于一种对金钱荣誉的考虑及显示有闲的考虑。一些日常消费品因为在形式上富有美感或者材料比较名贵就价格高昂,这不是出于实用的考虑,而是出于审美上的诉求。价格昂贵与价格低廉的消费品在使用价值上差别不大,两者价格悬殊是因为前者能够给消费者带来金钱荣誉感。消费品的美感与金钱荣誉感在有闲阶级的生活中常常交织在一起,用于荣誉消费的物品同时又是一件艺术品,荣誉感出自艺术品的美感,艺术品的形成源自于起初的荣誉消费目的,因此在生活中要想将两者截然区别开并非易事。那些具有美感的物品在动机上变成了一个诱发性因素,有闲阶级获取它,是因为它的美感具有昂贵的价格,能进一步满足自己博取金钱荣誉的需要,“高价这一准则还这样地影响着我们的爱好,使我们在对美术品的欣赏中把高价和美感这两个特征完全融合为一”[1]。
美学与高价因素的融合在衣着与家具等方面表现得比较明显。服饰在证明一个人的金钱地位方面更具有优势,人们可以通过衣着判断出他人的金钱地位。有闲阶级的穿着旨在表明自己的地位。服饰属于明显消费的对象,有闲阶层的穿戴打扮总是向人们表明这样的姿态,他是无需劳作的上流阶层,因此会在服饰上追求华美不实的款式,比如男性戴的高大礼帽,女性穿的高跟鞋,这些设计都有碍生产行为,有闲阶层这样的审美诉求无非是在与生产行为划清界限。在有闲阶级看来,服饰的审美原则应建立在金钱荣誉的基础上,背离了金钱荣誉服饰的审美效果也就荡然无存了。服饰的款式不足以成为时尚取舍的依据,人们追逐时尚的重要依据是荣誉准则,即服饰是否可以带来荣誉,它以价格高低作为标准;如果不考虑荣誉原则,仅以是否实用来衡量服饰,则很难以区分它们的优劣。金钱荣誉进一步促成了这样的消费心理:代价的高与低直接构成了审美的态度,低价的东西肯定是不美的。有闲阶层追求的是耗费大量时间和人力的消费品,因为这种物品是昂贵的,可以满足有闲阶层的金钱荣誉感与审美诉求。在消费审美心理方面,不同阶层之间对于物品的审美态度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并非简单因为物品的美感所形成的规范不同,也不是彼此在审美禀赋上的差异,而是他们在荣誉原则上的差别。我们还可以借用西美尔的一句话来解释这种现象:“价值从一开始就更实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价值的特征,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价值的主观性。由于同一个物品在一个人心目中有可能取得最高价值,而在另一个人心目中却有可能跌到最低价值上,……价值判断的依据,看起来就只剩下主体的正常或者反常、稳定或者多变的情绪和反应了。”[3]这段话的意思是价值其实是一种主观判断,它与尼采的一句名言“真理是一个价值事件”具有内在相通之处。某类物品在一个阶层中可能与该阶层的荣誉原则相称,而在别的阶层可能就违背了这个阶层的礼仪传统与荣誉原则,贸然使用这类物品会招致同阶层人们的奚落与不屑。一言以蔽之,在有闲阶级中,金钱可以弥补甚至决定物品美与不美。
在有闲阶层的消费文化中,金钱荣誉及明显有闲的准则也影响到对宠物及人自身的审美观念。比如人们喜欢豢养的宠物狗并不具有生产的能力或者辅助生产的能力,但恰是这一点可以使主人获得荣誉,即便是那些外貌怪异并不具有美感的宠物狗也丝毫不会减少人们对其的赞誉,因为外观怪异的狗属于稀少之物,价格不菲,能够给主人带来金钱荣誉,所以在人们眼里它是极具美感的。再比如赛马,属于非生产性用途,不能生利。饲养赛马的主要目的是满足主人求胜的欲望,为主人增添荣誉。在金钱荣誉准则之下,赛马在有闲阶级眼中能获得较一般的马更多的荣誉,因而更具美感,但事实上在一般人眼里赛马未必比一般的马更有美感。这种消费美学观念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提及过,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个性消费建立在符号化的基础上,脱离了事物的物质基础,人们追求荣誉过度区分,力图使自己与众不同或与别的群体不同,“这种过度区分不再通过过度张扬的方式……而是通过审慎、分析和删选的方式,……因而只是一种更加微妙的差异”[4]。在有闲阶级中,女性的美也被染上了金钱荣誉与明显有闲的色彩。上层阶级的家庭主妇美的标准是五官精致,身材苗条,手足纤巧,这种审美观念一直从骑士年代延伸到现代社会。与前面所述一样,这种形态之所以被视作美是因为它是不能胜任劳作的,属于有闲的象征,其背后是金钱荣誉。到了现代工业社会,有闲阶级女性美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女性作为代理消费者的地位有所下降,其身体各部分之美不再重要。有闲阶层中女性美标准转变背后的推动力量是金钱荣誉原则与明显有闲准则,女性要将自己的身体与代表着礼仪与地位的荣誉捆绑在一起,身体本身就代表着一种荣誉。
参考文献:
[1] [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6,23,47,60,97,102.
[2] [德]齐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61.
[3] [德]齐美尔.货币哲学[M].许泽民,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8.
[4] [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