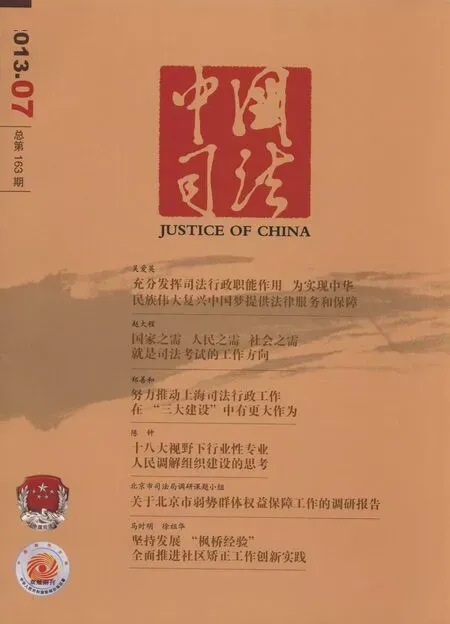关于罪犯减刑制度的探讨
2013-01-30杨习梅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教授
■杨习梅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教授)
■陈领先 (新疆兵团监狱局北野监狱)
关于罪犯减刑制度的探讨
■杨习梅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教授)
■陈领先 (新疆兵团监狱局北野监狱)
《刑法修正案 (八)》实施后,对监狱教育改造罪犯提出了严峻挑战。当前监狱刑罚执行中,减刑是最严肃也是最重要的法律制度之一。减刑制度已进行过不止一次的改革,目前仍应继续深化。
一、监狱罪犯改造与减刑现状
(一)减刑标准不够科学
目前监狱对罪犯的考核主要以计分考核为主。减刑政策原则上以考核分为主要依据,其他诸如行政奖励情况,老、病、残犯照顾,以及上缴罚金 (民事赔偿)等为辅。但部分地方的减刑办法中,考核分只能作为能否申报减刑的基础条件,与减刑幅度联系不紧密,甚至不挂钩。而罪犯日常改造的考核又以计分考核为主。罪犯会认为改造两三年挣来的考核分就换来三个月减刑,觉得不合算,而缺乏改造动力。因此,减刑政策的依据要科学合理设置。
(二)减刑随意性较大
罪犯减刑的期限都是以月计算,而且减刑的幅度与考核分数联系不紧密。在实践中经常出现分数高、行政奖励多的罪犯反而减刑少,而且没有人能给出合理的解释。减刑的计量单位是月,这也客观上拉大了罪犯之间减刑的差距,有失公允。这样的减刑政策会让罪犯找不到改造与减刑的必然联系,势必挫伤其改造的积极性。
(三)行政奖惩缺乏普遍适用性
对罪犯法定的行政奖惩大多是名为行政奖惩,实为变相的刑事奖惩,这样就难免造成重复奖惩,进而拉大罪犯之间减刑的差距,损害了法律的公平性。
1、行政奖励方面。《监狱法》规定的行政奖励有表扬、物质奖励或者记功。在监狱实际操作中还有嘉奖、各级改造积极分子等。其中仅仅物质奖励是名副其实的行政奖励,其他不过是名为行政奖励,实为刑事奖励。因为这些奖励措施最终是和减刑挂钩的,是作为减刑的依据之一,或者说可折抵减刑的刑期。如果不能作为减刑的依据,那么在现实中对于罪犯来说就失去了吸引力。这就是对于无刑可减的罪犯,行政奖励没有作用的原因。从法理学上说,它已经失去了普遍约束力,其存在的意义就有疑问了。
2、行政处罚方面。行政处罚中的警告、记过与行政奖励相似,对无刑可减的罪犯来说失去意义。而禁闭,作为一种对罪犯人身自由严厉剥夺的处罚,本身已是自由罚,还要扣分和推迟减刑。好比对一违法者同时判处行政拘留和有期徒刑,违背了一事不再罚的法律原则。合理的办法是将行政奖惩与刑罚执行变更剥离,或者采用更积极的措施来替代。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对不积极改造,违规违纪的罪犯降低和限制减刑的必要性。但应该是因扣分而处罚,不是因处罚而扣分。对减刑的限制主要应体现在考核分数中,而不是额外的处罚上,并且必须立法规范。
二、完善减刑制度路径探索
(一)提高立法规格,统一法源
减刑的规定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以及各种司法解释中,而规范刑罚执行的根本大法《监狱法》又是一个专门法,立法规格低,效力等级低。笔者建议剥离和吸纳所有零散的法条,制定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执行法》,对刑罚执行作高规格的、全面的、详实的规范。
(二)建立一元化减刑标准
当前的减刑制度中,对罪犯减刑的考量有以下几个标准:计分考核、行政奖励、老病残犯照顾、上缴罚金等。显然这一体系较为复杂,而计分考核在减刑中所占权重严重偏低,降低了减刑的严肃性和公平性。为此,应当建立一元化考评模型,把所有的这些因素,包括罪犯的社会危险性,全部予以量化,折合成罪犯改造质量考评分,建立罪犯改造质量考评模型,严格依考评分裁定减刑。新的模型尤为重要的是要加入思想改造测评系统。在心理学领域内,对心理测量和心理风险评估已较为成熟,业内已有多种测量量表和测量系统投入应用。在思想改造方面,应积极吸收和借鉴心理学领域的先进成果,建立思想改造测评系统,测评罪犯思想改造的质量,并把这一系统纳入罪犯改造质量考评模型中,作为减刑的依据。
(三)精细减刑之考评
当前罪犯减刑的单位是月,相对于法律的严肃性来说,这显然失之粗糙。建议改为按天减刑,多少考评分减多少刑,一一对应。这样罪犯就能把日常改造和减刑直接关联,罪犯每挣得1分,就知道能换成多少天数的刑期。每次犯错扣去1分,也知道到底损失了多久刑期。如此,一清二楚。这样可把减刑的激励作用大大提高。当前依法治监的实质就是依照权利义务治监。因此针对减刑这条法律,我们应该做的是对其进行细化,明确服刑人员减刑的权利和义务,使之更具可操作性。
(四)提高申报减刑的频率
大多数监狱对罪犯申报减刑一般为一年两次。这样可能造成的结果是:当罪犯考评分达到减刑的标准时,未到申报时间;或到了申报时间,考评分却差一点,都不能及时得到减刑。这一情况对于短刑期罪犯来说尤为突出。对于局外人来说,三月两月不算多久,但对于服刑的罪犯来说,每一天都是珍贵的,都是精心计算的。因此,一年两次申报减刑是不严谨的,也不利于罪犯改造。建议改为按季度申报减刑似更为合理。在条件成熟的地区,按月申报也无不可。
(五)数字化减刑,自动化管控
我国是个人情大国,这是不争的现实,而且这一现状还将长期存在下去。我们可以把前文所述的减刑标准模型数字化,制成计算机应用软件。届时,只需把罪犯的改造信息输入软件,计算机自动给出结果是否该减刑,以及减刑多少的参考数据。结合参考结果,作出相应的是否减刑的决定。
(六)减刑制度的补充
减刑是罪犯改造的最大动力,但也力有不逮之时。当罪犯被《刑法修正案 (八)》限制减刑,减刑幅度用完,或刑期太短无法减刑时,减刑就失去了激励效力。如何弥补这一缺位,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1、剥离行政奖惩与刑罚执行变更的关系,重新定义行政奖惩。在此需要重新对其进行定义和规范,剔除与刑事有关的内容,保留和补充与刑事无关的纯粹的行政内容,使其更具有普遍约束力。
(1)扩大行政奖励内涵。这里所说的是纯粹的行政奖励。可以从如下方面着手:一是处遇方面,诸如增加亲属会见、亲情电话,提高伙食标准,提供特许离监探亲。二是再社会化方面,如提供其学习培训的机会,提供其与社会交流的机会,为其推荐出监后的就业岗位。三是社会化服刑,这一措施必须在监狱分级成熟的条件下才能够实现。这些对监狱来说成本不高,但对改造罪犯来说却意义重大。
(2)严格规范行政处罚。行政处罚要取消警告、记过类的基于刑罚执行而设立的项目,建议用其他类型的行政处罚替代。比如可以增加下列种类:一是精神类的行政处罚,如训斥、点名批评、面壁思过,公开检查等。二是处遇类的行政处罚,如短期停止会见(包括通信、亲情电话),停止娱乐活动,改变工种等。三是财产类的行政处罚,如取消劳动奖金。四是人身类的行政处罚,如严管、禁闭等。对于行政处罚的使用程序应当参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制定,杜绝随意性。而且要明确救济机制,彻底扭转之前的有处罚无救济的局面。既然是行政处罚,则必须立法确认,纳入法制体系。
2、落实罪犯劳动报酬制度。《监狱法》第72条规定:“监狱对参加劳动的罪犯,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給予报酬并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该规定使罪犯获得劳动报酬有了法律依据,但当前这一规定的落实却大打折扣。暂且不论法律因素,就罪犯的改造而言,实行劳动报酬制度就大有裨益。因为在当前罪犯劳动报酬制度不完善或执行不到位的情况下,那些不减刑的罪犯参加劳动所得到的产品和功效往往与需要减刑的罪犯做交易,从中牟利。这样就形成了无形的监狱“黑市”和非正式团体。在监狱这样的环境中,有非法交易就必然滋生赌博和其他不良现象,甚至诱导再犯罪。
针对上述问题,监狱可以对罪犯的改造采取“一监两制”,即对减刑的罪犯,依据改造质量考评分减刑。对不减刑罪犯,依据改造质量考评分给付劳动报酬 (或者叫劳动津贴或改造津贴)。这样既提高了监狱产业的经济效益,也促进了罪犯改造。尤其在“首要标准”背景下意义更加明显。因为罪犯为了劳动报酬而改造时,这一改造本身就更接近社会成员自食其力的劳动,更有助于日后让罪犯进一步走向社会,融入社会,成为守法公民。
(七)落实刑罚执行中的罪犯辩护权
基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权的规定,罪犯不仅在刑罚执行变更即减刑、假释时享有辩护权,而且在服刑期间向人民检察院申诉、检举、控告时,也应当享有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要立法明确罪犯在减刑、假释案件中,享有辩护权。一方面,赋予辩护律师有与侦查、起诉阶段同等的会见罪犯和查阅案卷材料的权利。另一方面,赋予辩护律师在减刑、假释案件的庭审中有出庭辩护的权利。
(责任编辑 赵海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