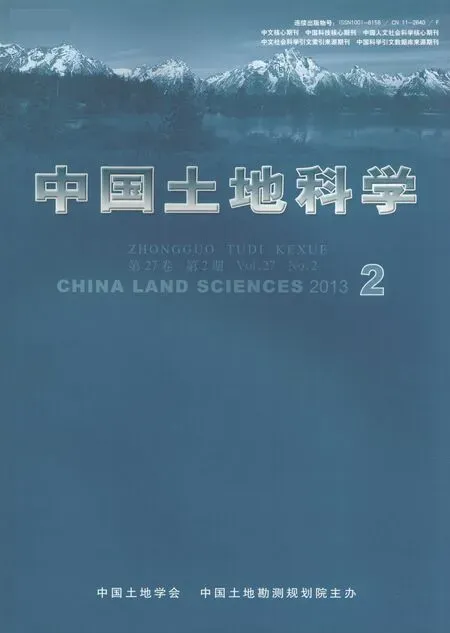试论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利益主体的缺位与错位
2013-01-30孟俊红
孟俊红
(1.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河南 郑州 450014;2. 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 上海 200042)
1 问题的缘起
近年来,拆迁造富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广东省广州市珠江新城的猎德村已建起37栋村民安置楼,若按市价,每平方米达2万元以上,其中补偿面积最大的一户有2000多m2,“身家”高达4000多万;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有三个村,配合亚运村工程拆迁,583户村民也一夜变成“百万富翁”;深圳市福田区岗厦村改造,村民大多选择房产补偿,原住户“身家过亿”的接近10个[1];河南省郑州市城中村拆迁改造让很多村民一夜暴富,上至老人下至顽童,每人都分到了200 m2的房子,折合市价百万元[2]。
与政府强制拆迁、被拆迁者的合法利益严重受损的情况相比,上述拆迁造富神话仅是个例,而且存在所谓的“财富”能否变现的问题[3],但是上述报道也的确反映了拆迁的另外一个问题:拆迁可能真的会使许多人一夜暴富。目前社会各界对待拆迁的态度不一,那种视老百姓利益如草芥的野蛮拆迁当然不能容忍,但是如果真的按照专家学者、被拆迁户所期望的那样给予完全补偿,又会发生什么问题呢?拆迁造富神话使我们不得不对完全补偿问题进行思考。笔者认为,完全补偿必须考虑三个问题:其一,完全补偿是针对被拆迁者的既得利益的,但这种利益是否合法?其二,被拆迁者的既得利益即使合法,是否都可归被拆迁人所有?是否还有其他应当分享利益的主体?其三,完全补偿是否考虑社会公平与公正问题?认真思考上述三个问题可以发现,目前的城中村改造拆迁造富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拆迁补偿中利益主体的缺位与错位造成的。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随着完全补偿理念的深入,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将会越来越突出。
2 拆迁补偿利益分析
拆迁造富神话中的拆迁补偿是以被拆迁者的既得利益为标准来计算的,那就必须对这些既得利益进行分析,考察利益界定是否存在问题,考察既得利益的构成和受益人等问题。
2.1 拆迁补偿考虑的主要是土地价值补偿
拆迁补偿一般包括房屋价值补偿和土地价值补偿。一般而言,在利用过程中,房屋等固定资产的使用价值会被逐步消耗,直到完全丧失,而土地资源,特别是建设用地资源,作为稀缺资源,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增值。因此,在拆迁补偿中必须考虑土地价值在拆迁利益中的地位,合理切分房屋价值补偿和土地价值补偿,并在此基础上按照不同的受益主体分割。
2.2 拆迁补偿中的受益人
拆迁补偿首先需要切分为房屋价值补偿和土地价值补偿,房屋价值补偿的受益人较为单一,争议不大,但是土地价值补偿的受益人较难确定。有学者认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所实现的土地收益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开发投资者、土地经营使用者和农民等参与主体共同行为的结果,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形成的土地收益应当在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合理分配[4]。笔者认为,按照产权受益和投资受益的基本原理,土地价值补偿的受益人应当为土地所有权人、土地使用权人、地方政府。
2.2.1 土地所有权人 基于产权补偿原理,集体土地所有权人——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参与土地价值补偿分配。城中村改造后,集体土地所有权灭失了,对土地所有权人自然应当给予补偿。虽然许多学者对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提出了质疑,但这并不影响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产权人参与分配拆迁补偿。许多关于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地方文件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如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试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通知》规定:为进一步加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力度,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收益,其中50%左右应用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安排,剩余的50%左右,一部分留于集体发展村集体经济,大部分仍应分配给农民。鼓励农民将这部分收益以股份方式,投入发展股份制集体经济。村集体提取的这部分利益在许多地方成为安置富余劳动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城中村改造时,城中村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权利分享土地增值利益。
2.2.2 土地使用权人 土地使用权(乡镇企业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乡村公益建设用地使用权等)是《物权法》规定的物权类型,不管是基于社会保障的宅基地使用权,还是基于公益事业的乡村公益建设用地使用权,或是基于商业化运作的乡镇企业建设用地使用权,均是通过使用过程中的收益或潜在收益来实现土地价值的。土地使用权人作为他物权人,拆迁势必会影响他们的经济利益。因此,土地使用权人也应当参与拆迁补偿的利益分配。关于土地使用权人参与拆迁补偿分配并无争议,现实中的问题是如何界定这些主体应该分得的土地补偿的份额。在中国,土地所有权是不能进入市场流通的,土地所有权均需借助在其上设立的土地使用权进入市场流通,在民法上土地使用权起着所有权的功能,土地使用权才是中国不动产的“自物权”[5]。这样,在拆迁补偿利益诉求和谈判中,土地使用权人成为主要力量,集体组织等土地所有权人由于组织虚化等原因反而退居次要位置,在拆迁补偿中经常出现土地使用权人“压迫”土地所有权人的局面。
2.2.3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参与土地补偿分配的问题一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也是有争议的问题。地方政府不是土地所有权人,也不是土地使用权人,凭什么参与土地价值补偿分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看法不一,主要有“土地增值归农说”、 “土地增值归公说”等。“土地增值归农说”的主要理由有:政府巨大的土地收益实际上是来源于农地的非农化,应主要按照“取之于农、用之于农”的原则确定土地收益的分配和使用,从而受益的主体应该是农民而不是政府[6]。“土地增值归公说”的主要理由有:(1)土地增值源于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2)地租理论。城市建设用地的土地出让金是按照城市用途产生的收益而转化来的,其实质是城市建设用地地租的表现形式,而城市建设用地的地租大部分来源于城市政府的投资经营,当然应归国家所有[7]。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投入,其产生的级差地租通过建在宅基地上的村民住宅的出租收益、转让价值而体现出来,也就是集体土地享有了城市国有土地的收益。城市功能的扩张,使农村土地大幅增值,给当地农村带来巨大的收益[8]。
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基于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参与土地增值部分的分配有一定的合理性。地方政府是公法主体,但是也可以是私法主体,不能因为他的公法主体身份而否定他的私法主体身份。不同城市的经营水平不同,地租收益也不同,这不是土地所有权人自身经营所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的“经营”行为所致。至于政府参与分配的理由,“归公说”阐述的已经很清楚,笔者不再赘述。该方面的立法例,台湾地区土地立法可资借鉴:各级政府于该管区域内,因推行都市建设,提高土地使用,便利交通或防止天然灾害,而建筑或改善道路、桥梁、沟渠、港口、码头、水库、堤防、疏浚水道及其他水陆等工程,应就直接受益之公私有土地及其改良物征收工程受益费[9]。
2.3 拆迁补偿中的违法建筑补偿问题
拆迁补偿还涉及房屋的补偿问题。被拆迁者计算房屋补偿时是以既得利益为标准计算的,既得利益的计算主要考虑房屋出租的收益。城中村被拆迁建筑的地理位置一般比较好,往往处于城郊结合部,或者就在城区。这种地理位置的优越导致城中村的租房业特别发达,家家户户基本上都靠房租作为主要收入,许多房东只是打打麻将、喝喝茶,轻轻松松收房租。但这种既得利益是合法的吗?
村民的这种既得利益与违法建筑是分不开的。村民的宅基地本来是为村民提供基础保障的,城中村的楼层一般不应超过三层。以此计算,村民的房屋除满足自住外,可供出租的房屋是有限的,但在租房利益的驱动下,城中村违法建筑大量出现,几乎家家都存在违法建筑。
与违法建筑相伴随的还有房屋出租业的监管问题。在实践中,税务、工商等管理部门往往疏于监管,导致村民应当缴纳的各种税费流失。村集体组织的监管也存在问题,村民的房租收入应当包含土地使用权的收益,村集体组织提供给村民的宅基地是保障用的,而不是投资收益用的,如果转变用途,村集体组织应当分享土地使用权的收益,但是在实践中,村集体组织的这种收益分享似乎从未实现过,老百姓对此也是闻所未闻。
3 拆迁补偿利益主体的缺位与错位
许多学者认为,城乡一体化进程应当让农民分享改革的成果,这似乎可以构成给拆迁农民完全补偿的理由,但分享改革成果是全体农民分享改革成果还是个别人分享改革成果?是让合法利益者分享改革成果还是让所有的既得利益者(包括非法利益者)都分享改革成果?部分人分享改革成果是否必然要牺牲他人的合法利益?思考这些问题,再考察拆迁补偿会发现现行的拆迁补偿特别是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问题存在明显的利益主体缺位与错位问题。
3.1 违法建筑导致的拆迁补偿错位问题
按照法理,在拆迁中对合法建筑是应当予以补偿的,对违法建筑是不应该补偿的,但土地权属不清、村民法治意识淡薄是城中村长期存在的问题,在利益驱动下,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城中村的违法建筑数量庞大。这样,在拆迁补偿中,拆迁主体就处于两难境地:如果不予补偿,则村民不会配合拆迁,违法行为的普遍性导致改造难以进行;如果予以补偿,则必将加大改造补偿成本并引发新的抢建风潮。因此,在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拆迁补偿中,大多数城市对违法建筑采取了妥协的办法,按比例进行补偿。郑州市的补偿比例可能是最高的,拆迁的补偿,原有房屋三层以下者按1∶1进行赔付,三楼以上者根据拆迁合同而定,有的按3∶1进行赔付,有的按4.5∶1进行赔付,还有少部分村庄是按面积补偿现金[2]。即使拆三补一,由于建筑成本很低,村民还是会竞相效仿、大建违法建筑,对拆迁形成巨大压力。现行拆迁补偿造就百万富翁、千万富翁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违法建筑补偿造成的。
3.2 集体土地产权关系与拆迁补偿利益主体的缺位与错位
要解决城中村改造中的利益补偿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农民与村集体财产的关系。《物权法》规定了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两种类型,村民对集体财产是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学界对于该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部分学者认为应当是共同共有关系,但是从村民加入村集体组织不需要支付任何代价、退出村集体组织时无权请求分割集体财产来说,共同共有关系无法解释村民的成员资格问题。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种关系更接近于“总有”关系。所谓“总有”,谓并未赋有法律上人格之团体,以团体资格而所有物之共同所有,依团体统制之规范,(村民)按其身份之得丧,而其权能亦随同发生与消灭,不得离开身份而就其权能为继承让与或处分,其物之管理处分,属于团体之全体的权能,各团员无请求分割权[10]。亦即,“总有”中团体的成员身份相对确定但不固定,团体的成员因取得成员身份而自然享有权利,因丧失成员身份而自然丧失权利。自然人加入某一个成员资格不固定的团体时,对其他成员的现有财产权利必然有所损害,但是依“总有”的法理,其他成员却没有对新成员的加入行使否决的权利[11]。从法理上分析,中国的农村集体组织与这种“总有”组织非常相似。基于总有关系,拆迁补偿时首先应当补偿的是村集体组织,然后让全体村民受益,但是在城中村改造时,村集体被改造掉了,“总有”关系在现实操作中被当作按份共有关系(村集体组织成员人均一份)处理,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补偿利益的缺位与错位问题。
3.2.1 土地所有权人补偿的缺位 城中村是一个类型独特的社区,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生存的依赖之源是土地和物业。村民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村集体经济分红、出租屋收入以及小规模的商业。如上文所述,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权人,在拆迁补偿中应当参与土地补偿的分配,但在许多城中村改造时,村集体组织被改造掉了(一般都改为社区,但城市社区一般被认为是缺乏自由财力的自治机构)。缺少了这样一个保护农民集体利益的“壳”,本该由集体组织分享的利益却转化为宅基地使用权人独享。这也是村民以此向政府讨价还价的理由:既然村集体没有了,土地就是我的,补偿就必须全部归我。
3.2.2 村集体组织成员受补偿利益的错位 在集体经济框架下,农民占有宅基地并不需要支付对价,是基于福利性质的无偿取得。由于各种原因,宅基地的分配肯定会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在土地为集体所有的情况下,集体土地出让的收益归村民享有的那部分为全体村民共享,这种矛盾被掩盖。城中村改造时,合理的做法应当是:合理界定每户村民应当享有的宅基地,对于超占的、不合理的部分应当收归村集体,将不公平、不合理的既得利益收归集体,但现实中基本上是按照村民占有的实际面积进行补偿。由于按照实际面积给予补偿,本该由村集体组织享有、间接由全体村民享有的那部分增值利益直接由宅基地使用权人独享,原来被掩盖的矛盾凸显出来,即:谁违法占地多,谁获得的补偿就可能多。
3.3 拆迁补偿利益主体缺位与错位之后果
这种利益补偿主体的缺位与错位导致的结果是:(1)地方政府利益受损,国有资产流失。政府想方设法要弥补这份损失,就会通过非法渠道(强拆等)获得土地收益。(2)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平,本该由全体人民分享的改革成果却由个别地区、个别人,甚至是违法占地、违法建筑的个人分享,造成严重的区域贫富分化。(3)产生了一大批“食利阶层”,严重偏离了宅基地使用权以保障村民最基本居住需求的社会保障功能[7]。一些大城市的城中村农民,因拆迁而骤富,因富裕来得太快和太容易,许多转型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受到极大冲击,少数人过起了游手好闲、斗富比奢的日子。
4 问题解决方案
解决拆迁补偿中利益主体的缺位(集体组织)和利益主体错位的问题,关键是解决集体土地所有权问题。目前有国有化主张、私有化主张和折中说三种主张。国有化、私有化均可以使土地主体明晰,但是国有化经济成本过高,私有化与中国国情不符,实不足取;折中说较为可行。傅鼎生教授分析了城中村改造的各种方案:强行改变“城中村”农民的身份,撤销农民集体建制;打破征收条件的限制,允许国家征收“城中村”农民集体的土地;在《物权法》中增加集体土地“进城”自动改变权属的物权变动规则;打破城市的土地属于国有的限制,允许农民集体的土地进入城市,最后得出结论:应允许农民集体保留“城中村”土地所有权,让农民参与城市建设[12]。笔者认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直接入市流转是理想的目标,但当务之急是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以解决利益主体缺位与错位造成的拆迁补偿不公平问题。
首先,政府参与土地增值分配的途径应当多元化。政府参与土地增值分配可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土地增值税的经验。英国为解决农地开发收益分配的公平问题,以课征税赋的方式实现征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早在1427年,亨利六世在英格兰授权对于地主的土地因海堤围筑而形成的增值,以课税方式予以归公;1947年的城乡规划法规定,土地所有权人或开发者,应对开发价值交纳100%的开发税;1965年,又制定了资本利得税,对土地买入、卖出的差价征30%的资本利得税;1967年,土地委员会制定改良税代替资本利得税,对开发净价值课征40%的改良税;1973年,制定开发利得税,对土地投机行为进行限制;1976年,工党政府开征开发土地税,税率为在不同起征点(5万英镑和7. 5万英镑)的60%比例税[13]。除了土地增值税制度,地方政府还可以借鉴台湾地区征收工程受益费的方法参与土地增值分配。工程受益费与土地增值税的理论基础是不同的:工程受益费的理论基础是初次分配中的投资受益;增值税的理论基础是政府强制无偿地用税收方式分配土地增值部分,以维护社会公平。因此,政府征收土地增值税是基于公法行为,征收工程受益费更多地是基于私法中的投资受益,二者可以并行不悖。
其二,完善拆迁补偿利益分配格局。现行体制下城中村改造时补偿利益主体的缺位与错位实质上是拆迁补偿设计的缺陷问题。如上文所述,拆迁补偿的利益主体应包括集体土地所有权人、集体土地使用权人、地方政府。完善拆迁补偿制度的前提是建立科学的土地价值评估体系,合理切分房地产价值中的房产价值与土地价值。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人,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建设用地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应该分配收益。集体土地使用权人在获得使用权后不断地增加对土地的投入、长期进行经营,分配收益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超占、违法占用的土地应做合理界定,将该部分利益补偿给集体,以社会保障的方式让全体村民受益。地方政府配套设施的投入,可以借鉴台湾地区工程受益费的方法分享土地增值,并专款专用继续投入到市政设施建设中去;以增值税方式分享的土地增值可用于维护社会公平方面的投入。中国目前开征土地增值税,但由于影响增值的因素很多,且程度不是很容易把握,所以应加强土地资源的评估工作,研究和总结一套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土地价值(价格)的动态变化准确掌握[14]。
其三,应当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对于违法建筑要从源头抓起,发现一起处理一起,不要等规模大了再去处理,形成尾大不掉的问题,对于城中村房租收入,要加大税收征管力度,通过税收维护社会公平。
(References):
[1]那烂陀. 拆迁“千万富翁”是个伪命题[N]. 羊城晚报,2010 - 08 - 22(A05).
[2]李凌,李杨,司新利. 一夜暴富不是梦 郑州城中村拆迁将造就15万个百万富翁[N]. 东方今报,2010 - 03 - 30(A05).
[3]佘宗明. 过度渲染的“拆迁致富”幻觉[N]. 江南时报,2010 - 08 - 20(11).
[4]张娟锋,刘洪玉,贾生华.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合法化:中国土地制度创新的战略选择[J]. 软科学,2010,(5):1 - 5.
[5]高富平. 土地使用权和用益物权——我国不动产物权体系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17.
[6]李龙浩. 土地问題的制度分析[M]. 北京:地质出版社,2007:241.
[7]阮梅洪. 宅基地价值化:一个义乌样本的观察与思考[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6.
[8]郭振维. 城市化进程中“城中村”改造问题的研究[D]. 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06:10 - 11.
[9]杨松龄. 实用土地法精义[M]. 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513.
[10]史尚宽. 物权法论[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53.
[11]孙宪忠. 中国物权法总论[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6.
[12]傅鼎生. “入城”集体土地之归属——“城中村”进程中不可回避的宪法问题[J]. 政治与法律,2010,(12):17 - 27.
[13]张丽,王永慧. 征地收益分配制度的国内外比较研究[J]. 兰州学刊,2007,(12):54 - 56.
[14]梁学庆. 土地资源学[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