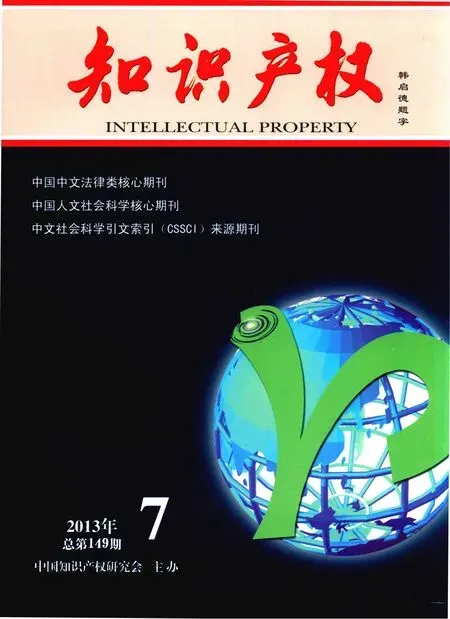药物专利VS公共健康:从冲突到共存
2013-01-30左海聪
宋 阳 左海聪
知识产权制度是西方文明走向繁荣与强大的根本基础,也是人类制度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以来,知识产权制度被纳入到了国际贸易体系下,成为国际经济制度的重要一环。但是,该制度在给世界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十分严峻的“人权危机”,如何理解和反思这种危机,显然是一个颇为重要的课题。
一、药物专利与公共健康的制度冲突
根据《TRIPS协定》序言的规定,知识产权被定义成一种“私权”。《TRIPS协定》要求通过在一定时间内赋予权利人对知识的“垄断”,来刺激社会对于知识的投入。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专利权的客体既然以“知识”为标的,那就必须考虑其公共物品属性。在专利制度出现以前,在不考虑传播能力的前提下,知识是作为一种“最优注入公共物品”(best-spots public goods)而存在的,发明与点子应毫无例外地造福全人类①对于知识和发明的公共物品特性,杰佛逊论述道:如果说大自然有创造一种比其他事物更少受到专有财产影响的事物,那就是点子,当点子释放出去之后,它就会强迫自己成为每个人的财产,而且接收点子的人也没办法强将之夺取私有。就像是一个点燃我的火柴的人,是在没有让我变暗的情况下接收了光线。那样的想法应该自由的散播到全球每个人身上,像是火,火可以扩散到许多地方而不会在任何方面削减它的密度。而像是我们呼吸、行动、存在的空气,也没有办法被限制或者是独自占有。转引自James Boyle, The Public Domain: Enclosing the Commons of the Mind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at17-19。。公共健康和贫穷人民的生命显然是人类所最需要满足的最大诉求。
对于专利权与公共健康权的关系,学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两者之间从根本上来说是冲突的;另一种则认为两者之间从根本上是一致的②Laurence R. Helfer. Human Right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nflict or Coexistence? , Minnesota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view, 2003, at48-49.。对此,本文认为,虽然从宏观和长远来看,对专利权保护的加强确实可以有效地通过时间界限和权利用尽制度来平衡社会的公共需求与私人财产权利之间的关系;不过从现有的证据出发,在现阶段两者之间的冲突是明显的。对药品专利保护的加强会产生一种“权利的溢出效应”,导致知识与科技的发展不但不能满足最贫困国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反会让他们背上沉重的负担③Keith E. Maskus and Jerome H. Reichman. The globalization of private knowledge goods and the privatization of global public good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2004, at285-286.。另一方面,对于贫穷的国家而言,那里人民的健康权作为一种具有经济与社会性质的人权,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医学技术作为一种公共物品来有效地进行供给才能得以实现,这样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实现公共健康权的制度之间便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正是由于药物专利制度所带来的这种“雅努斯之面”(the faces of Janus)效应,在制度构建方面,国际社会中会因为对于制度需求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同时正是由于药物专利所带来的复杂社会效果,会促使这些集团为了达到其自身的目的,获取自身利益,通过不同的渠道去影响国际社会中相应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二、国际知识产权造法过程中多元利益集团的博弈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任何立法的政策选择过程都是利益群体博弈和妥协的产物。如前所述,知识产权制度从本质上是公共物品转变为私人物品并且市场化的过程,那么这就必然涉及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与公共物品属性由于划分而产生的利益分配问题。在此过程中,由于利益配置不可能自发地达到平衡状态,因而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来试图影响政策走向,并出现了三类利益集团。一个利益集团以发达国家的制药寡头为代表。他们财力雄厚,有着对国家政府极强的游说能力,而他们的母国政府往往是政治、经济实力强悍的发达国家,在国际谈判的舞台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及控制力。在他们的主导下,国际知识产权造法很明显地出现了一种竞相逐高的趋势,这被国外学者称为知识权利主体的“圈地运动”。他们借助其母国的强大实力在与作为第二类利益集团的发展中国家的博弈中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以至于使得两种利益集团出现了“事实上的共谋”(de facto conspiracy)。不过,国际市民社会中的人权组织作为第三类利益集团,则与之针锋相对,强调知识产权的国际造法必须平衡知识产权的私有性与公共健康的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主张限制药品知识产权的垄断属性。在药物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权的实现问题上,最终的结果取决于两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态势与结果。
(一)制药寡头利益集团与国际硬法机制对健康权实现的不合作博弈
随着跨国经济交往的不断加深,知识产权造法活动受寡头利益的影响,呈现出逐步递加之效果和 “单向棘轮”(one-way ratchet) 之特征,这也被学术界称为对知识产权公共领域的“圈地运动”。例如,《巴黎公约》仅仅试图通过建立成员国之间的“非歧视性”专利保护体系来取消对外国专利不公正待遇。但是,《TRIPS协定》则采取了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该协定试图建立一种“全体成员一体均用”(one-size- fi ts-all)的超级体制④James Boyle. A Manifesto on WIPO and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Duke Law and Technology Review, 2004, at3-4.,强制所有成员方对于满足发明的技术方案都纳入专利保护范围,同时对强制许可进行严格的限制。此外,该协议将“利用化学个体成分”的数据纳入到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之内,使得制药寡头可以通过制药配方的数据控制来限制他人研制类似的通用药物,以达到对新型药物进行垄断性掌控的目的⑤Peter K. Yu. The International Enclosure Movement, Indiana Law Journal, 2007, at858-862.。然而发达国家的制药寡头仍不满足,他们通过劝说其母国政府通过区域贸易协定方式将超TRIPS机制(TRIPS-plus)义务施加于发展中国家成员之上。此类机制更加强调知识产权保护义务的刚性及严厉性,同时进一步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和保护力度以限制不发达国家专利制度的自主性。国际机制之外的单边措施也被发达国家用来保护制药寡头对药物专利的垄断力度。例如,欧盟通过其规范立法,授权欧盟成员可以不加提前通知,没收任何侵犯欧盟专利的过境产品,2008年到2009年间荷兰海关根据此规定,没收了大量销往尼日利亚的ARV通用药物⑥Monica Rosina and Lea Shaver. Why Are Generic Drug Being Held up in Transit? Journal of Law, Medicine & Ethic, 2012, at.197-201.。美国则强调,只有在发生公共健康危机时,才可以为了满足本国公共健康危机的需要对必需的药物采取强制许可措施。对于其他疾病,必须一事一议充分论证其必要性后,才可以考虑采取强制许可措施。总之,只要发展中国家的专利保护水平低于他们期待值,他们就会通过各种手段强迫发展中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确切地说是按照制药寡头的意志行事。
对此,有学者指出:“知识产权不可能对所有的国家提出完全一致的要求,而不考虑具体国家的本地需求、国家利益、技术水平、制度能力以及公共健康的需要。因此,给予《TRIPS协定》以必要的灵活性是必须的”⑦Peter K.Yu, The Objective and Principle of Trips Agreements, Houston Law Review, 2009, at980-981.。那么,该协定中第7条和第8条作为灵活性条款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这两条规定由于利益群体的影响而制定得过分原则,且被施加了很大的限制,最终造成了“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的尴尬结局。以第8条为例,该条规定:成员方有权在制定国内规则时采取措施促进其公共利益,但同时又规定“此类措施需与协定的其他规定相一致,且限于其本国之公共利益”。由此,在加拿大通用药品案中,针对加拿大提出的对该条款的援引,专家小组支持了欧盟所谓“公共健康、营养和其他公共利益应低于智慧财权的保护。此忽略该条主要在于确认会员的裁量空间的理解系误解该条之本旨,应不足採。⑧倪贵荣:《WTO 会员设定强制授权事由的权限》,载《台大法学论丛》2010年第3期,第409页。”的主张,采取了一种对于专利权极度偏袒的态度,甚至推翻了其在牛肉荷尔蒙案中所确立的“存疑者义务从轻”的原则,将《TRIPS协定》中第30条所规定的有限例外解释为“有限制条件下的例外,而不是对专利本身进行限制的例外”。进而实质上架空了作为基本原则的协定第8条所试图建立价值导向⑨Robert Howse, The Canadian Generic Medicines Panel: A Dangerous Precedent in Dangerous Times, Journal of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2000, at496-498.,从规则上对保障国际健康的药物的输出起到了阻碍作用。
透过上述现象,我们认为,之所以会出现整个国际法律机制的造法进程如此偏向于跨国制药寡头和发达国家利益的情势,从根本上来说源于现有的国际机制所产生的公共选择效应。个人的行动目标在于使其利益最大化,而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个人所组成的利益集团会影响国家的公共决策,对于政策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三个因素:1. 集团组成个体的多少,个体越少组织能力越强;2. 利益诉求强弱,通过影响政府决策的结果如果能给利益集团成员带来更大的潜在利益回报,那么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选择的动力便越强;3. 利益集团的经济实力也是其影响公共选择能力的根本决定因素。而国际制药寡头群体完全满足以上三个条件。一般认为,强势利益集团可以使用两种方法来实现增进其成员利益的目的,一种是通过对社会福利的增加来使得其获利更多,另一种则是在现有的福利规模下,为其成员争取更大的份额。经验表明,利益集团几乎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第二种策略选择⑩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因为这种选择对于他们来说是回报率最高以及最节约成本的,由此其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
与此相对应地,作为国际硬法机制中博弈的另一方的发展中国家,处于明显的劣势,他们缺乏与代表制药寡头利益的发达国家平等谈判的实力基础。且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公共健康以外,往往还有许多其他的政策诉求。比如,发展中国家急于扩大本国的外贸出口以换取更多外汇。那么在WTO一揽子总括谈判的基础之上,发达国家大可以通过施以减让关税增加发展中国家出口配额来换取发展中国家的妥协。另外,发达国家还可以采取对发展中国家分化瓦解的策略。例如,生产抗艾滋病等热带疾病药物的国家,可能其本国的公共健康问题并不严重,他们生产通用药物的动机仅仅是为了透过低价获取他国的市场份额,缘此,贸易制裁和政治压力会使这些国家很容易地进行妥协。总之,目前国际机制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之所以出现竞相逐高的棘轮效应的根本原因,在于“成员导向”的立法机制以及发达国家与贫穷国家的谈判实力的巨大差距,这导致作为富有强大的跨国制药寡头对弱小贫困人民健康权利的压制与剥夺。在国际硬法机制中,代表保护药物专利的制药寡头和作为其利益代表的发达国家处于一种绝对优势的地位,而发展中国家作为博弈的另一方却处于动力不足和组织不力的尴尬境地。在这种博弈环境中,本该相互竞争的两类利益集团出现了“事实上的共谋”,发展中国家并没能起到制约发达国家内部利益群体抬高对药物专利的保护水准的作用,反而成为使这种恶法获得正当性的帮凶,造成药物专利的国际制度对于公共健康实现的不合作特征。
(二)国际民间组织对于国际知识产权制度转移所作出的努力
如前所述,传统的国家导向的国际机制面临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在这种机制安排下,任何规则的形成都无不依赖于成员方之间的谈判所达成的协议。这就必然面临所谓的集体行动问题,各成员要想取得一致,必然要进行交易和妥协,但是这种交易和妥协是以牺牲第三方和公共利益为代价的。此外,在交易的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强国的权力导向和利益集团制度捕获的现象。此制度缺陷的负面效果是知识产权过度保护和对作为一种经济社会人权的健康权的选择性无视。为了缓和这种矛盾,国际社会正试图通过“制度转移”(regime shifting)来建立“位于国家间经济政策和协议之上”的人权义务(11)Laurence R. Heifer, Regime Shifting: The TRIPs Agreement and New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making ,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4, at.49-50.,在这个过程中非政府的民间组织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具体而言,首先,各种非政府组织可以作为诉愿渠道来影响正式国际组织的立法与司法活动,在WTO成立不久以后所发生的的荷尔蒙案、海龟与海虾案和南非国内法院审理的Hazel Tau v.Glaxo and Boehringer案中,司法机构都听取了环境保护和艾滋病患病团体等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并把他们的意见作为一种证据事实来作为最终断案的根据。其次,非政府机构正在逐步创造与正式国际法规则配套的非正式的二阶规则,厘清发达国家利益群体侵犯国际公共健康权的具体标准和行为表现,极大地丰富了人权法的内容(12)Wolfgang Hein and Suerie Moon, Informal Norms in Global Governance: Human Righ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ules and Access to Medicines ,Ashgate Publishing, 2013, at52-53.。第三,他们还会引导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开辟“第二战场”,建立起与现有知识产权国际体制相抗争的条约体系(13)Laurence. Helfer, Toward a Human Rights Framework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UC Davis Law Review, 2007, at1007-1008.。
不难发现,传统的国际政策选择机制是以国家成员为导向的,这种导向的最大弊端在于由于公共选择效应的出现,而被少数利益群体捕获,从而在制度上劫贫济富,忽视了世界上最贫困人群的基本需要。这与人类正义观念和国际机制规则导向的初衷是不相容的。但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民间组织机构正在发挥一种与这种少数利益集团对抗的作用。他们不分国界,通过各种诉愿以及起草非正式法律文件的方式组织起来,通过建立与国际硬法机制相抗衡的新的规则体系来促进公共健康的实现。
相对于传统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由于这些民间组织不是正式的国际法主体,所以在他们头顶上没有那么多的政治压力和国际义务,他们所提出的诉求和议案在现阶段可能会反映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真实问题和具有良心的解决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国际经济法体制出现的民主赤字和正义赤字。西雅图的抗议浪潮以及世界各国人权组织的游行示威活动,使得国家政要们不得不去关注社会民众的诉求和他们提出的方案。这种体系化的非正式的规则形成以及强大的舆论和道义压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将目前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对公共健康权的不合作博弈转换为斗鸡博弈,迫使发达国家的利益群体做出一定的让步。美国撤回在WTO对巴西专利保护措施提起的诉讼和“多哈宣言”的通过就是最好的证据。
三、构建药物专利与公共健康权之间的良性权利生态
由于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利益的分化产生了诉求针锋相对的利益集团,他们之间进行的博弈,从客观上促进了公共健康权利的实现。但从制度主义视角来看,通过博弈而建立的秩序平衡只是一种初步平衡的秩序。这种平衡在某种程度上是不稳定的,很容易随着博弈双方力量的此升彼涨而发生变动,尤其是在复杂的多元博弈下更是如此。人们在进行制度选择时,往往有一种将自我利益无限放大的趋势,从而挤压其他社会主体的权利空间。受到权利挤压的一方,便会通过其他途径对这种压迫进行反制,最终造成不同规则体系之间的冲突。当代表一种利益的势力规模壮大到一定程度时,便会对另一方所提出的规则体系发起进攻,并试图让对方做出妥协,这点在国际药物专利制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以《TRIPS协定》为例,该协定更多体现了发达国家和制药寡头群体的利益,为了维护他们今后的利益,其必然会想方设法将其他对其不利的非WTO规则排除于机制之外。于是他们强调,WTO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法律规则体系,WTO体制不得适用WTO规则之外的其他任何规则,包括非解释条约的一般国际法规则。换言之,WTO体制无帮助实现国际公共健康权之义务(14)Gabrielle Marceau, WTO Dispute Settlement and Human Right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2, at781-P784.。但这种对于WTO规则的狭隘解释既不能解决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国际公共健康问题,也不能够缓解现有体制与国际民间组织和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巨大矛盾。因此,传统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正当性质疑,必须考虑对该法律制度进行重构,平衡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使各方利益能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我们注意到,对于国际药物专利保护和健康权之间关系的构建上,很多学者都采取了一种“矫枉过正”的态度。例如,Petersmann教授从普世的人权主义出发,提出现有的国际经济法机制必须抛弃传统的国家导向的老旧范式,强调要将人权保护作为所有国际经济法规则之圭臬。通过对包括健康权在内的普世权利的保护来解决目前国际机制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缺陷(15)Ernst Petersmann, Methodological Pluralisms and Its Critic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Research ,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2012, at935-937.。Forman教授则从规则着眼,认为《联合国人权宣言》第25条和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和第15条具有国际强行法的性质,世界各国有义务实现最不发达国家国民的公共健康权利(16)Lisa Forman, An Elementary Consideration of Humanity? Linking Trade-Relat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o the Human Right to Health in International Law , Journal of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2011, at157-162.。Hestermeyer教授更是将这种义务扩展至私人主体,认为制药企业同样具有该项义务(17)Holger Hestermeyer, Human Rights and the WTO: The Case of Patents and Access to Medicin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at96-97.。我国学者则强调从价值角度来看,健康权作为一种道德权利具有当然高于作为一种财产权利的知识产权的价值,药品的需求关系到人的健康权这一基本人权,那么获取必需药品的规则就必然高于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则(18)贺然:《知识产权与健康权的冲突与协调——以TRIPS协定为视角》,载《苏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72页。又见宋慧献:《冲突与平衡:知识产权的人权视野》,载《知识产权》2004年第2期,第55页。。
以上观点都有可取之处,但都有将两类权利关系简单化之嫌,强调公共健康的重要性并不能想当然地认定两者孰高孰低。首先,我们必须从观念上树立价值多元的价值判断体系。现代社会关系强调对多种利益的理性刺激与调整,在构建规则体系时必须强调不同权利价值的合理边界。药品专利权与国际公共健康权的根本冲突不在于两者之间的价值位阶的高低,而是如何协调社会活动中两类完全不同的行动逻辑,如何化解经济理性规范与卫生语境中形成的规范之间的矛盾。必须对两类规范在现有法律机制下进行有效的沟通,来确立两者之间合理的动态的权利边界,在此过程中两类权利规范必须保持一种有沟通的自我限制状态,防止任何一种权利过分膨胀,进而造成一类利益群体通过制度变迁来压迫另一群体现象的出现(19)[德]贡特尔·托依布纳:《匿名的魔阵:跨国活动中“私人”对人权的侵犯》,高鸿钧译,载《清华法治论衡》2007年第2期, 第291~312页。,最终确保构建一种良性的权利生态,使每种利益都能够在新的法律机制框架内得到尊重与实现。
此外,从制度上来说,虽然构建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机制不太现实,但可以考虑在国际知识产权造法活动中,通过对公共健康权规则渐进地“柔性引入”,将多元的价值诉求嵌入到国内造法以及国际造法的规则中去,从而使两个相互冲突的权利透过制度缰绳分别被向反方向拉开,最终建立一种多层次的动态的知识产权协调体系,实现将多元的利益诉求有效协调的目的。应考虑积极展开有关健康权问题的谈判,适当降低治疗热带疾病专利药物的保护水平,同时进一步强化《TRIPS协定》中有关公共利益的条款,尤其当发生公共健康危机时,应简化和减少治疗对应疾病的药物的强制许可程序和限制。通过构建药物与医学信息的共享机制,对于药物的制造方法和生产流程的专利授予范围和条件进行限缩和限制。对于药物成分的数据,除非研发者能够证明使用者是为了不正当的商业目的来使用该数据,否则对药物成分个体的使用应认定为合理使用。
更为重要的是,在现有WTO体制中,各个协议都给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解释条约留下了充足的空间,这也构成争端解决机构通过裁决来实现国际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法律空间。同时作为WTO体制所借助的解释工具,《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也要求对条约进行善意解释、整体解释,必须充分考虑当事方的缔约意图和条约的解释结果。那么这就要求我们从解决全球公共健康这个大背景出发,充分认识药物专利过分保护所带来的社会福利缩减的后果。考虑在争端解决机制中,从某种程度上适当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限制,尤其是在《多哈宣言》通过以后,必须考虑该宣言对《TRIPS协定》规则解释所产生的指示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应当认定该宣言赋予WTO所有成员方为实现公共健康权利而保留对知识产权进行限制的权力,即便是与《TRIPS协定》其他规则的义务相冲突,只要没有超出比例性原则的限制,其他缔约方必须忍受为实现国际社会公共健康而对药物专利权进行限制的特别豁免。此外,鉴于WTO绝大多数成员都批准了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那么这同样可能构成“证明当事方缔约意图的证据”以及“当事国间因缔结条约所订与条约有关之任何协定”。最后,在解决WTO规则下知识产权争端时,必须发挥司法能动性,将《TRIPS协定》其他条款和该协议第7条和第8条,以及GATT第20条的一般例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善意地综合性解释。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成员应当在审理过程中将实现国际社会的公共健康这一价值目标作为得出结论的重要考量依据,并应该积极听取相关利益主体,尤其是致力于解决全球健康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的意见。
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应该对药物专利权给予必要的尊重,防止药物强制许可和通用药物贸易被滥用。例如,应该明确界定可以免费强制许可生产的为缓解国际公共健康问题之热带病药物的类别范围,以及ARV药物的类型和种类;同时,限制通用药物的销售国别范围,防止通用药物回流到其他非必需国家市场。再者,相关制药商的母国政府和通用药物生产国政府应本着一种负责任主权的态度对因专利强制许可而遭受损失的制药公司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偿(20)左海聪:《超越“国家利益”对经济主权概念的反思与重塑》,载《学术界》2013年第4期,第45页。。总之,通过一种利益沟通和自我限制使各方利益主体在不受到过分损害的前提下均摊解决国际公共健康问题的成本还是可行的。
结 论
在经济全球化以及知识大爆炸的今天,知识产权作为刺激人类创新力的制度显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种权利的行使与保护同样必须考虑其所产生的外部社会效果。贫困落后地区的生命健康权作为一种人权应当得到善良法律机制的尊重和满足,那么,通过对药物专利的适当限制实现该种人权就应该是必需的。当然,这种牺牲也不能被无限放大,必须通过理性协调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与诉求来使得各方权利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圆满状态。国际社会的每个主体都应该以一种负责任的行为模式来进行彼此之间的权利沟通与限制。那么,通过对现有WTO国际机制的善意解释和能动地重塑显然是一条较为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