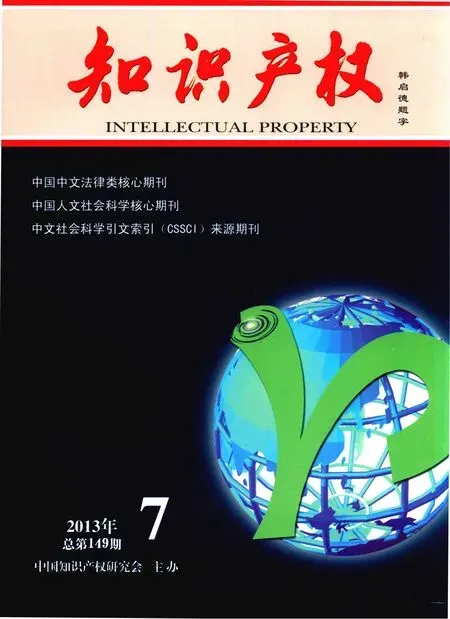对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反思
2013-01-30李庆保
李庆保 张 艳
著作权的合理使用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经著作权人的许可,也不必向其支付报酬而对使用其作品。其目的就是在智力产品所涉及的三方利益之间,即在作者的利益、利用该作品的企业的利益与广大公众的总体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公正合理的妥协。①德利娅·利普希克:《著作权与邻接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66页。还有学者认为,合理使用是著作权法中激励创作与接近作品之平衡。②参见冯晓青:《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之正当性研究》,载《现代法学》2009年第4期,第31页。然而,社会的发展、技术的巨变,打破了现行著作权法合理使用制度所建立的作者、使用者与公众间的利益平衡,亟需法律作出回应。国家版权局2012年先后两次公开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以下简称“《修改草案》”)中都涉及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修改,引致社会的广泛关注,体现了我国《著作权法》适用多年来所暴露出的一些不足。但是,这些修改仍不能满足我国著作权制度中著作权人、利用人和公众的需要。本文将对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与两《修改草案》中合理使用制度的相关条文进行比较,反思现行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范围、立法模式、一般条款与具体列举等几个方面的缺陷,兼评两《修改草案》中的相关条款的利弊优缺,并对重构我国的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提出建议。
一、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适用对象的完善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在规定情况下,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传统上认为合理使用制度仅适用于著作财产权利,不适用于著作人身权。我国秉承了大陆法系对著作权性质的认定,认为作品系作者人格的体现,著作权应分为著作财产权和著作人身权,著作人身权属于人格权,不可剥夺,不可转让,永久保护。作品的合理使用只保障公众合理地接近作品、创作新作品的机会,只涉及著作财产权,无需限制著作人身权,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因此不适用于著作人身权。此规定在著作权发展的早期阶段带来的问题尚不突出,但随着著作权保护范围的扩大,技术进步产生的作品利用方式的多样化,该规定就限制了公众对作品的接近和利用人对作品的合理利用。各国纷纷修改立法,放松了著作人身权排除适用合理使用的规范。如德国《著作权法》规定,应允许他人依诚实信用原则对作品适当改动,只有对作品的歪曲将危及作者合理的智慧利益和人格利益时才构成侵权,对于视听作品则必须是重大的歪曲才构成侵权。③德国《著作权法》第93条。计算机程序的使用人出于使用目的(如改正错误)而采取的必要行为无需取得权利人许可。④德国《著作权法》第69d条。日本则规定:首先,当未发表的美术作品或照片原件转让时,当电影作品的著作权属于电影制片人时,作者不得反对作品的发表;其次,根据作品使用的目的和性质,无损于作者要求承认自己是作者的权利,且不违反公共惯例时,可省略作者的姓名;再次,作者不得反对出于学校教学的目的对作品仅作不得已的字面改动,不得反对由于建筑物扩建、改建、修缮或装饰外观所做的改动,不得反对为了在计算机中使用或更好地发挥功能而对计算机程序的改动,以及不得反对其他依作品性质及使用目的或形式所做的不得已的改动。⑤日本《著作权法》第18条第2款、第19条第3款、第20条第2款。
《修改草案》第一稿第40条和第二稿第42条中都有“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作品出处,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的语句,看似对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是否适用著作人身权持相同的态度,但《修改草案》第一稿第39条中规定“不得不合理地侵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为合理使用制度适用著作人身权留下了空间,只要不是不合理地侵害著作权人的合理权益即可,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是包括著作人身权的。但《修改草案》第二稿则将此句放在第42条最末,与上文呼应,构成合理使用制度适用的共同条件,从语义上否定了合理使用制度适用著作人身权的可能性。我们认为就此而言,《修改草案》第一稿优于第二稿。
二、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立法模式的完善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具体列举了12种合理使用的情形,没有合理使用的一般性认定规范,也没有“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类似补充性的条款,是一种“具体列举的立法模式”,并且是完全列举模式。这种立法模式的法律规范非常具体,便于法律的执行,但过于僵化,无法应对多样化的社会事实和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这一点也是我国著作权法上合理使用制度的最大缺陷。另一种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模式是“概括的立法模式”,即对合理使用仅作概括的规定,不具体列举适用情形。主要的国际著作权公约,如《伯尔尼公约》、《TRIPS协定》,大都采用此模式。这种立法模式具有极强的灵活性,但缺少确定性,不便于具体适用。介于二者之间的是“概括加列举”的立法模式,有合理使用的一般条款,又列举了具体的适用情形。这种模式用具体列举明确法律的适用,用一般条款平衡特殊社会现象和技术进步冲击下的利益冲突。其立法技术更为先进,被较多地采纳。
据此,我们认为我国《著作权法》在修法时应摒弃现有的立法模式,改采概括加列举的立法模式。僵化的列举条款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已不能实现利益的重新平衡。如高教出版社曾就高校学生将整本图书在复印店复印的现象咨询国家版权局,这种行为是否属于我国《著作权法》合理使用条款中第一项规定的个人使用?版权局回复:可对有此行为的学生批评教育,不宜认定为侵权。此回复折射出我国合理使用制度存在的尴尬。这种尴尬就是因为技术进步导致的复印成本比买书成本还要低造成的。高教出版社的利益在此现象中受损,只能借助于道德,批评了事。我国著作权法多年的研究和实践已为概括加列举的立法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国法院在实际审判中已有运用概括规范审理案件的具体实例。例如,在北京电影制片厂诉北京电影学院的案例中,法院就参考了美国判断合理使用的四项标准去分析北京电影学院在教学中对他人作品进行改编、拍摄、在校内放映的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并做出了肯定的裁判,但却缺乏我国法律条文的支持。有学者将合理使用的立法模式又分为因素主义、规则主义和因素主义与规则主义二者相结合的模式。⑦参见于玉、纪晓昕:《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判断标准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学论坛》2007年第3期,第90页。所谓因素主义即为概括立法模式,规则主义也即列举立法模式,因素主义与规则主义二者结合模式也即概括加列举模式。认为我国应当借鉴因素主义的立法模式,调整现有规则,采用原则+要素+规则的立法模式。⑧参见于玉、纪晓昕:《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判断标准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学论坛》2007年第3期,第94页。我们认为,此种观点也支持我国合理使用制度应改采概括加列举的立法模式。
《修改草案》第一稿和第二稿都回应了现行《著作权法》的上述缺陷,第一稿单独制定了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一般条款,即第39条,随后第40条对合理使用进行了具体列举,明晰地体现出“一般条款+具体列举”的立法模式。第二稿未独立制定一般条款,但在列举具体适用情形中规定“其他情形”,并将具有一般条款的文句附于其后。我们认为,第二稿中的此种变化虽优于现行文本,但相较于第一稿却是一种温和的倒退。将一般条款附于具体列举之后,而非之前,统领具体列举,文意上表现为对具体列举的限制,并未实现一般条款的独立价值,即使某些对作品的使用不属于合理使用的具体列举也有可能属于合理使用。
三、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一般条款的制定
概括加列举的合理使用立法模式需要对合理使用进行抽象的概括而不仅限于具体列举使用的情形。抽象概括合理使用的条款应表明合理使用的共性,成为所有合理使用与否的判断标准,我们称这种条款为一般条款。目前,合理使用一般条款的立法范例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国际公约的“三步测试法”模式。《伯尔尼公约》、《TRIPS协定》等都采用了三步测试法。常见的表达是:缔约各方在某些不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抵触、也不无理地损害作者合法利益的特殊情况下,可在其国内立法中对依本条约授予文学和艺术作品作者的权利规定限制或例外。所包含的三步是指:第一步,一定的特例,也就是权利的例外应明确限定在一定的范围。第二步,不能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抵触。针对此点存在的争议较大,主要在于如何界定“正常利用”。各种条约都没有明确说清楚此点,世贸组织的专家组在报告中认为正常利用的标准需要考虑对包括目前能给作者带来收入,并可能在将来有重要性的利用形式。有人也提出新的观点:“和正常利用相抵触将仅仅当‘作者被从相当可观的经济和实际重要性的现有的或潜在的市场剥夺’的情况下发生”⑨克里斯托弗·盖革:《在版权法适应信息社会时三步检验法的角色》(2009-12-11)[2012-01-12]. http:// ncac.gov.cn/cms/html/205/2109/200912/693469.html。。第三步在不同的文件中以不同的形式被表述。在《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条约中,例外和限制必须不能“无故侵害作者的合法利益”。《TRIPS协定》则表述成“权利持有人的合法利益”。“利益”一词既包括财产性质的使用权也包括收益权,还包括版权人对潜在损害或利益的关注。“合法”不仅指符合法律规定,还指被要求保护的利益是正当的。⑩王迁:《著作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页。
第二,美国“四标准”模式。美国《版权法》第107条规定了判断是否为合理使用应考虑的四项因素:使用的目的和性质、版权作品的性质、所使用部分的数量和内容的实质性、此种使用所产生的影响。以上四个判断要素是被引用最多的用来判断合理使用的普遍标准,也是我国学者介绍得最多的一种。但上述四个要素仅仅是判定合理使用的一些指导性要素,而非排他性的和决定性的。法官奥卡斯即指出:“这四个要素是合理使用规定所确认的,……它们是由法院基于公平考虑来进行评估或权衡的要素;它们不是单纯的跨栏,被告不会由于跳过它们就可以逃避责任。合理使用的分析系由敏感的利益权衡构成,绝非四个僵硬的标准。”(11)“Financial Information, Inc. V.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Inc.”[751 F.2d 501,224 USPQ 632(2d Cir. 1984)].转引自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5页。
我国在修法时应如何表述合理使用的一般条款?我们认为国际公约的三步测试法更适合我国的立法体例。正如以上所述,美国模式中的四要素需要整体评价,个体判断并不具有决定意义,仅是指导性而非决定性要素,法官需要在个案中不断进行新的利益权衡。这既不合乎我国的司法体制,也不合乎我国的立法体制。我国的司法体制中,法官判案遵循概念法学,在概念具有精确、终局确定的要素构成时,其要求“当且仅当”该定义的全部要素在具体案件事实中全部重现,概念才可适用。法官习惯于只负责发现具体的案件事实是否具备了概念的所有要素,而不习惯依据具体利益的分析进行案件的判决。我国的立法体例更多地倾向于构成要件模式,必须满足规定的要件,不满足任何一个构成要件,相关的法律都不能适用。这种严格的规则分析可以达成法律的准确适用,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三步测试法正是一步接一步,不满足任何一步都不能满足合理使用一般条款的适用条件。《修改草案》第一稿和第二稿中有关一般条款的文句都更接近于“三步测试法”,第一稿更是明晰地体现出“一般条款(三步测试法)+具体列举”的立法模式。
婴儿呱呱落地两人被一点点成长的细节感动的幸福感也四处漂浮在小说中:“朝阳十天就盯着彩色摇铃看。十五天就笑了……。”[12]对于这样的场景,池莉直接发表了自己的言论:“这幸福凌驾于一切困苦之上。”“困难算什么!”[13]当然这也是赵胜天李小兰的心声,这就是为人父母的幸福。这是一个伴随着不断地惊喜和成就的过程,每一次进步激发你心中最柔软的部分,让你感受到这世上你是最幸福的。养一个孩子是充满着意义的,叫一声爸爸,都能让从来不哭男人激动的扑沙扑沙的流泪,这样的幸福也促使父母不停成长,成长为真正的成年人。
四、对合理使用制度具体列举条款的完善
尽管合理使用的一般条款已能确定哪些作品的使用情形属于合理使用,哪些不是,但立法中制定明确的合理使用情形的具体列举仍具有重大意义。《修改草案》第一稿和第二稿都对现行条款做了部分修改。
(一)个人使用
现行《著作权法》第22条第1款规定:“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此规定过于宽泛,现实中不乏公众利用此条规定不当侵犯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实例。我们认为,此款可作两处修改:一是限制使用目的。将个人使用的目的界定为“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然而因“个人欣赏”无偿而自由地利用他人作品的情形对著作权人的利益影响较大,建议删除,将个人使用的目的限定为“为个人学习和研究”。二是限制使用的方式。现行规定中采用“使用”表明个人对作品合理使用的方式可以是任何使用方式,过于宽泛。可借鉴法国《著作权法》第41条的做法,将个人使用限制为“私人表演”和“私人复制”,或采用俄罗斯《著作权法》第18条的方法,在允许个人复制的一般性规定的基础上,设定若干排除领域的例外事项。(12)参见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修改草案》第一稿将个人使用的合理使用界定为“为个人学习、研究,复制一份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删除了“欣赏”一词,将“使用”修改为“复制”,缩小了个人合理使用的范围,较为不妥。但草案第二稿在第一稿的基础上增加了“片段”二字, 使个人合理使用的空间更为缩小,更具合理性。
(二)引用
现行《著作权法》第22条第2款规定:“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该条中的“适当”是较易引起纠纷的。使用多少为“适当”,法律并未明确。司法实践中一般的标准是:引用非诗词类作品不超过2500字或是被引用作品的1/10,多次引用同一部长篇非诗词类作品总字数不得超过1万字。(13)参见吴汉东:《美国著作权法中合理使用的“合理性”判断标准》,载《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3期,第43~56页。这一标准掌握得准确与否对裁量者并无法律的约束,因而操作起来自由度较大,尤其是对处于合理使用与侵权临界点的著作权纠纷,司法实践中更多的是以著作权侵权来处理。使用者在与著作权人发生著作权纠纷时,胜诉的可能性较低。这也使得合理使用他人作品的使用者利益因法律上的模糊而不能得到完全的保障。此外,如果被引用的是图片作品,该如何界定“适当”?图片作品往往是整幅的使用,是否就不是“适当”引用?果真如此,图片的合理使用几乎就不存在了。我们认为,“适当”的判断不应从被引作品的多少来判断,更应从引用后产生的新作品来判断,新作是否具有自己的独创性,而不仅仅是对被引作品的抄袭或改编。《修改草案》第二稿关注到这一问题,对“适当”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即“所引用部分不得构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或者实质部分”。
(三)媒体使用
现行《著作权法》第22条第3款规定:“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第4款规定:“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第5款规定:“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此三款均为了便于特定作品的传播而赋予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对这些作品的合理使用。近年来网络技术的发展引起了对该问题的争议,即提供信息服务的网站是否具有与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一样的媒体地位,适用这三款合理适用的规定。我们认为可以适用,原因在于提供信息服务的网站在其网站上引用、刊登特定作品时,其目的与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的功能是一致的,都是更好地传播了特定的作品。《修改草案》第一稿并未关注网络媒体,但第二稿关注到这一新型传播主体,并在文本中明确肯定了他们与传统媒体同等的权利,更具进步意义。
(四)教学科研使用
现行《著作权法》第22条第6款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教学科研使用在各国合理使用制度中受到普遍关注。由于教育、科研针对的对象不同,对作品使用的需求亦不同,合理使用的程度亦不同,各国多将二者分开规定。我们也建议我国著作权法将二者分别加以规定。我国将教学使用的方法限定在“翻译和少量复制”,过于狭窄,不能满足教学手段多样化的需要。英国《著作权法》第32条至第36条,分别规定了教学活动中的“复制”、“汇编”、“表演”、“录制”、“影印复制”等情形;法国《著作权法》第47条规定了“为教育目的播放”、第52条规定了“学校举办活动中的表演”、第53条规定了“教学活动中的复制”。
《修改草案》第一稿和第二稿均未关注教学科研合理使用规定的不足,我们认为,我国《著作权法》也应扩大教学合理使用作品的方法,建议修改为“为教学目的,播放、表演、录制、演绎或者少量复制等已经发表的作品,但不得对外使用。”使用的方式为非穷尽式的列举,只要不违背学校教育的目的,不对外营利即可,适用的对象也不宜限定于教学人员。因科研而进行的合理使用的范围仍应限定于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科研人员内部使用,不得出版发行。
(五)公务使用
现行《著作权法》第22条第7款规定:“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实践中,容易引发争议之点在于如何界定“公务”。此点从北京三面向版权代理有限公司诉楚雄州人民政府案可见一斑。2005年初,原告发现被告主办的楚雄州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传播了其受著作权保护的《焦点》,但未支付报酬。后原告向楚雄州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提起著作权侵权诉讼。被告辩称,楚雄州人民政府公众信息网属于政府行政公务范围,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据此,被告认为不构成侵权。法院经审理后支持了被告的主张,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判决,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判决,指定该院重审本案。(14)天则:《以国家的名义合理并不常在——我国著作权法中合理使用制度:国家公务使用探微》,载《科技与出版》2008年第1期第37页。我们认为,“公务”的范围应界定为执行立法、司法、执法的目的,而不能是教育、宣传的目的。但《修改草案》第一稿和第二稿均未予以修改。
(六)图书馆、档案馆使用
现行《著作权法》第22条第8款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在此讨论两个问题:一是此款将合理使用的范围限定在本馆,能否将此范围扩充至供其他图书馆或档案馆使用,以弥补另一个图书馆或档案馆的永久性收藏品中已经丢失、损害或不能再用的样本?我们认为,这种扩充是允许的。首先需要该复制件的图书馆具有该复制件的原件,只是原件已损害,无法复制。其次,由其他图书馆向这些图书馆提供作品的复制件,不会造成作品不应有的扩散、传播。第三,这种保存版本的需要与图书馆复制本馆图书保存版本的目的具有一致性,应同等对待。二是随着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亦开始数字化。图书馆等将其馆藏作品进行数字化是否属于合理使用,图书馆等在数字化后能否在网络之上开展数字化服务,这种服务的边界在哪?将馆藏作品进行数字化是将馆藏作品复制的行为,为保存版本的需要可以将本馆收藏的作品数字化。但能否在日常借阅服务中以数字化作品代替纸质作品,考虑到图书馆的公益性质、公众到图书馆阅读的性质以及允许图书馆等可以将本馆收藏的作品数字化在馆内提供给公众阅读并不会扩大馆藏作品的不当传播,我们赞同图书馆等可以将本馆收藏的作品数字化在馆内提供给公众阅读,但不得为公众提供作品的复制件。图书馆的数字化工作有利于公众更方便地接近图书,故我们认为,图书馆亦可向馆外公众提供本馆图书的简介,便于公众选择图书,但对图书简介仅限于图书信息的介绍,不能向馆外公众提供作品的实质部分。《修改草案》第一稿和第二稿也未关注此点。我们认为,该款可修改为:“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或供其他同类机构使用以取代该机构的永久性收藏品中已经丢失、损害或不能再用的样本,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可将本馆收藏的作品数字化并在馆内供公众阅读,可将本馆收藏的作品的简介数字化供公众使用。这种简介应不构成作品的实质部分。”
(七)免费表演
现行《著作权法》第22条第9款规定:“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此款规定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表演的范围。我国1990年《著作权法》中将规定的表演权的范围限定于直接表演,又称活表演。2001年《著作权法》将表演权界定为“公开表演作品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表演的权利”,表演的范围包括了活表演和机械表演。免费表演的范围在法律未作特殊说明时,应与表演权的范围一致。二是免费的含义。我国1990年《著作权法》仅规定“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语义不详,缺乏限制条件,受到诸多批评。2001年我国《著作权法》对该条进行了修改,增加了“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的限定。此种限定是否包括不得具有直接或间接的营利目的?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企业为宣传作品而进行的免费演出,旅店、饭店为招揽顾客免费演奏音乐作品是否属于合理使用?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曾因北京东安商城在商场内播放背景音乐提起侵犯著作权之诉,要求给予损害赔偿。法院经过审理,判定被告向原告支付著作权许可使用费,显然否定了背景音乐的播放属于免费表演,不是合理使用。故此,免费表演应限定于“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且不得以直接或间接的营利为目的。”
(八)公共陈列品
现行《著作权法》第22条第10款规定:“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修改草案》第二稿将其修订为“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并向公众提供,但不得以该艺术作品的相同方式复制、陈列以及公开传播”。此一修改回应了现实中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的临摹品、绘画品、摄影品、录像品再利用是否侵权的问题,肯定了这些作品再利用的合理性,也限定了再利用的范围,较现行文本和《修改草案》第一稿更为合理。
(九)对汉语言文字作品的翻译使用
现行《著作权法》第22条第11款规定:“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有学者认为,此款与国际公约不协调,而且在汉语言文字作品的利用方面,对中国人和外国人采取差别待遇,建议在将来著作权法修订时删除。(15)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6页。我们认为此款具有其自身的使命,即促进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故建议保留该款。
五、建议增设新的合理使用列举
虽然从理论上说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具体情形是无法穷尽的,在立法中存在一般条款的情形下,也无需穷尽列举,但详尽的列举更有利于法律的释明与适用。《修改草案》第一稿和第二稿没有增加新的具体合理使用的列举,但我们建议增加下述两种情形。
(一)增加临时复制
在作品的数字化传输过程中,传输介质中会自动产生无数的复制件,这些复制件的存在是暂时的,但时间或长或短。信息的传输者是否会因为在其所有的传输介质中存在作品的复制件而导致侵权成立?回答这一问题须先判断:临时复制是否属于复制,即是否属于复制权的权利范围?《伯尔尼公约》第9条规定:“作者的复制权是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复制其作品的专有权。”美国版权法认为复制是以现在所知的或将来发展出来的方法将作品固定在除了录音制品以外的物质载体上,由此作品能直接地或借助机器或装置被观看或进一步传播的行为。欧盟在“关于协调信息社会版权和有关权规制指令的建议”中提到,统一的复制权的定义应当将一切直接的或间接的、暂时的或永久的、在线的或离线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复制都包括在内。(16)薛虹:《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0页。从上述对复制权的界定来看,临时复制亦是复制。但临时复制仅是因技术的需要产生的复制行为,本身并无独立的经济价值。故各国在肯定临时复制属于复制的前提下,均规定了临时复制的权利限制。美国的《跨世纪数字版权法》就针对网络传输的特点对复制权加了多方面的限制:包括就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做的特殊规定;就计算机维修和护理所做的特殊规定;就广播电台、电视台等传输组织的“暂时性”规定所做的进一步规定;就远程教学涉及的权利限制所做的构想;就图书馆和档案馆所做的特殊规定。这些特殊限定均规定满足特定条件的临时复制属于合理使用。欧盟在其版权指令的建议草案也要求成员国将暂时性复制规定在权利限制之列,条件是暂时性和附带性的复制行为是某个技术过程完整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包括使传输系统得以有效运作),其唯一目的就是使作品得以被利用,而且没有独立的经济价值。我国也应制定宽泛的复制权的定义,各种将作品复制的方式,无论介质、时间都是复制,但出于技术目的进行的临时性的复制属于合理使用,这种临时性复制不具有独立的经济价值。
(二)增加滑稽模
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引发了我国法律界对滑稽模仿的广泛探讨。有学者提出将滑稽模仿纳入合理使用的范畴。(17)参见罗莉:《谐仿的著作权法边界——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说起》,载《法学》2006年第3期,第60~66页。亦有学者建议将现行《著作权法》第22条第2款修改为:“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作品;为批评、评论他人作品而对其进行滑稽模仿,在模仿作品中对原作品的使用应当与滑稽模仿的目的相适应。”(18)卢海军:《论合理使用制度的立法模式》,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3期,第29页。我们认为,我国著作权合理使用中应包括滑稽模仿,但不应将滑稽模仿的目的限定在为批评、评论他人作品。多数的滑稽模仿不是为了批评、评论他人作品,而是为了娱乐。故建议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为创作谐仿作品,可以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