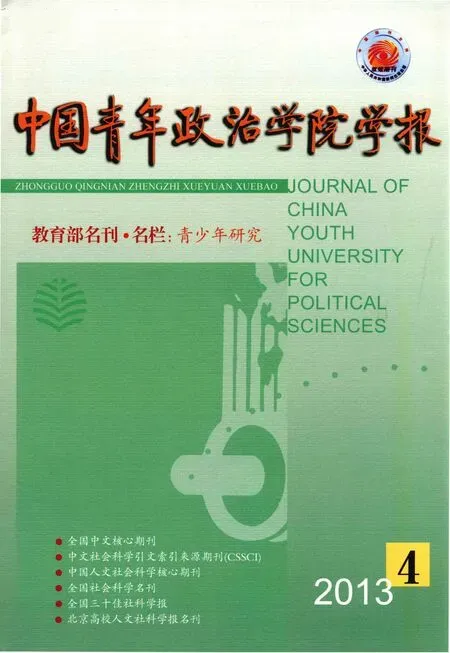论中止犯之司法判断
2013-01-29关振海
韩 哲 关振海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处,研究室;北京100043)
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都属于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二者区别的关键在于未完成犯罪的原因不同。前者是犯罪人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被迫放弃犯罪;后者则是行为人在自认为能将犯罪进行到底的情形下自动放弃犯罪。一般情形下人们根据上述标准能够将二者区分开来。但是,当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因遇到一定的障碍而放弃犯罪,且该障碍对行为人放弃犯罪意图之作用力大小存在差别时,人们对行为人放弃犯罪究竟是“自动”还是“被迫”往往存在较大争议,导致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区分困难,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中止犯司法判断的标准。
一、中止犯宽大处理的理论根据
大多数国家的刑法在将中止犯与未遂犯做出区分的同时①有的国家如德国、日本、意大利,将中止犯作为广义未遂犯的一种(中止未遂),对这些国家而言,中止犯与未遂犯的区别便是中止未遂与普通未遂的区分问题。,都给予中止犯更宽大的法律待遇,例如,德国刑法对中止犯规定为不罚,我国刑法对中止犯规定为“应当免除或者减轻处罚”,而对未遂犯则规定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理论根据主要有以下观点:(1)政策说。政策说又分为一般预防政策说和特别预防政策说。前者以李斯特提出的“金桥”理论为代表,认为减免刑罚可以激励行为人中断犯罪行为,从而为走上犯罪道路的行为人架起一道“返回的金桥”;后者则认为,行为人的危险性不仅是刑事责任的基础,也是其再犯罪的原因,刑法规定对中止犯减免刑罚是为了鼓励犯罪人中止犯罪,消灭、减少其危险性,从而不再继续犯罪②参见张明楷:《未遂犯论》,北京:法律出版社,东京:日本成文堂1997年版,第327~328、332~338页。。(2)法律说。法律说主要包括“违法性减少、消灭说”和“责任减少、消灭说”。前者认为,基于自己的意志中止犯罪时,受行为主观方面的影响,违法性便减少、消灭;后者认为事后撤回犯意是行为人的规范意识起作用的结果,因而非难可能性就减少、消灭③参见张明楷:《未遂犯论》,北京:法律出版社,东京:日本成文堂1997年版,第327~328、332~338页。。(3)法律、政策并合说。该说认为,仅用法律说或刑事政策理论都不能完全说明中止犯减免刑罚的理由,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刑法规定不处罚中止犯时,依据的是以政策说为基础的并合说;刑法规定对中止犯减免刑罚时,则依据的是以法律说为基础的并合说①参见张明楷:《未遂犯论》,北京:法律出版社,东京:日本成文堂1997年版,第344页。。(4)刑罚目的说。该说认为,自愿中止犯罪的施行或者设法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人,其犯罪意志远非犯罪既遂之人可比,其危险性格也远比一般犯罪人低,其撼动社会的程度已大为消减,从一般预防或者特殊预防的观点看,刑罚没有发动的必要②参见林东茂:《一个知识论上的刑法学思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页。。
第一种观点以假定行为人知道对中止犯的宽大处理规定为前提,但实践中只有极少数犯罪人知道该规定。有学者对德国最高法院关于中止犯的判决进行统计,指出行为人因知有中止犯的不罚规定而放弃行动者,相当有限③参见林东茂:《一个知识论上的刑法学思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页。。因而,政策说难以令人信服。第二种观点也存在问题,一方面因为违法是客观的,一经发生便不可能减少和消灭,因而“违法性减少、消灭说”只是一种假设;另一方面因为责任是主观的,行为人自动放弃犯罪表明其主观恶性减少,人身危险性降低,责任减少但没有消灭,故“责任减少、消灭说”有些片面。第三种观点只是前两种学说的简单综合,并不能消除各自的缺点。第四种观点能够解释中止犯免除刑罚的原因,但没有阐明中止犯减轻处罚的理由。
我们认为,探究中止犯宽大处理的理论根据,既要借鉴、吸收国外的刑法理论,又要立足于我国刑法规定,应当在中止犯与未遂犯、既遂犯处罚的比较中获得合理解释。基于上述思路,我国刑法关于中止犯应当减、免刑罚的理论根据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社会危害性说(客观危害较小、主观恶性降低)”和“刑罚目的说”的并合理论。前者能够说明中止犯应当减轻处罚的理由:中止犯相对于既遂犯客观危害较小,相对于未遂犯行为人主观恶性较低;后者能够解释中止犯应当免除刑罚的理由:行为既然没有造成刑罚意义的实际损害,并且行为人应予刑罚惩罚的人身危险明显降低,从一般预防或者特殊预防的角度来看没有适用刑罚的必要。
二、中止犯司法判断标准的学说
关于中止犯“自动性”的判断标准,我国理论界可谓众说纷纭,导致司法实践中认定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学说④参见赵秉志:《犯罪未遂形态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134页。。(1)主观说。该说认为,行为人中止的动机是基于对外部障碍的认识时,就是未遂,此外的场合便是自动中止。其判断标准是有名的弗兰克公式:能达目的而不欲时,系自动性,属于犯罪中止;欲达目的而不能时,系被动性,属于犯罪未遂。(2)限定主观说。该说主张只有基于悔悟、同情、怜悯等对自己持否定评价的规范意识、感情或者动机而放弃犯罪的,才是基于自己意志的犯罪中止。(3)客观说。该说主张根据社会一般观念对行为人放弃犯罪的原因进行评价。如果当时情况下一般人不会放弃犯罪而行为人放弃的,系自动性,就是犯罪中止;如果一般人也会放弃犯罪时行为人放弃的,系被动性,就是犯罪未遂。(4)折中说。该说以客观标准为基础,探讨外部事实对行为人意志是否产生强制性影响。如果产生强制性影响,系被动性,是犯罪未遂;否则系自动性,是犯罪中止。该说仍然主张根据客观标准进行判断,又称为新客观说。
上述四种观点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分歧:其一,中止犯自动性判断的标准究竟采行为人标准还是一般人标准。主观说和限定主观说都认为应当采用用行为人标准,而客观说和折中说都认为应当采用一般人标准,造成两大学说的分歧。其二,在采用一般人标准的前提下,究竟是通过一般人观念来判断,还是一般人通过客观事实对行为人的强制性影响来判断,造成客观说和新客观说的分野。其三,在采用行为人标准的前提下,行为人中止的动机究竟是基于怜悯、同情等伦理因素,还是基于其他动机,造成主观说和限定主观说的差异。
三、中止犯司法判断的新标准
中止犯自动性判断标准应当从一般人标准转向行为人标准,在某种犯罪障碍对行为人放弃犯罪意图作用力的大小存在差别的灰色地带内,自动性和被迫性的区分在于中止动机的考量,当中止动机中包含真诚悔悟、同情以及怜悯等伦理因素时应认定为犯罪中止,当中止动机中不包含上述伦理因素时应认定为犯罪未遂。
1.自动性判断标准:从一般人到行为人
一般人标准与行为人标准影响“自动性”认定结论仅在于以下两种情形:一般人认为能够继续实施犯罪而行为人认为不能,进而停止犯罪的;一般人认为不能继续实施犯罪,但行为人认为能够继续实施,却停止犯罪的。前一种情况下,如果采用一般人标准,结论是犯罪中止;如果采用行为人标准,结论是犯罪未遂。后一种情形下,结论正好相反。目前,各国的通说大多采取一般人的客观标准,但我们主张应从一般人标准向行为人标准转变,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我国中止犯应当减免刑罚的根据一方面在于其客观危害较小,另一方面在于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程度较低。尤其是后一方面,如果以一般人的观念或者理解作为判断标准,就不能精准反映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这与中止犯减免刑罚的根据背道而驰。例如,甲以漂亮的女性作为奸淫对象,甲看到乙女的背影以为其是美女,将乙女按倒在地意图奸淫时,发现乙女非常丑陋,顿时兴趣全无,放弃对乙女的性侵害。按照一般人的观念,丑陋不能成为甲继续实施犯罪的客观障碍,因而认定为犯罪中止。由于没有造成损害,依照我国刑法规定应当免除处罚。但这样的处理结果恐怕连主张一般人标准的人都不能接受,理由在于:(1)甲停止犯罪的原因不是主观恶性的减小、人身危险性的降低,而是乙女作为犯罪对象不符合甲事先设定的条件。如果依法对甲免除刑事处罚,甲还会继续寻找犯罪目标实施犯罪,难以发挥犯罪预防的功效。(2)对于丑陋能否成为继续实施犯罪的客观障碍,以及丑陋是否达到足以抑制犯罪的程度,往往因人而异。所谓“一般人的标准和理解”,并无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支持,采取一般人标准在实践中难以贯彻执行,其不过是司法人员作为支持自己判断的一种理由和说法。
其次,主客观相统一是我国刑法学界公认的定罪和量刑原则,这里的主客观都是指“行为人”的主客观,而不是“一般人”的主客观。一般人标准意味着将一般人的主观认识强加在行为人身上,在“一般人认为不能继续实施犯罪,但行为人认为能够继续实施,却停止犯罪”的情形下,其处理结论对行为人不公平;在“一般人认为能够继续实施犯罪而行为人认为不能,进而停止犯罪”的情形下,其处理结论又会纵容犯罪。世界各国采取一般人标准主要是基于案件事实证明的考虑,担心采取行为人标准会导致过于依赖行为人的口供,进而造成犯罪未遂或者犯罪中止认定的困难。其实,这种担心并不能成为采用一般人标准的理由,因为采取什么标准与能否证明是不同层面的问题,前者是更高层次的标准问题,后者是如何证明的操作问题。如果实在不能确定行为人是否能够继续实施犯罪,则可以朝着有利于行为人的方向推定。值得注意的是,一般人标准是学界的观点,而实务部门通常采用行为人标准,理论界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2.自动性和被迫性的界限——中止动机的伦理要素
从理论上说,自动性与被迫性难以界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学界通说将中止犯的范围理解得过于广泛,以致难以厘清犯罪中止与障碍未遂的界限,因而应当考虑对中止犯进行限缩性解释。从实践上看,在某一犯罪障碍对行为人放弃犯罪意图作用力的大小存在差别的灰色地带内,不同的司法人员往往做出不同的判断,因而,有必要考虑引入新的因素以增加司法判断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因为中止犯的法律待遇较之于未遂犯更为宽大,其构成要求也必须更为严格。从预防犯罪的角度考虑,只有诚挚悔悟者,社会危险性才较低,也才值得宽宥。待时而动的人,都还埋藏着危险性格,如果对其一并给予中止犯的宽大待遇,特别预防、一般预防的刑法目的都很难实现①林东茂:《一个知识论上的刑法学思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4页。。
我国刑法之所以对中止犯较未遂犯给予更为宽大的处理,在于前者比后者的主观恶性更小和人身危险性更低,而中止的动机恰恰能够反映上述两个因素,因此,将中止动机作为犯罪中止与障碍未遂判断的新因素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合理性。进一步而言,中止动机中包含真诚悔悟、同情、怜悯等伦理要素,才能更准确地反映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减小和人身危险性的降低。
不论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我国,刑法学界占支配地位的观点认为,自动性的成立不以中止动机的伦理性为必要,不论是悔悟、同情,还是惧怕惩罚、争取宽大处理,都不影响犯罪中止的成立。他们认为,设立犯罪中止制度的一个重要立法理由在于,通过减免刑罚的奖励以鼓励行为人中止犯罪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法益,因而对犯罪中止的自动性应当尽量从宽解释和认定。我们认为,通说观点建立在“行为人知道中止犯的宽大规定”这样一个理论假设之上,但实践中有多少人知道该规定,又有多少人是因为知道该规定而中止犯罪的,都有待于进一步实证考察,因而这个前提本身存在问题,其解释的科学性令人怀疑。正是由于自动性与被动性认定上的模糊,上述观点一方面认为因听到警笛声以为警察来抓捕自己被迫逃离现场属于犯罪未遂,另一方面又认为因惧怕刑罚处罚放弃犯罪属于犯罪中止。这样的观点容易令人产生疑惑:怀疑警察来了难道不是惧怕刑罚处罚吗?为什么前者定未遂而后者定中止呢?
不考虑行为人的中止动机,将因担心告发、畏惧刑罚、嫌恶被害人而放弃犯罪都解释为犯罪中止的通说观点和做法,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违背了中止犯的立法原意,难以实现犯罪预防的立法目的,也造成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界分的困难。尤其在基于轻微客观障碍而放弃犯罪的认定上,上述观点不仅难以自圆其说,而且有时自相矛盾,不能为司法实践提供比较明确的操作标准。反之,将包含真诚悔悟、同情、怜悯等伦理因素的中止动机作为自动性判断的客观标准,恰好能够克服上述弱点和缺陷,不但没有混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反而彰显了规范的伦理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司法实践中对于中止动机的判断要避免过于依赖行为人口供,应全面考虑行为时的客观情况,综合分析全案证据进行判断。如果在证据上对行为人是否包含真诚悔罪、同情怜悯等中止动机存疑时,可以朝着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向认定。我们十分欣赏这样的观点:“人与人的关系多么闪烁飘忽,人的情感世界多么复杂,利益纠葛多么难解,法律人如果用单元简易的标准决断人世间的是非,只会带来遗憾,甚至悲剧。避免遗憾与悲剧,除了努力于‘学问的生命’之外,‘生命的学问’的涉足,也是必需的。这两者的共通源流,是善。”[1]
[1]林东茂:《一个知识论上的刑法学思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