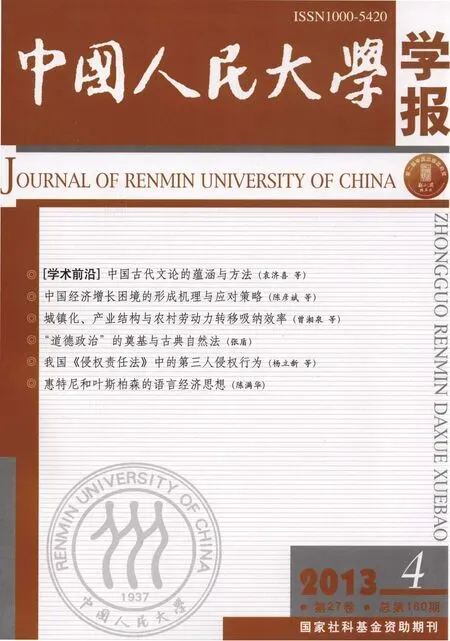常州今文经学:历史语境与内在理路
2013-01-23张广生
张广生
经学是中国传统的主流学术,以对儒家经典的注解和阐释为主要内容,其中蕴藏着各种思想意识。历代经学的形成和演变伴随着时势的变化与思潮的嬗替。有清三百年间,学术思想风气大体上有三变:一是顺治、康熙年间的 “实学”。清初大儒多明末遗老,以顾 (亭林)、黄 (梨洲)、王 (船山)、颜 (习斋)为代表,他们痛思明亡之祸,厌弃 “空谈心性,束书游观”的学风,提倡实学,其志在推求天下利病,图谋民族复兴。二是乾嘉 “汉学”。新王朝统治日渐稳定,一方面以开科举士、编修 《四库全书》羁縻士人,一方面大兴 “文字狱”,严密文网,士大夫讳言本朝事,绝口不提先儒经世之意而只是埋头于文字训诂、校勘辑佚的考据之学。三是嘉道以降的由常州学派开辟的今文经学,今文经学不仅开经世风气之先,而且成为百日维新运动最鲜明的斗争话语。三脉之中,考据学为清学中坚,苏州惠(栋)与徽州戴 (东原)、段 (玉裁)、二王(念孙、引之)被推为清学正宗。实际上在苏州、徽州之学外,还有常州之学。常州之学实为清代今文经学,只因乾嘉汉学势大时不显于世,直到道光、咸丰以降才取代惠、戴之学名于世,再领晚清思想之潮流。[1](P119)本文尝试对常州今文经学的独特历史价值进行深入探讨。
对于常州今文经学的思想史价值,有一种从整体上否定的意见,其否定的逻辑是:虽然清今文经儒者为超越理学的空疏和考据学的琐碎而致力于复兴汉儒以经术贯通自然、伦理与政治的大体,但是,今文经儒者推重的汉儒传统,也即征圣、宗经、神道设教的传统,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了;相反,考据学的 “求是”之所长,恰恰能够与时俱进,“夷六艺为古史”,更有利于人们理解古今进化之道。①对于这种全盘 “尊史抑经”的逻辑,非常有代表性的反驳意见是:一种派生
① 章太炎对庄存与和刘逢禄的经学专家之学的肯定毫不妨碍其对常州学派开辟出的整个今文经学传统的否定。但如果否定了清今文经学的整体价值,我们就会丧失 “以经还经,以史还史”的视野。参见章太炎:《清儒》,载章太炎:《訄书》,16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于古文经派 “六经皆史”说,且混合了朴素进化论信仰的史学主张,是否足以从一般意义上来衡量经学和史学的关系,进而具体评判清今文经儒者重建汉儒经学传统的努力呢?①周予同在参加 《辞海》经学史部分词目的编订工作中,对于那种把儒家经学还原为周秦诸子学的看法明显表示批评,在他看来,只根据后人说解,没有对经史关系变迁的追根溯源的长时段眼光,无法正确估量经史关系和经学本身的价值。参见周予同:《有关中国经学史的几个问题》,载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朱维铮编),694~69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为了重估常州今文经学的价值,回到常州今文经学的具体历史语境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两种典型对立意见争论的起点是,如何才能超越研究者个人和时代的偏见,对常州今文经传统的价值进行公允的历史评判呢?然而,要对常州今文经学进行恰如其分的估价,仅仅回到当时当地具体的历史语境恐怕仍然是不够的,因为持整体否定意见一方的深层预设不仅仅是要估定常州学术对当时当地历史的价值,而且要追问既超出研究者又超出历史当事者这种双重当时当地历史性的更加恒常、更加公正的历史价值。换句话说,常州今文儒者所开辟的经学传统,是否还有某种无论是前贤还是时贤都应该珍视的更加恒常的价值呢?这才是争论双方引领我们要面对的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在回到常州今文经学的历史语境的同时,深入常州今文经学的内在理路就是我们更加重要的研究任务。
一、常州今文经学的独立历史语境
常州学派开山人物庄存与 (1719—1788),字方耕,于六经皆有著述,主 《公羊传》,著有《春秋正辞》、 《春秋举例》、 《春秋要指》,发挥《春秋》之“微言大义”,不拘汉宋,重在推求经义疑义,以《春秋》之研究定下常州学派之发展方向。续其学者有刘逢禄 (1776—1829),字申受,著有 《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刘氏的主要影响在于引申发挥何休公羊解诂的 “三科九旨”说,以阐发孔子 《春秋》之 “微言”。又有宋翔凤 (1776—1860),字于庭,著有 《论语说义》,把孔子尊为 “素王”,提倡微言大义。
正如艾尔曼 (B.Elman)所发现的,长久以来,学界对于晚清今文经学的历史语境的讨论,习惯于从康有为一直追溯到魏源和龚自珍这样一条主线,而主线的解释中心又在于1898年今文经学对于维新改革的重要性。在以1898年为解释中心的线性历史叙事中,庄存与和刘逢禄在今文经学复兴中的角色只能聊备一格: “谁是庄存与?在接受了魏源和龚自珍代表19世纪中国的改革精神说法的史学家笔下,他通常会在注脚里被提上一笔。谁是刘逢禄?在历史叙述里,他通常只是魏源和龚自珍的老师。”[2](P12)
艾尔曼批评的是以19世纪90年代的政治改革为中心讨论晚清今文经学的常见路数。在这种路数中,庄存与和刘逢禄当然就显得不那么重要,至多只是作为今文经学学术回溯的远源提上一笔。但是,对庄存与和刘逢禄今文经学的历史地位的忽视恐怕还有另一条路数,那就是纯粹学术史叙事一脉。在这种 “以礼制判断今古”的学术史叙事中,庄存与和刘逢禄也要被提到,但他们不是作为士大夫而是作为纯粹的学者被提到,所以其 “聊备一格”的位置几乎没有太大改变:“庄存与、惠栋之流皆是,一经之义明,而各经相互间之关系尚未窥其全,是则所知者各家一隅之今文说,尚无综合各家以成整个之今文学派。刘逢禄之流,信 《公羊》则并驳 《左》、 《谷》,而 《周官》变为疑书,党伐之争以起。”[3](P104)
上述两种解释路径都倾向于忽视常州今文经学历史语境的独特性,从而让我们既不能从政治社会角度解读这段历史,也不能更好地估计常州今文经学的思想史位置。笔者认为,艾尔曼对于今文经学的复兴及庄存与、刘逢禄在王朝政治与家族社会生活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联系的提示,是相当有启发意义的,它对于我们观察庄存与和刘逢禄这里的独立 “今文经”语境十分有帮助。
汤志钧本来是强调常州今文经学起源的独特背景的。他认为,庄存与之所以讲 《公羊》,发挥 《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实际上是为了 “大一统”而找 《春秋》作为依附,其发挥 《春秋》微言的重点在维护“大一统”。这种“大一统”的诉求是指向两种离心背道的现象的:一种是学术的门户(汉宋)问题,另一种是政治的宗派 (朋党)问题,而后者往往与前者相缘附而得以巩固。乾隆严防门户、嫌忌朋党的“乾纲独揽”,就是要维护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大一统”。而庄存与“授读王子,任职内廷,对中枢情况,自较 ‘在野’为深,自易随时揣摩,仰承‘圣旨’”[4](P82)。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与其他汉人士大夫仕途际遇相比,庄存与已算颇得乾隆知遇之恩,但不从个人私情而从士大夫所信奉的儒家政治哲学来说, “德位合一”也即 “圣贤与王者合作治天下”,是儒家政治哲学 “大一统”主张的根本依据,实现这种合一才是王道政治的核心目的;“通过君主”只是由此派生的第二义,只从第二义上理解 “大一统”并简单将之化约成 “专制思想”,恐怕难免以今度古,错诬先贤。对于这种“专制主义归谬法”和“专制主义心术论”,杨念群就曾提出过商榷意见,他指出,清朝君主在“大一统”理念的建构上,并非专凭一己之私的断裂性创造,而是承袭了 《春秋》的古意。①杨念群提醒我们深思的是,《春秋》今文经学这一 “古意”恐怕不仅是因为古老,而且是因为蕴涵贯通古今的 “经常之道”,才能为华夏多元一体的秩序正当性提供恒常的超种族的根基性哲学论证。参见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1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更何况,就具体情境而言,庄存与的经学研究进路也许并非仅仅因为受到中枢的荣宠,才倾向于董仲舒、何休的。还有相反的情况,正是因为庄存与目睹这个时代贵族统治者德性的衰退和王朝政治的败坏 (和珅的腐败只是这种衰败症候浮出水面而已),正是因为与自己学识德性完善和政治抱负成长之 “上升过程”相伴的却是仕途上的长期停滞以至晚年被中枢疏远[5](P237-238),他才推动了晚清今文经学的复兴运动。
在笔者看来,这种自觉的思想学术转向具有进和退的两重含义。在进的方面,国家中枢政治的结构性限制使汉族士大夫的政治异议日益滋生,“微言大义”实质是庄存与表达政治异议的隐蔽形式,政治一统话语背后包含着政治抗议,圣贤应该得予中枢政治,圣贤与明君合作治天下的 “德位合一”,才是 “大一统”的真正微言大义。在退的方面,这种政治抗议的形式表现为从中枢政治舞台归隐常州族里社会。庄、刘宗族在18世纪80年代以前历代都有政治显达之士,但此后两家开始远离北京的中枢政治,专注于家乡的家族事务。正是在后代族人对 “真汉学”的弘扬中,今古之分际扩展向群经,今文经的激进微言大义才日益鲜明起来。
二、经世之志与《春秋》大义
对于庄存与、刘逢禄这样本来有广阔的参与中枢和地方政治机会的名门望族而言,辨别古籍的真伪被视作小术,而世道人心、国家的彝伦攸序更是其关切的重心所在。龚自珍在 《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中记述道: “公自顾以儒臣遭世极盛,文名满天下,终不能有所补益时务,以负庥隆之期,自语曰:辨古籍真伪,为术浅且近者也;且天下学僮尽明之矣,魁硕当弗复言。”[6](P141)
庄存与并不是简单地认为校勘、辑佚、辨伪之学是无益的,而是意识到对儒家所传经典的考索分辨会使经典受到怀疑,从而危害世道人心。如龚自珍所说: “古籍坠湮十之八,颇藉伪书存者十之二,帝胄天孙,不能旁览杂氏,惟赖幼习五经之简,长以通于治天下。昔者 《大禹谟》废,‘人心道心’之旨、‘杀不辜宁失不经’之诫亡矣;《太甲》废,‘俭德永图’之训坠矣;《仲虺之诰》废,‘谓人莫己若’之诫亡矣; 《说命》废, ‘股肱良臣启沃’之谊丧矣; 《旅獒》废,‘不宝异物贱用物’之诫亡矣;《冏命》废, ‘左右前后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数言幸而存,皆圣人之真言,言尤疴痒关后世,宜贬须臾之道,以授肆业者。”[7](P142)
庄存与最关心的是经书有益于后世的 “义理”,以至反对从科举考试通行的 《尚书》中删去已被考据家订为伪书的 《古文尚书》部分,甚至认为梅赜剟拾 《古文尚书》有罪亦有功。 “公乃计其委曲,思自晦其学,欲以借授古今之事势,退直上书房,日著书,曰 《尚书既见》如干卷,数数称 《禹谟》、 《虺诰》、《伊训》,而晋代剟拾百一之罪,功罪且互见。公是书颇为承学者诟病,而古文竟获仍学官不废”[8](P142)。庄存与这种不为考据学所动、兢兢济世之志颇得龚自珍的赞赏: “学足以开天下,自韬污受不学之名,为有所权缓亟轻重,以求其实之阴济于天下,其泽将不惟十世。”[9](P141)
庄存与作为清代复兴今文经的创始人物,不仅对《尚书》中被考为“伪篇”的内容多方维护,而且对当年刘歆争立学官的《周官》也颇为重视。他认为《周官》中虽然掺有后人增饰的内容,但仍包含着值得借重的古圣治国之法: “其道甚著,万世卒不可废,安可泯没哉!”[10]所以他 “原本经籍,博采传记、诸子”,作五卷 《周官记》,期望通贯“圣人制度”垂法之大义。[11]
既然庄存与这样力主调和汉宋,不以考据为壁垒,只以 “用世”为计,那就难怪他以义理之“要指”贯通 《春秋》了。庄存与认为 《春秋》非记事之史,读《春秋》要依循 《公羊传》的进路追索圣人之 “微言大义”。所谓 “微言大义”,就《春秋》而言,孟子有述: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 《春秋》作。晋之《乘》,楚之 《梼杌》,鲁之 《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恒、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 ‘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轲:《孟子·离娄下》)“其文则史”,当然是以史之文载当时之事,而 “其义”则是 “定天下之邪正,为百王之大法” (朱熹:《四书集注·离娄章句下》)。庄存与认为理解《春秋》的关键就是要明确:“《春秋》以辞成象,垂法示天下后世以圣心之极。观其辞必以圣人之心存之。史不能究,游夏不能主,故善说《春秋》者,止诸至圣之法而已矣。”[12]这是 “春秋要指”的第一条,也是最核心的一条。铭记此条于心才能会意余下的二十一条。通过分析 《春秋》的“要指”,庄存与强调,《春秋》非记事之史,而是圣人治乱之书。讲《春秋》,不仅要看到 《春秋》“所书”,而且还要看到其“所不书”。 《春秋》约文示义,不拘于凡例,关键是要究 “圣心之极”,如此才能止于“至圣之法”。最后,庄存与重申董仲舒和何休的看法,认为《春秋》实际上是本天人之教以统摄王道的经世法典,法典集中体现了圣人孔子“拨乱反正”的用世之志。
如果说 《春秋要指》侧重于指点 《春秋》“书法”的关键,提醒人们要善于从 “事”与“文”追索 《春秋》之 “微言大义”的话,那么,《春秋正辞》则直抒庄存与对 《春秋》 “法典大义”的构架性看法。
本来,庄存与的 《春秋》研究深受元末明初学者赵汸 (1319—1369)的影响。赵汸对于之前学者研究 《春秋》专主 《左传》感到不满,认为依 《左传》,虽事有可考,但于孔子 “笔削见义”则不知。[13]而《公羊》传、 《谷梁》传 “以书不书”发义,甚有启发,可补 《左氏》专以记事之不足,达孟子述微言之旨。[14]但赵汸又认为 《公羊》、 《谷梁》虽 “有见于经”,并传 “经之佚义”,然 “常据经以生义,是不知 ‘其文则史也’”,所以赵汸的 《春秋》研究虽然纠专主 《左氏》瞑义之偏,仍不废 《左氏》考事之长,以发挥 《春秋》 “属辞比事”的 “义例书法”特点。赵汸本着经世之志,博采今、古两派的 《春秋》传注,但仍脱不开杜预 《左传注》以凡例组织历史事件的模式。而庄存与自称: “读赵先生汸《春秋属辞》而善之,辄不自量,为隐括其条,正列其义。”[15]庄存与明显认为,不仅杜预的“凡例”不能把握孔子 《春秋》,而且赵汸 “属辞比事”的方法并列 “义”、 “例”,仍不够突出《春秋》不拘 “一义一法之凡”的 “约文志义”性质,所以,他把赵汸的 “条例”贬退到第二位,而把 “大义”列为第一位。如此,庄存与的《春秋正辞》实际上回到了公羊学的传统,直接把圣人经世大义的 “法典”构架揭示了出来。
这一法典由九部分组成: 《正奉天辞第一》、《正天子辞第二》、 《正内辞第三》、 《正二伯辞第四》、《正诸夏辞第五》、《正外辞第六》、《正禁暴辞第七》、《正诛乱辞第八》、《正传疑辞第九》。其中《正奉天辞》可以说是这部法典的总纲领部分。它叙述立法的基本精神和主要意旨,统摄其余的八个分论部分。法典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宗旨被归纳为十个方面: “建五始”、 “宗文王”、 “大一统”、“通三统”、“备四时”、“正月日”、“审天命废兴”、“察五行祥异”、“张三世”、“俟后圣”。
第一,“建五始”,是要给君主统治权创始以天命的宇宙论正当根据。公羊家认为, “建五始”是《春秋》经 “元年春王正月”一句表达的总意旨。所谓:“元,正天端自贵者始,同日并建,相须成体,天人大本,万物所系,《春秋》上之。”[16]
第二,“宗文王”,是讲后继君主的正当性非直源于天,而是来自 “继体守文”——延续受命之祖的圣王政教,守护其所积累的德业。所谓:“文王受命,武王述之;文武既没,文不在兹,稽古尧舜,道法所祖,闻而知之,万世以为土。”[17]
第三,“大一统”,是讲政权正当性的维系不仅要依靠政治权力的垄断,而且要依靠文教的正统性,儒家圣人之学才能提供这种圣王与德位合一的正统性。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郊社宗庙尊无二上;治非王则革,学非圣则黜。”[18]
第四,“通三统”,是讲一姓王者天命的正当性是可以转移的。所谓:“三代建正,受之于天。文质再复,制作备焉。师法在昔,恭让则圣。矧乃有监,匪独一姓。”[19]
第五, “备四时”,是讲君主既知天命无常,就要虔敬谨慎地奉顺天人的正当法则,以应四时长养生杀的自然之道。所谓:“谨于尊天,慎于养人,圣人以顺动,则日月光明,庶物露生,阴佐不可右,刑谧不可任。五辰之正,群生在命。”[20]
第六,“正月日”,是讲君主在日常政务中应勤勉地恪尽职守,才能于几微处保持天命不坠。所谓:“孰能慎微,日无不吉,载而始之,端在朔月。民主爱日,不遑暇食,夜曰日余,天光在牖,闰曰岁余,门以听候。”[21]
第七,“审天命废兴”,是说为政者不能自修其德,圣贤离之而去,天命动摇。所谓: “支与,坏与,饫歌,戒与民,不听,罪圣人,觉与。”[22]
第八,“察五行祥异”,是讲天以五行休征或咎征与人事感通,圣人见微知著,作《春秋》,行褒贬之权,期待天命正当性的修复和重建。所谓:“天乎,与人甚可畏也。欲止其乱,心仁爱也。上下之间匪虚而实,元气澹澹,骰撰相易,神乎难知,勿谓不然,所贬所讥,惟圣同天。”[23]
第九,“张三世”,是讲圣人将 “所见”、“所闻”、“所传闻”,与 “据乱”、 “升平”、 “太平”相配, “实不太平,文致太平”的寄托,成就“太平世”的希望。所谓: “据哀录隐,隆薄以恩,屈信之;志详略之文,智不危身,义不讪上;有罪未知其辞,可访拔乱启治,渐于升平,十二有象,太平以成。”[24]
第十,“俟后圣”,是讲孔子以 《春秋》法典为规范,以鲁国史事为例, “议礼”、 “制度”、“考文”垂法万世,非汉代可独专为正当性来源。所谓:“《春秋》应天受命作制。孟子舆有言,天子之事,以托王法鲁。无惕焉以治万世,汉曷觊焉。”[25]
我们发现,整部 《春秋》,在庄存与 《春秋正辞》的解释下,呈现为一部规范儒教国家 “统治权”的法典面目。它集中关心的是国家统治权的正当性问题。“天命”就是国家统治的正当化形式,就是统治权。整部法典对统治权也即天命的获得、维持和转移的法则进行了系统规范,在这种规范阐述中,天子制度或者说君主的法权显然居于一个中心的地位,政治的统一和文教的统一,都是围绕着 “天子”布置的,政治—社会秩序和道德—文化秩序的整合也是秩序构成的理想目标。因而,如果不是把 “大一统”理解得过于狭隘,“大一统”作为这部法典的重心也许是不错的。但需要强调的是,“天子”只是 “大一统”的媒介,而且仅仅是媒介之一,后世君主不能通过天子制度直接与天沟通,而是必须 “稽古尧舜,道法所祖,闻而知之”,才能守护住先祖为一姓赢得的 “天命”,必须 “通三统”才能维持“天命”,若圣贤辞王而去,则 “天命”将废。《正奉天辞》是对这部法典总精神的一个阐发,而《正天子辞》、《正内辞》、《正二伯辞》、《正诸夏辞》、《正外辞》、 《正禁暴辞》、 《正诛乱辞》,则分别就君主的礼法身份,及其对内对外统治的规范进行详细论述。每个部分都冠以 “正”字,意在突出 《春秋》为 “拨乱反正”、 “垂法万世”的圣人之书。《正传疑辞》再次强调 《春秋》不是对“十二公之策书”的历史整理记录,而是圣人笔削史文、索引微言大义的法典。
庄存与所揭示的 《春秋》今文阐释系统,不仅为中国王朝国家的正当性的获得、维持和转移提供了礼法规范,而且还有支撑这一规范的政治哲学论证。为了 “大一统”,援引儒家政治哲学,标榜超越王朝和民族的天下观和王道观,清王朝自然因此可以获得自己统治的正当性论证,但同时,由于这一规范与论证是超王朝和超民族的,所以,所有援引这一儒教 “正当性论证”的王朝也必然要受到这一儒家礼法的规范。对庄存与来说,康、雍、乾三世的成功统治,满洲贵族统治者教育的儒家化,满汉畛域的继续存在及由此造成的汉族士大夫仕途的结构性局限,这些都是政治与文化的现实。在这种语境下重新阐发儒家的《春秋》之教,重申儒家的经邦济世之志,就有了更加复杂的意涵。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正辞》这部《春秋》大义的阐发之作本身似乎也有 “春秋笔法”隐含其中。只是细微之处也许不让人注意。《正奉天辞》中“建五始”一条,引董仲舒解《春秋》建五始之义时,只到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不矣夫!自卑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便戛然而止。熟悉董仲舒 《举贤良对策》的人会自然联想到他下面的话: “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另一个尤为明显之处,我们就更不应忽略。也是在 《正奉天辞》这个 “总论”之中, “建五始”、“宗文王”、 “大一统”、 “通三统”、 “备四时”、“正月日”、“审天命废兴”、“察五行祥异”、“张三世”、“俟后圣”这十个条目按体例应该在简括各条目意旨后,分别详细阐述之。但是,《正辞》中对前八个条目都有分别详论,而对后两个条目,即 “张三世”、 “俟后圣”,只有开篇简单的概括,没有详细分述。这种 “有书”、“有不书”,在今文 “语法”中的确提醒读者 “以所不书知所书”、 “以所书知所不书”。从简略的对两个条目的叙说中,我们读到 “张三世”通过对“所见”、 “所闻”、 “所传闻”三世的不同 “书法”,不仅使圣人自己受到保护—— “智不危身,义不讪上”,而且也使经世救乱的希望得到保留—— “可访拨乱启智”。而 “俟后圣”只是说《春秋》乃“应天受命”而作,非独为汉代立国预备了宪章,而且为万世求治提供了法典。这种简略,无疑可用作作者在自己所处之世表达政治意见的有力工具。这种以今文经 “语法”谈政治的方式,除了教导君主外,当然更是对士君子有德无位,小人却以私恩取宠的现实的控诉和抗议。但其诉诸的形式是更加正统的儒教国家“正当性”观念,呼吁“圣王合一,德位合一”才能维护天命不坠于地的儒教“大一统”。从《正奉天辞》中“张三世”和 “俟后圣”两个条目的简略形式看,庄存与对今文家更激进的政治内涵,显然不是如艾尔曼所说的“不在意”[26](P81),而是有意地去抑制。庄存与的政治异议确实还没有激烈到与政治秩序全面对抗的程度,而是停留在 “于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的流连叹息之中。 “君在乾隆末,与大学士和珅同朝,郁郁不合,故于《诗》、《易》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际,往往发愤慷慨,流连太息,读其书可以悲其志云。”[27](P238)
这种叹息是在 “大一统”框架笼罩下的政治抗议,抗议没有指向王朝君主的专断权力,而是指向和珅这样的腐败小人对统一于君主的正统政治与道德秩序的破坏。这种今文经旗帜下的政治抗议的确是一种 “正统”的话语,它诉诸儒家经书所规范的 “传统正当性力量”来对抗它的败坏者。德与位在这里只是廉洁正统的儒家士大夫和腐败偏邪的得势小人之间的对立。
这种压抑已久的政治异议在嘉庆赐死和珅之后广泛地爆发出来,其高潮就是1799年的翰林编修洪亮吉上书事件。洪亮吉幼年曾在庄氏私塾读书,《春秋公羊传》和 《春秋谷梁传》都是他攻读的内容。在洪亮吉的上书中,充满了讽谏君主、批评吏治腐败的“是非邪正之辨”[28](P21)。我们可以把洪亮吉冒死上书的激进事件看做庄存与以今文经表达政治异议范式的一个突出形式。这种形式虽然被君主怀疑有 “君子党”式的宗派政治倾向,但正因为在维护 “大一统”的框架中发表抗议,才充满了正统力量和相应的政治行动能力。而更加激进的儒家政治哲学形式则是在庄、刘家族由中枢政治中疏离出来后,由庄存与的学术继承者逐渐发掘出来的。
三、常州今文经学的激进化
18世纪80年代后,庄存与、刘逢禄两家开始远离王朝中枢政治,专注于家乡的家族事务。家族里的庄述祖、庄有可、庄绶甲,以及刘逢禄和宋翔凤继续弘扬庄存与的今文 《春秋》阐释传统。在今文经复兴中,庄存与可谓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人物,而今文学由 “各家一隅”之今文学发展成为一今文学派,则宋翔凤、刘逢禄之功实不可没。如果说,庄存与是以义理通今文学的话,那么,宋翔凤和刘逢禄则受庄述祖的影响,而把考据学与今文经 “微言大义”的发掘结合了起来。正因为考据学的引入,汉代经师的 “家法”才逐渐明确起来,从而今古文经派之别才发掘出来。
在庄存与后学那里, 《春秋》的性质和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明确。 《春秋》被视为孔子 “行天子事,继王者之迹”的创作,只有公羊家得其大义真传,而董仲舒、何休是汉代的集大成者。但随着古文经派的兴起和汉晋儒风的衰落,今文大义几尽乖绝。理解 《春秋》的微言大义不能依靠《左传》,《左传》并不是 《春秋》经传,而是一部独立的史书,与孔子 《春秋》大义无关;是古文派为了对抗今文派才牵附 《左氏春秋》为 《春秋》经传的。 《春秋》大义,必须以 《公羊传》为中心,结合董 (仲舒)、何 (休)之言去发挥。圣人之道被认为备于 《五经》,而 《春秋》则被视为窥见 《五经》大义的 “管钥”。[29]
刘逢禄的 《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开列了公羊家解释 《春秋》的三十个义例,其中, “张三世例”、“通三统例”、“王鲁例”,把今文经的激进大义充分展露出来。
“张三世”一方面表示周道的衰微,另一方面表现了圣人拨乱反治,以 《春秋》匡正天下的志向。所谓 “世愈乱而春秋之文愈治,讥两名,西狩获麟是也”[30]。
“通三统”一方面讲天命所受不独一姓可专,另一方面讲孔子以《春秋》损益夏、商、周礼法,重建王者之始。所谓 “三王之道若循环,终则复始,穷则返本”[31]。“通三统”直接指向 “王鲁”。“王鲁”就是以 《春秋》当新王的意思:“夫子受命制作,以为托诸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引史记而加乎王心焉。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32]孔子制新王之法为什么要托于鲁呢?“因鲁史之文,避制作之僭,祖之所逮闻惟鲁为近,故据鲁以为京师,张治本也。”[33]意思是说,孔子凭借 《春秋》所制新礼法成为新王,即用春秋之法进退鲁史之时事,借此,孔子 “议礼、制度、考文”,为天下 “新王”。
除了 《春秋》这个 “五经之管钥”外, 《论语》这一历来被认为是孔子言行的可靠记载之书,也得到了今文学者的重视。“《论语》总六经之大义,闻《春秋》之微言,固非安国、康成治古文者所能尽。”[34]“先王既没,明堂之政湮,太学之教废,孝悌忠信不修,孔子受命作 《春秋》,其微言备于 《论语》。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当素王,微言者,性与天道言也。此二十篇 (指 《论语说义》)寻其条理,求其旨趣,而太平之治,素王之业备焉。”[35]宋翔凤认为,素王之志不仅要从性与天道中考索,还要从礼法制度中发掘。汉代今文家传七十子所受,比如《王制》和《孟子》中所谈的制度完全是相合的,它们都是孔子所制定的新法度。
在 “至圣先师”之外和之上,孔子颇具神秘色彩的 “素王”形象被展现出来,的确预示着更激进的政治选择可能—— “素王”和 《春秋》法典可以构成一种 “圣人革命论”。儒家圣人之教秉承天地人伦之常性,故超越任何王朝政治实体的具体存在,成为任何王朝政治社会的 “天命”,也即 “正当性”的来源。王朝一姓统治虽然在“家天下”的时代已经不可避免,但涉及与 “异姓兴王”相伴的天命转移,儒家的态度不仅仅是保守的 “俟后圣”,更是激进的 “托王法鲁”。在“俟后圣”的范式下,孔子不过是乱世中伟大文明传统的继承者、保存者和文明秩序重建的期待者;但 “托王法鲁”的范式则意味着孔子成为未来文明秩序的立法者,积极用儒家礼法政教之火点燃新的柴薪。
四、结语
今文经学在庄存与那里提供了一部衡量王朝统治权正当性的完整法典。围绕着王朝 “天命”的获得、维持和转移问题,统治权正当性的话语既可以提出维护 “大一统”秩序的保守政治主张,也可以孕育坚持 “异姓兴王”的激进政治意识。在乾隆晚期和嘉庆初年,今文经的发掘,“有德无位”的 “流连叹息”,与士大夫政治意识的复苏相为表里。在庄存与、刘逢禄的后学那里,今文经微言大义的发掘逐渐从 《春秋》扩展向群经。伴随着义理和考据相结合的学术进路,常州学派不仅在学术方法上吸纳和消化了汉学,而且在对 “真汉学”的追索中,孔子 “素王”的形象和六经的 “宪章法典”性质不断被强调,这为我们展现出今文经学更加激进的面相。今文经学思想无论表现为保守还是激进,都是对应于历史中的权宜变化而言的,因为依据儒家经学的理解,人伦秩序的历史性并非简单进化的线性历史性,而是蕴涵着永恒经常之道的、不断循环再现的历史性。正是在既知道 “经常”,又知道 “权宜”的双重意义上,常州今文经学为我们打开了一种长时段的历史视野。这一视野告诉我们,无论是王者还是众庶,只有尊重以永恒自然之道化育人伦的圣贤,只有珍视圣贤所开辟和传承的伟大政教传统,才能超越部落地域与王朝寿命的局限,创造出伟大的政治文明。
[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载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两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2][26] 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3] 蒙文通:《经史抉原》,成都,巴蜀书社,1995。
[4] 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北京,中华书局,2000。
[5][27] 魏源:《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载 《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
[6][7][8][9]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0] 庄存与:《序冬官司空记》,载王先谦编:《清经解续编》,卷一百六十一,上海,上海书店,1988。
[11] 庄绶甲:《周官记跋》,载王先谦编:《清经解续编》,卷一百六十六,上海,上海书店,1988。
[12] 庄存与:《春秋要指》,载阮元编:《清经解》,卷三百八十七,上海,上海书店,1988。
[13][14] 赵汸:《春秋左氏传补注自序》、《春秋集传自序》,载黄宗羲 《宋元学案》,卷九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
[15][16][17][18][19][20][21][22][23][24][25] 庄存与:《春秋正辞》,载阮元编:《清经解》,卷三百七十五,上海,上海书店,1988。
[28] 程农:《士大夫政治活力的恢复》,载彭明、程歗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 (1840—1949)》,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9][30] [31] 刘逢禄: 《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载阮元编: 《清经解》,卷一千二百八十,上海,上海书店,1988。
[32][33] 刘逢禄: 《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载阮元编: 《清经解》,卷一千二百八十五,上海,上海书店,1988。
[34] 刘逢禄:《论语述何叙》,载阮元编:《清经解》,卷一千二百九十八,上海,上海书店,1988。
[35] 宋翔凤:《论语说义序》,载王先谦编:《清经解续编》,卷三百八十九,上海,上海书店,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