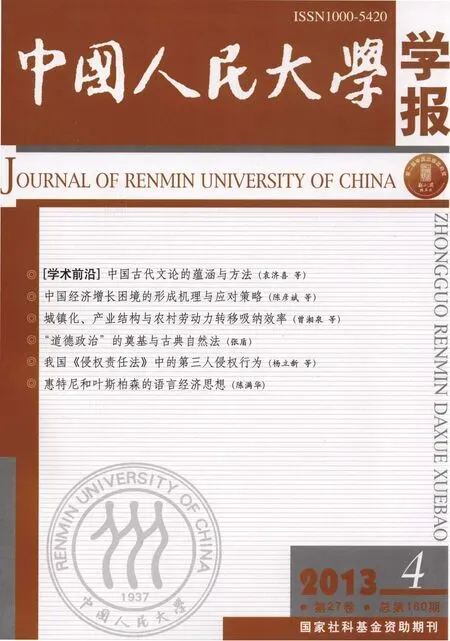阴阳五行与中国古代诗学
2013-01-23张毅
张 毅
阴阳五行原只是一种古人用来解释天地万物生成和社会变化的学说,当它与儒家的天道观和人性论相结合后,便形成涵盖宇宙人生各个方面的意识形态,成为支配中国人思想和审美判断的文化基因。它对中国古代诗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视诗为天地之心,以为诗歌之所以能感天地、动鬼神,在于诗能体现天道的变化,其声韵音律反映季节气候的自然律动;二是说天地四时的物色感动诗人情思,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因此创造情景交融的诗境;三是于 “无极而太极”的自然造化中领悟诗之神理,达 “万物静观皆自得”的天人合一境界。由开天辟地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宇宙论和天道观,到 “太极即理”、“诚即所谓太极”的本体论和心性说,是儒家阴阳五行思想两个相关联而又有所不同的发展阶段,充分体现了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诗性智慧。
一
阴阳五行作为一种以阴阳分判天地和以五行配四时的宇宙论和天道观,不仅是汉代今文经学的思想基础,也对纬书的过度阐释有深刻影响。诗纬《诗汜历枢》里的圣人 “明义以炤耀其所暗”和 “《诗》无达诂”两段文字[1](P482),均出自汉代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解经追求微言大义,是董氏“《诗》无达诂”说得以成立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成为纬书附会经义的思想根据。纬书是发明经义的,既然对经的解读可以没有达诂,也就很容易用流行的阴阳五行说附会经义,构成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诗纬《诗含神雾》说:
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孔子曰:诗者,天地之心,刻之玉板,藏之金府。集微揆著,上统
元皇,下序四始,罗列五际。[2](P464)
以诗为天地之心,意味着诗人可代天言志,体现天意之微,于是有 “四始”、 “五际”之说。诗纬 《诗汜历枢》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 《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3](P480)这里讲的 《大明》和 《四牡》等,均为 《诗》三百篇里的诗歌。所谓 “四始”,是将 《大明》等四篇诗,与五行中和四时相配的水、木、火、金相比附。而 “五际”则是把 《天保》等五篇诗,与表示阴阳二气消息的八卦方位图中的亥、戌亥、卯、午、酉等时辰相配。所谓 “卯, 《天保》也。酉, 《祈父》也。午,《菜芑》也。亥,《大明》也。然则亥为革命,一际也。亥(当为戌亥)又为天门,出入候听,二际也。卯为阴阳交际,三际也。午为阳谢阴兴,四际也。酉为阴盛阳微,五际也”[4](P481)。这样一来,表现人之性情的 《诗》,也就与由阴阳五行支配的天时相关联,为天人相感产生的神秘经典。
诗纬是谶纬神学的一种,其特点是把天人感应的灵异之说附会于对 《诗经》的解读中,使《诗》诡为象征性的谶纬神学隐语,似含有 “天”意,可预决吉凶。如汉元帝初元元年多水灾和地震,以传 《齐诗》著名的今文经学家翼奉奏封事曰:
臣闻之於师曰,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 《诗》、 《书》、 《易》、 《春秋》、《礼》、《乐》是也。《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臣奉窃学 《齐诗》,闻五际之要 《十月之交》篇,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犹巢居知风,穴处知雨,亦不足多,适所习耳。臣闻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天变见于星气日蚀,地变见于奇物震动。所以然者,阳用其精,阴用其形,犹人之有五臧六体,五臧象天,六体象地。故臧病则气色发于面,体病则欠申动于貌。[5](P3172-3173)
这种宣传天人感应的以灾异说诗,在汉代的诗纬里是很突出的。如 《诗推度灾》说: “上出号令而化天下,震雷起而惊蛰。睹旗鼓,动三军,骇观其前,动化而天情可见矣。逆天地,绝人伦,则天汉灭见。”[6](P468)以为诗小雅 《十月之交》象征阴阳错位,天下将乱,所谓 “百川沸腾,众阴进,山冢崒崩,人无仰。高岸为谷,贤者退;深谷为陵,小临”[7](P469)。又把某些诗看作天或神的预言,以为能给人以种种灾异的暗示。如此 “无达诂”的解诗,除了制造迎合当政者而曲学阿世的神学谶语外,就几近于六经注我的随意发挥了。
阴阳与五行的融合以天地间四时气象的变化为契机。孔子说过: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朗朗乾坤分判阴阳两仪,产生四时气象,天道即由春、夏、秋、冬“四时”节气的变化来体现。 《周易正义》在解释 《易系辞》的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时说: “两仪生四象者,谓金、木、水、火禀天地而有,故云两仪生四象。土则分王四季,又地中之别,故唯云四象也”[8](P70)。阴阳五行之气即天地四时之气,人秉天地之精气而生,实为天地之心,故汉儒除了用阴阳五行解释天道的自然气候变化,还用它来说明通人之性情的治道。翼奉说: “臣闻之於师,治道要务,在知下之邪正。人诚向正,虽愚为用;若乃怀邪,知益为害。知下之术,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贪狼,申子主之。东方之情,怒也;怒行阴贼,亥卯主之。贪狼必待阴贼而后动,阴贼必待贪狼而后用,二阴并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 《礼经》避之,《春秋》讳焉。南方之情,恶也;恶行廉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宽大,巳酉主之。二阳并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 《诗》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乐也;乐行奸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属阴,戌丑属阳,万物各以其类应。今陛下明圣虚静以待物至,万事虽众,何闻而不谕,岂况乎执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参实,亦甚优矣,万不失一,自 然之道也”[9](P3167-3168)。以为可用十二律来统御四方民众喜怒哀乐的情感,构建奉天承运而上下和谐的社会。所谓 “参知六合五行,则可以见人性,知人情。难用外察,从中甚明,故诗之为学,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兴废。观性以历,观情以律,明主所宜独用,难与二人共也”[10](P3170)。六情谓人的六种性情,即廉贞、宽大、公正、奸邪、阴贼、贪婪;律指与天文历法相配的十二乐律。
在与春夏秋冬四时相配合的十二乐律中,黄钟大吕被视为正声,以黄钟对应冬至所在的仲冬月份十一月为子月,而周历以建子之月为正月。董仲舒在解释《春秋》的“元年春王正月”时说:“元者,始也,言本正也。道,王道也。王者,人之始也。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11](P100-101)基于这种天人感应学说,天文历法可与十二律相配,而十二律源自古乐的十二调。《周礼·春官》云:“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以为乐器……凡为乐器,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以十有二声为之齐量。”[12](P42)《吕氏春秋》谓: “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13](P51-52)十二律可分为阴阳两类,凡属奇数的六种律称阳律,属偶数的六种律称阴律。阳律六: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阴律六: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应钟,皆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这些音律与一年四季月份的定数都是十二,汉儒在究天人之际时便把十二律和十二月联系起来。依照 《礼记·月令》上的记载,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为:孟春之月,其音角,律中太簇;仲春之月,其音角,律中夹钟;季春之月,其音角,律中姑洗;孟夏之月,其音徵,律中中吕;仲夏之月,其音徵,律中蕤宾;季夏之月,其音徵,律中林钟;孟秋之月,其音商,律中夷则;仲秋之月,其音商,律中南吕;季秋之月,其音商,律中无射;孟冬之月,其音羽,律中应钟;仲冬之月,其音羽,律中黄钟;季冬之月,其音羽,律中大吕。天文历法的节气与音乐声律的对应关系,就这样通过类比思维的方式建立了起来。
天道通过春、夏、秋、冬的节气变化来显示其周而复始的规律,反映自然界四季气候更替流转的乐律,在吟咏性情的诗歌声律里当有所体现。齐永明诗坛 “四声”说的倡导者沈约在 《答甄公论》中说: “作五言诗者,善用四声,则讽咏而流靡;能达八体,则陆离而华洁。明各有所施,不相妨废。昔周、孔所以不论四声者,正以春为阳中,德泽不偏,即平声之象;夏草木茂盛,炎炽如火,即上声之象;秋霜凝木落,去根离本,即去声之象;冬天地闭藏,万物尽收,即入声之象;以其四时之中,合有其义,故不标出之耳。”[14](P102)以 为 反 映一年四季气象的平、上、去、入四声之象,合于宫、商、角、徵、羽五音,故四象既立而万象生,四声既周而群声类。刘勰《文心雕龙·声律》说: “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故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 “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吟咏滋味,流于字句。气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故余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15](P552-553)唐代到中土来学习的遍照金刚弘法大师认为:“虽然,五音妙其调,六律精其响,铨轻重于毫忽,韵清浊于锱铢;故能九夏奏而阴阳和,六乐陈而天地顺,和人理,通神明。风移俗易,鸟翔兽舞。自非雅诗雅乐,谁能致此感通乎!颙、约已降,兢、融以往,声谱之论郁起,病犯之名争兴;家制格式,人谈疾累;徒竞文华,空事拘检;灵感沈秘,雕弊实繁。窃疑正声之已失,为当时运之使然。”[16](P396)在评论从齐梁到唐初的诗歌声律论时,他以阴阳五行揭示的自然音律为准绳,认为诗歌声律之美的关键在于音之轻重与韵之清浊的协和,而 “四声”、 “八病”之类的声病说则未免失之琐碎。
但在唐初的诗式、诗格著作里,各种声病说甚为流行,以至在 “八病”的基础上扩展至二十八病,将作诗的 “病犯”由声韵扩大到字义、结构等方面。如佚名的 《文笔式》论诗歌声病,除“平头”、“上尾”、 “蜂腰”、 “鹤膝”、 “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病外,还有 “第九,水浑病。第十,火灭病。第十一,木枯病。第十二,金缺病”等。[17](P88-89)五 行 里 与 四 时 相 配 的金、木、水、火,也被用来形容诗歌创作四声之象未协的声病。上官仪的 《笔札华梁》继承了齐梁 “永明”体重视声律的思想,除了谈 “的名”、“隔句”、“双拟”、 “联绵”、 “异类”等对法外,还有 “双声”对、 “叠韵”对的讲究。如诗曰:“放畅千般意,逍遥一个心。”[18](P245)上句的 “放畅”为双声,下句的 “逍遥”乃叠韵。相传王昌龄作的 《诗格》以为: “凡作诗之体,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辨则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19](P160)诗论家将建立在阴阳五行思想基础上的天地四时气象,与汉语文字的四声之象相类比,强调格高、律清、调美,声律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被凸显出来了。
二
经学的阴阳五行思想除了渗透在诗歌声律论里,对文学创作论也有影响。由于接受了 “诗者,天地之心”的说法,刘勰在 《文心雕龙》里称人 “为五行之秀”而倡论 “文心”。他以为:“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 《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 《乾》、 《坤》两位,独制 《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20](P2)他又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21](P1)基于这种文源于自然之道的思想,形成了文学创作上的 “物感”说。《文心雕龙·物色》谓: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气是联结物色与心情的媒介。钟嵘 《诗品序》云: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照烛三才,辉丽万有;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22](P1)
自然元气赋予万物和人类生命的活力,四时气象对诗人情感有直接的感发作用。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23](P2)四时的不同气候,以及种种人生际遇,皆可触发强烈诗情。 《二南密旨》论 “诗有三格”的情格时说:“耿介曰情。外感于中而形于言,动天地,感鬼神,无出于情。三格中情最切也。如谢灵运诗: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如钱起诗:‘带竹飞泉冷,穿花片月深。’此皆情也。如此之用,与日月争衡也。”[24](P179)《流类手鉴》说: “夫诗道幽远,理入玄微,凡俗罔知,以为浅近。真诗之人,心含造化,言含万象,且天地、日月、草木、烟云,皆随我用,合我晦明。此则诗人之言应于物象,岂可易哉!”[25](P414)这是说物色和物象与诗人情感有互动呼应的关系。
“物感”说凸显了天地四时气候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并与人文教化有联系。所谓 “顺春夏而生长,随秋冬而杀罚。开日月以照临,降云雨以洒润。均天地以载临,同阴阳以变化。察天象以定时,观人文以成化。则天地以行道,依鬼神以制义。履时以象天,养财以任地。治四气以教民,通八音以宣六气。律文而训俗,声为律,身为度,左准绳,右规矩。保合大和,克明俊德。谟九德,叙九畴,张四维,陈二柄。兴于仁,立于 《礼》,成于乐”[26](P567)。这里讲的 “兴于仁”,当为 “兴于诗”,也就是说诗歌是生命的感动、情意的抒发。王昌龄 《诗格》说:
昏旦景色,四时气象,皆以意排之,令有次序,令兼意说之为妙。旦日出初,河山林嶂涯壁间,宿雾及气霭,皆随日色照著处便开。触物皆发光色者,因雾气湿著处,被日照水光发。至日午,气霭虽尽,阳气正甚,万物蒙蔽,却不堪用。至晚间,气霭未起,阳气稍歇,万物澄静,遥目此乃堪用。至于一物,皆成光色,此时乃堪用思。所说景物,必须好似四时者。春夏秋冬气色,随时生意。取用之意,用之时,必须安神净虑。目睹其物,即入于心。心通其物,物通即言。言其状,须似其景。语须天海之内,皆纳于方寸。[27](P169-170)
诗歌创作的神与物游,源于自然物象的感召,落实在构思和语言艺术上。王昌龄以为:“夫文章之体,五言最难,声势沉浮,读之不美。句多精巧,理合阴阳。包天地而罗万物,笼日月而掩苍生。其中四时调于递代,八节正于轮环。五音五行,和于生灭;六律六吕,通于寒暑。”[28](P171)除物色外,由“五音五行”和 “六律六吕”构成的声律,也是诗歌美感的重要因素。皎然 《诗议》说:“夫诗工创心,以情为地,以兴为经,然后清音韵其风律,丽句增其文彩。如杨林积翠之下,翘楚幽花,时时间发。乃知斯文,味益深矣。”[29](P209)在强调诗歌创作感物兴情的重要时,亦注意诗的音律对偶。皎然《诗式》说:“气象氤氲,由深于体势;意度盘礴,由深于作用;用律不滞,由深于声对;用事不直,由深于义类。”[30](P224)他用高、气、情、思等词语来形容诗歌创作风格,以为 “风韵朗畅曰高”,“风情耿介曰气”,“缘景不尽曰情”,“气多含蓄曰思。”[31](P242)
吟咏性情的诗歌创作以感物言情为本色,这已经成为古代诗论家的共识。徐祯卿 《谈艺录》说: “情者,心之精也。情无定位,触感而兴,既动于中,必形于声。故喜则为笑哑,忧则为吁戏,怒则为叱咤。然引而成音,气实为佐;引音成词,文实与功。盖因情以发气,因气以成声,因声而绘词,因词而定韵,此诗之源也。然情实幼眇,必因思以穷其奥;气有粗弱,必因力以夺其偏;词难妥帖,必因才以致其极;才易飘扬,必因质以御其侈。此诗之流也。”[32](P765)他把诗歌视为精神之浮英、造化之秘思,又谓: “朦胧萌坼,情之来也;汪洋漫衍,情之沛也;连翩络属,情之一也;驰轶步骤,气之达也;简练揣摩,思之约也;颉颃累贯,韵之齐也;混沌贞粹,质之检也;明隽清圆,词之藻也。”[33](P767)主张诗歌应具有触感而兴的情韵和丽辞。陆时雍《诗镜总论》说: “诗之可以兴人者,以其情也,以其言之韵也。夫献笑而悦,献涕而悲者,情也;闻金鼓而壮,闻丝竹而幽者,声之韵也。是故情欲其真,而韵欲其长也,二言足以尽诗道矣。乃韵生於声,声出於格,故标格欲其高也;韵出为风,风感为事,故风味欲其美也。有韵必有色,故色欲其韶也;韵动而气行,故气欲其清也。此四者,诗之至要也。”[34](P1415)以为诗之佳者拂拂如风,洋洋如水,有情韵行乎其间而生气远出。他又说:“物色在於点染,意态在於转折,情事在於犹夷,风致在於绰约,语气在於吞吐,体在於游行,此则韵之所由生矣。”[35](P1423)诗之情韵源自感物,诗人须先自己受感动,其作品才能感动别人。
古人作诗讲究情动于衷而形于言的自然高妙。朱庭珍《筱园诗话》说: “盖自然者,自然而然,本不期然而适然得之,非有心求其必然也。此中妙谛,实费功夫。盖根底深厚,性情真挚,理愈积而愈精,气弥炼而弥粹。酝酿之熟,火色俱融;涵养之纯,痕迹迸化。天机洋溢,意趣活泼,诚中形外,有触即发,自在流出,毫不费力。故能兴象玲珑,气体超妙,高浑古淡,妙合自然,所谓绚烂之极,归於平淡是也。”[36](P2341)这种诗歌境界可以渐臻而难以强求。朱庭珍说: “写景,或情在景中,或情在言外。写情,或情中有景,或景从情生。断未有无情之景,无景之情也。又或不必言情而情更深,不必写景而景毕现,相生相融,化成一片。情即是景,景即是情,如镜花水月,空明掩映,活泼玲珑。其兴象精微之妙,在人神契,何可执形迹分乎?至虚实尤无一定。实者运之以神,破空飞行,则死者活,而举重若轻,笔笔超灵,自无实之非虚矣。虚者树之以骨,炼气熔滓,则薄者厚,而积虚为浑,笔笔沉著,亦无虚之非实矣。又何庸固执乎?”[37](P2337)他认为诗歌创作中,天然之趣为最上乘,使情景各得其真,使才气各逞变化,使虚实互相为用。其要义在于能以人工夺天巧,可与自然造化相媲美。
三
阴阳五行学说在儒家思想传统里有由经学到理学的发展变化,如果说汉儒侧重于宣传万物生成变化的宇宙论和天道观的话,那么宋儒则在此基础上发明了 “太极即理”的本体论,并将其落实于心性诚明,以为 “诚即所谓太极”。这种理学的精进对诗学的影响,可用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来概括。
宋代理学的奠基者周敦颐在 《太极图说》里说:“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 一 其 性。”[38](P5)朱 熹的解说为: “盖五行异质,四时异气,而皆不能外乎阴阳;阴阳异位,动静异时,而皆不能离乎太极。至于所以为太极者,又初无声臭之可言,是性之本体然也。天下岂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随其气质而所禀不同,所谓 ‘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则浑然太极之全体,无不各具于一物之中,而性之无所不在,又可见矣。”[39](P5)也就是说,“太极”蕴含互为其根的阴阳动静之理,阴阳二气交感而化生万物,而 “唯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40](P6)。人禀天地阴阳五行之秀气而生,人为万物之灵是指人的心性而言,其虚灵不昧之心体可用 “诚”来表示。周敦颐在 《通书》中说: “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41](P17)不诚无物,心诚则灵,以 “诚”作为纯粹至善的心体,静时中正平和,动则神明通达,其寂感已超越了动静。后来朱熹以 “真实无妄”定义 “诚”,以为 “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42](P31)。他又以 “诚”释 太极,谓“诚者,至实而无妄之谓,天所赋、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圣人之所以圣者无他焉,以其独能全此而已。此书与 《太极图》相表里。诚即所谓太极也”[43](P13)。宋儒以周敦颐的 《太极图说》和 《通书》为枢纽,完成了阴阳五行学说由言天地万物化生的宇宙论到心性诚明的本体论转变。
根据周敦颐 “立人极”时有关 “心”之动静的说法,程颢在 《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中认为:定性并非指心不应物而动,而是指心能超越动静而无将迎、无内外,做到动亦定、静亦定,保持心体大公无私的本然状态不变。他说: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 《易》曰: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孟氏亦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44](P460-461)他以天地 “无心”和圣人 “无情”,说明心体的廓然大公和应物无私。“无心”指无私心,“无情”指无私情,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心无内外和应物无累。从孔子说的天生万物而不言中,不难体会到天地生物之仁心,但唯有人心之灵明能觉察到这种生生之仁,并推及万物,有一种与物同体的感受和胸襟。程颢 《识仁篇》说: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45](P16-17)与物同体,谓视天地万物为一体,因人与万物皆由天地生生之德而来,所谓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缊,万物化醇’, ‘生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46](P120)。仁即天地生万物之意,为万物的本体,但它又是由人心来体现的性善,是心之全德,万物生生之理备于吾心而无内外。如此说,仁既是天道之自然,也是人道之当然,天命之谓性,天地间皆仁体的流行发用。二程将 《易传》和 《中庸》所讲的天道诚明,复归于 《论语》的仁学和 《孟子》的性善论所开辟的内圣之学,一举奠定了宋明理学 “内圣外王”的基本进路。
理得之于天而存之于心,以天地为依托的自然界是人的本源地,而人却是大自然的主宰,自然万物生机盎然而富有诗意,是由人心体验出来的。如程颢 《秋日偶成二首》所言: “闲来何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47](P482)从自然界和生活中体验生命意义,在追求人格道德完善的同时,心灵也获得一种情感的满足和美的愉悦,这是儒家理学的诗意所在。程颢说:“言体天地之化,已剩一体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对此个别有天地。”[48](P18)体即体贴、体验,指在自身心性中体察天理和人生意义,是心灵自证自明的内在感受,一种类似审美直觉的心灵活动。天地有生生之德,诗人可通过亲近和融入自然,体验万物一体之仁,并用吟咏性情的方式表达出来。朱熹 《送林熙之诗五首》其三谓:“天理生生本不穷,要从知觉验流通。若知体用元无间,始笑前来说异同。”[49](P251)他在《答杨宋卿》里说:“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50](P1757)所谓“高明纯一”指胸怀襟抱而言,要求保持心体的纯静虚灵。朱熹尝诵其诗示学者云:“孤灯耿寒焰,照此一窗幽。卧听簷前雨,浪浪殊未休。”“此虽眼前语,然非心源澄静者不能道。”[51](P113)他又说:
只如个诗,举世之人尽命去奔做,只是无一个人做得成诗。他是不识,好底将做不好底,不好底将做好底。这个只是心里闹,不虚静之故。不虚不静故不明,不明故不识。若虚静而明,便识好物事。虽百工技艺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虚理明,所以做得来精。心里闹,如何见得
朱熹主张作诗不应专意于声调格律的精粗和比事遣词的工拙,而要在心地根本上下工夫。他在 《易寂感说》里讲: “其寂然者无时而不感,其感通者无时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体,人心之至正,所谓体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时处分矣。然于其未发也,见其感通之体;于已发也,见其寂然之用,亦各有当而实未尝分焉。”[53](P3516)由 寂 静 感 通 明 心 之 体 用,使 儒家心性论性静情动的 “中和”说更为合理,这也是朱熹诗论的思想基础。他在 《诗集传序》中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54](P3965)以 心 体 虚 静 言 诗人感物而溢于言表,赋予 “物感”说更深邃的思想文化蕴含。
前人已注意到朱熹诗歌创作与其已经完全理学化了的阴阳五行思想的关系。吴师道 《吴礼部诗话》说:“朱子 《感兴》诗第一篇云:‘昆仑大无外,旁礴下深广。阴阳无停机,寒暑互来往。皇羲古神圣,妙契一俯仰。不待窥马图,人文已宣朗。浑然一理贯,昭晰非象罔。珍重无极翁,为我重指掌。’北山何先生曰:‘此篇三节,首尾一意。首四句言盈天地间,别无物事,一阴一阳,流行其中,实天地之功用,品汇之根柢。’”[55](P589)朱熹的 “《感兴》诗”,指他创作的组诗 《斋居感兴二十首》,其二云: “吾观阴阳化,升降八纮中。前瞻既无始,后际那有终?至理谅斯存,万世与今同。谁言混沌死?幻语惊盲聋。”[56](P177)以为天理通过阴阳二气的流行发用来体现。其十四云:“元亨播群品,利贞固灵根。非诚谅无有,五性实斯存。世人逞私见,凿智道弥昏。岂若林居子,幽探万化原。”[57](P180)谓“诚”乃人之心性最宝贵的品格,亦是万化的本源,正所谓 “静观灵台妙,万化此从出”(其四)。[58](P178)为说明这一点,还可举朱熹的 《水口行舟二首》为例:
昨夜扁舟雨一蓑,满江风浪夜如何?今朝试卷孤篷看,依旧青山绿树多。
在模山范水的性情吟咏中,在大自然鸢飞鱼跃的活泼生机里,作者体悟到天理的普遍和永恒,其山水诗所蕴含的生生之德,充分展示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诗性智慧。
受理学流行的影响,宋以后的诗论家倾向于从体天地之心、穷造化之变的角度谈山水诗创作。如朱庭珍 《筱园诗话》说:“夫文贵有内心,诗家亦然,而於山水诗尤要。盖有内心,则不惟写山水之形胜,并传山水之性情,兼得山水之精神,探天根而入月窟,冥契真诠,立跻圣域矣。”[60](P2344)之所以如此,正在于:
山水秉五行之精,合两仪之撰以成形。其山情水意,天所以结构之理,与山水所得於天,以独成其奇胜者,则绝无相同重复之处。历一山水,见一山水之妙,矧阴晴朝暮,春秋寒暑,变态百出。游者领悟当前,会心不远,或心旷神怡而志为之超,或心静神肃而气为之敛,或探奇选胜而神契物外,或目击道存而心与天游。是游山水之情,与心所得於山水者,又各不同矣。[61](P2345)
他以为 “况山者天地之筋骨,水者天地之血脉,而结构山水,则天地之灵心秀气,造物之智慧神巧也”。故 “作山水诗者,以人所心得,与山水所得於天者互证,而潜会默悟,凝神於无朕之宇,研虑於非想之天,以心体天地之心,以变穷造化之变。扬其异而表其奇,略其同而取其独,造其奥以洩其秘,披其根以证其理,深入显出以尽其神,肖阴相阳以全其天。必使山情水性,因绘声绘色而曲得其真,务期天巧地灵,借人工人籁而毕传其妙,则以人之性情通山水之性情,以人之精神合山水之精神,并 与 天 地 之 性 情、精 神 相 通 相 和 矣”[62](P2345)。也就是说,天籁尽在人籁,是一种精神状态。天地之心,生意盎然,精神焕发,人与山水性情相通,这是由具生生之德的虚灵诚明心体开出的天人合一境界。
[1][2][3][4][6][7]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5][9][10]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8] 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11] 苏舆:《春秋繁露义正》,北京,中华书局,1992。
[12] 崔高维点校:《周礼·仪礼》,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13] 高诱:《吕氏春秋注》,载 《诸子集成》,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54。
[14][16][18][26] 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5][20][21]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17][19][27][28][29][30][31] 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22][23] 陈延杰:《诗品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24][25] 陈应行:《吟窗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97。
[32][33] 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
[34][35][55]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36][37][60][61][62] 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8][39][40][41][43] 周敦颐:《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
[4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44][45][46][47][48] 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49][50][53][54][56][57][58][59] 朱熹:《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51] 罗大经:《鹤林玉露》,北京,中华书局,1983。
[52] 黎靖德:《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