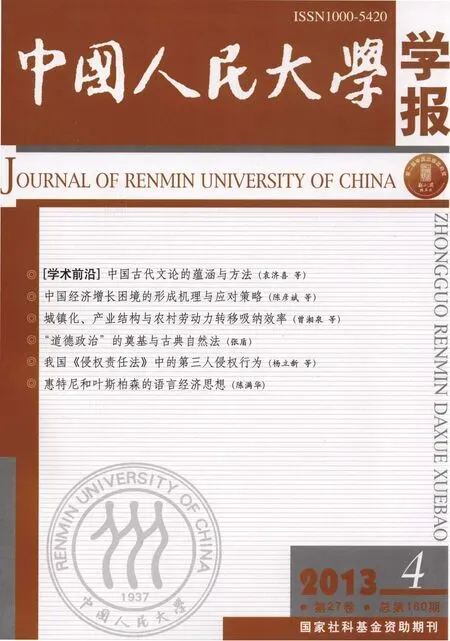惠特尼和叶斯柏森的语言经济思想
2013-01-23陈满华
陈满华
人类活动有一条根本性原则:经济原则(the principle of economy)。这条原则可以简单表述为: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益。作为人类的活动之一,人的语言行为处于该原则的适用范围之内,即存在一条语言的经济原则。语言经济原则是语言学理论里的一条重要原则,世界语言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其普遍意义。国外许多著名语言学家对此都有很深刻的论述,近年我国也有一些学者从共时和历史的角度分别探讨了语言经济原则在汉语中的表现。[1][2]本文拟梳理语言经济原则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侧重探讨语言经济原则的两位经典作家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的相关思想,兼论他们的理论与语言经济原则集大成者齐普夫(Gorge Kingsley Zipf)和马丁内(AndréMartinet)理论之间的承继关系。
一、语言经济原则的提出及其内涵
语言学界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美国语言学家齐普夫是第一位明确提出省力原则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的学者[3][4],法国语言学家马丁内在齐普夫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经济原则,他是最早正式提出这一原则的学者[5]①有人将省力原则和经济原则当做可以互换的概念,据此也可以认为最早提出经济原则的人实际上是齐普夫。参见姜望琪:《Zipf与省力原则》,载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1)。。然而,笔者近些年的考察表明,据目前掌握的资料,语言学界第一个明确提出经济原则这个术语的人是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马丁内提出经济原则,确实有齐普夫的影响[6],但是,也直接受到了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的影响,间接受到了惠特尼的影响。本节简述语言经济原则的产生经过及其背景。
有学者指出,在马丁内之前,有很多学者提出了类似经济原则的思想。例如,笛卡尔 (R.Descartes)、阿尔诺 (A.Arnauld)和朗斯洛(C.Lancelot)、保罗 (H.Paul)、科丘斯 (G.Curtius)、帕西 (P.Passy)等都间接提出了省力原则。[7](P9-12)索绪尔 (F.de Saussure)在谈“语音变化的原因”时也提到了省律 (the law of least efforts)的作用。[8](P148)
齐普夫于20世纪30年代发现文献计量学上著名的词频分布定律,世称齐普夫定律(Zipf's Law),并由此催生了1949年正式提出的省力原则。
1955年马丁内出版《语音变化的经济》(Economie des changements phonétiques),该书已经有了经济原则的思想,只不过主要谈的是语音问题。[9](P66)有语言学家将该书翻译为 《语音演变的经济原则》,因此也可以说马丁内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实际已提出语言经济原则。马丁内于1960年出版《普通语言学纲要》,书中正式使用了经济原则的术语。马丁内用语言经济原则解释语言变化的原因[10](P271),他认为,无论是语言成分的聚合还是组合方面,都有经济原则在起作用,有些简称也是经济原则作用的结果。他指出,语言经济原则对语音、词汇和语法各个层面的变化都有支配性的影响。经济原则作为规律支配着人们的言语活动,从该原则出发可以对语言结构演变的诸多方面做出合理的解释。[11](P76-77)[12](P13-14)在1962年出版的《语言的功能观》里,马丁内把省力原则和交际需要看成语言经济的两个主要构成因素,把两者结合起来考察。他指出:一方面,说话人需要传达足够的信息,达到一定的交际目的;另一方面,他(她)又尽可能少付出脑力和体力,从而达到最省力的目的。[13](P53-54)这就是语言的经济原则。
诚然,马丁内经济原则的提出受到了齐普夫的影响,但是,据我们所知,早于齐普夫和马丁内的叶斯柏森和更早的惠特尼都明确提出过类似的原则。叶斯柏森的 《语言的本质、发展和起源》(初版1922年)提出了语言学里的简易理论思想,这一理论与语言经济原则的内涵大体一致;而惠特尼早在1867年出版的 《语言和语言研究》里就有了语言经济原则的萌芽[14](P33),1875年,他在 《语言的生命和成长》里提出语言的简易倾向[15](P45-75),1876年他发表《作为语音动力的经济原则》一文,从语言视角正式提出了经济原则,该文即围绕语言里的经济原则展开讨论[16](P249-250)。 (详见本文第二部 分)据岑麒祥介绍,马丁内读过叶斯柏森的 《语言的本质、发展和起源》这本书,而且是他读过的第一本关于普通语言学的著作。[17](P63)因此,叶 斯柏森的这部名著无疑对马丁内产生了影响,可以确定,叶斯柏森的简易原则至少是马丁内的语言经济原则的来源之一,而叶斯柏森在讨论简易原则时又大量引用惠特尼的论述 (详见本文第三部分),可见他的简易原则又受到惠特尼相关思想的影响。
惠特尼、叶斯柏森、齐普夫和马丁内的相关思想或理论可统称为 “语言经济思想”。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称的语言经济思想不同于语言经济学。语言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门学科,其主要关注的内容包括人力资本理论下的语言与经济关系研究,例如语言的掌握状况与收入之间的关系;经济学语言的修辞分析,即经济学语言的运用本身;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来分析、考察语言的结构、现象及相关的语言问题。[18]①语言经济学在此处所述的最后一个研究领域与语言经济思想有交叉关系。例如,汉语普通话双唇音和舌尖中音d、t只能跟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韵母拼合,而不与撮口呼拼合,这样的分布主要是为适应人的生理发音系统,以求得发音的省力、和谐,从而在生理上达到经济的要求。参见王恩旭:《论经济机制在汉语言中的表现》,载 《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 (4)。语流中的许多音变现象,主要是因为拼读时发音部位来不及调整到原本的位置或精密度,音节或各音素的配合就会自然进行重新整合 (如:两个上声相连,第一个上声变为阳平;“不”字在去声前变为阳平,等等),这也适应了语言的经济性原则。这些体现了经济原则的变化可以用数据和数值精确显示。事实上,齐普夫已经把他的经济原则尝试运用到人口学和经济学等领域。参见姜望琪: 《Zipf与省力原则》,载《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1)。根据齐普夫的省力原则, “各种资源 (人力、货物、时间、技巧以及其他任何生产性资源)都存在一种进行自我调整以实现最小化工作量的趋向,因此,大约20%~30%的资源占到与这一资源相关生产活动的70%~80%。”(引自百度百科 “80/20法则”词条,http://baike.baidu.com/view/50,175.htm)可以说,齐普夫的省力原则在经济管理领域是对著名的帕累托法则 (80-20曲线法则)的重新发现和进一步阐发。语言经济学虽有交叉学科的性质,但是归根到底属于经济学范畴;而本文讨论的语言经济思想是由语言运用的简易原则发展而来的理论,基本不是交叉学科,属于语言学范畴。
我国学界对齐普夫和马丁内的相关思想已经有较为详细的评介,但尚未见到有公开出版物对惠特尼相关思想进行探讨,笔者见到的只有一篇硕士论文里有很简单的介绍[19](P20-23),且惠特尼的相关理论的许多内容在该文里没有谈及;而对叶斯柏森的语言经济思想,在学界也只被零星提
及过[20](P7-8)[21],尚无专题研究。鉴于此,我们在下文具体讨论惠特尼和叶斯柏森的语言经济思想。
二、惠特尼的简易倾向理论和经济原则
惠特尼 (1827—1894)是美国第一代语言学家的杰出代表,被公认为 “美国语言学的先驱和揭幕人”[22](P6、8)。在其一系列论著里,惠特尼提出了简易倾向、经济倾向、经济原则等概念,并进行了多角度论述,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简易倾向思想,并初步构建了语言的经济原则理论。
(一)简易倾向及其产生原因
惠特尼最早体现语言经济思想的论述见于其专著 《语言和语言研究》。他说: “所有的语音发出来都依赖力,消耗肺、喉和嘴里肌肉的能量。这个力,像其他所有人类发出的力一样,有一个本能的特点,就是寻求减负和避让——我们称之为惰性,或者称之为经济。”[23](P33)“实用的方便成了至高无上的考虑,其他的考虑都向其让步。”[24](P34)在本书中他已经使用了 “话语的简易倾向” (the tendency to ease of utterance)这样的表述,并初步提出这一倾向与语音变化有关系。[25](P35-36)不过作者没有展开深入讨论。这一思想在其代表作 《语言的生命和成长》里发展为简易倾向理论。
在《语言的生命和成长》的第3章,惠特尼通过具体例子提到了语言里的简省倾向 (tendency toward abbreviation)。他说:“我们又可以在许多词形里观察到减省倾向的影响。我们的Reste和hyngrede如今都失落了最后的e,这个e在古英语里存在,正如存在于今天的德语和意大利语里那样,构成了另一个音节。”[26](P38)该书第4章专门讨论简易倾向或经济倾向。惠特尼通过英语bishop这个词的外形演化过程说明语言里的这一倾向。他说,bishop这个见于多数欧洲语言的词来自希腊语的episkopos,这个希腊语词是个派生词,含有词根skep和词缀epi,词根的意思是 “看”(see、look),词缀的意思是“在”(at),因此这个词的原始义是 “检查者”、“督察者”。从形式上看,后来 “我们通过去除前后音节的方法把这个较长的头衔减缩为一个较短的形式”,并且保留的字母 (实际代表发音)也有变动。[27](P46)这样的变化有其内在的原因。惠特尼指出, “在这一处理上,我们发现的唯一倾向是话语里的力量经济倾向 (a tendency toward economy of effort)”。他说,语言形式 “会重新被调整,以让使用它的人感到更便利”,这就是语言的力量经济倾向。[28](P48-49)他 又 把 这 一 倾 向称为简易倾向(tendency to ease)。[29](P69)有时候,惠特尼也把这种现象称为经济倾向 (tendency to economy)。[30](P53)
惠特尼认为简易倾向造成语音衰减 (phonetic decay)。他说:语音变化有一个明确的趋势,那就是倾向于对语词和语言形式 (包括复杂的表达式和句法单位,如句型等)的简化和分解(mutilation),这种现象即语音衰减。语言单元组合的过程为简易倾向提供了广阔的活动场所,对简易的追求恰恰是在打破原有组合的过程中进行的。话语的组成单位起初统一起来,后来在“简易”目的的驱动下分裂。[31](P74)根据惠特尼的这一观察,我们可以认为,英语的hippopotamus(河马)简化为hippo,汉语的 “爱V 谁V 谁(如 “爱找谁找谁”)”在一定的上下文说成 “爱谁谁”,都是语音衰减的结果。
惠特尼还提出了精神经济性 (mental economy)的概念。所谓精神经济性,即 “避免费劲儿去记忆例外的形式以及在实际运用中遵守”[32](P74)。例如,英语里的ear的复数形式原来不加s,因为在盎格鲁 -撒克逊时期,单音节中性名词 (neuter noun)如果是长音量的 (即发长元音),复数则通常不加s。但是后来大家不愿去记这少数例外的情况,而是按照大多数名词复数加s的情形去表示,这样比较省事。[33](P38、74)这种经济性表面看多了一个音,实际上从记忆的负担角度说,少了记例外规则的麻烦,因此是一种精神上的经济性。
惠特尼认为简易倾向的产生与语言的性质有密切的关系。他说:“因为语言是一种工具,与其他工具相比,简化 (语言工具的)初始形式这一法则同样具有自然性和必要性。”[34](P226)他的意思是,人类在使用工具时自然会追求工具的易于操作性,语言既然是一种工具,人类在使用语言时,也自然会追求语言的简易性。
(二)简易倾向的重要意义
惠特尼主张,简易倾向并非简单地引导人们走捷径,这一倾向是语言发展的一个主流规律,符合语言本质的趋向,并且这一现象只会促进语言的简化和方便,而不会对语言产生任何伤害。他说:“省略掉语言的某些部分不会破坏对意义的理解,而会使语言更容易掌握,更符合习惯和偏好。语言科学还没有发现比这更基本的规律,或者能与此并驾齐驱的规律。这是贯穿世界语言的一个主流 (grand current),它推动语言材料向一个特定方向移动,尽管像其他潮流一样,它也有逆流 (eddies),小规模的相反方向的运动似乎可以占上风。这一主流趋势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引导人们在书写时使用简略写法,避开通常的路线而走捷径,以及诸如此类的办法。”[35](P50)
惠特尼还认为,简易原则 (经济倾向)具有建设性意义。[36](P23)他指出:“语言中的经济倾向恰恰在于它是 ‘破坏性’行为的同时也是具有建设性的行为。它最初产生的那些形式后来被删减(mutilate)、扔弃;如果没有简易倾向,合成词以及组合性的短语会一直是老样子。”[37](P53)简言之,其影响是使得松散的构造 “变成纯粹的符号,使符号更加简易”[38](P53)。这实际揭示了新词和新表达式产生的方式之一:对已有的形式进行删减或压缩,换句话说,惠特尼已注意到简易倾向对新语词和新表达式产生的推动作用。
惠特尼在讨论简易倾向的意义时已经有很周全的考虑,他细心地区分了 “经济”和 “糟蹋”(wastefulness)。他说:“这些举措不会对语言有任何伤害①“这些举措”指简易倾向带来的具体语言现象。,除非比潜在的经济性失去了更多的东西,那样确实就是 ‘懒惰’而非 ‘经济’了。在语言的运用过程中会出现两种情况:真正的经济 (true economy)和懒惰的糟蹋 (lazy wastefulness)。”[39](P50)这 里 实 际 提 出 了 两 个 观 点:第一,运用经济原则时的 “经济”是有度的,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不再是 “经济”而是由于懒惰而在“糟蹋”语言;第二,在语言演化过程中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是 “真正的经济”而非 “懒惰的糟蹋”。惠特尼的这一思想可用具体语言里的许多例子来解释,例如,汉语的 “俩”和 “仨”是 “两个”和“三个”的合音,是经济原则在语流里的体现,是“真正的经济”。然而,数字与 “个”的合音不能类推,类推就听不懂了,即成了 “懒惰的糟蹋”。又如,北京口语的代词“人家”在一定的场合可以省略为“人”,这是合适的“经济”用法,但是在某些位置上 (如处于句末)不可以省略。②“人牛大姐是怕你失足”(电视剧 《编辑部的故事》台词)是 “人家牛大姐怕你失足”的简省说法;但是 “这事你没告诉人家”却不能简省为 “这事你没告诉人”。[40]假如省却,就成了 “懒惰的糟蹋”。
(三)简易倾向对语言变化的具体影响
惠特尼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简易倾向对语言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将这些影响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简易倾向在语音同化现象上有充分的体现。语音同化是一个音接受另外一个音施加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发音变得更简易。惠特尼从元音和辅音的过渡谈起,他说,对于一个有经验的说话人来说,在连续的语流中,发音器官在元音和辅音之间、在开口较大和开口较小的位置不停地迅速转换。“通过减少开口音的开口度以及闭合音的闭合度,减少这种转换的摇摆幅度,就是一种经济表现,发音器官凭借经验肯定无意识地发出来了,并且学会付诸实践。”[41](P69)于是产生了最普遍的同化作用 (assimilating influence):元音和辅音彼此发生作用,每一类发音都使其他一类音靠近自己,元音变得有辅音特点 (consonantal),辅音变得有元音特点 (vocalic)。这样的话,语音变化的主导方向就是:某一个音从语音的极端位置移向语音图表的中间 (如低元音向央元音转化)③例如,字母a在重读音节里常读作 [ɑ:],是最低、最 (靠)后元音 (属于此处所谓 “极端位置”),但是在非重读音节里常读作 [ə](属于央元音),这就是低元音向央元音转化。America里前后两个a读作 [ə]就是这一央化现象的结果。,闭塞音 (mute)向擦音变化。[42](P69-70)
惠特尼观察到了一个他认为比较普遍的现象:在语流中,浊音成分 (包括元音)比清音多,因此语言里同化动力 (assimilative force)通常倾向于浊化方向 (the direction of sonancy),换句话说,更多的情况是清音 (surds)转化成浊音 (sonants)。[43](P70-71)这些现象都可以从简易倾向那里得到解释。①惠特尼所阐述的这一规律可能与汉语发展史的情况不符,甚至正好相反。
语音同化的对立面——异化 (dissimilation)也被惠特尼纳入了简易倾向的讨论视野。他说:“虽然在语音的相互调整中同化是主导性原则,但是其对立面异化也并非整个地不为人所知,因为人们感到同一 (发音)器官的两个动作紧挨着重现很累赘,便通过改变其中一个而避免这种累赘。”[44](P71)对累赘感的有意回避,显然是对简易的追求。
2.对语词形式的影响
(1)缩略倾向的出现。惠特尼指出,简易倾向导致缩略倾向 (abbreviating tendency)的出现。缩略倾向的一个表现是书写时词的缩写,另外一个表现是,一个曾经独立的词转化为词缀。这个词语成了依存性成分,即仅仅表明语法关系。随着语言的变化,某一复合词就变成了一个派生词。 “例如,语音方面的减缩会造成godly和godlike之间的区别:前者是一个派生词,包含一个词根和一个形式成分 (a formative element②“形式成分”此处指词缀。),后者只是一个复合词。”[45](P52)这告诉我们,派生词原来可以是复合词,词缀也可能来自于一个曾经独立的词,这一结果是缩略造成的,而缩略是简易现象的具体表现之一。
(2)形成不发音字母。英语等语言里的词汇有大量不发音的字母。惠特尼指出,书面语出现的不发音字母也是简易倾向或者简易原则导致的。他指出: “在英语和法语这样的语言的书面语中出现了数不清的 ‘不发音字母’ (silent letters),这些字母以前都有发音,其省略声音的字母在书面记录的过程中保留下来了。这些字母是以往普遍存在的话语模式的残余。”[46](P55)惠特尼认为,现代英语里频频出现的不发音字母 (如hour里的h)都是简易倾向带来的后果。
(3)造成音节衰减现象。这一现象是比字母不发音更进一步的变化形式。所谓音节衰减,是指简易和缩略倾向引起某些多音节的词的某一音节 (往往是末尾的音节)的丢失,最后成为单音节的(monosyllabic)。惠特尼指出,这种音节蜕变倾向如此之强,以致语言发展中的 “保守力量以及对语言传统的严格传承,已经不足以抗衡这一趋势的冲击 (inroads)”[47](P105)。当人们在实用过程中学习新语言时,往往犯错,尤其学不好词尾部分;如果他们已经掌握了词的主体部分 (即词根部分),能正确地沟通,那么他们就会求简易、省事,满足于从词语主体部分的联系上来理解主体部分与其他部分的关系,也就是理解这个词的意思。在这个过程中,词尾部分就蜕变、销蚀掉了。拉丁语在意大利人、凯尔特人、伊比利亚人等人的嘴里出现衰减现象、删略现象,形成了现代罗曼诸语言 (Romanic dialects)简化的形式,原因就在于此。
Yamaguchi等[27]发现,腺病毒E1A基因可显著增强HDACI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但正常卵巢组织细胞中并未观察到这一现象。HDACI可下调卵巢癌细胞中的抗凋亡基因BCL-xL,同时上调促凋亡BH3-only蛋白家族中的BIM蛋白。而E1A通过上调Egr-1直接参与BIM蛋白反式激活,BIM在肿瘤细胞中的表达进一步增强,起到协同促进肿瘤细胞凋亡的作用。HDACI联合E1A治疗卵巢癌,为临床提供了新的思路。
惠特尼说,在这一方面,英语与其他语言只是程度上的不同,为简易而出现缩略形式,为省劲而出现的表达形式是很普遍的,并且没有目标,是盲目的。在这一过程中到处都有对原语言系统的破坏。这样,音节衰减也就司空见惯了。[48](P105-106)上文提到,Reste在现代英语里丢失了e,双音节词成了单音节词,就属于此类情况。
(三)对语法的影响
惠特尼认为,简易倾向对形态和句法的历史演变也能产生影响。他指出,简易倾向可以弥补语法手段的不足,或者导致某一语法现象的消失或产生。例如,他认为,简易倾向导致了人们倾向于选用更加简单、省力的语法形式,因为运用某一更简洁的语法手段可以不占用多余的语法手段资源。例如 “格系统的脱落伴随着介词类的兴起”③例如,英语名词 “与格”(dative case)的消失伴随着介词 “to”、“for”的使用功能扩大。在惠特尼看来,这一重大历史演变也是简易倾向在起作用。,“语气 (mood)和时态的贫乏被丰富的助动词手段的引入所补偿”,等等。[49](P107)值得注意的是,这表明在惠特尼看来,运用介词是比运用格更加简易或经济的语法手段,助词的运用比语气和时态的运用更简易、经济。就是说,在英语发展史上,表示语法意义时词汇手段越来越丰富,而形态变化越来越萎缩,即以词汇形式代替形态变化,也是经济原则发挥效应的结果。
(四)经济原则及其作用
惠特尼在 《作为语音动力的经济原则》一文中,在语言简易倾向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原则这个概念,并对其在语音变化中的影响进行了阐述。惠特尼没有直接定义经济原则,从具体的解说看,这一概念所指基本是其简易理论,但有所深化。有时他也用经济倾向 (the economic tendency)、经 济 律 (the law of economy)的说法,指的都是经济原则。上文已述他曾经论及语音同化、异化与简易倾向有密切关系,在此基础上,惠特尼进一步指出:“要说明语音变化的全部,无需其他的方面,亦不可设想出其他的东西,归为 ‘缩略’和 ‘同化’这两方面即可。”[50](P250)
惠特尼说,语言的外向框架 (即语言形式)的节省,具体表现各式各样,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可以很方便地且很公平地用一个词 ‘经济’来总结。的确,所有变化,不管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目的都是为了增加使用的方便”[51](P253)。就是说,语言形式的一切变化都是出于对方便、简易的追求,即都有经济原则在起作用。他还进一步指出,“经济”或 “增加使用的方便”虽然没有直接提供新的语音形式,而只是使语音外壳“更加便于管控”而已,但是,“形式变化并非完全不能产生新的形式”[52](P253)。
惠特尼还批评有人怀疑经济原则的重要性,指出他们的思想表现出了一种不合理性。他强调语音方面的经济原则是语音变化的根本原因,非常重要,这一原则应当处于言语(speech)外部发展史的头等位置(a first-rate place)。[53](P250)
三、叶斯柏森的简易理论
惠特尼之后,丹麦著名语言学家叶斯柏森(1860—1943)对语言经济思想有较多的阐发。叶斯柏森系统综述了前人的简易理论及某些学者的不同观点,在介绍主张这一理论的学者时,正是以惠特尼作为代表,他还明确表示支持惠特尼的观点。显然,叶斯柏森的语言经济思想与惠特尼的经济思想有承继关系。下面简介叶斯柏森的简易理论及其相关工作。
(一)将简易倾向发展为简易理论
叶斯柏森的 《语言的本质、发展和起源》深入探讨了人类语言变化的原因,他的主要立足点是语音变化的动因,但也涉及词汇和语法等方面。他将语言发展的原因归为两大类:一为转化(transference)类,即一种语言传至外族人,外族人的母语的底层(substratum)影响新的语言;二为非转化类。[54](P191)我们认为,一类是外部的因素;二类是内部的因素。内部因素主要是人们追求省力对语言的变化产生影响。他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简易理论(the ease theory)。[55](P261-266)
叶斯柏森首先罗列了前人的几种语音 (乃至语言)变化观,主要有: (1)解剖学原因,即不同的生理构造影响语音的变化,如,有的语言学者提出,瑶族妇女在她们的上唇穿一个木制圆片,结果她们无法发出唇齿音 [f],而母亲对孩子说话的影响更大,久而久之,孩子学不到这个音,这个音从他们的语言里消失了,虽然在借词中可能死灰复燃。 (2)地理原因,即人们 (民族)所处的不同地理环境影响语音的变化,如高地德语的辅音音变在山区尤为明显。 (3)民族心理,如著名语言学家、 《格林童话》作者之一的格林(J.Grimm)认为,日耳曼语的辅音历时变化 (即格林定律所揭示的演变)是 “德国人进步的倾向和渴望自由的结果”。(4)说话的速度影响语音的变化。这里的 “速度”不是指个人的语速,而是一个民族或部落说话习惯语速。 (5)急剧的社会变动,如英法战争、黑死病等。叶斯柏森直接或委婉地否定这些语音变化观,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简易原则是语音变化的根本原因。[56](P256-264)叶斯柏森大量直接引用了惠特尼的观点,他说,惠特尼认为,在发音时,主要倾向是省时省力,而莱斯俭(Leskien)等人则持相反的观点。叶氏回顾了这一争论,大致倾向于前者,说明了人们在使用语言时的确都尽可能减少消耗,出现省力趋向,这种倾向使得有些词语被截短、缩略。他认为有一个求简易的原则在左右语言的演变,这一思想他称为简易理论。[57](P261-264)显然,简易理论的表述比简易倾向更进了一层。
(二)对简易理论的解读和运用
叶斯柏森不只是在字面上将惠特尼的简易倾向改进为简易理论,在对这一理论进行阐述时,增加或加深了相当一部分内容,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叶氏对语言要素是否简易进行了辩证的阐释。语言里什么要素简易?叶氏认为,对这个问题不一定有统一答案,“要确定两个发音中哪个更容易,并不总那么轻而易举,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意见不同——我们在相邻的两个国家可能发现相反的语音变化,而操这两种语言的人都确认各自的语言都朝着更为简易的方向发展”[58](P262)。就是说,语言要素的简易与否是相对的,对此的感知因民族语感的不同而不同,有时答案甚至截然相反。
其次,叶氏提出了简易倾向可能被其他因素中和 (neutralize,或译 “抵消”)的思想。所谓中和,是指某些因素抵消、削弱甚至阻止这个省力或求简倾向。他说: “正确的推理只能是简易倾向在某些情况下起作用,而非在所有情况下都起作用,因为别的因素有时抵消了这个倾向,或被证明比这个倾向力量更强大。”[59](P262)经验告诉我们,叶斯柏森所述这一现象确实存在。汉语里的 “外国语学院”这个名称在一定场合可以简化为 “外院”,但是结构相似的 “计算机学院”、“测绘研究所”却不能简为 “计院”、“测所”,因为它们分别与 “妓院”和 “厕所”谐音,从语用的角度说,既可能产生误解,又可能产生不雅的联想。于是,需要保持语义不被误解或保持和谐的交际,就成了中和或抵消追求简易的因素。
再次,叶氏加大了简易倾向的解释力度,扩大了解释范围。例如,语法方面,英语里曾经有丰富的格 (case)和性 (gender),但是现在基本消失了,他认为简易理论可以用来说明这一事实。许多语言学家认为这纯粹是语音现象,除了有语音自身的类推因素在起作用外,根本不用解释、也无法解释。英国词典编撰家慕雷 (J.A.H.Murry)就持有这种观点。但是,叶斯柏森坚定地表示 “我不敢苟同”,他认为这些变化的背后还有原因,这个原因就是简易原则在起作用。[60](P269)这些观点显然有惠特尼思想的影子,但是论述的范围更广、观点更为明晰,他甚至明确主张:“简易因素在语言变化的所有方面都发挥重要作用。”[61](P273)
(三)价值原则的提出
在阐释简易理论时,为了进一步说明语音变化的原因,叶斯柏森又提出了相关的价值原则(principle of value)。[62](P267-268)他没有直接定义这一概念,但是他所说的 “价值”有时用 “意义” (significance)代替,就是说,一个语言形式是否有意义就意味着是否有价值,而价值决定其是否受到简易原则的影响。前人 (如他的老师、著名语言学家汤姆逊 (Vilhelm Thomsen))提出使用频率高是语言变化的原因,但是叶斯柏森认为频率高并非真正的决定性原因,而是另有原因,即人们在交际中求简易,尤其是一个词或形式在实际语境中出现、具有无价值性 (worthlessness)的时候。[63](P268)根据他对无价值性的解释和提供的例子,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具体的上下文或情景中,一个语言形式通过简易原则被“简易”掉了以后不影响理解,那么这个语言形式在此环境里即具有无价值性。譬如,英语的Madame在名字前常常缩减为 [mam],mistress省为miss,旧式的说法还有用mas代替master的现象,等等。这些当时在叶斯柏森看来是极端的例子,就是因为这些语言形式在具体语境中其某一部分具有了无价值性,便受到了简易原则的约束,即出现了减省的情况,进而出现了语言变化的现象。叶斯柏森还举了俄语等其他语言的例子说明价值原则与简易原则之间的紧密联系。
叶斯柏森认为,无价值性不是语言变化的动力 (moving power),却是人们倾向于省力的原因,即为简易原则的成因。换言之,当一种形式在交际中失去富有意义的价值 (significatory value),就会出现变化,或者说,较为简易的形式 (此时为有价值)可以达到同样的交际目的时,那么较为费力的形式 (此时为无价值)就会发生变化。这是价值原则的基本思想之一。
四、讨论和结语
在上文的介绍和分析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惠特尼在19世纪70年代已正式提出语言的经济原则,比马丁内阐述这一原则早了80多年,比齐普夫提出 “省力原则”也早70多年。马丁内的语言经济原则直接来源于叶斯柏森的简易原则,而叶斯柏森的简易原则又受到惠特尼的相关思想的影响。到了齐普夫和马丁内,经济原则的论证更加科学和严谨,得到了数理统计的支持和确证,臻于成熟,其影响超出了语言学的范畴,自此,经济原则在许多学科和领域得到了成功运用和发挥。
(2)语言经济思想 (包括惠特尼和叶斯柏森的相关理论),不仅可以运用于对简单的语言表层现象的观察,也可以对深层现象进行阐释。正因为如此,这一思想对语言现象的解释力和适用范围远比一般人能想象的要深刻得多、广泛得多。例如,人们一般仅仅能感到缩略语是简易倾向或经济原则造成的,但是并不会意识到不发音字母、语音同化甚至异化、英语的形态减少而词汇手段增加,等等,归根到底都是简易倾向或经济原则带来的后果。惠特尼和叶斯柏森等的语言经济原则理论深化了人类对语言现象的认识。
(3)语言经济思想对于当前语言研究中的某些重大热点问题有显著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引起广泛关注的 “语法化”现象也与经济原则有紧密的联系。语法化指的是意义实在的词 (实词,如动词、形容词等)逐渐转化为意义较虚、表达语法功能的词 (即虚词)或其他成分。我国传统语文学的 “实词虚化”即属于语法化,但语法化除此之外还包括句法结构在历史演变中转化为词法结构,等等。语法化经典作家吉万 (Givón)甚至声称: “今天的词法就是昨天的句法。”[64](P28)霍珀 (Hopper)和特劳哥特 (Traugott)在讨论语法化问题时,都提到了经济原则和简易性(simplicity),注意到了经济原则与语法化之间的关系,并且指出,语法化是语言演变的一种方式,而经济原则是其内因或动因之一。[65](P72)
(4)无论是惠特尼的简易倾向观和叶斯柏森的简易原则,还是齐普夫、马丁内的语言经济思想,都不是简单地指出语言应用过程中存在追求省力的现象,而是都强调简易倾向或经济原则是语言变化的原因。惠特尼率先指出简易倾向是语言变化的原因,叶斯柏森进一步指出简易因素影响语言发展的所有方面。这种语言变化观揭示了语言演变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自有其深刻之处,但也有缺陷。语言的发展变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正如上文所述,不少语言学家曾经提出过多种理论来解释语言的演变发展,本文介绍的简易原则就属于 “说话快速省力论”之一种。这些原因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应该说都不是根本原因,这些理论只是揭示了语言变化发展的局部原因或表层原因,简易倾向也不可能作用于语言发展的所有方面。语言发展演变的根本原因和深层原因是语言参与社会交际活动,社会的进步、分化和统一,社会之间的接触,等等,都从根本上制约和推动了语言的发展。[66](P182)[67](P274)
当然,无论怎么评价这些学者的语言经济思想,我们都应该肯定:他们对语言变化的原因的探索精神难能可贵,他们前赴后继地为语言学理论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1] 王恩旭:《论经济机制在汉语言中的表现》,载 《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 (4)。
[2] 徐正考:《语言经济原则在汉语语法历时发展中的表现》,载 《语文研究》,2008 (1)。
[3][13][5] 韩芸:《“经济原则”发展概述》,载 《中国外语》,2007 (6)。
[4] 姜望琪:《Zipf与省力原则》,载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1)。
[6] Vicentini,Alessandra.“The Economy Principle in Language”.MotsPalabrasWords,2003 (3):37-57.
[7][12] 王晓娟:《语言经济原则——俄汉口语对比研究》,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
[8] Saussure.F.de.CourseinGeneralLinguistics.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
[9][11][17] 岑麒祥:《普通语言学人物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0] 廖秋忠:《马丁内,A》,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北京·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14][23][24][25] Whitney,W.D.“Language and the Study of Language”.In Michhael Silverstein (ed.).WhitneyonLanguage.London,Cambridge:The MIT Press,1971.
[15][26][27][28][29][30][31][32][33][34][35][37][38][39][41][42][43][44][45][46][47][48][49] Whitney,W.D.TheLifeandGrowthofLanguage.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Inc.,1979.
[16][50][51][52][53][54] Whitney,W.D.“The Principle of Economy as a Phonetic Force”.In Michhael Silverstein (ed.).WhitneyonLanguage.London,Cambridge:The MIT Press,1971.
[18] 张卫国:《语言经济学三大命题: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2-23。
[19][36] 王琳:《惠特尼语言学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20] 任绍曾:《叶斯柏森语言学选集》译序,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
[21] 李朝:《叶斯柏森论语言的变化》,载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 (6)。
[22] 赵世开:《美国语言学简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
[40] 陈满华:《北京话 “人家”省略为 “人”的现象考察》,载 《汉语学习》,2007 (4)。
[55][56][57][58][59][60][61][62][63] Jespersen,Otto.Language:ItsNature,Developmentand Origin.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22.
[64] Hopper,P.J.&Traugott,E.C.:《语法化学说》(沈家煊导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65] Hopper,P.J.&Traugott,E.C.Grammaticalization.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
[66] 马学良:《语言学概论》,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1。
[67] 胡明扬:《语言学概论》,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