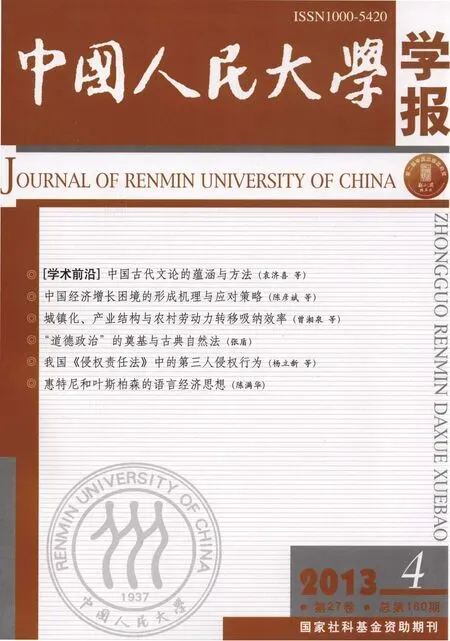社会管理创新的儒学解读——康德权利话语的倒转意义与内在困境
2013-01-23李兰芬朱光磊
李兰芬 朱光磊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较多的社会问题,社会管理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在当下中国的社会管理理论中,对于 “社会”的解读则显得较为模糊。事实上,对于 “社会”的理解正确与否,不但关涉社会管理的目标状态的设定,更影响到具体的治理方案的实施。有什么样的 “社会”解读,就有什么样的价值目标及相应的治理措施。因此,厘清 “社会”的真实意涵,就成为中国社会管理创新中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中国儒家传统的天下观在深层意义上可以与当今社会管理的 “社会”意涵相会通,并为中国社会管理的目标状态的设定和治理方案的实施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当前中国社会管理中“社会”的两种意义指向及其理论困境
当前中国社会管理的多种实践模式反映了人们对于 “社会”的不同解读。周笑天等学者编著的 《社会管理学概论》一书认为: “依据管理主体的不同,划分为国家管理和社会组织管理。国家管理又称社会行政管理,指国家政权机关依据法律和政策,运用各种手段,对社会组织、个人、社会活动进行指导、调控,使社会系统协调、稳定、有序地发展;社会组织管理又称社会自治管理,指社会组织、群众团体根据社区公约、组织章程、活动计划,对一切范围或方面的社会生活、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进行指导、约束和协调。”[1](P9)上述两种模式的不同在于:国家管理在于通过国家行政来管理社会,国家是管理主体,社会是管理客体。社会组织管理在于通过社会组织自身来管理社会,社会既是管理主体又是管理客体。在前一种模式中,社会被认为并不具有自我完善的功能,它的完善需要依靠外在的力量。在后一种模式中,社会被认为具有自我完善的功能,它的完善来自于内在的力量。
然而,无论是国家管理还是社会组织管理,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将人类生活整体划分为国家与社会两个部分。国家与社会对立两分的状态是两种管理模式的隐性前提。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社会管理理论中 “国家—社会”对立两分的前提来自于西方的公民社会理论。在西方的政治学语境中, “社会”的最初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从现代意义上看,对“社会”的理解以霍布斯的相关思想为发端。自霍布斯开始,社会被分为政治社会和公民社会两部分。在随后的发展中,政治社会逐渐指向政治,公民社会逐渐指向社会,社会就成为政治之外的分立之物。黑格尔与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来理解社会,黑格尔将作为政治领域的国家置于社会之上;而马克思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社会作为基础决定着国家意识形态。葛兰西则标明了社会的文化意涵。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中,社会作为最为原发性的公共空间,以一种广义文化的形态异于政治、经济,又是政治、经济得以合理化运行的基础。[2]固然,“社会”的含义在西方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政治哲学家文本中有不同的理解,但他们却具有将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的共同特征。在马克思以前,他们普遍抬高国家的地位,强调国家的神圣职能;在马克思及其之后,他们则抬高社会的地位,强调社会的基础性作用。郑杭生先生认为:“在西方的文化和社会语境中,‘国家—社会’的紧张关系既是一种历史的常态也是一个现实的困境。在社会学理论中,一些代表人物和一些理论流派,都是在将国家和社会对立起来的前提下,理论地描述两者那种尖锐的对立关系。这些观点也许适合或部分适合西方的情况,但它们既不符合中国的传统,也不符合中国的现实,不能照搬。”[3]
在国家与社会对立两分的前提下,无论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管理模式,还是以社会为主体的管理模式,都会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对于国家为主体的管理模式而言,它的实质是国家控制社会,仍旧为 “家长式”的管理,完全不利于社会自身的成长,是一种消极的管理方式。对于社会为主体的管理模式而言,固然承认了社会的自足性,但国家的作用似乎成为累赘。这既难以从理论上说明国家存在的合理性,也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笔者认为,对于上述管理模式问题的解决,需要借鉴中国经验。如果我们用返本开新的方式对儒家天下观做出深层解读,并与“社会”的意涵做一会通,或许能够对于中国当下社会管理的理论创新产生引导作用。
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社会管理目标的儒学解读
在讨论儒家天下观之前,需要将传统的政治现实与政治理想做一区分。在传统的政治现实方面,中国具有长期的极权主义传统。但在政治理想上,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政治设计多与现实政治有所抵牾。儒家将政治理想假托为三代,认为三代符合了儒家的政治理想,三代之治为王道;而自三代以降,则是架漏过日,只有霸道而没有王道。天下观集中体现了儒家的理想政治设计,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儒家对于社会管理的积极态度。
“天下”意为上天之覆,它并不表达地域含义。“天”指 “天道”, “天下”乃是 “天道”所覆所载,为 “天道”在现实中所体现的人伦生活。作为人伦生活的人道就是天道的落实,而天道亦是人伦生活发展完善的终极力量。《易》曰:“观乎人 文,以 化 成 天 下。”[4](P246)“人 文”即 为不离天道的人伦生活,故人伦生活终将在天道的作用下发展完善。所以,儒家的天下观旨在说明人伦生活中含有道义的运行,由此展现出人与人、人与物和谐相处、一体遍仁的生活世界。儒家天下观在 《礼记·礼运》中有十分精彩的表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5](P582)
儒家的天下观与大道合为一体。在大道运行的情况下,天下呈现出公平正义的良好状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儒家社会管理的目标与使命。在此总纲下,建立 “选贤与能”的人才选拔机制,“讲信修睦”的人际交往关系,“皆有所养”的社会福利保障, “男有分”的多样职业选择,“女有归”的妇女权益保障,“货、力不为己”的自我奉献精神,“谋闭不兴、盗贼不作、外户不闭”的社会安全体系。
韩愈在 《原道》中对 《礼运》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拓展,将儒家的天下观阐发为整个文明人的日常生活共同体,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蔬果、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 ‘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6](P3-4)韩愈所描述的大道包含了文教、礼法、身份、服饰、食物、道德准则、宗教信仰等。这些既是 “大道之行”的存在域,又是古代中国人最为完整的日常生活共同体。
由《礼运》篇与《原道》篇中的描述可以看出,儒家的天下观涵盖了人类生活的整体,不但包含经验性的事物以及人际交往,更包含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作为整体的生活世界,大道在生活世界中默默地发挥着作用,于是,儒家的天下具有了自我完善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是道的承载,每一个人在 “我”的视域中既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而受到普遍的尊重,又以一个特殊身份者的形象而获得具体的交往。因此,他人对于 “我”并不是工具性的物,而是与 “我”共在的活生生的人。在此共在的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建立在相互尊重对方人格的前提下,并据此而设置生活世界的礼法。公平正义之所在,即是大道运行之所在。在此天下状态中,人伦交往趋于和谐,事物安排趋于合理。
三、天下为主,君为客:社会与国家辩证关系的儒学解读
钱穆认为: “就中国历史大传统言,政治与社会常常是融合为一的。上下之间,并无大隔阂。”[7](P44)儒家经典 《大学》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做了如下表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8](P3-4)大道与天下的一体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它以个体的 “明明德”为始端,终于 “明明德于天下”的至善状态。“明明德”在于说明每一个体对于健康的生活态度都有所体悟和实践,它最初仅仅在个体身上获得觉醒,继而有所扩充,在家庭、社群、国家中获得显现。个体、家庭、国家既为“天下大道”的生成建构,又是 “天下大道”的显现载体。 “天下大道”是潜在的本体,存在于每个个体 “明明德”之先; “天下大道”又是实践上展开的必然结果,呈现于 “明明德”扩充之后。如果说 “天下”大道具有潜在的客观普遍性的话,那么, “明明德”就是主体对于此客观普遍性的践履和实现。天下既是生活世界的本源又是生活世界的整体。儒家从本源中寻求人之为人的终极依据,并通过每一个体当下的生活实践,建构和谐的人与人、人与家、人与国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逐步展开天下整体。
在儒家的视域中,天下具有整体性和奠基性的特征。从整体性上看,天下包含了个体、家庭和国家,国家是天下的一部分。因此,天下是整体,国家是部分。从奠基性上看,天下是原发的创生性的力量,而国家合法性的基础需要建立在此力量之上。因此,天下是原发,国家是后发。黄宗羲认为 “天下为主,君为客”[9](P2),天下具有整体性和奠基性的特征,是主导性的力量,而以君主为代表的国家则是客从的部分与后发的机构。天下若缺少良好的国家的体现,就无法完满地开展;国家若缺少天下的基础,就丧失了合法性地位。因此,天下与国家的关系是主导与客从的一体关系。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天下与国家的主导与客从的一体关系并没有得到完全体现。于是,天下与国家就呈现出两种关系:当国家显现 “天下大道”之时,国家获得国家之所以为国家的合法性地位,国家与天下为一体。国家与天下一体的状态是藏天下于天下,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天下的资源为天下之人所共享。当国家遮蔽 “天下大道”之时,国家丧失其合法性地位,国家与天下就由原来的部分与整体、后发与原发的关系转变成部分与部分的对立关系。国家与天下对立的状态是藏天下于筐箧,天下是执政者一人之天下,天下的资源为少数人所独占。
在一人之天下的状态中,天下的整体性丧失了,国家成为与天下对立的东西。天下的奠基性隐退了,国家就丧失了合法的根源,成为高居于民众之上、不需经过民众同意而自我裁断的权力实体。在固化的国家的视域中,天下成为乱民与群氓流动的空间,故国家需要对天下进行强制管理;在狭隘化的天下的视域中,国家成为政治独裁、经济聚敛的渊薮,天下就有暴动与革命的趋势。顾炎武面对国家与天下对立的情况,分辨了丧失合法性的国家与具有整体性和奠基性的天下的区别,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10](P756-757)亡 国 是 后 发 的 政 治 建构的灭亡,而亡天下是文化生活共同体的终结。在国家与天下对立的情况下,国家本身不具有合法性地位,故亡国仅仅是作为 “肉食者”的执政者承担责任。只要作为源泉的公平正义的力量还在人心中显现自身,则良好的政治构架不久就会重新建立。但亡天下与之不同,在亡天下的状态中,公平正义的力量无法再从人心中显现自身,人的存在基础已经隐藏,身、家、国也就失去了价值的来源,国家渐趋于独裁专断,由客从地位上升为主导地位,天下则日渐萎缩,由主导地位下降至客从地位。
四、天下之法与一家之法:社会管理途径的儒学解读
中国传统的管理之道即是治道。在儒家哲学思想中,治道需要通达政道才真正具有合法性地位。政者,正也。 “正”可以就具有普遍性的天下而言,亦可以就具有主体性的天下人而言。从普遍性上说,政道即是天下敞开自身,成为天下人之天下。从主体性上说,天下人皆有良知天理,即人人皆有自我完善的潜在能力。天下之人需要由封闭转向敞开,扩充自己的存在域,发挥自己的潜能,健全自我的人格,协调与他者的关系。这种良好关系的范围由最初的 “明明德”而拓展至作为整体的 “天下”。每个人在天下状态中,将良知所营造的和谐关系推广至他人他物,把他人看做是与自己一样具有良知的人而不是实现自我目标的工具,从而形成人人自主自律,人人与他人他物同源共生的大同社会。这种天下状态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也是治道所要促成的最终结果。因此,儒家的治道既是政道的体现,又是促使政道实现的途径。
儒家的治道在于防止天下与国家分为两截,促成天下与国家复为一体。治道主要体现在法、礼两个方面,它们的共同指向则是天下大道。法是刚性的制度,其意在于预防恶迹;礼是柔性的约束,其意在于规范善行。当法被不正当运用时,法成为执行者镇压异己的工具,法即是非法之法。当礼被不正当运用时,礼成为人格自由发展的束缚,礼即是非礼之礼。正当的法、礼有助于天下状态的展开,非法之法、非礼之礼则阻塞了天下状态的展开。
儒者黄宗羲在 《明夷待访录》中也阐述了类似的理念,在“天下大道”的状态中,治道的实施是为了成就天下的自足性,其管理之法度为天下之法。在天下与国家对立的状态中,治道的实施是为了造就执政者自身的权威,其管理之法度为非法之法。黄宗羲说: “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在后世方议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见上之可欲,不见下之可恶,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11](P6-7)天下之法能够促成天下的展开,而非法之法则阻塞了天下的展开。天下之法的执政者将自己融入天下之中,每个人在此生活世界中都得到良性发展。而非法之法的执政者则将天下藏入自己的私囊,每个人的生活都被压榨敲剥,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资源都被执政者所独占。政治、经济资源的不正当倾斜必然制约每个人自我发展的内在要求,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争夺,最终导致暴乱的产生。
执政者是实施法之主体。执政者的正义与否在于是否秉承天下的生生之源。倘若执政者体现了公平正义的天下精神,他所实行的就是天下之法。倘若执政者掩盖了天下的生生之源,他就成为天下开显的阻碍。如此的执政者则不具有合法的价值,其所实行的是非法之法。非法之法及其执政者都需要在“天下大道”的实现过程中得到转换和破除。管理之法由阻塞天下转变为疏通天下,执政者由强力占权的独夫转变为民众同意的贤者。
五、会通与转型:儒家天下观对于当今社会管理的现实启示
当我们在社会管理理论的问题域中追问何为社会时,需要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为什么要进行社会管理?社会管理的主体和客体是什么?如何进行社会管理?儒家天下观可以回答上述三个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与社会管理理论会通。
其一,儒家天下观与社会管理的目标和使命的会通。为什么要进行社会管理?或者说,社会管理的目的是什么?孙立平先生认为:“社会管理的真正目的是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而积极的社会管理则以主动的建设和变革为手段,以改善社会的状况、建设一个充满幸福感的、更好的社会为目标。公平正义是积极社会管理的实现途径。健全社会机制是积极社会管理的关键。”[12]儒家天下观强调“天下为公”的整体生活世界,追求止于至善的最终状态,是对于在群体中的人的最大的尊重,在实质上与社会管理的目标相同。
其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重新解读。谁来进行社会管理?管理谁?这是社会管理的基本问题。无论是社会为主体,还是国家为主体的解读模式,都无法处理国家与社会两分对立的困境。通过借鉴与吸收儒家天下观的解读模式,则可以发现社会的整体性、原发性的特征,国家的部分性、后发性的特征,以及社会与国家是主导与客从的一体关系。作为整体的能够自我完善的社会是管理主体,而社会自身局部的不完善是管理客体。如果国家能够以整体的生活世界为本位和基础,那么,国家对于社会局部的不完善的干预为正当;如果国家不能够以整体的生活世界为本位和基础,则国家反而作为社会局部的不完善而需被剥夺僭越的权力。
其三,天下之法与社会管理途径的会通。如何进行社会管理?社会管理的途径或方法是什么?王宁先生认为: “社会管理的 ‘管’主要是指 ‘负责’,理指的是调节、处理和供给。因此,不能把 ‘社会管理’理解成去 ‘管社会’或去‘控制人’,而应该主要理解成 ‘提供服务’,即为满足人们的社会需要而进行的社会服务的供给、社会事务的处理和社会关系的调节的过程。”[13](P3)“管社会”、 “控制人”是一家之法,而 “提供服务”则为天下之法。天下之法的具体实现途径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天下之法具有无为而治的色彩,即不干预、不折腾,让社会自身良好地发展;另一方面,天下之法具有有为而治的色彩,即积极创造有利条件,服务社会,为社会的完善建制立规,保驾护航。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阐释,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天下观与社会管理理论具有内在一致性。借鉴儒家天下观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社会是人类生活世界的整体,具有自我完善的能力,其目标指向是公平正义。社会与国家是主导与客从的一体关系。社会管理是社会自己管理自身局部的不完善,而国家成为促进社会成熟的辅助设施。由此,社会管理隐含着国家退居与社会成熟的意味。在社会尚未成熟而有待发展的阶段,良性的政府需要引导社会的完善:一方面,依据天下大道生生之源的力量,构建正当的礼法措施以保证全社会的公平正义;另一方面,破除错误的礼法措施以疏通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在社会成熟后,国家需要自我避让,退居为公共领域的服务者。
中国当前的社会管理服务于现代化转型的总体布局。正如邓正来先生所说: “中国现代化始终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结构性挑战:作为现代化的迟—外发型国家,中国必须作出相当幅度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调整,以容纳和推进现代化的发展。在这一结构调整过程中,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被认为是如何改造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权威形态,使其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获致合法性并转换成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核心。然而,正是这一挑战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困境。”[14](P14)当下中国的社会管理既包含了国家对于社会的管理,又包含了国家帮助社会进行自我完善的管理。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作为自治共同体、国家作为公共服务者的格局尚未形成。这是中国在全面现代化转型中所遇到的重大问题。
从近期来看,中国社会由于多种原因尚不成熟而有待完善,国家对于社会的干涉与调控仍然十分必要。在社会自治尚未完善之时,国家可以减少错误的行政干预,普及社会自治的文化理念,制定良性的社会运行规则。就长期发展而言,社会管理的现代转型则为中国社会管理发展的必由之路。在中国全面现代化的转型期,国家应该抓住契机,引导社会发展成熟,培育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国家自身逐渐从公共领域的治理者转化为公共领域的服务者,社会逐渐从被管理的受动者转变为管理的主动者,从而真正实现“还天下以天下”的理想。
[1] 周笑天等编:《社会管理学概论》,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2] 李佃来:《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探讨》,载 《哲学研究》,2004 (6)。
[3] 郑杭生:《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与中国社会学使命》,载 《社会学研究》,2011 (4)。
[4]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华书局,1994。
[5] 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
[6] 韩愈:《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卷一,北京,中华书局,2010。
[7]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8]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9][11]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10]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2] 孙立平:《走向积极的社会管理》,载 《社会学研究》,2011 (4)。
[13] 王宁主编:《社会管理十讲》,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
[14] 邓正来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