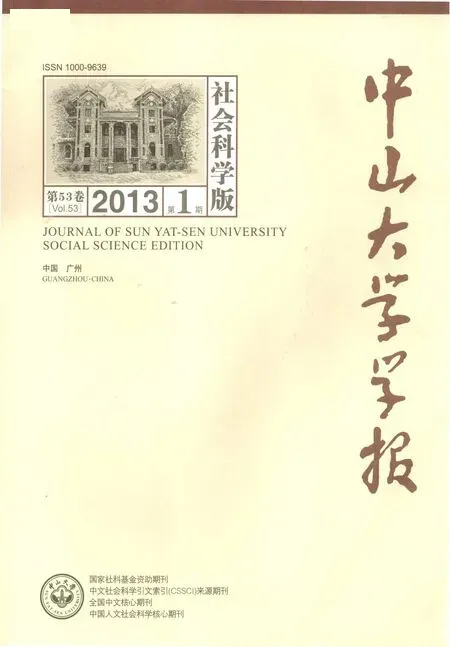组织化利益表达:理论假设与经验争论*
2013-01-23黄冬娅
黄冬娅
多元主义关于组织化利益表达的理论假设以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作为经验模板,然而,即便在成熟的西方民主政治中,利益集团政治在相当大程度上也只是美国独有的政治生态。在欧洲国家,阶级政治是更为凸显的政治主题;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它们在政治和经济转型过程中面对更加严峻的挑战。因此,与多元主义坚持组织化利益表达的重要性的观点不同,在经验研究中,特别是对于非西方国家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组织化利益表达发挥的并不一定都是积极的作用。不管是新兴民主国家民主化进程中面对的政治稳定问题,还是东亚国家经济腾飞阶段所要处理的政治开放问题,抑或中国国家重建过程中面对的特殊利益集团问题等,都使得研究者对于组织化利益表达的影响产生了争论。本文以多元主义组织化利益表达的理论作为参照,回顾和评述相关经验研究中有关利益的组织化表达存在的争论,以期深化对当前中国组织化利益表达的认识。
一、关于“组织化利益表达”的理论假设
“利益表达”是指公民和公民团体向政府表达他们的需要和要求。多元主义者向来假设有组织的利益表达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阿尔蒙德把利益表达区分为原子化(Anomic)利益表达,比如,通过庇护关系追求个人利益;非团体式(Non-associational)利益表达,比如,松散组织罢工中的工人以及游行中的市民寻求共同利益的实现;制度性 (Institutional)利益表达,比如,官僚组织追求本部门的利益;团体式(Associational)利益表达,比如,女权组织、环保组织和劳工组织等通过组织化的方式追求其成员的利益。而所谓组织化利益表达主要是指团体式利益表达,即公民通过组成社团或者利益集团(group)来表达自己的利益①Gabriel Almond,Comparative Politics Today:a World View.New York:Longman,c2000.。其中有劳工组织、同业协会、农业集团以及诸如医学协会、退伍老兵协会和妇女协会等职业和非职业的团体组织。
可以看到,多元主义对于利益表达的分析有两个层次,即以个人为单位的表达和以组织化的利益集团为单位的表达。相对于个人化的利益表达方式,组织化的利益表达是实现民主政治最重要的途径。在阿尔蒙德看来,最简单的利益表达是个人通过政务官和议员等向政府提出要求或请求,而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则加强了个人要求的力量和有效性。
在对于组织化利益表达的分析中,多元主义者的根本立场是为利益集团正名。在他们看来,利益集团并非代表了“自私”和“特殊利益”。其重要的理由在于,并没有具有超越不同集团利益的国家整体利益存在。虽然在战争时期,国家利益被用来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但是,从集团的角度解释政治时,我们就不需要解释一种完全一致的整体利益,因为这种利益并不存在②David B.Truman,The Governmental Process: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ublic Opinion .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c1951.。因此,如本特利(Bentley)所言,民主政府就是平衡社会中各种竞争性的利益,而组织化利益的相互竞争是社会中利益表达的主要方式③Authur Bentley,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a Study of Social Pressures.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c1995.。组织化利益团体中的多重成员身份是在多元民主政治中的一个平衡因素,它使得没有一个固定的利益集团永远并在任何地方都处于支配地位④David B.Truman,The Governmental Process: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ublic Opinion .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c1951.。
在过去几十年中,多元主义的利益表达理论不断地遭遇挑战。比如,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奥尔森(Olsen)对多元主义利益集团的可能性发出了挑战,他认为多元主义的利益集团理论忽视了搭便车以及交易费用的存在。事实上,由于这两个因素的存在,现实中的组织化利益团体总是那些人数少而获利大的集团。因而,组织化利益表达最终导致的是特殊利益集团占据支配地位,操纵公众的偏好和官员的行动;而大多数的公众利益则无法组织起来影响政府⑤Mancur Olse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所以结果并不是如多元主义所预测的那样,社会各种利益都能够组织起来并相互竞争,而是特殊利益集团统治了国家。美国国内的民意调查也显示,2000年大约60%的公众认为政府由少数大的利益集团所操纵⑥David Lowery and Holly Brasher,Organized Interests and American Government.Boston:McGraw-Hill,c2004.。
同时,被称为“新多元主义”的学者也在尝试对多元主义理论进行修正,以求论证并坚持组织化利益表达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为此,他们提出了两个概念:变化性(Variation)和随机性(Contingency),即不把利益的组织化看成是不需任何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现象,也不把之看成是完全不可能的存在,而去分析为什么相似的潜在利益存在,却有完全不同的利益动员和组织的结果。由此,新多元主义聚焦于影响利益的组织化及其成功与否的因素是什么,而变化性和随机性的概念涵盖了在组织化利益完全存在和完全不存在之间的各种情况。同时,它还尝试提出一些控制大利益集团的解决方案,以使得利益表达更具包容性⑦Ibid.。
总的来说,在多元主义者看来,国家是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舞台,并不存在一个超越利益集团利益的国家整体利益,而组织化的利益表达可以增强社会利益表达的力量,是多元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
二、组织化利益表达的积极作用
多元主义强调了组织化利益表达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要意义。在对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经验研究中,特别是中国政治的研究中,许多学者也认为,组织化利益表达可以推动组织性社会力量的成长,增强社会弱势群体的力量,从而有助于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进而,它还防止人们通过原子化的利益表达方式去寻求利益的实现、侵蚀国家的自主性和内聚力;也防止人们求助于暴力和游行示威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导致政治的不稳定。最后,这种组织性的社会力量还有助于提供克服既得利益的改革动力,推动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深化。
(一)维护弱势群体利益
组织化利益表达最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可以推动组织性社会力量的成长,以此来增强那些缺乏政治资源和政治影响渠道的社会群体的力量。因此,对于工人、农民以及农民工等缺少现实政治资源的群体而言,畅通组织化利益表达渠道是维护这些社会弱势群体利益最重要的途径。有的研究者明确提出,应将组织农业利益集团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症结的出路①闫威、夏振坤:《利益集团视角的中国“三农”问题”》,《新华文摘》2003年第12期。。崔大伟(David Zweig)认为,在中国,农民的力量在于其人数的庞大,因而,要使得农民的权益得到保护,就需要创设农民组织②David Zweig,“Contesting Rural Spaces:Land Disputes,Customary Tenure and the State”,in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eds,Chinese Society:Change,Conflict and Resistance.London;New York:RoutledgeCurzon,2003.。于建嵘对于湖南农民的研究也认为,农民的集体抗争表明了村民们为保护自身利益对“组织”的需要。他认为,这种组织性需求恰恰是重建农村社会秩序所必需的。而对待这类事件,最为现实的对策就是,在树立国家权威的同时,以整合地方政府和村民的利益为前提,将那些体制外的组织力量纳入到农村基层政权的运作之中,实现政治整合。其中首要的就是通过国家立法成立能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组织③于建嵘:《利益、权威和秩序——对村民对抗基层党政群体性事件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4期。。
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随着公有制经济范围的逐步收缩,下岗工人逐步失去了原有通过庇护关系来表达利益的可能性,同时政权体制外的农民工数量急剧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组织化利益表达成了维护下岗工人以及农民工利益的重要方式。周雪光和唐文方等对于国有企业的研究认为,在中国,改革前的政治运动、就业保障、平均工资、计划经济体制、竞争缺乏、价格统制、投资过剩等等都使工人享有较之于改革后更切实的权利保障;而在经济改革后,随着国企管理层的权力随意性增强,工人的利益再难以通过庇护关系网络来表达④周雪光:《西方社会学关于中国组织与制度变迁研究状况述评》,《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4期;唐文方:《谁来做主——当代中国的企业决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在国家庇护网络之外的农民工也难以通过国家开辟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来有效地保障自己的权益。在诸如人民代表大会等制度安排中,农民和工人等群体只有象征性的代表⑤史卫民、雷兢璇:《直接选举:制度与过程——县(区)级人大代表选举实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国家的保障。李青莳(Ching Kwan Lee)提出了“无组织化的专制主义”(Un-organized Despotism)来形容这种状况⑥Ching Kwan Lee,“From Organized Dependence to Disorganized Despotism:Changing Labour Regimes in Chinese Factories,”The China Quarterly,157:44—71.1999.。所以,从这个思路出发,研究劳工权益问题的学者努力寻找工会可能会发生的转变。有的研究进而提出应该走向合作主义政治,以求通过推动工人的组织化来实现工人的组织化利益表达,维护工人的权益⑦安戈、陈佩华:《中国、组合主义及东亚模式》,《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
(二)保持国家自主性和内聚力
组织化利益表达渠道的缺失会使得人们求诉于原子化的利益表达来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而侵蚀国家的自主性和内聚力。在关于中国利益表达的研究中,从白鲁恂(Lucian Pye)注意到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关系”开始,庇护关系受到了研究者广泛的关注①Lucian Pye,The Mandarin and the Ca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8.。魏昂德(Walder)在他经典性的研究中指出:国家权力在社会主义工厂中呈现出来的并不是极权主义的形式,即国家控制一切,工人完全沦为原子化的个人;同时它也并不是多元主义的形式,即社会团体纷纷出现,它们相互竞争并追求自己的利益。魏昂德认为,中国的工厂政治是一种“新传统主义”,即在国家权力对社会资源拥有垄断性的支配情况下,工人通过类于庇护关系的社会网络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寻求策略性的利益表达②Andrew G.Walder,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c1986.。
在国家权力集中的情况下,这种以庇护关系网络为主要渠道的利益表达方式为公民打开了表达和追求自身利益的空间,但却带来了两方面的消极后果:其一,虽然庇护关系使得人们从中获取一些边际利益,但它却分割了社会,使得人们不愿意在社会上形成平行的利益同盟,从而难以组织起来进行组织化利益表达以求影响政府决策;其二,人们通过特殊主义导向的庇护关系侵蚀着国家的内聚力,显现出一个貌似强大却很虚弱的国家,即国家垄断了广泛的资源和权力,但实际上却难以实现它③Vivienne Shue,The Reach of the State: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c1988;Susan Shirk,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c1993.。
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这种庇护关系对于国家自主性的侵蚀进一步加剧。研究者发现,与经济改革之前的“依赖性庇护关系”(Dependent clientelism)加强了国家基础权力不同,经济改革后出现的“共生性庇护关系”(Symbiotic clientelism)损害了国家基础权力。因为前者在事实上加强了官僚机构中的权威等级,强化官员的向上负责而促使其有效地执行政策,而后者则使得下层官员倾向于在市场中寻求利益,并且通过对于政策执行的扭曲来获得回报,从而使得国家难以自主地制定社会经济政策。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这种情况,在印度和许多拉美国家都可以看到④David L Wank,“Bureaucratic Patronage and Private Business:Changing Networks of Power in Urban China“,in Andrew G Walder ed,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此外,组织化利益表达的缺失不仅使得各种“关系”盛行,而且还使得国家内部的改革派难以获得克服地方和部门既得利益的改革动力,侵蚀了国家的自主性。在被形容为“碎片化权威主义”的体制之下,国家内部不同政府层级之间和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一种特殊主义之上,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充满了讨价还价。在很多时候下,改革者难以克服部门和地方出于维护既得利益而产生的改革阻力,从而使得国家自主性遭到侵蚀,阻碍了改革的深化。而只有来自社会的组织化利益表达,才可以为改革者提供克服既得利益的力量⑤Kenneth G.Lieberthal,and Michel Oksenberg,Policy Making in China:Leaders,Structures,and Processe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立平认为,在转型期中国,地方部门利益和庇护关系是蚕食国家自主性的最主要因素⑥孙立平:《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可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在缺乏组织化利益表达渠道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一种零和局面:一方面,公民的利益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难以影响到政策的制定;另一方面,国家的自主性和内聚力在原子化和制度性利益表达的策略中受到损害。因此,我们需要通过畅通利益组织化表达渠道来使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走向制度化和常规化,进而,使得国家的自主性和内聚力免遭社会和国家内部各种利益的侵蚀。
(三)维系政治稳定
当组织化利益表达遭到压制的时候,人们往往不得不求助于暴力和游行示威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导致政治的不稳定。在阿尔蒙德(Almond)的系统功能分析中,组织化的利益表达是整个系统关键的输入机制,通过这个机制,社会把需求和要求输入到政治系统中,政治系统再输出政治决策,从而实现政治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在阿尔蒙德看来,在没有实现民主化的政权中,组织化利益表达不被允许,原子化和非团体式的利益表达就会占据完全的支配地位。因此,阿尔蒙德认为,民主并不会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会带来两极化,相反,对组织化利益表达的压制并不能消除实际上的两极化,只是把矛盾掩盖住了,最终会导致政治系统的突变①Gabriel Almond,Comparative Politics Today:a World View.New York:Longman,c2000.。
在第三世界政治研究中,研究者也发现对利益组织化表达的压制隐埋了政治不稳定的种子。在对拉美国家官僚权威主义(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的研究中,奥唐奈(O'Donnell)认为,国家通过诸如“民族”、“公民权”和“公共空间”等“调和”(mediation)机制来使得它呈现为一种“公域”,而官僚权威主义压制了这种使国家表现为“公”的调和,它对任何组织化的利益都表现出高度的强制力控制,通过恐惧和经济奇迹来进行合法化。这使得它难以得到大众的支持,同时它的统治联盟中也会发生分裂,最终造成它的瓦解②Guillermo O’Donnell,“Tensions in the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State and the Question of Democracy”,in David Collier eds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c1979.。
在中国现实政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由于缺乏组织性利益表达的渠道,在诸如信访等利益表达渠道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时,集体抗议对政府构成了很大压力,对政权稳定形成了威胁。因而,畅通组织化利益表达渠道可以作为保持政治稳定的解压阀,舒缓社会矛盾,保持有效的政治沟通。
(四)提供改革动力
如果从精英政治的角度分析,改革要么是上层精英派系斗争的结果,要么是上层精英理性选择的结果。在这种分析中,改革完全由上层推动,下层民众的利益表达难以上达,难以构成改革的动力和压力。虽然民众可以通过“关系”来影响改革政策的执行,但是,却难以影响改革政策的制定。
与这种观点不同,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并不能完全由精英政治来解释,民众在推动改革中扮演了重要作用。柯丹青(Daniel R Kelliher)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研究就认为,中国的农业改革并不是上层理性决策或者派别斗争的结果,而是来自农民的底层力量推动。她认为,农民的这种力量来源于两个条件:其一,农民内聚力的形成。在家庭联产承包制中,南方农民出于自身利益而不约而同地实行包产到户,这对中央的政策造成了挑战。其二,国家有追求平衡发展的目标。如果国家追求意识形态目标,或者追求社会改造,那么国家就可能不重视农民提出的挑战。相反,国家重视经济目标,这使得国家不得不回应农民的挑战,从而使得农民的力量和利益能够为上层所体察并构成了改革的动力③Daniel R.Kelliher,Peasant Power in China:the Era of Rural Reform,1979—1989.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c1992.。
与此同时,民众依然缺乏组织化利益表达的渠道,这又使得改革的深化缺乏足够的动力,民众的利益也难以在改革中得到维护。柯丹青认为,由于农民利益的表达是所谓的“日常抵抗”,并非是通过组织化和制度化的渠道实现的,因此,它十分脆弱而没有任何强制力。80年代中后期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如调低粮食统购价和取消议购超购等,就已经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除了所谓弱者的武器外无能为力。对城市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研究也发现,由于缺少组织化的利益表达渠道,所以贫困群体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中难以影响到政策的制定,因而在改革中处于弱势的地位④陈剩勇、林龙:《权利失衡与利益协调——城市贫困群体利益表达的困境》,《青年研究》2005年第2期。。
在这种分析中,组织化利益表达而非精英决策模式对于改革的深入和公平等价值目标的实现具有决定性影响,它是改变既有利益格局的动力和压力的来源。从这个角度来看,有的学者所提出的只要法治不要民主等观点忽视了民众组织化利益表达对于中国改革的重要性①潘维:《民主迷信与中国政体改革的方向》,《天涯》2000年第1期;康晓光:《再论“行政吸纳政治”:90年代中国大陆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研究》,《二十一世纪》2002年第4期。。布尔隆在对于政策制定过程的分析中就指出,政策的分析不能代替政治②[美]查尔斯·E·布尔隆著、朱国斌译、王瑾校:《政策制定过程》,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
三、组织化利益表达中潜藏的挑战
对于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的非西方国家而言,它们在政治发展和经济改革中面对着更多的挑战和困境。组织化利益表达之中潜藏了不平衡的利益代表所导致的特殊利益集团问题;转型社会政治制度化程度相对滞后于组织化利益表达的发展则可能带来政治不稳定,而经济自由化改革中所产生的经济不平等的扩大和社会利益的冲突则可能加剧这种政治动荡;同时,组织化的社会力量并不总能够提供改革的动力,自主的国家更能够在经济发展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一)特殊利益集团的问题
通过利益集团的相互竞争实现民主是多元主义建构的理想模型。虽然新多元主义者试图对这种理想模型进行修正,但现实中却似乎更多的是特殊利益集团在影响政府的政策。在一些研究者看来,防止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维护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关键并不是在于开放组织化的利益表达、以组织性的社会力量来制约它们;相反,由于组织性的社会力量总是属于奥尔森所说的人数多而获利小,往往难以形成切实的行动力量,抗衡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特别是以资本为核心的利益集团,因此,遏制特殊利益集团更重要的是保持国家的自主性。
在中国问题的分析中,萧功秦认为,利益集团在民主政治中发挥作用有一系列的配套因素,如公民社会的成长、契约关系的信守以及包容性的政治文化等。这些社会因素并不是人为的设计结果,而是长期经济发展的历史产物。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下,组织化利益表达呈现出来的是以垄断排他性为特征的分利集团化。这种分利集团化又可能与以弥散性腐败为特征的“软政权化”相互结合,并不断地蚕食国家的政治权威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实现所谓的西方式民主,其结果就会使垄断性的分利集团在“民主政治”的护身符下如虎添翼,任何有利于大众的结构改革将会在垄断集团把持的议会中轻而易举地受到否决。拉美国家的情况就是前车之鉴③萧功秦:《后全能体制与21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6期。。
对这种观点的批驳会提出,正是组织化利益表达受到压制,才会缺乏有组织的社会力量来遏制分利集团的膨胀。但同时,对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经验研究表明,组织化利益表达并非总能发挥这种作用。丁学良对俄罗斯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所谓“国家分封化”进行了反思。他认为,西方民主体制的确立,并没有带来组织性社会力量的成长,相反,被分封了的国有资产成为由政治统治者和财经寡头联手的权势集团随意支配的政治资源,他们窃取了国家的资产,又以这些资产作为政治献金,掌控了国家权力④丁学良:《转型社会的法与秩序:俄罗斯现象》,《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2》,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第218—235页。。在东欧,虽然独立工会等社会组织性力量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在新政权建立后,即便开放了组织化利益表达的渠道,工人的力量仍然分散而虚弱,难以对政策有重要影响。对匈牙利的研究表明,随着向多党制民主的转变,匈牙利劳工运动的力量明显减弱,工业重组和私营部门的扩张侵蚀了蓝领工人的内聚力,政治左派的分裂又削弱了工人组织通过政党政治所能获取的政治影响力。在这些国家,组织化的社会力量并未能够真正构成对抗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大力量①David L Bartlett,“Lodging the Political Initiative:the Impact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n Hungary”,in Andrew G Walder ed,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这个问题同样突出。这些国家掌有所有的重要资源,却难以执行社会政策和让民众听令于他们,这种情况的出现往往是由于国家为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所支配,而缺乏独立地制定公共政策、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自主性。我们一般将这种情况称之为“国家捕获”,即国家成了特殊利益集团的操纵对象,而丧失其超越于社会经济利益的公共性②Joel S.Migdal,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
因此,遏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出路并不是在于组织化利益表达,而是在于保持国家的自主性。这意味着国家拥有不等同于或不混淆于统治阶级或集体集团的利益和目标,它不是多元主义者所假设的争夺社会经济利益的平台,它能够自主地制定公共政策并保证政策的执行③Peter B.Evans,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进而,如前所述,对于组织化利益表达持积极乐观立场的研究者而言,保持国家自主性就需要防止庇护关系、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蚕食,而这就反过来需要畅通组织化利益表达,一方面防止人们通过原子化利益表达方式来侵蚀国家的自主性,另一方面提供克服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改革动力。然而,在另外一些研究者看来,保持国家自主性的根本途径不在于畅通组织化利益表达,而在于国家自身的制度化建设,通过国家建设来重塑一个有效政府,防止特殊利益集团对于国家的支配和操纵④Shaoguang Wang,“The Problem of State Weakness,”Journal of Democracy,Vol.14,No.1,2003。在中国,一些研究者也认为,利益集团的政治化和利益代表的不均衡性,需要加强政府能力建设,提高政府对各利益集团的调控能力、整合能力和自主能力⑤汪永成、黄卫平、程浩:《社会利益集团政治化趋势与政府能力建设》,《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1期;杨光斌、李月军:《中国政治过程中的利益集团及其治理》,《学海》2008年第2期。。
(二)保持政治稳定的问题
在多元主义者看来,组织化利益表达是政治系统的解压阀。虽然开放劳工组织和劳工运动之后往往紧接着大规模的劳工抗议,但随后几年,它们就会趋于平静,因而组织化的利益表达是有利于政治稳定的解压阀。但是,另外一些研究者却认为,组织化利益表达的开放需要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它并非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有利于政治稳定。
组织化利益表达常常需要国家的政治制度化程度相应的发展。亨廷顿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团体意识和组织性增强而带来的组织化利益表达会不断膨胀,而如果以国家的自主性、内聚性和适应性等为特征的政治制度化程度滞后,就会产生所谓的“普力夺政权”(Preatorianism)。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丧失其自身的自主性,而成为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的工具,整个社会生活高度政治化,社会处于高度动员的状态,由此导致政治的不稳定⑥Samuel P.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在他看来,政治稳定取决于团体式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平衡,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之所以处于风雨飘摇中都是由于政治制度化落后于组织化利益表达的发展。
同时,以经济自由化为导向的市场经济改革完成之后往往才是开放组织化利益表达的最好时机,否则会对政治稳定形成巨大的压力,甚至导致政治系统的瓦解。如波兰尼所言,市场经济的孕育和发展往往会带来社会不平等的绝对扩大和社会的失序。西方民主国家用普选权的扩大、制度化的产业关系调整、社会保障网络的建立和对绝对贫困的救济等方法来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以避免对于政治稳定的挑战①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1985]c1944.。在新兴民主国家,经济自由化带来了同样的社会问题,但却难以通过同样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研究者发现,在这些国家,经济的自由化对政治稳定有更尖锐的挑战。经济自由化改革无可避免地带来贫富差距的拉大,从而催生了劳工组织和劳工运动,对国家的经济自由化改革构成了强大的社会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要么向国内的劳工组织和劳工运动妥协,使得经济改革完全停顿下来;要么政治上对劳工组织和劳工运动进行压制,保持国家的自主性,依靠进一步推进经济改革来获取支持。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保持政治稳定,国家必须要恰当地平衡政治势力、达成社会共识、避免政治极化和碎片化以及争取稳定的政治支持。
在韩国和日本等国的经济起步阶段,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劳工组织和劳工运动的压制。到70年代,自由开放的经济体系已经形成,这些国家才慢慢开始放松对劳工组织和劳工运动的压制②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R Kaufman eds.,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Adjustment:International Constraints,Distributive Conflicts,and the Stat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c1992.。对叙利亚、希腊、韩国和台湾的比较研究也发现,造成这四个地区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绩效不同的原因在于对于大众进行政治吸纳的时机。在叙利亚和希腊,政治精英之间的分裂和冲突导致它们在经济改革前就不得不开放组织化利益表达,吸纳社会其他阶层进入跨阶层联盟,这时候,国家建设也尚未起步,从而造成了政治的不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迟滞。台湾和韩国则相反,对于大众的政治吸纳在经济稳步和快速发展几十年之后,同时政权建设也比较成熟,从而使得开放组织化利益表达并未阻碍经济改革和导致政治不稳定③David Waldner,State Building and Late Development.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对于东欧剧变的研究也表明,匈牙利社会主义体制的最终崩溃正是为组织化利益表达和经济改革之间的张力所催生。在经济出现通货膨胀的时候,一方面,组织化的工人和工会通过罢工反对实际工资的下降,不断要求提高工资;另一方面,先前经济自由化改革中在诸如信贷金融等领域存在的问题,使得政府缺乏足够的能力来控制通货膨胀和压制工人的要求。最终国家不得不在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之时仍不断提高工人工资,这又进一步恶化了通货膨胀的形势,使得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从根本上影响了政治稳定,推动了原有体制的瓦解④David L Bartlett,“Lodging the Political Initiative:the Impact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in Hungary”,and Akos Rona-Tas,“The Second Economy as a Subversive Force:the Erosion of Party Power in Hungary”,in Andrew G Walder ed,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三)促进经济发展
如果说组织化利益表达是改革动力和压力的来源,那么,在民众利益不能够有效表达的情况下,中国的改革必定中途夭折。在1993年出版的专著中,谢淑丽就认为,由于没有更包容性的政治改革把组织性的社会力量吸纳到改革中来,所以诸如价格双轨制这样的改革遇到强大的既得利益阻碍,就难以得到推行。但是,在现实政治发展中,我们却看到这些研究中认为不可能实现的改革在中国都得到逐步进行。那么,改革是如何发生的?如何可能?这种理论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之所以会出现,因为在理论假设上我们将政府看成是“掠夺者”。从这个假设出发,为了使得政府不沦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掠夺者,就需要社会上分散的个体能够集结为利益团体进行利益表达,通过利益聚合把利益传输到决策中心,从而构成一股控制政府的力量。但是,在现实中,与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改革事实上由政府主导,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经济改革的必要条件,而不是阻碍因素⑤Peter Evans,“The State as Problem and Solution:Predation,Embedded Autonomy,and Structural Change”,in 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Kaufman eds.,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Adjustment:International Constraints,Distributive Conflicts,and the Stat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c1992.。
有的研究者认为,那些把利益集团的压力作为经济改革动力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人们往往不知道在变动的改革中他们的利益在哪里;并且,人们对自身的利益界定往往是可以被劝说的,意识形态在利益界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而,在人们知道利益在哪里的情况下,利益集团也是很无力的,因为人们虽然经常批评或抱怨存在的问题,但往往难以通过组织化的形式来支持改革。这是因为改革的收益分布广泛,利在将来而又不确定,而成本和损失却是集中的和近在眼前的。这种改革的公共物品性质,使得改革的动力往往抵不上既得利益反对的力量。因此,不能指望将组织化利益表达作为深化改革的动力①Robert H,Bates and Anne O.Krueger,“Generalizations Arising from the Country Studies,”in Robert H,Bates and Anne O.Krueger eds.,Political Economic Interaction in Economic Policy Reform.Blackwell Publishers,1993;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R Kaufman,“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Adjustment,”in 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R Kaufman eds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Adjustment:International Constraints,Distributive Conflicts,and the Stat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进而,研究者从“国家自主性”出发,强调发展中国家保持国家相对于社会利益的自主性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在国内国际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直接面对世界经济,面对相应的压力;同时,国家还掌握着相应的权力。拉美国家和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也都表明了发展型国家能够积极地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对于国家如何能够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积极的企业家角色,研究者认为,这在于国家在改革的发起阶段是否能够保持“自主性”。并且,他们并不把政权性质作为决定国家是否能够保持自主性的决定性因素。埃文斯(Evans)把韩国和日本作为处理好国家自主性的典范,即韩国和日本在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中,与国内的大资本集团保持了密切却又是有选择性的联系,通过为它们提供稀缺的资本和信息等等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由于其官僚系统自身的传统、录用系统等的凝聚性和独立性,两国政府都保持了自主性,没有像印度和拉美国家那样为庇护关系和腐败等问题所困扰。针对这种现象,他提出了“嵌入式自主性”的概念。他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所需要做的不仅是制定正确的政策,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持久地推动政治系统的制度化建设。这种制度化建设决不是要求打碎国家,而是重建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自主性和内聚力是嵌入的前提,它们保证国家不会为社会中的既得利益所统治,也不形成一个单独的利益集团;而嵌入性则是要求国家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②Peter Evans,Embedded Autonomy: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c1995.。总的来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维持国家的自主性意味着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来推进经济改革,同时,利益集团力量发展的不均衡性更要求国家保持其自主性,避免成为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的对象,从而使得国家可以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推动改革的深化。
四、启示与思考
在非西方国家政治和经济转型过程中,组织化利益表达所潜藏的种种挑战,不管是特殊利益集团问题、政治稳定问题还是经济改革动力问题,其中涉及的核心问题都是“国家”。一个成功地应对政治经济转型过程中若干挑战的强大国家并非自然而然地存在,它需要通过持续的国家建设来提升国家的制度化水平,保持国家的自主性、内聚力和适应性,从而遏制特殊利益集团的操纵,并防止政治参与爆炸导致的政治动荡,进而通过有效的政府积极地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失序,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推动经济的转型和发展。
然而,强调国家在政治经济转型中的重要性,又必须要面对如何控制国家的问题:如何控制国家自身利益的膨胀?如何能够使得国家拥有改革的偏好和动力?如何处理保持国家自主性与保持政治系统的吸纳性和包容性之间的关系?在现实中,保持国家的自主性有可能不仅遏制特殊利益集团的侵蚀,而且还将公众的参与要求也排斥在外,最终是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此外,强调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为了保持政治稳定而对组织性的社会力量进行压制,并将国家作为经济改革的推动力量,最终也有可能带来改革对于弱势群体利益的忽视和改革为事实上存在的特殊利益集团所操纵。
在转型期中国,一方面,国家的制度化水平仍然有待提高,国家的自主性、内聚性和适应性都远未成熟,政治制度化水平进展缓慢①Harvey Nelson,“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 State,”in David Shambaugh eds,The Modern Chinese Stat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脆弱的制度和腐化的行政体系更容易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侵蚀和操纵②Kenneth Lieberthal,Governing China: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New York:W.W.Norton,c2004.。因此,旨在建立有效政府的国家建设是必需的。在国家自主性建设中,国家需要加强政府机构的能力;提高政府独立于社会中各利益群体的自主性程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大众的消费需求,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③孙立平:《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问题》,《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过程中,对于下岗工人诉求的压制已经为公有制经济转型奠定了基础,如今进一步的市场改革符合大多数社会群体的利益,民意所向是改革的深化而非反对改革的深化,因此,国家在市场改革过程中面对的社会压力已大大减弱。事实上,深化市场改革需要的是通过畅通组织化的利益表达来提供克服既得利益的改革动力,推动改革的深化,并提供缓和社会矛盾的解压阀,保持政治的稳定。
因此,鉴于这两方面问题的同时存在,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国家政权建设需要吸纳社会各种力量的参与,从而达致民主发展和国家建设的有机统一④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增订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同时,国家的自主性必须以民主政治作为条件,由此来保证公民利益表达的畅通和对于特殊利益集团的控制⑤孙立平:《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问题》,《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这就是说,国家建设与国家逐步开放组织化利益表达应该是同时推进的两个发展目标。对于组织化利益表达经验研究的争论告诉我们,在转型期中国,对于两者中任何一方的强调都不利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