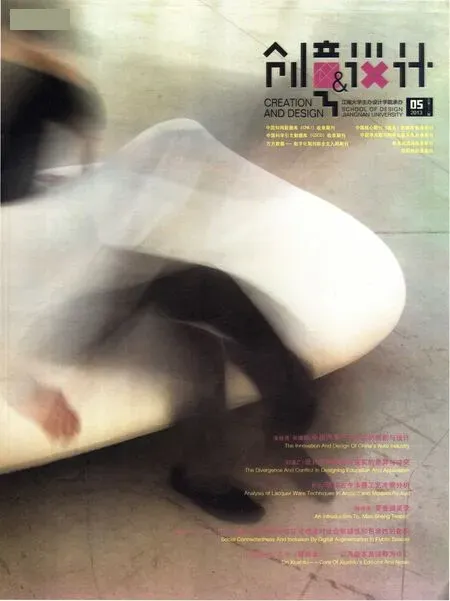设计学科教育与现实的差异与冲突
2013-01-21刘道广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文/刘道广(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
设计是人类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从一定程度上讲,设计改变了人的生存形态;设计也是生产力的一种形式。
设计学科教育一方面有历史的总结、理论的探讨;另一方面也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设计能力与运用工具能力的训练,即艺术创意、艺术表现能力和工艺制作感受的互动协调的训练。这是因为设计作为社会职业之一,业界的需要是设计学中的应用型教学的动力,也是设计学理论前瞻性研究的基础。
作为学科的设计学研究的基本概念是严谨的,作为业界的实践型设计在市场面前是“急功近利”的,这种“急功近利”状况也会返流入学科教育,引发概念的似是而非,结果是出现了对同一个基本概念的理解差异。作为互动协调的训练,要求的是“艺术创意”统领下的“技术”运用;而“技术”功能总是在不同程度地“制约”着“设计”;于是“主观”的“创意”的“艺术设计”和“客观”的“工具”技术的“冲突”就出现了。
一、基本概念的差异
现代设计艺术以计算机技术为工具已是常态,随着新专业软件的开发,工具的专业表现技能在不断增强和丰富,这就使设计艺术教学的“兴奋点”也在不断变换。设计业界在软件技术训练中把基本概念泛化,反映了设计艺术教育的失察。目前最明显的反映在对“CG”、“3D 打印”与“界面”基本概念的理解。
从学科要求说,英文缩写的“CG”的基本概念本来是清晰严谨的,如“百度”等网络所释:
多指计算机图形。计算机图形学(Computer Graphics,简称CG)”是一种使用数学算法将二维或三维图形转化为计算机显示器的栅格形式的科学。随着以计算机为主要工具进行视觉设计和生产的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形成,国际上习惯将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视觉设计和生产的领域通称为CG。
在计算机技术来说,“图形”和“图像”两个概念有各自不同的生成形式:
图像纯指计算机内以位图形式存在的灰度信息,而图形含有几何属性,或者说更强调场景的几何表示,是由场景的几何模型和景物的物理属性共组成的。
还有相近的解释: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计算机产生令人赏心悦目的真实感图形。为此,必须建立图形所描述的场景的几何表示,再用某种光照模型,计算在假想的光源、纹理、材质属性下的光照明效果。所以计算机图形学与另一门学科计算机辅助几何设计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上,图形学也把可以表示几何场景的曲线曲面造型技术和实体造型技术作为其主要的研究内容。同时,真实感图形计算的结果是以数字图像的方式提供的,计算机图形学也就和图像处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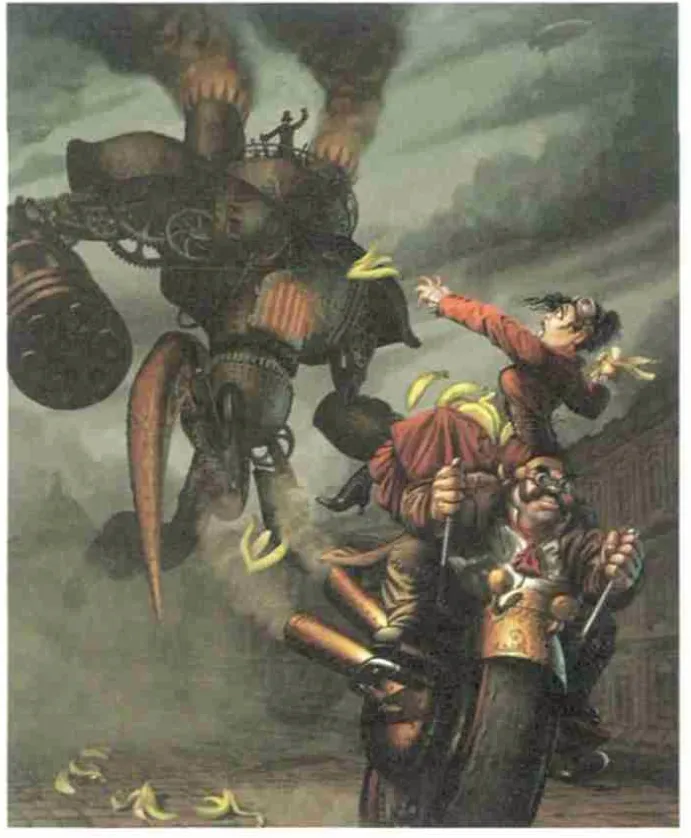
图1 CG 插画

图2 美国Shapeways 公司3D 打印出的概念珠宝首饰
在这些释义中,有三点和设计艺术的关系应当厘清。
第一,CG 是一种以计算机为工具的图形、图像处理技术。
第二,今天所有设计领域,只要运用计算机技术处理的图像图形,不论是手绘扫描、还是拍摄的照片、镜头,输入计算机后加以修整,最终输出的图形,都可称之为“CG”图形。于是服装设计、书籍装帧设计、产品设计、建筑CAD……所有使用计算机技术修整的图形,皆为“CG”。动画(含动画故事片)、影视特效镜头等都是在计算机技术支持下完成的CG 图形,也是“CG”之一。
显然,在现代设计艺术教学系统中,没有哪一个方向的内容可以涵盖所有的运用到计算机辅助图形处理的各个领域,各个不同专业、方向的设计艺术都在运用着计算机图形技术、即应用着“CG”制作技术,任何一个设计方向都不能笼统的自称为“CG 制作”。倘若有这种情况出现,只能说明“CG”的基本概念出了问题,用一句通俗话说是一个“手推馄饨店”,自我误解成“同庆楼”了。
第三,CG 技术功能虽然强大,但设计艺术的目标并不是如上述的“产生令人赏心悦目的真实感图形”。这是偏尚计算机技术的技术员和“艺术设计”师之间最难以沟通的基本概念之一。前者的看法其实代表了不少非艺术专业背景(有艺术专业背景的人毕竟有限),或者可以说代表了一直缺乏“艺术欣赏”、“审美”教育的中国社会的认知。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包括设计艺术的艺术创意、创作目标并不是追求“真实感图形”。在计算机技术诞生之前,艺术设计用的工具是各种规格的笔和几何学工具,设计师的创意构思通过笔、尺、规等工具在绘图纸上一一展开。设计师的艺术创意通过他擅长的工具及形式(如水彩、淡彩、水粉等)表现,可以形成个人独有的“设计风格”。“风格”之间会发生影响,“波普艺术”从艺术家“手工”拼图构成导引到计算机PS 软件“拼贴”功能,使照片应用率大为提高。由之要求计算机设计师对拍摄镜头和镜头处理技巧有所训练。但这些都和计算机单独建模、贴图、打光的最终效果有别,因为不论绘图,还是照片,都取自客观对象,其色彩无不是“灰色调”呈现,和绘画“色彩学”原理一致。而计算机模拟图形的色彩都有“正确”的“纯度”,图形的色彩明度按科学规律变化产生“炫感”,没有人的“视觉误差”;而“视觉误差”则是设计师个人风格得以形成的条件之一。任何一个设计师在追求个人设计风格的时候,或者在把笔、橡皮换为“压杆笔”、鼠标、键盘,纸换为液晶面板等工具、材料后。他的构思、创意不可能因为工具表现功能的丰富而把设计目标改变为追求充满“炫感”的“真实感图形”;如果事实如此,那只能说是中国的设计艺术水平流向“技术”的呈现,“艺术”部分被“边缘化”。
计算机技术的基本概念是外来的,翻译有直译、义译两种形式。语言翻译的难点在译者对母语的熟练度,历史上佛经传入就遇到梵文“空”的翻译难度。汉语中并没有能与梵文义合的词,鸠摩罗什以“空”字对译,确是最能接近释迦牟尼本意的“义译”。以前强调“信、达、雅”的“翻译家”的要求;今天已经少有译者能达到此专业水准。但译者至少应该对相关的专业现状有些了解,以免混淆视听。
直译会带来更多的概念混乱,如现在快要约定俗成的所谓3D 打印。
3D printing 的printing 是印刷的意思,但其终端作品却是360°的立体物。
在印刷工艺中,本来就有一项“立体印刷”,“印刷”工艺是一种传统的复制技术,就其本身说,终端产品的介质(如纸、皮革、塑料、金属等材料)是平面的形态。立体印刷仍是在平面介质上进行,至于其视觉效果有“立体”、“3D”的特点,是借助人的视觉误差而产生的“错觉”,其终端产品仍属平面。正如“3D 电影”,不论裸视与否,仍属“平面”艺术一样。所以“3D 打印”的译名其实也反映了译者、3D 技术操作者对“印刷工艺”、“平面设计艺术”基本概念及工艺实践缺乏认知的现状。
译名可以其终端形态为标准,工业设计中已有三维雕塑机(成型机),工作原理有两种,一种是把工件材料“雕刻”而成;另一种是把粉状材料“喷塑”而成,两种都通过计算机技术。对“造型”来说,前者用“减法”,后者用“加法”。现在称为3D 打印技术,如译为“3D 印塑”更为合适。3D,指其终端产品形态是立体的;“印”,仅仅表示其工作原理是把三维模型逐层剥离为众多的二维平面;“塑”,指众多二维平面再通过特定的组织材料逐层输出叠加组合;最终在累积过程中完成造型。
这种3D 印塑技术目前的发展空间甚大,业者预测其成型能力几乎能涵盖人的“衣、食、住、行、用”的各个方面。可以印塑出简单的活体组织,未来能印塑出人的内脏器官。到这时候,印塑出人的食物已不在话下。
界面设计也有一个因基本概念含混导致的“界面”、“介面”的义译问题。
Human Interface Syetem Design 这个词含:人类、接口、系统、设计四个语义。译为“介面”的“介”,即“中介”、“媒介”的“介”,有供双方、多方沟通的意思;“介面设计”的“介面”,就是“人”与“机”的沟通、交流,即互动的平面。如译为“界面”的“界”,在汉语语义中则是有轮廓的平面,本身并不含有双方或多方(不论是人与人,还是人与物)的交流、互动语义。但作为“介面设计”时的平面,其本身在客观上既有“交互”的功能,也有轮廓的平面。在汉语中要找到一个恰当表达其四个语义的词还有待翻译语言学者的研究。
二、技术和艺术的冲突
今天的设计教育现实中对计算机技术与艺术训练的关系大抵有两类认识,一类认为计算机技术的强大已足以取代设计者的“手绘”写生、造型、色彩等训练,因为计算机工具窗口、材质库、资料库等己储备足够量内容,可供设计者选择应用。另一类认为计算机技术是工具,最终要服从设计者的“艺术”感觉,而此感觉是通过“手绘”诸形式才能在他的“心中”诞生。他运用计算机、或指导计算机操作者完成“设计”,是追寻、重现这样的“感觉”;是设计者的“人”操纵“计算机”工具的创作。而计算机的各式工具功能及丰富资料库(尽管是“虚拟”的),却已使缺少艺术基本训练的设计者“找不到”设计的“感觉”,只能在已有的“线条”、“色彩”、“材质库”中选用对象,实质上是计算机在完成“设计”,是人为主体的“设计异化”。
现在的“设计学”已经有“工学”、“理学”、“艺术学”的不同归属,前两种归属中的教育大都重计算机技术训练甚于艺术基本训练,对软件功能技术的热忱超过了对“艺术”自身训练的追求;在课程分配上,前者在机房的计算机软件操作课多,在专用教室的造型、色彩等基本“手”、“眼”、“脑”协调训练课少,有关艺术思想、鉴识能力、审美能力的训练课更少;后一种则反之。这种教学比重上“艺术”创意、表现能力等重要的基本训练与计算机“技术”训练的多有失衡与冲突,客观原因在他们自己师资结构的现实。其结果是前者的“设计”概念有被“技术”屏蔽的状况,后者则不能恰当发挥计算机工具的功能。
说到“技术”的呈现,软件的一般技术操作能力训练在“中职”、“高职”,“本科”则倾向“创意设计”的基础史论、方法论和具体领域方向的教学层面,“研究生”层面则在创意和整合、统筹能力的训练。三个不同层面的训练彼此不是“高”、“低”关系,而是设计艺术学科作为跨学科领域所需要的分工。各个层面都会有自己的“高手”,就像现在俄罗斯避难的美国情报员斯诺登只是高中学历,但已是网络技术操作高手一样。
从艺术设计教育的体系说,有不同的层次阶段,不同层次有不同比重的“技术”训练和“艺术”创意训练。技术如何运用,最终仍归结到“艺术”创意的需要及设计者本人艺术审美表现力的水准。即如耳熟能详的《阿凡达》的CG制作技术是世界一流,须知在全世界也只有美国才有条件(财力、人力、智力、设备等)完成。而且他们的工作绝非纯技术的处理,以设在苏黎世的该公司工作室来说,他们自述的工作程序是:计算机图形技术的设计师是以艺术设计师的“需要”为目标,去创造完成新功能软件。换句话说,技术功能向哪个方面延伸和强化,由“艺术设计”需要的效果决定。
1986年美国最高科学奖“国家科学奖”由总统里根授予建筑家林同炎,赞词写的是:“他的科学分析、技术创新和富于想像力的设计,不仅跨过了科学与艺术的壕沟,还打破了技术与社会的隔阂。”全美顾问工程师奖状中评价他:“他的工程设计的创意与优雅的造型,为后人提供了一份使全人类都获益的国际遗产,并使所有工程界人士都能分享到职业的荣誉感。” 林同炎先生在东南大学讲座时,展示其作品之间还介绍了美国“设计”与“工程技术”的关系,说:设计(艺术)是工程技术突破的指路标。令我印象深刻,他还说:正因为美国的设计创意有新突破,才使工程技术有跟进;所以美国的设计创意是世界一流,工程技术也是世界一流。上述最高奖中所说的“富于想像力的设计”、“优雅的造型”,都是设计艺术范畴的创意,只要对照他的曲面斜拉罗卡巧克大桥,虽然没有能够走到工程实现的一步,但其路标性的设计艺术已为世公认。可见,任何一种“艺术设计”的创意、构思,都是对技术功能延伸强化方向的导引:先有艺术的“迁想妙得”,然后才会有如何去实现的技术手段。
技术的发展是客观存在,利弊得失毋须本文讨论。仍以前述3D 印塑技术为例,从设计教育的角度提出:如果3D 印塑技术可以取代工业设计的模型制作,就要看模型制作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模型制作仅仅只作为一个产品的外观,那么模型制作课就简单多了;如果模型课不但要有成型,还要有手感;不但要有手感,还要在成型中测试、调整结合度,其中包括了模型内部的结构处理。那么,目前的3D 印塑技术中先前完成的建模数据就要向“手感”呈现的方向研发。此外,较大型工业产品设计模型,如摩托车、汽车、飞机的模型都有等大的体积要求,3D 印塑技术要完成的模型,先需解决其喷嘴结构和材料与储备箱(假设有此功能)的体积及整个工艺流程。只要解决上述包含手感在内的这些要求,3D 印塑技术要涵盖、取代工业设计中的模型设计与制作,就并非不可能。
从教育立场看,更加强大而方便的虚拟能力的建模技术流行后,必然弱化设计者对材料质感的感知能力,包括对材料加工精度效果的审美能力。仅此两点,就似乎有违设计艺术教育对“人的能力的均衡发展”的主旨。所以,3D 印塑技术的无限延伸,并如其爱好者的希望那样最终取代其它学科(如材料学、工艺学)的时候,也将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设计艺术学的本质。
同样是CG 技术处理的界面设计教育,还未有如3D 印塑技术涵盖工业设计模型制作的宏愿,顶多提出的是跨界的“设计视角”,如提出从“人类文化学”进入界面设计的观点。我认为作为界面设计最好“单刀直入”进入“设计”就好。因为“人类文化学”的重实验室数据,是整个工业设计都强调的方法论之一,有一套问卷分值设计、数据釆集和统计学有效P 值分析方法。作为整个工业设计体系必须具备的先期工作是毋庸置疑的,作为具体的界面设计者并不必要求亲历亲为,只要能看懂先期工作的调研结论就好。
介面设计或界面设计,在设计艺术方面包含两个特色,一个是有轮廓的界面,另一个是此界面有“人”、“机”互动交流功能,而具有“介面”的因素。其中“交互”的功能是重要的,这就使“界面设计”的要求不仅仅在一个具体轮廓的“构图”,更重要的在于第一个界面与后续界面的连续关系的设计。
界面设计都依靠专业软件进行,不管这些软件的功能怎样,仍然都是工具的性属。决定软件如何工作的是“设计”,首先是设计者对上述界面“连续”关系的思考,反映出设计者“设想”与“计划”能力。简言之,“界面设计”的艺术设计者先要有“逻辑设计”的能力,然后是“构图”,或“构成”的艺术思考才能组成“界面设计”的完整流程。
逻辑设计含对界面系统整体内的“分类”,以及每一类下的“子项”层级数的分析归纳,其原则是从“大”到“小”。如从“类”到“群”、到“列”、“个”等若干层级;所以界面设计者同时要具备“编辑”的素养,有“分类”的知识和能力。先确定“类”,逐层推演,每一“类”下进入“群”;每一“群”下进入“列”……直至“个”。完成了文字排列的逻辑关系图,即可进入具体界面的总体风格设计及单位页面设计。应指出的是,当进行逻辑关系设计时,前列的“类”、“群”的归纳涵盖面的“广”与“狭”、“大”与“小”,会直接影响到该界面的文图版式设计的系列效果。前列涵盖面大,后续的“子项”数就会增多。以手机界面设计说,如某款N0K1A 的功能界面有10 类,逻辑设计较简明;日本的某款Sony Ericsson 的功能界面12 项,较复杂。但前者“信息类”后的二级标题有15 项,后者为12 项。前者在“新建信息”列完成信息,点击“发送”即完成全部操作程序。后者则会提示“确认”,“确认”后完成发送。前者整个流程的逻辑设计为5 步,后者为6 步。虽然只是一个步骤的差异,却反映了北欧与日本不一样的思维重点,一偏简洁,一尚繁复:这是双方文化习惯的差异所致。
界面设计软件的功能是技术性的,完成了界面的逻辑设计就进入具体“界面”的 “版式设计”,只是“界面设计”的界面有自己的“连续”展开方式,特别是由于“界面”的画面呈现是依靠“后台”的技术,“点位”十分精确,因而有“资本”与“技术”干预。
“资本”追求“利润”,希望一个“单位”的界面要容纳最大量的信息;而计算机后台技术又恰恰能满足其要求。于是一幅页面就如同“大字报”一般,上下左右完全填满文、图成为“界面”的常态。因为没有“构图”、“构成”的艺术处理,每一个“界面”都呈现“开排窗”、“摆地摊”式画面,“类”、“群”的一级、二级标题混同,文、图相接,大小失序;表面上琳琅满目,实际上杂乱无章,极易产生视觉疲劳。
界面设计,或“版式设计”都牵涉到构图和造型、色彩这些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艺术因素,而这些都依赖于设计师的艺术设计功底。一个“界面”,至少有“栏”、“列”的统筹设计,有文、图的疏密设计,有造型和色调的调和与对比设计,这三项设计中的“栏”、“列”的“数”有多少,由文、图的需要决定;文、图的大小(分辨率)、多少由编辑的需要决定。造型和色调则由设计者艺术创作能力、艺术审美能力决定。
如果说前两项偏重于设计者“理性”的训练,那么后一项则是设计者专业的“感性”、“悟性”的基础了。这个基础应当是设计者对艺术史、设计史、工艺史上优秀作品的认知、了解程度和自我表现能力诸条件共同构筑而成。落实到“界面设计”,除了“版式”构成外,就是“字体”和“图像(造型)”的设计。尽管计算机设计软件功能多和“材质库”、“资料库”的容量大,方便检索;但需要“人”去选择。能否恰当的选择和处理字体(不是字体的设计)是需要设计者认真思考的。要能认真思考,起码要知道中外文字的字体特色,如中文字体的真、草、隶、篆的若干流派,外文字体的罗马正体、哥特体、瑞士花体,甚至伊斯兰的硬笔书法,都有何种字体适宜于何种内容的文本、具体文字有无间架结构的修饰、便宜变化的需要等等问题;这时候才名符其实地进入具体的字体设计范畴。
图形资料库里资料总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设计者缺乏辨识其高下、优劣的能力,艺术审美能力欠缺,就谈不上对界面“版式设计”有什么总体艺术效果的把握和塑造。他们只能到资料库中去“找”一个现成的“对象”,稍加改变(大多是出于知识产权原因,而非出于原创的要求),属于拼凑式的“设计”。即使如此,还会因为不能识别“对象”的艺术形式、意味的高下而“混搭”一气,界面格调恶俗难免。所以即使是选择现成的“图形”,也要有鉴识水准,譬如在中国艺术史、设计纹样史上最常出现的“龙”形象,已经被赋于“中国人”、“中国文化”,甚至“东方文化”的寓意。从艺术造型特色说,“汉”、“唐”两代的“龙”造型有生气勃发的意味,宋元已失深沉雄壮的风格,明代初期一度有所生活化,不乏生动情趣,此后直至清代,“龙”形已皆呈张狂之态,尽失雄放风范。其它如“凤”、“虎”等多种形象及二方连续各种构成骨式也都各有其辉煌的历史时期,并不是自古至今全都是优秀典范之作。此外,北魏石窟的佛背光;唐代经师碑侧的“唐草”、民间青瓷的“花鸟”造型、织锦的“联珠纹”与“对”的构成;宋代吉州窑的“木叶”手法和对温润色调的追求;明清蓝染织品的“折枝”和明快的蓝白色调,等等;都足以供设计者在其中体悟其造型规律。倘若能总结出如“水”、“火”、“云”、“雾”的构成规律,以及如“宝相花”、“缠枝莲”等植物、人物、动物的造型要素、构成骨式。就必有相应的手、眼、脑的“三位一体”的艺术感悟深度与表现能力,也就必然会有潜移默化而来的鉴识水准和创意思维习惯,也就能脱离资料库的依赖而推陈出新。独立创新的能力来自手、眼、脑协调训练的基本功力,借助计算机工具的应用,可以把创新图形设计的效果发挥到极致而可能形成自己的设计艺术风格。到这个阶段远离了拼凑式的“设计”桎梏,而进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意设计的“自由王国”,“界面设计”如此,其他领域的艺术设计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