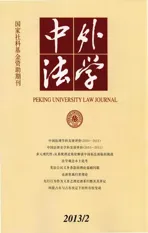法学观念本土化考从新中国60余年立宪史之视角
2013-01-21何勤华
何勤华
法的移植和法的本土化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基本路径和客观事实,中国近现代法律从观念到制度、原则乃至术语,几乎都是从西方(大多通过日本)移植进入中国,并逐步本土化的。虽然学界对此有许多不同的看法,〔1〕如李玉福主编《中华法系的形与魂》一书,就对20世纪以来我们所进行的法律近代化表示了强烈的遗憾:“以大规模法律移植为主要特征的法律近代化,在法律实现的社会实效上却举步维艰,辛苦构建的近乎完全‘西化’的法律体系却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很难植根于我们这块土地。究其原因,乃因视西方法律文化成为法律移植的主要对象和评判法治变革成效的主要标准,忽视、冷落甚至批判、攻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强制推进的急功近利的方式迫使中国法律现代化,事实已经证明这是失败的”。参见李玉福主编:《中华法系的形与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也有一些反思的作品面世,〔2〕如何勤华、李秀清:《外国法与中国法——20 世纪中国移植外国法反思》,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但笔者以为,由于中国近现代移植的基本上是西方先进国家法律中的精华,代表了人类法律文明的最高成就。因此,中国近现代法的移植和法的本土化基本上是成功的,它是世界法律发展进步之规律(法的移植和法的本土化)发生作用的又一个成功事例,具有普适性的价值。
考虑到近几年学界对中国近代法律制度和概念术语等方面的移植与本土化的论述比较充分,而对新中国60多年法的移植与本土化,尤其是法学观念本土化的分析论述比较薄弱,本文拟从新中国立宪史尤其是从1954年宪法到1982年宪法等相关规定,以及之后的历次宪法修正案出发,就近代法学观念在新中国的本土化实践,以及这种实践成功背后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和进步进行一些论述,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
法学观念这一用语,并不是中国本土的产物,而是近代从西方传进来的。它是指人们尤其是国家的领导人(统治者)对法这一社会现象的基本看法。西方近代法学观念形成于17、18世纪,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摇旗呐喊的过程之中提出的。在格老秀斯(H.Grotius,1583-1645)、洛克(J.Locke,1632-1704)、孟德斯鸠(L.Montesquieu,1689-1755)、卢梭(J.J.Rousseau,1712-1778)和贝卡利亚(B.Beccaria,1738-1794)等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一整套政治法律学说中,涉及对法的基本观点,就构成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学观念,其核心内容为:法律是公意的体现,法律的目的是为人民谋幸福,法律至尊至上(法治),主权在民,所有人生而平等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就是做法律所允许的事情,权力必须分立、互相制约,罪刑法定,无罪推定,刑罚必须人道,司法独立等。
上述近代西方的法学观念在英法等西欧国家形成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也迅速传播至世界各地,中国也不能例外。早在1833年,即1840年鸦片战争尚未发生时,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Gutzlaff,1803-1851)就在广州创办了在中国内地出版发行的第一本中文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这本刊物上,刊登了不少宣传法治、三权分立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西方近代法学观念的文章。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1785-1850)、魏源(1794-1857)、梁启超(1873-1929)、严复(1853-1921)和沈家本(1840-1913)等人,进一步通过著书立说、修律变法等方式,将近代西方的法学观念引进了中国,〔3〕详细可参阅何勤华:《中国法学史》(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页9以下;李贵连:《沈家本传》,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页208以下。并影响了之后近40年中华民国的法制发展。〔4〕如中华民国1923年宪法、1936年宪法草案(“五五宪草”)和1946年宪法,均规定了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和司法独立等基本法学观念。
1949年9月29日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第一份宪法性文件,一方面宣告了“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和法令”(第17条);〔5〕这是继承了1949年2月22日《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的精神。另一方面,重视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在处理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等项原则时,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基本认可的态度。经历了1952年司法改革运动和政法院系调整的波折,人们开始认识到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也意识到西方近代法学观念是人类所创造的法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1954年宪法基本上都将其接受了下来。然而,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及接下来的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1962年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直至1966年爆发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将上述各项法学观念又统统予以了否定。
直至1982年宪法颁布,以及之后的四次修宪,才将1954年宪法规定的各项法学观念再次予以确认,其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法律至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司法独立等原则,对建立法治国家的价值最为重要,在新中国60多年的本土化历程也最为坎坷。由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观念,在我国已经不存在任何争议,而另外三项观念则多少还有一些分歧,〔6〕如最近,《法学研究》2012年第3期所发的顾培东先生的文章“当代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构建”,还对西方自由主义法治理论以及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顾先生的观点笔者基本上也是同意的。笔者想说的是,在数十年从事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以及不时参与司法实务活动的经历中,笔者深深体会到,在中国这么一个崇拜专制集权、习惯于人治而不讲法治、行政与司法界限不清、审判工作很难独立的国家中,作为我们法律人,多讲一些近代启蒙思想家提倡的法学观,强调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奉行法治、权力分立和制约,以及司法独立,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本文以下重点就法治、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司法独立这三项观念,做点分析和论述。
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对法治问题并没有明确的提法。在1949年2月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简称“指示”)中,我们对法治等西方法学观是持否定态度的,指示强调:“司法机关应该经常以蔑视和批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其他一切反动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人民的法律、法令的精神,来从事法制建设。”
这里,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和“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人民的法律、法令”,其实也包括法治等西方法学观念在内,因为西方法学观念在当时也被当作“旧法观点”,而“所谓旧法观点,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的法律观点”。〔7〕李光灿、李剑飞:“肃清反人民的旧法观点”,载《人民日报》1952年8月22日,第3版。根据当时我们党的要求,对这些不仅要批判,而且还要蔑视。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法学观念不仅没有地位,而且属于反动的思想,一般的人就根本不敢触及了。在1952年的司法改革运动中,“法治”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被屡屡点名,被指斥为旧法观点,而受到进一步的批判,并被彻底否定。〔8〕参见“必须彻底改革司法工作”,载《人民日报》1952年8月17日;陈传纲:“反人民的旧法律和人民革命政权绝不相容”,载《人民日报》1952年8月26日,第3版;曹杰:“旧法观点危害国家经济建设”,载《人民日报》1952年9月13日,第3版;叶澜:“清算反人民的旧法观点”,载《人民日报》1952年10月17日,第3版等。
受上述历史背景的影响,1954年宪法制定颁布时,我们没有能够直接提出法治的口号,也没有明确确立法治的原则。但是,在宪法制定前后全国(党)上下尊敬法律、重视法律的整体氛围之下,强调法律的统治,强调法律至上,强调对法律的敬畏,得到了宪法起草者的肯定。因此1954年宪法第18条是这么表述这种法治的精神的:“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
这里,宪法使用了“效忠”和“服从”来表示对民主与法制的尊敬,强调宪法和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结合宪法第2条、第20条、第21条规定的主权在民、代议制,第8条、第11条规定的依法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以及第78条、第83条规定的司法机关只服从法律等来思考,笔者认为,宪法第18条阐述的就是中国语境下的法治原则,或者说法律至上原则。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只过了两年多,1954年宪法规定的“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就为1957年的“反右运动”所否定,并遭受批判。之后,法律在中国的地位越来越低,法治始终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法学观而遭受批判和谴责,在20世纪50年代末及60年代初《政法研究》和《法学》上所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法治”甚至被描述为资产阶级法律“虚伪”、“反动”的特征之一。〔9〕参见丘日庆:“走上法西斯专政道路的美国‘法治’”,《法学》1957年第4期;叶孝信:“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的批判”,《法学》1958 年第4 期;孙国华、郭宇昭、许崇德:“肯尼迪叫卖的‘法治’”,《政法研究》1962年第2期等。有学者宣称:“(以‘法治’为核心的)旧法思想中有某些部分,(即使)在发生时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在今天已成了不合时宜的文化渣滓。”〔10〕刘焕文:“在‘百家争鸣’中谈旧法思想”,《华东政法学报》1956年第2期。实际上,作者刘焕文本人也是一名在民国时就已经成名的旧法人员,他于1956年写作此文的目的,实际上是想阐述对旧法观点不能全盘否定,应该吸收其中对建设新中国法制有益的成分。但在当时对旧法观点基本上一边倒地持批判、否定态度的氛围下,即使有一些试图阐述对旧法观点不能全部否定的文章,一般在开始时也要对旧法观点进行一番批判和谴责,然后再用“但是”等转折词来小心冀冀地诉说自己的观点。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之一。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我党长期以来实施的左的路线,实行法治的必要性得到了学界的重视。1979年12月2日,李步云等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要实行社会主义法治》一文,正式拉开了“法治与人治”讨论的序幕。《法学研究》还专门开设了“关于法治和人治的讨论专栏”。1980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小礼堂举办了全国第一个“人治与法治”专题讨论会,有400多名专家踊跃参加,气氛极其热烈。〔11〕这次讨论会的论文最后由群众出版社于1980年公开出版,取名《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从讨论的情况来看,当时主要提出了三种观点:①法治与人治是根本对立的,法治与民主相联系,人治与独裁相表里,因此社会主义要法治,不要人治;②法治与人治是可以统一的,法律要靠人去执行,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③法治与人治的区分是中国历史上的观点,我们应当抛弃这种提法。讨论的结果是第一种观点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正是在理论界对“法治”展开讨论并取得共识的基础上,1982年宪法第5条明确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经过30年的风雨历程,1982年宪法第5条规定的尊重和遵守宪法和法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不仅获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尊重,而且也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广泛认同。经过四次大的修改,30年之后的现行宪法第5条第2款以下一字不改地保留了1982年宪法的原文,而且还在1999年第三次修改宪法时增加了第5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而使法治从一个法学观或法律原则,上升为国家的基本方略、基本国策。
上述是宪法文本的本土化规定,在实际生活中,法治也已经开始慢慢地深入人心,受到党政机关和司法实务部门的高度重视。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王家福研究员应邀第二次进中南海,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讲授法律课,题目就是“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12〕讲座的详细内容,参见曹建明等:《在中南海和大会堂讲法制(1994年12月-1999年4月)》,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页64-83。讲座的观点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认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被写入了第二年中共中央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成为全党上下遵循的准则。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和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在全社会弘扬法治精神。
2012年7月,已经退休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第一任首席大法官肖扬出版了个人的法学文集,标题就是《肖扬法治文集》。从标题上看,肖扬与以往一般法律人出文集时都用“法律文集”或“法学文集”不同,用了“法治文集”,足见他对“法治”的重视。他在文集中说:
经过百年摸索,人们终于懂得:“法律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别的发明让人类学会了驾驭自然,而法律的发明,则令人类学会如何驾驭自己”。所以,为了体现人民意志的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不蒙污受辱,法律的殿堂不被摧毁,法律的光辉不黯然失色,法律和公平正义不被任意践踏,我们所有从事法律、法治、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人们必须肩负起神圣使命,实践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段话字数不多,但一位从事法治建设几十年的法律工作者对法治的期待和执著,在字里行间已完全显现。
同年6月18日,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王胜俊在全国大法官研讨班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在全社会弘扬法治精神,在审判工作中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并将“坚定法治信仰”列为法官的“政治责任”和“人格体现”。而2012年11月我们党的十八大报告则进一步明确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循私枉法”。
由此可见,法治这一西方法律文明的基本观念在新中国的本土化已经成功,成为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和法律生活中的核心价值。尽管在今后的征程中,法治在社会生活中的真正实现还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阻力,国内学术界的认识会有分歧,世界各国政府对法治的内涵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但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并经过二三百年各国法治建设实践证明的法治的一些核心要素,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政府公权力的运用进行限制,对公民个人(私)权利予以制度化的切实保障,强调法律是公意的体现,其目的就是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法律至尊、至高、至上,以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等,无疑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素和共同的普适价值,已得到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敬仰和遵守。
三
在近代法学观念中,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更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观念。
在西方,古代罗马早期的法律中,虽然私法很发达,但对私有财产或者说个人财产所有权的法律保护是不充分的,也是不平等的。当时法律中存在着市民法所有权、裁判官法所有权和万民法所有权等不同的所有权形态,法律依次给予不同的保护。随着罗马法治社会的进步,公元212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Caracalla,211—217 年在位)颁布了著名的《安敦尼努敕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13〕皇帝卡拉卡拉的本名,就是安敦尼努(Antoniniana)。将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境内的所有自由民(包括外邦人)。这样,不同种类的所有权之间的差别就开始消除,罗马人在财产上的法律平等才真正得以实现,从而使所有自由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得以真正实现。而个人财产所有权得到国家法律的平等保护,就使个人通过奋斗获得财产的劳动得到了尊重,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也得到了彰显。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开始萌发,并成为罗马法上的一个重要价值观,成为罗马留给后世的法律遗产之一。〔14〕2012年12月14日,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就《安敦尼努敕令》颁布1800年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意大利、德国、日本和中国的学者,就该敕令颁布的社会历史背景、敕令颁布之后西方公法和私法的变迁,以及该敕令的世界意义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收获颇丰。
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通过阐述、宣扬、传播近代政治观和法学观,在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摇旗呐喊、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的时候,将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提升到一个非常的高度。一方面,他们认为,个人对自己财产所有的权利是一项天赋权利,是人一生下来就具有的,它并不由法律来创设,甚至也不是由宪法来规定,而是先于宪法和法律,后两者只是对它认可而已。“在社会中享有财产权的人们,对于那些根据社会的法律是属于他们的财产,就享有这样一种权利,即未经他们本人的同意,任何人无权从他们那里夺去他们的财产或其中的任何一部分。”〔15〕(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页86。因此,个人所有权绝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人类理性的要求,是自然法的观念。《法国民法典》的主要起草者波塔利斯(J.E.M Portalis,1745—1807)将私人所有权原则称为“新的财产制度的灵魂”,甚至是“所有新的法律制度的灵魂”。他阐述道:私人财产所有权“本身就存在于我们中间,它不是人类协议和实体法的产物,而是一直存在于人类的构成当中,存在于我们与我们周围之物之间的关系当中”。〔16〕Chapitre 6:L’âme Universelledelalégalisation,in la naissance du Code civil,la raison du législateur,Travaux préparatoires du Code civil,Flammarion,1989,éd.2004,p.272.拿破仑(Napoléon,1769-1821)本人也完全支持私人所有权绝对性原则。他曾经说过:“所有权具有不可侵犯性。如我本人,手中掌管着大量的军队,却不能侵占一小块田地。因为侵犯一个人的所有权,就是侵犯所有人的所有权。”See Jean Guillaume Locré,Esprit du Code Napoléon,t.Ⅳ,Paris,impériale,1805,p.235.
另一方面,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认为,人们通过个人的努力、奋斗所获得财产的行为,是人类所享有的自由的一种,人们对自己财产拥有自由支配和处分的权利,是解放人性、张扬个性,实现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实现自我完善的必要前提。而这尽管看起来是一种获取财产的经济行为,但它和其他所有自由一样,与法律捆绑在一起,是互为因果的,即获得财产的自由,也是法律范围内的自由,是法律允许、保护的自由。如果没有法律,这种自由也不复存在。英国思想家洛克明确指出:人们享有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随其所欲地处置或安排他的人身、行动、财富和他的全部财产的那种自由”。〔17〕洛克,见前注〔15〕,页36。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反复强调:“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18〕(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页154。而另一位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也指出:“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的。”〔19〕(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页30。正是因为人们追求、获得、支配和处分财产的自由是法律上的自由,因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成为了近代西方法学观的核心价值之一。
此外,近代启蒙思想家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视为一项基本人权。洛克在《政府论》中明确指出:“最高权力,未经本人同意,不能取去任何人的财产的任何部分。”〔20〕洛克,见前注〔15〕,页86。1789年8月26日,在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由国民制宪议会发布的《人权宣言》继承和发展了洛克等启蒙思想家的观点,向全世界宣告人的自然的、不可动摇的四项基本权利: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人权宣言》第17条进一步宣称:“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人权宣言》确立的原则,后来就获得了西方各个资产阶级国家立法的认可,〔21〕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17A(III)号决议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其第17条也明确宣布:“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任何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所有权神圣、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成为了西方资产阶级法学观的重要组成部分。〔22〕私人财产所有权绝对、神圣不可侵犯,首先意味着法律给予所有权人支配其所有之物最大的自由权,凡是法律未明确禁止的行为,所有权人皆可为之;其次表明法律对权利人的所有权予以最大的尊重和保障,除了法律规定的之外,任何人不得对所有权人的财产进行侵害。这一法理认识和法律规定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性,因为在此之前,任何时期的法制都从未正式承认过私有财产所有权的这种绝对性质。20世纪的法律对私人所有权行使的限制虽然越来越严格,但上述私人所有权的本质以及进步意义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正是在上述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引领下,1804年《法国民法典》在第537条明确规定:“除法律规定的限制外,私人得自由处分属于其所有的财产。”第544条规定:“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但法令所禁止的使用不在此限。”从而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作为近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确立了下来。之后,1866 年的《意大利民法典》、1898年的《日本民法典》、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都继承了《法国民法典》的传统,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作为一项法治原则固定了下来。1929年9月至1931年1月间通过的《中华民国民法典》,也在第765条规定了此项原则:“所有人于法令限制之范围内,得自由使用、收益、处分其所有物并排除他人之干涉。”同时,无数资产阶级的法学家对这项原则进行了充分的理论研究和阐述,使其上升为一个资产阶级的重要法学观,成为资产阶级法律生活中的核心价值之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原则和观念的认识是清楚的,但表述是策略的。1949年的《共同纲领》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实际,提出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第26条)。明确提出:“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第27条);“凡有利于国针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政府鼓励并扶助其发展”(第30条)。这些规定,虽然比较简略,但显示出的精神对公民的私有财产还是持积极的法律保护政策的。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几年时间,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共同纲领》上述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原则和观念的实事求是处置是分不开的。
1953年,在起草宪法时,一方面,党和政府当时对周鲠生(1889-1971)、张志让(1893-1978)和钱端升(1900-1990)等老一辈的法学专家比较尊重,将他们或任命为宪法起草委员,或任命为法律顾问,让他们参与到起草宪法的队伍中来,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另一方面,当时我们也参考了世界各个国家(如苏、罗、波、德、法、捷等)的宪法文本,以及中华民国时期的宪法文本(如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1923年曹锟宪法、1946年蒋介石宪法),注意吸收各宪法中有利于我们新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23〕韩大元:《1954年宪法与中国宪政》(第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页66-67。此外,当时我们也比较务实,考虑到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私有财产在国民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等各项因素。尤其是在1954年宪法起草过程中,我们的民主发扬得特别好,有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全国各地参加宪法草案讨论的人数约占成年人的70%以上,有些大城市中约占90%以上,提出修改宪法的意见有50多万条)。因此,我们当时的理想尽管是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但在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项原则时,我们还是比较科学的,兼顾到了吸收西方用法律来保护私有财产和中国正在向社会主义转型的国情这两个方面。〔24〕关于1954年宪法的起草、制定、颁布之详细过程,可参见同上注,韩大元书之各个章节。
具体而言,1954年宪法对公民私有财产的规定是这样的:“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第8条);“国家依照法律保护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第9条);“国家依照法律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第10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第11条);“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第12条)。当然,1954年宪法这种实事求是的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不久就因为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25〕参见张懋:“彻底与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决裂”,《政法研究》1958年第6期。以及1966年以后延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而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不仅在宪法和法律上取消了对公民之“劳动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之外的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保护(1975年宪法),〔26〕1975年宪法关于公民的“劳动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规定极其简略,仅有两个条文涉及:第5条“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在城镇街道组织、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统一安排下,从事在法律许可范围内,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第7条“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牧区社员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在实际生活中,宪法上规定的这些个人财产只能限于生活资料(满足自己吃用)的范围,如果多余了拿出去交换(卖)的话,就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就要被没收和处罚,这在当时叫做“割资本主义尾巴”。笔者当时(1971-1977年)在农村时,就多次经历过这些事情。而且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予以严厉批判,彻底否定。〔27〕在上海出版的1958年9月15日《解放》(半月刊,第6期)上,发表了张春桥(时任中共上海市委政策调查研究室主任)所写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提出了有关资产阶级法权就是通过法律来保护私人占有财产的不平等的制度,而这种制度到新中国时虽然已经被推翻,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还严重存在。张春桥回顾了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与人民共甘苦,在经济上实行供给制的那种崇高境界,主张“在新的条件下,(应当把上述光荣的革命传统)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张春桥的观点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经毛泽东批转(编者按由毛泽东撰写),全文由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转发。张春桥的这一文章虽不长,提出的观点也不复杂,但被接受成为了中国执政党的理念后,对公民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所产生的冲击则是巨大的(张文的中心思想是私有财产多寡不均,而法律保护这多寡不均的私有,就是维护了财产制度的不平等,因此,资产阶级法权的核心就是等级制)。仅从1958年10月以后《人民日报》开展的“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讨论”之专栏来看,在11月一个月中,就刊登了7期专题文章,批判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不平等性,提倡实行供给制,并就要否按劳取酬和多劳多得、要否实行八级工资制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1978年宪法制定时,虽然我国已经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但由于当时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治国思想还比较左,局限于“两个凡是”的左倾指导路线,在法治建设上并无建树,因此,关于公民个人财产法律保护的规定,一字不改地沿袭了1975年宪法的规定。1982年宪法克服了“两个凡是”的左的路线,在公民私有财产保护方面,比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要大大前进了一步,但囿于当时的经济体制现状(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开始)以及人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性质的认识水平,除了第13条和第14条延续了1954 年宪法第11 条和第12 条的规定之外,其他方面仍然十分简单。1978 年宪法第11 条的规定,即“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连“私有财产所有权”的概念都没有使用。
社会的变迁、经济的进步是法律制度和法学观发展的原动力。1984年以后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依次确立,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形态在我国经济发展总量中所占比例的日益扩大,公民的私有财产在中国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富裕、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大,我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以及中国加入WTO 等,都促使我国的立法(修宪)者逐步意识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项原则和法学观念在人们的法律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伟大指导意义。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揭示的私有财产所有权是人类所享有的自然权利,法律只能对它认可而不能创设和剥夺的观点,虽然还没有得到中国法学界的普遍赞同,但私有财产所有权是基本人权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也是法律文明进步的标志,这一观点则得到了全体法律人的认同。
基于上述认识,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对宪法关于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做了重大修改,并明确宣告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法治原则,与近代以来为主要法治国家所一致认可的法学观念相比,只是在语句表达上做了适当修改,如在“私有财产”前面加上了“合法的”等限制词,以及在“不受侵犯”前面去掉了“神圣”之形容词,即表述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第13条)。同时,强调了对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的保护(第6、7、8条)。
笔者认为,在中国目前社会转型剧烈、某些人的巨额财产并不是通过辛勤劳动、合法取得的情况下,在“私有财产”前面加上“合法的”等限制词,并突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强调对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的保护,是非常合适,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总的来说,从古代罗马法中萌芽、在近代西方诞生的、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人类法律文明进步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和观念,已经为新中国的宪法(包括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所公开确认。经过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其本土化已经成功,这应该是没有疑问了。〔28〕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强调“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同时,也明确指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四
司法独立作为一项法治原则和法学观念,是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留下来的法律文化遗产,其物质形态就是当时古代希腊罗马社会存在的独立于行政机构的法院,如古代希腊的陪审法庭等。此外,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等思想家关于政体,关于立法、行政和司法互相分立并互相制约的思想,也成为了西方政治法律学界关于“司法独立”的萌芽。〔29〕在《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作为构成的基础”。“倘使三个要素(部分)都有良好的组织,整个政体也将是一个健全的机构。”这三个要素就是议事机构(负责立法)、行政机构(负责管理城邦国家的日常事务)和法庭(负责司法)。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页214、220、228。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西方启蒙思想家为了给资产阶级的统治设计政治蓝图,也为了使资产阶级的统治长治久安,开始在理论上提出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的设想。1689年和1690年,在英国“光荣革命”取得成功的第二年和第三年,洛克出版了《政府论》两篇,提出将国家的统治权力分为三个部分: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以便互相监督、互相制约。〔30〕洛克,见前注〔15〕,页82、94-95、98。1748年,孟德斯鸠在吸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考察欧洲各个国家的政治法律现状之后,针对当时法国的实际,提出了更为完善的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的理论,强调“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31〕孟德斯鸠,见前注〔18〕,页154。强调了司法独立的重要意义,“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32〕同上注,页156。
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思想,一经提出,便为各资产阶级国家所欣赏和接受。美国联邦党人汉密尔顿(Hamilton,1757—1804)、麦迪逊(Madison,1751—1836)等,就以洛克、孟德斯鸠的理论为指导,结合美国的革命实践,为美国设计了如何使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有效运作的制度,他们认为,“合众国任命的一切法官,只要行为正当,即应继续任职”(即法官终身制)。〔33〕(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页390。他们认为,在国家统治权中,与立法权和行政权相比,司法权是最小也是最弱的。因此,“除使司法人员任职固定以外,别无他法以增强其坚定性与独立性;故可将此项规定视为宪法的不可或缺的条款,在很大程度上,并可视为人民维护公正与安全的支柱。”〔34〕同上注,页392。“在任何政府设计中,此项规定均为保证司法稳定性及公正不阿的最好措施。”〔35〕同上注,页391。为了提升司法机关的权威,联邦党人甚至还提出了赋予法院以审查国会立法是否违宪的权力。〔36〕“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如无此项规定,则一切保留特定权利与特权的条款将形同虚设。”同上注,页392。
在中国古代,既没有司法独立的学说或者理论,也没有与行政机关相分离的独立的审判机关。在地方,知县、知府等既是行政长官,也是审判官员。在中央,虽然管理审判事务的机构曾经有过廷尉、刑部、大理寺、御史等专门机关,但审理重要的案件时,各个朝代始终都会有一些其他各部门首长(在明代甚至有锦衣卫、东厂等特务机构)的参与,而所有案件的最高审级则是皇帝。“从理论上而言,所有的司法机构不过是皇帝作出最终判决的咨询机构而已。”〔37〕郭建、姚荣涛、王志强:《中国法制史》(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页366。司法独立的观念传入中国,是近代沈家本进行立法改革时的事情。1901年,沈家本受命变法修律,他聘请外国法律专家,翻译外国著名的法典和法学著作,引进外国先进的法律理念和制度,使西方法学观开始在中国传播,而司法独立就是西方法学观中最为重要的内容。〔38〕宣统元年(1909年)制定颁布的《法院编制法》和宣统二年制定的《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和《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均由沈家本主持,其中都规定了司法独立的原则。1928年中华民国政府制定六法全书时,也继承了沈家本的立法成果,在法律体系中规定了司法独立的观念和制度。
新中国建立以后,司法独立作为资产阶级的法学观首先受到了批判和否定。1952年的司法改革运动,其三个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批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和司法独立等“旧法观点”。〔39〕另外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将我国司法队伍中的旧法人员总共6000多人全部剔除出去(当时全国共有司法人员27000多人);另一个是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法学观、国家观改造我们的司法队伍。详见何勤华:“论新中国法和法学的起步”,《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当时基本的认识就是,旧法观点“包括了反动统治者所遗留的反人民的整套法治,从法律的思想体系到司法的组织制度以及许多统治、压制人民的方法和作风”。而司法独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等,则是旧法观点的核心内容。这些旧法观点,尤其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司法独立,既是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一种“欺骗”,也是资产阶级法律制度“虚伪性”的突出表现。〔40〕参见李光灿、李剑飞:“肃清反人民的旧法观点”,载《人民日报》1952年8月22日;陈传纲:“反人民的旧法律和人民革命政权绝不相容”,载《人民日报》1952年8月26日;叶澜:“清算反人民的旧法观点”,载《人民日报》1952年10月17日,第3版。
制定1954年宪法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宪法和法律开始予以关注,开始强调宪法和法律的重要性,对司法独立这一西方重要的法学观念有了新的认识,意识到它对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不仅不再将其作为“旧法观点”而加以批判和否定,而且将其精神用中国式的语言在宪法第78条中作了精确地表述:“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应该说,1954年宪法的这一规定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司法独立”,但能够从确保审判独立、强调审判活动只服从法律、以实现司法公正为出发点做出上述规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之下,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当然,1954年宪法的规定严格意义上只能说是“审判独立”,还不是“司法独立”。司法独立的范围要比前者宽广得多。笔者认为,审判独立是司法独立的核心,也是司法独立的基础和底线。因此,笔者在多篇论文和讲座中提到,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当时的语境下,审判独立和司法独立具有相通性,“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就是中国语境下的司法独立的表述。但如果仔细推敲的话,实际上两者还是有着重要的区别:
第一,司法独立除了法律意义之外,还具有政治意义,而审判独立只是一个法律原则,是一个法律概念。司法独立在政治层面上讲述的是政体的问题,即国家的统治权力如何设置,才能最为有效地管理好国家,协调好各种群体和各个利益集团的关系,防止权力走向腐败,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它是和三权分立这一基本原则是相关联、相配套的。司法机关通过与立法和行政机关的分离,不仅能够保证不受干预地独立审判案件,而且在政治权力格局中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力,司法权形成对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监督和制约,防止国家最高统治权力由一个部门行使、缺少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而可能造成的权力腐败。因此,在政治层面上,司法独立并不仅仅是一个司法的问题。
第二,就是在法律意义上,司法独立的内涵也要比审判独立丰富得多。司法独立在法律层面上讲述的是司法公正的保障问题。审判独立只解决了审判阶段保证审判机关不受干预地独立审理案件的问题,只强调了法官的司法公正的责任问题。但是,法官是生活在复杂的社会之中的,他们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也要养家糊口,在审理案件时,也有许多后顾之忧。如何消解法官的后顾之忧,确保法官能够义无反顾地、在心理上和生活上都不受干预地独立审理案件,真正实现司法公正的目标,就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制度保障。对此,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设计了各种制度,如法官的高薪、法官的荣誉、法官任职的严格条件和法官就职的庄重程序(如在宪法面前进行宣誓等),乃至法官的终身制等。〔41〕对于这一点,中华民国时期的宪法就已经关注到了,虽然在实际生活中,民国政府并没有能够做到。如1946年宪法延续了1923年宪法第102条、1936年宪法草案(“五五宪草”)第81条的规定,在第81条更明确地强调:“法官为终身职,非受刑事或惩戒处分,或禁治产之宣告,不得免职。非依法律不得停职、转任或减俸。”
但是,在1957年夏天开始的“反右运动”中,为1954年宪法所肯定并作出规定的审判独立(还没有上升为司法独立)的原则和观念,再一次作为“右派言论”而受到批判和否定。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间,司法独立的原则和观念再也没有人敢提及。其间,1975年的宪法和1978年的宪法都没有明确规定司法独立的精神。一直到了1982年宪法,才在第126条再次规定了审判独立(中国语境下的司法独立)的原则:“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1982年宪法颁行30年来,已经经历了四次重大修改,但此条规定没有变动,一字未改地保留在现行宪法之中。
与1954年宪法的规定相比,1982年宪法(现行宪法)的规定有两个方面的改动:第一,在独立行使审判权之前加了“依照法律规定”,从而将1954年宪法规定的第二句话“只服从法律”作为定语提前,来修饰“独立行使审判权”。第二,增加了“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表面上看,1982年宪法更强调了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独立性”,因为增加了“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内容,但实际上,与1954年宪法的规定相比,1982年宪法削弱了法院审判的独立性以及法律的权威。一方面,对排除N 个主体的干涉,用列举式总是无法穷尽的,不如用一句“只服从法律”可以全部覆盖。另一方面,“依照法律规定”和“只服从法律”,无论在语气上,还是在审判工作是否能够独立进行上,都有着相当大的区别。“只服从法律”,表明了只有法律才是审判工作唯一可以依据的本源,表明了对法律的尊重,体现了法治的精神。尤其是在目前高科技社会、网络世界、微信时代,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而“只服从法律”,则可以排除各种组织、政府、人大、社会团体以及舆论、网络、媒体等各种形式对审判工作进行干涉的任何可能性。
因此,下一次对宪法进行修改时,笔者建议恢复1954年宪法的规定,使司法独立(审判独立)的精神真正落实到实处,以确保司法公正,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虽然司法独立的原则至今还没有被规定进我国的宪法和法律之中,但一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某些场合已经发表了要求贯彻“司法独立”原则和观念的讲话。如温家宝总理于2012年9月14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明确指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自由平等,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坚持司法独立和公正,是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的根本要求。”〔42〕温家宝:“各方面改革须逐步推进”,2012年9月14日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另一方面,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明确地规定了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法律。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王胜俊在2012年6月18日全国大法官研讨班的讲话中,也进一步要求所有法院干警:“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自觉把宪法和法律作为最高准则,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坚守公正底线,敢于排除一切干扰,秉公执法,公正办案,切实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和权威。”
此外,无论是党的报告还是国家领导人如胡锦涛、习近平、温家宝、李克强等的讲话,都明确要求司法机关做到“司法公正”。而在西方语境下,司法公正是和司法独立相联系的,甚至有时就是同一个含义,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司法独立,司法公正是不可能的。西方各国包括我国的港澳台地区,还为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设计了各种保障措施,如法官的高薪、法官的特权以及法官终身制等。因此,笔者认为,在法律层面上,从审判独立到司法独立,虽然只是两个字的区别,但体现了在确保司法公正上的一个飞跃:审判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初级阶段,司法独立则是审判独立的高级阶段。与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仍然处在初级阶段相适应,我们目前也只能以实现真正的审判独立为目标——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审判工作往往会受到各种干预。等到我们真正实现了审判独立的目标,我们再争取早日实现法律层面上的司法独立的目标。从这一点来看,司法独立在新中国的本土化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它的完全成功,还需要我们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五
上述三项原则和观念既互相呼应,又密切相关:法治,就是在治理国家、使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各个领域都遵守法律的规定,体现法律的权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强调了人们对财产的获得和拥有的自由,必须是在法律范围内的自由,离开了法律,这种自由也不复存在;〔43〕“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的这一命题,虽然已经过去了320多年,但其真理性丝毫不减。参见洛克,见前注〔15〕,页36。司法独立,在中国语境下的意思就是审判独立,即“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只服从法律”,它是指在法治框架内的独立。而且,司法独立的唯一目的就是实现司法公正,而司法公正是树立人们对法的尊敬、对法的信仰的唯一路径。
因此,在上述三项原则和观念中,法治是最高的。如果我们能够对此形成共识,并将其本土化的实践持之以恒的进行下去,笔者认为,中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时就不会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