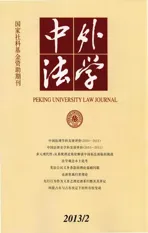宪法公民义务条款的理论基础问题一个反思的视角
2013-01-21姜峰
姜 峰
引 论
与对基本权利的大量研究文献相比,公民的宪法义务问题较少受到关注。〔1〕近年关于公民宪法义务的讨论主要有:张千帆:“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王世涛:“宪法不应该规定公民的基本义务吗?——与张千帆教授商榷”,《时代法学》2006年第5期;朱孔武:“基本义务的宪法学议题”,《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沈寿文:“中国宪法文本规定公民(人民)义务的原因探析”,《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李勇:《论公民的宪法义务》,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其中,张千帆教授对宪法义务持明确否定态度;王世涛教授、李勇研究员持支持态度;朱孔武教授、沈寿文教授主张对宪法义务作新的理解。且大多数学者对宪法义务条款的合理性没有提出质疑。原因有二:第一,宪法义务条款似有足够的理由支持:它是权利义务“统一论”的要求,符合宪法的“纲领性”特征,顺应宪法的“发展趋势”,也有助于构造公民的“国家认同”或强化“集体价值”。第二,宪法义务在实践中没有引发严重的问题:权利常常受到侵害,义务却从未缺斤少两,而且,人们很少出于关心权利而对义务条款投去怀疑的目光。
然而,这两个方面都大可存疑。概言之,就第一个方面中的权利义务“统一论”而言,尽管其在一般意义上无可厚非,但并不适用于“宪法”层面,亦即那些支持“宪法权利”的理由可能并不支持宪法义务;关于宪法的“纲领性”说,其将宪法义务视为一般法律义务之纲领的看法,把宪法自身的规范性转移给了具体立法,这本身就是一个误解;关于那种把义务入宪归为宪法发展“趋势”的说法,其问题可能尤为明显:它既不符合经验事实,也有违论证的逻辑——它是一种“类比推理”而非论证方法。对于宪法义务有助于构建公民的“国家认同”这一更具哲学意味的理由来说,我们也大可存疑:它贬低了权利对于社会合作的价值。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公民的宪法义务的确不存在受到侵害的问题,这与宪法权利的处境形成鲜明对照,但这或许恰恰是问题之所在。同为宪法规范,权利条款之易受政府侵害与义务条款之受政府青睐,乃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它们尤其反映了当下中国宪法面临的窘境。因此,对宪法义务背后理论基础的反思将是建设性的,它有助于揭示盘踞在宪法学核心地带的一些误解,并为我们推进基本权利保障排除若干认识障碍。
本文赞同已有研究对宪法义务条款提出的挑战,但拟提供新的理由和观察视角。文章分五个部分展开讨论:第一至第四部分将分别对支持宪法义务的四个理由——“统一论”、“纲领说”、“趋势论”以及“国家认同”说进行批评性讨论。这几个部分中所质疑的宪法义务,是从为公民课以负担的意义上使用的,这既是宪法起草者的原旨,也是人们对义务条款的通常理解。第五部分讨论了理解宪法义务条款的一个可能路径——权利视角,亦即义务条款不是要对公民课以负担,而是为这种负担设定条件。这一视角是权宜性的,系出于维护宪法稳定性考虑而理解现有义务条款时可能采行的路径。
对宪法义务之理论基础提出挑战,并非要发动一场索然无味的战争,它与权利保障密切相关。以宣告公民负担为目的的宪法义务条款,不仅无须存在,而且不应存在,其背后的支持理论不仅阻碍着对现代立宪主义的正确理解,而且也是当前我国妨碍基本权利得以落实的认知原因。
一、权利义务“统一论”?
我国1954年《宪法》规定了遵守宪法和法律、护卫公共财产、依法纳税、依法服兵役等四项公民基本义务,其支持理由清晰易辨。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在我们的国家里,人民的权利和义务是完全一致的。任何人不会是只尽义务,不享有权利;任何人也不能只享有权利,不尽义务。”〔2〕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62。长期以来,对宪法义务的支持延续了这一理论,当下的学者也大多对此深信不疑。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宪法调整的是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作为主体双方的公民与国家,既是权利主体,也是义务主体。对国家而言,公民享有权利意味着国家的义务;对公民而言,某一权利的另一面也是其义务。两方面结合同时表明,宪法规定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符合权利义务关系的一般原则,是权利义务相一致原理的宪法体现。〔3〕郑贤君:“权利义务相一致原理的宪法释义——以社会基本权为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1996年,李龙教授、周叶中教授在《宪法学基本范畴简论》中也明确提出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是宪法学的一对基本范畴。这种观点极具代表性。〔4〕类似的表述还可参见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184;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88;沈宗灵主编:《法理学》(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76-77等。
令人惊讶的是,“统一论”言之凿凿的辩护大多是针对“义务”而非“宪法义务”提出的。论者为证明宪法义务而援引的苏格拉底的回报论、西塞罗的合作论、格老秀斯的社会交往论、洛克的权利让渡论、黑格尔的“他人”理论、密尔的群己权界论等,皆系针对“义务”而非“宪法义务”提出的。〔5〕相关讨论可参见李勇:“宪法义务理论及发展趋势”,《中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论者也多援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页16。——来论证宪法义务的合理性。的确,就整个法律规范体系而言,“统一论”无可厚非,因为义务规范与权利规范都是必要的组成部分,但就“宪法”层面而言,必须另当别论——写入权利并不意味着也需要写入义务。换言之,基本权利的入宪理由并不因为“统一论”而支持宪法义务。对此,一个前置性问题是:为什么要有宪法权利?堪称“权利”的事项很多,但为什么有些成了“宪法权利”而有些仅需以“法律权利”存在?对此问题的探究能够帮助我们检讨支持宪法义务的理由是否成立。
使某些权利成为“宪法权利”,是有特定原因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是,成文宪法之所以必要,是因其具有先于并高于政府的地位。汉密尔顿的解释最为清晰:宪法是“由人民制定、政府不能更改的”,而法律是“由政府制定、政府能够更改的”。〔7〕(美)杰伊、汉密尔顿、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页273。宪法是为规范日常政治过程、防范其侵权危险而存在的。这一属性使宪法同以管理社会为目的的普通法律区别开来。因此,哪些权利写入宪法,哪些权利写入普通法律,就成了一个问题。本文在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宪法权利的两个遴选标准。
首先,宪法权利具有特殊重要性。权利的重要性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第一,康德主义立场。按照这一立场,权利之所以重要,在于其为个体人格的独立和完整所必需。以表达自由这一最无争议的宪法权利为例,人既然是有理性、有思想的动物,思想的表达就成为这一特性的延伸,剥夺它等于否定个人完整性,而这无异于使人复归于动物。这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信条。对此,一个较弱意义上的、稍显庸俗的理解是把个人权利理解为一种可以自主取舍的私人利益,它与那种“放弃权利也是在行使权利”的法理学观点一致。第二,密尔的功利主义立场。根据这一立场,表达自由的价值不在于对个人如何重要,而在于维持政治社会的健康运转。个体表达自由的功能是社会性的:它是有效的信息提供机制,只有差异性观点在“思想的自由市场”中充分竞争,立法和公共决策才可立基于充足的信息基础之上,而对思想市场的政治垄断,将导致政府像一个人格化的主体一样闭目塞听,敏感而易怒,削弱其做出合理决策的能力。就此而言,政府对充足信息的依赖与个人决策的条件是相同的。
关键的问题在于,仅仅基于康德主义立场不足以区分宪法权利和非宪法权利的“重要性”,因为权利对个体的重要性通常因人而异。对于一个同性恋者来说,与同性结婚可能比批评政府或选举国会议员重要。个体重要性这一理由,会支持将所有“权利”都写入宪法,但这显然会导致“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的边界不复存在,而宪法条款也将变得极其冗长。功利主义立场凸显了表达自由的宪法地位,并使两种权利的界限清晰易辨。亦即,由于表达自由事关民主社会的健康运转,而追逐公共利益的政府又往往怠于为其提供充分保护,其在宪法层面上庄重宣示才是必要的。而表达自由的公共属性支持将其写入宪法。换言之,区分的标准在于:关涉个人利益的权利可单独由普通法律规定,而作为构造政治过程之基础性条件的权利,应当写入宪法。言论自由、选举权、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等传统宪法权利,皆具此一特征。
宪法权利的第二个特征是它们不但重要而且“脆弱”——它们首先容易受到政府的侵害。对于私人之间的权利侵害,政府有足够的动机和手段予以救济,因为这会强化政府的权威。但是,就人的天性和权力的本性而言,批评政府的言论、集会、示威等会天然地令其不悦,无论是独裁政府还是民主政府,都希望公民服从而不是挑战自己。体现“正当程序”价值的沉默权、禁止双重危险、辩护权等基本权利,亦有同样的特征,它们本质上是在为政府追究犯罪设置障碍而不是提供方便。因此,这里的“脆弱”并非指宪法权利比其他权利更容易受到私人侵害,而是因其常常为政府所厌恶而岌岌可危,宪法之所以把这类权利确定为“基本权利”,就是要凭其“先于并高于政府”的“超规则”地位防止政府的漠视和侵害。
个人与政府的实力对比反映了权利的脆弱性,接受这一点无须假定掌权者个人品质有堕落风险,侵权应被视为负向政治激励的产物;我们也不需要区分威胁到底来自民主政府与专制政府,前者对个人的威胁并不一定小于后者。遏制君主或贵族寡头统治的任务,在近代已经由民主制度的确立完成,但民主制又带来了“多数派专制”危险——多数派在议会中趾高气昂,少数派则显得势单力孤,这种新型专制比君主专制似乎更容易获得正当性、更加隐蔽,因此也更难抗拒。这就更需要“宪法”权利,它要担当德沃金所说的个人手中的“王牌”的角色,以限制议会立法和政府政策的范围和深度。关于立宪主义的这一关键属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大法官杰克逊说得切中要害:“权利法案的真正宗旨,就是要把某些事项从变幻莫测的政治纷争中撤出,将其置于多数派和官员们所能企及的范围之外,并将其确立为由法院来适用的法律原则。”〔8〕West Virgini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v.Barnette,319U.S.624(1943).
上述两个特征,使“宪法权利”(基本权利)同“法律权利”(非基本权利)区别开来,亦即,指向私人主体、满足个体偏好的权利用普通法律来确认,由政府保护之;而指向政府的具有强烈公共属性的权利,以宪法来确认,由独立于政府的部门(如法院)保护之。这一区分不在于使两种权利的边界泾渭分明,其意义在于提供一个一般性理解,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检讨“宪法义务”的理论基础是否恰当。区分两类权利以及强调宪法权利的重要性与脆弱性,并不是要说宪法保护的利益不同于民法,而是说它们的防范对象和保护方式不同,这也使那些同属宪法权利和普通法律权利的事项具有了不同含义。例如,民法上的财产权、人格权、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是为防止平等主体之间侵害的,而宪法上的这些权利则旨在训诫和防范政府。
让我们回到主题:被称为“宪法义务”的事项,是否也像宪法权利那样“重要”且“脆弱”,以至于必须诉诸宪法宣告才能保证其实施?宪法权利是为了防范政府,宪法义务是否亦然?根据上面的分析,答案是否定的。与对权利的态度形成对照的是,义务虽然不可或缺,但政府从来都不厌恶它们,而且其既不缺少动机、也不缺少手段来落实之。此一判断,同现代成文宪法普遍设立严格修改程序之目的也是完全一致的。对修宪的程序性控制,只有针对公共权力机关才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在日常政治中不免承受党派利益或紧迫情势的压力,最易产生克减公民权利的冲动,公民义务却不会面临这种克减风险。综上,义务——无论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都无须以宪法条款来确保其实现,它们固然不可缺少,但交由普通法律足以保证其落实,并且可随日常情势的变化而适时调整。由是观之,将权利写入宪法的理由并不适用于公民义务。
二、宪法规范的“纲领性”?
另一种支持宪法义务的理论可以概括为“纲领说”。根据此说,宪法乃一国政治法律制度的基本纲领,凡普通法律中的事项皆应有宪法依据,因此义务也应于宪法中载明。这一理解常常借助一个比喻——两类规范系“母子”关系:“母法”是立法大纲,“子法”是规范细则;“母法”指导“子法”,“子法”落实“母法”;二者构成一个封闭的整合关系。这体现了宪法起草者以及为其辩护的理论家们一种相当特殊的宪法观——宪法是一部宣示性强于规范性的“政治法”,其功能在于对具体法律提供指导,且因宪法规范较为原则和抽象,其自身可以不具有直接的规范效力。〔9〕例如可参见王世涛:“宪法不应该规定公民的基本义务吗?——与张千帆教授商榷”,《时代法学》2006年第5期。
许多宪法教科书在解释宪法规范的特征时,将“规范性”与“纲领性”并举,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纲领性”有排斥“规范性”的内在冲动,因为既然宪法要为政治和社会生活诸方面建章立制,而出于宪法文本不能过分冗长的考虑,又不能将所有的具体规范宪法化,这就必须以条文的抽象性和原则性为代价。这种无奈等于是把抽象性和原则性视作宪法规范的一个内在缺点了。值得注意的是,“纲领说”并非对此无所应对,它的策略是对宪法和普通法律进行功能区分,构建一种前述的“母法”与“子法”关系。这样来看,宪法就成了普通法律的立法目录,而普通法律则成了宪法的规范细则。
这种“母子”比喻的问题在于,它把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简化为效力等级的高下之分,而忽略了实质性不同。“纲领说”认为宪法权利统领普通权利,宪法义务统领普通义务。但是,诉诸于宪法的好处可能不过是加强了说话的语气。在这一问题上,可以推定它们与当前那种把各色权利呼吁“入宪”的主张如出一辙,虽然这看似不属于本文的论题,但所依持的理由是一致的。它们也误解了宪法权利与普通法律权利的某些关键性区别。比如,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关键区别并非在于效力等级有别,而是适用不同的标准。一个立宪政体能够容忍某人对政府的尖锐批评,但不会对他针对邻居的恶语相加袖手旁观,而对政府管制政治性言论的司法审查,通常也比对管制私人言论更为严格。宪法“平等权”亦然,它义正词严地告诫政府不能按性别、种族、民族等先天因素对公民进行“可疑分类”,但注定对个人交友、择偶、选择商业伙伴时近乎毫无约束的区别对待无能为力。说到底,历史悠久的公/私法二分观念坚不可摧。“私人主体无须追逐公共利益:他们是自治的,而且可以依照他们对正义的理解来作出自己的选择。”〔10〕(荷)杨斯密(Jan Smits):“私法和基本权利:一个怀疑的视角”,程雪阳译,《国外社会科学论丛》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页509-520。另可参见Ernest J.Weinrib,The Idea of Private Law,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5.p.208ff.中译本:(加)欧内斯特·J.温里布:《私法的理念》,徐爱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在这本著作中,作者以现代视角对公共利益和私法之间的本质不同进行了令人信服的解说。换言之,公民个人“没有遵守宪法的义务”。〔11〕相关讨论可参见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页21-29。宪法与普通法律这对“母子”的基因差异竟如此之大!
“纲领说”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是一个危险:它将宪法与普通法律简化为抽象与具体、模糊与清晰、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因此理所当然地把宪法的规范性转移给了普通法律。这种对日常政治过程的信任而不是警惕,与立宪主义的基本预设是矛盾的,因为日常政治的党派特征恰恰是宪法防范的危险之源。例如,作为现代成文宪法之起源的美国宪法,其关键性的立宪安排——两院制、总统否决权、权利法案、司法独立和违宪审查,皆基于对日常政治过程(尤其是立法活动)的不信任而设定,它们通过限制立法决策的深度和范围来发挥作用。而且,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制度的有效运转强烈依赖于对宪法自身规范性的诉求。“纲领说”则削弱了宪法自身的规范特征,使它同普通立法和政治过程之间的紧张关系被遮蔽。正确的看法是,宪法条款的含义和规范性应从其自身产生,而非借助“具体化”立法,否则现代立宪主义所推崇的司法独立、违宪审查等制度设计根本无须存在。
宪法正因其“先于政府并高于政府”的地位,才有对政府立法的规范作用,此一规范性立基于其与政府的建设性紧张关系。事实上,宪法在其所关注的两大基本内容即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设置上,这种规范作用都极为明显。就国家权力而言,宪法之所以把国家机关的组成、任期、职权、相互关系等规定下来并设定严格的修改程序,就是为了防止日常政治中的强势党派做出利己性修改。一方面,尽管这种情况或许并不经常发生,但一旦发生将对政治游戏的规则造成根本性破坏;另一方面,对日常政治竞争的宪法限制一旦缺席,则其导致的反向激励将造成政治生态趋于败坏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宪法不但要把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秩序规定下来,更需把那些最易受到日常政治中强势派系破坏的规则加以明确规定。就此点来观察,宪法自身的规范性责无旁贷。美国宪法对总统和国会议员选举方式不厌其烦地加以规范即属此例。就公民权利而言,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正是基于对政府怠于保护某些权利的担心才将其写入宪法。而与此同时,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宪法地位之所以在许多国家的宪法学说中受到排斥,是因为它们根本上并非政府所厌恶的对象,日常政治的竞争性特征使得追逐选票的势力有动力对这些权利作出承诺和改善。〔12〕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不具有前文所说的公共“重要性”和“脆弱性”,对它们的保障主要应依赖于一个富有活力的民主政治过程,相关讨论可参见姜峰:“权利宪法化的隐忧——以社会权为中心的思考”,《清华法学》2010年第5期。综上,无论从哪个方面说,把宪法的实施寄望于具体立法,都是在削弱其规范基准地位,并放纵日常政治对宪法秩序的挑战。
“纲领说”削弱了宪法对日常政治的防范,其所强调的宪法的“原则性”,在实践中可能带来两个互为映射的危险后果:一方面权利规范的原则性可用来限制权利,另一方面义务规范的原则性可以用来扩张义务。这两个方面可以分别以我国宪法中的表达自由和纳税义务来说明。就前者而言,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可以被视为宪法第35条表达自由条款的“具体化”,但这部法律虽只有36条,却规定了10个“不得”、1个“不能”、7个“必须”、4项“不予许可”、3项“应当予以制止”以及6条“法律责任”,而且该法把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批准权交给了县级公安机关的行政许可。〔13〕参见王磊:“人权的宪法保护的几个误区”,《法学家》2004年第4期。不难看出,立法的目的在于凸显秩序价值、限制个人权利。由是观之,“具体化”显示的是庄严的宪法权利被“抽象肯定而具体否定”的困境。就后者而言,关于我国宪法规定的纳税义务,由于“纲领说”无视宪法同具体法律和行政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也就不承认存在对征税权的宪法约束。在实践中,纳税义务在具体化中扩张而不是限制了征税权,它表现为“税收法定”这一基本的宪法原则在我国没有得到遵守。一方面,国务院的税收权力从未受到全国人大的严肃审查;另一方面,征税权有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沉的趋势。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出于敛财需要而假借抑制房价之名拟开征房产税、“加名税”的举措所引发的争议,已经凸显了此一议题。〔14〕例如可参见吴半亩:“‘加名税’风波并非偶然”,载《中国青年报》2011年8月29日,第2版。即使存在对此问题的反思,原因也多被归结为“具体化”过程中的技术性缺陷,而不是从宪法的税收法定主义角度来加以检讨。在我国,对征税权的宪法监控明显不足,这同悬置宪法自身的规范性直接相连。
宪法对权利的宣告是原则的和抽象的,但这既非“具体化”策略所要克服的“麻烦”,也非宪法内在品质削弱的表现,而是为日常政治和公共讨论留下审议余地的明智选择。这一安排立基于两个事实:第一,日常政治过程是为回应具体社会情势的变化而设置,它在立法和政策调整方面的功能不能为宪法规范所取代;第二,宪法并不负责分配具体的利益,而只是为日常政治中的利益分配设定规则。如果宪法权利的内涵与外延绝无争议,反而会阻却政府、政党、公众根据情势进行政策选择的机会,这会抑制民主过程的活力。〔15〕对此,张千帆教授也认为,宪法内容的无所不包和政策性条款会使得“代表民主和法治的权力将受到过分限制和削弱”。参见张千帆:“论宪法效力的界定及其对私法的影响”,《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2期。宪法对于前一个事实是防御性的,它防范政治过程参与者的道德风险;对于后一个事实则是构成性的,旨在为政治过程留有决策空间。
“纲领说”还有一种防御性观点:把它们写入宪法并不浪费纸张,它总没什么害处吧!的确,由于宪法乃一国之根本法,“宪法义务”因而确有一种增强语气的效果,它能够凸显言说者的情感。不幸的是,它也贻害非浅。“纲领说”明显与当下制度建设上的“叠床架屋”和“法律上访”存在某种血缘联系。由于忽视宪法自身的规范性,并把宪法置于“纲领性”指导位置之上,“具体化”策略反过来激励了以增加宪法条款来保障权利的冲动,因为只有宪法规范作为“纲领”,才能为“具体化”提供依据。我们习以为常的维权路径,也是在权利保障陷入僵局时一次次地求助于更高级的立法,直至“上访”到宪法。不绝于耳的权利“入宪”主张,即显示了这一呼吁的迫切性。更为重要的是,“无害论”和“纲领说”的结合也激励了扩张义务条款的冲动——既然具体法律总需要以宪法条款作为指针,那么有多少公民义务也就该有多少宪法义务条款。于是义务的宪法化成为一个回应策略:政策性义务可以转化为强制性义务;未曾明确的义务可以创造性地写入宪法。例如,基于对环境问题的担忧,有学者认为宪法中的环保义务主体应该突出个人而不只是国家,“在以后的修宪中宪法应该以明示的方式全面确认所有义务主体(包括个人、企业、社会团体)都负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16〕金明明:“环境义务入宪的路径分析”,《唯实》2009年第12期。关于环境权入宪的主张,还可参见胡建华:“论我国公民环境权的宪法保障”,《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何良龙:《公民环境权的宪法化》,华东政法学院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等。“纲领性”说还试图对一些具体主张的入宪大开方便之门:“非典”之后出现了“紧急状态”入宪,“三鹿奶粉”事件后出现了“食品安全”入宪,“范跑跑事件”后出现了“尊师重道”入宪等诸多诉求,不一而足。
三、宪法“发展趋势”论?
支持公民宪法义务的另一个理由是:它是现代宪法的“发展趋势”。当今世界上大约170多个宪法文件中,大多有义务规范。〔17〕Giovanni Sartori,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An Inquiry into Structure,Incentives,and Outcomes,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7,p.101.这些规范中不但有守法、纳税、服兵役等基本义务,还有受教育、劳动、保护环境等新义务。例如,俄罗斯宪法规定:“每个人都有保护自然环境、爱护自然财富的义务。”作出类似规定的还有塞尔维亚、摩尔多瓦、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国宪法。有学者据此认为:“从内容上看把权利义务结合在一起规定,几乎是现代宪法关于公民权利义务的一种趋势。”〔18〕李步云编:《宪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页574。甚至有学者认为,仅规定公民基本权利,不规定基本义务“是一种没落的法价值观”,〔19〕张庆福:《宪法学基本理论》(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页684。而这种价值观“已经成为人类历史的陈迹”。〔20〕李步云,见前注〔18〕,页736。这种看法暗示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义务也是合理且必要的。
不过,仅就论证方式来看,“趋势论”至多是一种类比推理,而类比推理不是推理。类比推理并非逻辑错误,只是不能视其为一种论证方式。毕竟,别人怎样并不能推导出我们应该怎样。正如成功的商业广告往往利用人们的从众心理一样,这一心理学规律也表现于制度选择,“趋势论”不过是人云亦云和从众心理的学术版本。顺应“趋势”有助于节约思索和搜寻成本,但也阻止积极反思。“趋势论”对统计学方法的依赖也大可存疑,因为一个成功的法治国家的例子会无情地被一个失败的反例抵消,“趋势论”对此则无一例外地保持了沉默。
关键的问题在于,“趋势论”并不符合经验事实,它忽视了许多国家(尤其是法治状况较好的国家)没有宪法义务的事实,更没有去认真检讨其背后的理论。例如,美国宪法没有义务条款,其学术讨论中亦从未出现义务入宪的呼声。难道可以推论说这是否认权利义务“统一论”,或美国公民无须向国家履行义务?而且它缺乏宪法义务是因为没有注意到宪法发展的“趋势”?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公民基本义务问题一直是英美宪法思想史上的空白。〔21〕例如,有学者曾统计1982-2002年间共830篇英美宪法学文献,其中没有一篇是研究公民义务的。参见郑彦鹏编:《宪法与行政法学:问题点与文献源》,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页84以下。大陆法系虽有不少国家的宪法规定有义务条款,但其学术研究的相关讨论亦付之阙如。法国著名宪法学家莱昂·迪骥的《宪法学教程》,对公民宪法义务问题只字未提。即使被许多人视为“国家主义者”的卡尔·施密特,在其著名的《宪法学说》一书中,也未曾论及公民义务,更未把宪法义务作为强化国家主义的手段。现代宪法倒是存在相反的“趋势”——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成文宪法中加入权利条款或颁布单行人权法案,另一方面义务并未与权利结伴而行。二战后于1949年制定的德国基本法,就废除了1919年《魏玛宪法》中的全部公民义务条款。〔22〕1919年《魏玛宪法》第二章首次规定了基本义务,但1949年德国基本法上未延续这一做法,即使纳税义务也未保留,而只从第14条第2项规定的“财产权之社会义务”中间接导出。实际上,《魏玛宪法》是“将一系列完全不同的原则并列在一起”的一部具有“混合性质”的宪法,这本身就是可疑的。参见(德)卡尔·施密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页174。亚洲新兴民主政体——韩国、蒙古和前苏联解体后独立的一些国家,宪法中也没有义务条款。这种对义务宪法化“趋势”的反动,不应被统计学方法中的众数思维所遮蔽。
不仅如此,如果“趋势论”能够为宪法义务提供支持,那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我国对之采取了选择性姿态。在大多数法治国家的宪法以及国际人权文件中,刑事诉讼方面的宪法权利普遍得到确认,例如正当程序、禁止自证其罪、禁止双重危险等,这些同样可以当之无愧地位居“趋势”之列,但我国宪法要么对之视若无物,要么以“与国情不符”而拒之,以致近年公众对沉默权的诉求只能依靠刑诉法修正案孤军奋战。而这些体现正当程序价值的诉讼权利之所以被普遍认为应当拥有宪法地位,原因即在于它们最能显示国家在维护公共秩序时引发的侵权风险。〔23〕张千帆:“宪法人权保障还需要保障什么?——论刑事正当程序入宪的必要性”,《法学家》2004年第4期。如前所述,它们在国家权力面前总是颇显“脆弱”。与对现代权利发展“趋势”的回避态度形成对照的是,我们在设定公民宪法义务上显示出十足的开放性和创造性,不但有服兵役、纳税、守法等方面的法定义务,更有计划生育、环境保护、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厉行节约等政策性义务。这种在权利条款和义务规范上的高度选择性,显示了我们在宪法哲学上的“中国特色”:强调国家权力的主导性,轻视现代宪法普遍强调的控权功能。很难说这是为现代宪法的“发展趋势”所支持的做法。
“趋势论”的另一个版本是所谓“推定义务”说法。有人提出,许多国家的宪法“隐含”了宪法义务,“宪法虽未明文规定公民的义务,但规定了政府有征收租税之权,则公民应有纳税的义务;规定了政府有保卫国家的职责,则公民应有服兵役的义务,虽不言义务而义务已在其中。”有些国家则通过判例的形式确认了公民的宪法义务。〔24〕李步云,见前注〔18〕,页573;还可参见李勇:《论公民的宪法义务》,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页35。由于规定国家机关之权力是宪法的基本内容,此说无异于主张所有国家莫不承认有宪法义务,而公民与政府同属违宪主体之主张,也似有被推向极端之虞。的确,政府征税权必然伴随着公民纳税的责任,但这无须是“宪法的”责任。从立宪的角度来看,征税权的设定旨在控制政府超越民意的财产掠夺,而不是强调公民的纳税责任。否则,由于每项权力都附带着义务,义务就必然面临被任意扩展的风险,宪法的功能将不再是规范政府权力,而是为权力张目提供口实。宪法征税权既是为了防止征税主体滥用该权,也是为了防止其他主体僭越这一权力,它旨在凸显分权原则和制衡价值。否则,公共权力就会由于不受限制而诱发垄断和滥用。因此,“推定义务”不仅是一个貌似巧妙的文字游戏,也在根本上颠覆了宪法哲学的基础,把公民对政府的戒备转向了消极服从。而与此同时,主张“推定义务”的学者并没有把同样的逻辑适用于相反的方向——从公民权利推定出政府的责任。比如,我们能够从财产权推定出对征税权的限制吗?以及我们能够从人身自由条款推定出正当程序原则吗?这并非一个疏忽。这一矛盾的景象,再次揭示了对宪法义务的热衷所隐藏的危险倾向。
以上讨论主要基于对宪法的控权功能的强调展开,这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个重要主题。近代国家在治理范围和人口上均已超出希腊城邦式小国寡民的状态,故普遍以代议制替代直接民主,这凸显了人民自身所订立之宪法同人民代表所制定之普通法律间的紧张,而正是这一格局,使宪法对日常权力运作的控制成为必要。就此而言,同属社会契约理论谱系但尤为强调主权“公意”和个人臣服“义务”的卢梭政治学说,会对本文的主题构成挑战吗?卢梭基于对(法国)绝对主义王权的反思,强调个人意志自由以形成“公意”,这已经具备了立宪主义的价值基因。与众不同的是,他视代议制为公民精神的腐化,而党争不啻对公意的威胁。他因而强调“主权者”需要对他们的代表(政府)保持戒备,其“人民:政府:臣民”的连比关系阐明了这一点,即“越是政府应该有力量来约束人民,则主权者在这方面也就越应该有力量来约束政府”。〔25〕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页75。相关讨论可参见陈端洪:“人民主权的观念结构——重读卢梭《社会契约论》”,《中外法学》2007年第3期。这同样可以为宪法权利提供论证:一方面,个人自由乃是培育卢梭式有教养公民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这些赋予个人主动精神的自由正可作为防范代议制风险的手段,它们为个人直接参与“公意”提供了制度性机会。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也主张个人的臣服义务,但从思想的逻辑上看,他强调的是道德意义上的“政治义务”而非规范意义上的“宪法义务”。在这一问题上,处于美国宪法诞生前夜的卢梭,可能尚未察觉一个现实的立宪政体中个人权利的价值以及宪法的“超规则”特征。对此,联邦党人的理解或可提供一个补充。
汉密尔顿更为清晰地界定了“人民”与“人民代表”、“宪法”与“普通法律”间的内在张力:“代议机关的立法如违反委任其行使代议权的根本法自当归于无效乃十分明确的一条原则。违宪的立法自然不能使之生效。如否认此理,则无异于说:代表的地位反高于所代表的主体,仆役反高于主人,人民的代表反高于人民本身。如是,则行使授予的权利的人不仅可以越出其被授予的权力,而且可以违反授权时明确规定禁止的事。”〔26〕杰伊等,见前注〔7〕,页392。这也是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关切,他预见到以“身份平等”为特征的民主制度将势不可挡,因此倡导以个人自由来对抗“多数的暴政”,以“洁化民主的风尚”、“规制民主的行动”,并“以对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27〕(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页8。这与卢梭对充满风尚与德性的古代城邦的钟情和对个体直接参政的共和主义思想有着共同的追求。
四、“国家认同”与“集体价值”?
在诸多支持宪法义务的主张里,尚有一种更具思想史意义的理由,即以公民义务强化“国家认同”和“集体价值”。与统一论、纲领说、趋势论不同,它首先是一种政治理论,并非特别针对宪法义务问题提出。它与本文的关联在于,依照这一看法,义务是高尚的付出,它强化集体价值;权利是自私的索取,它削弱集体价值。中国人长久以来的主要身份系家族成员身份,国民观念淡漠,无助于完成建设现代国家的紧迫任务,而宪法义务可满足此一需要。〔28〕民国时期制定的多部宪法文件,如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1936年《训政时期约法》、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中,皆有人民义务条款,或多或少与此种主张有关。可参见卞修全:《近代中国宪法文本的历史解读》,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页171以下。这方面的理由或许可以分解为两个问题来讨论:第一,宪法义务与强化国家认同或者集体价值的关系是什么?第二,即使国家认同这一价值诉求不能为宪法义务提供一般性辩护,它是否因为适应了特殊历史阶段的需要而具有正当性?为避免讨论大而无当,下面将努力集中于与论题最为密切的方面。
首先,对国家认同和集体价值的诉求,恰恰应该求助于个人权利而非宪法义务,这一问题的关键,是理解个人权利的起源和政治功能。民主观念源远流长,个人权利却是近代产物。“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29〕《道德经》。意识形态是对社会紧迫需要的回应,个人权利亦然。近代权利观念乃是民族国家兴起、传统共同体衰落在政治哲学上的产物,强大的国家权力与个人的直接对峙,把个人抛入孤立无助的境地。为使个人与国家力量平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现代价值才应运而生。即使是施密特也承认:“真正的基本权利本质上是享有自由的个人的权利,而且是与国家相对峙的权利……如果一项权利完全取决于专制君主的意愿,或者听任简单的或特定的议会多数的决定,想授予就授予,想收回就收回,它就不能被实实在在地称为基本权利……这是个体的权利,孤立的个人的权利。”〔30〕施密特,见前注〔22〕,页175-176,着重号为原文所加。因此,宪法强调保护个人权利,并非假定个人利益高于社会和他人,更不是鼓励自私自利的价值观念,而实因个人面对国家时的孤立寡援尤需特殊关照,这同以特别立法保护妇女、儿童、老人等的权益完全相同。与此同时,义务之所以没有成为近代宪法思想的主题,根本上是因为它并非回应现代政治之所需——公共权力必然强大,无须宪法义务“锦上添花”!
“国家认同”说之动机无可厚非,它回应了我国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要求,但对于受到国家主义驱使的思想家们来说,对个人权利的误解似乎也成了正当的事情。例如,在孙中山看来,本意为防范多数的“民权”概念,被理解为“人民整体的政治权力”,〔31〕潘慧祥:“晚年孙中山”,《二十一世纪》2003年3月号。孙中山在《民权主义》第一讲中说:“什么叫做民权主义呢?现在要把民权来定一个解释,便先要知道什么是民。大凡有团体有组织的众人,就叫做民。什么是权呢?权就是力量,就是威势,那些力量大到同国家一样,就叫做权。力量最大的那些国家,中国话说列强,外国话,便说列权。又叫机器的力量,中国话,说是马力,外国话,说是马权,所以权和力实在是相同。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群伦的力量,就叫做权。把民同权合拢起来说,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而以对抗国家为己任的“个人自由”,却成了令人扼腕的“一盘散沙”,非强化国民义务不能克服。“民权”与“自由”在孙中山那里是分裂的:国人缺乏的是民权而不是自由,而且自由已经太多。“自由”太多是因为公民并不了解自己的权利,而不了解自己的权利也就不会知道义务何在。而且,他所认为的自由也并非宪法强调的政治自由。〔32〕同上注。梁启超对西方的理解亦然,他深为“中国人之缺点”所刺激:“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无高尚之目的”。〔33〕梁启超:“新大陆游记”(1904年2月),载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页432-435。他的自由观是相对于“奴隶”而言的,而且“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34〕同上注,页227。由于强调“个人自由的价值在于增进民族国家之富强”,他往往“将任何有关个人自由的法规都看作是对集体自由的潜在伤害”;〔35〕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页143。梁氏著名的“新民”主张,要义也在于引进西方(主要是德国)国家主义以铲除国人的“利已主义”,因此“新民”的主旨不是张扬个人权利,而是强调个人之于国家的义务和责任,这一认识与近代立宪主义规范国家权力、保障个人权利的主旨明显相悖。
孙中山和梁启超的上述思想,是否可以因为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而得到辩护,从而使他们对集体价值的诉求能够被同情地理解为民族国家成长过程中的“阶段性”要求或权宜之计?换言之,近代中国之“弱社会”与“弱国家”并存的现实,是否表明“国家——个人”的二元对立这一立宪主义的基本假定暂可不论?我们的理解是,这是一个规范问题,而非经验问题。国家无论强弱,皆存在整体目标与个人选择间的紧张,所以这种二元对立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集体行动困境”命题。社群与个人的紧张是所有共同体的宿命,小到家族、部落,大到民族、国家,皆无例外。没有不同的问题,只有对问题的不同解决方式。部落式共同体的秩序依赖的是传统权威和习俗惯例,而现代国家则依靠非人格化的规则之治。或许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一个励精图治的“弱国家”而言,对强大的渴望反而会放大其与个人的紧张,激励其通过对个人施以强制来满足集体目标,这一境况使得对个人的严格宪法保护成为必要而不是相反。从这一意义上说,对宪法义务的强调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之举。历史的经验也会对“阶段性”说法给予重重一击,因为以控制公共权力、保护个人权利为要旨的立宪主义,恰恰是与近代民族国家由弱及强的生长过程相伴而行的。另外,如前文所述,我们对“宪法义务”的怀疑并不同时指向普通法律义务,也不否认个体对他人和社会应尽的法律责任,我们反思的是义务的“宪法化”立场对立宪主义本意的误解及其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说,对宪法义务的“阶段性”辩护方式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无关宏旨的。
关键的问题仍然是理解“权利”。宪法权利是“个人”的,但它并非仅属私有之物,它也具有公共属性。在一个传统社会纽带分崩离析的“去魅”时代,“权利”已经成为共同体团结的粘合剂。一如史蒂芬·霍姆斯所说的,正是个人权利提供了“社会合作的先决条件”,它们使各种社会联系成为可能:言论自由确保公民之间的脆弱交流渠道保持通畅,使人们能够相互合作和彼此学习,结社自由明显地保护群体活动,而宗教宽容则肯定信仰的多样性,它防止宗教分歧政治化。〔36〕参见(美)史蒂芬·霍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曦中、陈兴玛、彭俊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318。个人权利也能确保公共决策的品质:“新闻和出版自由……是集体认识并补救自身缺陷的一种途径。当政策得以公布,公众批评受到鼓励,政府就能避免自相矛盾的立法,在局面失控前察觉问题并改正错误。”〔37〕同上注,页293。洛克、孟德斯鸠等自由主义思想家,无意以个人权利肢解社会,他们想要革除的是专制对人性的践踏,因为那是令人厌恶和不道德的。瓦解社会联系和导致社会“原子化”的,不是个人自由而是独裁政府。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记载的乌兹别克的后宫,就是“揭示非自愿性奴役在心理上的残忍性的生动例子”。〔38〕同上注,页272。宪法不是价值中立的,它并非消极地适应所有成例与习俗,它的革命性特征正是宪政、法治、人权这些非人格化机制的功能所在。倘无宪法划定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边界,则必导致权力触角任意侵入私人领域,以“公共利益”和“国家建构”之名行专制之实。因此,对共同体价值和公民责任的关切,既无须诉诸于向个人权利叫板,也不必声嘶力竭地呼吁宪法义务。
以明确的宪法义务条款矫正个人权利,与宪法的价值不相一致。从原则上说,宪法权利是“绝对的基本权利”,法律对它的限制只能是例外的、可预见和可审查的。〔39〕施密特,见前注〔22〕,页177。而宪法义务会将对权利的限制从例外变为一般,给予政府过分的动机和手段去限制令其不悦的个人权利。这一境况并非由宪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决定,而是因为其与政府的关系。认为宪法义务能够强化集体价值的观点,源于对权利的误解甚至贬低,它把权利当成“自私自利”的代名词,将其化约为“利益”甚至“物质利益”,这完全忽视了权利作为制度的功能。一般性的公民身份和权利观念意在通过有效的政治参与处置公共议题,它并不妨碍国民于私人生活中践行那些促进社群团结的价值。立宪政治的革命性特征指向公共领域,而不是私人生活。一个于公共生活中行使选举权与言论自由的公民,无论是参与政府抑或挑战政府,同时可以在私人生活中秉持夫妇之道、父子之伦,也并不妨碍其对家族、团体权威之服从。只有公共生活(国家)与个人生活(市民社会)之间的伦理和政治边界大体两分——前者体现现代立宪民主制的要求而后者表现社会生活对于秩序之自然要求,才能真正使本国传统在经受自由选择之后有裨益于共同体的团结。日本、韩国等亚洲立宪政体的实践,已经提供了正面的经验,而哈贝马斯倡导的以“宪法爱国主义”替代“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也意在以公民权利和宪政民主作为政治整合和国家认同的基础。〔40〕Cf.Jurgen Habermas,The New Conservatism:Cultural Criticism and the Historians'Debate,ed.and trans.Shierry Weber Nicholsen,MIT Press,1989,pp.255ff.
五、权利视角
行文至此,需特别说明的是,以上讨论主要系从宪法义务作为一种公民负担意义上展开的,这也正是本文所怀疑的统一论、纲领说、趋势论以及国家认同说所强调的含义。但是,本文无意把清除宪法义务条款作为唯一的选择,尤其是当我们把维护宪法规范的稳定性作为一个重要的、不乏权宜性的因素来加以考虑的时候。对于我国宪法中的义务条款,既然不能从公民负担意义上加以理解,则应作何选择?我们愿意接受某种含义的宪法义务,但这需要严格限制。正如有些国家的宪法理论昭示的那样,义务条款存在一种“权利理解”的可能,下文将讨论并拓展这一理解路径。
“宪法义务”一词并不仅仅意味着对公民课以负担。义务论者忽视的一个关键事实是:一些国家宪法中的义务条款恰恰是为保障权利而设的。这将再次显示“趋势论”对义务性规范之宪法含义的深刻误解,亦即一些宪法条款虽名为“义务”,其目的却不是对个人课以负担而是相反:它们非但不是反映一种与控权传统相反的趋势,而是为了强化这一传统。有学者已经指出此点在宪法条文和理论上的根据。〔41〕沈寿文:“中国宪法文本规定公民(人民)义务的原因探析”,《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以兵役义务为例,德国宪法第12条第2款规定,“可以要求由于宗教道德上的原因而拒绝使用武器为战争服役的人提供替代的服役”;俄罗斯宪法第59条第3款规定,“俄罗斯联邦公民在服兵役违背其信念和宗教信仰以及在联邦法律规定的其它情况下,有用服适当的民役代替服兵役的权利”;葡萄牙宪法第276条第4款规定,“出于道德或宗教原因拒服兵役者应服民役,其服役期限和强度与武装兵役同。”〔42〕参见李勇:“宪法义务规范研究”,《兰州商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再以纳税义务为例,我国台湾地区的“大法官”曾多次指出,宪法规定人民有“依法纳税之义务”,系指人民仅依法律之明定义务纳税,“大法官释字”217号解释即称:“举凡应以法律明定之租税项目,自不得以命令作不同之规定,否则即属违法租税法定主义。”〔43〕法治斌、董保城:《中华民国宪法》(修订三版),台北空中大学2001年版,页199。作者认为:“人民之纳税义务是国家主要的财源,因为牵涉人民之财产权,须以法律定之,即为租税法定主义。立法机关亦可授权行政机关行使规范租税之权利,但是必须符合授权命令明确性原则。”参见该书第198页。日本学者青柳幸一指出:“在历史上,纳税义务与税收法律主义原则的成立,构成一体的两面。”〔44〕(日)阿部照哉等:《宪法》(下),周宗宪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页376。日本宪法规定,国民对于自由与权利负有“应不断努力以保持之的义务”、“不得滥用的义务”以及“为公共福祉而利用的义务”。〔45〕日本国宪法第12条规定,“本宪法保障国民之自由与权利,应由国民不断努力以保持之。国民不得滥用之,负有常为公共福祉而利用之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应不断努力以保持之的义务”系公民抵抗权的根据。〔46〕阿部照哉等,见前注〔44〕,页368。而按照“统一论”者的观点,我国宪法中的“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只是强调公民消极服从而已,若借鉴日本宪法的理解方式,则应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意指公民可以以积极的行为制止政府的违宪、违法行为,而此种维护宪法和法律秩序的义务,又实则表现为公民的表达自由、选举权等宪法权利的行使。这样的话,公民权利、公民责任、国家权力就不再仅仅是对峙和冲突,而是可以相互促进。
权利视角下的宪法义务,凸显了一种不同于“统一论”的政治哲学:个人主张其宪法权利不仅仅是在保护私利,也是为国家尽到作为“公民”的责任。如前所述,宪法权利的重要性和脆弱特征即主要是基于其对民主社会的正常运转而言的。“公民”这一概念的共和主义精神亦寓于此。而“统一论”似乎只是暗示“个人权利”是自私和可疑的,它对抗公共利益;而义务意味着服从,服从才是美德。“统一论”将权利视作私利、将义务视作负担的看法,在纳税义务问题上压制了“税收法定”原则的空间。在当前的我国,一方面“统一论”大行其道,另一方面税收法定原则不兴,两者之并行既反映了宪法理论上的误区,其存在看来也并非偶然。
从原旨主义的视角来看,我国宪法的公民义务条款并不具有进行权利理解的空间,它是为给公民课以负担而存在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是“一种荒谬的思路”,因为宪法义务本可为防止在普通立法中对公民课以过重负担而设定,它蕴含的是控制公权力的思想。“假使宪法文本中有必要列举公民的义务,那么这种思路应该是为了避免政府(国家)没完没了、任意科处公民的义务而设置的。”〔47〕沈寿文,见前注〔41〕。基于权利视角而做出的理解可能是建设性的,循着这个视角,我国宪法义务条款中的“依法”字眼就变得非常重要,例如对“依法纳税”义务的理解,其重心可在“依法”而不在“纳税”,亦即“不依法律不纳税”、“法律无明文规定不得征税”。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只有从保障人权的意义上,才能够理解宪法纳税义务规范,否则国家大可不必在宪法中写进‘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以设置一个‘依照法律’的前置条件以自我设限,因为只有保持随时剥夺臣民财产的权力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专制政府的财政嗜好。”〔48〕朱孔武:“基本义务的宪法学议题”,《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此种理解不是扩张而是约束政府征税权,它意指公民有权拒绝缴纳法外之税,这同基于对政府侵害财产权的风险而设定的税收法定原则是一致的。具体而言,有关纳税主体、税种、税率、纳税方法、纳税期间、免税范围等事项,必须由最高立法机关自行规定,而行政部门只能根据税法制定一般性的实施细则,否则即有违宪之嫌,公民可以诉诸政治过程(如选举压力)或司法程序寻求救济。在这里,对征税权的约束虽并非直接由宪法条款规定,但税收法定主义体现的仍然是对政府敛财冲动的宪法性限制。
因此,逆原旨主义解释方式而动,基于现代宪法的基本价值,对我国宪法诸多义务条款给予一种权利理解是可行的。除上述守法、纳税义务之外,对于“依法服兵役”的义务,可以理解为“公民有权拒绝非法兵役”;甚至对于“计划生育”这一特殊而罕见的宪法义务,也可以理解为“公民只能依照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而非行政部门的政策履行这一义务”等。当然,此种理解注定在理论上不会一帆风顺,因为恰恰是“统一论”、“纲领说”以及“趋势论”设置了障碍。因此,必须从理论上重新理解宪法规范的属性,其核心是将宪法理解为一部高于且先于政府、为日常立法和行政活动设定戒律的“超规则”文件,其不可动摇的功能是防止政府活动基于公共利益而显示的侵权冲动,而不是将其视为缺乏规范性的“立法大纲”或“立法索引”。必须承认,我国宪法中的义务条款从立法初衷来说是对抗和排斥权利诉求的,“统一论”本身就说明,权利是权利,而义务是义务,宪法义务就是对宪法权利的限制,“权利理解”与“负担理解”将狭路相逢。但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宪法义务之保留并非全然不可,它与普通法律义务的区别,即在于强调现有宪法义务条款的条件性,只有赋予宪法义务一种权利视角,义务条款才可能具备同基本权利相同的控权功能,也不枉其宪法地位。
六、结语
当误解成为通说,常识就尤为可贵,质疑宪法义务并不是在无事生非,也并非如堂·吉诃德般与风车开战。由于政府对权利和义务的态度注定截然相反——落实义务时从不缺斤少两而保障权利时总是瞻前顾后,将权利写入宪法才天经地义,而将义务写入宪法却似是而非,中外于此概莫能外。这一普遍存在的矛盾景象,恰恰反映了问题之所在。支持宪法义务的诸种理论既源于对宪法属性的根本误解,也正日复一日地强化着这一误解。将负担性义务与宪法权利并举,不但对倡导公民责任于事无补,反而会诱发宪法的“精神分裂”,因为它们背后的哲学针锋相对,水火难容。对负担性宪法义务的主张貌似为权利划定合理边界、彰显集体价值,实则在销蚀和颠覆宪法权利。宪法是一部“高级法”,它不可动摇的特征是规范性和“超规则”特征;宪法也是一部“特别法”,它之所以关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就是因为这一关系适用特殊的标准,它对政府严加管教,对公民袒护有加。“统一论”、“纲领说”、“趋势论”和“国家认同说”正是忽略了这一点,它们将宪法视为“看上去很美”的立法目录的立场,致命地消解了宪法与政府之间必要的和建设性的紧张,使得宪法这一后封建时代的政治构架在实践中显现出再封建化的危险。我们的社会正变得越来越民主,这一事实将对宪法的“超规则”属性表现出更多的渴求。当政治生活越来越不太可能为单一的权力源所掌控时,社会将更加直接地求助于宪法规范,以期在政府权威与个人自由之间获得平衡。这既是近代宪政发展的历史经验,也预示着理解未来中国宪政发展的方式。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能进一步对分权制衡、司法独立、违宪审查等现代宪法原则以及保障基本权利的合适方式做出恰当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