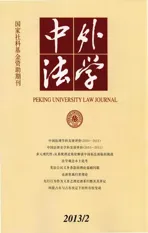先行行为作为义务之理论谱系归整及其界定
2013-01-21王莹
王 莹
我国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理论的通说在传统上采取的是形式的义务来源说,认为作为义务来源于法律规定,合同约定,法律行为、职务或业务上的要求,以及先行行为,即所谓的形式四分说。〔1〕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版,页67-69。在上述作为义务之中,因先行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基于先行行为保证人地位的不纯正不作为犯刑事责任一直以来都具有较大的争议性,尤其是传统的形式四分说仅从形式的角度对先行行为进行认定,导致先行行为范围界定模糊,对先行行为的认定有过于形式化与扩大化的倾向,导致先行行为类型的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刑事责任泛滥。我国学界与司法实践围绕先行行为的界定素来存在较大的争议,例如先行行为是否必须为违法行为,合法行为是否可以构成先行行为?犯罪行为是否可以构成先行行为?以及先行行为是否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欲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首先明确先行行为本身的性质,以及它与其他形式作为义务之间的区别。
与法律、合同以及职务或业务要求等其他作为义务来源相比,先行行为具有特殊的性质,必须在探明这种特殊性质的基础上,才能为上述问题提供满意的解答。本文拟在对先行行为教义学演进与理论谱系进行整理的基础上,揭示先行行为的特殊性质,继而尝试对先行行为进行合理的界定,以妥善解决先行行为类型的不纯正不作为犯刑事责任问题。
一、先行行为保证人地位的教义学发展与理论谱系
我国传统的作为义务形式四分说是从法律形式的角度对作为义务来源进行论证,在德国刑法理论上被称为“形式的法律义务理论”。与“形式的法律义务理论”相对的是实质的作为义务说,实质说尝试跳出以作为义务形式上的来源论证结果防止义务的格局,寻找法律要求不纯正不作为犯对于损害结果应承担损害防止义务的实质性的根据,故称之为“实质的法律义务说”。晚近德国学者从实质角度对作为义务进行论证的尝试颇多,此处仅略举一二。例如“信赖说”〔2〕参见Wolff,Kausalitaet von Tun und Unterlassen,1965Heidelberg,S.36ff。认为作为义务来源于社会生活中对他人实施一定行为的信赖。后来又有学者提出“介入说”,〔3〕参见Seelman,Opferinteressen und Handlungsverantwortung in der Garantenpflichtdogmatik,GA 1989,241(251ff)。认为通过创设风险或者使他人丧失损害防止的意愿而介入他人权利领域者,负有损害防止的作为义务。而实质说中最有影响的当属Schuenemann提出的“结果原因的支配说”,〔4〕参见Schuenemann,Grund und Grenzen der uechten Unterlassungsdelikte,zugleich ein Beitrag zur strafrechtlichen Methodenlehre,Goettingen 1971,S.235ff.该观点近年来在我国学者中获得广泛的赞同,例如黎宏:《刑法总论问题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148以下;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页155。主张唯有对结果发生的进程具有现实的支配力者,才负担防止该结果发生的义务。除上述两种学说以外,在德国学界还盛行一种功能说,〔5〕参见Kaufmann,Die Dogmatik der Unterlassungsdelikte,Goettingen 1959,S.282ff;Kindhaeuser,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4.Aufl.,Baden-Baden 2009,§36Rdn.52。该说跳脱了形式说过于形式主义的框架,也反对以一种统一的学说论证所有不纯正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而是主张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将作为义务划分为两大类别,即来源于保护保证人地位的作为义务与监管保证人地位的作为义务。
在上述作为义务理论之中,先行行为到底具有何种地位,其概念界定又随着上述理论的发展经历过何种变化?唯有在梳理先行行为教义学发展的基础上,明晰其在不同不作为犯理论框架下的地位,揭示这种演变背后的动因,才能对先行行为进行合理的界定。下文将从形式法律义务理论开始,从不纯正不作为犯理论发展的粗略梳理之中,勾勒先行行为教义学演进的大致脉络,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揭示上述问题的答案。
(一)形式的法律义务理论
“形式的法律义务理论”由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Feuerbach)于19世纪初创立。费尔巴哈以康德的法律理论为基础,试图从自由国家理论角度对不作为的可罚性进行论证: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公民原则上只具有不实施侵害他人法益的义务,因而一般来说只有积极引起损害的行为才会被处罚。所以原则上来说,不实施救助或补救行为并非当然可罚,只有当存在实施该行为的特殊义务时(如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6〕Feuerbach,Lehrbuch des gemeinen in Deutschland gueltigen peinlichen Rechts,2.Aufl.,1803,§24,转引自Schuenemann,Zur Garantenstellung beim unechten Unterlassungsdelikt:Dogmenhistorische,rechtsvergleichende und sachlogische Auswegweiser aus einem Chaos,in:Grundlagen des Straf- und Strafverfahrensrechts,FS-Amelung zum 70.Geburtstag,(Hrsg.)Boese u.Sternberg-Lieben,Berlin 2009,S.305u.309。费尔巴哈对不作为来源与根据的自由国家理论式的论证不仅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获得了判例的青睐。德意志帝国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将该观点发展成为所谓的“形式的法律义务理论”(formelle Rechtspflichttheorie),认为如果行为人具有来源于法律或合同的行为义务,那么其不作为等同于作为,义务人对其不作为所造成的损害也应当如同对于作为那样承担刑事责任。
19世纪中后期,人们开始尝试从因果一元论角度对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进行自然主义的论证。这种理论发展动向植根于当时几乎在所有科学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的自然主义哲学(Naturalismus)。早先在不作为犯因果关系方面采取的准因果关系论主张,如果行为人实施相应的作为可以避免损害后果发生,那么行为人不作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就存在一种类似作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效果联系,这种效果联系并非现实的因果联系,而是一种假设的因果联系,即准因果联系。而受当时盛行的自然主义哲学影响,学者试图在因果概念中寻找一切刑法归责的根据,不再满足于准因果关系理论,而是认为在不作为犯中也存在真正的因果联系,只不过这个因果联系不是存在于不作为之中,而是——向前追溯——存在于行为人在先所实施的行为之中。〔7〕参见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II,Muenchen 2003,§32I,Rdn.3;Schuenemann(Fn.6),S.310。如果行为人能够阻止在先实施的行为所带来的损害后果而不阻止,致使后果发生,那么该后果就是行为人在先行为自然发展的结果,在先行为即是导致该损害后果的原因。此即“在先危险行为”(Ingerenz)概念的发端。〔8〕“Ingerenz”的拉丁语原义为“干涉、介入”,被用在不作为犯理论是指gefaehrdendes Vorverhalten,即“危险前行为”,故译为“危险前行为”更为恰当,鉴于语言使用上的习惯性考虑,下文仍沿用通常的“先行行为”概念。在先危险行为理论诞生之后,与费尔巴哈的形式法律义务理论成为当时德国不作为犯教义学的两大理论流派,在其支持者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战。而判例对两种理论也没有厚此薄彼,而是将二者结合起来,将法律和合同上的义务与来自于在先危险行为的法律义务并列视为作为义务来源的根据。〔9〕参见德意志帝国法院的判决RGSt 18,96,98;Schuenemann(Fn.6),S.310。
二战以前,先行行为适用于那些不作为导致了刑法所禁止的后果,但是人们既无法从法律规定之中,也无法从合同之中推导出来作为义务的情形,充当着一种“堵漏”(lueckenbuesser)的角色。〔10〕参见Stratenwerth,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I,Die Straftat,4.Aufl.,Köln 2000,§13,Rdn.26。后来在法律、合同与先行行为基础之上,判例又承认了虽然没有法律上基于婚姻、血缘关系、但事实上处于生活共同体的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作为义务,〔11〕参见德意志帝国法院的判决RGSt 69,321,323。形成作为义务的四来源说。作为义务四来源说虽然不再拘泥于最初的法律与合同的形式作为义务根据,但是仍然没有尝试从实质的角度寻求义务根据的论证,故仍属于形式法律义务理论的范畴。
形式法律义务理论实际上所解决的不是作为义务的论证问题,而仅仅是对作为义务的来源进行描述。从作为义务来源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发现,先行行为与其他的形式法律义务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法律和合同上的义务是刑法外的形式上的法律义务,而先行行为的法律义务则是刑法上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这就提示我们,在先行行为的界定方面,必须以刑法的目光予以特别的检视。
(二)功能二分理论
与判例所采取的形式法律义务立场不同,Armin Kaufmann于上世纪50年代末提出功能二分理论,逐渐在学界取得通说地位。Armin Kaufmann认为,在林林总总的作为义务之中,存在内容与功能上的区别,根据这种区别可以将作为义务的来源分为以下两大类别:〔12〕参见Kaufmann(Fn.5),S.282ff。来源于保护保证人地位的作为义务(Obhutsgarantenstellung)与监管保证人地位的作为义务(Ueberwachungsgarantenstellung)。前者是指行为人对于被保护者所承担的实施一定作为而保护其法益不受侵害的义务,这种作为义务是一种全面的保护义务,有义务防止一切可能损害被保护者法益的危险,如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以及夫妻之间的作为义务、来自于生活共同体或危险共同体的义务、自愿承担的保护义务(即事实上自愿接管或承担他人的保护义务,如行为人本无保护保证人义务,但因自愿承担对婴儿的照看、对病人的护理等而获得的义务);后者是指行为人对于特定的危险源具有监管该危险源不对他人造成侵害的义务,这种保证人仅对其所监管的危险源所造成的损害负有防止义务,其作为义务是一种特殊的作为义务,紧紧围绕危险源对法益造成的危险指向,例如危险设备运营人对其运营的危险设备、饲主对其饲养的动物负有监管而防止其伤害第三人的义务,对属于自己监管职责范围内的被监管人对第三人造成损害的阻止义务,以及来自于先行行为的义务,即防止其在先行为的危险致人损害的义务。〔13〕Roxin(Fn.7),§32,Rdn.6;Wessels/Beulke,Strafrecht Allgeminer Teil,40.Aufl.,Heidelberg u.a.2010,§16,Rdn.716。在功能二分论中,因先行行为引发的作为义务属于监管保证人地位,而来自于法律、合同的义务则多属于保护保证人地位范畴。当然,在监管保证人地位之中,并非所有作为义务的根据都是先行行为,与其并列的还有危险设备运营人、饲主等危险源监管人的危险源监控义务。
这种功能二分法不迷恋于对作为义务来源进行一体化的实质描述与论证,而是根据作为义务功能与内容上的区别,将作为义务进行类型上的基本区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不同的作为义务亚类型,对作为义务的整理与归类可谓逻辑清晰、结构明确。这种功能主义的路径综合了形式说与实质说的优点,它避免了对作为义务进行统一实质论证所带来的过于抽象与不周延的风险,也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形式说的言之无物。更为关键的是,功能说在实践适用中具有较大的优势:由于各作为义务具有根据各自不同的特性形成的判断规则,而且相互之间层次与边界清晰,根据这种类型化的层级结构可以对保证人地位进行更加有效率与针对性的检验。因而,功能二分法经受住了种种实质说的风起云涌的挑战,至今仍屹立于通说地位。甚至采实质说的学者,也无法完全脱离功能二分说进行理论建构。
因此,对先行行为范围进行正确的界定,首先必须明确其在功能二分说之中的分类。因先行行为产生的保证人地位在早期判例与学说中并未与其他监管保证人地位分立,往往与后来的保有危险物或运营危险设备产生的保证人地位混同起来被探讨。随着德国二战后交通事故犯罪的大大增加,交通肇事者对事故受害者不实施救助的情形时有发生,判例开始改变以往的判决路线,对不实施救助的行为人不再按照第323c条见危不救罪处罚,而是将交通过失行为视为先行行为,要求肇事者承担救助的责任,否则即有可能成立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14〕Roxin(Fn.7),§32,Rdn.145,m.w.N。学者开始注意到这种先行行为犯罪与传统的先行行为犯罪,尤其是保有危险物或运营危险设备产生的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之间的区别。在这种转变了的先行行为观念下,在保有危险物或运营危险设备产生的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中,人们很难再对其中的“先行行为”进行合理地论证。例如Schuenemann以房屋所有人对来自于房屋的危险,即房屋上的瓦片掉落而砸伤路人为例,指出如果房屋所有人在这个案例中因先行行为承担不作为的责任,那么这里的先行行为就必须追溯到房屋的建造行为或房屋的交易行为(在房屋所有权人发生变更的情况下)。〔15〕Schuenemamm(Fn.4),S.284。如果如此追溯下去,那么先行行为的范围就会被无尽地扩大,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因此,保有危险物或运营危险设备产生的作为义务地位逐渐被从先行行为之中分离出去,学说开始将保有危险物或运营危险设备产生的作为义务地位作为交往安全义务(Verkehrspflicht)或交往安全保障义务(Verkehrssicherungspflicht)的情形来对待。交往安全义务是来自于侵权法上的作为义务,即如果物根据其特征可能给他人带来危险,物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就具有危险防止的作为义务,这种危险主要来自于危险物本身或者危险的技术操作过程。〔16〕Schuenemamm(Fn.6),S.281.这些义务根据具体危险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内容,例如房屋所有人对房屋的修缮义务,建筑工地管理人对建筑工地设立警示灯、进行隔离的义务,机动车所有人、运营人对车辆是否符合安全驾驶要求的检查义务以及车辆运行过程中发生危险时的刹车义务、动物的饲主对其所饲养的动物负有防止其袭击他人造成损害的义务等。〔17〕参见Roxin(Fn.7),§32,Rdn.111ff。
因此,在功能二分说的框架下,交往安全义务从先行行为义务之中分离,使得先行行为的范围大大限缩,先行行为作为义务不再包括那些来自于侵权法的作为义务,不再包括民法上的所有与占有等适法的行为,而是集中于那些应当在刑法的意义上被检验的“真正的”先行行为之上。
而我国的先行行为理论中,存在将先行行为保证人地位与保护保证人地位或危险设备运营人等其监管保证人地位相混淆的倾向,将后者也视为先行行为之一种(详见下文二(一)、(二)),实际上已经偷换了“先行行为”的概念。从这种错误的先行行为概念出发,自然难以对真正的“先行行为”范围进行合理的界定。
(三)实质法律义务理论与否定先行行为保证人地位的观点
上世纪70年代Schuenemann提出“结果原因支配理论”,尝试从实质角度对作为义务进行论证,认为作为与不作为的归责基础都是行为人与结果之间存在某种特定的关系,即行为人对结果发生的原因或根据具有现实的支配力。因而,对结果发生的原因进程具有现实支配力,是作为与不作为等价性的物本逻辑根据。〔18〕参见Schuenemann(Fn.4),S.235ff。基于该观点,Schuenemann以在先行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情形下不存在对结果原因的支配为由,对先行行为的作为义务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源于先行行为的因果进程对于不作为犯行为人来说是“过去的”因果进程,在实施先行行为之后,该因果进程已经离开了行为人的支配领域,行为人对其不再具有现实的控制力,这种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刑事责任不啻于是一种纯粹的结果责任(quivis ex populo)。〔19〕参见Schuenemann(Fn.6),S.316。但是,这种彻底否定先行行为保证人地位的观点并未被广泛接受。Roxin认为,承认先行行为的保证人地位与结果原因支配理论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关键在于对“支配”的理解。在Roxin看来,这种支配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实然的现实支配,而应该是一种规范的支配概念——从规范的角度来说,先行行为所引起的危险的继续发展仍然属于先行行为人支配领域之内。如果承认人们应当避免给他人法益侵害带来危险这一原则,也应当承认引起该风险者具有避免该风险继续发展成为构成要件结果的义务。否则就会产生一个价值评判的矛盾,即一方面要求法规范对象避免给他人法益侵害带来危险,另一方面却允许该危险继续发展造成实际的法益侵害。〔20〕参见Roxin(Fn.7),§32,Rdn.150f。
Roxin试图以规范的“支配”概念论证先行行为人对结果的支配,以反对否定先行行为存在必要性的观点。国内学者张明楷教授也(主要)从严密法益保护的角度论证先行行为存在的必要性。〔21〕参见张明楷:“不作为犯中的在先行为”,《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另可参见此处关于先行行为存在之必要性的争论。笔者以为,将论证的靶心集中于先行行为本身,从先行行为的特殊构造角度出发,以证明从先行行为中产生作为义务的合理性,可能更加具有教义学上的说服力。在笔者看来,先行行为乃是一种介于作为与不作为之间的“特殊行为”。当行为人创设了法益侵害的风险,该风险又在客观上继续发展成为构成要件结果,如果不存在第三人负责的行为或被害人在完全的风险意识下的自我危险行为等例外情形,该结果在客观上完全可以归责给行为人,但是该行为却不能被直接处罚,原因在于先行行为人缺乏构成要件的故意,因而不能对其进行主观上的归责。而如果在先行行为发生之后,行为人认识到其行为可能继续发展成构成要件结果,并且在能够阻止该结果发生的情况下不阻止,则就具有了针对构成要件结果的不作为的故意,此时可以对先行行为人的不作为进行主观上的归责。而该不作为在规范的意义上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因而对于该不作为也可以进行客观归责。尽管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定在作为领域与不作为领域之间确实具有存在论上的差异,但是不能以此否定不作为与结果之间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或者说可归责性:无可否认,不作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缺乏事实上的因果力,例如父亲不救助落水的儿子致儿子溺水死亡,儿子溺水死亡的事实上的原因是水进入肺脏所引发的窒息,即溺水死亡是水的物理性质与哺乳动物的呼吸生理机制相互作用所导致的结果,而不是父亲的不作为。只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想阻止类似事件的发生当然不能通过处罚水等自然界的事物来达到,而只能是根据家庭社会的紧密关系赋予父亲以作为义务,以追究其不作为的刑事责任。此时父亲的不作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就获得了这样一种联系,即如果父亲在具备作为能力以及具有作为可能性等条件时实施相应的作为,则儿子死亡的结果不会发生,即假设的因果关系。〔22〕关于不作为与结果之间的假设因果关系,可参见Gropp,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3.Aufl.,Berlin u.a.2005,§11,Rdn.71ff;Stree in:Schönke/Schröder Strafgesetzbuch Kommentar,28 Aufl.,Muenchen 2010,§13,Rdn.61。这种假设的因果关系是一种准因果关系或曰规范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因而即使在不作为领域,结果在刑法上也具有可归责性,即归责给行为人的不作为。因此,德国刑法理论也认为作为与不作为在归责的意义上并无不同,〔23〕例如Roxin在不作为的客观构成要件中同样要求结果的客观可归责性(Fn.7),§31,Rdn.182;Kindhaeuser也明确指出,在不纯正不作为犯中同样适用客观归责理论的相关规则(Fn.5),§36,Rn.27;同样,Jakobs 也主张,客观归责理论可在不纯正不作为犯领域得到相应的适用,参见Jakobs,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2.Aufl.,Berlin u.a.1993,29.Abschnitt,Rdn.19。只是在作为领域适用的是风险创设或风险升高理论,而在不作为领域适用的是风险降低理论,即如果行为人实施相应的作为会降低结果发生的风险,则结果就可以归责给行为人的不作为。〔24〕关于在不作为犯领域具有广泛影响的风险降低理论,可参见Roxin(Fn.7),§31,Rdn.46ff;Otto,Wahrscheinlichkeitsgrad des Erfolgseintritts und Erfolgszurechnung,JURA 2001,275;Rudolphi u.a.(Hrsg.),Systematischer Kommentar zum Strafgesetzbuch,Band I,7.Aufl.,§13,Rdn.16。
因而,无论是从客观归责还是从主观归责方面考察,无论从行为无价值角度还是从结果无价值角度衡量,基于先行行为保证人地位的不作为都具有与作为相当的等价性。因而,要求先行行为人对于构成要件结果承担不纯正不作为的刑事责任,是对先行行为结构进行教义学分析所得出的必然结论。而先行行为与其他形式作为义务来源的区别在于:合同、法律等形式义务是在当业已存在的风险(来源于自然界、被害人本人或第三人等)威胁到被害人的法益时,基于法律上的规定、合同约定或者业务要求与被害人具有某种特定稳固的社会关系的人承担降低该损害风险的义务,这种作为义务具有稳固的制度性保障;而先行行为的作为义务则不具有这种稳固的制度性基础,往往来源于偶然的行为,因此必须从这种行为之中去寻找作为义务得以证成的根据。如上所述,如果因为纯粹偶然的符合社会相当性的一个行为而要求行为人负担结果防止义务,不啻于结果归责。因此,先行行为必须与风险的实现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先行行为必须创设了结果发生的风险,唯有如此,先行行为人才负担使这种风险降低的义务,否则应由其他人来承担保证人地位,比如由保护保证人如被害人的父母、幼儿园的老师或者危险源监管人等其他监管保证人来降低风险,防止结果发生。总而言之,在不纯正不作为犯罪领域,客观归责理论仍然可以得到适用,来自于法律、合同等保护保证人如果实施相应的作为能够降低业已存在的风险,则不作为具有可归责性;而先行行为人如果实施相应的作为能够降低自己创设的风险,则其不作为具有可归责性。
先行行为保证人地位虽然受到以Schuenemann为代表的学者的批判,但是仍然为德国主流观点所接纳,无论在形式法律义务理论、实质法律义务理论还是功能二分理论中都有其无可撼动的地位。在德国司法实践中,以先行行为作为义务为依据判决不纯正不作为刑事责任的判例也获得了持续的发展。
从上述先行行为理论的发端与演进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传统形式四分法将先行行为与法律、合同、业务要求共同视为作为义务的来源,但先行行为与其余的形式法律义务有着显著的体系上的差异。其一,先行行为的思想基础是自然主义的因果关系理论,而来自于法律和合同的义务的形式法律义务理论立论于自由主义。其二,来自于在先危险行为的法律义务是刑法上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在刑法之外根本无存在空间,而法律和合同上的义务是刑法外的形式上的法律义务,二者分属于不同的体系。
而我国关于作为义务来源的通说即形式四分法却并未注意到先行行为与其他形式作为义务来源的异质性。来自于法律、合同、职务或业务要求的作为义务,由于以法律、法规、行业惯例或者合同作为判定的基础,其形式较为固定,以此作为出发点进行作为义务的论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既然法律、法规、行业惯例既定了一定的职责与义务,或者行为人基于私法自治而承诺履行一定的义务,就表明社会生活中对该职责与义务具有普遍的合理的期待,行为人违反这些期待而致人损害,与那些不具有这种职责与义务之人相比,自有所不同,可以作为判断责任承担的基础。〔25〕当然,未必具有法律、法规、行业惯例或者合同基础就一定能够推导出作为义务,此外还须满足其他的标准,这就是实质的作为义务理论所要研究的问题。但是,与法律、法规、行业惯例与合同相比,先行行为没有固定的形式,也没有可资判断的文本依据。如何界定先行行为,从而为作为义务来源的判断划定一个范围,就成为重要的问题。如果不对先行行为概念予以必要的限制,出现损害无法处罚直接致损的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时即追溯到在先的行为,追究在先行为人“不防止其行为导致损害的责任”,无疑会导致不作为刑事责任的泛滥。下文将结合德国关于先行行为的判例与学说,尝试对先行行为的范围进行界定。
二、先行行为的界定:客观归责理论在不作为领域的适用
在先行行为的范围限定方面,德国判例与学界都进行了不同的尝试。Rudolphi主张,在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之中,保证人是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防止法益侵害危险这一保护功能的人,是引起法益侵害事件中的“中心人物”。这种保护功能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原发的(primaer)保护,直接来自于为维持共同体生活所必需的危险防止地位;另一类是继发(Sekundaer)的保护,即因特定的干扰社会秩序的行为而产生的危险防止地位,其中可分为承担的保证人与先行行为保证人。〔26〕参见Rudolphi,Die Gleichstellungsproblematik der unechten Unterlassungsdelikte und der Gedanke der Ingerenz,Goettingen 1966,S.160f。这种分类与Armin Kaufmann于上世纪50年代末提出的功能二分理论在实质上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原发的保证人大致相当于保护保证人,而继发的保证人也与监管保证人具有很大程度的重合。只是在承担的保证人地位分类上,二者存在区别。令人感兴趣的是,Kaufmann与Rudolphi两人在对先行行为的归类方面也是不谋而合,二人都将其视为第二位的、不属于稳固的社会秩序或法律制度之组成部分的保证人情形。在因特定的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而形成的作为必要性这一所谓“继发的”保证人地位之中,Rudolphi认为只有可为行为人意志控制并且违反义务的前行为(Vortat),才可成为先行行为。〔27〕Rudolphi(Fn.26),S.153ff.;163ff。由于他将义务违反理解为“指向法益的违法性”,以与合法行为进行区别,故而其先行行为判断标准被称为“违法性标准”。
判例中则发展出“义务违反标准”〔28〕参见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刑事判例集BGHSt 37,106;43,381,397。与“社会相当性标准”〔29〕例如可参见Bay NJW 53,556;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刑事判例集BGHSt 26,35。以限定先行行为。“义务违反标准”认为先行行为必须是违反义务的行为,实际上是对Rudolphi“违法性标准”的接纳,因为判例并未在违反义务与违法之间作出区分,一方面肯定违反义务行为的先行行为性,另一方面认为合法的行为即使包含着致人损害的危险,也不能成为先行行为,实际上将违反义务与合法行为相对而言,等于承认违反义务即违法,只是将紧急避险为先行行为引发作为义务等情形视为义务违反标准的例外。该判例观点也受到众多学者的肯定,成为学界通说。〔30〕参见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刑事判例集BGHSt 23,327;25,218,220ff.;34,82,84;众多德国刑法教科书也采此说,例如Gropp(Fn.22),§11,Rn.32ff;Fischerin:Tröndle/Fischer,StGB,52.Aufl.,Muenchen 2004,§13,Rdn.11a;Wessels/Beulke(Fn.13),§16,Rdn.725。后来判例又提出“结果发生的紧密危险标准”对“义务违反标准”进行补充,认为一个行为要成为先行行为,除了违反义务以外,还须引起了具体构成要件结果发生的紧密危险,即要求构成要件结果的发生与先行行为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以防止先行行为的无限回溯。〔31〕例如参见《新刑法杂志》刊载的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BGH NStZ 2000,414。
义务违反标准虽然成为德国判例与学界界定先行行为范围的通说,但却一直存在义务违反标准的确定问题。如何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义务违反标准”,值得研究。例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一则皮革护理剂致人健康损害的案例中曾试图以先行行为论证缺陷产品生产商的产品召回义务,进而确定其不作为的刑事责任时,指出义务违反并非是就违反谨慎义务而言,因而先行行为也不一定是过失行为,但该见解受到大多数学者的批判。〔32〕例如Roxin指出,客观的义务违反即谨慎义务违反,二者是一回事。参见Roxin,见前注〔7〕,§32,Rn.199。其余的批评意见参见Roxin(Fn.7),§32,Fn.338。如果此处的义务违反不是指谨慎义务违反,那么是指何种义务的违反?如果是指法律或者合同义务的违反,那么先行行为与其他的形式法律义务区别何在?
而社会相当性标准将先行行为限定在非正常的不具有社会相当性的行为之上,在社会普遍认可的行为导致危险的场合否定先行行为的存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以此标准在一则判决中否定了饭店老板向顾客售卖含酒精饮料的行为成立先行行为,判决其不对顾客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承担不作为责任。〔33〕参见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刑事判例集BGHSt 19,152ff,参见Schuenemann(Fn.4),S.310。但是,与义务违反标准说相同,社会相当性标准也面临着判断标准过于模糊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义务违反标准与社会相当性标准的问题不仅仅是判断标准不够精确或者缺乏可操作性的问题。从规范的角度来看,所有的标准本身都是不“精确”的,需要用价值判断与规范的理解才能够得以运作。如客观归责理论的“法所不容允许的风险”也是如此,但这并不影响该标准在规范意义上的适用。实际上,义务违反标准与社会相当性标准最大的问题在于二者都不是一个完整的标准,因而不能为先行行为的范围提供合理的界定。无论是义务违反标准,还是社会相当性标准,都仅仅解决了行为本身是否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缺陷”,即在法律或社会经验上来说本身是否存在问题,这仅仅是先行行为成立的前提条件,即法律不应要求行为人为一个本身(在行为当时来看)没有任何问题的行为承担责任,包括作为与不作为的责任。但是,这个条件并非是充要条件,也就是说,不能从行为本身存在缺陷就要求行为人对这个行为有关的损害承担不作为的责任(当然也包括作为的责任)。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须判定损害与这个缺陷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否则就有违反罪责原则和纯粹结果归责之嫌。因而,德国判例又借助“结果发生的紧密危险标准”对义务违反标准进行补充,也正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结果发生的紧密危险标准”并无法从实质上揭示损害与行为缺陷之间的关联。对此下文将有进一步的论述(参见下文二(二))。
综上所述,如果不对先行行为设定任何条件加以限定,当出现损害无法处罚直接致害行为时即追溯到在先的行为,径直追究在先行为人不作为的责任的做法,尚停留在原始的形式法律义务理论阶段。这种不作为犯的理念又堕入自然主义因果论的泥淖,混淆了归因与归责的区别。从上述先行行为理论的发端我们可以看到,先行行为的作为义务与其他形式法律义务具有体系上的差别,先行行为保证人与因法律或合同等规定产生的保证人地位不同,先行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相对固定的法律、合同或业务关系,而是因其实施了先行行为而与被害人产生的一种偶然的特定关系,因其先行行为而负担阻止该行为的继续发展、损害被害人利益的义务。因而,这种作为义务的原因也必然只能够在先行行为之中去寻找。那么,先行行为须具有什么样的品质,才能够使得实施了这种行为的人应为其继续发展的损害后果负责?首先,先行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必须具有联系,或者说,先行行为必须包含着结果生长的“种子”,即对于结果所损害的法益来说,必须具有侵害的风险。其次,这颗危险的种子必须是顺乎自然地生长与发展,没有其他异常的因素介入(例如异常发展、被害人或他人的行为介入等)导致原来先行行为所创设的风险被替换,形成新的风险,否则对结果发生而承担责任的人就不再是原先行行为人,而是制造新风险的人。所以,这样一来,先行行为的特殊品质就昭然若揭:对于损害结果来说,先行行为必须具有可归责性。
我们之所以承认因先行行为而推导出来的保证人地位,并非由于行为人实施了任何一种在先的行为客观上导致结果的发展,而是因为在先行为对于构成要件的结果而言具有可归责性(zurechenbar),因而具有了探讨其不作为可罚性的基础。如果在先行为根本就不具有客观可归责性,即结果的发生与在先行为之间根本没有刑法上的相关性,我们为何还要因为行为人实施了所谓“先行行为”而处罚他?此时处罚实施了所谓“先行行为”的人,与处罚任意的与结果发生无关的第三人何异?〔34〕此处我们可以以一个极端的例子加以说明:例如甲与其妻在饭店因琐事相争,甲怒称要与其离婚,坐在邻座的乙女刚好正在向其友丙哭诉其夫有外遇、夫妻失和之事,听到甲叫嚷离婚,触动前情,即要自寻短见,从甲身后的饭店窗户跳下。丙速向甲说明原委,请甲出手拉住正欲跳楼的乙,甲甚觉讶异,虽看见身旁乙爬窗欲跳仍不加阻拦,乙遂从窗户跳下摔伤。在这个例子中,虽然乙女确实是听闻甲叫嚷离婚而采取不理智行为,但如果将甲与其妻吵架叫嚷离婚的行为视为先行行为,要求其承担阻止乙女跳楼致伤的义务,恐怕很难令人接受。
从上述先行行为理论演进之中(参见一(三)),我们可大致追踪到这样一条线索:先行行为范围的界定经历了从自然主义因果论到规范的因果论或者说归责的发展历程。因此,对先行行为进行合理的界定,也可以从客观归责理论之中寻找方法论资源。因而,客观归责理论的创立者Roxin将该理论推行到不作为犯领域,主张以客观归责的标准来判定某在先行为是否为“先行行为”,从而对不作为人进行归责,是有着深刻的教义学根基的。
(一)先行行为必须是风险创设或升高行为
如上文所述,在交往安全义务从先行行为义务之中分离之后,先行行为作为义务不再包括来自于侵权法上的作为义务,先行行为不再包括民法上的所有与占有等适法的行为,对先行行为的考察必须从刑法的角度,寻找先行行为保证人地位的根据。而在刑法内部,从先行行为的界定从自然主义的归因到规范的归责的发展历程之中,我们发现,并非行为人实施了任何一种在先的行为客观上导致结果的发展就可以成立先行行为保证人地位,在先行为对于构成要件的结果而言必须具有可归责性(zurechenbar),即先行行为人如果实施相应的作为能够降低自己创设的风险,则其不作为具有可归责性。因而,先行行为必须是风险创设或升高行为,如果一个先行行为没有创设或升高结果发生的风险,而是与结果的发生仅仅具有偶然的事实上的联系,则该风险降低或防止的义务应由与被害人具有某种特定稳固社会关系的保护保证人或与该风险来源有关的危险源监管人这一监管保证人来承担,实施该行为的人没有作为的义务。
按照Roxin的观点,如果在先的行为虽然引起了结果发生的风险,但是如果该风险对于结果来说并非升高的风险或者尚在可容许的范围之内,则该在先行为不能为先行行为引出作为义务。〔35〕此处及下文案例参见Roxin(Fn.7),§32,Rdn.160f。例如,改变与他人去剧院看戏剧的计划而建议一同去看电影,他人在看电影的路上遭遇交通事故不实施救助的,其不作为不可罚。在看电影的途中遭遇风险并非升高的风险,因为他人如果不是去看电影而是去看戏剧,也可能在前往剧院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再如,甲借给乙刀具,乙突然超乎预料地用该刀具刺伤他人,甲目睹他人受伤生命垂危而不予救助,他人流血过多死亡,甲是否承担不作为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因乙用刀具伤人是甲所不能预见到的,甲出借刀具的风险是可容许的风险,不构成先行行为而引出作为义务,因此甲不承担不作为的刑事责任。
以创设法所不容许的风险标准限定先行行为的范围,在处理交通领域的不作为犯时也能够得出妥当的结论。例如,如果驾车人遵守交通规则正常行驶,而他人无可避免地撞上机动车受伤,此时驾车人不具有保证人地位,因为行为人未违反交通规则,机动车本身因高速运动而具有的致人损害的风险本身是可容许的风险。无论是碰撞行为,还是往前追溯他人的正常驾车行为,本身都不是先行行为,不产生作为义务。〔36〕参见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刑事判例集BGHSt 25,221:“在各个方面都合义务性的、符合交通规则的机动车驾驶人,在受害人因自己责任导致交通事故时,不负保证人义务。”
1.关于犯罪行为是否可为先行行为的争论
在我国关于先行行为范围的讨论中,存在先行行为是否可为合法行为或者犯罪行为的争论。〔37〕例如参见杨阳,黄晓帆:“不作为犯之先行行为范围浅析”,《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29期;刘东明:“不作为犯中先行行为的再认识”,《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4期;杨晓娜:“先行行为研究”,《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28期;蒋晗华:“浅析犯罪行为可否成为先行行为”,《当代法学》2002年第2期;刘世心:“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中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研究”,《北方法学》2007年第6期。学者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往往区分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大多数观点同意过失犯罪可以成为先行行为引发作为义务,而否定故意犯罪构成先行行为的可能性。之所以进行这种区分,主要原因在于,承认过失犯罪的先行行为性,较易解决由此引出的罪数问题,得出过失犯罪与其后的不作为犯罪数罪并罚的结论;而承认故意犯罪的先行行为性,则会导致复杂的罪数问题。表面上看,作为故意犯罪的先行行为本身与故意的不作为犯罪之间存在故意、损害后果上的重叠关系,但罪名适用的问题与先行行为范围界定的问题是两个问题,详见下文论述。其实,如果认识到先行行为是一种风险创设或升高的行为,诸如此类的争论就可以轻易地得到解答。法秩序要求法规范对象不得介入他人的法益领域对他人的法益创设风险,因而创设风险或升高风险的行为一般来说也是一种违法的行为。但是如果该创设风险的行为本身是刑法所禁止的构成要件行为,即先行行为客观上符合构成要件而且行为人对损害结果具有故意或过失的情况下,则在先行为本身也构成作为的犯罪,如果行为人在已构成作为犯罪的先行行为实施完毕之后,对进一步发展的更重的损害后果能够阻止而故意或过失地不加阻止,则对于该加重的损害后果而言,行为人理论上也存在承担故意或过失的不作为刑事责任的可能性。至于是否构成不作为犯罪,还须视该重结果与在先行为之间是否存在风险关联而定(参见下文二(二))。如果能够肯定风险关联,那么该在先行为就能够推导出行为人的保证人地位,则行为人针对更重的损害后果成立不作为犯罪。不可否认,如果承认在先行为可为犯罪行为,就会出现在先行为本身所构成的犯罪与其后的不作为犯罪两个罪名,加之如果在先行为所构成的犯罪已包含了不作为所造成的加重结果,即在先行为本身构成的犯罪为结果加重犯的情况,罪名适用可能更为错综复杂。但这并不能成为反对先行行为可以为犯罪行为的理由。因为如何确定最终适用的罪名是罪数的问题。罪数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解决待评价的数个罪名所对应的行为或行为后果之间的需罚性的(Strafbarbeduerfnis)问题,而根据先行行为风险创设与风险关联标准进行先行行为范围界定的问题,是可罚性的问题(Straf-barkeit)。可罚性问题通常是一个须经受严谨的逻辑检验的教义学问题,而需罚性的问题则是在可罚性的基础上结合刑事政策因素予以考量的问题。二者不应混为一谈,更不能以需罚性考量对可罚性问题进行论证。
因而,以需罚性问题试图对可罚性问题进行论证,其所得出的结论必定难以经受教义学上的检验。例如,如果否定犯罪行为可以成为先行行为,会导致共犯场合的刑事可罚性漏洞。例如在他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之后,第三人帮助或教唆该行为人不救助被害人,如果否定实施犯罪行为人因其犯罪行为产生保证人地位,则其不成立不作为犯罪。相应地,第三人的帮助行为或教唆行为也因正犯行为不可罚而无法受到追究。〔38〕参见Roxin(Fn.7),§32,Rdn.194。对将犯罪行为排除在先行行为之外可能导致的共犯场合的刑事可罚性漏洞问题,张明楷教授也表述赞同,参见张明楷,见前注〔4〕页157-158。另外,在承认犯罪行为可以成为先行行为的前提下,才不致得出对故意伤害他人后故意不救助致被害人死亡时的刑法评价(即否定先行行为可为犯罪行为则仅成立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反而轻于行为人无罪责地意外引起他人伤害而故意不救助致被害人死亡的评价(即成立不作为故意杀人罪)这样明显不合理的结论;最后,承认先行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可以为针对正当防卫不作为的问题提供更为合理的解释。〔39〕参见张明楷,见前注〔21〕。关于故意不法前行为作为先行行为的探讨,详见蔡圣伟:“论故意不法前行为所建构之保证人义务”,载《刑法问题研究(一)》,元照出版社2008年版,页221-236。
2.关于合法行为是否可为先行行为的争论
我国关于先行行为的通说认为合法行为也可以为先行行为引发作为义务,例如我国关于先行行为的文献通常将带邻居孩子去游泳,当孩子在河中遇险时有救助能力而不救助视为因先行行为引发不作为刑事责任的一种情形。〔40〕参见杨阳等,见前注〔37〕;刘东明,见前注〔37〕;杨晓娜,见前注〔37〕。学者在论证这种“先行行为”时指出:“带孩子出去玩,不管到哪里玩,都使孩子脱离了监护人的监管,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当这种危险状态具有转化为现实危险的紧迫的可能性时,行为人就负有阻止危险结果发生的义务。”〔41〕杨晓娜,同上注。但是带邻居的孩子去游泳,虽然与带孩子逛街或者不带孩子做任何事情相比,具有更大的风险,〔42〕带孩子逛街有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不带孩子做任何事情也不可能排除任何风险,孩子也可能在家中遭遇火灾。但这种假设因果关系不能免除现实因果关系导致损害的可归责性,参见Gropp(Fn.22),§5,Rdn.30f。但是这种风险并非法所不容许的风险。只要行为人对该风险进行合理的管控,该风险就不会实现,因此将此种行为视为先行行为,无疑会导致不纯正不作为犯范围的无限扩张。如果合法的或具有社会相当性的行为也能够为先行行为推导出作为义务,要求实施上述行为者作为保证人负有损害防止义务,将会使得本就具有开放性的不作为犯构成要件更加无边无际。而保证人地位、不作为犯与作为犯的等价性等理论的提出即是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构成要件划定边界,发挥不作为犯构成要件的保障功能,防止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可罚性扩张而导致对公民自由的侵害。如果以此种宽泛的先行行为概念证明保证人地位,实质上又将保证人地位的内容形式化,使得保证人理论形同虚设。
实际上,上述情形属于自愿承担导致的保护保证人情形,即邻居自愿承担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保证人地位,自当归入保护保证人范畴予以探讨,对此上文已有论述。而我国学者却将其视为属于监管保证人地位范畴的先行行为,由此证明其保证人地位。这种对先行行为保证人地位类型的混乱认识,也带来了先行行为界定的混乱。
缺乏对先行行为风险创设标准的认识,使得我国司法实践对先行行为的界定过于形式化,导致不纯正不作为犯刑事责任认定过于宽泛。例如甲男与乙女在网上相识,二人相约某旅馆发生一夜情,事后乙女对甲男产生感情,欲与其发展恋爱关系,遭甲男拒绝后伤心欲绝。某日乙女找到甲男,威胁说如果甲男不答应与其建立恋爱关系就割腕自杀,甲男仍不应允,说:“你要死就死,与我何干?”乙女怒而割腕,甲男目睹乙女流血倒地而不实施救助,最终乙女因血流过多而死亡。甲男是否因不作为的间接故意杀人而承担责任?如果采取肯定回答,就必须论证甲男的作为义务。甲男与乙女并非夫妻也未长期同居,无论从法律规定还是从生活共同体的角度都无法推导出其保证人地位,二人之间当然也无合同关系,可以考虑的似乎只有因先行行为获得保证人地位的可能性。但是,此处何为先行行为?是甲男不答应与乙女建立恋爱关系的行为,还是与乙女发生一夜情的行为,甚或再往前追溯——二人的网聊行为?如果以风险创设或升高的理论审视,上述任何一种行为都未创设法所不容许的风险,如果将这些行为视为先行行为,势必大大限制公民行动自由的范围。以此种不加限制的先行行为概念追究不作为刑事责任,也会损害构成要件的保障功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当然,否定本案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还可以根据客观归责理论从另外一个角度展开,即将乙女的行为视为自我答责的行为,从而否定该行为对甲的可归责性。此种解答路径是首先肯定甲男因先行行为具有保证人地位,负有作为义务而不作为,再根据损害发生在他人自我答责领域这一例外规则来否定不作为的可归责性。但是虽然这种论证思路得出的结果与前述论证结果相同,却过于繁琐、低效。如果我们能够对先行行为进行合理的界定,根据合理的先行行为概念否定甲的行为属于先行行为继而否定其保证人地位,那么就可以径直得出其行为不符合不作为的构成要件的结论,毋需再通过以自我答责例外规则排除客观归责来否定甲的刑事责任。可见,合理确定先行行为的概念与范围,在不作为犯论证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样,上文所举的出借刀具案也可以直接通过否定先行行为的存在而得出出借人不构成不作为犯的结论,毋需再通过以他人负责的例外归责排除可归责性的方式推导出这一结论。〔43〕当然,此案还可通过以信赖原则否定预见义务,从而否定谨慎义务违反的方式得出行为人不具有过失的结论。但这种论证并不影响先行行为概念界定的意义。
综上所述,先行行为可以是犯罪行为,也可以是一般违法行为,我国学界与之相关的争论并不能为先行行为范围的界定提供实质性的标准,对先行行为的界定必须抛开这种形式主义的窠臼。先行行为必须是可归责的行为,首先必须是创设法所不容许的风险的行为,因此一般来说也是违法行为。风险创设标准是界定先行行为的第一个标准,接下来必须进行第二个标准的检验,即审查犯罪行为所创设的风险与不作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风险关联(参见下文二(二))。
(二)风险关联:不作为的风险实现须在先行行为违反的规范保护目的范围之内
如果在先行为创设或升高了风险,但是损害结果的发生却并非是在先行为所直接导致的,即在先行为与损害结果发生之间不具有风险关联时,是否应当要求实施了在先行为的行为人承担不作为的刑事责任?仍以交通领域的不作为犯问题为例。被告人违反时速100公里的限制,以120公里的时速驾驶,撞上摩托车骑车人K,将其甩到一边。州法院不能排除K 在察觉到被告人的汽车时向右驾驶试图避开,但在相撞之前却向左侧偏向一至两米。根据罪疑从无原则,应当认定被告人对该交通事故的发生并无责任,由被害人K 对事故负全责。被告人下车看到受伤大量流血的K 躺在路上,却未实施救助行为而驾车离开,被害人K 因未得到及时救助而死亡。〔44〕参见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刑事判例集BGHSt 34,82=NJW 1986,2516。该案中被告人虽然违反了限速规定,存在谨慎义务违反的行为,但是损害结果的发生却不是因为谨慎义务违反所导致的,即与谨慎义务违反之间不具有关联性,因而根据关于过失的通说即谨慎义务违反标准说,〔45〕参见Gropp(Fn.22),§12,Rn.48ff。被告人不因超速驾车承担过失的(作为的)刑事责任。但此处值得探讨的是,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告人有能力救助被害人而不予救助,是否因其不作为可罚?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虽然被告即使不违反交通规则交通事故也无法避免,但是仍然认为“被告人违反交通规则行为可能对事故的发生有所贡献,因而与损害发生具有直接的联系”为由肯定了被告不作为的刑事责任。〔46〕参见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刑事判例集BGHSt 34,82,84=NJW 1986,2516。该观点受到通说的批判。〔47〕参见SK-Rudolphi(Fn.24),§13,Rdn.39 b;参 见Roxin(Fn.7),§32,Rdn.170ff;Kindhaeuser(Fn.5),§36,Rn.71。Roxin指出,成立先行行为引发的不纯正不作为犯罪要求先行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风险关联。虽然在先行为创设了风险,但如果该风险的防御超出了先行行为所违反的规范的保护目的范围,该在先行为也不能成为先行行为产生保证人义务。〔48〕Roxin(Fn.7),§32,Rdn.171。Kindhaeuser以事故发生的危险并非来自于超速行为为由否定驾车人的保证人地位,认为判例针对同一风险一方面因缺乏谨慎义务关联否定了作为的过失责任,另一方面却肯定不作为的责任,存在矛盾。〔49〕Kindhaeuser,见前注〔5〕,§36,Rdn.71。即使是采取义务违反标准的判例,也赞成违反义务的先行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须存在义务违反关联。例如联邦最高法院在皮革清洁剂一案中肯定了以往判例和学界主张义务违反关联(Pflichtwidrigkeitszusammenhang)的观点,重申先行行为所违反的命令必须具有保护被侵害的法益这一规范目的。〔50〕参见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BGHSt NStZ 1990,587,590。学界持相同观点的,参见Jescheck u.a.(Hrsg.):Leipziger Kommentar zum Strafgesetzbuch,10.Aufl.,§13Rdn,30ff;SK-Rudolphi(Fn.24),§13,Rdn.39b。
这种风险关联思想是与客观归责理论中的规范保护目的理论(Schutzzweckslehre)一脉相承的。以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对先行行为保证人范围进行限制,能够防止不纯正不作为可罚性的不当泛滥。例如盗窃犯潜入他人家中实施盗窃而惊动主人,主人察看情况时不慎滚落楼梯受伤,在作为犯刑事责任的检验中我们根据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可以得出主人受伤的损害结果不可以归责给盗窃犯的结论,因为盗窃规范的保护目的是他人的财产权而不是生命健康权。同样,如果盗窃犯看见主人受伤流血而不采取救助行为,主人因得不到救助而重伤或死亡的,也可以因损害超出了先行行为所违反的规范保护目的范围而否定先行行为的存在,从而得出行为人不承担不纯正不作为刑事责任的结论。〔51〕Streein Guenter Kohlmann(Hrsg.):Ingerenzprobleme,FS- Klug,Koeln 1983,S.399。当然,根据德国刑法第323c条见危不救罪的规定,行为人纯正不作为的刑事责任并不受影响。同理,被害人因被盗走贵重财产而悲痛欲绝欲撞车自伤、自杀,在场的行为人并不因其盗窃行为而产生阻止被害人自杀或自伤的义务。
近年我国学者也主张先行行为的实质根据在于使刑法保护的具体法益面临紧迫的危险,即赞同将先行行为限制在制造紧迫危险的范围内,〔52〕参见张明楷,见前注〔21〕。可以说是对上文所提到的德国判例“结果发生的紧密危险标准”的接纳。但危险的紧迫标准主要是从事实的层面,根据危险发生与不作为之间的时间、空间间隔角度进行判断,如伤害被害人致其手指骨折,不会产生死亡的危险,如果不对被害人救助,并不成立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53〕参见张明楷,见前注〔21〕。但在一些场合,行为人的行为即使引起了从时空间隔角度来看具有紧迫性的危险,也不应将该行为视为先行行为而要求行为人承担不作为的责任。
例如,甲违反交通规则撞翻乙的货车致乙昏迷,周围群众见状立即一哄而上,将乙货车上装载的货物一抢而空,甲旁观整个过程而不加阻止。甲对乙的财产损失是否负有防止义务?根据紧迫危险标准说,甲的行为在客观上制造了乙财产损失的紧迫危险,因为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的角度来看,其财产被转移的风险都是现实的、紧迫的,因而应当对乙的财产损失承担不作为的责任,即构成不作为的盗窃或侵占罪(根据是否承认丧失意识的人或死者的占有而有不同),但这种结论显然令人难以接受。而如果采取风险关联标准则可以得出妥当的结论:甲违反交通规则对乙的生命、健康权创设了风险,应当因为这种先行行为承担对乙的救助义务,如果乙未得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甲在满足其他条件(如具有救助可能性、明知其不救助行为会导致死亡结果)的情况下,应承担不作为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但甲的先行行为违反的义务规范保护目的主要是被害人的生命、健康权,不包括其财产权,因而对其财产损害不承担不作为的(盗窃或侵占)责任。因此,风险关联标准相对于紧迫危险标准更加合理,后者试图从事实的角度根据危险发生与在先行为之间的时空间隔限定先行行为范围,而前者则是从规范的角度判断实现的风险与在先行为创设的风险之间在规范上的同一性问题,更加精确合理。实际上,强调危险发生与在先行为之间时空间隔的紧迫危险标准所探讨的并非是先行行为成立范围的问题,往往是作为的必要性与作为的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如上文手指骨折的案例,由于致人手指骨折的伤害行为一般不会造成死亡结果发生,如果手指感染而果真导致被害人死亡,则实施伤害行为的人或者在行为时因感染未发生而没有实施作为的必要性,或者在感染发生时不在现场而缺乏作为的可能性。另外,伤害结合感染因素是否还能视为原先伤害风险的实现(即是否属于异常的介入因素而阻断了原先伤害行为的风险实现),也颇值得疑问。所以,紧迫危险标准难以为先行行为范围提供合理的界定。
由于缺乏基于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的风险关联的思考,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先行行为认定过于宽泛,从而不当地扩大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而先行行为所创设或升高的风险与损害结果之间的风险关联要求,为我们合理限制先行行为的范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参见如下案例:〔54〕郑志军、常玉峰:“从一个案例谈不纯正不作为犯罪问题”,载谢望原、赫兴旺主编:《中国刑法案例评论》(第二辑),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页25-26。
2004年4月5日,犯罪嫌疑人平某驾车在巩义市免费搭载陌生女青年李某、张某二人由高速公路去郑州。车辆行驶中,平某对二人进行语言挑逗,并抚摸坐在副驾驶座位的张某的手和大腿,遭到张某和坐在后排的李某的呵斥,二女青年要求平某停车,否则即跳车。平某不予理睬,继续对张某搂抱,李某随即从高速行驶的车上跳下,造成重伤。
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引起较大争议,争点主要在于被告平某是否因其先行行为负有防止被害人受重伤的作为义务。第一种意见认为,平某对李某并未实施强制猥亵行为,李某跳车是因为精神上受到平某对张某强制猥亵行为的威胁,由于张某的强制猥亵行为是犯罪行为,犯罪行为不能为先行行为推导出作为义务,因而平某不构成不作为的故意伤害。反对犯罪行为可以成为先行行为的理由如下:其一,实施犯罪行为者本身没有减轻或避免犯罪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的义务;其二,犯罪行为本身就包含了对被害人的侵害,创设了对被害人的风险,因此不能由犯罪行为推导出对被害人救助的义务,否则对故意伤害致死的行为人都可能定故意伤害罪与间接故意的不作为杀人两罪,对一个犯罪行为进行刑法上的两次评价,违反了重复评价原则。第二种意见认为平某的强制猥亵行为属于先行行为,因先行行为负有损害防止义务。其中又分为主张犯罪行为一概可为先行行为的观点与区分的观点。区分的观点认为,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先行行为是否可为犯罪行为,应以行为人所放任发生的危害结果是否能为前罪的犯罪构成,包括加重的犯罪构成所包括进行区分:能包括的,直接根据相应法定刑幅度定罪量刑,没有作为义务;不能包括的,则产生作为义务。《刑法》第237条规定的强制猥亵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其它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侮辱妇女,不包括致人重伤、死亡的结果,所以应认为平某有作为义务,构成强制猥亵罪与故意伤害罪(不作为的间接故意)。〔55〕参见郑志军、常玉峰,同上注,页26-32。
本案中判断平某的行为是否属于先行行为,首先要明确判断的对象。本案中我们要判定的先行行为是平某的哪种行为?平某分别针对张某、李某实施了不同的侵害行为。平某对张某进行语言挑逗,并违反张某的意志抚摸其手和大腿,其行为可以构成强制猥亵。但是跳车的并非是直接受到强制猥亵侵害的张某而是坐在后排的李某,针对他人的侵害行为是否可以构成先行行为,从而产生对被侵害人以外的第三人的损害防止义务,值得怀疑。笔者以为,应当对此持否定态度。因为,根据先行行为风险判断标准,平某针对张某所实施的强制猥亵行为只是针对张某的风险创设行为,并未对李某造成(具体的)风险,从而不宜将该行为视为针对李某重伤这一损害结果的先行行为。否则,实施侵害行为者对于被害人以外的第三人都要承担防止其因受到侵害行为精神刺激而受伤害甚至是自伤、自杀的义务,过大地扩张了保证人的范围,显然不妥。另外,从客观归责的角度来看,对于平某强制猥亵张某来说,李某的跳车行为虽是由平某的行为引起,但是平某的行为只是一种事实上的条件,这种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并不具有可归责性——因为平某的侵害行为对李某而言并未严重到跳车是唯一自救手段程度,而李某在认识到跳车风险的情况下实施了跳车这一自我危害的行为,应当自己承担该风险。因而,以李某精神上受到平某对张某强制猥亵行为的威胁为由,即肯定平某对张某强制猥亵行为构成先行行为,应当承担防止李某跳车受伤的义务的观点不可采。平某针对张某实施的强制猥亵行为无法成为李某身受重伤的先行行为。
再看平某对于李某的行为是否属于先行行为。平某经李某要求停车而不停车,并对李某进行语言挑逗,按照前述判定先行行为的风险创设或升高标准,平某的语言挑逗行为侵犯了李某性的自由与尊严,创设了其性方面的权利被侵害的风险,可以视为风险创设行为,符合先行行为判断的第一个标准。但李某受到平某语言侵犯以及在平某对张某猥亵行为的影响下跳车而身受重伤这一损害结果是生命健康法益的侵害,而平某在先行为所违反的是性的自由保护方面的规范(强制猥亵罪一般来说不会对被害人的生命权与健康权造成重大的侵害,故强制猥亵罪也不有在结果加重犯,其中不包括致人重伤、死亡的结果),这一规范保护目的并不包含(严重的)身体健康法益的损害,因此先行行为所创设的风险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风险关联,从而根据风险关联规则可以判定平某的挑逗行为并不是李某受重伤这一损害后果的先行行为,平某不具有防止李某受重伤的作为义务。
但是,此案中否定了先行行为的存在,并不等于否定平某对李某重伤结果承担刑事责任的可能。实际上,平某对于李某重伤的结果仍应承担不作为的刑事责任,但作为义务并非来源于所谓先行行为,而是来源于平某的危险源监管保证人地位。如上文所述,高速运动的机动车属于危险源,平某作为机动车驾驶人,应对该危险源进行合理的管控,负有保障搭乘其车辆的乘客张某、李某二人与车辆行驶相关的安全义务,遇有紧急情况应刹车或减速。此种义务与张、李二人是否支付搭乘车辆的相应对价无关。在平某认识到李某欲跳车时,无论李某是因为何种原因欲下车,在认识到李某可能跳车的一刹那,平某都负有停止车辆或者将车速减至可以安全下车的义务,否则高速运行的车辆即会给李某造成伤害。故对平某应当按照强制猥亵罪(针对张某而言)与不作为的故意伤害罪(针对李某而言,至于是间接故意还是直接故意,尚有待于主观方面的查明)数罪并罚。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虽然与肯定先行行为所得出的结论相同,论证过程却殊异。法律论证并非只以结果是否可以令人接受为衡量标准,更重要的是论证过程是否具有教义学上的严谨性。
对于这种论证的教义学严谨性,我们还可以用一个变形案例予以进一步的证明:假设平某没有驾车,平某对张某的猥亵行为不是发生在高速运转的机动车内,而是发生在多层或高层建筑的房屋内,平某对张某进行猥亵并对李某进行语言挑逗,李某因而跳楼,显然难以要求平某对李某的伤害承担不作为的责任。针对张某的不法行为与针对李某的挑逗行为,没有对李某的法益造成重大威胁,李某选择跳楼这一不理性的行为,属于自我危险的行为。平某对他人的自我危险行为没有损害防止的义务。在我们替换了平某驾驶机动车这个变量而保留平某的猥亵与语言挑逗行为的情况下,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可见,对于结论具有影响意义的因素不在于平某的猥亵与语言挑逗行为这一所谓“先行行为”,而在于机动车这一危险设备的控制。后者才是引发作为义务的真正根据。
(三)行为创设或升高风险,但是风险实现为被害人自我危险行为所导致
如果行为人实施的在先行为虽然创设或升高了风险,但是因介入被害人自我危险行为,被害人创设的自我危险阻断了在先行为的风险实现,在先行为人不因之承担保证人义务,由被害人自负其责。这一规则属于客观归责理论例外规则之一,同样也适用于对先行行为的论证。例如向吸毒者贩售毒品,在吸毒者吸食毒品后陷入昏迷时不对其进行救助,如果吸毒者死亡的,不承担不作为故意杀人或不作为过失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56〕Roxin(Fn.7),§32,Rdn.175。对此Roxin并未给予进一步的论证。实际上,吸毒者在对吸食毒品的风险有足够认识的前提下仍然实施吸毒行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担责任的理由如下:之所以要求行为人对自己的先行行为创设的风险负责,是因为每个人都有管理自己行为不导致他人损害的义务,如果该行为直接导致他人损害,则行为人对损害结果承担作为的刑事责任;如果该行为虽然不直接导致损害,但是结合其他因素间接导致损害,行为人也有防止其行为所包含的风险实现的义务,否则对损害后果承担不纯正不作为的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虽然创设了风险,但是该风险实现是他人在完全的风险认识情况下由他人行为导致的,那么在先行为所包含的风险为他人的风险行为所阻断,在先行为不构成先行行为,在先行为人不具有保证人地位。
这一由Roxin创立并主要适用于吸毒、参与他人危险飙车等情形的规则,〔57〕Roxin(Fn.7),§32,Rdn.175f。可以被扩展到所有存在被害人自我危害行为的案例之中,为此种类型的先行行为界定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参见下例:
甲与乙因谈恋爱产生矛盾,甲购买硫酸倒入喝水的杯中,随身携带至乙处,欲将硫酸泼到乙身上。甲与乙见面发生激烈争执,此时甲已忘记以硫酸泼乙的计划,乙见甲身上携带水杯,以为是清水,因情绪失控抓过来倒在自己头上,甲未加阻拦,导致乙被硫酸重度灼伤。〔58〕此案例由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演化而来,参见刘京川:“杨某某故意伤害案——明知先行行为会引发危害后果而不予以防止的行为构成故意犯罪”,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编:《刑事审判参考1999-2008分类集成之三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权利罪》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页356。
关于甲的刑事责任存在如下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乙的行为属于自伤行为,甲并未实施伤害行为故不负刑事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甲携带硫酸的行为属于先行行为,甲因先行行为承担阻止乙以硫酸自伤的义务。如何解决本案甲的刑事责任问题,关键在于判断乙的自伤行为是否阻断了先行行为的可归责性。甲携带硫酸欲伤害乙属于伤害罪的预备行为,该行为对于乙的生命健康法益来说无疑制造了风险,而且对该法益的保护也符合先行行为违反的规范即故意伤害罪(预备)的规范保护目的,故可以肯定乙身受重伤这一损害结果与甲行为之间的风险关联。值得怀疑的是,以上述客观归责理论对先行行为进行限定的规则,是否因存在自我危险的行为而排除甲在先行为的可归责性,从而认为甲的行为不构成先行行为?如上所述,如果行为人虽然创设了风险,但是该风险实现是被害人在完全的风险认识情况下由被害人自己行为导致的,在先行为所包含的风险为被害人自己创设的风险行为所阻断,那么在先行为不构成先行行为,在先行为人不具有保证人地位。但本案中乙在抓过杯子往自己头上倾倒时并不知道其中所装为硫酸,对自己行为的风险没有认识,因而甲行为的风险结合乙的行为发展成最终的损害结果,在先行为所包含的风险未被被害人自己创设的风险行为阻断。因为在客观归责理论中,被害人对自我危险行为自负其责的前提是行为人与被害人相比,对风险没有更好的认识与掌控。假设本案中甲已(以乙相信或应该相信的方式)告知乙杯子所装液体为硫酸,但被害人仍将硫酸倒在自己头上,则甲的行为就不再是可归责的先行行为,不承担阻止损害结果的作为义务。
在行为人针对被害人实施了先在的风险行为,同时又介入被害人自我危害行为导致损害结果时,究竟是认定存在因先行行为引发的作为义务而追究行为人的不作为责任,还是认定被害人因自陷风险的行为而自己对损害承担责任,在司法实践中易于引起争议。而以客观归责的标准对先行行为进行界定,在先行行为与自我危害行为之间进行正确的归责选择,可为妥当解决此类案件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
因此,是否具有对先行行为风险的认识,以及被害人与在先行为人二者谁对风险具有更大的控制力,是在存在被害人介入行为时判断行为人在先行为是否构成先行行为引发作为义务的关键,也为此类案件中自我危险或自我答责原则的适用划定了边界。
三、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先行行为理论谱系的整理可以看到,先行行为发端于自然主义的因果关系思想,经历了形式法律义务理论、功能理论与实质理论的发展,完成了从归因到归责的发展历程。来自于先行行为的作为义务与其他的形式法律义务存在体系上的差异,是刑法内部的一种作为义务,因此对先行行为必须以刑法特殊的规则进行审查。对先行行为的认定,应当在功能二分说的框架下,明确其与其他作为义务来源的区别,继而根据客观归责理论进行审查。在我国刑法中,应明确只有对损害结果具有可归责性的行为,才能构成先行行为引发阻止该损害的义务这一原则,以防止对先行行为进行过于形式化的认定以及相应不纯正不作为犯刑事可罚性的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