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插图与评点的互文性解读——以《六合同春》为例
2012-12-31李巍男
李巍男
(东南大学,江苏 南京 210000)
戏曲评点是中国古典戏曲鉴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是指在剧本正文的有关地方予以圈点、短评,并与读法、总评和序跋合为有机整体,从而对文本进行阐释归纳与导引升华,充分体现评点家本人的基本思想、审美情趣和哲学观念。进行戏曲评点的过程本身就是鉴赏的过程,评点是对文本的一种解读,体现出评点者的思想与对文本的评价。插图是依据文本所述内容而为文本所做的配图,即将文字内容转换为图像的过程,亦体现了绘图者对文本的一种理解。“书籍的版式与插绘的设计者可说是文本最初的读者,一如注释或评点者;他们所创造出来的形式,正如评点者可以影响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一般,也可能模塑读者的视觉习惯或观览方式。”[1]可以说,插图是以图像的方式充当评点的功能。
插图评点本的意义在于文本、评点、插图三者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文本增殖。互文性理论指出,一个文本的产生离不开其它的文本,为文本的建构提供了新的思想。每一个单独的文本都不是独立的创造,都与其它文本有关联,都是对旧文本的改写、复制、模仿、转换、拼接等。插图与评点作为对文本的解读,二者相互补充、相互阐发,形成新的互文性。既有研究关注插图与文本、评点与文本的关系,至于插图与评点之间的关系却鲜有问津。本文以师俭堂本《六合同春》为例,解读插图与评点之间的互文性关系。
一、《六合同春》的版本、评点者及插图绘工
本文所要探讨的《六合同春》为汇集陈眉公所批评的《西厢记》、《幽闺记》、《琵琶记》、《红拂记》、《绣襦记》及《玉簪记》的六部合刊。陈眉公批评的这六种戏文原为明代书林师俭堂所刻,清代时被修文堂购买,重新印行,六部著作合刊称为《六合同春》,收录在马氏《不登大雅文库珍本戏曲丛刊》中,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具体版式为“单栏白口,栏内刻有眉批,眉批是用明体字,小字双行,版心上端刻书目‘陈眉公批评某某某’,中刻卷次页数。各出出末有出批,手书体;剧末有总评性质的文字,手书体。”[2]每部戏文卷首均题有“云间眉公陈继儒评,一斋敬止余文熙阅,书林庆云萧腾鸿梓”。
明代文学家陈继儒(1558-1639),号眉公,科举不第后放弃仕进之路,隐遁而居。正如钱谦益所云:“少为高才生,与董玄宰、王辰玉齐名。年未三十取儒衣冠焚弃之,与徐生益孙,结隐于小昆山。”[3]在文艺思想方面,陈眉公与晚明戏曲的“主情”思想一致,他崇尚至情说,认为抒发真心真情之作才能流传久远。在《吴骚集》序文中,陈眉公写到:“夫世间一切色相俦有能离情者乎?顾情一耳,正用之为忠愤、为激烈、为幽宛,而抑之为忧思、为不平、为枯槁憔悴,至于缡缡一腔难以自已,遂畅之为诗歌,为骚赋,而风雅与三闾诸篇并重于世。”[4]陈眉公认为世间万物都不能离开情而独立,情是世间一切色相的关键。在《六合同春》的评点中,亦鲜明地体现出陈眉公的重情思想。
《六合同春》中的插图散见于各出之中,版式均为双叶连式。插图包括《西厢记》图10幅,《琵琶记》图15幅,《红拂记》图10幅,《玉簪记》图11幅,《幽闺记》图11幅,《绣襦记》图11幅,共计68幅。其中,除7幅插图无明确署名及题记外,其余均有题记和署名。从插图署名来看,《六合同春》插图的绘制者不止一人,包括了萧腾鸿、萧照明、蔡冲寰、丁云鹏、熊莲泉、王廷策、以及“米元章”、“赵松雪”等。其中,署名“米元章”、“赵松雪”等名家为托名之作。
插图和评点都是书商为了招徕顾客而使用的推销手段。如《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的封面上印有题记:“此曲坊刻不啻牛毛,独本堂是集出评句释、字仿古宋,随景图画俱出名公的笔,真所谓三绝也。”[5]由此可见,插图本、评点本是吸引顾客的重要方式。同样作为对文本的解读,插图和评点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
二、《六合同春》插图与评点的关系
《六合同春》是集“文——图——评”为一体的经典畅销本,文本与插图、文本与评点、插图与评点之间形成多重对话关系。插图与评点都是对文本的一种解读,二者之间的对话关系较之文与图、文与评之间的关系显得更为复杂。本文通过分析《六合同春》中的68幅插图与陈眉公的评点,解读二者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插图与评点交相辉映,形成间接的互文,具体表现为插图营造的意境与评点形成呼应,插图表现与评点思想暗合,插图与评点形成冲突与反讽以及插图充当评点的功能。
(一)插图营造的意境与评点形成呼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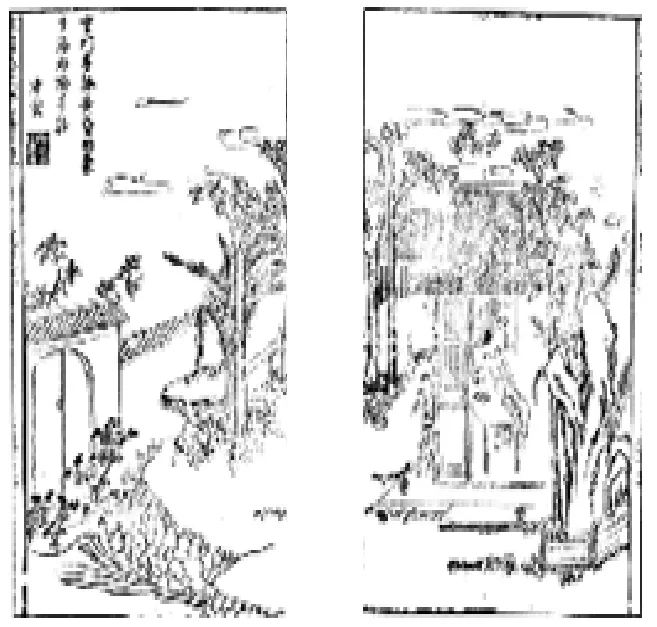
图1 《琵琶记》第13出“官媒议婚”插图,摘自《不登大雅文库珍本戏曲丛刊》第11辑第75-7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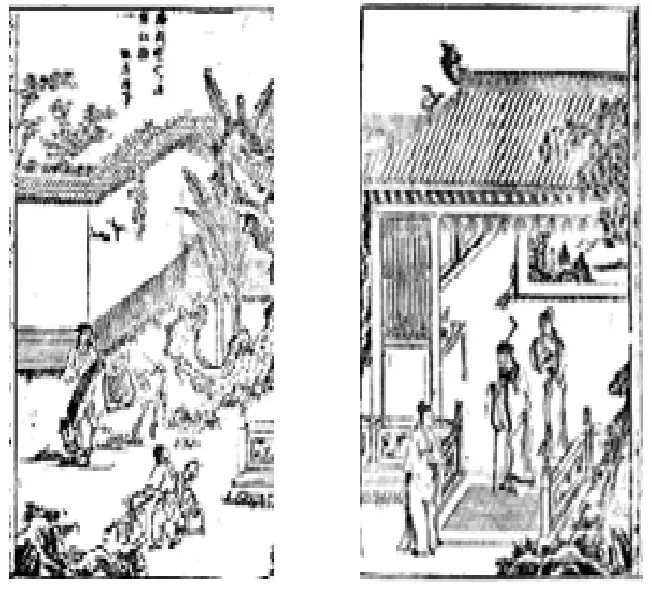
图2 《玉簪记》第2出“潘公遣试”插图,摘自《不登大雅文库珍本戏曲丛刊》第11辑第350-351页。
陈继儒的评点对文中紧要文字或认为关目妙处皆做了圈点,据粗略统计,68幅插图中,24幅插图的题记取自陈眉公圈点的戏文。如《西厢记》第七出“夫人停婚”插图。图画老夫人于堂前端坐,莺莺与张生侍立一旁。插图题诗为“有意诉衷肠,争奈母在侧”[6],化用本出戏文唱词“[月上海棠](旦)而今烦恼犹闲可,久后思量怎奈何?有意诉衷肠,怎奈母亲侧坐……咫尺间如间阔。”[7]插图形象地将张生、莺莺二人相恋却为老夫人阻挠的无奈传达出来。评点本中陈继儒将此处圈点出来,眉批“关目妙”[8]。《琵琶记》第十三出“官媒议婚”的插图(图1)。画面中左边部分为庭院风景,右边为蔡伯喈一人独坐在书桌前,神色落寞,表情忧郁。题记“重门半掩黄昏雨,奈寸肠此际千结”[9],取自戏文原文,陈眉公对此句的眉批曰“一字一泪”[10]。插图正选取了此景来表现,并且直接选用陈公所批点的戏文作为题记。再如《玉簪记》第二出“潘公遣试”插图,如图2。图画潘公赴试远行前离别之景,潘必正与父母作揖拜别,远处书童和马匹已经备好,准备出发。题记“肠断云霓,泪沾红袖”[11],取自戏曲原文。陈继儒在戏文“肠断云霓,泪沾红袖”句有圈点,并且眉批曰:“0别离却0离别尽”[12],其中两字字迹模糊,无法辨认。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本文不再一一列举。圈与点是明代戏曲评点本中最常见的评点符号。“它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对剧本的某些曲词、道白、舞台动作加以突出强调,警示读者注意,相当多的圈点符号都辅之以批语,从批语内容看,均为肯定、赞赏性质的。因此,圈、点两种符号所突出强调的也都是评点者认为值得赞赏的内容。”[13]在《六合同春》中,陈眉公将他所认为的精彩之处圈点出来,形成自己的批评,也为读者阅读文本提供指导。“圈点的批评指向,一是从叙事文学或戏剧文学角度出发的精彩之处,如推动情节发展的细节、显示人物性格、表现人物感情的语言和舞台动作,等等。另一指向则是文学化的语言。中国是诗的国度,传统诗词的语言风致往往是评点者不自觉的评论尺度,他们对戏曲作品中的丽词佳句总是欣赏不已,也就留下了大量的圈点符号。”[14]像“肠断云霓,泪沾红袖”这样富有中国传统诗词风致的佳句不仅被陈眉公圈点出来,评为佳句,也受到绘图者的关注,绘图者将这一诗词所表现的意境敷衍成图,并且将其题写为图记。文本中的关键情节或文笔精彩之处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评点者插图所选取的场景多与陈眉公所认为的“关目妙”处一致,插图题记也多取自陈眉公所圈点出的戏文,由此可看出绘图者与陈眉公对文本解读的统一。
(二)插图表现与评点思想暗合
《琵琶记》第三出“牛氏规奴”中塑造了一个生于富贵之家而谨守传统礼法的牛小姐形象。小姐贞洁无瑕,毫不为春色所动。而小丫环惜春却活泼灵巧,懂得欣赏春色,嬉戏消遣。[祝英台序]采用问答的方式描写丫鬟惜春与牛小姐的对话:
〔贴〕把几分春,三月景,分付与东流。〔丑〕小姐,如今鸟啼花落,你须烦恼些么?〔贴〕啼老杜鹃,飞尽红英,端不为春闲愁。〔丑〕你不闲愁,也还去赏翫么。〔贴〕休休。妇人家不出闺门,怎去寻花穿柳。〔丑〕小姐你不去赏翫,只怕消瘦了你。〔贴〕我花貌谁肯因春消瘦。
小姐不仅不赏春色,反而以极富道学气的口吻指责丫环。这一段戏文之后,陈眉公评点道:“小姐不惜春乎?”[15]对美好春色的欣赏以及对自己青春美貌的珍惜是年轻女子应有的心理特征,但受传统礼法浸濡的牛小姐却充当了道学礼法的代言者。推崇真性情,厌恶假道学是陈眉公的主导思想,也是其评点的特色之一。对此,崇尚真性情的陈眉公显然不予赞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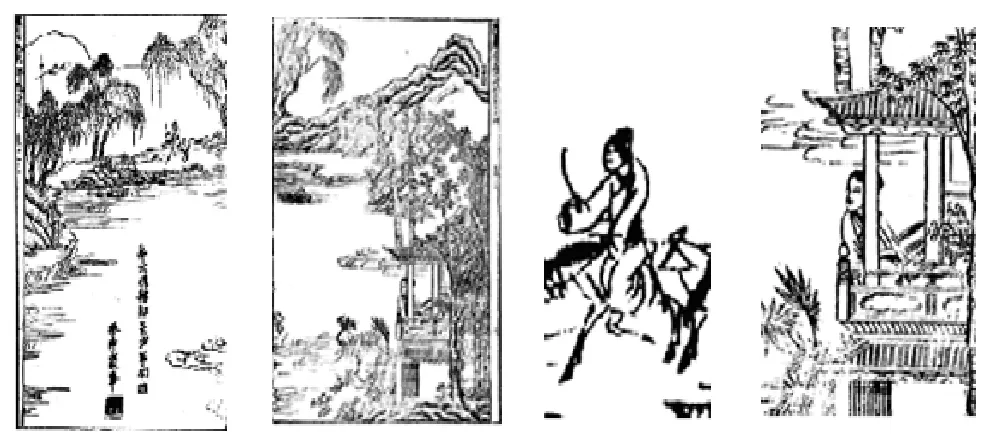
图3 《琵琶记》第三出“牛氏规奴”插图及其局部放大,摘自《不登大雅文库珍本戏曲丛刊》第12辑第18-19页。
与此出戏文相配的插图(图3)所画的正是一幅春日景色,湖水清浅,杨柳依依。一个坐在亭榭之中的年轻女子,正喜笑颜开地望着远处一个骑马的少年男子。插图题记:“柳丝雕鞍,都是少年闲游”[16]。此题记出自戏曲原文中丫环的唱词:“[丑]那更柳外画轮,花底雕鞍,都是少年闲游。”[17]绘图者没有画一个不出闺阁的道学小姐,反而画的是一个赏春惜春的美貌女子。这一女子可以解读为丫环惜春,其实解读为牛小姐亦未尝不可。正如陈眉公所评“小姐不惜春乎?”[18],思春之情人皆有之,难道小姐真如戏文中所说不惜春吗。插图正是对这一评点做了延展想象,与戏文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相悖,却与陈眉公的主情思想相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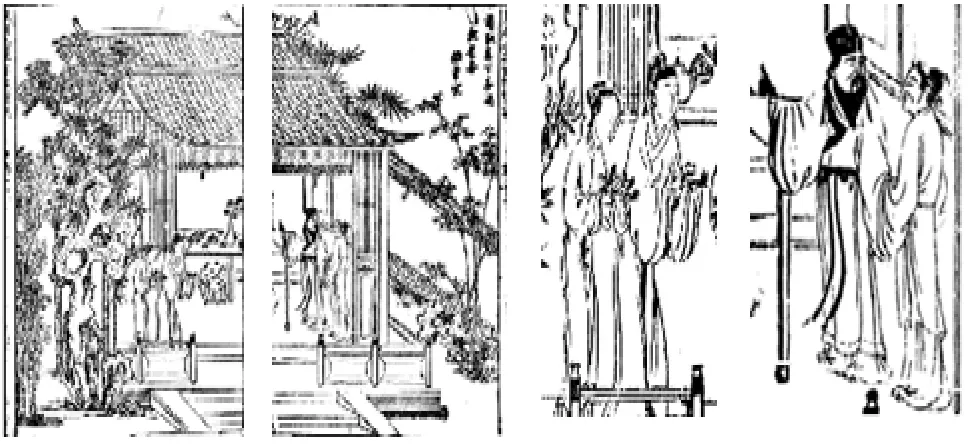
图4 《琵琶记》第二出“高堂称庆”插图及其局部放大,摘自《不登大雅文库珍本戏曲丛刊》第12辑第8-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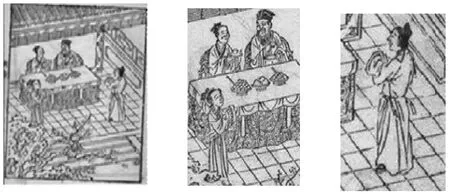
图5 《绣像第七才子书》第二出“高堂称庆”插图及其局部放大,清成裕堂刻本,第5页
再如《琵琶记》第二出“高堂称庆”,如图4。此出描写蔡氏一家欢合,蔡伯喈与妻子赵五娘相商为双亲庆寿,这本该是一幅高堂端坐、欢喜和谐之景。但与之相配的插图所画的是蔡、赵夫妻二人手捧着酒,在一旁俯首侍立,欲为双亲祝寿。两位老人却没有端坐在高堂之上,享用儿子儿媳的美酒,而是站在另外一边,似乎在商量什么事情。题记:“看取花下喜酒,共祝眉寿”[19],来自文中唱词“酌春酒,看取花下高歌,共祝眉寿”[20]。此出陈眉公批曰:“各还它本色,像个庆寿光景”[21]。“酌春酒,看取花下高歌,共祝眉寿”,是蔡、赵夫妻二人的真实心声,他们一心渴望养老奉亲,为父母祝寿,表达自己的孝心。蔡伯喈唱词云:“怎离却双亲膝下?且尽心甘旨,功名富贵,付之天也”[22]。然而,蔡公却一心想让儿子外出寻取功名,无心庆寿。蔡婆亦渴望家人团聚,尽心维护家庭的完整,不愿独子新婚不久又是在家有二老的状态下离家赴京。后文中,蔡公以求取功名为由逼迫蔡伯喈动身赴京赶考,蔡伯喈为父命尽大孝之道,最终离家赴京。蔡公、蔡婆、蔡伯喈、赵五娘各怀心事,并没有“花下高歌,共祝眉寿”的闲淡心情。画面虽是静态无声的,但通过人物的动作举止,却将人物内心所思所想表现得淋漓尽致。出批“各还它本色,像个庆寿光景”[23],是陈眉公对文本的解读,绘图者用图画的形式将这一批语所传达的情致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同为“高堂称庆”一出的插图,清代成裕堂刊刻的《绣像第七才子书》中的插图却是完全不同的表现。如图5,所画的是蔡公、蔡婆在高堂上端坐,尽情享用儿子、儿媳敬奉的肴馔美酒,蔡伯喈、赵五娘在堂下侍立。一家人面带笑容、喜笑颜开,正与文中所描写的“夫妻和顺,父母康宁。酌春酒,看取花下高歌,共祝眉寿”相统一,是一幅真正的合家团圆安乐庆寿的场景,不再如《六合同春》本那样“像”个庆寿光景。通过对比,《六合同春》本插图的绘制受陈继儒评点思想影响的痕迹十分明显。
(三)冲突与反讽:插图与评点在差异中形成新的意义
1.插图表现与评点矛盾
对于同一文本,评点者与绘图者的解读并不会是完全统一的,有时也会出现差异甚至矛盾之处。比如,《琵琶记》第五出“南浦嘱别”插图(图6)。图画临行前,蔡伯喈和赵五娘依依惜别的情景。题记“两下里传言慰别离”[24],由戏曲原文“从今后,相思两处,一样泪盈盈”[25]概括而来。但此出出批云:“只家中离别,夫妇相对流连耳。十里长亭便不通。”[26]从插图来看,画面中远处群山起伏,近处也是荒郊野外的景象,一条小路延伸通向远方。可以看出,画面中所显露出的一角亭台并非家中之亭台,而是十里长亭。绘图者并没有接受陈眉公的观点,画面依旧画的是二人在十里长亭离别之景。对于夫妻二人惜别的地点,戏曲原文中也并没有明确指出,究竟是家中离别还是十里长亭离别,绘图者与陈眉公分别作了不同的解读。戏曲文本是原始的文本,评点在对其批评的过程中融入评点者的观点,绘图者则结合自己的理解,对文本的内容做改变、拼接,形成插图。文、图、评三者之间的相异之处正是这种版本的价值所在,它给读者提供了新的视野,同时也激发读者的思考,由原文本之外而衍生出来的新的意义则由此产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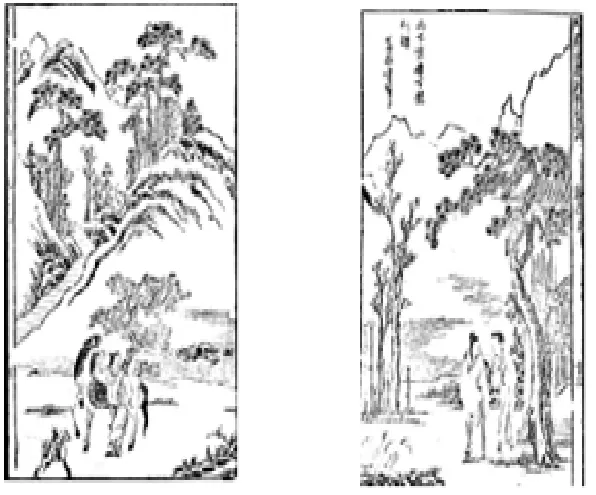
图6 《琵琶记》第5出“南浦嘱别”插图,摘自《不登大雅文库珍本戏曲丛刊》第12辑第30-3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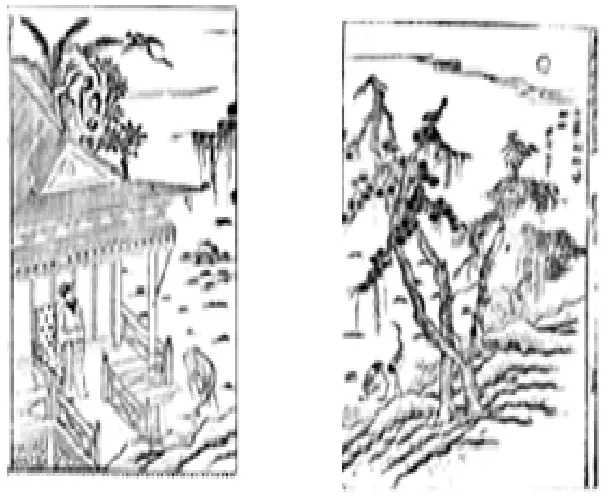
图7 《琵琶记》第31出“几言谏父”插图,摘自《不登大雅文库珍本戏曲丛刊》第12辑第370-371页
2.插图与评点形成反讽
何为反讽?“反讽的形式机制,是一个符号文本不表达表面的意义,实际上表达的是正好相反的意思”。[27]也就是说,反讽是表象与事实相反的一种表达方式。两个不相容的意义被放在一个表达方式中,用它们的冲突来表达另一个意义。这样文本就具有了两层意义:字面义与实际义。而在插图本这种文本、图像多媒介共存的艺术形式中,文本或评点与插图的意义形成冲突,从而在曲折的表达中获得了超越原有意义的反讽效果。
如《琵琶记》第三十一出“几言谏父”(图7),评点和插图便具有反讽的艺术效果。此出戏文主要写牛小姐得知蔡伯喈已有妻室,并且家中有年迈的父母之事,于是主动向父亲提出与蔡伯喈一同回家照顾他的父母。牛丞相丝毫没有矜怜之意,不许女儿前去。戏文直接暴露了牛丞相的丑态:“[外]休胡说!他既有媳妇在家,你去做什么?”[28]眉批曰:“真可恶”[29]。陈眉公在此出的眉批中多处使用犀利的言辞直接批判牛丞相。如“自家招赘蔡伯喈为婿,可谓得人。只是他自从到此,终日眉头不展,面带忧容,不知为着什么。”[30]陈眉公批曰:“岂不知不知乃是牛”[31]。后文“[外]他自有媳妇,你管他做什么?”[32]此处眉批曰:“他自有媳妇,你为何又把儿女嫁与他。伤风是牛家。”[33]陈眉公在出批中更是对牛丞相的行为表现出强烈不满:“解驳剴切,节孝双彰,无奈不入牛耳何!”[34]很显然,陈继儒在评点中直接点明牛丞相的丑态并强烈批判。然而,本出戏文所配插图并没有直接描绘牛丞相的“伤风”,而是画着牛丞相独自一人在亭台中站立,望着天上的一轮明月,若有所思,似带些伤感之情。插图题记为“女萝松柏望相依”[35]。题记实取自《琵琶记》第三十九出“散发归林”唱词:“[风入松慢]女萝松柏望相依,况景入桑榆。不种他椿庭萱室齐倾弃,怎不想家山桃李?叹当初,中雀误看屏里,到如今,乘龙难驻门楣。”[36]戏文流露出牛丞相有一种早知今日,悔不当初之意。如今,女终不可以为儿,婿终不可以为子,小姐执意要与蔡伯喈一同回去守孝,女儿、女婿都要离自己而去,自己“定要招蔡伯喈为婿,指望养老百年”的设想全然无法实现。此时的牛丞相不禁有悔过之意,又不免带着些许感伤。这幅插图所表现的情境实与此时牛丞相的心境相合,但此幅插图却是第三十一出的配图。陈眉公在评点中痛斥伤风自私的牛丞相,而插图却描绘了一个悔过伤感的牛相,插图所塑造的牛丞相越高大,他的伤风自私的行为就被反衬地越强烈。二者在鲜明的对比中形成互文,达到反讽的效果,呈现出一个血肉饱满的真实人物形象。
(四)增强与补充:插图也是评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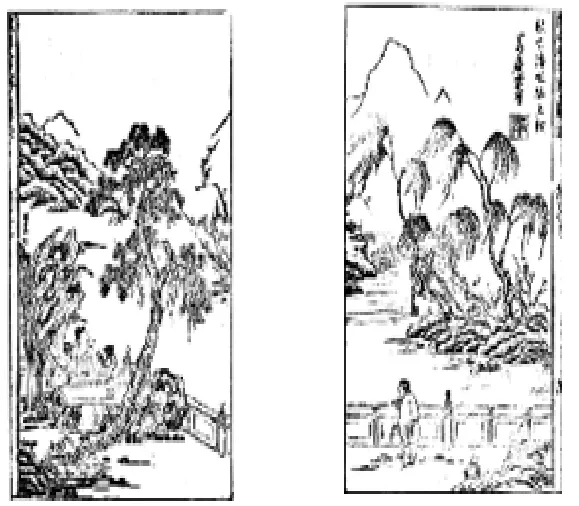
图8 《玉簪记》第6出“于湖借宿”插图,摘自《不登大雅文库珍本戏曲丛刊》第12辑第362-36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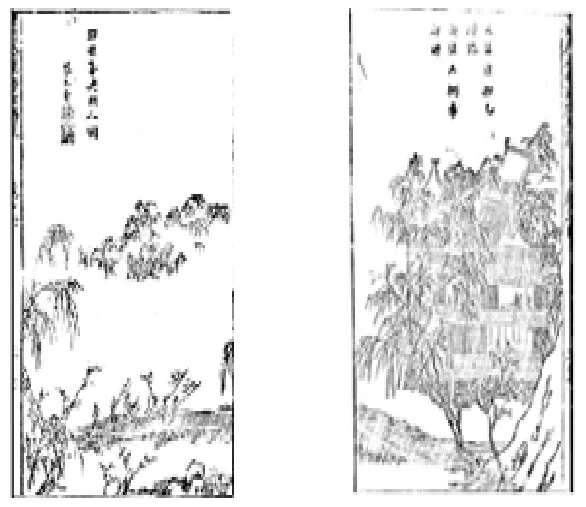
图9 《红拂记》第33出“天涯知己”插图,摘自《不登大雅文库珍本戏曲丛刊》第12辑第332-333页
插图所绘场景的选择以及插图中的题记实际上反映了绘工对文本的看法,是绘工对于文本的解读,也是以图像的方式对文本的评点。《玉簪记》第六出“于湖借宿”(图8),戏文写张知府隐瞒身份,扮成王公子前来女贞观借宿,在观中见到陈妙常,被其深深吸引。此出末句戏文“溪溜合松声,残霞弄晚晴。要知今日话,难尽此时情”[37],形象地传达出王公子在清雅的道观之中偶遇一心仪女子,心中欣喜而又意欲接近的难言之情。陈眉公对此诗的眉批曰:“诗中有画”[38]。而插图正是将此诗的意境敷衍成图,图画的背景清幽,远山起伏,杨柳掩映,一名男子在松树下抚琴。图中题记:“竹下清风琴上弦”[39],取自戏曲文本,原文为老旦唱词:“[长相思]昼幽然,夜幽然。竹下清风琴上弦。”[40]原文表现的是道观中出家女子的清净生活和心境,绘图者却将其移用来表现王公子之心境,实为对原文的一种加工,又与陈眉公的评点形成呼应。
插图题记大多是出自戏曲原文,或直接选用戏曲唱词,或对唱词加以概括而来。但也有少数题记并不是来源于文本,而是由绘图者自己所拟,这种类型的题记便表达出绘图者对文本的理解。如《红拂记》第三十三出“天涯知己”插图(图9),左半面题“归程喜与故人同”[41],摘自本出戏文结尾诗:“归程喜与故人同,指日铭勳共鼎钟。一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42]右半面题“天涯逢知己,归路遇佳人,何幸得此”[43],这句话在戏曲文本中找不到对应的语句,显然是绘工自己所题。绘图者通过题记这一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于戏文中男主角李靖人生际遇的评点,认为逢知己、遇佳人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幸运之事。在此,插图融入了绘图者对文本的看法,充当了评点的功能。
结语
插图所表达的是绘工对文本的理解,以图像的方式呈现,但并不与文本完全一致,而是对文本内容做了转换、拼接与改变的结果。评点是对文本中精妙动人之处、重要关目情节以及人物形象的品评。对于同一文本,不同的读者有着不同的解读,有共鸣也有冲突。绘图者与评点者也是如此,正是二者之间的共鸣与冲突形成了新一层的互文关系,从而使集“文——图——评”为一体的评点插图本与单纯的文本相比,具有了更为丰富的意义。
总体看来,《六合同春》的插图与评点形成互文关系,具体表现为插图营造的意境与评点相呼应、插图与评点思想暗合、插图与评点形成冲突与反讽。另外,插图充当评点的功能。“文本作为一个文本空间,其中各种潜在的联系无限制地增衍。从读者的视角看,这种文本乃是一种反思的空间,或反思的媒介。读者可以对它一步一步探讨,却无法穷尽。”[44]《六合同春》的插图、评点在同一个文本空间中不断增衍,互相补充,互相生发,从而产生巨大的阅读张力。这也是师俭堂本《六合同春》的独特魅力所在。
[1]马孟晶.耳目之玩——从《西厢记》版画插图论晚明出版文化对视觉性之关注.颜娟英.美术与考古.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643.
[2]徐嫚鸿.明代陈继儒戏曲评点本研究:以《六合同春》为讨论中心.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国立中央大学,2010:14.
[3][清]钱谦益,钱陆灿辑.列朝诗集小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637-638.
[4][明]陈继儒.陈眉公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6.
[5][明]王实甫撰,陈继儒评.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二卷).书林萧腾鸿刊本.现藏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库.
[6][明]陈继儒评.《鼎镌西厢记》二卷,11辑,收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编《不登大雅文库珍本戏曲丛刊》,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280.
[7][明]陈继儒评.鼎镌西厢记(二卷),11辑:278.
[8][明]陈继儒评.鼎镌西厢记(二卷),11辑:278.
[9][明]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11辑:75.
[10][明]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11辑:72.
[11][明]陈继儒评.鼎镌玉簪记(二卷),11辑:350.
[12][明]陈继儒评.鼎镌玉簪记(二卷),11辑:349.
[13]朱万曙.评点的形式要素与文学批评功能——以明代戏曲评点为例.中国文化研究,2002(6):34-40.
[14]朱万曙.评点的形式要素与文学批评功能——以明代戏曲评点为例.中国文化研究,2002,6:34-40.
[15][明]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12辑:20.
[16][明]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12辑:19.
[17][明]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12辑:20.
[18][明]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12辑:20.
[19][明]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12辑:8.
[20][明]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12辑:10.
[21][明]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12辑:12.
[22][明]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12辑:7.
[23][明]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12辑:12.
[24][明]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12辑:30.
[25][明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12辑:38.
[26][明]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12辑:38.
[27]赵毅衡.反讽:表意形式的演化与新生.文艺研究,2011,1:18-27.
[28][明]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12辑:167.
[29][明]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12辑:167.
[30][明]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12辑:166.
[31][明]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12辑:166.
[32][明]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12辑:169.
[33][明]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12辑:169.
[34][明]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12辑:174.
[35][明]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12辑:370.
[36][明]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12辑:211-212.
[37][明]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12辑:366.
[38][明]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12辑:366.
[39][明]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12辑:362.
[40][明]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12辑:364.
[41][明]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12辑:333.
[42][明]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12辑:331.
[43][明]陈继儒评.鼎镌琵琶记(二卷),12辑:332.
[44]张廷深.接受理论.四川: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