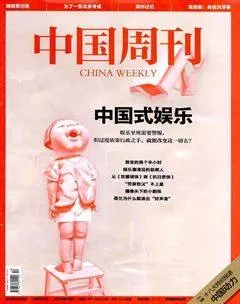慈善超市困局
2012-12-29叶宇婷
中国周刊 2012年10期

慈善超市该怎么办?是由政府控制,还是该民间发力,十年过去,依然没有清晰的答案。
中秋前,恩金通来到一家酒店“劝捐”。还没等他讲完,对方说,刚给别的爱心超市捐了月饼,“要不,我再向领导汇报批几盒给你们”。
“几盒月饼怎么分给几百户的救助对象?”恩金通离开了这家酒店。恩金通是北京市第一家爱心超市的负责人,2003年8月,朝阳区高碑店乡政府成立了这个超市。
九年前,恩金通可不需要向企业劝捐,他根本不用为物资发愁。
慈善超市乱局
高碑店爱心超市刚成立头几年,乡政府的大礼堂里堆满了捐赠衣服,“会都没法开了”。恩金通回忆,当时专门用来保管物资的有7间库房,共300多平米,最多时的捐赠衣物达十三四万件。
在我国,民政部门是募集物资的主要渠道,但募集物资容易,将物资送到最需要的人的手里,则是个复杂的工作。捐赠的衣物或被扔山沟里、垃圾中转站,或过于破旧,发生霉变,这样的事时不时会被媒体曝光。考虑到清洗、消毒、打包、运输,每个环节都需要成本,而这些成本往往比购买新物品高很多,这些原本以救灾名义募集的捐赠衣物很多被留在了募集地,免费发放给当地的困难群众。
高碑店爱心超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最初,超市的物资都是募集来,大量的物资曾经让这个超市非常红火。
“我们一打开门,他们队也不排了就往里冲,局面根本控制不了。”恩金通说。起初,特困群众凭民政部门发的“爱心救助卡”到爱心超市免费任选两样捐赠物品,先到先得。这样的结果就是先到的把大件物品拿走了,“他卖废品也要卖点钱啊”。
为了避免再出现哄抢,恩金通和同事走访附近的商店,对比着给捐赠物定价,“外面一个暖壶10块,我们就定5块”。“爱心救助卡”也规定了一定的虚拟金额,最初是一年300元。每周二和周五,特困群众可凭卡挑选物品。这样的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开始的一两年,朝阳区民政局的领导经常召集各企业负责人开会,号召其捐衣捐物,企业成为了爱心超市的最大捐赠方。
2007年以后,“领导没那么重视了,号召少了,捐赠衣物也没那么多了。”恩金通说,“企业也学聪明了,会上答应捐,下来也不兑现。”
2008年汶川地震后,企业都给灾区捐赠衣物,“库房和货架开始空了”。
一方面捐赠衣物变少,一方面被认定的低收入人员不断增多,由最初的几十人增加到了二百多户。
为了不让爱心超市“断粮”,恩金通开始到各企业“劝捐”,“哪儿都去,最远去了昌平、房山、通县”。刚开始“劝捐”,恩金通感到有些尴尬,“外企还好,中国企业大都不愿意聊”,恩金通没少吃闭门羹。
有次恩金通到朝阳蓝岛大厦募捐,进门就看到摆了一遛的各种募捐箱,“红十字会的,各家慈善机构的”。“我们这儿的募捐箱多了,成天给你们捐也不现实。”对方这样告诉恩金通。
在恩金通去企业“劝捐”后不久,朝阳区民政局开始拨款给爱心超市采购基本生活用品,以补充捐赠衣物的不足。
2012年9月,《中国周刊》记者在高碑店爱心超市看到,里面陈列的捐赠的衣服不足十件。货架上零散地摆放着米、面、油、盐等基本生活品。看起来,就像个不起眼的普通超市。
相比勉强维持的高碑店爱心超市,有些爱心超市则没那么幸运。2007年,通州关闭了一家爱心超市,原因是“没捐赠衣物了”。在北京市民政局的调研中,关闭的爱心超市不在少数,一些尚存的爱心超市也是名存实亡,几乎不开门。
这些的情形也在全国范围内发生,据媒体报道,山东济南的36家慈善超市,有21家先后关闭;江西南昌一家慈善超市开业11天就停业;海南海口2011年开设的几家慈善超市大部分时间都关门歇业。河南漯河31家慈善超市全部关门。
这个由政府大力推动的慈善项目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这要从慈善超市在中国的诞生说起。
“物理空间”
2002年,中国最早的慈善超市在沈阳诞生,当时名叫扶贫超市。其运作模式,和高碑店爱心超市一样,物资都来源于民政部的募集,政府以超市的形式将其发放给当地的贫困人群。
2004年5月,民政部下发了《关于在大中城市推广建立慈善超市的通知》。9月,又下发了《关于加快推广慈善超市和做好今年“捐助月”工作的通知》,慈善超市的功能被定为“把建立慈善超市与完善捐助接收站点结合起来”。
在民政部门的推动下,爱心超市在全国各地开始迅速推广开来。
民政部门募集物资的模式,很快就后续无力。北京调整了募集物资的使用办法,物资由各区捐赠中心的工作人员统一收集,然后由北京市捐赠中心集结运送到北京市的对口支援地。这样,北京的慈善超市没有了物资来源,后来建立的爱心超市多以政府采购,贫困人群凭“爱心救助卡”领取物品的形式存在。
为了保证民政部门设计的“把建立慈善超市与完善捐助接收站点结合起来”的功能,很多慈善超市会划出专门的区域,作为接受捐赠中心的衣物代收点。
北京的北下关街道慈善超市就保留着捐赠点,这家超市虽然临街,但没有明显的标识,超市面积较小,货架上多为米、面、油、卫生纸等基本生活用品,凭街道发放的“爱心券”领取。超市入口处有一个一米高的圆桶,用于放置捐赠衣物,桶内空荡荡的,超市工作人员说,它已经空置了好久。
“很多的慈善超市只是一个物理空间,它并没有很严格的制度设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贾西津教授说,大部分的慈善超市只是名义上的,只在捐赠者和受赠对象之间进行很简单的对接,并没有成熟的经营模式。
在北京,慈善超市的管理者也悄然改变,原本由民政局牵头建立的爱心超市被下放到了各个社区街道,由街道自行管理。“民政局只负责爱心超市的指导,不参与具体的管理工作。”北京市民政局捐赠中心一名工作人员介绍。
在记者的走访过程中,发现有些爱心超市就是原来街道的便民超市,只是改了名字,增加了“爱心救助卡”的使用。和高碑店爱心超市相比,这些爱心超市以街道负责人的名义进行了工商登记,对所有普通民众开放。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超市。
从仅针对贫困人群,到向所有人开放,这样的超市,如何体现它慈善的初衷?早期成立的慈善超市,似乎走上了一条死胡同。
不成功的市场化
就在北京市民政局把爱心超市下放到各街道,让其自行管理的同时,民政部开始酝酿推广慈善超市的新模式。
民政部从福利彩票基金中拨出1500万元,委托北京市民政局开展慈善超市创新试点,北京市选西城区作为试点区。这个试点最大的不同,是吸引企业加入。
这笔项目经费确实吸引了不少企业。2009年世纪盈通(北京)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开始和北京市民政局接洽,与此同时,物美超市、货栈网也在争取此项目。“当时为了挣钱嘛。”当谈及争取慈善超市创新建设项目的初衷时,世纪盈通公司的负责人徐明波坦言。
最终,民政局最终选择了货栈网,一家河北企业。
2011年,西城民政局在区社区服务中心(新街口街道)、德胜街道、什刹海街道、广外街道相继开设由区捐赠中心与货栈网合作的慈善超市。
民政局希望以企业化的运行,盘活慈善超市,实现“让慈善具备造血功能”的目标。“这是将市场化的模式引入慈善超市的运作,企业是想要盈利的。”北京市慈善超市创新建设课题组组长马仲良解释说。
但民政部门和企业之间的诉求差距甚大,“货栈网是想让民政局买它的系统,没想到最后被拉去搞经营了”,徐明波说,为了达成合作,民政局购买了货栈网的一套网上进货平台。可这套网上操作的进货平台,并不适合慈善超市的员工。慈善超市的员工多为社区内年龄较大,知识程度较低的“4050”人员,不适应网上操作。不合拍的环节不止如此,广安门外慈善超市的负责人梁志新说,货栈网的库房在昌平,运货到各个慈善超市,物流费是笔不小的支出。加上人工、水电等支出,慈善超市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货栈网)原以为政府会有补贴及相关政策优惠,但一直没有。”北京市慈善超市创新建设课题组组长马仲良教授透露。
今年年初,货栈网北京站关闭,正式退出慈善超市运营。货栈网退出后,徐明波再次看到了机会。世纪盈通以社会企业的身份接管西城区中心店,成为“试点中的试点”。
在这家慈善超市,不管盈利与否,世纪盈通会直接从每笔消费中抽出2%的金额捐给北京市民政局捐赠中心,收银小票上会直接打出:您此次消费为慈善事业捐款××元。徐明波认为这是他们区别于市场化运营最显著的一点,“捐赠金额逐渐增长,而且公开透明”。
“我们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要改变这样的状态只有靠规模化经营。”徐明波为慈善超市设计的一整套系统,可只能用于一家店。
截至目前,北京民政局还在与世纪盈通谈判,整个慈善超市项目是否交给企业做,仍未确定。
“政府一直就没有搞明白慈善超市是怎么回事,1500万就这样东用一点西用一点。”徐明波称自己已经陷得太深,“进退两难”。
“政府对社会企业还不了解,没把它提上议事议程,没有制定相应的政策。”马仲良教授认为这是政府没有最终拍板的原因。
停滞的政府之手
直接管管不好,与企业合作也在犹豫,北京市再次打出第三张牌——让协会出头运营。
2011年7月30日,媒体报道说,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北京市慈善义工协会正式成立,该协会成立之日即向公众推出了慈善超市项目,具体由西城区慈善义工协会管理运作。项目计划称,慈善超市由北京市慈善义工协会发起、统一管理,民政部门支持参与,通过募集社会捐赠资金,协会在社区建立实体慈善超市。
可过了一年多了,西城区慈善义工协会始终没能正式接管慈善超市,原定召开的全国慈善超市创新建设经验交流会也来开始。“我们一直在为接手慈善超市项目做准备,但不知什么原因,突然接到通知不做了。”曾在西城区慈善义工协会工作的高强透露。目前,这个协会处于停滞状态。
更吊诡的是,北京市慈善义工协会否认了与西城区慈善义工协会的关系。小小轰动的一次慈善超市的改革,成了一个迷案。
新的管理者又出现了,2011年10月,北京市慈善超市发展协会注册成立,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均为北京市民政局。协会工商登记注册了北京市爱心超市管理有限公司,拟负责慈善超市的具体运营。
这家协会成立整整一年了,却没有任何动作。记者就此事致电北京市慈善超市发展协会,对方以“一切还在筹备阶段”为由,拒绝透露更多。
至此,政府掌控的慈善超市,到底应该以什么模式运转,如何有效实现慈善功能,区别普通超市,仍然没有清晰的描述。
就在民政局的慈善超市频陷困境之时,在北京,一个健康的民间慈善超市模式在成长。
创办于2006年的同心公益商店通过向社会募集闲置富余物资,对可以再次使用的物品,经过维修、消毒等必要的处理后,低价卖给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的低收入人群,收入除去成本后全部用于打工者公益项目。
这个清晰的模式,与发源美国的慈善超市几乎完全相同。
2011年,同心商店在顺义、通州等郊区共计开到了10家,至少实现了10万元的盈利。
创办人王德志曾多次尝试将同心商店注册为社会组织,可一直未果。多次尝试无果后,王德志只好对同心商店进行了工商注册,自我定位为社会企业。可目前,官方并未对社会企业做清晰的界定,也不可能获得任何政府的扶持。
“要想让慈善超市更好地发展,以行政体制吸收和分配社会资源的方式应逐渐退出。”贾西津教授说。
对话马仲良
应由社会企业运营慈善超市
Q:《中国周刊》
A=马仲良(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北京市慈善超市创新建设课题组组长)
Q:在政府主导和市场化运营下的慈善超市频陷困境时,什么样的主体可以扭转这样的局面?
A:社会企业。
Q:“社会企业”在我国属于一个较新概念,你如何定义它?
A:社会企业是一种新型的企业,它仍具有企业经营的特点,要有投入产出,有企业式的管理和目标。它承诺并坚持不分红,资本不给投资者带来资本回报。投资者可以是政府、社会组织或个人,他们用自己的资本做公益。社会企业的工作人员是要拿工资和奖金的,要有保险和福利。
Q:社会企业管理下的慈善超市有哪些优势?
A:相比于政府,社会企业更善于经营。政府是一个整体,上级命令下级,下级服从上级,比较僵化、没有活力。老百姓的需求是多样的,而政府不善于多变,而且上下命令的传递是需要时间的。社会企业是一个独立经营的个体,很灵活,很多事不需要层层请示,是一种扁平化的组织。
带有经营性质的事情不应该由政府直接操作,而是应该委托给社会企业或社会组织来做。
传统企业有资本分红,它要通过资本分红的机制来吸引投资者,它必须把利润分红这块纳入成本,社会企业则不同。它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投资者不分红,这就大大降低了社会企业的成本,社会企业可以为社会提供低价的服务,这是传统企业做不到的。
Q:目前由社会企业来主导运营慈善超市,存在哪些困难?
A:大家对于社会企业还不是很了解,理论界还存在严重的分歧,没有达成基本的一致。政府还没有把社会企业提上议事日程,没有制定相应的政策。
慈善超市本身是一个较为新生的事物,政府做过一些行政化的探索,但很吃力,成本很高。后来又探索用市场化的方法解决,让传统企业来做。传统企业试过后也不愿意做,觉得老背着个包袱,又得不到利润分红。最后开始进行社会企业的探索,但具体怎么做也不太清晰。我们今年初拿出了一套成熟的方案,但让政府认可需要过程。
Q:美国好意慈善商店致力于提供就业援助服务,我国社会企业运营下的慈善超市的定位是什么?
A:我们正在做试点的慈善超有有两个目的,一是把社会上人们的捐赠收集起来,帮助捐赠人实现他们的捐赠愿望;二是扩大就业,安排一些在市场经济下就业困难的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