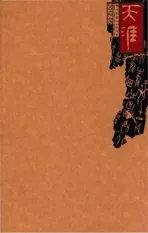新人文主义的建构
2012-12-22胡水君
胡水君
新人文主义的建构
胡水君
一般来说,从人出发,以人间事务为中心,以人的道德、能力、尊严和自由发展为价值准轴,重人力和人事而轻宗教,是人文主义的基本特质。从文化比较的角度看,人文主义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中西之别。
西方人文主义构成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之后形成的现代西方文化的主流。如果把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第一个发展阶段,中世纪的希伯来宗教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第二个发展阶段,那么,西方人文主义可被视为西方文化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它至今已经历近五百年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西方人文主义是对中世纪宗教文化的一次否定。尽管它也表现出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回归,但它与古希腊罗马文化也存在很多差别。对于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中国来说,西方人文主义可谓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化形态。
大体而言,西方人文主义表现出这样几个基本特点。一、摆脱宗教和神的束缚,从人出发并以人为中心来观察、思考和界定世界。二、承认意志自由,充分认可人的能力和尊严。三、扎根于自然世界和人的自然本性。四、在认知上,以人的经验和理性为判断根据。在西方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宗教文化逐渐走向衰落,历史上以宇宙秩序以及宗教、道德或自然义务为基点的伦理政治,最终转变为从“自然权利”出发的自然政治,旨在保护人权和公民权利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因此得以建立。不过,与以往古希腊、罗马文化以及中世纪的宗教文化对照起来看,西方人文主义也实际促成了自然权利与“自然法”以及神法的断裂、“意志自由”与“自然道义”的断裂、权利主体与德性主体的断裂、道德精神与民主法治的断裂。可以说,在造就现代政治法律文明的同时,西方人文主义附带着与之相关的“现代性”问题,如“自由帝国主义”、“做错事的权利”等,它因此也需要探寻新的出路,并不足以被视为一种终极的、更高级的乃至最高级的文化形态。
如果说,西方人文主义主要立足于人的身体、生理本性以及认知理性,那么,与之相对照,中国人文主义则一直表现出以人的道德精神、道德本性以及道德理性为基础。立足点或出发点的不同,使得中西人文主义呈现出发展路径的差异,这种差异并不能因为西方在现代的一时强势而被简单地归结为发展层级的高低之别。中国人文主义大致形成于周代,一直持续至今,但在近一百多年里受到西方人文主义的巨大挑战。
大体而言,中国人文主义表现出这样几个基本特点。一、非宗教性。在以儒教、道教、佛教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中,缺乏作为“第一主宰”的上帝观念,人自身一直被认为具有超凡入圣的超越性。因此,中国人文主义有时也被人称为“超越宗教的宗教”。二、内在超越和主体性。人被认为是天然具有善性、神性和佛性的主体。人与神、佛之间并没有严格的、不可逾越的界限,也不是上帝与选民的关系。只要努力,“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成佛。这是一种道德上的意志自由,它意味着人经过自身的努力可以改变在尘世的命运,而且这种能力是人本身完全具备的。三、公共责任。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源远流长的“天地万物为一体”、所有的人都与己相关的观念,并由此生发出“民胞物与”、“四海一家”的道德情愫。每个人被认为对天下人都负有仁慈的道德责任,而此种道德责任的实现实为人之为人的基本要素。四、德性认知。在经验和理智之外,中国文化中还包含着一种独特的“德性之知”。它是人在可感知的自然世界之外发现同样对人具有实际制约作用的道德世界、发现自身的道德“良知”的基本认知途径。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文主义所表现出的这些基本特质,尽管遭受西方人文主义的剧烈冲击,而且在构建现代自由主义民主政治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它们对于重建现代人的价值系统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在“古今中外”的时空背景下,现时代有必要结合中西人文主义之精华来形成一种新的人文主义。这样一种新人文主义旨在实现生理本性、认知理性、见闻之知、自然权利、民主法治与道德理性、道德本性、德性之知、“自然正当”、道德精神的衔接或汇通。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尚未完全形成自己的政治和法律发展道路之时,尤其需要这样一种融会古今中外智慧的新人文主义,以为其构建民主法治国家及其未来发展设定合理的理论基础。
回顾历史,不难看到,二十世纪是中国文化屡遭摧残、饱经风霜的一个世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国传统文化被长期置于“古今中外”和“海陆黄蓝”的简单对比结构中,由此形成了一种钱穆所说的“惟分新旧,惟分中西,惟中为旧,惟西为新,惟破旧趋新之当务”的文化观。在一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中,中国传统文化更是遭受前所未有的批判和否定,终致飘摇破败、花果凋零。可以说,在现实政治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冲击下,政治形势、社会功利乃至群情激奋明显盖过了对于根本道理的终极追问。
这种状况,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发生了一些改变。近二十年,是“冷战”结束后文化获得相对平稳发展的一个历史时段,其间不仅相继出现“国学热”、“人文精神”讨论、“传统文化复兴”等文化事件,而且,现代“人权”和“中华文化”在国家层面都得到了明确认可。在文化和理论界,一种试图彰显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文化自觉”正在兴起,立足普遍因素来承接融会“古今中外”、沿着中国文化理路来开拓中国的政道法理的文化姿态也日趋明显。总体来看,如果说中国近一个半世纪是外来文化大势涌入的“低谷”时期,那么,经历近二十年乃至以后更长的时期,中国文化可望以其择善处下、兼收并蓄而重现“百谷王”的态势。
在此现实条件和趋势下,沿着自身的文化理路、历史脉络和社会现实来重构据以长远发展的道统、政统、法统和学统,可谓近代以来的中国至为基本的历史任务。套用中国“内圣外王”这一传统理论框架,此任务归根结底涉及的是“内圣”与“新外王”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人的道德精神与民主法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关系问题。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一个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普遍问题。在通向现代民主宪政的道路上,是完全舍弃“内圣”来开“新外王”,抑或与传统思路一样秉承“内圣”开“新外王”,还是在“内圣”与“新外王”之间建立某种共生并济的外在衔接,是这个时代迫切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完成现时代的历史任务,至少需要从价值、政制、法律、学术,或者,道、政、法、学四个方面作根本考量。
在价值方面,需要处理好道德精神与自然权利的关系。自然权利,是现代政治和法律道路的新的出发点,也是西方人文主义在价值层面的集中表现形式。从自然权利出发的现代政治,明显有别于以德性或道德、宗教义务为基点的传统政治。在很大程度上,现代权利政治在有效保障人权和个人自由的同时,也呈现出一些与“现代性”相关的政治和道德问题。就政治而言,权利发展在国内层面与现代国家权力的精微伸展相伴随,在国际层面则与“自由国家主义”乃至“自由帝国主义”相伴随,这使得人权保障在全球范围仍然面临现实困境。就道德而言,在“意志自由”以及“无害他人”的自由主义原则的主导下,权利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伴随着人的道德精神的衰落,由此呈现出一定的道德危机。在这些方面,中国人文主义表现出广阔的作用空间,中西人文主义之间也呈现出实现历史结合的可能性。从中西人文主义相结合的观点看,现时代正可以也需要同时立足人的生理本性和道德本性,来重构现代民主法治、权利政治的道德根基,开拓一种作为道德责任或义务的人权,实现同为普适之道的人权与德性的融合或衔接。如此,既避免单纯从人的道德本性和道德理性出发而抑制人的生理本性和认知理性,乃至抑制自然权利和民主法治生发的传统伦理道路,也避免单纯从自然权利出发而完全剥离人的道德精神的“单向度的”现代发展道路。事实上,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自然权利与自然法、自然权利与自然正当之间的缝隙或断裂,在西方被更多也更深刻地意识到,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重构人权和权利的道德根基的历史需要。倚重丰厚的道德人文资源,实现道德精神与自然权利的历史衔接,对于处在发展中的中国来说,构成了一种历史机遇。
在政制方面,既需要处理好“道”与“政”的关系,也需要处理好“政”与“治”的关系。中国传统政治被梁启超、钱穆、牟宗三等人,或者判定为有“道”无“政”,或者判定为有“治道”无“政道”。“政”与“道”、“政”与“治”之间的关系在当前仍可谓中国政治发展的两个关键。从“政”与“道”的关系视角看,现代政治并不扎根于仁义道德,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非道德乃至反道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要表现为一种自然政治。此种政治迥异于道德与政治同构的中国传统政治,也与秉承内圣开外王的传统政治哲学背道而驰。就近一百多年的近代进程而言,构建和完善现代民主之“政”仍构成中国的重要历史任务,而在此过程中,如何将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重新结合起来,实现民主政治与仁义道德在当代的融合或衔接,是需要深入思考的理论问题。从“政”与“治”的关系视角看,尽管很早就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但民主政制的构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长期被搁置,对“治”理的擅长在很大程度上也减弱了对民主之“政”的需求,由此长期存在着一种以“治”统“政”的格局。就此而言,如何从社会“治”理最终转向民主之“政”,实现现代民主政治与传统民本治理的合理结合,也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中国语境下的“道”与“政”以及“政”与“治”这两层关系,与中西两种人文主义有着内在关联。如果说,政制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主要是与西方人文主义相联系的历史现象,那么,中国人文主义在历史上则更多地体现于治道与治理两个方面。就此而言,无论是在“道”的方面实现自然权利与自然正当的结合,还是在“政”的方面实现民主政治与仁义道德、民本治理的衔接,都需要在中西两种人文主义之间做出协调和融会。
在法律方面,需要理清“法治”的道德、功利、治理、政制四个层面,并摆正四个层面的关系。从中国自古以来文治武功的实际发展看,法治在中国大致出现过三种历史形态。一是作为武功的法治。这是人们所熟知的法家法治,它以严刑峻法、信赏必罚、通过法律追求国家富强为重要特征。二是作为文德的法治。这在历史上主要为儒家所主张。儒家法治的精髓在于“德主刑辅”,把道德放在第一位,把法律放在第二位。三是作为宪政的法治。这是以通过政治和法律制度设计来有效约束和规范国家权力或政治权力,保障人和公民的权利为基本特征的民主法治,也是中国近代以来努力寻求建立的一种法治。如果以道德、功利为纵栏,以政制、行政为横栏,那么,大体可以说,作为武功的法治是一种功利、行政层面的法治,作为文德的法治是一种道德、行政层面的法治,作为宪政的法治或民主法治是一种功利、政制层面的法治,也可以说是“新外王”层面的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儒家法治蕴涵有中国人文主义的要素,而民主法治起初则是主要在西方人文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它以启蒙时代以来的现代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为理论基础。从这样一种比较看,在很大程度上,民主法治忽略了道德层面,而法家法治和儒家法治则忽略了民主政制层面。中国目前的法治实践,事实上融合了这三种法治的某些特点。同民主之“政”相联系,现代中国的要务正在于拓展政制层面的法律,着力打造中国自古以来长期缺乏的政制层面的法治。而在此过程中,法治各个层面之间的关系也是需要理清和协调的,以使一些传统的治理和道德因素也得以涵容于作为宪政的法治之中,发挥其积极功效。在形成中国法治道路的过程中,从政治或宪制层面建立起民主法治是首要的,同时,为避免重走法家法治的老路、防止西方人文主义的某些“现代性”后果,在新人文主义的基础上加强道德对政治和行政的影响、实现道德精神与民主法治的现代连接也是必要的。
从新人文主义的视角看,现时代需要一种新的法治理论——法治的道德理论。熟为人知的是,道德在现代社会与政治、经济、学术等系统发生了很大分化,这种分化也发生在道德与法律以及权利之间。讲法治的道德理论,并不意味着通过法律来强制执行道德伦理,或者像历史上所做的那样,通过政治和法律力量来建立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和伦理秩序,而是要在道德精神与民主法治之间建立连接。具体来说,受西方人文主义影响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构成了民主法治的理论基础,它是立足于人的身体、自然本性和认知理性建立起来的;而按照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政治必须基于人的道义、道德本性和道德理性来构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从“内圣”开“外王”。在新人文主义语境下,这样两套政治思路可以结合起来,也就是同时立足人的认知理性和道德理性来构建民主法治。一方面,基于人的身体,建构权利主体、市场法则和宪政制度,另一方面,基于人的道义,建构德性主体,建立以人的道德精神为核心的价值系统,并由此让道德通过作为德性主体的人在市场竞争、民主法治以及国际政治中发挥积极功效。这样有助于把人从权利角逐、市场竞争、政治斗争和法律纠纷中解脱出来,使民主法治成为精简有效机制,同时也有助于人找寻到生命的终极意义,成为真正的主体,使法治成为蕴含人的道德精神的法治。
在学术方面,尤其需要协调好“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关系。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明显有一个从“德性之学”、“通人之学”转向“专门之学”,从“六艺之学”、“四部之学”转向“七科之学”的历史变迁过程。在此过程中,科学知识以及科学认知方式明显占了上风,以至于价值和道德领域也受到了并不完全适用于该领域的科学认知方式的影响乃至支配。在现代社会,欲重建现代人权、民主、法治以及现代学术的道德和精神基础,首先必须区分“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及其各自适用的领域,以使价值系统和知识系统并行不悖。就此而言,重开中国的学统,未必意味着从中国的道德知识体系中开出科学,而在于在现代科学研究中,存留并发扬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德性认知”方式,由此为开辟价值之源、挺立道德主体提供可能,也为在现代民主法治体制下弘扬中国文化所蕴涵的道德主体精神、公共责任精神和内在超越精神创造条件。
胡水君,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法律的政治分析》、《法理学的新发展:探寻中国的政道法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