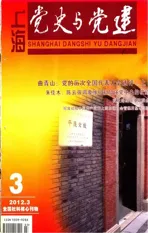关于对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研究
2012-12-22吴海勇
● 吴海勇
关于对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研究
● 吴海勇
本文梳理了上海执行部历史研究发展的三阶段,指陈当代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对研究前景作出积极展望。
国共合作;上海执行部;历史研究;综述
一、从往事追述到史料钩沉,促成专题研究在新时期的展开
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国国民党“一大”后,决议在上海、北京、汉口等地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以下简称“上海执行部”)于1924年2月25日在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召开了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并定于3月1日正式办公。到1925年底,该部办公地被西山会议派强占,国民党中央遂终止上海执行部行使职权。经历近两年风雨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划上了句号。
由于上海执行部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在“四一二”后建立起来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此有所忌讳,此后产生的国民党党史著述均不见述及上海执行部,直到国共开启了第二次合作,才在1940年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党史纪要》中略有述及。[1]偶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两篇报章短文,一为1936年的《小史料:上海执行部之驱逐共党》,另一为1938年的《毛泽东在上海执行部时代》,终究改变不了上海执行部被打入历史“冷宫”的状况。随后台海两岸长时间处于紧张对峙状态,很长一段时间内,上海执行部历史研究处于沉寂状态。海峡对岸,台湾学者对上海执行部历史的冷落持续,1994年出版的煌煌巨制《中国国民党史述》中对于上海执行部也仅一笔带过。[2]
两相比较,中国大陆学界对这段历史的关注趋向回暖的走势。大陆学界对上海执行部历史的涉及,至迟可追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梅龚彬曾被上海执行部聘为宣传委员会委员,他有关五卅运动的回忆自然地提及了上海执行部。[3]1963年,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有关同志还对曾任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的张廷灏进行了访谈。[4]然而,就相关史料的公开与专题研究而言,还是要等到改革开放新时期。
1980年《新文学史料》第1期刊载茅盾的《文学与政治的交错:回忆录(六)》,述及上海执行部的建立、管理区域范围,以及机构设置与人员组成,提到列宁追悼会、平民教育工作,实际上揭橥了共产党人在上海执行部相关运动中的努力。同年,罗章龙在某座谈会上也深情忆起上海执行部的往事。[5]
以此为起点,有关上海执行部的史料在短期内层见迭出。《历史研究》1981年第4期刊载了《吴玉章自传》,其中提到作者在“五卅”后,受上海执行部提议回川组织国民党(因四川国民党为西山会议派石青阳、谢持等所包办),改组当地国民党,选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等往事。1982年出版的《广东文史资料》第37辑系“黄埔军校回忆录专辑”,其中不乏黄埔人对当年赴上海执行部参加黄埔军校入学考试的回忆,特别是郭一予《我对黄埔军校的片断回忆》还提及了毛泽东对报考人员的接待。[6]1983年初,由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研究资料》,将该馆收藏的1924年2月至3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次至第四次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油印件)全文刊印,并作“编者按”介绍时代背景。3月,上海历史研究所派人进京找罗章龙访谈,相关内容发表于《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4辑,内含上海执行部的史事。[7]
1984年,《党史资料丛刊》第一辑增辟现代史资料栏,即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资料专辑为一通“威风锣鼓”,集中发表了1963年访谈张廷灏的整理稿《回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刘重民1926年的《上海党务报告》(部分)与任武雄的《关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后殿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史料选辑”,系从当时的上海《民国日报》、上海执行部印发的传单以及上海执行部内刊《党务月刊》中摘出。同年稍后,罗章龙的《椿园载记》出版。该书专设有“上海执行部国民党主持人”一节,[8]提供了更多的历史细节。年初,《团结报》发表罗章龙回忆上海执行部合影的文章,[9]客观上为该书的问世作了前期宣传。
随着相关史料的披露,上海执行部研究随之起步。在这一领域,任武雄的研究工作涉足较早。他早在1963年就参与了对张廷灏的访谈工作。多年在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收集的相关史料,为其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任武雄发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10],就有所涉及上海执行部。1984年《党史资料丛刊》第一辑中,他发表了《关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次就此展开专题论述。同年,他又发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一文,文字更详,且首次采用了1983年对丁君羊的访谈材料。[11]
二、20世纪最后15年上海执行部的相关研究概况
1985年后,任武雄继续在上海执行部的研究领域扩大影响。比如,1985年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五卅运动的发动》,1987年发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右派在上海的斗争》,1989年发表《国共第一次合作在上海的活动》,皆设专节论及上海执行部。[12]1993年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任武雄接连发表了《毛泽东在中央局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毛泽东早年在上海的革命活动》、《毛泽东早期在上海的革命活动大事年表》,均涉笔上海执行部;[13]另有“任止戈”署名文章《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14],亦出自任氏之手。
任武雄的坚持,使其处于上海执行部历史研究的前沿位置,相关的研究也弥补了同时期权威党史部门的不足。在他的努力下,上海执行部历史得以进入上海地方党史。1989年问世的《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收录了相关内容。1999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史》出版,其中“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章节即为任武雄受邀执笔,且以上海执行部为主打内容。这是上海执行部进入中共上海地方党史正本的开始,同时也代表了该研究在20世纪末的水准。
在20世纪最后15年间,对于上海执行部研究具有实质性助推力的还来自于该专题之外,主要有:中共早期人物研究的进步、民国历史研究的发展、相关回忆文章的发表以及民国人物日记、苏联解密档案等相关史料的整理出版。
中共早期人物研究方面,恽代英、向警予、侯绍裘等人的研究在20世纪的最后15年间皆有进展,其中不乏与上海执行部相关的内容。特别是何先义等人整理的《向警予同志生平事迹年表》,有关向警予任职执行部妇女部后的内容,[15]皆有补于上海执行部的历史。
民国史方面,国共合作史的一些专题亦有助上海执行部历史研究。如第一次国共合作在苏浙皖等地资料的汇编出版,提供了上海执行部职责范围的史料。曹力铁的《国民党在五卅运动中的作用》,对五卅运动中的上海执行部运作多有揭橥。[16]附带提及,这阶段学术界有关张静江、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叶楚伧等国民党人物的研究也有所进展,虽深度与针对性有限,但亦有助于对上海执行部历史的了解。
回忆文章方面,熊辉的 《党的老朋友——喻育之》[17]、郝长兴的《先父郝兆先的早期革命经历》[18],分别述及喻育之和毛泽东在上海执行部的经历,为上海执行部研究提供有意义的历史细节。关于对上海执行部任职的国共双方要员留下的唯一合影中人员的辨认亦有进展。周氏后人指出,合影后排右一原认为是戴季陶,实为其先父周佩箴,进而又指出中排左二为其伯父周颂西。[19]
这一时期,民国人物日记、苏联解密档案等相关史料相继整理问世。原受命负责上海执行部工作的邵元冲虽终未赴任,但一直身居要职,不仅见证了国共相争,而且后来还成为西山会议派的成员,成为国民党“分共”的重要推手之一。1990年出版的《邵元冲日记》中不乏与上海执行部直接相关的内容。[20]20世纪末,联共(布)与共产国际解密档案在中国翻译出版,其中,黄仁事件后(档案编者时间判定有误)中共中央写给鲍罗廷的信,揭示了国共在上海执行部角力方面的重要内幕,[21]绝对不可轻忽。
三、21世纪以来相关研究的突进
步入21世纪,有关上海执行部的宣传与研究齐头并进,前景更趋看好。在宣传方面,除报刊发表的若干宣介文章之外,相关内容集聚于毛泽东类专书上。2003年出版的马建离《毛泽东与国共关系》,专设章节“活跃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22]。2006年张万禄的《毛泽东的道路:1921-1935》,亦有专门章节“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的日子里”[23]。2009年6月,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举办“永恒的丰碑——纪念孙中山先生文物文献展”,展出了上海执行部的若干手稿、信函、电文、薪资册等,加上媒体的宣传报道,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兴趣。
在学术方面,上海执行部研究的突进愈见明显。主要有三:
一是对“环档”等资料进行探宝式发掘与初步解读。1930年初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以下简称“党史会”)成立后,对存放于环龙路44号的档案(简称“环档”)进行过接收与整理。[24]尔后,“环档”等档案随着国民党政权渡海去了台湾,最终入藏国民党党史馆。中国大陆学者对台湾馆藏“环档”等史料的探寻,实际上始于20世纪末。杨天石到台湾查阅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案早于1996年,相关文章发表则始于2001年,[25]对大陆学者无疑具有示范作用。2002年,史洛对“环档”的一份上海执行部经费收支表进行了专门分析。[26]2003年,田子渝发表《在台北发现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两份史料》,其一为毛泽东写于1925年底的《关于上海〈民国日报〉审查结果报告》(“汉档”),涉及上海《民国日报》在1924年的劣迹,[27]存录了毛泽东当年任职于上海执行部时期的记忆。同年出版的深町英夫专著引用了《中央宣传部部长毛泽东上中执会函》(1925年12月26日,“汉档”),矛头也指向上海《民国日报》[28],与上一档案可以合观。而杨天石发表于同年的《毛泽东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则堪称运用“环档”研究上海执行部的典范之作。[29]2005年发表的梁尚贤《台湾国民党档案中的一组重要史料》,钩沉出一份1924年廖仲恺发给上海执行部胡汉民的密电文。[30]同年刊发的田子渝《1995年至2005年宣传、研究恽代英新成果评析》,又钩出1924年至1925年恽代英任职上海执行部时期的3封信函。[31]青年学者苗青的《国共合作见证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对新近展示的上海执行部薪资册进行分析,[32]在学术上可谓预流。
二是历史亲历者的记录、事迹继续得以出版与披露。李晓光《怀念父亲李宇超》[33]、喻育之《百岁自述》[34],分别涉及曾任上海执行部宣传委员会委员的李宇超和上海执行部干事喻育之的事迹。2007年,《谢持日记未刊稿》得以付梓出版[35],为上海执行部历史研究又增添了一份亲历者的记录。
三是国共合作史、西山会议派等研究取得长足进展。2001年王奇生的《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36]和2002年杨奎松的《“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37]俱为长篇大论,有新的创见。杨奎松后又撰写出版了《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38]。此外,曾成贵《中国国民党汉口执行部解析》接通了上海执行部拓展职责、兼管两湖的历史。[39]李攀的 《上海国民党基层组织研究——以1924-1927年为界》,从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上海党建角度透视了上海执行部的运作。[40]对于西山会议派的历史,中国大陆学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所涉足,新世纪初尚红娟的相关研究成果具备了学术前沿水准,[41]上海执行部历史研究多可参考。①
四、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有关上海执行部的历史研究以中国大陆学术界为主,且明显呈现出三阶段的特点。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以大陆相关知情人的历史追忆与史料公开为先导,上海执行部研究迅速跟进,清理出大体史脉,此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1985-2000年这15年间,对既有研究成果进行了交叉专题的整合,并最终实现了经典化重写工作,使上海执行部历史写入上海地方党史正本。此外,相关学术研究的进步,以及有关史料的披露,亦对上海执行部历史研究有积极意义,只是未能为上海执行部历史研究及时吸纳。21世纪,上海执行部研究进入第三阶段。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进一步缓和,始于20世纪末的大陆学者赴台湾查档收获在此阶段得以发表,由此带动新一轮的赴台查档热潮。对台湾藏“环档”、“汉档”等档案的发掘利用,一时间较其他史料的发掘与相关研究的进展,之于上海执行部历史研究似更具学术推动力。
历史研究必须建筑在丰厚史料的基础上,新史料的发掘每每能推动学术研究的突破,当代学者对台湾档案的兴趣即基于此,这对于史料较为稀缺的上海执行部历史研究来说更是如此。然而,倚重“环档”不应偏废对大陆史料的发掘运用。事实上,就上海执行部专题而言,当代学者对大陆史料的了解多仅限于第一阶段成果,甚至连这都未必尽数掌握。此外,上海执行部历史研究要实现突进,还应即时吸纳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赋予此专题以新的视域。唯有如此,上海执行部历史研究方能走出低水平重复的层级。
就近期而言,台湾相关部门不允许查档者对“环档”、“汉档”等档案进行复印,给大陆学者赴台查档、全面掌握这部分资料增加了困难,这成为上海执行部历史研究的瓶颈问题。在大陆学界努力推进上海执行部历史研究的进程中,真诚希望台湾学者能够加盟到相关研究中来,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为人类社会存一份历史本真,这理应是中华学人的共同追求。
[1]邹鲁.中国国民党党史纪要[M].重庆:黄埔出版社,1940.148.
[2]李云汉.中国国民党史述(第二编)[M].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94.
[3][10][11][12][13]任武雄.党史研究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00,201-212,200,254-256.260-279.213-217,228-239.330-331.342-344.
[4]张廷灏.回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J].党史资料丛刊,1984(1).118.
[5]黄启权.王荷波传[J].党史研究与教学,1983(7).
[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广东文史资料(第37辑)[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73.
[7]罗章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国共合作[J].党史资料丛刊,1983(4).
[8]罗章龙.椿园载记[M].北京:三联书店,1984.296-303.
[9]述直.从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谈起:罗章龙回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 [N].团结报,1984-1-7.
[14]任止戈.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J].党史研究资料,1993(11).
[15]何先义,唐德佩,何先培.向警予同志生平事迹年表[J].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3).
[16]曹力铁.国民党在五卅运动中的作用[J].近代史研究,1989(3).
[17]熊辉.党的老朋友──喻育之[J].湖北文史资料,1994(1).
[18]郝长兴.先父郝兆先的早期革命经历[J].江淮文史,1995(2).
[19]陆米强.一帧国共两党成员合影照片引出的故事[J].上海档案,1998(4).
[20]王仰清,许映湖.邵元冲日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2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535-536.
[22]马建离.毛泽东与国共关系[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3.
[23]张万禄.毛泽东的道路:1921-1935[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24]陈鹏仁.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党史史料编纂工作 (上册)[C].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9.61.346.乔宝泰.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党史史料编纂工作(下册)[C].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2000.381.387.593.
[25]杨天石.《瞿秋白的声明》与国共两党的“分家”风波——读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档案[J].党史纵横,2001(12).
[26]史洛.账单里有文章[J].档案与史学,2002(5).
[27]田子渝.在台北发现的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两份史料[J].中共党史研究,2003(5).
[28]深町英夫.近代广东的政党·社会·国家:中国国民党及其党国体制的形成过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52.
[29]杨天石.毛泽东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J].百年潮,2003(6).
[30]梁尚贤.台湾国民党档案中的一组重要史料[J].百年潮,2005(4).
[31]田子渝.1995年至2005年宣传、研究恽代英新成果评析[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5(5).
[32]苗青.国共合作见证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J].世纪,2010(2).
[33]李晓光.怀念父亲李宇超[J].炎黄春秋,2007(9).
[34]喻育之,肖志华,施裕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要事见闻录[J].武汉文史资料,2011(3).
[35]谢持.谢持日记未刊稿[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6]王奇生.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J].近代史研究,2001(4).
[37]杨奎松.“容共”,还是“分共”? ——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J].近代史研究,2002(4).
[38]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9]曾成贵.中国国民党汉口执行部解析[J].民国档案,2009(4).
[40]李攀.上海国民党基层组织研究——以1924-1927年为界[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8.
[41]尚红娟.革命党精英在联俄容共后的蜕变—西山会议派之再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8.
注释:
①以上仅就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国知网”收录的学位论文)展开综述,有关职能部门的内部研究报告暂不在论列,无所新见的专题论文更不赘言。
D231
A
1009-928X(2012)03-0014-04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副处长
■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