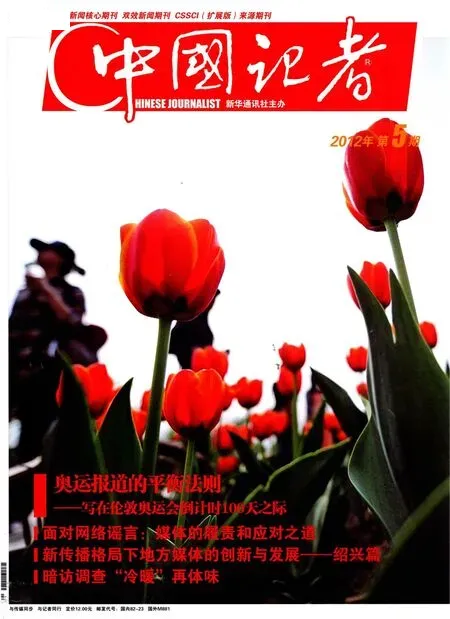永恒的追求——随李从军同志采写《永恒的召唤——雷锋精神世纪交响曲》的感悟
2012-12-21□文/赵承
□ 文/赵 承
编 辑 张 垒 leizhangbox@163.com
《永恒的召唤——雷锋精神世纪交响曲》(下称《召唤》)播发一月有余。时至今日,人们仍从不同角度对《召唤》作出自己的解读。
媒体受众说,这是一首新时代的《雷锋之歌》;新闻理论工作者说,这是一篇全方位创新的经典之作;雷锋精神研究专家说,这是一部雷锋精神的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家说,这是一段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录……
作为其中一个亲历者,今天重新翻阅李从军同志在采写过程中近五万字的谈话笔录,品味前后十余次修改的酸甜苦辣,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回苦思冥想,多少次峰回路转——回荡在胸中的那段难忘经历,就像一部孕育生命的交响,交织了希望、失望,乃至绝望……
在从军同志的引领下,最终在回旋激越的碰撞中,在超越自我的激励下,演绎出一曲昂扬的旋律。
那是一个永恒的召唤,它召唤着我们:勇于变革,敢于创新,坚定地朝着更高的目标迈进,谱写出贴近群众思想的新闻精品;那是一个永恒的追求,它激励着我们:不畏险阻,永远攀登,勇敢地担当起历史赋予新闻人的重任,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闻经典。
思想的苦旅
一个多月来,脑海里时常涌动着这样一个场景:
“看到大山极力地阻挡着江水,江水猛烈地要冲破大山的阻拦,就是一首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此时此刻,自己仿佛也融入江水当中,想和江流一起冲破大山向前奔腾。江水愤怒着、咆哮着、冲撞着,有时又无奈地回流,但最终冲破山峦叠嶂。过了三峡,豁然开朗,一泻千里。猛然地,想起辛稼轩的词: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那是采写过程中,我们濒临崩溃的情绪下,从军同志向我们讲述的30年前他过三峡的一段感受。
跟随从军同志采写《召唤》的过程,何尝不是一段过三峡式的思想苦旅。
在被通知参与采写之初,我不解:从军同志为何要亲自写这样一个选题——雷锋这棵“老藤”上能盛开出新鲜的花朵吗?
去年的11月21日,第一次碰头会。从军同志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给自己出了一道难题。他这样对我们说:“自从决定写这篇稿子,就觉得在面前横着一座难以跨越的山峰。但追求精品的过程,就是不断攀登、不断超越自己的过程。用雷锋精神审视观照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回答当代中国人追求怎样的生命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这是我们作为新闻人的担当。”
普利策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了望者……”
从军同志带领我们登上“船头”,目光投向了“大海”——
“雷锋精神十分丰富,什么是这个世界最急切的呼唤?我认为,当代中国呼唤的最强音是雷锋对生命和幸福的价值追求,是人与社会、与他人关系的价值选择。”
他将雷锋精神的实质概括为:对国家、对人民、对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对需要帮助的弱者,满怀爱心,施以善举(后改为“真诚奉献”),并从中获得人生价值的实现和幸福愉悦的满足。
他对这种精神做了深刻的哲学分析:“这种幸福在雷锋那里达到了纯粹的境界,使他完成了人生价值由有限到无限,由普通到高尚,由短暂到永恒的本质性升华。”他顺势提出了高更那永恒的三个疑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从军同志曾在自己的哲学专著《价值体系的历史选择》中有过这样的论述: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追求是人类社会演进的精神冲力。
“人,为什么而活着?”——
显然,从军同志将雷锋精神放在人类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去分析和追寻。
立意的高远,哲学的思考,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文章的思想确立了,如何朝着思想的目标前进?
未及深思,我们便一头扎进了采访。
然而,60多天的采写过程中,那种徘徊于丛峦叠嶂中的左冲右撞,那种寻而不得的痛苦行程,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与张严平、肖春飞我们兵分三路——我去了辽宁抚顺,那是雷锋战斗和牺牲的地方。
隆冬季节里,辽宁分社社长马义做了周到的安排,常务副总编王振宏此后的数日里一路陪同采访。
抚顺市委对此极其重视,先后召开了两场雷锋精神座谈会。坐在雷锋精神研究专家,学校、公安、武警和企业方面的代表中,我认真倾听他们对雷锋精神的理解和思考。
我还采访了雷锋生前战友乔安山、望花社区“爱同舟”帮扶队、学雷锋标兵张光富、抚顺市领导等。之后到雷锋生前班组以及雷锋纪念馆寻找雷锋的身影,在雷锋墓前凭吊思索。
我们努力寻找着——循着从军同志竖起的那座思想之山。
然而,面对汹涌而来的素材,我迷失了,甚至有点沮丧——所有的故事太熟悉了,有些虽感人但琐碎。当时的感觉是,那座思想之山耸入云端,而我却如没有方向的流水绕山流转……
采访即将结束时,从军同志打来电话,关切地询问采访的情况。我不记得都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当时挂上电话,头脑一片茫然。
12月8日,我们三人再次聚到从军同志办公室。半个月来,我们手里有了不少新鲜的素材。肖春飞,马不停蹄地跑了许多地方,采写的人物很多都能独立成篇。张严平,在广州采访的好人网等故事让人耳目一新。我们七嘴八舌地交流着采访见闻,从军同志认真地倾听着,若有所思。
“今天是历史的延续,在这样一种复杂、胶着、矛盾的时代,我们寻找什么?呼唤什么?雷锋精神能给我们怎样的价值理念?”他突然发问。
蓦地,那座我一直躲闪的“大山”又横在面前。
显然,那思想的高度在我们的认识和掌握的素材中是无处安放的。
从军同志娓娓道来:“这篇稿子不能写成一般的好人好事或学雷锋群像。在社会转型中,价值观的迷失与精神的缺失,阻碍了社会发展。要通过呼唤雷锋精神,回答人们如何寻找和谐社会的终点……”
苏东坡曾提倡文章要“有为而作”,要有诊治社会的作用,所谓“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
我们这篇文章如何有为而作?如何成为文明生活中起作用的社会力量?
从军同志要求我们在扩大采访范围的同时,多做思考。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本是中国绘画的最佳境界,讲的是自然景色与画家内心感悟的辩证统一。新闻通讯的创作亦如此——外在的采访素材只有与内在的思想和谐统一,作品才能达到佳境。
我们一边采访,一边按照从军同志的要求 “补课”——补思想课。
这是一个匆忙而又不得不做的功课。关于人生价值的哲学命题,我们向萨特“求解”,找川端康成、海明威“提问”,还到托尔斯泰的《忏悔录》里寻找答案。同时,我们重新翻开雷锋的日记,一字一句地找寻他的心灵足迹……
这是一个痛苦的思想跋涉过程。历史上,我们看到高更的迷茫,在一些思想家身上同样存在;现实中,我们在乔安山、郭明义等许许多多当代人身上看到了雷锋的影子,却也看到小悦悦事件给人们的伤痛,体会到老人摔倒扶与不扶的社会纠结……
思考的路在采访中延伸……
人生的价值意义到底如何凸现?雷锋到底能给我们多少启迪?进入写作过程中,这个疑问折磨着我们。
同样夜不能寐的还有从军同志。
2月9日凌晨3点,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远在湖南采访的从军同志在电话那边询问稿子的进展。
我谈了自己的困惑——如何思考社会中一些扭曲的价值观。他耐心地讲起了贝多芬的《命运》,讲到主题的冲突,他说这才是真实的人生。他甚至在电话里吟唱起其中的旋律,边对比,边讲解……
此后,他与总编室主任刘思扬,以及严平、春飞研究稿件直至天明。
我们几乎是被他拖拽着前行。
读书时,看到有价值的话语,他就划下来送给我们参考;思考时,突发灵感,便写在便条上,托秘书韩冰转交给我们。稿件采写过程中,十余次谈话每次少则一个小时,多则一天,他倾尽了心力。
而我们,就像三峡的江水,刚绕过一个险滩,又一座山峦挡在面前……
稿子一遍一遍地写,三人一遍遍地接力修改,眼看发稿的时间进入了倒计时。
2月15日,第三稿拿出时,“‘披头散发’。可以上升的哲学层面不多,思想笼罩不够”……
2月21日,第四稿完成。结果大段的故事淹没了思想的身影。
从军同志说:“对刘真茂2000多字的叙述,却看不到他的个性,故事太完整,思想必单薄。现在人人都是思想的提供者,谁爱听你讲故事呢?……”
此时,离发稿只剩一周时间了。24日,从军同志还要到江西出差。稿子还没有立起来……
我们开始怀疑自己,甚至有些绝望了。
2月22日上午9时,我们如约来到501会议室,愧疚着,沉默着,焦虑着。也许,一场批判的风暴就在眼前了。
出乎我们的预料——从军同志面带笑容走了进来,落座后说道:“我把今天一天时间都空出来,研究这篇稿件。现在没有震撼力,关键是要上个层次。我先总体讲下来,再具体讲每一部分怎么改。不着急。如果不行,晚上再加加班。”
屏气凝神,我们准备最后一搏。
从总体指导思想到文章架构,从每一部分到每一段落,从材料的运用到字词的修改,从军同志指导得十分细致。他娓娓道来,希望用这种谈心的方法为我们减压,真正让我们想得通,想明白。
从军同志说,“‘风筝虽高,线犹在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问题,就是人为什么而活着?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得到了自在状态,觉得幸福快乐。围绕这一问题,选取事例和语言,就能解决整篇思想问题。”
他进一步说,要做一些哲学的思考,人生有三大关系需要处理:一是人与时空的关系;二是主观与外在的关系,面对种种诱惑,挫折和压力,怎么去解脱自己;三是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当人没办法处理这些矛盾时,就会感到苦闷,甚至否定生命的意义。雷锋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些问题。
……
回过头看,这次思想指导成为文章成功的决定性一环。如果说从军同志最初的思想构想指明了方向,采访中的一次次谈话让这种构想逐步丰富,那么这次谈话,真正使思想贯通全文。
思想的江水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出差前,从军同志托人转来一张便条,上面再次强调,稿子要把雷锋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结合在一起。
三天时间里,我们几乎不眠不休。
2月25日,距发稿还有不到72小时,第五稿传到江西。
两个小时后,我接到了赶往南昌的指令。
飞机晚点。走进南昌滨江宾馆10号楼111房间,已是深夜11点钟。台灯下,从军同志疲惫地靠在床头,修改着稿件。
在江西三天时间里,从军同志利用工作之余的休息时间带着我改稿,每晚都到凌晨时分。

□ 2012年4月1日早晨,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左)会见湖南郴州宜章县护林员刘真茂。

□ 2012年2月8日,李从军在湖南雷锋纪念馆内参观。
与此同时,严平和春飞在北京紧张地修改着。
28日上午,从军同志参加会议。他一边听会,中间还有发言,一边修改稿件,大脑高度紧张。工作严重超负荷。
短短三天,他对稿件进行了大力度修改。思想和形式都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下午2时30分,翻着誊清的稿件,从军同志疲惫的脸上终于露出笑意:过去没有迈过去的坎现在都迈过去了。
此时,离发稿还有不到24小时。
半个小时后,我们乘飞机返京。
次日下午,历经千难万险的《召唤》如期播发。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我们的畅快就如那冲出重围的江水……
新闻因时效特性而被归入“易碎品”,但也会因其鲜明的时代色彩,厚重的思想性而充满生机。近一个世纪前,蔡元培对新闻生命力做了这样的注解——“余惟新闻者,史之流裔耳”。
一位读者说,《召唤》从大处着眼,挖掘出了雷锋精神的高远意蕴,超越局限、摆脱束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站立时代的船头,瞭望历史、现在和未来,唱响思想与生命的交响,才能有持久的“时效”。
交响的启示
“命运之神前来敲门。激昂有力,勇往直前的第一主题倾泻而出,表达了一种勇于挑战的坚强意志。接着,圆号引出抒情、优美的第二主题,抒发了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渴望和追求……”
——如果没有参与《召唤》的采写,我很难理解在贝多芬宏大的《第五(命运)交响曲》中,有如此丰富的思想内涵,有如此多彩的表现手法。更难想象新闻也可以用音乐的语言来“谱写”。
用音乐的格式写通讯,这在新华社历史上是第一次。然而坚持创新的精神,不断增强新闻报道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却是新华人80多年来永远不变的追求。
长期以来,从“游记”视角新闻的独树一帜、到“向散文式方向发展”的新闻文体改革,再到做“脚印探索者”,新华人无不在坚持新闻规律的原则下顽强地追求着创新。
美国学者梅尔文·门彻提出要把新闻“当成艺术品去雕琢。”这与1956年刘少奇向新华社提出的 “新闻要有思想性和艺术性……”要求不谋而合。
在“走转改”活动的创新舞台上,《召唤》进行了艺术雕琢的尝试。
应该说,这一尝试,是偶然,也是必然。
音乐式的艺术雕琢,出自从军同志两次“灵光一闪”——
还是要从2月9日凌晨3点的那次电话指导说起。
那天,从军同志还兴奋地谈起了他在望城雷锋纪念馆的一个音罩下听到了雷锋的声音:
“那是一个稚嫩、青涩,又充满理想、激情的声音。我突然感到中国精神的奏鸣曲在奏响……”
奏鸣曲?听说过,具体是什么,我并不懂。
从军同志最早在谈及文章的架构时,计划使用的是随想曲的方式。没有太多音乐元素的考虑,只不过觉得随想的方式,写起来更开阔,更洒脱。
这次用奏鸣曲构思全文,令人耳目一新。
从军同志在电话中继续介绍他的思路:“文章用奏鸣曲式分序曲、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尾声,第一部分序曲写高更的三问,提出问题;第二部分呈示部:历史的回响,把雷锋最精华的部分呈现出来。第三部分展开部:展现当今社会人们精神的缺失和彷徨……”
这个部,那个部,这个主题,那个主题,电话这头,我一头雾水。
又是一个非补不可的课程。我们三人找来柴可夫斯基的《悲怆》和贝多芬的《命运》,几乎天天听。还找来了《傅雷谈音乐》一书,恶补。
然而,音乐的修养又岂是在短暂的时间里培养起来的。
写到第三稿时,奏鸣曲的元素并没有贯穿进去,好像贴了个标签。
从军同志此时的心情也十分纠结:融不进去,宁可不要。但又舍不得:音乐太切合这个题目了,用音乐叙事,别开生面,对新闻写作是一个极大的突破和创新。
他在不断地思考着破解的办法。在办公室里,他再次谈起《悲怆》和《命运》——他一方面给我们普及音乐的知识,另一方面也在交流中寻求破题。
三个多小时的交流,始终无法冲破眼前的障碍。
当我们离开时,已夜色沉沉。他留在办公室里继续思索着。
下班的车子驶出新华社大门一瞬间,他突然灵感来了:“奏鸣曲改成交响曲,小提琴手、小号手、领唱、指挥,一下子爆发出来……”
第二天,他对我们说,文章用交响曲架构分成五个部分:序曲和四个乐章。每个乐章开始,先起一段引子。第一乐章,雷锋是第一小提琴手。拉出了交响乐的第一主题,就是雷锋精神的价值理念;第二乐章,雷锋是小号手。把人生信仰和理想的主题引进来;第三乐章,雷锋是领唱。让更多的人加入到雷锋精神的行列中来;第四乐章,雷锋是指挥。在世纪交响乐中,指挥着无数中国人。最后,落在“永恒的召唤”上。内在逻辑很清楚。
短短十分钟谈话,茅塞顿开。
但落在笔端又是何其艰难。
我们起草的第四稿融入了音乐的元素。尤其是每一部分的开头用音乐起笔,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但是,仅此而已。再听《命运》与《悲怆》,在文章中我们却感受不到交响曲的雄浑激荡。
怎样办?
“缺少碰撞。”从军同志说:“《命运》之所以摄人心魂,主要是其中各种碰撞,第一主题与第二主题,各种元素激烈交锋。”
“用在文章中,表现这种碰撞要靠对比的手法。”
文章起草之初,从军同志就一再强调,要出现第一主题和第二主题的对比。
何为第一主题与第二主题的对比?
他又以《命运》为例吟唱给我们听,然后分段讲解。他说,《召唤》中,雷锋精神的主旋律与社会不和谐的灰色音调不就是分别代表着第一主题和第二主题吗?
有了这样的对比,就有了碰撞的感觉,而这正是对现实生活中美与丑,善与恶同时存在的真实把握。
除两个主题的对比外,他还告诉我们,适时地将人物与人物对比,历史与现实对比,一个人性格的不同侧面对比……
“对比之外,还有烘托。主调之后,还有变奏……”
他还给我们讲到雷锋精神的变奏,那是一个大众化的雷锋,一个时代化的雷锋,一个个性化的雷锋。
他甚至用音乐的元素来解决思想逻辑贯穿的问题。
比如在第一乐章中,他用“人,为什么而活着?”的反复——“就像《命运》中那叩门声在旋律中不断出现,使每个人物,每个段落,既独立又有勾连。”
事实证明,这样做,不仅增强了文章的节奏感与旋律美,同时也使哲学思辨更加强烈。一个真实的人生,一个真实的社会,一曲雄浑的旋律也从纸上流淌出来。
一篇一万多字的稿件,很多人说,一口气读完,“行文方式一改近几年新闻报道的模式,内容引用上新颖而独树一帜……读来荡气回肠,余味无穷。”
行文中,人们听到思想者的踱步声,听到思想的潮水拍打山石的撞击声。由高更三问拉开大幕后,时而如流水潺潺,时而如巨涛轰响,时而如大江东去……
这难道不是一曲雄壮的交响乐吗?
如果可以说,音乐是用音符谱成的文字,那么,文章也可以是用文字写就的音符。音乐与新闻,在不懈的探索中于攀登的山峰上竟如此神奇地握手了……
一位新闻专家曾做过这样的统计,《召唤》一稿全文12271个字,点名道姓的人物有48个,涉及的地方场所39处……
哲理的思考,众多的人物,澎湃的情感,复杂的场景,没有创新,如何将之充分地表达?没有全新的载体,又如何使之大放异彩?
内容决定形式,创新决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音乐与新闻在《召唤》中的结合又成为一种必然。
也许,《召唤》交响的架构和手法无法复制,但它教给我们一种思考的方法。面对众多的艺术门类,面对新闻之外的众多表现手法,任意打开一扇门,开启的都可能是一个无限的空间……
改造我们的采访
4月1日,《召唤》文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山神”刘真茂,穿着那不变的军装来到新华社,看望从军同志。
一个多月前,从军同志曾采访过他。
何其相似的一幕——
4个月前的一天,从军同志采访过的林州百泉村支部书记张福根也曾来到新华社探亲。
为什么只有一面之缘就让他们亲如家人?
曾就这一问题询问过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他懂得我们。”
从军同志提醒我们:“任何价值观念的东西,是形而上的,只有植根于大众,才能显示其价值。否则就是飘渺的,在云端。”
然而,仅仅深入基层,把话筒对准大众是远远不够的,从军同志提出:“要有一个科学方法论,科学地采访调研,才能不断提升新闻报道的质量。”
我有幸几次跟随从军同志采访,对于采访有了一种新感受。
——成功的采访,是一种“剥笋式”的理性把握。
对于人物采访,从军同志有着自己的方法:“先不要过多问,让他说,然后抓住一两个细节引申开来。问他这个那个是怎么回事,让他讲故事,他就自然把很多东西讲出来了。不要一开始就问很大的问题。大问题,要留在最后才问。”
1月11日下午,从军同志带着我们采访了司占杰。
这个80后的“海归”。本可有令人羡慕的工作,却选择了做麻风病康复者志愿者。很多读者印象深刻。
开始,司占杰介绍自己的情况时,从军同志只是静静地听,并不发问。
也许是有些紧张,也许是拙于表达,司占杰在二十分钟时间内很概念化地介绍自己的人生经历。
当注意到司占杰无话可说的窘迫时,从军同志突然发问:“当志愿者,有哪些让你感动的事情?”
说起感动,司占杰的表达突然流畅起来。
他一个又一个故事讲下去。其中,讲到麻风病康复者李光学,讲到他30年难以回家的不幸遭遇,讲到自己用一周时间帮他结束噩梦的幸福感……
“你现在靠什么生活?”“你打算坚持多久?”……就像剥笋一样,从军同志一层层提问,边听边归纳和梳理。
最后,问道:“你知不知道雷锋?你怎么看待雷锋?”
几个问题下来,从军同志对司占杰已有了深刻的把握。他谈了自己的感受:“你刚开始做律师,是外在环境的强迫,非心所愿。后来做义工,是听从内心的呼唤。你的价值是帮助别人,感受到一种自由。你给自己的人生画了一个圈,不是回到出发点,而是到了价值实现的更高点,这是一个价值实现的螺旋图。”
我们注意到司占杰眼睛一亮,表情兴奋起来,频频地点头——这些话显然说到了他的心里……
面对采访对象,要一步步走进他们的内心,分析他们、把握他们。起笔时,才能寥寥数语,勾画传神。
——成功的采访,是一种“立体式”的真实把握。
从军同志说,人毕竟不是完美的,要遵守真实性原则,不要有意去掩饰采访对象的缺点,也不要刻意去强化。
我没有亲历对“山神”刘真茂的采访,但从军同志在写作中对人物的把握,还原了他采访中的思索:“刘真茂有着超乎常人的信念,但也有常人的孤独与愧疚。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种人性的色彩。”
这让我想到了《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里的林州人桑中生。他曾是一个亿万富翁,又因市场突变而一文不名,只能借钱搞实业。
在林州采访时,当地的同志提到他,从军同志立刻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说实话,当时我内心有不同看法:桑中生是一个失败者。见人一说话就流泪。与表达的精神主题不契合,有什么写头?
然而,从军同志眼里的桑中生,却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但始终追求理想的人,一条路走到黑的人。
《守望》一稿播发后,桑中生性格中的强烈反差,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到今天还有人在关切地询问:那个桑中生翻身了没有?
面对采访对象,不仅要观察成功者身上不为人知的弱点,也要观察失败者身上的闪光点。恰恰是这些反差,让笔下的人物真实、丰满。
——成功的采访,是一种“发散式”的感性把握。
由此及彼,连类感发,浮想联翩,是这种采访方式的特点。
采访司占杰后不久,我们又采访了他的恋人田星。她特别动情地讲起了第一次与司占杰在天安门广场相识的过程。
从军同志听后,道出自己的感受:“你们的相识真是太浪漫了。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场景:拍电视的话,一开始就是天安门当背景,摩登和历史交织,田星站在那里四处寻觅的时候,占杰带着十几个麻风病康复者出现了。那些人中,有的是眼睛往外翻,有的还缠着绷带。这种场景下,你们相识了……”
从军同志“发散式”的感受,引起了田星的共鸣。她有声有色地描绘出那次去麻风病村的场景,《召唤》中李光学为田星编唱凄美山歌的“镜头”,就是在这次采访中“拍摄”下来的。
《召唤》采访中,还有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对采访方向的把握。记得在第一轮采访结束,从军同志在听了我们的汇报后说,采访的人物要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你们的采访还缺少主干性人物。比如工人、农民,企业家、基层党支部书记,党员干部等等,他们才是社会的中坚和脊梁。有了这些主干人物,稿件才能立得住。
今天,我们该如何采访?
是搜集到最新的新闻事实?是寻找到最动人的故事?
是,但还远远不够。
采访,是一个创造性的劳动,它包含着情感、包含着思索,包含着科学的理念。
当前,新闻界的“走转改”活动正在走向深入,我们要正确理解这个“走”字的含义。只有反思我们的采访,改造我们的采访,带着感情、带着思想、带着科学的方法走到群众中间,才能真正走出实效。
通讯写作的新境界
《召唤》是一种什么样的通讯文体?
新闻研究工作者无法将它归入传统教科书上的任何一类,因而将其暂名“哲理通讯”。
《召唤》用的是怎样的写作方法?
新闻研究工作者无法准确地界定,因而将其形容为“塔式递进式结构”。
有人说,它是一部雄奇辽阔的交响曲,有人说,它是一篇诗中有画的电视解说词,有人说,它是一种时空交错的电影蒙太奇……
当新闻的实践超越了新闻的理论,它就创造了无限解读的可能。
2月27日深夜,江西南昌。
灯光下,稿件修改告一段落,从军同志谈起了自己对通讯写作的一些想法。
他说,这篇稿件内容、形式都有新的表达,包括最后的想象,有人可能会说,你这样写太过分了,哪能这么去写呢?真是匪夷所思。但是,通讯要表达思想,必须渲扬出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不敢或不善渲扬,制约了思想的发挥,阻挡了创新的步伐。当然,渲扬是很难做到的,要调动哲学、文学、音乐、绘画、摄影等各种表达手段……
——渲扬,是一种多元化的视角表达。
稿件采写之初,从军同志曾经说过,这篇稿件是对时代精神的高度归纳,对社会现象的哲学反思,对人内心共有价值的贯通。视角应该是多元的,有时像在天上俯瞰芸芸众生,有时像在世俗社会平视观察,有时把自己放在最底层表达对崇高的敬畏。只要文意不断,大可纵横捭阖,恣情四溢。
在《召唤》的舞台上,人们仿佛可以看到,追光灯的光斑在不断转变,光柱下的人物不断转换,与主光下站立着的雷锋遥相呼应。作者在文章中时进时出,用时空频繁转换的大角度变换素材,对雷锋精神进行了多角度的阐释,强烈叩击着人们的心灵。
——渲扬是让跳跃的故事音符串起的思想旋律。
一切都围绕思想的主题服务。通讯中常用的叙述事实、讲述故事、刻画人物的手法在《召唤》中也进行了全新的改造。
从军同志说:“哲理的沉思,要求我们行文必须做到高度凝炼。人物要为思想服务,不求讲述完整的故事,不写人物思想的完整轨迹,可能就是那一瞬间的特写。”
“叙述一定是超于现实的一种叙述,超乎叙述性的展示……”
“在一种跳跃的、看似不流畅的衔接中表达思想,文理上‘不讲理’,但内在是合理的。”
“长短句多一些,用一些质问、反问、疑问,包括判断句,不能全是陈述句式……”
“要打破陈规,让读者看到,长篇通讯可以这样写。”
……
对于思想的表达,从军同志强调议论的重要性,但要求议论有的放矢。
针对其中一稿,他曾尖锐地指出,议论太多,且大而空,不能就一点上有深刻的发问和把握,不是往深里去写,而是往上发散。刺就要刺到骨子里面去,而不是飘到天上去。
修改中,他增添的多处议论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也体会到这一要求的含义。
采写过程中,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篇记载“协和号” 邮轮侧翻的文章:
“协和号”侧翻时,船上正在播放《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歌《我心永恒》。而船上一位英国女乘客的祖母就曾从泰坦尼克上逃生,她的叔祖父则葬身大海。
从军同志剪了下来,交给我们:“把泰坦尼克号和‘协和’号勾连起来,一个撞上了现实的冰山,一个撞上了精神的冰山,前后穿越一百年,截然不同的对比,太有讽刺意义了。”
写入稿件后,他又认真进行改造,尤其是在江西改稿中第一次加上这样的议论:席琳·迪翁如天籁般的歌声是那样温暖,彼时的地中海涌动的波涛却如此冰冷。失去灵魂的躯壳哪里还能存放一丝的爱心?
第二次改稿,他又跟上了一句:面对泰坦尼克号与“协和”号的触礁,我们无法相信,时代前进了100年,而一些人的精神却倒退了100年。这无疑是理想的泯灭,灵魂的丢失。
一种悲愤、叹息、呼唤的情感呼之欲出。
——渲扬,是一种美学的表达。
《召唤》写作中,调动了丰富的表现手段,包括哲学、文学、音乐、绘画、摄影等,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写刘真茂,从军同志这样描述“30年过去了。杜鹃花开花谢,鸿雁飞去飞回,青山依旧,碧水长流,刘茂真古铜色的脸,早已爬满岁月的风霜。”
寥寥数笔,勾画出一个色彩丰富的油画。
其中的镜头语言更是随处可见。
有远景镜头:“湘江北去,少年远足。依依不舍之余,赵阳城久久伫立在江边,望着那远去的背影……”
有近景镜头:“年轻姑娘刘文秀微笑着走了上去,给了那个绝望少年一个轻轻的吻。”
有广角镜头:“个子小小的雷锋,站在时代的最前列,引吭高歌,他的身后,合唱的队伍,排山倒海。”
……
——渲扬,是一种穿越时空的丰富想象。
《召唤》第四乐章,大胆地想象了作者与少年雷锋和老年雷锋的对话,如梦幻般的穿越。
湖南望城采访时,当从军同志走过一排排楼房,来到雷锋故居的三间茅屋时,他说自己有一种走过历史的感觉。
“当时我在想,如果雷锋还活着,有七十二岁了,应该在安度晚年,可能就住在这一排排楼房里,这也是他期望的生活。时代在变,但人们所期待的精神是不变的。少年和老年的雷锋,非常鲜明的对比,可以跨越时空……”
他马上产生了一种与少年和老年雷锋对话的奇妙感觉。回京之后,他口授了这个片段。
我们听了之后,感到诧异:新闻怎么可以这样写呢?是不是走得太远了?
从军同志解释说:“从高更的追问起笔,一步步推演,到与雷锋对话时,已水到渠成。在丰富的想象中,在梦幻般的穿越里,让读者感受到的是再真实不过的事实:雷锋没有死,雷锋就在我们身边。”
新闻是事实的反映。《召唤》用想象挖掘了本质的、哲学意义上的真实。
黑格尔在分析美的要素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美的要素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内在的,即内容;另一种是外在的,即内容借以表现出意韵和特性的东西。
《召唤》正是将宏大的历史性思维、辩证深刻的哲学性思维和激情四溢的文学性思维融会贯通,以立意、结构、手法、语言的立体式创新,创造了深厚而多彩的通讯新境界。
回望《召唤》采写的日日夜夜,那不仅是一个对人生价值的追溯历程,更是一个艰难的超越旅程。
超越的力量从何而来?
来自新华人一代传承一代的历史责任感。
《召唤》以挖掘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和当代昭示为平台,对中国人的精神进行溯源。这是新闻人对时代的担当,对未来的召唤。
超越的灵感在哪里闪现?
闪现于“走转改”的旅途上,闪现于与群众的鱼水之情中,闪现于张扬新闻理想的风帆上。
《召唤》一文,没有基层的采访,就不可能有交响的构思;没有岳麓山下的徜徉,就不可能有穿越的联想;没有大山深处与“山神”的对话,就不可能有理想与信念的深度思考……
超越的平台靠什么铺垫?
用哲学夯实思想,用艺术滋养灵魂,用文学触摸人生……
书生报国无长处,唯有手中笔如椽。作为一个新闻人,没有历史、哲学的积淀,如何“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没有文学、艺术的修为,怎可“目极四海,挥斥八荒”?
71年前,范长江在《怎么学做新闻记者》中说过:“新闻记者之所以可贵,除了有正确的认识与坚贞的人格而外,就是要有丰富的知识。这个知识,既要博,又要精……新闻记者不是有了一支笔,就可以信口开河,而是要有终身不停地刻苦学习……”
今天的我们怎敢停下学习的脚步?!
事有不可变者,有不可不变者。坚持新闻本真,把握时代脉动,以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胸怀,实现自我超越。这是一种精神,一种气度,也是变则兴、不变则衰的生命法则。
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大时代,国家通讯社如何勇立潮头?这是每个新华人都在思考的重要命题。
唯有以更加踏实的态度深入基层,以更加科学的态度对待创新,以“一种追求极致的作风,精益求精、精雕细琢,才能打造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精品佳作。”
这是我们永恒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