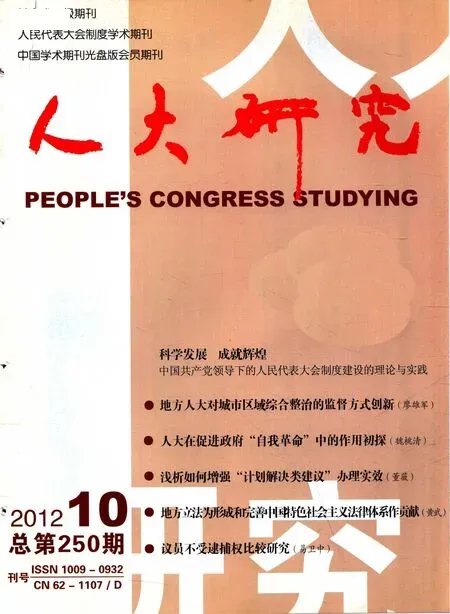人大行使监督职权途径问题研究述评
2012-12-21徐永利王维国
□ 徐永利 王维国
人大制度研究
人大行使监督职权途径问题研究述评
□ 徐永利 王维国
早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就赋予了人大监督职权。不过,缺乏实现途径的监督制度只能是僵硬死板、空洞无物的制度;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缺乏实效只能说明制度诚信和政治权威不足。由于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实效一直与宪法法律的规定及人民的期待之间有一定的差距,因而学界和人大工作者围绕增强人大监督实效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其中,有一些学者和人大工作者从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途径角度,就如何增强人大监督实效进行了探索。尽管人大行使监督权的途径与加强或强化人大监督权的途径是两个概念,但是一些学者和人大工作者却往往并不对二者加以区分,不在同一个逻辑层面上所阐述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不同途径。这样不仅容易导致理解误区,而且提出的对策建议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也会受到一定影响。
一、既有研究概述
有的学者和人大工作者在加强、完善或改进人大监督工作,提高人大监督实效的意义上阐述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途径。例如:
胡正扬在1996年认为,提高地方人大监督实效的途径有:一是突出监督重点,二是完善监督形式,三是健全监督机制,四是优化监督环境[1]。这里,其实只有完善监督形式、健全监督机制才与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途径直接相关,其余只是改进人大监督工作、提高人大监督实效的措施和方法,同人大行使监督职权途径间接相关。
吉雅杰在2001年认为,地方人大行使监督权的完善途径有:一是健全并完善地方人大行使监督权的各相关要素,即:加强地方人大自身的监督职能,增强监督活力;完善地方人大监督的内容,突出监督重点;完善地方人大监督的方式和程序,探索监督新渠道。二是健全监督立法机制,使地方人大监督权的行使纳入法制轨道。三是加强和改善党对地方人大监督工作的指导,理顺党政关系[2]。这里,只有完善地方人大监督的方式和程序,探索监督新途径才与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途径直接相关,其余只是加强人大监督工作、提高人大监督实效的措施和方法,同人大行使监督职权途径间接相关。
贺兴洲在2004年认为,加强和改进人大监督工作的途径有:一是尽快出台监督法,推动人大监督步入法制化轨道;二是在党的执政过程中保障和支持人大的监督工作;三是健全和完善人大监督机制,增强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四是以人大监督为中枢,构建公共权力监督体系[3]。这里,只有出台监督法,健全和完善人大监督机制才与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途径直接相关,其余只是加强和改进人大监督工作,提高人大监督实效的措施和方法,同人大行使监督职权途径间接相关。
盛涛在2007年认为,人大监督的完善途径有:第一,深入学习监督法,提高人大监督重要性的认识;第二,健全监督机制,强化人大监督的权威;第三,加强人大组织建设,健全人大监督的自身运行机制;第四,实现人大监督与舆论监督相结合,提高人大监督的社会影响力[4]。这里,只有健全监督机制才与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途径直接相关,其余只是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工作,提高人大监督实效的措施和方法,同人大行使监督职权途径间接相关。
邓光荣在2007年认为,地方人大监督的有效途径有:一是抓住实质,提高监督的针对性;二是选准议题,提高监督的准确性;三是贴近人民,增强监督的公开性;四是督促整改,增强监督的权威性;五是提高素质,增强监督的自觉性[5]。这里讲的全是加强和改进人大监督工作,提高人大监督实效的措施和方法,同人大行使监督职权途径间接相关。
胡连芳在2008年认为,树立人大监督权威的途径有:一是以“权”树威,二是以“为”树威,三是以“实”树威,四是以“严”树威[6]。这里讲的全是加强人大监督工作,提高人大监督实效的措施和方法,同人大行使监督职权途径间接相关。
倪春纳在2012年认为,以往学者认为强化人大监督权力的途径主要有:一是提高对人大监督的认识,二是理顺党与人大的关系,三是完善人大自身监督的制度建设,四是改进人大监督机制,五是探索人大监督形式[7]。这里,只有改进人大监督机制和探索人大监督形式才与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途径直接相关,其余只是加强和改进人大监督工作,提高人大监督实效的措施和方法,同人大行使监督职权途径间接相关。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和人大工作者仅仅把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途径看作为人大监督的形式、手段或方式。例如:
张文麒在1996年认为,新的形势迫使国家权力机关必须寻找一个力度适中、方法灵活、效果良好的监督形式。执法检查就是以其适用性、时效性、灵活性等特点,能够适应当前加强人大法律监督的需要,能够体现我国民众民主意识中所需要的便利、快捷、直接等要求,登上人大法律监督舞台,在实践中不断健全和完善,成为人大法律监督的重要形式和途径[8]。
李洪刚、许柏峰在1997年认为,实践中,国家权力机关对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主要方式和途径有以下几项:(一)审议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制度,(二)人大对检察干部的任免权,(三)人大对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四)执法检查和代表持证视察制度,(五)组织人大代表评议检察机关工作,(六)对检察长和检察干部进行述职评议,(七)对检察机关提出质询和询问,(八)通过交办案件和其他工作来监督检察机关的工作[9]。
赵复武在1998年认为,人大司法监督的有效途径有:一是必须坚持和完善行之有效的监督方式,二是要遵循正确的原则和方法,三是要在完善工作机制上下工夫[10]。
刘嫣姝在2002年认为,人大司法监督完善途径有:首先,制裁性的人事组织控制监督权的适用范围应严加界定,同时应加强人大对法官的评议监督,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采取某种追责制的监督方式。其次,决策性事务控制监督权能的应用程序要严格界定。由于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决议权的行使程序,所以造成了人大决议权的行使在某些领域虚置而同时又可能对某些问题滥用的状况。第三,应充实人大司法监督中平等化的沟通性监督权能[11]。
显然,上述不同学者、人大工作者,不仅在不同意义上使用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途径,把思想认识、体制机制、制度措施、工作策略统称为途径;而且,即使是同一个学者、人大工作者,往往也未能在同一逻辑层面上看待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途径。
二、简要评价
途径,简单地讲,就是起点和终点之间的通道或管道。对于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途径来说,就是由监督活动的启动、监督权力的运行、监督活动的结束等环节组成的系列活动及其程序。人大为了实现不同的监督目的,到达不同的监督目标,要确定监督活动的启动与结束要求,要采取不同的监督权力运行方式,因而形成了不同的监督途径。监督活动的启动包括启动要件的确定(确定要监督的问题和事项及所对应的监督形式)、监督活动方案的确定与组织实施等。监督权力的运行方式主要解决怎样监督(方式、手段、步骤),其特征体现为对监督事项触及的广度、深度和强度。监督权力触及监督事项的广度、深度和强度不同,直接影响监督目的的实现和目标的完成。也就是说,划分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途径类型的主要依据是监督权力运行的方式。监督活动的结束包括监督的法律后果的确定、监督实效的评估、监督责任(包括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落实等。当然,围绕不同的监督目的和目标,监督活动启动和结束的条件与要求也不同。因此,监督活动的启动的条件与要求、监督权力的运行方式和监督活动的结束条件与要求共同构成了完全意义上的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途径。完全意义上的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途径包括由谁来监督(主体),监督谁(对象),监督什么(内容),怎样监督(方式、手段、步骤),如何保证监督效果(效力、责任)等规定和要求。可以说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途径是一个在人大制度下的完整的监督制度、规范和程序体系。现行监督法规定了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职权的七种方式,即:听取和审议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决算,听取和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的执行情况报告,听取和审议审计工作报告;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询问和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也有学者和人大工作者将其称为七种监督形式或手段。甚至有人将其直接称为七种监督途径[12]。显然,这七种监督方式对监督事项触及的广度、深度和强度有很大的不同。例如,询问虽有广度,但深度和强度明显不足;而特定问题调查主要目的就是要对监督事项进行深度把握,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的强度是所有监督方式中最强的。人们普遍把监督法看做是对监督方式,或监督形式与手段的具体规定,而只有个别人称之为监督途径,这就说明这七种监督方式的确是分辨人大行使监督职权途径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这也表明这七种监督方式也可以看做是不完全意义上的监督途径。也就是说,这七种监督形式的启动要件、运行过程和方式、法律后果各不相同,基本上涵盖了人大对“人”“财”“事”的监督;但要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监督途径,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程序,创新方式方法;还需就这些监督方式运行所需的初始与结束条件和要求作出明确的规定。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不断完善人大行使人大监督职权的途径,以确保人大的监督职权能够真正发挥作用,而不仅是文本上的规定。
监督总是相对于被监督者而言的,因而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过程,就是人大与“一府两院”的一个互动过程。如果“一府两院”对人大的监督采取回避、不配合、抵制、不回应,甚至反监督的话,那么人大的监督就会受到阻滞,监督的效力就会减弱,甚至没有,监督的途径就会失效。出现这种情况,人大监督的目的就难以实现,目标就难以达到。当然,人大监督的效力也与人大在整个国家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人大组成人员的责任意识、行使监督职权的能力与决心有着密切的联系。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人大工作者,把人大自身与“一府两院”的人大意识、监督意识的强化与自觉,人大与党委关系的完善、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制度安排、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机制建设及人大行使监督职权措施办法等都看做是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途径或加强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途径,而且有的还放在了同一个逻辑层面上来论述。加强人大监督职权涉及诸多方面、诸多因素,除了需要进一步完善监督程序、创新监督方法外,还要进一步增强监督意识、完善法律法规、理顺党政关系等等。也就是说,人大自身与“一府两院”的人大意识、监督意识的强化与自觉,人大与党委关系的完善、人大机构建设,只是有助于强化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效力,增强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实效,还并不是人大监督权力运行中直接环节。因此,上述方面,可以看做是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间接途径。我们在说明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途径时,应将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加以区分,因为它们属于不同的逻辑层面。所谓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直接途径,就是指由人大监督活动的启动、开展、结束等环节组成的系列活动、步骤、过程和程序。当然,就目前来说,人大监督活动的启动、开展、结束等环节,无论是在法律法规的规定方面,还是实践探索方面,都存在许多需要细化、明确和完善的方面。也就是说,现有的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途径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完善、延伸,才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监督途径。尤其是人大监督权力的运行方式,监督法只是对已经较为成熟的进行了规范。然而,地方人大普遍反映,对于人大权力的运行方式在不违背宪法规定和法律精神的前提下,应该持开放态度。这样,才能扩大和拓宽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途径,更加有效地利用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途径,进一步增强人大监督的效力和实效。当然,我们将人大行使监督职权的途径分为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并非要说明间接途径不重要。实际上,只有二者共同发挥作用,才能使人大的监督职权真正落到实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注释:
[1]胡正扬:《提高地方人大监督实效的途径》,载《人大研究》1996年第4期。
[2]吉雅杰:《我国地方人大行使监督权的完善途径》,载《中国律师》2001年第6期。
[3]贺兴洲:《加强和改进人大监督工作的现实意义及途径》,载《求知》2004年第12期。
[4]盛涛:《人大监督的性质及其完善途径》,载《党政干部学刊》2007年第9期。
[5]邓光荣:《积极探索地方人大监督的有效途径》,载《人民之声》2007年第11期。
[6]胡连芳:《浅议树立人大监督权威之途径》,载《新疆人大》2008年第5期。
[7]倪春纳:《强化人大监督权力途径的研究述评》,载《天府新论》2012年第3期。
[8]张文麒:《执法检查:地方人大实施法律监督的重要途径》,载《人大研究》1996年第7期。
[9]李洪刚,许柏峰:《正确认识人大监督的方式和途径不断提高接受人大监督的自觉性》,载《政法战线》1997年第10期。
[10]赵复武:《积极探索人大司法监督的有效途径》,载《人大研究》1998年第4期。
[11]刘嫣姝:《论我国人大司法监督权能的完善途径》,载《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12]李青灵:《认真贯彻实施监督法 依法规范监督程序》,人民网·中国人大新闻网(h t t p://n p c.p e o p l e.c o m.c n/GB/1 5217/5381742.h t m l)。
(作者分别系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所所长,北京联合大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所研究员。本文系“加强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监督权的途径研究”基金项目,批准号〔12 BZZ 0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