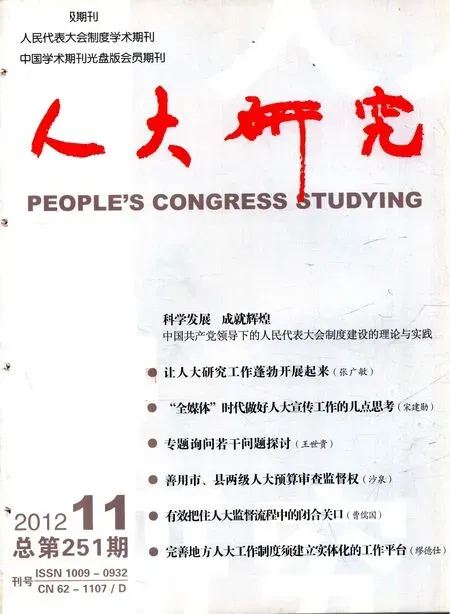代表辞职制度的实践观察
2012-12-21卢鸿福
□ 卢鸿福
人大工作探讨
代表辞职制度的实践观察
□ 卢鸿福
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可以试,可以实践,可以完善,当被实践证明成熟了的制度再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规范,这也是有关人大制度方面立法的重要途径。
2012年4月,湖南省涟源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接受了一名代表辞去人大代表职务的请求。
自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首推的代表辞职制度,十余年来,一直在争论和质疑中不断前行,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很多地方人大出台了代表辞职制度。
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代表机制,让代表肩负起应有的责任和担当,地方各级人大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代表辞职制度逐步推开
2002年4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大常委会按照代表法规定,实行了代表辞职制度,先后接受15名人大代表辞职。这是最早见诸报端的有关人大代表辞职制度的报道。
2003年下半年,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大开始建议代表辞职制度试水。建议辞职的主要是三方面的人员:由组织推荐并当选为县人大代表的镇乡、街道和县级机关部门领导干部,其工作岗位或工作职务变动的;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不能执行代表职务的;其他情形需要辞去代表职务的。
该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文蛟认为,人大代表调离原选区后,继续保留代表资格,直到任届期满,这是目前基层人大工作中的通行做法。由于代表“终届制”的实际存在,代表调离极易导致原选区代表职位的“空置”现象。
避免代表职务“空置化”,解决乡镇、街道办事处新任负责人的代表身份问题,是宁波探索“人大代表建议辞职”的直接动因。
2005年,刚刚作出关于届内代表辞职的暂行规定时,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人大常委会还有一点惴惴的感觉。直到消息传出后,天津、山东等省市的一些城市纷纷打电话取经,媒体也穷追不舍,才像吃了定心丸。
钟楼区关于代表辞职的想法源于2005年3月份的人事变动,区政府提请的一批新政府组成人员中,有5名是代表,不利于人大开展监督。因为换届选举前,常州市人大常委会就政府组成人员中代表配备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显然,新一届政府增加的5名代表名额与此不符。
“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比如第十二届代表也是按比例分配的,一届5年任期下来,原来的结构被打破,甚至面目全非,不过问题没有现在这样集中,一下子解决了118名干部。”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玲君说,“所以改革在所难免。”
有了先行者,代表辞职制度逐步在一些地方人大得以推开。先后有四川、湖南、辽宁、河南、山东、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市、县、区先后施行了代表辞职制度,并出台了相应的暂行规定或实施办法。
据观察,代表辞职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调离原选区或原选举单位的。(2)担任地方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的人大代表调到其他部门工作的。(3)担任党政部门主要领导和人大常委会领导的人大代表改任非领导职务或退休的。(4)担任群、团领导职务的人大代表调到其他部门工作的。(5)因健康原因不能执行代表职务的。(6)其他原因,如长期在外地工作,与原选区选民无法联系、不愿联系的;当选代表后没有履行过代表职责、不参加人大会议或代表小组活动的、犯有严重错误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的人大代表等等[1]。
从地方实践来看,代表辞职制度的适用主体或对象主要还是针对有特殊身份的代表,如“岗位代表”或“官员代表”。这些代表因岗位变动,但又未调离本行政区域的、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种特殊身份的人大代表被作为辞去代表职务的首选。而不作为代表建议辞去代表职务的尚处于偶尔实践阶段,很少破题。
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
由于法律对代表辞职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辞职制度在法律上存在争论,地方人大在推进代表辞职工作的过程中,大都采取积极稳妥的方法。
依靠同级党委的支持。在出台建议辞职的办法时,先经同级党委同意;对要求辞职的代表,由主任会议研究确定后,向同级党委报告。对建议辞职的代表,由组织部门负责谈话,向代表说明辞职的原因、依据和程序,建议其提出辞职。
遵行自愿的原则。对建议辞职的代表不是一味强求,而是通过思想引导、法律宣传,让其自愿主动提出辞职请求,再经常委会审议通过。对个别坚决不辞的代表也尊重其意见,不搞一刀切,不违背法律。
从下到上渐次推进。由于县市区人大代表变动相对于上级而言,更频繁,更重要,所以,代表辞职制度率先在县市区施行。而省、市(地级)的人大常委会却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2005年4月,辽宁省公布《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加强人大代表工作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的意见》,规定对不称职的代表可以劝辞、罢免,打破代表终届制。至2006年年初,该省已有5名省人大代表、至少40名市人大代表因各种原因被提前终止代表资格。这是省级层面最先对代表辞职进行的规定,但其他省市鲜有关于代表辞职的报道。
不履职者要求辞职也在探索之中。因工作需要的“官员代表”建议辞职显然得到了人民的认可,与此同时,一些缓作为、不作为、乱作为代表的辞职,也在一些地方开始探索。2005年,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一宾馆的老总是区人大代表,但是企业转制、老婆生病,让他忙得够呛,基本上无法正常履职,后来组织部门找他谈话,建议他辞去人大代表职务。但此类情况,目前尚是个别现象。
主动辞职折射代表观念的改变。2005年,广东省人大代表王泽华,因妻子患病需要照顾等原因,正式提请辞去省人大代表职务。王泽华在12年人大代表生涯中,共领衔提出250多件议案和建议,发起了13次询问案,被称之为“议案大王”。2005年1月份,在安徽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高明伦提出辞职申请,请求辞去委员职务,理由是科研管理工作繁重,并且感觉自己法律知识有限,不适合承担立法责任。舆论认为:“人大代表从政治待遇到责任意识的可喜转变,最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身份自觉和角色归属意识。”
辞职制度的是与非
事实上,代表辞职制度一出台便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争论不止,质疑不止。
赞成者认为,在选举法规定的罢免程序无法有效启动的现实面前,建议代表辞职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一是有利于端正社会对人大代表的性质和地位的认识,增强人大代表的责任感、使命感。二是有利于民主资源的优化配置。代表调离原选区或者原选举单位后,联系原选区选民或原选举单位、接受原选区选民或原选举单位的监督流于形式。代表辞职后,可以让出位置来给那些能够充分反映选区选民要求和意愿的代表,从而实现民主资源的优化配置。三是有利于保持代表工作的连续性,确保代表作用更好地发挥。实施人大代表辞职制度,把不能或不尽力执行职务的人大代表及时调整出代表队伍,可以及时、合法地补选空缺的代表,保证代表在结构上的合理性、界别上的广泛性和素质上的先进性[2]。四是有利于调动代表履职的积极性、主动性。打破“终届制”,建立能上能下、能出能进的代表机制,能增加代表的压力,激发履职热情,发挥代表作用。五是有利于人代会的组织,发挥大会的制度功效。同时,可以降低社会成本,又符合当前实际。
然而,有关人士指出,建议辞职制度的执行程序体现了操作者们力图在现行的法律和制度的构架之下进行操作的良苦用心,但却面临着法律的尴尬。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适用问题。从代表法和选举法看,对人大代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终止其代表资格:由于犯错误或选民不满意而罢免;自愿辞职;代表资格自行终止。代表如有违法违纪、工作严重失职或不能履行职责等情况的发生,应适用罢免程序,选民或选举单位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这也是我国选举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在人大代表犯严重错误或选民不满意时,用辞职代替罢免,适用代表辞职规定使其失去资格。也有学者认为,在处理代表资格的问题上,原选区选民或选举单位有权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这是选举权的延伸,也是对选举权的一种保护。以辞职代替罢免,将原选区选民和原选举单位置之一旁,忽视了对选民享有的这项罢免权的保护,实质上剥夺了选民的这一权利[3]。
二是超越了权限。法律没有授权任何机关和个人有要求代表辞职的权力,建议代表辞职是一种权力运作的偏差和错位。代表的地位是法定的,代表资格的终止只能依法进行,在法律之外,人大常委会以及有关组织都无权建议人大代表辞职,无权妨碍甚至剥夺代表的权利。作为县、乡人大代表,除了法律对停止执行代表职务和代表资格终止的规定外,无论其是否适合担任代表职务,还是其能否履行代表职务,最终决定的权力都应由选区选民来行使。绕过原选区选民,擅自为原选区选民做主,实质是不尊重原选区选民意愿,其目的是为了解决无法补选的问题,而非为了维护原选区选民的合法权益[4]。
三是难以避免一些侵权现象。比如当有关机关和组织向人大代表提出辞职建议后,代表明确表示有愿望、有能力履行好代表职务,而有关机关和组织却反复给被建议辞职的代表做工作,最终使代表极不情愿地提出辞职。这种情况违背了代表本人的意愿,有人大工作行政化之嫌[5]。
建议辞职的努力与期待
代表辞职制度已经在基层试行多年,支持者侧重的是实践、工作需要,反对者侧重的是理论、缺少明确具体的规定。
无论如何,在选举法规定的罢免程序无法有效启动的现实面前,如何疏通代表的进出口,建立能上能下的代表机制,是大势所趋,也是各级人大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一些人大代表除了开会举手外,沟通民意的作用并没有发挥,对这些代表还没有很好的制约办法。”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教授认为,“选民与代表双方都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这是一个制度的空白。”
事实上,这一制度在探索实践中,并未听到来自最高权力机关的反对声。
2002年1月,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于乡镇人大换届时,在全县23个乡镇都成立了人大常委会。此事,引起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高度重视,立即叫停。
“没有叫停”,意味着为这一制度的探索和实践预留了空间。
理性看待代表辞职制度,有其创新的一面,也有其与法律法规不尽一致的一面,这也是这一制度未能在更广阔的实践层面得以推广的重要原因。
要真正解决代表辞职问题,有赖于选民意识的觉醒。在这点上,显然需要待以时日。
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可以试,可以实践,可以完善,当被实践证明成熟了的制度再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规范,这也是有关人大制度方面立法的重要途径。执法检查、代表视察、工作评议等大都如此。
无疑,代表辞职制度对于打破“终届制”,打造责任代表、职务代表提供了实践的平台,“不履职便辞职”,这也是现代民主的应有之义。
注释:
[1][2][3][4][5]马蕙瀛:《地方人大建立人大代表辞职制度的相关情况及相关讨论》,载《人大研究》2005年第10期。
(作者单位:湖南省娄底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