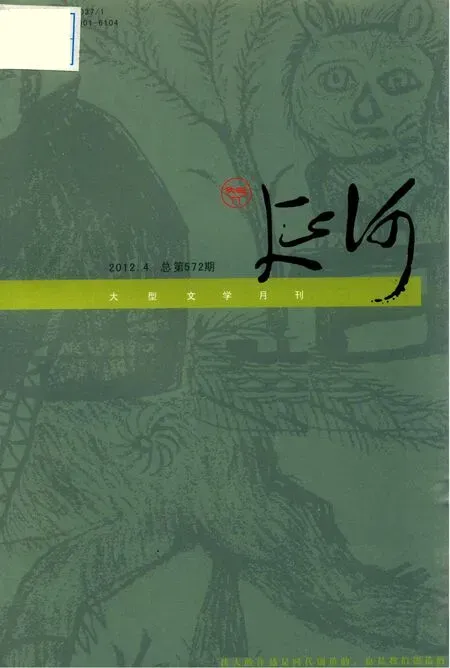你是我的神
2012-12-18凌春杰
凌春杰
一座村庄弥漫深爱
我在网上看到一幅电子地图,可以找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很快,我就找到了那个叫花屋场的去处,虽然看不清山川树木房屋,从蜿蜒的公路轮廓,却可以想象生养我的那个村庄,有着怎样的蓝天,怎样的溪流,怎样的乡亲,怎样的炊烟,想象我的亲人怎样在田间地头劳作。花屋场,这三个简单的汉字,顿时成为可触可感的心灵隐秘之地。
那里的泥土,不仅养活着那里的人们,泥土中的尘灰,交融着或远或近的亲人的肉体、骨殖、血液,从自我的世俗走向后人的精神世界。
2011年7月7日,爹带着他的满足与遗憾,像他的祖辈,闭上遍阅世俗的眼睛,回到了那片土地,安息在青山之中,以另种精神的方式,日夜守侯,注视着他生活过的村庄。爹的去世,使我忽然失去了根源一般,充满了沉坠感,常常一想起他就噙满泪水。这是我从没有过的哀伤和疼痛,这也是我对爹从来就存在却直到现在才苏醒过来的爱。
生老病死只是人作为生物的一个过程。爹用生命使这一过程变得完整。现在,这个过程留给了我。我只有看着自己的孩子从母体降临,一天一天,一岁一岁地呵护着孩子长大,只有用手去搽过孩子粘满金黄色大便的屁股,只有看着孩子会笑、会咿咿呀呀、会坐、会爬、会走,会喊爸爸,我才找到了自己原本存在的根源,我的生命因此不是一个断裂了婴幼时期的轮回,而是从父亲母亲那里开始了自己的起点,像一颗裂变出来的行星,开始绕着人类运转。
关于爹小的时候,很多事情无从考证——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爷爷,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奶奶——我所见到的是爷爷的父亲,他已经老到八十几岁,而我那时像1945年代的爹,穿着满带补丁的衩裆裤。在和爹四十年的生命相依中,爹很少讲他自己的事情,而我也从没有意识到要去追问。关于爹的少年,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讲过的“过兵”的记忆。
推算起来,应该是1947年的秋天。因为爹在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几次提到那棵我无数次攀爬的柿子树,树上的叶子落光了,挂着红彤彤的柿子。那天,忽然数百数千的军人从溪底上来,爹后来回忆,应该有上万人。在鄂西长阳,经历过林之华起义,长阳红六军的兴衰,花屋场也经受着战争时期的种种灾难,土匪的骚扰,地主的欺压,保长的抓兵,甲长的搜粮。躲兵,成为花屋场百姓的间歇性习惯。爹和他的家人一起,躲进了屋后叫老湾的那座大山。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过兵,在花屋场住了一夜。乡亲们躲在山上,看着路上密密麻麻的军人,看着这些军人渐渐分散聚集在一家一户,爹充满了好奇,悄悄溜回了家,发现自己家里也住满了兵。爹好奇地跟在一个兵的后面,带着这个兵去摘了十几个柿子。整个过程中,爹的眼睛没有离开过这个兵肩上挎着的步枪。摘完了柿子,这个兵让爹摸了一下他的枪,给了他两只金黄的弹壳。趁兵们吃柿子的机会,爹又悄悄溜进了后山里。
我不知道,十年后的1960年,爹成为花屋场解放后第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时,在19岁的他的心里,是否还隐约有着一支旧军队的影响。在他8年的军旅生涯中,爹随部队调防走过17个省,荣立三等功两次,被部队授予技术能手称号。
关于爹的军旅生涯,我只能东鳞西爪地感受,甚至用想象来弥补自己对爹的无知。
我没有见过我的爷爷和奶奶,奶奶在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爷爷在爹当兵转业后的那年,也因文斗武斗而自杀了。奶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那时候村里还没有照相这个行当。而爷爷留下了他唯一的一张照片,那是一张合影,爷爷和幺叔站在一起,幺叔没有成年,就因病去世了。爷爷头上包着土家族人才有的白头巾,一脸严肃地看着前方。爹去世后,我把爹留下来的老照片都带到深圳,一张张分拣,以2400dpi扫描,我要以影像的方式,把爷爷、爹和我们以纸质的文本永远地联系在一起,让自己逐渐适应冷静地面对爹遗留下来的一切,包括他遗留下来的我自己。
在部队里,爹似乎是一个司机。在他年轻的时候的老照片中,大多都是一些穿着军装的头像,或者是一些风景照,只有一张能够体现他在部队的职业。爹蹲在一个履带拖拉机驾驶室前,安静地看着镜头,照片只有一寸见方,在高分辨率扫描之后,依然可以看见他眼睛中的微笑。很长时间,我在心里以为爹当的是汽车兵,虽然我没有见过他在部队开汽车的照片。后来,零星地听爹讲过他和他的战友带着枪跑青藏线,到福建云南等地,爹讲述的都是一些纲要式的事件,没有什么血肉,我都印象不深了。爹被确诊为胰腺癌后,我很想知道爹的故事再多一些,却小心翼翼地不敢多问,怕引起他的什么警觉。我只知道,爹是因病,从排长带病转业回乡。
一生不舍的厮守:土地
花屋场是这样一个村庄。它像一个微型盆地,四面环山,只是其间没有一块完整的平地,斜坡、小块平地和沟壑错落在一起,有一条叫大沟的溪沟自东向西逶迤而下,却有一半时间属于干涸。暴雨的时候,大沟里的洪水汹涌而下,这才知道这条大沟是多么地威力,水声轰鸣,水烟阵阵,气势磅礴。大沟长不过四五里,接山脚的天池河,在天池口注入清江。
有山的地方,则有明显的阴阳之分。东边那座山口,也是一个斜面,而南面的山,逼仄陡峭。以大沟为大致界限,尤其在冬天,太阳总是在北面的时间长久很多,我们把那边叫做阳坡;而太阳在南面这边只有正当顶的时候才投照在地上,眨眼就只看到阳坡一片艳阳了,村里人把南面这边叫做阴坡。花屋场作为严格村庄的名字,还包含了一些小小的、甚至细小的地名,阳坡西头有大屋场、花屋场、钱家坪、铺子包等之分,而阴坡则有熊家溪、壕沟溪、史家台子、凌家湾等之分,在凌家湾譬如我家周围,又还分出楠树槽、偏坡、园子、柿子树塔、中领、岭上、老湾、酸枣子坡、旁边沟、门口、大坡等十几个具体的地段。凌家湾沿旁边沟而上,自老湾大致呈70度而下,直接大沟而成丁字。近两百年来,凌氏的祖坟就在凌家湾附近。凌家湾最上面的第二户,就是爹在那里出生、长大,出去闯荡世界又回到的地方,最终,爹怎么也不愿意在医院里,而固执地要在那栋有着一百年历史的老屋中进入另一个世界。
在手术之后,爹再次经历了生死劫难。他似乎隐约感觉到什么,悄悄给自己选下了一块墓地。第二次去医院住院之前,爹私下跟妈说,我给你我选了一个屋儿,就在板栗树旁边的柑橘树林里。我从未见过的奶奶就长眠在那里,那颗板栗树,就从奶奶坟前茁壮而起,遮了有两三分地,收成好的话,有好几百斤板栗。爹去世后,按照村里懂阴阳八卦的人的算法,打完丧鼓后,他的灵柩要在墓地搭棚安放一晚,次日凌晨2点到3点之间动土。我去看爹自己选定的墓地时,两个基桩已经插好了。墓地座南朝北,头顶老湾最高处也是我们的责任山林,面对的北面,是大屋场背后雄峻的二担坡山,暮色中很有巍峨之势。二担坡山背后的上坪,则是我妈的娘家所在。起初,我也不知道这地方的好处,经村里熟悉掌故的老人一解释,便也觉得确实有很多奥妙,爹给自己的风水,当真是一块宝地。
爹在墓地的右边,给妈留了一块地方。自此,爹把他的爱恨情仇,他的手艺,他的一切,都留在了花屋场这个日渐凄凉的地方。他可以听中岭上的松涛,看二担坡上的白雪,嗅着地里瓜果成熟的香味,看着他的儿子、他的一代一代的后人在地里耕种收获,在茂密的枝叶间静悄悄地微笑,用他的爱,烛照着他所见到的善的一切。我想,在群山苍翠之间,我看到爹的坟,看到奶奶的墓,看到凌家湾祖宗的碑,我也看到了二十万年前长阳人居住的山洞,看到了五十万年前周口店抬起的头颅。因为我们自觉不自觉在往上看,因为他们在世的时候往后看,我们有了与自然灵气相通的精神世界。只要我在,我就一定有自己的源头。或者,五百年前,我姓张或刘,又或者,五千年前,我什么姓氏也没有,只是在历史的河流中,形成了一个地理上的宗族,只是在更近的空间,感受到血脉的温热,而在这种无限循环的父子之间,结成一粒一粒的珍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繁衍,只有繁衍的人,才懂得在老幼之间满怀着爱的感恩。
爹去世后,我没有按照古老的传统一个一个地给乡人挨着磕头,我只将双腿跪向爹,跪在爹深爱的土地上。回想起来,花屋场的人却对我表现出莫大的宽容。我在心里,深深地感谢,敬重这些人。我忽然觉得,他们和爹一样,比我更深爱着这片土地。
一双眼里的融合:自通
有关爹的记忆,我是从他暴躁的脾气开始记忆的。很长时间,这种记忆是一种不快,甚至还夹杂着怨恨。
作为一个有着8年军龄的退伍军人,爹在部队养成了粗暴而直性的脾气。在我少年渐渐凸起的记忆中,稍有不慎,就要面临挨打。很长时间,我们对爹充满了畏惧。记得有一次,是冬天,我不知道做错了什么,被爹发现了,我爬起来就飞跑。爹一气之下,跟在我的后面狠追,眼看就要追上,我不顾雪地里有收割不久的玉米茬,从两三米高的坎上飞落而下,滚落在积满雪的地里。爹停住,用手抓起一团雪揉紧朝我砸来。那一次,我躲在雪地的草丛里,直到天黑才悄悄地回家。
但爹又对我充满着诱惑的魅力,他像一个巨大的谜团,使我总是想和他走得更近。在爹的身上,聚集着以17个省市为纬度、以8年南来北往为经度的见闻,他以一个农民的好奇和不服输的姿态,学会了数十种技艺。在部队,爹因为爱钻研成为一名技术能手。转业到家乡后,爹把在外近十年的见闻所习,浓缩在花屋场这片土地,成为一方的参谋长和万金油。在我很小的记忆中,爹会修的,先是修收音机录音机手表,接着是修柴油机发电机,再接着是修拖拉机农用车,后来还修电动机电视机,干湿磨,磨浆机,大凡从外面买来的机械,无论是要用放大镜看着用细小的镊子去拨动修理的,还是要轮起铁锤把拖拉机瘪了的车厢矫正的,莫不在爹的维修范围之列。这还不算,爹还有会做的,木匠,篾匠,铁匠,弹花匠等,椅子都自己做的,粗背篓是他自己编的,火钳锄头之类的铁器是他自己打的,甚至窗户上的玻璃也是他自己划的,九佬十八匠,似乎他都试过。在我的记忆中,爹还会养蜜蜂,擅长放铁猫子,会照相洗相这样的细活儿,会裁剪缝衣服,会烙饼子,年轻的时候还会吹笛子拉二胡……爹所会的,有些是农村里大多数人分别会的,还有些是整个村儿好长一段时间只他一个人会的。花屋场村有句老话,叫艺多不养人,成了万金油,只能到处抹一下。爹却因此把这个家撑了起来,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吃粮食以外的东西。爹所会的,大都就不是只懂点皮毛,他找机会偷学,买书自学,看别人做瞄学,有些是求学,从没有跟过师傅,大多属于无师自通,然后自己添置工具,首先把自己家里需要的都做了,以不求别人。
爹去世以后,我和弟弟收拾他的东西。单是工具,锤子大小有五六种型号,平口起子近20把,梅花起子十余把,活动扳手大小7把,套筒扳手一套,尖嘴钳子两把,虎口钳子两把,铜烙铁一把,电烙铁两把,各种型号的螺丝钉螺丝帽数千个,电锤一把,电钻一把,手摇钻一把,各种木工用凿子15把,大小刨子十几把,各种锯子7把,废旧的晶体管数十个等等,还有废铁数百斤,爹的遗存,列到清单上肯定不下于数千项。爹的这些工具,无不都指向他所会所能的某种手艺。
这些手艺中,我也学会了的,是照相和洗相。现在,我使用的是两台专业级的机器,佳能5D2的相机,佳能XF305摄像机。当我在取景器中构图的时候,我就会想起爹那台双镜头的老海鸥。爹有从部队里带回来的显影粉定影粉,请外公在城里买了一盒相纸。爹自己划了一块玻璃,用木头做出一个镜框样的东西。那时村里还没有通电,爹用一块红布包住一只手电,用一块绿布包住另一只手电。到了晚上,天完全黑下来了,再用白瓷盆打来半盆清水,把显影粉和定影粉分别用温水在瓷碗里融化。打开绿手电,拿一把临时做的竹刀把相纸裁成要冲印的底片大小,把相纸和底片叠在一起放正,放进玻璃框中压实。这时,爹一再嘱咐,不能亮灯啊!而他自己,却忽然关了红手电,开了去掉绿布的手电对着镜框一扫,只那么一瞬,就一片漆黑。就在黑暗中,我听见爹摸摸索索地又把绿布蒙到手电上,才开了红手电,将相纸取出来放进融化了显影粉的那只碗里,用两只竹片轻轻搅动。不一会儿,相纸上现出了人影子,起初淡淡的,越来越明显,等看的鼻子眼睛都很清楚后,爹把照片夹出来放进定影碗里,等一会,再捞出来放进清水盆中,这时,照片就可以用手去拿了。
爹在洗相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绝活,是我所没有学会的。照片洗完后,爹会挑一两张,拿细巧的毛笔沾上颜色,把照片中的帽子描成黄色,衣服描成草绿色,皮肤也加了若有若无的色彩,一张黑白照片在爹的精心描绘下,顿时有了神采,生动起来。这种描摹我曾悄悄试过几次,不描还好,一描连人都分不清是谁了,反而把黑白照片给浪费了,只好作罢。
我在清理爹的那些老照片时,我看到了爹年轻时候的英俊。这种英俊,在那些彩色照片中更有神韵。我想,那鲜红的五星,火红的领章,鹅黄的军装衬托出来的一个年轻军人的风采,多半该是来自爹自己的杰作。
爹还有很多东西,有的装在我母亲的嫁妆——那口红色的樟木箱中,我的印象中有他当兵时的帽徽领章,帽徽是一颗鲜红的五角星,领章有平板的,也有两颗星三颗星的,还有爹的一些奖状、证件等,里面还有书,比如《内燃机的原理》《晶体管收音机》《电子管收音机》《科学养猪》《科学种玉米》等,有些书是爹从部队带回来的,有些书是爹后来买的,还有文艺书如邹狄帆的《大风歌》,还有一套凌氏的家谱……爹的另一些衣物,装在他自己做的大木箱子里,那是他的军装,新的,旧的,这么多年爹还保留有两套新的军装棉裤,母亲把这两套棉裤分给我和弟弟,作为对爹的念想。
很长时间,我不敢去触碰爹的这些东西。在我对爹的怀想中,我一再跟弟弟说,谁也不要去动爹的任何遗物。
一个山村的师傅:手艺
在我小学初中的那段时间,爹一直在大队加工厂。后来我上高中的几个假期,帮他在加工厂加工面条。和面,碾皮,压条,晾挂,然后切成一捆一捆。这是我所学的第一个与生存有关的手艺。
我的记忆,不是如何制作面条,而是那部195型的立式柴油机。那时,村里很少有工业化的产品,除了收音机,就是这部柴油机。这两种一粗糙一精密的机器,很长时间浓缩着爹的手艺,成为爹在村里的荣光。在尝试过几次之后,我学会了用很小的油门,在力气即将用尽的时候松开减压,终于也可以用摇把启动柴油机了。但是在冬天,无论我怎样用劲,哪怕一连三个来回,那柴油机在我松开减压停止摇动的刹那,哼了两声,就一动不动。这时,爹找到一根铁丝缠住的抹布,伸到废柴油里沾一下,拿火柴点燃伸到柴油机的进气口,叫我再摇。我已经精疲力竭,却依然带着好奇一把扣住减压,把着摇把慢慢摇动起来。爹伸在进气口的那团火苗顿时一伸一缩般,刚被吸了进去又被吐了出来。爹说,注意摇把打人,加把劲!我于是咬住牙闭上眼,一圈一圈地加快速度,只觉得胳膊木然般在做机械运动,整个身体要飘起来似的,不自觉间手就松了减压,摇把也脱出了飞轮,只觉得耳边忽然嗵嗵嗵地响起来。柴油机启动了,爹加大油门,拿一把扳手上好皮带,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
我见过一次爹修柴油机。有一天,柴油机忽然砰地一声,就熄火了。另两个人看着爹,意思是只能靠他修了,而他们这时就成了帮手。爹把柴油机全部拆开,螺丝和小零件放在一个装有机油的铁盒子里,大件放到地上,不出半天,半人高的柴油机就成了一堆油腻腻的铁。就是这次维修,我对柴油机有了初步概念。汽缸是怎样的,活塞和活塞环是怎样的,气门挺杆是怎样的,曲轴是怎样的,还有油封、滤油器、化油器、滤清器等,我有了大致印象。第二天,爹把拆开的这些零件又组装起来,快要装完的时候,爹忽然要在旁边帮手的那个人去供销社买二两八号铁丝。那个人出去不到十分钟,估计还没到供销社,爹已经全部装好了,叫我摇燃。我拿起摇把,一口气摇了十转后忽然松开减压,柴油机就欢快地响起来了。不一会儿,买铁丝的人空着手回来了。爹问,铁丝呢。那人说,我听见机器响了,想到不要铁丝就回来了。爹从柴油机沙锅内取下机油尺,说,这个环得换换,怎么不要呢。
后来,我听见那个人开玩笑说,爹是怕他学到了诀窍,故意把他支开的。这件事情,我没有问过爹,但我后来明白,爹给别人修一次柴油机,除了管吃管住,还要收十五到二十块的工钱。我们一家人,就因为爹有着这样那样的手艺,即使在最艰苦的时候,也没有旁人过得那么艰辛。爹去世后,照土家族的风俗,打一夜丧鼓。买铁丝的人是治丧的督官。在他和另一人的安排下,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
有七年多时间,我在一家时尚服装企业工作,期间还主编企业的一本时尚杂志。关于时尚,关于服装,我从这里得到启蒙。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爹和这家企业的老板一样,他们最初是一个裁缝,只是选择的生活不同,他们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因此也很不同。
爹会缝纫,像他的很多手艺一样,主要是用来自用,也属于无师自通。在我十几岁时,家里就有了一台大桥牌缝纫机,爹在缝纫机上给衣服打补丁,用拆开的旧衣服缝袖笼子,后来我姐姐还在这缝纫机上缝鞋垫子。一般在过年或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出门做客时,我妈会提前扯回来几尺棉布预备。到了下雨天,爹在家支起案板,铺开那块布,拿划粉在布上画出一些线条,那些线条有的直,有的弯,有的半圆,有的交叉在一起,有的交叉后又冒一些出来,一件衣服的雏形,在爹凝神思考中渐渐显露出来。画好了,再用裁剪一刀一刀剪开。往往这时,爹会让我帮忙倒线,把线团上的线转到底线轴上。这是我很乐意的事,脚踩着踏板,扶着细细的黑线,任它在指丫间水一般流动,有点酥痒的快感,于是脚下加劲,嘭的一下,那线就断了。裁剪好了布料,我也把线倒完了。爹卸下缝纫机头,将锁边机头装上,穿好线,在突突声中将边都锁好了。然后再换回机头,正式缝纫。爹端坐在缝纫机前,一手在胸前掌着布,另一手的食指带着压脚,小指头带着布的方向,脚下一动,两块折叠在一起的布之间就走出一条细密的针脚,不出两个小时,一件衣服就出来了。
很长时间,花屋场是没有裁缝的,村人缝衣服要到邻近村里的佘师傅家去,佘师傅是远近闻名的裁缝,和我家带点转折的亲戚,我妈有时候也过去找他缝点什么。我家虽有缝纫机锁边机等一应工具,爹却从不给外人缝任何东西,他的缝纫只是给一家人用。在这个意义上,爹不是一个裁缝,缝纫也不是他的手艺。或者,爹对服装也有着某种热爱,在崭新的布上划出红黄的线条,听见剪刀沉稳而清脆的声响,看见一块块布料在手上缝合成一件衣服,设计的快感,或者是居家温暖的快感,都有点不可抗拒。渐渐,供销社不卖布了,店头直接挂着成衣,裁缝在刚刚升起温度拥有一大批刚出师的学徒后,竟然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裁缝从乡下进到城里,变身为设计师、打版师、车工等行当,成为工业化流程中的一个无论多么重要也都毫不起眼的一个细节。爹也逐步习惯买衣服穿,那台缝纫机,起初还用来缝缝补补,后来就只有姐姐偶尔来缝一下鞋垫,以至于终于冷落到墙边,长年盖着最开始的那块厚厚的帆布。
回想起来,爹对生活也是这样,不断设计,不断将设计稿亲手变成他想要的东西。他这种设计看似散漫,实用中甚至带点自娱自乐,却使我们一家人保持着幸福平安。他对生活的精心设计,对我们几个子女却有着一些放任的空间。我一直在想,这是不是也是他的一种设计?
遗憾的是,爹的所有手艺,都被他带进了尘土,我们三个子女,谁也没有继承他的衣钵。
一颗心的无限:世界
在花屋场,我家最早有一台收音机。1970年代,收音机在花屋场还是一个神秘的物件。爹从部队带回来的是一个小小的矿石收音机,据爹后来描述,当他把收音机摆在大桌子上调出声音时,他的父辈先是惊讶得半天不敢出声,诧异人怎么能够装在那么小的一个盒子里,继而小心翼翼地凑近,绕着桌子看来看去,想从那盒子的缝中看到里面的小人儿在怎么拉二胡在怎么唱歌。爹的一个叔叔无限感叹:那女的声音真好听啊,一听到这声音就想象得出人长得有多么乖!起初,大家都一致附和,过了一阵,这附和的人又一起来笑话这个叔叔,仿佛当初自己没有赞同过他的观点。
红旗牌收音机是爹转业后的事情。红旗收音机有两个波段,中波和短波,能收很多台。除了天线之外,还有一根连在墙角的地线,每当信号不好的时候,爹就会往地线上浇些水,声音马上就清晰起来。有好几年,这收音机保持着村里唯一的纪录。同村里结婚,做满月酒,红事白事,收音机都成了要借的必备之物。借的时候,是借的人家自己来背回去,还的时候,还是借的人家背着还回来。借去的收音机,放在堂屋正中的香火台上,声音开到最大,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这过事的人家就有了面子和热闹。
平常在家,爹也喜欢播放中央台。往往,趁爹不在意的时候,我调成少儿节目《小喇叭》,哒嘀哒哒嘀哒,小喇叭开始啦!爹主要听新闻和天气预报。每当要播放天气预报的时候,爹时常把收音机从香火台拿到门外挂起来,把声音开到最大。第二天,村里就流传着明后天的天气状况,有人没听太清楚,总要找个机会,顺便问一下爹,心里才格外显得踏实。
1976年的一天,收音机忽然播放出低沉的哀乐。爹无比伤痛地说,毛主席去世了。第二天,我们全家人戴上青纱,到大队参加悼念毛主席的大会。一路上,爹的眼睛里噙着泪水,我奇怪地看着他。到了大队,我发现几乎所有的人在哭,而爹终于哭出了声音,我顿时也号啕大哭起来。
这是生命中第一次,为一个人的离开,朦胧地感到伤痛。当我再次从心灵上面对一个人离开人世时,这种伤痛已被时间之水深深覆盖,在我日渐平静的面容下,是始终难以释怀的长长隐痛。生离死别,无论以何种方式,都是生命中最动情之处。
花屋场处处显得落后,因而也处处显得淳朴。很长时间,地里的犁铧用过后就插在地里,以便第二天接着再用。有时候因一场雨或别的什么事情,将犁铧忘在了地里,日晒夜露,那花栗树的手柄长出了白色带着细细绒毛的菌子,依然稳稳地插在地里。很多人并不锁门,养了一条狗作为来人的动静,狗就像现在人们手里汽车的遥控钥匙,来人时汪汪叫几声,再听听脚步和咳嗽,大致就知道来的是谁。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现代电器开始走向农村,我们家也买了一台熊猫牌黑白电视。自从有了电视,爹的晶体管电子管收音机就渐渐冷落下来,起初从堂屋的香火台上移到睡房里,再移到他的枕头边,四节电池完了,就几乎再也不用了。自此,爹在晚上7点,要准时收看新闻联播,接着看天气预报和焦点访谈,之后,就是妈的电视剧时间。而爹这时就去洗澡,然后上床睡觉。在我的印象中,爹向来保持着早睡早起的习惯,即使在生病中,也绝无例外。
爹看了新闻,喜欢和人谈论国家大事。中央出台了什么政策,有了什么精神,要在农村采取什么措施,他都一清二楚。有一次,住在高山上的姑父在席间和爹闲聊,说着说着,就从田间地头转到了国家大事。姑父说,这中央的政策都那么正确,怎么一到我们这里就不灵了呢?爹听到这就不说话了,我不知道,他是真不清楚,还是愤怒到什么也不想说,只在心里悄悄存下一种美好愿望。此后,爹渐渐少谈国家大事,把心思用到科学种田上去了。当然,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直到他病得倒床之前,都是他铁定的节目。
2001年,我曾将一岁的女儿留给父母照料,到广东试图寻找到另一种生活。两年以后,我从深圳回到花屋场,女儿已经三岁了。晚上我抱着孩子陪爹边看电视边拉家常,女儿忽然伸出小小的手指指着屏幕说:温家宝!
这样的村庄作为一种存在,也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或者也可以看作世界多元性不可或缺的体现。她在封闭和固守中保持了自己的秉性,常常以新奇的眼光和双耳对待外面的世界。尽管有时外面的世界对这样的封闭持有某种不屑,一旦他们在都市碰得头破血流,这样的村庄又成为他们暗自疗伤的去处。
一种终结的身份:农民
无论爹有什么手艺,爹最终都是一个农民,而我无可回避地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从1968年带病转业回乡开始,爹开始了他贯穿一生的农民生涯。
在他十七岁之前,他还没有完全学会种地,部队生活八年后,拿过枪柄的手开始拿锄把了。在生产队,爹得到了一个参谋长的绰号。这个绰号,大约与他当时的见多识广有关。关于爹在农业社、生产队、互助组、承包小组的种地事迹,我当时还是一个顽童,成天只知道和小伙伴们疯来疯去,根本没有什么记忆。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我们家的粮食吃不完了,爹第一个当了养鸡专业户。那年开春,爹到县里买了300只良种小鸡,回来后把屋后的空地围起来,做了好几个鸡笼和食槽,养鸡场就开张了。很长时间,我不习惯一群公鸡早早地打鸣,却没有任何办法。为了把鸡养好,爹买了好几本关于养鸡的书,怎样配饲料,怎样防鸡瘟,怎样孵小鸡,书被他翻了一遍又一遍。大约两三个月后,有鸡开始下蛋了,并渐渐多了起来。我记得,几乎要每隔两天,妈就要背着一筐鸡蛋去供销社卖。那一年,我们家开始富了起来,县里还奖励给了爹一床线毯。
不久,全县开始涌现万元户,据说山上有户人家在算万元户时,几乎找遍了家中所有,算来算去还差六七块钱,忽然发现墙头还有几把晒干的萝卜菜,由于不好定价,就按七块的总额除以萝卜菜的重量计算,终于算成了万元户。这个段子在村子里流传很广。不想第二年,上面就有人来找爹算万元户了。但爹不愿意,他觉着专业户这个称呼很好,他喜欢这个虚帽子,他说这样的虚帽子实在。遗憾的是,这鸡养了不到三年,最终还是鸡瘟无以攻克,在鸡们大面积的死亡之后,养鸡专业户开始只养几只鸡下蛋自己吃了。
不养鸡了,爹专心种地。地是承包的责任地,种什么都可以。爹有一本书,叫《科学种田》,里面讲玉米油菜如何套种,小麦如何高产,从土壤特性到如何巧施化肥,每样都讲得详尽细致。种了粮食作物,又种经济作物,施了化肥,还要喷农药。在我的印象中,在不同的时令,爹种过的粮食作物有玉米,油菜,大豆,花生,小麦,芝麻,红薯,土豆,经济作物主要是烟叶,后来又栽了不少经济林木,主要是板栗树、核桃树、银杏树和杜仲树,现在门口的那几棵银杏树,已经有人出到四五千的价格了。爹在种好地之余,总想找一些新鲜的品种试验。花屋场以前是不种西瓜的,西瓜就是爹第一个引进种植的。像这样的,还有很多蔬菜瓜果,香瓜,地瓜,蛇豆,等等,都是爹先种起来,然后把种子一家一家地传出去。
关于土地,我在医院陪爹住院时,写过一篇叫《村庄之上》的文章,文章中描述过爹的上一代对土地的深情,这种深情在爹这一代,充满了眷恋,也有一点迷茫,我的父辈,他们作为最后一代传统的农民,最终保留了对家园和土地的无限热爱。在他们之后,土地将不再充满灵性,而只是一种资源,是一种逃离无望而用以交换的物质。
在睡觉前,在睡梦中,我反复地回忆叫做花屋场的那个村庄,我想,最后一代几千年意义上的农民,他们最终实现了自由耕种无徭无役的梦想,而到他们苍老的时候,他们的葬礼,是一代农民的葬礼,少一个老农,就荒芜了一块土地。
关于爹,我很长时间在醒着的时候想着他,而最近才梦到过他一次。这个梦,在我醒来时已经破碎到不完整。依稀记得,大约是爹手术后,我和爹在某处,爹从后面一把揽住我说,我知道,我这个病是不治之症。我回头看到,爹充满病容的脸上,洋溢着慈祥和平静。在对这个梦的追寻中,我忽然意识到,我已经开始了对爹的下意识虚构。一个与我最亲的人,过去那种现在进行时已经不可能再有了,无论我对他的情感怎么真挚,我只能借助梦幻这种真实的形式进行下意识地虚构,在这种虚构之间,我对事件的回忆也忽然变得不那么完整可信,明明他还活在我的心中,却真的阴阳两隔。
关于爹的世界,我可能真的需要虚构,才能把心中的那个爹刻画出来,才能把他的神情面貌和他的精神世界释放给他的子孙后代。随着岁月的递增,爹越来越远离真实的个体,逐渐进入到一个家族的精神世界,先是成为我的文字,继而成为一代先人,成为我心中隐藏着的一个神,成为列祖列宗。而我对爹的虚构,只能在我经历过、看到过、听说过、感受过的基础上,最终在精神上完成爹的真实复原。
在深圳的一天,我和朋友喝完就酒打车回家,看着后视镜中自己疲惫而渐红的脸膛,不知为什么,我竟然在心里对着那个自己喊了一声:爹!回过神来,我已泪流满面。
从此,爹从我的生活中渐渐远去,从一个亲近的人,成为纯粹的父亲,成为我心灵的神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