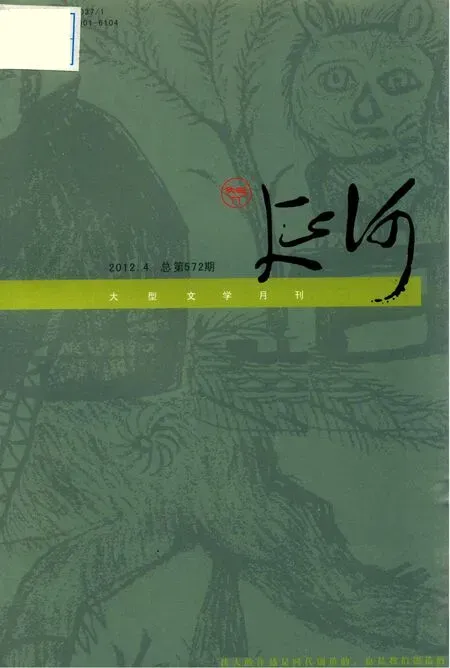西夏简史和一个学者的“西夏学情结”
2012-12-18王蓬
王 蓬
本讲座,是作者献给一位中国西夏学专家及其研究历程的崇高敬意!
他独守荒陵,只为了编写《夏汉字典》。整整7年!他从发掘出土的残破砖瓦中找到有价值的残碑多达3270块,写出《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
贺兰山下,大戈壁滩,冬天滴水成冰,北风尖利;夏日酷热难耐,蚊虫叮咬,每天他都沉浸在新的发现成果中,对身外一切则全然不顾!
他在荒芜的王陵散步,白霜如银的清晨,风清月朗的夜晚,看着那些掩没在荒芜草中的赭黄色塔形陵墓军阵般排列,900年前那个马背上的民族仿佛眼前复活。
讲述中国著名西夏学专家李范文,讲述西夏历史及其专业研究者背后的故事。
丝绸之路,历经千载,沿途有不少建在绿州上的城邦王国和部落汗廷,或被风沙掩埋,比如楼兰国、精绝国;或被战火吞没,比如回纥汗廷,吐谷浑王国;没有一个像党项羌人创建的西夏王国,立国近200年,占地2万余里,且能在与中原王朝北宋的抗争中,三战三胜,尤其好水川之战,被史学家誉为足以同淝水之战相比,西夏首领李元昊以弱抗强,虚实结合,灵活指挥,大败宋军,兵锋直逼关中,北宋王朝只好赔款议和。公元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国,传位十代,制定典章,创造文字,占据丝路咽喉河西走廊两个世纪之久。之后,西夏在成吉思汗如大海波涛般汹涌的铁蹄下覆灭,数百万臣民不知去向,尤其贵族王室后裔消失的无影无踪;在贺兰山下,留下众多被称为东方金字塔,谜一样的西夏王陵;再是比繁体汉字还要复杂的西夏文字,人亡政息,无人破译,遂被岁月掩埋。
19世纪,地理大发现在欧亚掀起热潮,一批西方探险家把目光转向亚洲腹地和中国内陆,继敦煌藏经洞、楼兰古城遗址被发现,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弄走了大批经卷、文书和壁画,急红了眼的俄国人科兹洛夫也在古居延西夏黑水城发现和掠走了大批西夏经卷、手稿和文书,在国际考古学术界引起巨大的震动和反响,继敦煌学、楼兰学之后,又添上了一门西夏学。能够做为一门新诞生的综合交叉性学科,西夏学涵盖丰富,举凡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政治格局、郡县设置、官吏任命、典章制度、司法律令、经济状态、民族组合,林林总总,包罗万象。
依据常规史书与文字是了解这些“国情”的窗口和钥匙。偏偏,中华五千年,二十四史中,有《辽史》,有《金史》,却没有西夏史,而西夏自身创造的文字,形体与汉字相似,初看似能认识,细看无一字能识,如同天书,复杂难辨,这也给西夏学的研究增加了难度,破译西夏文已成考古学术界一道急待攻克的难题。
中国学者在西夏文的破译上做过许多努力,清代河西学者张澍在武威大云寺发现西夏碑,正反两面有用汉字与西夏字分别书写的碑文,为《宋史》记载西夏创造“番字”提供了实物依据,引起国内外学者瞩目。仅依据此碑制成的汉文与西夏文拓本,便有多种文本出版。之后,曾在甲骨文研究取得不小成就的罗振玉、罗福成父子,王国维、陈寅恪、王静如等学人对艰涩难懂的西夏文也进行过多方面探索。可惜,此后随着这些学人的先后离世,西夏文的研究便陷入沉寂。直到1972年,西夏文的研究终于启动,为一个人破译一个神秘王国的“神秘天书”提供了历史机遇。这个人便是我国著名西夏学专家,宁夏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李范文。
李范文涉足“绝学”,攻克“天书”,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历经坎坷,倍受磨难。
1931年,李范文出生于陕西汉中西乡一个普通教师之家。汉中盆地因南北有秦巴拱围,其间有汉水滋润,汉王朝以此发祥,颇有名气。汉中历代文风炽盛,讲求耕读传家,西乡弹丸小县,便出了一代学人,解放后任北大首任党委书记的江隆基,曾任彭德怀秘书、中央民族学院党委书记的张养吾,再是天津美院院长陈因,北京市教育局负责人的刘力邦等。耳濡目染、默移潜化,李范文亦自幼刻苦、品学兼优,1952年一举考取中央民族学院语言系主攻安多藏语。中华民族为多民族国家,语言文字历来是文化文明薪火相传之工具,属基础且根本的学科。数千年间,各民族融和交流又各自形成民族特色的过程中,其语言文字也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若钻研进去,亦能感受到这是一个博大精深、气象万千的世界。公允地说,解放以后五十年代初,曾大张旗鼓号召:向苏联学习、向科学进军。知识界很欢欣鼓舞过一阵,已在北京读大学的李范文自然也不例外,做为教师家庭子弟,他深知一切都来之不易,格外刻苦奋进,教室、宿舍、图书馆,到处都能见到他勤学苦读的身影。也许要归结到命运,应该发生的事情迟早总会发生,大约是在读大三的时候,李范文在学校的图书馆中偶然见到被称为“天书”的西夏文,那一瞬间,李范文竟像被人砸了一拳,他被西夏文虽然繁复却优美飘逸的字形吸引,这种吸引竟在他内心深处掀起波澜久久不能平息,以至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使他在半个世纪中与那种优美飘逸的西夏“天书”结下不解之缘。
若是细究,偶然中也带着某种必然,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幼小时大都经历过毛笔字的基本训练,这便是所谓的“童子功”。在这个过程中,不少人会与笔墨纸砚结下缘分,注入情感。以至每每提笔便心血齐涌,有飞扬灵动之感,对毛笔字的喜爱会影响毕生。笔者与李范文先生联系交往,所得书信,少则两三页,多则十数页,竟全用毛笔书写,可见毛笔字在李范文心中的情结之深。西夏立国,正值北宋,宋代修文偃武,把中国文化推向鼎盛,“苏、黄、米、蔡”,诸家竞秀,亦把中国书法推向峰巅。依据繁体汉字创造的西夏文,在文字结构,横、撇、竖、捺无不受汉字的深刻影响。书写毛笔字的人都有体会:简笔字难写,不好摆布;相反,繁体字由于笔划较多、整体结构撇捺争让,首尾气势呼应都给书家留下较大审美创造空间。西夏文由于笔划繁多,在传播沟通方面会造成障碍,但就书法审美方面,则如同龟文鸟羽,奎星曲园,山川脉势,禽兽蹄迹,造就另一种气象。这显然是让李范文“怦然”心动的最早或者说表层原因。
我以为真正让李范文心动的是因为西夏文这种无人能识的“天书”已成“绝学”,兴衰续绝、探幽发微素为学人天性,也是最可宝贵的文化品质。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复兴最终有益的是人类和社会。我推测青年的李范文正是那时就已树起涉足“绝学”,破译“天书”的雄心壮志,他日后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历经磨难,不改其志,两次对调入北京安定舒适、荣誉地位的放弃,和对边城对事业的坚守就是最好诠释。这没有什么不好,古人讲究“少怀大志”,老百姓都知道“从小看大、三岁至老”,何况上世纪五十年代,党和政府也曾号召“向科学进军!”可以想见,当初李范文会因有了奋斗的目标兴奋激动。假如能在破译西夏文方面做出一番事业,挽灭绝于新兴,纠谬误于盛世,不仅填补国内乃至国际西夏学文字研究上的“空白”,为社会主义祖国增光添彩,亦是对党和人民的最好回报。
怀着雄心壮志的李范文大学毕业后,又考取了研究生,继续深造。当时,研究生极少,关注西夏学的更是凤毛麟角,李范文对自己的追求充满了信心,但是没有想到,这年(1957年)中国几百万知识分子还沉浸在向科学民主进军的社会主义春潮之中,伟大领袖毛泽东却亲笔起草《事情正在起变化》,紧接着《人民日报》刊登《工人说话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本来,这场灾难危及不了李范文,他出身贫民家庭,根正苗红,进入大学后积极上进,还担任学院学生会主席,属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革命不正需要他这样又红又专的接班人吗!
谁也没有想到,李范文被打成右派!原因简单,反右高潮中,院党委书记动员他这个院学生会主席批判他的老师费孝通、吴文藻(冰心丈夫)等人。费孝通、吴文藻当时都在中央民院任教授,都是学有专长,术有专攻且有独立人格的学者,在学生中很有威望。费孝通因为在报上发表《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已被全国点名,在中央民院更是重点批判对象。但李范文对这两位老师却怎么也恨不起来。因此,李范文在1958年12月被正式宣布为右派。
岂料,不到一年,李范文又奇迹般地成为英雄,摘掉了右派帽子!这件事极富戏剧性。李范文被打成右派后,下放至北京四季青人民公社劳动,同去的还有北京市的上千右派。李范文去后被分派在炊事班,驻地濒临永定河的灌溉大渠,其时水量相当充沛。一天,北京市一位水文测工工作时,不慎被激流冲走,大声呼救,许多老乡和劳教干部闻讯赶来,但看着汹涌湍急的渠水,谁也不敢下去,这情景正好被李范文撞见,他正好会游泳,立刻奋不顾身跳进渠中,拼命地抓住那位落水工人,把他推向岸边,危险的是,距他们仅20多米就是一处落差近30米的跌水,李范文救起别人,自己来不及上岸,被激流冲下跌水,冲走一百多米,待到他醒来,已躺在医院病床,身上多处受伤。这起无法掩盖的救人壮举和北京市地质局的感谢信,给李范文帮了忙。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李范文被摘掉了右派帽子,被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这实在万分幸运,按说,留在北京科研单位,风浪过后一切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平静生活何尝不是一种幸福。但工作不到一年,李范文又做出一件让院领导和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大吃一惊的事情。他一连六次打报告给院领导,要求调往宁夏。这就意味着离开首都北京,去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右派分子”流放的边城远地,简直是没事找事,不要说妻子和同事们不理解,即便半个世纪过后,李范文当年的追求已经成功的今天,也要费好大劲才能理解他当年发神经般的冲动。
其实,人的心灵颇似一架永不止息的天平,政治上的失意,必定会向学术上倾斜,此塞彼通,此消彼长也是宇宙间、人世上的一大规律。当然,这是对学人而言。李范文虽然在反右后,属第一批摘帽右派,但在当时那个宁左勿右,人人争相“革命”的年头,摘帽右派也是“右派”,在政治上绝无出头之日。从根本上说,还是李范文内心深处的“西夏情结”在蓬勃萌芽,挥之不去,渐成块垒,冥冥之中发出召唤,日夜困扰,坐卧不宁,倍受焦灼,欲罢不能。其实,这仍然是中国历代传统知识分子拳拳报国之心在起作用,“天生我材必有用”,不甘心碌碌无为地度过一生!
我想,只有在这个精神层面上,才能理解李范文当初何会离京离婚,因为妻子不同意他去宁夏,提出分手,这在今天来看也没有什么不对,但“西夏情结”依然在李范文痛苦的抉择中占了上风,他最终义无反顾地登上了西行的列车,告别了多少学人梦寐以求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告别了当时六亿中国人都向往的共和国首都;任凭列车驶出灯火辉煌的北京车站,驶向遥远的中国西部,驶向贺兰山下那个还很荒凉的边城。
千百年来,岳飞的《满江红》使绵亘于内蒙和宁夏之间的贺兰山广为人知,多少人想往瞻仰贺兰山雄姿而不可得,连李范文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会呆在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而且一呆就是整整7年,每天清晨起床,抬头第一眼就注定看见贺兰山,正是那铁黑色的巨大剪影,拱围着这片荒芜千载的西夏王陵,这儿距银川市30多公里,已属大戈壁滩,偏僻荒芜的大白天也有野狼野狐,除了偶然有放牧时经过的牧人和羊群,鬼都见不着。当时就连生活在银川的人也没人来过这里,更没有人会想到,李范文盼望来到这里,已盼望了多少个年头,大学种下的“西夏情结”使他离京离婚,独奔宁夏。他以为西夏王朝的国都所在地,应该有专门的西夏学研究机构,有资深专家,有图书资料,有……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甚至连“西夏”这两个字都很少有人知道,又为什么要知道呢!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难时期,宁夏地处河套,“黄河百害,惟富一套”,虽没有像邻近的甘肃大规模地饿死人,但形势也相当严峻。宁夏当代作家张贤亮的小说对宁夏那时的饥饿有十分真实逼真的描述,救人要紧,谁还去管逝去千载的劳什子事!
李范文到宁夏后,没有研究西夏的机构可去,就被安排到宁夏师范学院历史系去当老师,但无课可上,只好去资料室管理图书资料。当时,银川虽为宁夏自治区首府,但城区街道还相当陈旧,甚至不如内地像样的县城,物资供应奇缺,文化娱乐贫乏,连电灯供电都时断时续,十分昏暗,一切都远不能同北京相比。这些李范文都全不计较,从小在农村长大、吃过苦也就知道好歹。苦闷的是不能接触自己喜爱的西夏学专业,闲愁最苦。而且,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后,宁夏还增加了两项大运动:“反坏人坏事”和“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三年苦日子刚过去,又开始折腾,“四清”、“文化大革命”,一次比一次历害。有封资修之嫌的西夏王陵西夏文之类的更是沾不上边了。当然,也不能说李范文到宁夏一无所获。从内心和情感上讲,来到宁夏总是贴近了他心里的“西夏情结”,再是到宁夏后,他又重新组建了家庭,妻子是北京市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支援大西北到宁夏来的,在商业物资部门工作,专业虽不同,却有那一代人支边的豪情,对李范文来宁夏非常理解和支持,对李范文来讲,有这一点就够了。事实是温柔但坚强的妻子后来成为他呕心沥血、废寝忘食研究西夏学最坚强的后盾。
1972年,李范文来到宁夏整整10年之后,他的“西夏学情结”出现历史性转折。年初,周恩来总理视察中国历史博物馆时,也为繁复独特、充满神秘色彩的西夏文字吸引,询问陪同参观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国内懂这种文字的人还有没有?”王治秋回答:“不多了,顶多一两位”,这便是终生研究甲骨文,并对西夏文亦有重大贡献的罗振玉父子,其幼子罗福颐,当时也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下放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周总理当即指示:“要培养人学这种文字,绝不能让它失传”,随后,罗福颐调回北京,为落实周总理指示,作为西夏故都故地的宁夏也启动对西夏学研究,对西夏王陵正式开始发掘,李范文被抽调到组建不久的宁夏博物馆,并被派到了发掘工地,由于他是“脱帽右派”,所以并不是作为研究人员,仅仅是让他管理后勤。对李范文来讲,只要是到了发掘工地,只要接近了他梦寐以求的西夏学,这就够了。天空变得明净高远,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光。这一年,李范文已经40岁,步入中年,“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他心中惟一想到的事就是抓紧时间,分秒必争地搞他的西夏学和西夏文字。那时候,他最喜欢的是每天收工之后和星期假日,别人都回家休息,偌大的工地空无一人,他独守荒陵,整天缀拾残碑编写《夏汉字典》。整整7年,他从发掘出土的残破砖瓦中找到有价值的残碑就多达3270块,写出《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为编写《夏汉字典》、《西夏通史》提出了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贺兰山下,大戈壁滩,冬天滴水成冰,北风尖利;夏日酷热难耐,蚊虫叮咬,李范文全然不顾,每天他都沉浸在收集来的断碑残垣之中,一块一块地辨识、比较,再做详细的笔录。实在困了,就在荒芜的王陵散步,白霜如银的清晨,风清月朗的夜晚,看着那些掩没在荒芜草中的赭黄色的塔形陵墓在繁星闪耀的星空下如军阵般威严排列,他仿佛触摸到900年前西夏文明的底蕴,那个生机勃勃马背上的民族,他们的前世今生,所作所为,由遥远朦胧遂渐在李范文胸中变得清晰明白。创建西夏王朝的民族属羌人一支,羌人则是甲骨文就有记载的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他们最早生活在川北、藏东和青海省东南,在青海乐都柳湾一带出土的大量彩陶图案,都有鲜明的羌人风格,尤其是一件距今5000年的彩色陶盆,画有三组图像,每组五人,手拉着手,摆动跳舞,简洁生动,头上则明显为羌人发辫,出土后震动了国内外考古学术界。表明羌族先民创造的文明不在中原先民创造的仰韶文明之下,或者说共同丰富了华夏文明。
羌人久居西北,抗苦耐寒,无论男女,皆体形高大,高鼻大眼,有阳刚之美。他们崇武尚猎,重视生育,是以游牧为主的马背民族。早在唐时,党项羌人部落开始强大,协助李唐王朝立国有功,被赐姓李,封平西公,在宁夏定居,此为经营宁夏之始。至唐末,藩镇割据,李氏集团亦渐成气候,尾大不掉。到宋时,党项一代枭雄李元昊继承夏国公位,此时,李氏家族割地封疆,已历数代,李元昊精通汉字汉法,胸有谋略,精明强悍,其文韬武略不在宋王朝任何一位封疆大吏之下,他崇尚“英雄之生当王霸”,对先辈臣服中原王朝不屑一顾,在24岁时便率军采取突袭方式一举攻占回鹘王廷甘州,回军途中,又声东击西夺取凉州,把控制的地盘扩展到千里河西。
这位党项英雄,携挟风雷,于公元1038年在宁夏兴庆(银川)正式宣布成立西夏王朝,李元昊登上皇帝宝座,年仅38岁。之后,又在贺兰山下,黄河两岸,驰骋厮杀,抗辽攻宋,占地划疆,农牧并举,开科取士,制定典章,创造文字……很轰轰烈烈地干了一番大事,开创的西夏王国竟传位十代,历200年之久。至于他赖以立国建都的京畿腹地宁夏,李范文已定居十年之久,他对这里山川地貌、气象物候、历史沿革、人文景观、民族人口、经济状态、文化教育……无不细心研究,了然于胸,他认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宁夏这片土地能够成就西夏王朝、西夏文字、西夏文明绝非偶然。
宁夏虽属面积不大的内陆省份,却因位于陕西、甘肃、内蒙之间而举足轻重,可谓东接关陇,西锁西域,南通祁连,北控大漠,且黄河流经此地,滞留大量泥沙,形成水草丰茂、可农可牧的河套平原。古语“黄河百害,惟富一套”便指这里,所以是古代游牧民族进犯中原集中和必经之地。中国古代建都关中的中原王朝无不重视宁夏的防务,早在秦代,便在此设郡筑城,开渠屯田;汉代曾迁70万汉民充实宁夏;唐代亦设朔方节度使,由名将王忠嗣镇守;“安史之乱”发生,唐肃宗便是在宁夏灵武登基,调集各路兵马平叛,使盛唐文明得以延续。党项羌人正是占据了宁夏这块风水宝地,才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王业。
自己要研究西夏学,要破译“天书”,若不来宁夏实地感受,高高在上,空守书斋,研究就是一句空话!
大千世界、宇宙万物,莫不相互关联,相互渗透,互为因果。此时,他对涉足“绝学”,攻克“天书”已是胸有成竹,蓄势待发,充满了信心。他已不满足于仅仅对西夏文的破译,他对公元十一世纪,并列于华夏大地的宋、辽、夏、金已有全面把握和认识,他对史家著有《宋史》、《辽史》、《金史》而惟独没有《西夏史》大为不满。他认为中国历来史学发达,早在汉代便设有专门修史机构,司马迁父子均为朝廷史官,否则怎么会有国史开篇巨著《史记》问世。与西夏并存的宋代史学更属鼎盛,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范仲淹等不仅为朝廷重臣,身居要津,且均是与西夏王朝直接打过交道,办过交涉,曾亲历、亲见、亲闻西夏兴衰,又皆为一代大家,其史才不在司马迁之下,欧阳修所著之《新唐书》、《新五代史》,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均附有《西羌传》等涉及西夏的重要文献,可惜没有专门立国史。当然,这也因西夏文繁复艰涩,在蒙古铁蹄下覆灭,缺乏直接史料记载有关。元统一后,痛恨当年西夏的顽强抵抗,六次讨伐多次大战方才攻克,致使一代骄子成吉思汗病逝阵前。故而,不修西夏历史。千载逝去,尘埃落定,无论如何,应该有一部堂堂正正的《西夏史》,每念及此,李范文便热血沸腾,不能自己,他暗自给自己定下两大目标:一是破译“天书”,出版一部能让西夏文千古流传的汉夏对照的《夏汉字典》,二是出版一部《西夏通史》,真正探幽发微,兴衰续绝,填补历史留下的空白,绝不能让中国学人对在中国本土诞生的国家研究“失语”。
西夏立国近200年,但党项人的崛起,则可追溯至唐初,李氏家族长期受中原汉文化影响,深知文化文字、典章制度的重要,故开国之初,李元昊便命精通熟悉汉字汉文的大臣野利荣仁创造西夏文,利用汉字的偏旁部首,重新组合,共创造出5000多个西夏字,形体方整,笔画繁冗,初看如汉字仿佛能识,细看却无一字能认得。而且,党项羌人原来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其发音使用和日常用语与汉字汉音相距甚远。用这种重新创造的文字去反映与汉语完全不同的发音与拼音,其学习掌握的难度可想而知。况且这种文字语言自西夏灭亡后,800年来无人使用,成为地道的死文字。
偏偏,西夏文自开国创立,就被尊为西夏国字,应用范围很广,几乎涉及西夏国需要用文字书写的所有文件,举凡典章制度、法律条文、官吏任命、佛教经典、学子课本、借贷文书,几乎无所不包,从19世纪初,俄国人在黑水城发现的大量西夏文书文献和西夏故地出土的各类文字,无不是用西夏文书写,所以要了解那个神秘的西夏王国,破译西夏文就成为关键,李范文为自己定下的两大奋斗目标:完成《夏汉字典》和《西夏通史》,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两相比较,《夏汉字典》则为重中之重。目标明晰,李范文把精力主要放在对西夏文残片收集和识别上,要编好这本《夏汉字典》,首先要懂西夏字的音韵,这种千年之前使用过的文字及其韵律失传太久,西夏亡国后,其臣民逃亡分散各地,早已汉化或融入其它民族,几乎找不到再使用的民族,哪怕是极少的个案。当时国内只有古文字学家罗振玉的幼子罗福颐还懂西夏文,但也年过花甲,李范文去北京向罗福颐先生借来西夏文献,不顾酷热,硬是把文献重新抄录了一遍。做学问,摘文献,卡片是必备工具,但那个年月,宁夏却没有人造卡片、售卡片、用卡片。这些事难不到李范文,他找到一种适合做卡片的硬纸,自己动手划样、切割,没有卡片盒,他也找来三合板的边角废料,自己制做,三万多张、近百斤的卡片竟是用如此原始的办法制成。凡见到至今保持完好的原始卡片的人都无不感叹:非大智大勇者不可为之,非意志顽强者不可担当!
1977年,西夏王陵首次发掘工作结束,需要有人留守现场,西夏王陵远离市区,荒芜可怕,谁都想躲开,领导只好决定让李范文留守,他也愿意留守。他的目的十分简单,这里安静,无人干扰,正好破译西夏文,不定那些躺在这里的西夏亡灵冥冥之中还能给自己帮助呢!日后,著名学者余秋雨如此评价李范文:“当初李范文用一个帐篷、一袋大米、一碟咸菜在西夏王陵守望和解读了7年,他是一个真正的田野工作者,值得人钦佩。西夏有幸遇到李范文,因为他的解读,西夏王朝才被世人聚焦”。
何止7年,从1972年李范文到西夏王陵当伙管员,到《夏汉字典》1997年正式出版,李范文用了整整25年时间,这期间,单是为了解决字典的注音,李范文便根据历代典籍记载的点滴线索,仔细分析判断出西夏遗民流失的去向,到川西北高原和甘肃河西走廊去寻找遗民后代,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些地区的交通极差,道路皆是不上等级的沙石路面,客运车辆陈旧,沿途食宿困难,但对李范文来讲,只要能对破译西夏文有用的资料,哪怕是一星半点,吃多大的苦,李范文都不在意。有谚语说:世界上没有打不开的锁子,就怕你没找到那把钥匙。真正“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也是得益于李范文当年在中央民族学院本硕连读时他所学专业安多藏语与古西夏语均属藏缅语系,当年又在甘南藏区实习打下坚实基础,这对调查十分有利,几乎是事半功倍。他深入川西北阿坝、丹巴、道孚、木雅一带,搜集到8000多个有用的单词,对西夏文及语音的形成有了更深的理解。一个独特简明编排体系在思想中由朦胧变得明晰。之后,又是数年艰苦异常的伏案工作,不分一年之冬夏寒暑,不知饭菜之酸甜苦辣,为拼组破译那些“天书”般的文字,李范文耗尽心血,近1米8的块头,体重仅剩50公斤,爱人心疼,喂了一群鸡,一次次地给他“恶补”。 整整25年的心血,赢得了《夏汉字典》的编纂成功。这部秦汉砖块般厚重的字典共有150万字,采用科学简明的检索方法,从语音、语义、语法、字型等各个方面,对已知现存的6000个西夏字进行辨形、解义、注音和例句。可谓解读“天书”西夏文的利器。这部《夏汉字典》做为世界上正式出版的第一部由现代人编著的西夏文字典,首次搭建起古代西夏语言文字与现代语言文字沟通的桥梁,为推动整个西夏学的研究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为进一步研究西夏史做出重要贡献,也让国际西夏学同仁对中国学者刮目相看。
诚如我国著名学者王仲翰教授在《西夏通史》序言中所说:“李范文先生在完成了煌煌巨制《夏汉字典》之后,又组织全国西夏史专家,历时六年写出了《西夏通史》这一部扛鼎之作。《西夏通史》是国家‘九五’重点课题,《西夏通史》的完成使我多年想看的西夏史终于看到了。”其实,这不仅是王仲翰教授的心声,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心声。
2008年国庆,我采访了李范文教授,在此之前,他曾邀请过我参加西夏学国际研讨会,可惜因事未能成行,一直遗憾。在银川市隐藏于闹市中一座普通的住宅楼里,我见到了心仪已久的李范文教授。因已经多次通信、通电话,读过专著,见过照片,没有陌生感,倒像老熟人,老人的卧薪斋亦如想象:坐拥书城。这座上世纪八十年代宁夏为高级知识分子修的专家楼,如今看来已很简陋,自治区又为李范文安排了副省级的住房,老人摆摆手,还是我这卧薪斋好!
这位学有专长、术有专攻、著作等身、享誉中外的学者,像所有真正的大家,态度谦和,说话直率,有时还有种孩童般天真。
那天李老见着故乡来人兴致很高,要带我去参观银川为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刚建成的标志性建筑“三馆两中心”,其中就有宁夏博物馆,那可是李老一生心血所在啊!其实,不仅是宁夏博物馆,途经银川的任何一条街或一个广场,李老都兴致勃勃如数家珍地谈起这些地方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那种热爱热情溢于言表,让人深深感动。
算算,李老在宁夏银川这个塞外边城已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他的努力和希望早同这片土地融合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