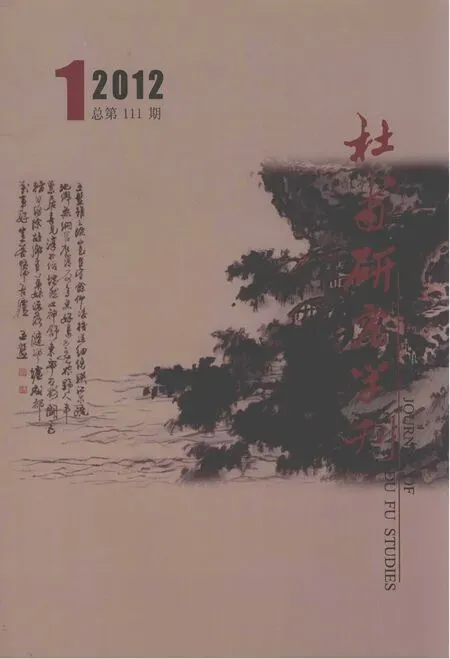元好问的杜诗学
2012-12-18赫兰国
赫兰国
元好问 (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山西秀容 (今山西忻州)人。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七月初八,于元宪宗蒙哥七年(1257年)九月初四日,卒于获鹿 (在今河北省)寓舍,归葬故乡系舟山下山村(今忻县韩岩村)。 “中兴定第,历内乡令。正大中,为南阳令。天兴初,擢尚书省掾,顷之,除左司都事,转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①元好问诗文成就极高,“为文有绳尺,备众体。其诗奇崛而绝雕刿,巧缛而谢绮丽。五言高古沉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歌谣慷慨挟幽、并之气。”②著有《杜诗学》一卷、《东坡诗雅》三卷、《锦畿》一卷、《诗文自警》十卷,采摭金元君臣遗言往行,至百余万言,成《壬辰杂编》若干卷;小说《续夷坚志》四卷等;编有《中州集》,现有《元遗山先生全集》。元好问是我国金末元初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文坛盟主,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其诗、文、词、曲,各体皆工。诗作成就最高,“丧乱诗”尤为有名。今存诗1361首,内容丰富。一些诗篇生动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动乱和百姓苦难,如《岐阳》、《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诗,沉郁悲凉,追踪老杜,堪称一代“诗史”。其写景诗,表现山川之美,意境清新,脍炙人口。诗歌体裁多样,七言是其所长。其词为金代一朝之冠,可与两宋名家媲美;其散曲虽传世不多,但当时影响很大,有倡导之功。元好问之文继承唐宋大家传统,清新雄健,长短随意,众体悉备。元好问为金代文学批评的巨子,仿杜甫《戏为六绝句》体例所写《论诗绝句三十首》,在文学批评史上影响颇大,将绝句论诗这种体式从涓涓细流推广成浩浩江河。《续夷坚志》为其笔记小说集,为金代现存的优秀短篇小说。金代汉语文学相对其他朝代较为落后,程千帆先生说正是因为元好问的出现才“使我们这金代这一百二十年中的汉语文学,消失了寂寞之感”③
元好问学杜论杜资料宏富,下面仅选其大者从三个方面论述其杜诗学思想。
一、《论诗绝句》的杜诗学
杜甫曾为《戏为六绝句》,以绝句的形式进行文学批评,从而开创了一种新颖的诗歌批评方式。元好问是继杜甫后又一个大量采用此种形式进行文学批评的大家。
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评论了自汉魏至宋代许多著名的作家和流派,表明了他的文学观点,是继杜甫之后运用绝句形式比较系统地阐发自己诗歌理论的著名组诗。作此组诗时元好问年仅28岁,虽为青年时所作,但作品中的许多见解却高出时人,颇为中肯。对后世影响很大。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论杜的篇章,共有五首。从这五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元好问对杜甫诗歌推崇有加。其十、十一诗云:④
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
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珷玞。
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
画笔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
此二首论杜甫。前一首针对元稹《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一段话而发,元稹云: “……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对杜甫的评价很高,特别推崇杜诗的“铺陈始终,排比声韵”,认为李白“尚不能历其藩翰”,何况其他人哪能入其“堂奥”呢?元好问对此甚为不满,认为所谓“排比铺张”不过是杜甫诗歌之一体,创作方法之一种,且并非杜甫诗歌之上乘,杜诗更有其“连城璧”玉,上乘佳作,只不过元稹识见狭小,并不知晓,因而舍美玉而拾石头罢了。元氏此论表现出金人特别是金末文人对杜诗的再认识,唐人重视“排比铺张”的艺术手段,其实,杜甫的长篇排律多有名篇,功力深厚,在艺术形式上也是一种新的开拓。诚如翁方纲所说:“诗家之难,转不难于妙悟,而实难于‘铺陈终始,排比声律’。”⑤元稹的评价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是不应否定的。但元好问在此强调的却并不在于此,而在杜诗关心时事、关心民瘼的题材内容。因而他指出:“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眼所接触的实境,激发诗情,自然就能写出入神的好作品来。如果没有现实社会的感受,只在暗中摸索,虚拟生活,无论如何都不是真实的。杜甫所以能在他的许多诗歌中描绘出秦川真实的自然景色和社会现实,正是由于他亲临长安,亲历感受的原故。正如施国祁注云:“少陵自天宝五载至十四年以前皆在长安,见诸题咏,如《玄都坛》之‘子规山竹,王母云旗’;《慈恩塔》之‘河汉西流,七星北户’;《曲江三章》之‘素沙白石,杜曲桑麻’;《丽人行》之‘三月气新,水边多丽’;《乐游园》之‘碧草烟绵,芙蓉波浪’;《渼陂行》之‘棹讴间发,水面蓝关’;《西南台》之‘错翠南山,倒影白阁’;《汤东灵湫》之‘阴火玉泉,横空浴日’;凡兹景物,并近秦川一带,登临俯仰,独立冥搜,分明十幅画图。都在把酌浩歌,旷怀游目中,一一写照也。”⑥这里元好问对那些没有亲身体验而凭空捏造和发表感慨的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因此他认为杜甫的长篇排律与其他作品相较,反映现实不够,表现了某种追求形式美的倾向,着眼点不同,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看来,元好问论诗是强调真情实感的,认为有实历,有真情,才能写出好诗。其《论诗绝句》十五云:
笔底银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饭山前。
世间东抹西涂手,枉着书生待鲁连。⑦
此诗论李白,但亦涉及到杜甫。《旧唐书·李白传》载:“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有饭颗山之嘲诮”⑧。唐孟棨《本事诗》中有云:“太白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盖讥其拘束也。”元好问首先赞美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认为李白之诗直如庐山瀑布,从九天飞落,气势豪放,不像杜甫那样“晚节渐于诗律细”“语不惊人死不休”“新诗改罢自长吟”,深思熟虑,冥搜旁求,以至于“憔悴”伤神。更有别于世间那些“东抹西涂”之人,东剽西窃,求奇求怪。这里元好问只是强调了李白诗风与杜不同,并没有指责批评杜甫之意。正如元好问《自题二首》其一中说:“共笑诗人太瘦生,谁从惨淡得经营。千秋万古回文锦,只许苏娘读得成。”⑨人们都讥笑诗人作诗伤神费力,太过认真,以致“太瘦生”,谁又能象杜甫那样“惨淡经营”,一丝不苟呢?回文诗所以流传千秋万代,只是因为苏蕙才有那样的真情实感,才写得出来。由此可知,元好问并非反对“惨淡经营”,而是主张要有真情,要有实际的体验而已。其《论诗绝句》二十八又云:
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⑩
此首是针对江西诗派而发的,此时的元好问对江西是持全面否定的态度。“只知诗到苏黄尽”、“未作江西社里人”明确表明自己不做江西派的态度;“古雅难将子美亲”则指出了江西诗人虽标榜“一祖三宗”,却难以从精神上得杜甫的精髓。元好问认为,仅仅是以“古雅”学杜,还不可能学到杜甫诗歌的真髓,效法学习杜诗却去步李义山的后尘,只是汲汲于艺术上的所谓“精纯”,也同样不可能得其“真”。黄山谷虽然不以古雅学杜,亦不是如宋初昆体诗人那样仅学李商隐之精纯而失其真,但黄庭坚仅仅学杜甫的“读书破万卷”,讲求句法字法,以“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11相标榜,同样也不是正道,因此黄庭坚虽有“本朝诗家宗祖,在禅学中比得达摩”12的崇高赞誉,江西诗派在金朝的影响也十分深广,但元好问却论诗“宁下涪翁拜”, (关于此句的理解,历来有争论,笔者倾向于岂肯向黄庭坚下拜之意。)论诗歌创作,岂肯向涪翁下拜,并表明自己一反潮流,也不会向江西诗派学习,作江西诗社中人。所谓“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也是这个意思。正是由于元氏崇尚“真”与“天成”,所以他对宋朝一代字模句拟杜甫的江西诗派风气极为不满,认为:“谓杜诗为一字无来处,亦可也;谓不从古人中来,亦可也。”13这在当时无疑是振聋发聩之声!元氏的见解明显高于由宋入元的方回。方回入元后继续大力鼓吹“一祖三宗”的说法,欲以江西诗法挽救宋末诗坛颓势。而元氏则认清楚了江西诗人所谓“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不过是文字游戏,难以真正接近杜甫堂奥。故而元好问不肯作江西社里人。
撼树蚍蜉自觉狂,书生技痒爱论量。
老来留得诗千首,却被何人校短长?14
这是《论诗绝句》的最后一首,是借韩愈《调张籍》诗论李杜以自论。韩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这是作者自谓“狂妄”、 “技痒”,故对前人之诗作了评价与论析。自己也留下了诗“诗千首”,只好让后人去较短论长了。这是自谦,同时也十分清醒、自信,认为自己的诗作不怕被人评短论长。这与诗人尊杜及批驳江西诗派的思想是一致的。
在杜甫之后,率先以绝句论诗为题的有戴复古和元好问二人。戴复古只有十首,而元好问却有三十首之多,数量不及元好问。且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一反前人重在阐述作诗原理的论诗方法而重在衡量评论作家,始自汉代,贯穿魏、晋、刘宋、北魏、齐、梁、唐、宋八个朝代,所论述的诗人从曹植开始止于南宋陈师道,共计三十四位,数量不少,其评论亦颇精到,故对后来的影响很大。
此后,以绝句形式论诗者不乏其人,明清两代就有很多人直接明确表示自己是模仿元遗山。如清代王士祯就有《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五首》。马长海有《效元遗山论诗绝句四十首》。袁枚有《仿元遗山论诗三十八首》。谢启昆竟然仿元好问论诗绝句达到360首之多。尹嘉年竟然还以此为话题,运用绝句论诗的形式创作了《论国朝人诗仿遗山体》。由于元好问的推衍,绝句论诗这种文论样式被发扬光大,由杜甫《戏为六绝句》的涓涓细流发展成为浩浩大河,从而大大丰富了杜诗学的内容。这其中元好问的推波助澜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二、《杜诗学引》的杜诗学
元好问36岁时闲居崧山,编纂成一部专著《杜诗学》,奠定了他在杜诗学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标志着杜诗学发展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期。遗憾的是,《杜诗学》一书已经亡佚。据明代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三十二著录:“元好问《杜诗学》一卷。”《文渊阁书目》卷十著录:“《杜诗学》一部三册,缺。”(按:黄虞稷书目著录为一卷,当是有误;《文渊阁书目》著录为一部三册较为可信,否则不可能涵盖那么多的内容。)由此可知《杜诗学》当亡于明时。现有元好问撰写的《杜诗学引》一文,弥足珍贵,全文如下:
杜诗注六七十家,发明隐奥,不可谓无功,至于凿空架虚,旁引曲证,鳞杂米盐,反为芜累者亦多矣。要之蜀人赵次公作《证误》,所得颇多,托名于东坡者为最妄,非托名者之过,传之者过也。
窃尝谓子美之妙,释氏所谓学至于无学者耳。今观其诗,如元气淋漓,随物赋形,如三江五湖,合而为海,浩浩瀚瀚,无有涯涘,如祥光庆云,千变万化,不可名状。固学者之所以动心而骇目,及读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则九经百氏,古人之精华,所以膏润其笔端者,犹可仿佛其余韵也。夫金屑、丹砂、芝木、参桂,识者例能指名之,至于合而为剂,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咸之相入,有不可复以金屑、丹砂、芝术、参桂名之者矣。故谓杜诗为无一字无来处亦可也,谓不从古人中来亦可也。前人论子美用故事,有著盐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皋之相马,得天机于灭没存亡之间,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为可略耳。
先东岩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以为今人读杜诗至谓草木虫鱼皆有比兴,如试世间商度隐语然者,此最学者之病。山谷之不注杜诗,试取《大雅堂记》读之,则知此公注杜诗已竟,可为知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乙酉之夏,自京师还,闲居崧山,因录先君子所教与闻之师友之间者为一书,名曰《杜诗学》,子美之传志、年谱,及唐以来论子美者在焉。候儿子辈可与言,当以告之,而不敢以示人也。六月十一日河南元某引15
“杜诗学”的概念由元好问提出并建立,并不是偶然的。首先,这是由人们对杜诗研究学习的发展情况决定的。两宋时期是人们研究学习杜甫及杜诗的高潮时期,注家蜂起,论者云集,如赵次公《杜诗证误》、无名氏《千家注杜诗》、鲍彪的《杜诗谱论》、杜田《注杜诗补遗正谬》、徐居仁《门类杜诗》等注杜之书,陈师道《后山诗话》、严羽《沧浪诗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魏庆之《诗人玉屑》、张载《岁寒堂诗话》等论杜之作,皆前赴后继、新见迭出,各出机杼、特点鲜明。但受宋代政治文化的影响,特别是理学思想及议论诗风的时代风气影响,宋人研杜论杜多从微言大义出发,尽力挖掘杜诗的忠爱之思,多借杜诗的思想内涵激励自己和他人,崇尚气节与人品,更多的是关注杜诗本身的社会功用。成果虽然丰富,但从学术层面对杜诗进行总结,尚有所未及。特别是对于整个两宋时期论杜学杜的经验教训、优长不足进行概括总结,虽有必要,但却尚未进行,而有待于后来者。其次,也是由金代末期的社会政治形势决定的。金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一个国家,本身对中原文化无特殊的兴趣。特别是金代初期,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杜甫诗歌与金统治者的官方意识形态严重抵触,因而杜诗在北方并未得到广泛的传播,对北方文人并没有产生多少直接的影响。但是到了金代后期,这种情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宋的杜诗研究成果逐步传到了北方,并产生了较大的反响。金初虽然也曾刊刻过杜诗,但却并不多。而到了金末,赵次公、杜田、鲍彪等注杜之书,诸家论杜之作皆进入北国,影响所及遍于士流。金朝面临蒙元的威胁,亦须杜诗这样的爱国忧民之作以激励士气,不再抵触杜诗。因而对杜诗的研究蔚然兴起,这也是时代使然。再次,元好问本身的条件所决定的。元好问学问深厚,曾师从当时著名诗人赵秉文,并与当时京师文坛众多文人交游,诗酒酬唱,切磋琢磨,成为了金代著名诗人,对于诗歌创作有着自己独特的深刻体会。他从小喜好杜诗,自己虽未直接笺注过杜诗,但他对杜诗的认识却是十分深刻的,年轻时所作的《论诗绝句》便是明证。加之他生活的年代,在元蒙统治者的侵扰下,金政权风雨飘摇,江河日下,有似于杜甫所处的安史之乱时期。元好问感同身受,因而对杜诗及杜诗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全面地总结,从理论与实践的高度上将杜诗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提出并建构《杜诗学》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元好问的《杜诗学》是他精心撰写的一部论杜学杜的学术著作,从《杜诗学引》一文中我们不难窥见元好问论杜学杜的见解与精华。首先元好问总结了两宋时期人们注杜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元好问认为两宋时期注杜者“六七十家”,人数众多,他们的功劳,在于“发明隐奥”,即对杜诗中隐藏的深奥意蕴发明揭示出来,让读者懂得杜甫的思想及感情。其中蜀人赵次公的《杜诗证误》成就最大,“所得颇多”。元好问充分肯定了赵次公对杜诗的功劳,可见他对当时诸家之注是非常严肃认真对待的。与此同时他又指出各家注杜的毛病: “凿空架虚”,毫无根据地凭空捏造,穿凿附会;“旁证曲引”,到处引经据典,所谓“无一字无来处”;“鳞杂米盐”“反为芜累”,繁冗芜杂,头绪纷乱。总之,繁琐考证,毫无根据。这其中以“托名于东坡者为最妄”,假托东坡之名注释杜诗的最是虚妄不实。并进一步指出,“传之者过”,不分真假、以讹传讹的人是杜诗传播的罪魁祸首,最应受到批评。
其次元好问高度评价了杜甫及其诗歌创作。他认为“子美之妙”在于“学至于无学”,达到了高深莫测的神妙境界,正如他在《陶然集诗序》中所说:“方外之学有‘为道日损’之说,又有‘学至于无学’之说。诗家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后,乐天香山以后,东坡海南以后,皆不烦绳削而自合,非技进于道者能之乎?”16其诗“元气淋漓,随物赋形”,酣畅痛快,随物而变化,就像三江五湖汇为大海一样,气势浩大,宽广无边。又像“祥光庆云,千变万化,不可名状”,就是气势大,变化多。对杜诗要“读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才能真正了解他熔铸“九经百氏”“古人之精华”的博大精深和包罗万象。因此他认为“杜诗为一字无来处亦可也,谓不从古人中来亦可也”,既是继承了前人,又不依傍前人而自铸伟词;其“用故事”,即用典故,如“著盐水中”,融入诗中,毫无痕迹,是很好的;仿佛“九方皋相马”一样“所观天机也”17,“乃有贵乎马者”18(《列子·说符》),得到了一般人所不能得到的,是自然形态的,没有雕琢的本朴之真。这就高度肯定了杜诗的艺术价值和杜甫的创新精神,对杜诗进行了高度的评价。
再次,对黄庭坚论杜进行了评价。他肯定了黄庭坚“最知子美”,认为黄庭坚虽然未注杜诗,但读他的《大雅堂记》就可以知道他已经读完了杜诗。这是因为黄庭坚在《大雅堂记》中指出“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致,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19杜诗继承了《诗》、《骚》传统,自然地抒发真情实感。这与元好问在《陶然集诗序》中所表达出来的观点是一致的、相同的20,亦即“学至于无学”。同时黄庭坚在《大雅堂记》中还批评了那些“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这与元好问批判时下之人“凿空架虚,旁证曲引”也是一致的。而且元好问认为“此最学者之病”,正是那些注杜者常犯的毛病。从这里可以看出,元好问虽然严厉地批评了江西诗派,也指出了黄庭坚论杜学杜的弊端,但对黄庭坚《大雅堂记》中的论杜还是肯定的。
最后元好问提出了“杜诗学”概念并规定了杜诗学的内容。元好问认为杜诗学有三部分内容:一为元好问父亲及其师友有关杜甫的言论。这既是元好问杜诗学观的本源所自,也是其杜诗学观产生的社会条件。二为有关杜甫生平的材料,即“子美传志年谱”。知人论世,这对于研究杜甫及其诗歌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三是唐宋以来有关杜甫及其诗作的评论。集思广益,这对于进一步准确地研杜论杜也是十分重要的。其实元好问一生致力于搜集整理保存金元文物典制,金人学杜论杜情况尽数收在《杜诗学》一书之中应无疑议,如能得以流传至今,当是非常珍贵的资料,定能大大丰富杜诗学的研究内容,可惜亡佚。这不能不是杜诗学史上的一件憾事。杜甫传志、生平材料、历代评杜 (诗)汇集,就今天看来,依然是当前杜诗学研究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仍是值得注意的。
元好问《杜诗学》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杜诗学”的概念,准确地确立了杜诗学的研究范围,表现出了元好问锐利非凡的学术眼光。其开山之功是不能磨灭的。
三、《唐诗鼓吹》的杜诗学
《唐诗鼓吹》是一部特色鲜明影响深远的唐诗选本。说它特色鲜明是因为该选本只选七言律诗,显示出选者对诗艺的重视;说它影响深远是因为后世对该本的注释评点、模仿借鉴者甚多。
1.关于选者与注者
关于《唐诗鼓吹》 (以下简称《鼓吹》)的选者,历来争议颇多,至今尚无定论。大概存在四种说法:1.认为确系元好问所选,以《鼓吹》诸序及曹之谦《读唐诗鼓吹》21诗为代表。明高儒著《百川书志》,其中有云:“《唐诗鼓吹》十卷,金进士河东遗山先生元好问裕之选,郝天挺注之。”222.认为不是元好问所选,以明杨慎《升庵诗话》为代表,认为所选诗“皆晚唐最下者,或疑非遗山之选,观此益知其伪也”。23沈德潜、罗汝怀等同此说。3.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不著编辑者姓名,据赵孟頫序称为金元好问所编,其门人中书左丞郝天挺所注”24,而且就所见几个版本中,都未著录选者姓名,而直接写“元中书左丞郝天挺注”字样。4.认为是元好问之师郝天挺26所选,持此说者以清施国祁为代表。
《鼓吹》最早刊本为元至大浙江儒司刊本,大约在1308年前后。该本前有赵孟頫、武乙昌、姚隧序、卢挚跋,都说是元好问所选。赵序云“中书左丞郝公,当遗山先生无恙时,尝学于其门,其亲得于指授者,盖非止于诗而己。……唐人之于诗美矣,非遗山不能尽取其工,遗山之意深矣,非公不能发比兴之韵……公命为序,不敢辞,谨序其大略如此”。武序与赵序作于同一年 (至大元年,1308年),《武序》云:“鼓吹,军乐也,大驾前后设之……取以名书则由高宗退居德寿,尝纂唐宋遗事为《幽闲鼓吹》,故遗山本之。选唐近体六百余篇,亦以是名,岂永歌之,其声亦可匹是宏壮震厉者乎……至大戍申省属儒司以是编锓之梓,仆实董其事。工将讫,庸公适以使事南来,命仆序。仆以诸阁老雄文在前,谢不敢。公命至再,用拜手书于编末,是年六月十又八日”。姚序云:“国初遗山元先生为中州文物冠冕,慨然当精选之笔,自太白、子美外,柳子厚而下,凡九十六家,取其七言律之依于理而有益于性情者五百八十余首,名曰《唐诗鼓吹》……今中书左丞新斋郝公以旧德为时名臣,早尝讲学遗山之门……自童子时尝亲几杖,得其去取之指归。……公由陕西宪长以宣抚奉使河淮之南,欲序,故隧书此。”卢跋言: “新斋郝公继先注唐诗鼓吹集成,既命江东肃政内翰姚公端父为之序,而嘱挚跋于篇末。《唐诗鼓吹》集者,遗山先生元公裕之之所集。公以勋阀英胄,幼受学遗山公,尝以是集教之诗律,公慨师承之有自,故为之注。”26四人皆生活在元初,与郝天挺有着密切交往,距元好问亦不甚远,故其言可信;曹之谦是元好问挚友,二人过从甚密,其诗所言则更为可信。至于后来众人之疑问,多为臆测,并无实据。关于这一点,张立荣曾撰文辨析27,分析透彻,兹不赘述。
元好问此选,当是选于金末元初,故多选中晚唐战乱之诗,有所寄托之意非常明显。但该选刊刻于元初,故而其朝代归属可两属之,但它确实表达了元好问的故国之思。
元代郝天挺《注唐诗鼓吹》是最早注本。郝本只注出典,“虽颇简略”而“尚不涉于穿凿”28。其后,明代廖文炳重为补正,增加诠释,疏解诗意,成《唐诗鼓吹注解大全》。清初,钱朝鼐等又对廖氏注解进行了修正,保留郝天挺注释,该注本前有钱谦益之序。何焯后来又对钱氏注本做了眉批。朱东岩《东岩草堂评订唐诗鼓吹》,每个诗人都添加小传 (原来有传的做了增补,无传的加传),并标以初、盛、中、晚,个别诗人不详时期的未标。几乎每首都有评,其解评偏重作诗之法,俨然将《唐诗鼓吹》作为一本教科书。当代韩成武先生又对何氏眉批本加以整理、点校,成《唐诗鼓吹评注》。
以上即是《鼓吹》注本的大致情况。除此而外,明清两朝《鼓吹》刊本尚多。可以看出,对此唐诗选集虽然批评的声音不少29,但对它持赞同、肯定意见的人也是很多的。如钱谦益之孙钱朝鼐等即是以《鼓吹》为学习写诗的教材30。
2.选诗特色
《鼓吹》不选李杜韩
《鼓吹》一书共选96位诗人,其中盛唐6位,中唐32位,晚唐51位,其它(五代、宋)7位。偏重于中晚唐,尤其是晚唐。《鼓吹》选盛唐王维8首,张说2首,高适1首,岑参1首,李颀2首,崔颢l首;中唐32人,100首诗;晚唐51人,433首。
《鼓吹》不选李杜、元白、韩柳以及重视中晚唐,成了历来批评者攻击其无识,认为其去取不当并因之否定其为元好问所选的口实。
韩成武先生认为,不选杜甫诗歌,是元好问出于对杜诗的极为尊崇的心理反映。在元氏看来,杜甫诗歌篇篇皆为金精美玉,是不可另选的31。尊崇杜甫而不将杜甫与其它唐代诗人并列可以算做《鼓吹》一个不选杜诗的原因。另外,还可以有其它的解释。李白、杜甫、韩愈等唐代大家,在唐人选唐诗的各个集子中,也大多未曾入选32,元好问对此当有所继承。李杜韩等大家,或在其生前,或在其去世不久,就有自己的集子行世,故选集多不再选。据说元好问尚有《杜诗鼓吹》一书33,如真是这样,则《鼓吹》不选杜诗就有更合理的解释了。那么,元好问不选杜诗,则是他尊杜的一个有力证明了。
《鼓吹》只选七言律诗。何焯对此有独到的认识,他在批语中引用王止仲的话道:“元人为诗,独尚七言近体。盖元裕之衮之常裒萃唐人此体,为鼓吹十卷,以教后学。”何氏认为,元人作诗,特别喜好七言近体,大概就是因为元好问曾经选编七言近体为《唐诗鼓吹》十卷,用来教授后人作诗的原故。而元好问自己的诗歌创作,对近体也用力甚勤,他特别偏爱七律,金亡前后所作的大量“丧乱诗”是他诗歌中成就最高的一部分,其中绝大多数都用七律写成。
《鼓吹》重视中晚唐诗。如上文统计,《鼓吹》选诗共涉及到96人,选诗共580余首,其中,中晚唐诗人为83位,所选诗数量为533首,人数与篇数都占绝对多数。《鼓吹》选唐诗因仅选七律,而唐代律诗又是中晚唐时期特别发达,所以中晚唐七律占大部分是与当时诗人创作实际情况相吻合的。盛唐大量创作七律的只有杜甫,也不过150余首,不选杜的原因前文已作剖析。
《鼓吹》选诗,重视思想内容,特别是重视抒写感怀离乱之思的诗歌。韩成武先生认为,元好问侧重选中晚唐伤时感怀之作,是用以寄托自己故国丧乱之思。《鼓吹》是元好问晚年所选,当时金朝已经灭亡,而大元王朝还在继续着一统天下的战争,到处战乱,满目疮痍,时时刻刻触动着诗人的心灵,故而在选取诗歌时更偏重于描写战乱、感时伤怀的作品。这也使得这部唐诗选集在特色上有别于同时乃至以前和后来的所有唐诗选集。而这正好体现了选诗者的诗歌理论、创作主张。
3.《唐诗鼓吹》的杜诗学思想
元好问的诗学思想,除了集中反映在他的《论诗绝句》三十首、为人所作序跋、《杜诗学引》、《锦机》等诗文中外,同样,也体现在他的《中州集》、《唐诗鼓吹》等选集中,其中也包括他的杜诗学思想。这里仅就其《鼓吹》所反映出的杜诗学思想做一探讨。
首先,元好问主张“风雅”。如“大雅久不作,闻韶信忘肉”、“诗亡又已久,雅道不复陈”34等。而杜诗在元好问看来正是对诗经“风雅”的继承。在《鼓吹》中,元好问首选柳宗元,是因为他认为柳宗元诗歌符合“风雅”的特点。元好问在《东坡诗雅引》中云: “柳子厚最为近风雅。”35《中州集》卷四:“柳州怨之愈深,其辞愈缓,得古诗之正。”36那么,首选柳宗元诗,就具有树立标准之意。
其次,重慷慨雄浑、沉郁顿挫,斥轻艳绮靡的诗风。对于杜甫诗歌所确立的沉郁顿挫、慷慨雄壮之风格,元氏大加推崇,而对晚唐绮艳柔靡之风则斥而远之。《鼓吹》选诗虽然中晚唐居多,但所选诗歌内容多为感时伤怀,慷慨淋漓之作。温庭筠、李商隐,被称为“温李”,诗歌创作多艳丽之什,元氏选二人诗歌时经过了精心的取舍删择,“艳歌”一首未取,入选诗以咏史、感怀之作为主。李商隐诗入选了34首,在整部《鼓吹》中名列第三,是因为元好问看重他能学杜变杜的特点,重视他是继杜甫后又一律诗大家的地位。
总之,《鼓吹》一书,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元好问尊崇杜诗,推广杜甫诗学的思想。鼓吹者,钲鼓箫笳之乐也,多行于北方,即北方之音也;鼓吹者,亦宣扬鼓动之意也。《中州集》原名为《翰苑英华中州鼓吹》,元好问将中州集定名为《中州鼓吹》当有宣扬北方金代之诗的用意,但从书名,便可知其深意;《唐诗鼓吹》之名亦当为元好问自定,37其中亦不乏此种深意。据载,元好问尚著有《杜诗鼓吹》,如果真有《杜诗鼓吹》一书,则更可见元好问对杜诗之不遗余力的“鼓吹”了。
4.《唐诗鼓吹》的影响
《鼓吹》一经问世,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反映了金朝中后期诗风的转换。金朝是女真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文化比较落后。建国之初,采取“借才异代”的文化政策,但由宋入金的文人因为多方面的原因,诗文创作并未取得较大成绩。国朝文派,以苏黄为旨归。南渡后,赵秉文、王若虚等人大力提倡唐代诗风,文风、诗风为之一转。元好问此选,即是对此风气的推波助澜,亦是当时实情的反映,更开启了元人宗唐的风尚。
第二,《鼓吹》在选取诗歌时对感时伤怀作品的情有独钟,以及对慷慨悲歌、沉郁顿挫诗风的重视,使此部唐诗选集每到换代之际往往备受文人重视。钱谦益之孙在明末清初整理、重注《鼓吹》,以其作为诗友切磋诗艺、传授子弟的教科书就是明证。
第三,《唐诗鼓吹》在后世不仅出现了许多评注、解评本,而且出现了许多续书、仿书。明瞿佑《归田诗话》言:“元遗山编《唐鼓吹》,专取七言律诗,郝天挺为之注,世皆传诵。少日效其制,取宋、金、元三朝名人所作,得一千二百首,引为二十卷,号《鼓吹续音》”38。其它如明朝庆王朱栴《增广唐诗鼓吹续编》、萧彦《初唐鼓吹》、王化醇《百花鼓吹》等,都在效法《唐诗鼓吹》。
第四、由于元好问在金末元初文坛的地位和影响,由于他在各方面全面鼓吹唐诗,特别是杜诗,使得本不重视杜甫的金代,在王朝覆败之际,涌现出好几位学习杜甫的诗人。有元一代,杜诗学的发展虽然难敌两宋的繁盛,但也还是沿着其应有的发展轨道前进并展示出新的特点——即重视杜诗诗艺。《鼓吹》是第一部专选唐诗七律的选集,而元代则出现了杜诗学史上第一部专选杜诗七律的《杜律虞注》和第一部专选杜诗五律的《杜诗赵注》,其受元好问《鼓吹》的启发是不言而喻的。
注释:
①② 20 脱脱等撰.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741页。
③ 程千帆.对于金代作家元好问的一、二理解〔J〕.文史哲,1957(6):7。
④⑦⑩14 15 16 元好问撰.遗山先生文集 (卷十一)〔M〕. (四部丛刊初编221-222),上海:上海书店1989。
⑤ 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石洲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1783页。
⑥⑨34 元好问著,施国祁注.元遗山诗笺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527、582页。
⑧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5055页。
11 黄庭坚.豫章先生文集:卷十九〔M〕.四部丛刊初编缩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04页。
12 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M〕.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78页。
13 姚奠中,李正民.元好问全集 (卷三十六)〔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50页。
17 18 杨伯峻撰.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57、258页。
19 元好问《陶然集诗序》: “‘毫发无遗恨’、‘老去渐于诗律细’、‘佳句法如何’、‘新诗改罢自长吟’、‘语不惊人死不休’,杜少陵语也;……今就子美而下论之,后世果以诗为专门之学,求追配古人,欲不死生于诗,其可已乎?虽然,方外之学有“为道日损”之说,又有“学至于无学”之说。诗家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后,乐天香山以后,东坡海南以后,皆不烦绳削而自合,非技进于道者能之乎?诗家所以异于方外者,渠辈谈道,不在文字,不离文字。诗家圣处,不离文字,不在文字。”
21 “杰句雄篇萃若林,细看一一尽精深。才高不似人间语,吟苦定劳天外心。白璧连城无少站,朱弦三叹有遗音,不经诗老遗山手,谁识披沙拣得金”。(房琪编,《河汾诸老诗集》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22 28 高儒.百川书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2页。
23 明杨慎《升庵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 1983年。第673页。
24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卷一八八)《<唐诗鼓吹>提要》 〔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06、P156、P106页。
25 26 历史上有两个郝天挺。一位是金人郝天挺(1161-1217)字晋卿,元好问之师。一位是元人郝天挺 (1247-1313)字继先,元好问之徒。
26 四序、跋皆出自明经厂刻元刊本《唐诗鼓吹》。
27 张立荣.《唐诗鼓吹》选者辨析〔J〕.晋阳学刊.2005(6)。
29 周容《春酒堂诗话》言“家旧有《唐诗鼓吹》一册,俱七言近体,意主绮靡,而魔诗俗调,十居其七,不知定之谁氏。首幅有‘元资善大夫郝天挺注’一行,余笑谓固应是此时之书,……见牧斋先生《有学集》中有《鼓吹》一序,证为元遗山选次,以比之王荆公《百家选》。夫荆公《百家选》必可观,惜未见也。若《鼓吹》之狠鄙,何以当先生意如是,恐不足以服严氏、高氏之心”。(清周容《春酒堂诗话》,郭绍虞编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沈德潜:“《鼓吹》一书,嫁名元遗山者,尤为下劣。学者以此等为始荃,泊没灵台,后难洗涤” (沈德潜《说诗晬语》,王夫之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30 “里中陆子勅先、王子子澈、子吁,偕余从孙次鼐,服习《鼓吹》……” (钱谦益《<唐诗鼓吹评注>序》,韩成武.唐诗鼓吹评注〔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
31 参见韩成武《唐诗鼓吹评注》前言。(韩成武.唐诗鼓吹评注〔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
32 现存较为完整的九种“唐人选唐诗”中,仅韦庄的《又玄集》选杜诗七首,其它如《搜玉小集》、令狐楚《御览诗》、姚合《极玄集》、芮挺章《国秀集》、殷璠《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元结《箧中集》、韦縠《才调集》等皆未选杜诗,且多未选李白等人。
33 王基.元好问在河南文论著作简论〔J〕.学术月刊.1994(6)96。
35 元好问.中州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37 元好问好友曹之谦有《读唐诗鼓吹》一诗。
38 瞿佑《归田诗话》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2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