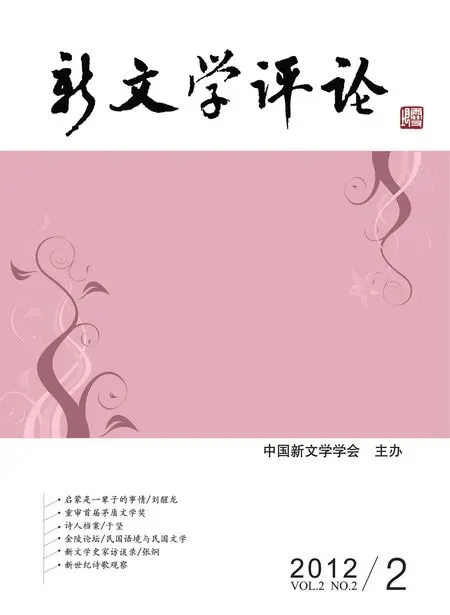新时期之初长篇小说中的“神鬼”叙事
——重读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
2012-12-18◆肖敏
◆ 肖 敏
新时期之初长篇小说中的“神鬼”叙事
——重读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
◆ 肖 敏
众所周知,长篇小说的创作实绩历来是衡量一个时代的文化生产质量高下的重要尺度。新中国成立后,长篇小说的写作和出版被纳入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史诗写作范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而十七年文学中,长篇小说确实在出版数量、在传播范围、在塑造一代受众的精神面貌上,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然而,新时期之初的长篇小说创作实际上并不发达。“应该说,在新时期之初特别是80年代早期,长篇小说并不发达,其原因一是由于表达的急切和思想的需要,使作家无暇去顾及长篇小说的营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因其快捷短小而成了一种首选的文体。”①这是否隐含着一层意味,就是长篇小说因其创作的特殊性,很难完全跳脱其固有思路(哪怕这种思路是作者本人所极力反对的)?下面,我们不妨以李国文出版于1981年的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为例,来论述新时期初期长篇小说的创作和出版的复杂性。
一、历史逻辑的正义性——《冬天里的春天》的历史书写
《冬天里的春天》讲述的是一个大型军工动力工厂的负责人、老革命于而龙(二龙),在“文革”结束不久后回到自己战斗过的老区调查前妻解放前遇害一事,最后调查出当年的凶手正是自己的战友、同事王纬宇,小说在两人的对峙中结束。尽管作品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局,但在对主人公携长风、驭雷电般的英雄主义气概的描写中,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小说最终的光明结局。
正如小说的题目所显示的,尽管处于严冬,但是春天还是会到来的,而在这个过程中,先进——落后、正义——邪恶、对——错等二元对立的势力进行着殊死搏斗,具体到小说情节中,就是对阶级斗争路线的冲突的集中描写。在这个冲突中,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是须臾不能被丢弃的,始终拥有着历史话语权。这样《冬天里的春天》就以带有某种侦探小说意味(于而龙调查前妻的被害原因,调查过程始终扑朔迷离)的情节外壳,一跃为一部正剧式的长篇小说,蕴含某种历史逻辑的正义性。
如同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的多数长篇小说一样,《冬天里的春天》的整个情节线索是建立在某一条路线完胜另一条路线的历史逻辑基础上的。尽管王纬宇潜伏长达30年,且身居高位,但依然暴露,其背后的实质性原因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他的覆灭?先看以下小说中的文字:
“无论什么时候,共产党员也得靠人民,就如同鱼和水一样,水没有鱼照样流,鱼没有水,可活不成。只有那些老爷,和存心祸害党的败类,才把党变成救世主,人民得看它的脸色行事,得靠它的慈悲恩赐生活。……那样的老爷,那样的败类,早早晚晚要垮台的。”
“冷哪!尽管那不是冬天,却比冬天还冷;直到后来,他们才悟过这个道理来,把心和老百姓贴在一起,才明白真正的春天,是在人民群众中间。”
看来,王纬宇最终暴露的缘故,是因为他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他是一个隐藏了30年的国民党特务,仅这个就已经足以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他的失败不单是他个人的失败,更是无产阶级历史理性的胜利。为了表现这种历史理性的不易和伟大,作家不惜采用多重方式来进行层层铺排。
小说首先重点描述了阶级出身的重要性,这种出身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记忆,使得人物无法摆脱其固有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王纬宇起初是封建家庭的贼臣逆子,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而走上革命道路,但始终不能从情感上和行为上脱离其原有反动的阶级出身,在革命队伍里动摇迷惑,继而与自己的地主家庭的大哥勾勾搭搭,甚至成为国民党特务而长期潜伏在我党内部,成为历史的罪人。而于而龙和芦花之所以对革命坚贞不渝,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出身是苦大仇深的穷人,对革命有着天然的向往,且具有坚不可毁的革命意志。他们在道德、情感、革命情操上都无懈可击,是真正的历史的英雄。
其次,小说强调了历史理性最终必将战胜一切不和谐的势力,这个过程可能是漫长的,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必定的、不可动摇的。这也是王纬宇左右逢源、苦心经营仍不能摆脱其耻辱命运的主要原因。“作家把王纬宇形形色色的花招,作为时代的产物和整个社会的现象来表现,这一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又是颇深刻的。于是,不仅是这形象本身是复杂的,就是对这形象的创造,也是同样复杂的艺术现象。”②确实,王纬宇的覆亡命运隐含着更为复杂的社会政治内涵。
而实际上,《冬天里的春天》中的历史书写呈现了相当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特点,甚至有的时候是比较狭隘的政党斗争。这也是这部小说尽管获得了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却在后来被人逐步遗忘的缘故。
二、神鬼书写的初步确立
《冬天里的春天》之所以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是有其深刻原因的。这项以著名作家茅盾的名字命名的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一直以来(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较青睐以某种带有政治色彩来筛选作品的标准。“回顾历届茅盾文学奖,虽然我们无法准确地判断他们在具体执行标准中更强调哪一种规则,但从评委成员和评奖结果来看,政治的质量认证明显大于艺术的审美认证。”③而大多数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对所谓史诗、宏大叙事等比较关心,他们更希望在候选长篇小说中看到关乎民族、作家、人民等的描述,这也是被学术界所诟病的茅奖的“史诗情结”。“认为一部长篇小说‘尚未达到史诗的标准’,那也就等于说它的价值是可疑的。写作史诗的目的是要‘揭示历史的本质’,但‘历史的本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来体现。‘正确的历史观’,当然是‘重中之重’。”④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的茅盾文学奖的最终获奖作品中,这种史诗情结毋宁说也是一种“神话情结”。而实际上,《冬天里的春天》只是典型地体现了新时期初期的长篇小说的一种写作范式而已,即神鬼书写的范式。
小说是这样开头的:
于而龙两眼一阵发黑,不相信这一切全是真的,可眼前的现实,使他想起江海所说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是一个无论对于生者,还是死者,都是严峻考验的年头啊……他想起一个梦,一个芦花的梦,一个他从来也不相信的梦。哦,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漆黑的世界,从来也不曾这样黑过。
带有混沌初开之时的神秘主义氛围,这个开头其实预示着主人公与其背后的黑暗势力进行搏斗的不易,也为展现主人公的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及其英雄主义壮举作了铺垫。接下来,作家穿越于当下现实背景和历史情境中,表现了冬天必然蕴含着春天的主题。
恩斯特·卡西尔曾经指出,神话不是按照逻辑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事物,而是有其独特的神话思维方式,其独特性表现在诸如直觉性、自发性、象征性、情感性等方面。卡西尔认为,现代政治体制中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神话特征,“神话一直被描述为无意识的活动和自由想象的产物,但在这里我们发现,神话是按照计划来编造的。它为20世纪这一我们自己伟大的技巧时代所保存下来,并发展为一种新的神话技巧”,“在当代政治思想的发展中,也许最重要、最令人惊恐的特征就是新的权力——神话思想权力的出现。在现今一些政治制度中,神话思想显然比理性思想都具有优势。在一场短暂而猛烈的激战之后,神话思想似乎赢得了一次确定无疑的胜利。”⑤卡西尔提出,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政治神话俨然成为一种具有广泛性的运动。“文革”的爆发和具体进程有明显的神性特征,譬如对领袖的非理性的疯癫崇拜、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政治想象等等。而实际上,“文革”结束后,这种神性的政治表征并没有立刻消失,尽管新时期之初的社会文化生态不再沉湎于对某一个具体领袖的个人崇拜中,但是这个时代的人总有一种开天辟地、日新月异的新奇感,总认为自己已经和过去迅速决裂、去到一个更为美好的明天。实际上,这就带有明显的神话主义文化色彩了。“1978年代的文学在20世纪下半叶首次以英雄的姿态通过凯旋门,这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中则是少见的景观。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文学所表达的情感和愿望不仅仅只属于作家们,同时它也来自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和守护。”⑥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和守护,以文学的方式缔造更为美好的明天,是这段时期文学的首要任务,这种引导和守护,有时免不了以具有浪漫激情的神话方式加以展现。
具体到新时期初期的长篇小说创作,这种神话思维可谓比比皆是,如张笑天的《严峻的历程》、谌容的《光明与黑暗》等等。就那个时代的很多作家来说,他们在作品中往往会体现出一种喜不自胜的情怀,一种对未来的展望之情,同时也对埋葬旧时代、迎接新时代进行了浪漫主义式的瑰丽想象。已有学者明确指出,《冬天里的春天》以“国共两党斗争的延续”来解读“文革”,是大大违背历史真实的。不过作者之所以这么设置情节,除了与作者所处的特殊时间(中央对“文革”刚刚有定论,还有很多说法流传)有关,也与作者的神话式写作方式有关。人们似乎只有用那种夸饰的神话写作方式,才有可能与过去彻底决裂,才能真正跨入到新的时代中。
就具体写作而言,《冬天里的春天》在人物塑造方面进行了神话式的充分想象。作者在小说中设置了两组不同类型的人物,分属神和鬼的行列,前者有代表历史理性的正面人物于而龙、芦花,后者有坏人王纬宇和王经宇,芦花牺牲了30年,但在冥冥中一直指引着丈夫于而龙战斗和报仇。小说所展示的历史逻辑是这样的:在长达30年的对峙中,主人公于而龙与其对手王纬宇在多数情况下处于一种表面相安无事的状态,后者以其隐忍的城府进行着潜伏的工作,这种阴暗的生存状态就已经为其代表的阶级打上了历史的价值论色彩。而与此相对的是,正面主人公可以超越历史过程的细节,获得某种神奇的力量。于而龙几十年来出生入死,被敌人偷窥,却屡次化险为夷,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英雄豪杰,而是成为政治路线的神话斗争的符号。王纬宇年轻的时候确有向往光明的冲动,他反抗封建包办婚姻、投奔革命队伍就是一个证明,但终究他还是一个来自陈腐、黑暗世界的鬼魅,因此潜伏达30年,沦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忠实代言人,奸诈阴险到令人发指的程度。这样鲜明的人物对照描写,更深层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两个人物不再具有他们自身的性格特征,而更多是阶级身份的代言人。这样鲜明的人物谱系的对照,其实带有相当明显的神性书写的味道,在古代神话中也并不鲜见。
三、《冬天里的春天》之神鬼叙事的手段呈现
所谓的神性书写,还需要通过一系列艺术手段加以呈现,而细节描写和人物刻画不失为重要的手段。而我们再向前追溯上去,神性书写在“文革”文学中更是屡见不鲜的。如“文革”中发行量相当大的长篇小说《东风浩荡》是这样描写主人公刘志刚抢救集体物资时的雄姿:
“刘志刚,这个在党的培育下长大,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在阶级敌人面前,在一切难关险道面前,从来眼不眨,心不跳,他敢于迎着风浪进,踩着漩涡行,顶着逆流上,向着火海冲!毛泽东思想给他铸成了一颗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红心;毛泽东思想给他装上了一副无产阶级的钢筋铁骨!
狂风暴雨,你算什么!你纵然能把大地上的一切摧毁,你也决然挡不住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前进的脚步……
刘志刚劈开风墙雨幕,飞奔前进!英雄胸中有朝阳,千难万险无阻挡!你看他,身体前倾,虎眼圆睁,象一支能够穿透一切的利箭,直向那狂风雨雾中射去!”
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可以成长为这样的不可思议的英雄,其实质原因是因为他身后有伟大领袖的精神支援,因此可以抗拒自然界的规律获得神奇的力量。这样一种神性书写因其过于夸张的叙述语气和粗鄙的细节而很快被时代抛弃,而《冬天里的春天》则要高明很多。请看王纬宇如何嫉妒于而龙所拥有的巨大感召力的:
“难道他王纬宇不也有一种嫉恨的感情么?每逢二四六的傍晚,只要电讯大楼敲过六点,那个娉娉婷婷的姑娘,准会出现在部大院,朝于而龙家的楼栋走去。
准得不能再准,六点整。是什么因素使得那个女孩子把自己的命运,依附在一条覆灭之舟上?是一种他觉得恐怖的殉教徒精神。不但那个舞蹈演员,连那个会三国语言的翻译,连那些骑兵,那些和工人一起长大的年青人,他都恨得要命。很清楚,只要于而龙张开怀抱,他们会情不自禁地扑上去。而他,革委会主任,倒有点类似英女王派往殖民地的总督一样,工厂里的人,绝大多数对他是侧目而视的。是的,于而龙是块磁铁,当然,他想砸碎它,整整砸了四十年,结果又如何呢?”
与“文革”主流小说中生硬的、夸张的神性书写比较起来,《冬天里的春天》的神性书写则要自然许多,作品主要运用生活细节的描绘、心理活动的细致记忆、场景的对照描写,来突出主人公的正面的形象。作家的意图并非是想把主人公塑造为一个单纯的神性人物,而是要通过这个正面一号主人公透视出某种意识形态内涵。于而龙之所以拥有那种非凡的领袖般的人格魅力,其实质原因在于他是政治正义的化身,是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者,即使他现在被打倒了,他也仍肩负着历史话语权,这样他就从一个普通的干部上升为历史理性的代言人了。而这样一个逻辑恰恰是“文革”主流小说所大力采纳的,在“文革”小说中,我们所习见的情节模式是书记(厂书记或大队书记)的革命意志坚不可摧,坏人不论隐藏得多么深,还是最终暴露,原因在于,书记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人,他是无产阶级历史理性的化身,而这个历史理性是必然要取得胜利的。吊诡的是,一部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竟然也有这样的思维轨迹,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时期之初的长篇小说创作确实带有相当多的过渡性特征。
于而龙的高大、正面形象与王纬宇的卑琐、罪恶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俨然是神-鬼两个世界的代言人。甚至为了表现后者的罪恶,作家不惜用一些离奇的情节加以展现。如小说后半段写王纬宇遇到一个美丽的姑娘叶珊,被罪恶的情欲驱动而给她下了迷药,尽管他猜测这个姑娘很可能是他的亲生女儿,但仍然把她强奸了:
“雾越来越浓密了,当那艘小舢板贴近三王庄的堤岸,划船的妇女猫着腰,领着她的狗悄没声摸上岸时;在县城北岗谜园水榭里,王纬宇把那个颤抖的,哀告着‘别!别!’满眼泪光的女孩子,紧紧压住,心里还在作最后的挣扎:‘万一,她真是我的亲生的女儿呢?’
‘管它咧!’那个畜牲自己回答自己:‘需要就是一切!’”
作家之所以设置这样的情节,可能是为了更细致、具体地表现王纬宇的来自鬼魅世界的恐怖和罪恶。为了把坏人尽量写坏,不惜营造极端的违背人伦的罪行,且这种罪行的描写并没有经过足够的铺垫,仅仅用“需要就是一切”来解释,给人一种作家是故意为之的感觉,这对于创作者来说,显然是不够深刻的。
此外,《冬天里的春天》的艺术结构在1980年代前期的长篇小说中是特殊的,作品主要描写1937年到1947年的游击队战斗和十年动乱中的场景,同时以人物的心理活动来展开复杂的故事情节,时空颠倒,历史和现实穿插。作品使用了当时较少使用的意识流、蒙太奇、跳跃、场面切换的手法,这些新奇的手法较好地提升了小说的阅读效果,另一方面,也强化了作品的神——鬼的人物谱系的书写。譬如,小说是这样描写于而龙如何挣扎在死亡线上的:
“她好像害怕一旦停止喊叫,于而龙的魂灵就会飞走似的,把那冰凉的脸,揽在胸前,俯身朝他喊:‘二龙,二龙……睁开眼,看看我,看看我吧……’滚热的泪珠,一颗一颗跌落在他的脸颊上。
突然间,他眼前的场景变换了,不是石湖。他从昏迷的状态里惊醒了,他发现他躺在医院的手术台上,身边站着眼睛哭肿的谢若萍,还有愤怒的于莲,和那个咬着嘴唇的小狄。”
在这里,作家将两个不同的场面组合在一起,穿插以主人公的意识流动,文字紧凑,节奏急迫,并留有悬念,最终达到了其神鬼叙事的目的。
结 语

注释:
①吴义勤:《长篇小说与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②周良沛:《写在诗弦上的小说——再版代序》,《冬天里的春天》,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③洪治纲:《无边的质疑——关于历届“茅盾文学奖的二十二个反问和一个设想》,《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
④王彬彬:《茅盾奖:史诗情结的阴魂不散》,《钟山》2001年第4期。
⑤[德]恩斯特·卡西尔,范进、杨君游译:《国家的神话》,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42页。
⑥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⑦李国文:《自序》,《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李国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学研究中心”]